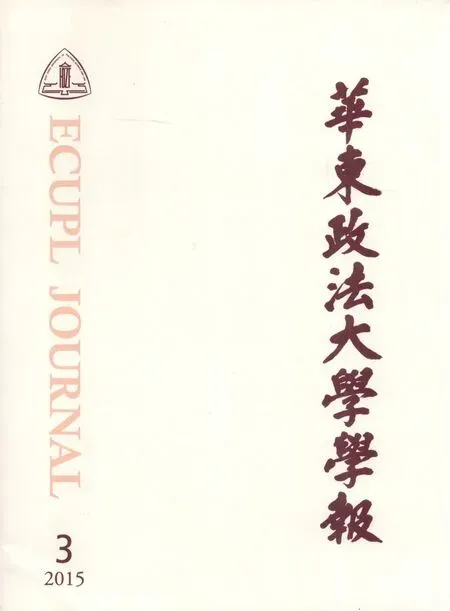“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多重敘事與邏輯
——基于知識社會學的考察
徐 斌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多重敘事與邏輯
——基于知識社會學的考察
徐 斌*徐斌,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

目 次一、問題的提出二、鍍金時代中的普通法法院三、民權運動中的高級法法院四、里根革命后的政治法院五、作為法治文化符號的馬伯里案六、結語
作為經典法學文本,“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在美國政治譜系中呈現出多重面相。以知識社會學方式考察,該案在鍍金時代、民權運動與里根革命的不同政治環境與意識形態中,因為不同的目的而被闡釋出迥異的敘事與邏輯。與此相關,馬伯里案背后所代表的司法哲學也經歷了普通法法院、高級法法院到政治法院的角色變遷。上述歷史將馬伯里案鍛造成了美國法治文化的符號。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司法權 高級法 司法自制
“尋找世系不是要創建基礎,恰恰相反,它擾亂了原本被視為固定的東西;
讓原來一體的東西破碎;
暴露了原本被想象成一體的東西的多樣性。”
——福柯*[法]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學》,轉引自[美]羅伯茲:《審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傳統》,王寧等譯,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版,第1頁。
一、問題的提出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以下簡稱馬伯里案)在國內最早的譯介是1981年潘華仿教授的《略論美國最高法院的憲法解釋權》。該文介紹了美國最高法院憲法解釋權的起源,即馬伯里案。*參見潘華仿:《略論美國最高法院的憲法解釋權》,載中國法律史學會主編:《法律史論叢》(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如潘華仿所總結:“美國最高法院享有解釋憲法、審查法律的權力,就可以根據階級斗爭的不同形勢,對憲法做出‘靈活’的解釋,形成各種具有憲法規范性質的判例,以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潘華仿:《略論美國最高法院的憲法解釋權》,載中國法律史學會主編:《法律史論叢》(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在經歷政治的動蕩之后,80年代法律學人的問題意識與其說是憲法如何適應階級斗爭的新形勢,不如說是中國憲法如何得以實施。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馬伯里案作為“憲法司法化”方案的經典文本而得以在中國法學界確立地位。但是,這也導致了中國學界對于馬伯里案采納了單一化的理解。在過往三十年的法學研究中,馬伯里案及其所代表的司法哲學更多的是美國上世紀60年代的“沃倫法院”版本:法院通過解釋作為高級法的憲法來規范政治秩序,從而追求社會正義的價值。*參見徐炳:《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起源──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述評》,載《外國法譯評》1995年第1期;朱蘇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關于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故事》,載《比較法研究》1998年第1期;黃松有:《憲法司法化及其意義——從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個〈批復〉談起》,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8月13日第B1版;龔祥瑞:《比較憲法與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09-122頁。近期學界試圖努力超越馬伯里案的現有理解,發掘除司法審查之外的憲政意義。但是作為知識社會學的文本考察對象,本文只局限于司法審查知識文本背后的權力運作機制。參見劉晗:《憲制整體結構與行政權的司法審查:“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再解讀》,載《中外法學》2014年第3期。但是,在美國憲政歷史中,馬伯里案所代表的司法哲學呈現出多重面相,“沃倫法院”版本也只是眾多歷史重構中的一個時代片段。
專攻聯邦最高法院問題的美國政治學家麥克洛斯基,在《美國最高法院》成書時,曾說道:盡管歷史總是被現代所闡釋,但歷史與現代仍存在互動。*McCloskey, Levinson, Sanford, 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p.229.《美國最高法院》成書于20世紀60年代,是現今美國主流憲法學教材《憲法決策的過程:案例與材料》一書的前身。中譯本參見[美]羅伯特·麥克洛斯基:《美國最高法院》,桑福德·列文森增訂,任東來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麥克洛斯基強調的是美國憲法學中的知識/權力關系。事實上,麥克洛斯基本人的問題意識乃是希望通過重述聯邦最高法院的歷史,為20年代的沃倫法院劃定政治邊界。在美國憲政史的敘事與現代的邏輯互動中,馬伯里案作為美國乃至世界憲政的法學經典文本成為各個時代所必需處理的對象。以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對待法學經典文本時,我們不僅要懂得文本解讀、語境分析、意義闡釋、風格賞析,*許章潤:《經典:文本及其解讀——關于閱讀法學經典的五重進境》,載《法律文化研究》2006年第1期。更應當熟知不同時代對于經典文本的譜系定位,因為這種定位時刻改變著經典文本的解讀與意義。從譜系定位來看,從麥克洛斯基在20世紀50年代的“高級法”解讀,到列文森于2000年宣告無需向美國本土法科學生講解該案,*Sanford Levinson, “Why I Do Not Teaching MARBURY (Except to Eastern Europeans) and Why You Shouldn’t Either”, 38 Wake Forest Law Review 553 (2003).文本意義的變遷能夠幫助我們深入理解美國憲政知識背后的學術與政治的互動。
學術與政治的互動或知識/權力關系不只具有知識社會學上的意義,還有政治意義。對于中國而言,知識/權力關系的揭示對中國的現實政治與學術自覺有著重要意義。馬伯里案的法學經典文本地位已經隨著美國政治的全球化而成為各個民族國家的憲政學術基石。無論是“司法獨立”,還是“憲法是法”,這兩個來自馬伯里案的命題,*“馬歇爾聰明的地方就在于一方面反復強調法律與憲法之間的相互抵觸,從而利用政治哲學和成文憲法來強調憲法高于法律的權威性;但另一方面,在觸及決定司法權性質本身的憲法的關鍵時刻,他馬上引用普通法法理學中的司法權來強調法院在憲法和法律之間進行選擇的權力。一方面是強調憲法高于法律的成文憲法至上這個政治哲學,另一方面強調憲法與法律作為兩種不同的規則或者法律淵源而供法院自由選擇的司法哲學,馬歇爾在這兩種學說之間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從而把決定司法權之性質的憲法至上學說轉變成普通法中法院自由選擇法律淵源的學說。這種轉變的關鍵就在于馬歇爾將‘憲法’偷偷地轉換為‘規則’,從而把憲政學說變成了法理學說。正是經過這樣一種隱秘的轉化,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無效問題就變成了由司法機關來決定哪些法律無效的司法審查問題,從而將法院的普通司法職能變成了對立法的司法審查”。參見強世功:《司法審查的迷霧——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政治哲學意涵》,載《環球法律評論》2004年第4期;強世功:《憲法司法化的悖論——兼論法學家在推動憲政中的困境》,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早已成為“普世化”的司法審查的法理基礎。可以說,馬伯里案已經如“特洛伊木馬”一般潛入到中國政治改革的話語體系中,發揮著政治改革的行動力量。由此,我們不得不追問的是,處在這種世界憲政主義的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學術,如何能夠客觀看待美國的憲政知識,以主人的心態來面對西方知識?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理解美國憲政知識背后的學術與政治互動關系,從而在對待西方憲政知識的同時保持一種“解毒”的狀態。
本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考察馬伯里案在美國政治譜系中呈現出多重面相。在美國時代變遷維度中,不同的社會環境與政治語境對馬伯里案的敘事與文本邏輯有著不同理解。具體而言,本文截取了美國的鍍金時代、民權運動與里根革命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段,分析發現不同的政治環境與意識形態誕生了不同的馬伯里案敘事,也展現出不同的文本邏輯解讀。與此相關,馬伯里案背后所代表的司法哲學也經歷了普通法法院、高級法法院到政治法院的角色變遷。盡管不同時代議題下的含義迥異,但是歷史含義的不斷重塑也使得馬伯里案擁有了民族共同體認同的文化功能,成為了美國法治文化的符號。
在正式進入對馬伯里案在美國政治譜系中的分析前,本文先簡單回顧一下馬伯里案的邏輯與司法審查的早期憲政實踐。1803年的馬伯里案中有關違憲審查的討論,針對的是聯邦法院是否有權否決違反憲法的國會法案。馬歇爾在該案中處理了三個問題:第一,申訴人馬伯里是否有權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狀?第二,如果他有這個權利而且這一權利受到侵犯時,政府是否應該為他提供補救的辦法?第三,如果政府應該為申訴人提供補救的辦法,是否該由最高法院來下達強制執行令,由麥迪遜將委任狀派發給馬伯里?在處理第三個問題時,馬歇爾提出了司法審查的三個邏輯推理,分別為成文憲法、有限政府與法官宣誓。
從歷史的維度來看,盡管該篇判決充滿了馬歇爾的政治智慧,但在此之后,針對國會法案的司法審查在近半個世紀中并沒有得到運作。可以說,美國憲政自1800年杰斐遜選舉之后進入了以“議會-政黨”為中心的“弗吉尼亞王朝”時期。*參見[美]奧魯夫:《杰斐遜的帝國:美國國家的語言》,余華川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1-123頁。直到引起美國內戰爆發的1857年斯格特案,坦尼法官才第二次運用司法審查否決了國會的法案——《密蘇里妥協》。*Dred Scott v. Sandford, 60 U.S. 393(1857).這半個世紀中,聯邦最高法院并沒有沉睡,而是積極地行使聯邦法院對州法院的司法審查權,依托貿易條款*《美國憲法》第1條第8款第3項:“管制同外國的、各州之間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業”。和契約條款,*《美國憲法》第1條第10款第1項: “任何一州都不得:締結任何條約,參加任何同盟或邦盟;不得頒發緝拿敵船許可證和報復性拘捕證;鑄造貨幣;發行紙幣;使用金銀幣以外的任何物品作為償還債務的貨幣;通過任何公民權利剝奪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或損害契約義務的法律;或授予任何貴族爵位。”不斷否決違反聯邦憲法的州法案與州法院判決。可以說,這段時期的司法審查體現了法院積極參與聯邦主義建設的憲政職能。
二、鍍金時代中的普通法法院
19世紀末的美國正值內戰結束后的經濟革命時期。新經濟立刻在美國取得了支配地位,緊接而來的就是勞資雙方的激烈斗爭。社會形成了經濟領域的自由放任主義和文化領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由此,美國進入了鍍金時代,美國的政治問題隨之轉變為了資本主義問題。漢密爾頓的“工商立國”最終戰勝了杰斐遜的“農業立國”。*關于美國早期“工商立國”與“農業立國”的現代化道路之爭的研究,請參見張少華:《漢密爾頓“工商立國”與杰斐遜“農業立國”之爭》,載《歷史研究》1994年第6期。擺在重建之后的大法官們面前的事實是一個全新的司法環境與問題——聯邦政府是否有權干預經濟發展。當時,在聯邦法院的一系列判決當中,都是將契約自由奉為核心價值,反對州或聯邦政府管制經濟活動的立法,包括保護女工、建立最長工作時間、安全工作條件的立法。聯邦最高法院的新精神首先由法定貨幣案表露出來。內戰期間,由于聯邦的財政困境,中央發行了4.5億“綠背紙幣”,作為支付所有公私債務的法定貨幣。由此,該法案給國會帶來了如同“美國銀行案”一樣的老問題:國會是否有權發行這樣的貨幣,以抵消債務?1863年,該案件呈遞到了聯邦最高法院面前。大法官們仍然運用了馬歇爾的司法技術——管轄權——而回避了此案的審判。一直到1869年,債權人將該法案提交到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贏得了法定貨幣法案違憲的結論。*See McCloskey, Robert G., Levinson, Sanford, 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67-77.
法定貨幣法案的判決預示了聯邦法院審查國會立法的“幽靈”正在浮現。隨著馬歇爾法院與坦尼法院對州法的審查實踐,法院的司法審查似乎成為了一種理所當然的司法審判原則,超越了質疑。*See John W. Burgess, “The Ideal of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10(3)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404 (1895).內戰標志著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歷史的一個偉大時期的結束和新時期的開端。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環境給當時的美國憲政結構提出了變革需求。在此環境中,司法審查的界限和法院的定位如何得到解答呢?馬伯里案擁有了新的時代意義。最早反思馬伯里案的論證、建立起“普通法法院”司法哲學的,當屬1893年塞爾發表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See James B. Thayer, “The Origin and Scope of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Law”, 7(3) Harvard Law Review 129 (1893);中譯文參見詹姆斯·賽爾:《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張千帆譯,載《環球法律評論》2005年第2期。本文對于賽爾文章的引用參考了張千帆教授的譯文。
在塞爾看來,有關司法權性質的討論才是馬伯里案的真正核心。從語境論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鍍金時代的最高法院逐步涉入經濟規制的議題中,原有的“政治問題”理論是否可以類比于經濟領域?法院是否可以憑借憲法解釋來否決州的治安權法案?立法權與司法權之間的界限是什么?這些現實而緊迫的憲政問題背后,其實追問的就是共和國憲政體系下的司法權的性質到底是什么。司法權的討論并非是為了厘清司法的性質,而是為了在新資本主義發展情形下劃清立法與司法的關系。
馬伯里案的原初理解將憲法的解釋普遍化,這在塞爾看來極為危險。“人民對立法機構建立了成文限制;這些限制控制著所有違憲的議會立法;這類立法不是法律;這項理論從根本上和成文憲法相聯系;司法職權是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如果兩條規則相沖突,有權宣布哪一條規則更高;司法機構應宣布和憲法相沖突的議會立法無效,否則就將使這部基本文件無足輕重。”*James B. Thayer, “The Origin and Scope of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Law”, 7(3) Harvard Law Review 129,139 (1893).究其關鍵,馬歇爾推理的致命之處不僅在于把憲法偷偷運送到了法律的概念范疇之中,*強世功:《司法審查的迷霧——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政治哲學意涵》,載《環球法律評論》2004年4期。還在于把制定法的解釋方法運用到了憲法身上。*See Antonin Scalia,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從而,法院的法律解釋方法具有了“普遍性”。這種普遍性是可以超越馬歇爾在判決書第二問題分析時所提出的“政治問題”規則。毫無疑問,上述邏輯的發展必然幫助鍍金時代的最高法院剝奪立法機構的憲法解釋權。
塞爾對馬伯里案最大的批評就在于這種“普遍性”解釋方法。在他看來,當馬歇爾擔心憲法的實施缺乏守護時——“將使這部基本文件無足輕重”——這份判決本身才是對憲法的最大侵犯者。在判決中,馬歇爾以一種限制司法行為的方式完成了司法職能的擴張。這不僅體現在了司法管轄權的條款分析上,也體現在了司法審查的法理上。馬歇爾的視角轉化極為迅速,對于憲法的政治哲學基礎的論述迅速變為了對法院職責的敘述。似乎,法院的職責只是在于解釋兩種文件并相互比較,就和在兩份契約或兩部立法被認為發生沖突的時候進行解釋與比較一樣,然后宣布每一種文件的真實意思,且如果它們之間相互沖突,實施作為更高義務的憲法。司法審查“順利推進,就好像憲法是律師的私人信箋一樣,而法院的憲法職權就和其任何最平常的運行一模一樣。”*James B. Thayer, “The Origin and Scope of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Law”, 7(3) Harvard Law Review 129,139 (1893).
這種解釋很容易導致忽視立法所考慮的因素。具體而言,在社會日益復雜的情況下,政府、議會面對的是宏大、復雜和不斷發生變化的迫切需求。而且,憲法的抽象性總是容許多元化的解釋,在一部分人看來是違憲的立法,在另一部分人看來卻是合憲。考慮到政府所面對的特殊治理職能,憲法并不將任何一種具體意見強加在立法機構之上,而是在此范圍內任其選擇,且任何理性的選擇都是合憲的。庫利法官舉例闡述了該原理:當一位議員反對的法案通過后,設想他為法官,盡管他仍然反對,但他仍然擁有宣布法律合憲的義務。而馬歇爾在馬伯里案中所犯的錯誤是,法院在行使司法審查權時,不僅拒絕將它們作為判決依據而發揮直接效力,而且還可能完全拒絕考慮這些因素。*See James B. Thayer, “The Origin and Scope of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Law”, 7(3) Harvard Law Review 129,140 (1893).
錯誤的緣由在于誤解了司法權的性質。相反,失職的法律學究們并不考慮這些因素,也不將它們作為立法行為的可能依據,而是以憲法和法律文本取而代之,將憲法問題變成了一個學術問題。“有根有據的疑問、文字的嚴格解釋、抽象的解釋規則對于解決個人之間的爭議是合適的,但不適用于決定立法的憲法效力。”*James B. Thayer, “The Origin and Scope of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Law”, 7(3) Harvard Law Review 129,141 (1893).司法權的認識需要一個“他者”權力。從三權分立的角度來理解司法權,純粹的司法權不應當涉及政治行為或自由裁量行為,首先在其適用的案件范圍上有所限制。司法部門永遠不得行使立法權或執法權,它總是偶然與滯后。
但是,事實上,美國憲政的變遷確實為司法機構賦予了與眾不同的權力,與司法權力相區別。從英國殖民地傳統來看,司法審查是美國的人民和政府為解決君主缺位問題提供的方案。在英國憲政傳統中,司法審查意味著殖民地法院與英國終審法院一同,審查違反英國國王簽發的章程的殖民地議會法案。這項政治經驗的基礎在于英國國王作為外部主權施加的章程限制。當美國革命割裂了美洲與英國的紐帶時,外部主權也被人民主權所替代。問題在于,作為人民自我表達的成文憲法失去了外部權力的支撐,如何得以實施呢?許多州的處理辦法是直接沿用以往的殖民地章程。但是1787年憲法并沒有認可這種司法實踐。因為,在當時的制憲會議中,殖民地議會取代英國議會從而取得無限權力的觀念成為主流,1787年憲法的框架設計也是以議會為主導。*參見徐斌:《被遺忘的憲法條文》,載《讀書》2011年第3期。
造成這種分水嶺的關鍵就在于憲法第3條的規定:“由于本憲法、合眾國法律和根據合眾國權力已締結或將締結的條約而產生的一切普通法的和衡平法的案件(all Cases, in Law and Equity)”。公民個人可以依據憲法而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在解決此類案件時,就不得不在提供救濟時處理憲法政治問題。這種嘗試使得法院需要不斷回答不同的立法難題。在法院的日常職能之中,主權性質的權力逐漸被孕育出來。
如何行使或者限定這項主權性權力?塞爾提出了他的“陪審團信任理論”。使用擁有主權性質的司法審查權,就如同普通法法官面對人民陪審團一般,堅持法律判斷與事實判斷的區別。換言之,在憲法問題上,司法與立法的關系更應當是法官與陪審團之間的關系。在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中,由于法官相信陪審團對于事實判斷的能力,因而法官只依據法律對陪審團進行引導,并不直接對事實進行判斷,從而恪守司法的職能。同理,司法審查制度的前提首先是相信人民的自治能力。“我們政府理論的假定是,人民是明智的,具備美德并有能力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Eakin v. Raub, 12 S. & R.,p. 355.當司法機構在判斷議會的立法是否符合規范時,應永遠假設這個機構具備美德、常識和適當知識。公共事務的運行必須建立在這類習慣和假設之上。如果這一點經常受到質疑,那就將削弱對法律的尊重,而這種尊重卻是對公共安全和幸福而言至關重要的。正是基于對人民自治德性的信任,法院在行使司法審查權時應當采用“明顯錯誤原則”。
所謂“明顯錯誤原則”指的是,法官在審查憲法案件時,應當如同普通法法院判決中所保持的“良知”,一旦立法的違憲性有所遲疑,就不得作出判決。出于對法律的尊重,法官應當首先認定立法是有效的,只有在法律明顯違反憲法成為社會共識的時候,才是無效的。法院并不是進行法律比較的學術部門,而是具有更為復雜的功能。這種司法自制傳統來自于馬歇爾法院的精心塑造。馬伯里案之后的許多判例已經形成了對司法權如何行使司法審查的看法。在1810年的弗蘭徹案,在1819年的美國銀行案中,馬歇爾確立了法院審查權的有限性,以聯邦主義為核心,司法審查才擁有了否決州法的正當性基礎。而1803年的馬伯里案不過是美國早期憲政史的一段插曲而已。不僅成文憲法無法通過邏輯推理得出,傳統的司法審查權也只是政府框架中最為羸弱和遙遠的機制。*See“Judicial Check on Un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9(4) Harvard Law Review 277,277-279 (1895).
法律條文與歷史淵源的考察結果重新定位了馬伯里案的憲政意義。從對司法權性質的討論中,一種“普通法法院”的司法哲學力圖重新確定鍍金時代的司法能動主義。但是,隨著正當程序條款不斷被最高法院所使用,州法否決危機逐步延伸到了聯邦國會法案。在“洛克納時期”的前夜,那個可怕的問題終于被提出來:“最高法院有權否決國會的立法嗎?”*Henry Flanders, “Has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al Power to Declare Void an Act of Congress? ”, 48(7) The American Law Register 385,387 (1900).法蘭德清楚地知曉當時的司法審查權正當性的討論不在于憲法條文是否予以支持,而在于三權分立的框架下,最高法院與議會、總統之間的權力是如何分配的。鍍金時代的最大挑戰就在于聯邦最高法院的權力逼迫一種新的憲政架構。由此,馬伯里案中的那個蘇格拉底式的提問“司法機構應宣布和憲法相沖突的議會立法無效,還是宣告憲法這部基本文件無足輕重?”,其實質乃是追問:議會與總統的意見至上,還是最高法院的意見至上?因為這項被審查的立法首先受到了議會與總統的通過。在這個意義上,塞爾的普通法法院的敘事與邏輯,恰恰是想將代表人民的議會與總統放置在“人民陪審團”的位置上,從而矯正法院的權力位置。
隨著保守主義法院在洛克納時期的興起,圍繞馬伯里案及其司法哲學的意見也逐漸多元化。激進者認為“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篡奪了司法審查權;*See L. B. Boudin, “Government by Judiciary”, 26(2)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38 (1911).保守者仍然認為憲法條文賦予了法院以司法審查權;*See J. Hampden Dougherty, The Power of the Federal Judiciary Over Legislation, Putnam's Sons, 1912.法學家們拒絕回歸馬伯里案,而是堅信此后的實踐才真正賦予了司法審查原則;*See James Parker Hall, Constitutional Law, La Salle Extension University, 1911.而歷史學家則認為之前的制憲會議期間,國父們就已經確立了司法審查原則,并且作為立法原意而成為美國的憲政慣例。*See Edward S. Corwin, “Marbury v. Madison and the Doctrine of Judicial Review”, 12(7) Michigan Law Review 538 (1914).多元化的知識系統的出現也意味著新政前的法院與議會的權力斗爭達到了頂峰。最終,羅斯福總統的“填塞法院”計劃與最高法院的“及時轉向”奠定了美國的新憲政秩序。
三、民權運動中的高級法法院
哈佛大學教授霍維茨曾在《沃倫法院對正義的追求》中寫道:最高法院發布的判決改變了美國的憲法原則,并隨之深刻影響了美國社會。沃倫法院的意義就在于掀起了一場美國的政治社會革命。二戰結束之后,以1954年布朗案為原點,聯邦最高法院正式走向民權領域,集中處理了種族、性別、性取向、婦女墮胎、隱私權、嫌疑人等眾多涉及日常倫理生活領域的案件。聯邦最高法院繼鍍金時代之后,再一次成為“一個革命性的團體,一種社會變革的強大力量。”*[美]盧卡斯·A.鮑威:《沃倫法院與美國政治》,歐樹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也正是沃倫法院的影響,至此,美國的諸多社會議題爭論都變成一場永不停息的“權利話語”,*See 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ree Press, 1993.司法與法律全面地意識形態化。
在美國政治學家看來,沃倫法院比新政法院更忙于徹底拋棄舊法律。新政法院為了扭轉鍍金時代泛濫的最高法院權力,在8年間推翻了30個先例,肯定了一個新憲法秩序。*[美]盧卡斯·A.鮑威:《沃倫法院與美國政治》,歐樹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397頁。而沃倫法院卻在7年間推翻了45個先例,創造了一個開庭期推翻7個先例的記錄。與新政法院集中在聯邦主義與政府經濟管制不同,沃倫法院多集中在民權道德領域,種族融合的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S. 483 (1954).議席分配的貝克案,*Baker v. Carr, 369 U.S. 186 (1962).墮胎權的羅伊案,*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宗教祈禱的恩格爾訴伊塔爾案,*Engel v. Vitale, 370 U.S. 421 (1962).刑事罪犯權利的米蘭達案*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1966).以及曾廢除死刑的費曼案*Furman v. Georgia, 408 U.S. 238 (1972).等改革急先鋒式的判決。而這些民權背后隱含的道德倫理問題大多屬于傳統的州“治安權”的范疇。在早期的共和憲政理論中,州擁有地方自治的原始主權,這主要涉及地方人民的道德生活秩序的維護,如健康、衛生、安全與福利。由此,沃倫法院給美國憲政帶來的挑戰是:如何在社會倫理道德領域重新塑造與界定一個如鍍金時代的能動主義的聯邦最高法院?
在新政治環境中,上世紀60年代美國學界的主流問題意識是在理論上辯護“沃倫法院”的憲政變革,從而以法院為中心推進“自由”事業。*See Linda Greenhouse,“ On the Wrong Side of 5 to 4, Liberals Talk Tactic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8, 2007, p.3.正是為了服務這一問題意識,馬伯里案的奠基性象征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美國學術界得到了廣泛的青睞與研究。*See Sanford Levinson, “Why I Do Not Teaching MARBURY (Except to Eastern Europeans) and Why You Shouldn’t Either”, 38 Wake Forest Law Review 553(2003).與新政時期對于法院的定位,可以說沃倫法院的轉型逼迫美國的現代法學思想轉型。
在此,馬伯里案的經典文本重釋必定要承擔時代的命題。問題已經不是法院司法審查的合法性,而在于它的制度正當性。馬伯里案給沃倫法院的正當性論證拋出了一個悖論:一方面,沃倫法院力圖激活司法審查作為民權保障的絕佳工具;另一方面,歷史上的司法審查并非必定是民權的“守護神”。甚至,馬伯里本人的權利在馬歇爾手中也沒有得到救濟。與民權時代的政治要求相比,馬伯里案的敘事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奠定否決州法的案例傳統;二是如何建立民權與馬伯里案的邏輯聯系。 由此,一種代表高級法的“正義之所”——法院,其追求民權的敘事被逐步闡釋進馬伯里案的歷史與邏輯中去。在民權的背景下,法院的正義被填充了自然法、高級法、道德與理性的因子。
1954年的布朗案是一個政治性極強的司法判決,不僅是因為冷戰背景。*See 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13.從判決書的形式來看,符合報刊頭版的篇幅控制,以及沃倫對大法官“臺前幕后”所作的一致性判決的“思想工作”,都為美國的意識形態宣傳作了準備。在判決書的內容上,基于社會科學的論據,并非堅實的法律推理,以及對先例的推翻都給其合法性蒙上了陰影。針對這樣的政治性判決,麥克洛斯基首先強調馬伯里案也是馬歇爾為鞏固利益而展現的政治智慧。作為當時的聯邦黨人,為了完善共和國的新憲法秩序,避免司法部門在與政府部門的斗爭中衰落,而采取了一種迂回的司法審判技術,雖然沒有完成對馬伯里的司法救濟,卻建立了司法審查的長久原則,并符合當時的政治現實。
另一方面,盡管馬伯里案針對的是聯邦立法的《1789年司法機關法》,馬伯里案仍然被放置在否決州法的聯邦司法審查傳統中,構成馬歇爾的聯邦主義判決的一貫邏輯。這就是所謂以政治的智慧來推動聯邦的統一。這項理論工作是由“高級法”概念完成的。聯邦最高法院對州法的司法審查的正當性根基就是自然法/高級法傳統。如果說,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敘事乃是以自然法來糾正州法,那么馬歇爾的弗蘭徹案就變得非常重要。正如麥克洛斯基所總結的:“美國歷史中的政治思想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人民主權原則與高級法原則之間的矛盾沖突,它解釋了美國最高法院權力的崛起。”*McCloskey, Robert G., Levinson, Sanford, The American Supreme Cou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7.人民主權原則意味著以人民的意志為主,它通常表現為以代議制度表達出的總統與國會的意志。而高級法原則意味著對政府權力的限制,更多的是由獨立革命所激發出來。由此來看,人民主權與高級法之間總是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張力。
從高級法的角度來重新理解馬伯里案,馬歇爾的司法審查理論的奠基基礎,似乎不再是“人民主權”原則的推論,更多包含了“高級法”的影子。“與憲法相抵觸的法案能否成為這個國家一項法律的問題,是一個與合眾國利害攸關的問題;但幸好,其復雜程度與其重要性并不成比例。要做出裁定,看起來只需要承認某些原則,它們被認為確立已久,頗為牢固。”*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與其說,馬伯里案將憲法降級為法庭可以解釋的普通法律,不如說,馬歇爾將成文的、紙面的憲法提升為抽象的、原則的高級法。高級法由此可以通過憲法文本而“道成肉身”。
從高級法的角度來看,與馬伯里案相呼應的就是弗蘭徹案。*Fletcher v. Peck, 10 U.S. 87 (1810).1795年佐治亞州議會多數議員接受賄賂,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將從印第安人手中獲取的數百萬英畝土地廉價出售給行賄者地產公司。該地產公司將購得的土地分割后以高價出售。后一屆議會發現了前屆議會的舞弊行為,遂通過一項法律,宣布撤銷前屆議會出售土地的該項立法,由此,對該土地買賣均無效。聯邦最高法院需要判斷的問題就是這項取消契約合同的法律是否有效。在該案中,馬歇爾提出訂立契約的權利并非來自政府,而是社會使這一權利生效,合同不是根據法律而產生,而是當事人的行為。政府沒有任何權力去影響“契約自由”這項自然權利。在考文看來,最高法院中的自然法傳統來自于美國18世紀的觀念與實踐。“成文憲法是自然狀態下的個人達成的社會契約,私人權利先于憲法而存在。換言之,這些權利并非是因為它們在成文憲法中被提及而成為基本權利,相反,它們正是因為是基本權利而在憲法文本中提及。”*Edward S. Corwin, “The Basic Doctrin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12(4) Michigan Law Review, 247(1914).正是在自然法與基本權利的范疇內,我們可以理解沃倫法院的一系列民權判決繼承的是馬伯里案開啟的美國司法傳統。
從高級法/自然法法院的視角來看沃倫法院,頗被詬病的布朗案判決的推理,*See Learned Hand, Bill of Rights, Atheneum Books, 1964, p.9; Herbert Wechsler, “Toward Neut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73(1) Harvard Law Review 1(1959).也不過是將現代人的高級法——平等——寫入了憲法之中,宣示了聯邦最高法院在民權道德領域中的高級法地位。比克爾的“反多數難題”批判揭示的就是現代美國政治思想中的人民主權原則與沃倫法院的高級法原則之間的抗議。針對“反多數難題”的回答也是美國政治原則中的兩股理念斗爭的當代表現。
對于“反多數難題”,最激進的解答莫過于德沃金的“道德解讀”。比克爾本人的“原則治理”理論就為最高法院構建了一個道德的基礎世界。“我們所說的原則是指普遍的命題,霍姆斯如是說。他認為,形成原則是人的首要目標……就是說,在一個給定的文化范圍內,在一個地方,組織普遍有效的觀念,經常是以倫理和道德的預設為基礎的。原則、倫理、道德規范,這都是能夠讓人產生情感共鳴的用語,而不是定義清晰的用語;但他們終究是定位含義的努力,而不是排除含義的努力。”*[美]比克爾:《最小危險部門 : 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頁。在這個道德世界中,與其說聯邦最高法院是執行制憲會議的結果,不如說是仍在進行中的制憲會本身,不斷解讀那些“不證自明的真理”。這些真理般的道德律令就需要德沃金的“道德解讀”。
在道德世界中的道德律令表現為一種絕對主義道德。由此,道德真理容不得妥協。只是簡單地給予少數人以福利空間這樣的無原則的妥協與綏靖政策是不被允許的,因為這種退讓與妥協根本不足以承認少數人享有的絕對的道德權利。一旦道德權利被司法所解讀,那么社會就必須“只爭朝夕”地建立盡管對多數人不那么舒服的制度。“雖然種族融合措施導致很多人的境況變糟,但是,讓黑人兒童在黑人學校受教育也是不公平的。”甚至,“多數人的舒服也要讓位給少數人的絕對權利”。*[美]德沃金:《自由的法:對美國憲法的道德解讀》,劉麗君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頁。
但沃倫式的“正義之所”并沒有給社會帶來一種普遍的正義,*See Gerald N.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反而使得法律精英們喪失了群眾基礎。在手握高級法的“正義之所”的敘事中,法官發現并宣告憲法文本的道德規律,并塑造成客觀的道德。柯克法官的司法理性終于在美國憲法中找到了根基。德沃金的道德閱讀,不過是普通法法官以憲法文本依據,宣告美國人民的道德世界為何。從此,道德也上升為人類社會的自然規律,專屬法官的司法理性之域。同樣充滿了精英主義氣息的“正義之所”的司法哲學追求的卻是一種60年代文化左派的“正義”,逐步離人民漸行漸遠,終于導致法律與民情、精英與大眾的沖突。*參見徐斌:《社會契約、社會革命與美國最高法院》,載強世功主編:《政治與法律評論》(第五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四、里根革命后的政治法院
1980年代的保守主義里根革命結束了自由派的伯格法院,迎來了保守主義的倫奎斯特法院與羅伯茲法院。司法能動主義轉變為推進保守主義進程的司法策略。*See Ernest Young,“ Judicial Activism and Conservative Politics”, 73(4)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1217 (2002); William Marshall, “Do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differ in Judicial Activism”, 73(4)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1401(2002); Keenan D. Kmiec, “The Origin and Current Meanings of ‘Judicial Activism’”, 92(5) California Law Review 1441(2004).針對保守主義政治與司法現狀,自由派法學希望重新解釋馬伯里案,但是問題意識已經與沃倫法院不同。馬伯里案不再是正義之所的前身,更應當作為一種司法傳統,擺脫保守主義法學對現實的司法政治施加“司法自制”的知識影響力。*See Robert H. Bork, The Tempting of America: the Political Seduction of the Law, Sinclair-Stevenson Ltd, 1991.這個工作當屬阿克曼的完成度最高。
在保守主義主導的里根革命之后,一種共和主義的政治思想開始復歸。在共和主義的視角中,馬伯里案所包含的邏輯更多地體現為權力制衡的共和體制。針對保守主義的批判,共和主義對于馬伯里案的理解逐步回歸到了新政前后的敘事中。巴爾金與阿瑪、布萊斯特、列文森等編纂的主流教科書《憲法決策的過程:案例與材料》初版于1975年。但與其他案例教科書以馬伯里案開篇不同的是,該書已經逐步回歸到了新政的“機構比較優勢”傾向上,*See William N. Eskridge, Jr. and Philip P. Frickey, “The Making of ‘The Legal Process’”, 107(8) Harvard Law Review 2031 (1994).以“美國第一銀行案”和“第二銀行案”開頭。*參見[美]布萊斯特等:《憲法決策的過程:案例與材料》,張千帆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70頁。
由此,在20世紀60到80年代間的積極進取追求正義的馬歇爾法院形象之外,美國其實還存在著一個保守、審慎的馬伯里案。*See William Van Alstyne, “A Critical Guide to Marbury v. Madison”,1969(1) Duke Law Journal 1 (1969); Michael Klarman, “How Great were the ‘Great’ Marshall Court Decisions?”, 87(6) Virginia Law Review1111 (2001); Richard H. Fallon,“Marbury and the Constitutional Mind: A Bicentennial Essay on the Wages of Doctrinal Tension”, 91(1) California Law Review 1 (2003).馬伯里案的歷史背景不是1800年的換屆與黨派政治,而是美國革命以來存在的民主總統制的問題。民主總統的興起和杰斐遜聯系在一起。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的兩屆任期內實行的是共和制,其組閣原則是唯才是舉。華盛頓憑借克里斯瑪的統治,把漢密爾頓和杰斐遜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結合起來。此時,持迥然不同的政治原則的人還能夠在一個政府中調和。但是,在第二任總統亞當斯那里,共和的政府原則無法持續下去。*參見李一達:《“共和君主制”的興起——1787-1796年間的美國總統制的誕生》,載《北大法律評論》第13卷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亞當斯政府的副總統是杰斐遜,國務卿是馬歇爾。共和主義的總統制無法調和政府內部的斗爭。由此,1800年的選舉意味著新型總統制的誕生——杰斐遜的民主總統制。整個杰斐遜帝國類似雅典平民政府的興起,不同于之前的貴族體制。
耶魯憲法學教授阿克曼的新憲政敘事就在于論證1800年角逐總統的人選并不只是亞當斯與杰斐遜,還有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在阿克曼看來,馬伯里案的核心問題就不是20年代自由派所關注的建立司法審查正當性的憲法第3條,而在于《憲法》第2條(總統制)問題。總統制的問題意識下,阿克曼挖掘出了斯圖亞特案,來論證總統、國會與法院之間的憲政慣例,展示出與馬伯里案不同的——保守自制的馬歇爾形象。此后,斯圖亞特案馬上成為自由派憲法教科書的經典案例,與馬伯里案一同討論。*See Paul Brest, Sanford Levinson, Jack M. Balkin, Akhil Reed Amar, Reva B. Siegel: Processes of Constitutional Decisionmaking: Cases and Materials, 5th ed. Aspen Pub, 2006, pp.123-201.
斯圖亞特案于馬伯里案后一周內判決,判決結果與馬伯里案大相徑庭,完全同意了總統的法案。*Stuart v. Laird, 5 U.S. (1 Cranch) 299 (1803).此案源起于《1801年司法機關法》。該法案任命了一位巡回法官約翰·拉爾德,但卻因為國會在1802年通過了《1802年撤銷法》而喪失了巡回法官職位。當拉爾德要求重建的巡回法院執行此前的判決時,休·斯圖亞特的律師——查爾斯·李,此人也是威廉·馬伯里的律師——提出反駁,認為只有簽發判令的法官才能夠執行判決,而這位法官已經根據《1802年撤銷法》被撤職。李同時主張《1802年撤銷法》是違憲的,因為它將“未曾在任上行為不端的法官”撤職。
馬歇爾在初審中判決斯圖亞特敗訴。斯圖亞特案與馬伯里案同期開庭辯論,并在馬伯里案判決后六日下發。如果聯邦最高法院判決《1802年撤銷法》違憲,杰斐遜黨人將作出迅速而堅決的反應,限制司法部門的權力。馬歇爾在此案中回避。佩特森(Paterson)大法官在法庭判決中宣稱:“憲法賦予國會權力,以其認為適當的時候設立下級法院(inferior tribunals),把某類訴訟案的管轄權(cause)由一個(下級)法院轉移到另一個。在最近的情形中,憲法里并沒有條文禁止或阻礙這種立法權力的行使。”*Stuart v. Laird, 5 U.S. (1 Cranch) 299 (1803).
有趣的是,斯圖亞特案中法院意見并未理會李針對《1802年撤銷法》合憲性的論點,即法院仍然沒有關注被馬歇爾遺漏的管轄權條款,轉而把國會調整司法機構的權力的正當性建立在于《憲法》第3條第1款上:“合眾國的司法權,屬于最高法院和國會不時規定和設立的下級法院。”從而將第1款的“司法設立”條款在邏輯上延伸至第2款的“管轄權”條款。“憲法賦予國會權力,以其認為適當的時候設立下級法院,把某類訴訟案的管轄權由一個(下級)法院轉移到另一個。”*Stuart v. Laird, 5 U.S. (1 Cranch) 299 (1803).從而,在實質上避免處理司法法與憲法管轄權的規定,而在形式上處理為司法法和憲法中司法設立條款的關系。這樣的處理方式完成了兩個效果,一是避免直接推翻馬伯里案,盡管兩個案件在違憲問題的審查上極為類似;二是避免了與國會的沖突,轉而承認國會的憲法權利。
由此,在阿克曼提供的新憲政敘事中,斯圖亞特案的最高法院既不與先例,如馬伯里案相沖突,又不與當政的國會和總統等政治部門相沖突,展現出一種謹慎、自制的保守形象。由此,佩特森代表的聯邦黨人的司法系統對杰弗遜的政府(國會與總統)完成了一次正式的服從。佩特森的最高法院展現出一種與馬伯里案中的最高法院完全不同的謹慎保守形象。法院極為尊重國會與總統這樣的政治機構的正當權力,不輕易行使司法審查權利,有效地緩解了民主與法治之間的張力。也就是說,斯圖爾特案的最高法院開啟的是一套“司法謙抑”,“講政治”、“顧大局”的人民法院傳統。
1803年的美國面臨了兩種司法的模式:馬歇爾的激進的精英法院和佩特森的保守的人民法院。在當時來看,佩特森的司法模式挽救了美國共和國,合成了民主與法治的兩個憲法原則,開啟了以總統和國會為中心的憲法敘事。因而,佩特森,而不是馬歇爾,成為了阿克曼筆下杰出的法律人政治家。斯圖爾特案,而不是馬伯里案,成為美國司法的中心原則。這種新知識的生產當然與阿克曼的問題意識相關。在2005年羅伯茲法院上臺后,一個長達三十年的保守主義法院已經拉開序幕。以阿克曼的新憲法敘事為基礎,當下美國的保守主義法院應當尊重“人民法院”的佩特森司法傳統,尊重民主黨所控制的總統與國會的政治決定。
五、作為法治文化符號的馬伯里案
無論馬伯里案是否為司法審查確立了堅實的法理基礎,這樣的推理總是在不同的政治語境中有著不同的理解。關鍵問題是,馬伯里案本身作為共和國早期的司法判決,它對于美國兩百年憲政的意義是什么?它只是一篇主張司法審查權的法庭意見嗎?它只是一篇政治論文嗎?它只是一個最高法院的先例嗎?是什么樣力量最終使得最高法院“一貫正確僅僅是因為我們最終說了算”?*Brown v. Allen, 344 U. S. 443, 533 (1953), (Jackson, J., concurring.).我們更要繼續追問的是,馬伯里案的多重面相對于美國憲政的意義是什么?美國憲政給馬伯里案塑造的多重面相又對案件本身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保羅·卡恩的《法律的統治:馬伯里訴麥迪遜與美國憲法》一書即是將馬伯里案作為標本放在了美國的法治文化中來理解。*See Paul W.Kahn, The Reign of Law:Marbury v.Madis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在卡恩看來,馬伯里案的理解不僅僅是放在1800年代的黨派斗爭中。在這場政治斗爭中,黨派利益斗爭只是一種形式,更為根本的是關于美國立國的根本原則的爭論。馬伯里案的意義在于,從時間上與空間上奠定了法治為新共和國的基礎性原則。
亞當斯政府為了鎮壓杰斐遜民主共和黨的組織宣傳,曾經動用司法系統貫徹執行其頒布的《1798年反顛覆法》,對任何惡意反對政府的言論和出版物處以罰款或監禁。在這段時間里,總共有二十五人因此被捕,十人被起訴,多是民主共和黨人。*參見[美]西蒙:《打造美國: 杰斐遜總統與馬歇爾大法官的角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頁。在這段經歷之下,杰斐遜領導的共和黨認為,美國聯邦法律和聯邦司法系統就是一種無法無天的黨派政治(partisan lawlessness)的表現。法庭只是國家政治的產物,附屬于國家與政黨政治,在法治和政治之間并無明顯的界限,只是更好或更壞的政治之分。*See Paul W.Kahn, The Reign of Law:Marbury v.Madis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作為政治活動中多數人民自己的意見,才更值得信任。法庭判決所能體現的不過是黨派政治和個人政治。
在時間上,馬伯里案告別了革命,開啟了“法治政府”的紀元。在卡恩看來,杰斐遜的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在于沒能在美國建國之后處理好革命與法治的關系。革命和法治本就是政治中的一對張力。美利堅合眾國和其他很多現代國家一樣,都是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然而,革命勝利后,接踵而至的問題卻是如何終結革命。而革命的終結就意味著要建立常態的政治秩序。在現代政治中,這種秩序就是法治。*革命與法治的關系論述也可參看強世功:《革命與法治——中國道路的理解》,載《文化縱橫》2011年第6期。因此革命本身是法治的起源,法治的全部正當性都深深地根植于革命傳統之中。正是這場歷史性的革命塑造了此后的日常政治秩序。革命本身是以秩序為歸屬,革命的目的是為了終結革命本身。最為緊張的是,革命的起源必然是對革命對象的前法治的反動。“革命總是以人民的名義實現的。現代是要確認一個革命傳統的人民共和時代,但這一革命傳統總是使得以人民主權者代表的名義挑戰政府成為可能”。*Paul Kahn, Putting Liberalism in its Pla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63.也就是說,任何以人民之名進行統治的現任政府永遠都面臨著以人民的民意掀起下一次革命的危機。
因此,以革命者姿態出場的杰斐遜的民主共和黨,針對的絕不僅僅是國會里的聯邦黨人,同樣也指向聯邦黨人剛剛接手的脆弱無力的司法機構。他們真正對抗的是法治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意義。說到底,杰斐遜呼吁人民出場,是要在人民與國家,在當下革命與法治的信仰之間做出抉擇。在這場歷史性的抉擇中,法治的表征就是1787年的美國聯邦憲法。這也是馬伯里案面臨的最大難題。在卡恩看來,馬伯里案中,法院代表人民的意見是美國政治秩序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使得美國完成了18世紀民主政治的難題——公眾意見的啟蒙。*Paul W.Kahn, The Reign of Law:Marbury v.Madis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11.正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觀察到的,美國的現代民主下,人民啟蒙由政黨完成,也是由法院完成。*參見[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95-203頁。從而,美國沒有走上法國的循環革命的時間軌道,而是走向一種線性的時間觀。結束革命,開啟法治政府的就是馬歇爾的馬伯里案。
在空間上,馬伯里案與英國憲政不同,開啟了一個新傳統。馬歇爾在這一案件中重新塑造了法治,明確了法治與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ion)之間的界限,進而明確了法治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意義。馬伯里案所塑造出的法治表象,是與人治相對的法治。盡管至今為止學者們都用“馬歇爾寫到”、“馬歇爾宣稱”等個人化的詞匯來宣稱馬伯里案的判詞,認為是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奠定了司法審查這一傳統,但如果仔細考究判詞,我們會發現,馬歇爾根本沒有在這份法庭意見中署名,而是冠以“法庭意見”的抽象名稱。在此之前的英國司法傳統中,每個法官都表達自己的意見,判決理由的申述要在眾多的個人意見中尋找依據。但在馬伯里案中,馬歇爾作為首席大法官和判決的執筆人放棄了這一傳統,而是建立“法庭意見”這一獨立的權威性。從法治的角度來說,不署名的司法意見可以使讀者與文本之間建立起多重聯系。因為它不屬于任何一個有形的作者,它是一個文本,從而屬于無形的讀者——人民。卡恩指出,促使馬歇爾放棄普通法的上述傳統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憲法不同于普通法的特點:相比起源于古老過去的普通法,憲法起源于現存的記憶中,因此法官發表意見就變成了獨立的法律觀。馬歇爾對這一傳統的放棄,恰恰對內加強了法庭內部的統一性,對外則強化了法庭意見的非個體性。而這種對主體的超越塑造了法庭的權威。*See Paul W.Kahn, The Reign of Law:Marbury v.Madis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ter 6.
法治傳統的塑造需要給人民以起源的故事,猶如圣經故事之于基督教信仰的認同。馬伯里案對于美國的憲政意義猶如上帝的“創世紀”,馬歇爾成功塑造了美國的法治傳統,成為美國這個新民族的起源故事,告訴美國人民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縱觀美國法律與政治之間采取了怎樣的路線之爭,他們都首先認定馬伯里案為美國憲政的經典文本。傳統依附于經典文本,正是建國一代的文本,馬歇爾的最高法院判決,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的文集,麥迪遜的制憲會議記錄,甚至是1787年憲法本身,都代表了美國從那一時刻起形成了文明自覺與制度自覺,與英國訣別。可以說,馬伯里案,以及后續美國學者的討論,進一步加深了其神話意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兩百年的美國歷史塑造的就是盧梭的“公民宗教”。*參見[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四卷,第八章。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解了阿克曼的學術努力。美國只有一部憲法,美國人民生活在同一個共和國和時間序列中。這樣的政治想象就奠基于美國憲政的連續性構建。美國只有一部1787年費城憲法,美國只有一個政治紀元,一種政治時間。與歐洲憲政傳統相比,“法國自1789年經歷了五個共和,而我們只生活在一個共和國內。”*[美]阿克曼:《我們人民:奠基》,汪慶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美國憲政的連續性成為了美國憲法學的前提假設。“我們向自己講述的有關我們憲法根基的敘事是具有深刻意義的集體自我定義行為,這種連續不斷的講述在國家身份的延續中起了重要作用。”*[美]阿克曼:《我們人民:奠基》,汪慶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頁。連續性的憲政敘事正是為了構建美國政治共同體想象的邏輯。馬伯里案作為經典文本也在這種連續性中獲得了憲法根基的民族認同意義,成為美利堅民族的法治文化符號。
六、結語
在法治文化符號的意義上,美國的法學研究已經“不可能通過割裂同以往的聯系來建立更好的秩序。因為美國人已經習慣于認為憲法歷史包含能夠解釋美國人當下政治的有價值的線索。”*[美]阿克曼:《我們人民:奠基》,汪慶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法治文化符號的真正含義就在于,法治通過常講常新的民族記憶建立在人民的內心上。
講述故事的舞臺無疑是大學教育。但是列文森卻希望將馬伯里案拿離法學院。*See Sanford Levinson, “Why I Do Not Teaching MARBURY (Except to Eastern Europeans) and Why You Shouldn’t Either”, 38 Wake Forest Law Review 553(2003).他認為該案根本不適合對美國本土學生教授。首先,理解這個案子需要相當的歷史知識,甚至是所有的歷史細節。列文森重點批評了馬伯里案的推理和分析非常拙劣。在邏輯上,馬歇爾引用并解釋第13條時,有意地把《1789年司法機關法》引向跟憲法相沖突的方向去解釋;甚至,馬歇爾引用憲法第3條的時候,把但書條款給遺漏了,直接引用前面的部分。這樣的結果是,馬伯里案逐漸會淪為修辭。
特別是在保守法官當道的情形下,在憲法課程當中,如果一開始的課程安排就是此案的話,即使不是有意的,該案也灌輸給學生“司法至上”的觀念,而不是“憲法至上”的觀念,并且容易受到法律現實主義的侵害,錯誤地認為“憲法是法官任意解釋的法,法官說它是什么就是什么。”*Sanford Levinson, “ Why I Do Not Teaching MARBURY (Except to Eastern Europeans) and Why You Shouldn’t Either”, 38 Wake Forest Law Review 553,567 (2003).這種理解從規范意義上和描述意義上都是難以為繼的。從規范意義上講,這是一種精英主義解釋,違背“人民憲政”的理念。*See Larry D. Kramer, “The Supreme Court, 2000 Term-Foreword: We the Court”, 115 Harvard Law Review 5 (2001).從描述意義上講,它也是不準確的。因為憲政互動的過程并不是法官說它是什么就是什么,而是在一個歷史大環境下,各種參與者都把它的因素融合進去。如果要說明司法至上,不如從麥卡洛克聯邦銀行案*McCulloch v. Maryland, 17 U.S. 316 (1819).講起,談論聯邦司法的至上,“至上”于州法院,而不是國會與總統。至于馬伯里案還有什么意義?列文森認為,它的生命也許在于本國正身處憲政發展轉型期的東歐學生。
將馬伯里案拿離法學院當然不是對美國法治文化的失望,畢竟不是拿離大學。反而,這種拿離本土,而投放世界的想法正是文化自信的表現。因為美國正在領導著一場全球普世主義法治文化。也因此,經歷東歐劇變與憲政轉型的東歐學生最需要馬伯里案的外來法治文化的“輸血”。這種文化自信更體現在對來自大洋彼岸的大量中國留學生的“不屑一顧”。因為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中已經自覺將馬伯里案所代表的美國法治文化納入到思想范疇與日常實踐中。長久以來,中國學界對于馬伯里案的討論基本延續了美國60年代自由派學者的正義之所方向。1999年肖揚司法改革的啟動,2000年美國發生布什訴戈爾案,2001年齊玉苓的“憲法司法化第一案”,這些事件導致學界爆發了對于司法審查和馬伯里案的研究熱潮。那篇刊登在《人民法院報》上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文章,*黃松有:《憲法司法化及其意義——從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個〈批復〉談起》,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8月13日第B1版。它對于馬伯里案的論述與以往美國的“高級法法院”的司法形象如出一轍,都關注判決書如何通過司法的力量尋求該案當事人的權利救濟,或者說,正義的實現。但是,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馬伯里案及其所代表的司法哲學在美國兩百多年的政治譜系中有著多重面相。
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治科學家集中反思日益意識形態化的司法知識時,曾說:“聯邦最高法院不是在真空中運轉的。”*[美]盧卡斯·A.鮑威:《沃倫法院與美國政治》,歐樹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頁。對馬伯里案的敘事與理解也隨著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中的地位變遷而發生著位移。馬伯里案連同司法審查制度在中國與美國語境中面臨了不同的問題意識與服務目的,展現了學術研究與公共輿論的不同發展軌跡。由此,在漫長的憲政傳統中,本文截取了其中的幾個歷史斷層,展現了馬伯里案所代表的普通法法院、高級法法院與政治法院等不同的司法哲學。出于不同的歷史境況,20世紀以來美國人不斷對該案進行重讀甚至神化,馬伯里案在諸多憲法問題上的重要意義會在之后不同的政治背景當中被分別強調。*參見劉晗:《憲制整體結構與行政權的司法審查:“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再解讀》,載《中外法學》2014年第3期。人們不斷在諸多憲政時刻重塑馬伯里案的解讀,融入多種傳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不同于中國學術界,馬伯里案在美國語境中的研究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狀態。無論是早期的保守派,還是當代的自由派與保守派,在提出他們的司法審查理論的同時,都會重新回到馬伯里案中,從中找到自己的傳統價值。從而,馬伯里案本身成為了美國的法治文化符號,在兩百多年的歷史中,被解讀出多種面相。
要理解這些復雜面相以及作為法治文化符號的美國憲政文本,我們就需要深入到美國不同時期的語境中,從他們的思想共識、問題意識、政治社會背景出發,才能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如果中國學人與公共知識分子不能充分認識這些面相中體現的迥異的敘事與邏輯,那么,單一的知識不免淪為一種意識形態。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不經反思的知識將中國憲政的命運納入到了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政治秩序中。
(責任編輯:肖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