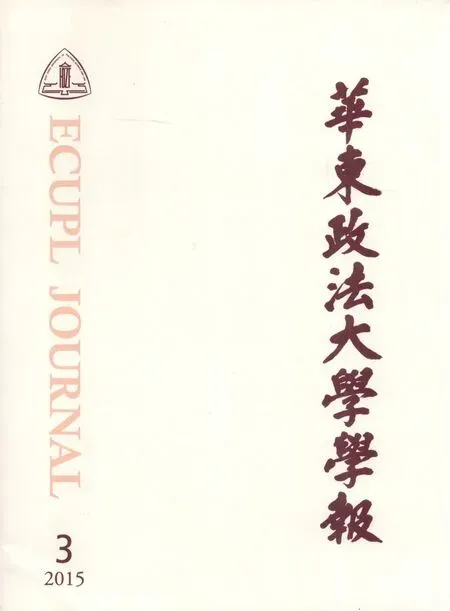釋憲者林肯
——在美國早期憲法史的敘事中“找回林肯”
田 雷
釋憲者林肯
——在美國早期憲法史的敘事中“找回林肯”
田 雷*田雷,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受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創新專項(項目號106112015CDJXY470008)資助。

目 次一、“找回林肯”:為什么與如何做?二、“兩次建國”與早期憲法史的路線之爭三、林肯的聯邦(共同體)觀四、林肯的民主觀五、林肯的法治觀六、“林肯”:一種進入美國憲法史的方法
林肯總統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憲法解釋者,他對建國憲法的解釋結束了縱貫美國早期憲法史上的路線之爭,解決了1787年制憲者“合眾為一”,卻未“定于一”的建國不徹底的問題,由此成為新憲法秩序的奠基人。回到內戰這場憲法危機所規定的憲法解釋場域,林肯認為聯邦共同體是永續的,因此南部蓄奴州無權單方面退出;由國父們所開創的立憲共和國是一場試驗,而共和國是否有能力對抗內部敵人而維持領土完整,將是由戰爭結果加以裁決的問題;林肯是憲法的“維護者、保護者和捍衛者”,護憲的前提在于護國,因此“拯救聯邦共同體”是林肯這位戰時總統至高無上的目標。一方面我們要在早期憲法史中發現林肯。另一方面,林肯可以成為我們進入美國憲法史的一種方法,豐富我們對于這段“漫長”而又“擁擠”的美國早期憲法史的理解。
林肯 憲法解釋 憲法文化 聯邦 民主 法治
一、“找回林肯”:為什么與如何做?
自1860年11月當選美國第十六任總統,至次年3月4日宣誓就職,林肯總統候任的四個月,*在第二十修正案于1933年寫入憲法之前,總統就職日為大選次年的3月4日,漫長的候任期會造成“跛鴨”政府在危機時刻的無所作為,因此被列文森教授稱之為憲法的“愚蠢”條款,參見Sanford Levinso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Constitutional Stupidities”, 12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183-186 (1995)。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分裂之冬”。在此期間,南部七個蓄奴州宣布退出聯邦共同體,組建了南部邦聯。正如林肯著名的“分裂之屋,無力自立”的演講,自美國立憲建國以來就確立的北方自由制和南方奴隸制的“一國兩制”狀態,至此再也無法和平共處于同一憲法秩序內,面對著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林肯在就職時肩負著一個“比華盛頓當年擔負的還更艱巨”的任務。*[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72頁。本文所引用的林肯文本,絕大多數是在朱曾汶先生譯文的基礎上對照英文原文,進行程度不等的調整所得出。為了方便讀者進一步查閱,腳注內標注的為相應文字在商務版《林肯選集》的頁碼。我所參考的英文版林肯文選,主要是Steven Smith edited,The Writings of Abraham Lincol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如果說八十多年前,華盛頓及其建國兄弟們是要創建一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現在,歷史交給林肯總統的任務就是要將這個由國父所開創的立憲政府傳承下去,正如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演講中的結束語所言,“要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78頁。
在共和國命運危在旦夕的嚴冬里,“跛鴨”總統布坎南認為南方諸州無權單方退出聯邦,但他同時卻宣稱,聯邦政府亦無權以武力強制任何一州留在聯邦內。行將進入休會期的第三十六屆聯邦國會,也在林肯就職前夕拿出一條妥協修憲案,為了安撫南方奴隸主,這條修憲方案明文宣布聯邦政府無權在蓄奴州內干預它們的地方性制度。而在此“分裂之冬”,林肯留在伊利諾伊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在一間借來的辦公室內,起草他的總統就職演說。在起草過程中,林肯手邊不離建國者在1787年之夏起草的費城憲法(以及前十二條修正案),不僅如此,他還從律師合伙人那里借來三份參考文獻,分別是:(1)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丹尼爾·韋伯斯特在1830年國會辯論中對南卡羅來納州(以下簡稱南卡州)參議員羅伯特·海因的答復;(2)杰克遜總統在1832年末對南卡州廢止關稅之抗爭的宣言;(3)肯塔基州參議員亨利·克萊就1850年大妥協所發表的演講(1850年2月)。*Mark Neely, Jr., Lincoln and the Triumph of the Nation: Constitutional Conflict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pp. 38-42.1861年3月4日,一個清冷的春日下午,林肯面對五萬名觀禮群眾發表了他的就職演說,據現場報道者稱,新總統的聲音“清晰而堅定”。*Eric Foner, The Fiery Trial: Abraham Lincoln and American Slaver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p. 157.
此時距離南部邦聯打響內戰第一槍還有一個月多的時間,但內戰這場憲法危機的大幕,自以南卡州為首的南部七州宣布退出聯邦共同體之日起就已經徐徐拉開。遙想費城當年,建國者在長達百日的“辯論”后起草了作為美國政治根本法的1787年憲法,將在《邦聯條款》治下的保留主權的北美諸邦“合眾為一”,但此時的合眾為一,首先是為了解決“不聯合,必定死(join, or die)”的生存問題,制憲者在費城會議上“擱置爭議”,并未將所有的政治問題都“定于一”。因此,立憲建國之日,也是政治問題憲法化的開端。但是,內戰前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妥協,并沒有從憲法源頭解決制憲者遺留的問題。在林肯這位以自由勞動為施政綱領的總統上臺時,南部蓄奴州宣布退出聯邦共同體,在這些分裂分子看來,他們是美國革命以及《獨立宣言》的繼承人,他們合乎憲法地退出了聯邦。簡言之,美國內戰是一場憲法危機乃至失敗,林肯這位戰時總統面對著許多憲法問題,也是在解決或者回避這些憲法問題的過程中,林肯成為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憲法解釋者。*關于將美國內戰作為憲法危機的分析,可參見Arthur Bestor,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s a Constitutional Crisis”, 69 (2)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27-352 (1964);關于討論林肯所面對憲法問題的導論著作,可參見James Randall, Constitutional Problems under Lincoln,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26;近期的討論,可參見Daniel Farber, Lincoln’s Co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時至今日,美國公民——乃至任何一位現代共和國的公民——都生活在林肯的憲法政治遺產下。借用法學界常用的修辭,在美國內戰結束以及林肯總統遇刺一百五十周年之際,我們應當認真對待林肯。
題名內包括“找回林肯”,之所以要“找回”,是指我們當下對美國憲法史的研究受限于以司法審查為中心的學術范式,將美國憲法的歷史化約為美國最高法院的憲法解釋史,林肯在這種敘事邏輯中被冷落在歷史的角落里,甚至有可能因其批評最高法院的言論而被視為法治的破壞者。有鑒于此,本文借用20世紀80年代在政治學中興起的所謂“找回國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學派,*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主張對美國憲法史的研究也需要一場“找回林肯”的思想運動。“找回林肯”,不是指我們都要成為就林肯論林肯的林肯研究者,而是要讓林肯成為我們進入美國憲法史研究的一種立場、方法甚至姿態,任何一種面向美國憲法的歷史敘事必須安放林肯的憲法言與行,否則就不足以形成整全的憲法史觀。在近期紀念林肯的一篇文章中,美國保守派憲法學家邁克爾·鮑爾森就這樣寫道:
如果說內戰是美國憲法解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那么林肯總統就是美國憲法最重要的解釋者——憲法的維護者、保護者和捍衛者。大多數法學教授和法官如何解說當下的憲法議題,全世界不會關注,也不可能銘記,但是,林肯在適用美國憲法時做過些什么,又說了些什么,全世界必定不會忘記。正是林肯塑造了過去一百五十年來我們對美國憲法的理解,其程度遠非任何一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甚至也非任何一位制憲者所能及。*Michael Stokes Paulsen & Luke Paulsen, “The Great Interpreter”, First Things, May 2015.鮑爾森教授借用了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演講中的著名句式,“……全世界不會關注,也不可能銘記(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但是……全世界必定不會忘記(but it can never forget)”,這是寫在字里行間對林肯的致敬和紀念。葛底斯堡演講,參見[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78頁。
林肯的憲法解釋和決策早已化為美利堅合眾國這個憲法共同體的立國之本。正因如此,如何理解林肯,就成為每一代美國人的“當代史”問題——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林肯。正如杜波依斯在1922年所言,林肯“殘忍卻也仁慈;熱愛和平同時又是一名斗士;看不起黑奴但卻讓他們選舉和戰斗;保護奴隸制,最終卻解放黑人奴隸”,因此“林肯博大,包羅萬象(big enough to be inconsistent)”。*轉引自George Fredrickson, Big Enough to Be Inconsistent: Abraham Lincoln Confronts Slavery and Ra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而在又過了近百年后,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林肯,更是經過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亞文化的解讀者的演繹,因此林肯體現在學術資源中的形象更是多變、復雜乃至零碎的。 如何將林肯“由知道許多事的狐貍”變為“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用刺猬和狐貍這一對形象來描述林肯,可參見James McPherso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es”, in James McPherson,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3-130。本文所限定的視界就是“釋憲者林肯”。林肯總統生活在美國早期憲法秩序內,是建國憲法的最偉大解釋者,當然,這里的偉大并不是說林肯的憲法解釋是完全原創或融會貫通的(這是學術標準,但憲法解釋在憲政國家從來就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在于他對建國憲法的理解最終成為了自由新生和憲法再造的歷史根基。林肯代表著美國憲法史上最根本的分水嶺,他以自己的犧牲終結了美國漫長的建國時刻,啟動制憲權解決了建國者遺留在1787年憲法內的結構性難題,正是在此意義上,21世紀的美國仍處在林肯之后的憲法時間內。
研究釋憲者林肯,首要材料就是林肯自己的憲法言與行。在林肯的政治人生中,特別是擔任內戰總統的四年中,林肯圍繞憲法議題發表過一系列演講和書信。長期以來,我們將林肯的文本當做學習文字修辭的政治美文,主要用以文學鑒賞,而沒有將這些文本還原到美國憲法解釋的場域內進行法學解讀。背誦只有272個單詞的葛底斯堡演講從來不是難事,但如何將林肯的演講帶回到美國憲法史所規定的語義和語境內,就是我們“帶回林肯”的首要挑戰。本文將林肯的文本視為法教義學意義上的美國憲法“經典(canons)”。*關于美國法語境內的教義經典,可參見Jack Balkin and Sanford Levinson, eds., Legal Canons, NYU Press, 2000。當然,可見于文字的林肯是多彩多姿的,即便是收錄在《林肯選集》內的文字也并非通篇都是本文所講的解釋經典,*比如,林肯年輕時所寫的一些私人信件,也收入在《林肯選集》中,但這些文本對于我們今天理解林肯的憲法解釋顯然并沒有直接的關系。我們以下主要關注林肯的如下文本:(1)1838年1月27日,林肯對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青年學會的演說;(2)1861年3月4日,林肯總統的第一次就職演說;(3)1861年7月4日,林肯總統致國會特別會議的咨文;(4)1862年12月1日,林肯總統致國會的年度咨文;(5)1863年11月19日,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國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禮上的演說;(6)1865年3月4日,林肯總統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以上六篇演講,分別參見[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3-12、178-188、190-195、254-257、277、278、307-309頁。
在解讀林肯的憲法文本時,我們應當意識到要閱讀的不僅是林肯是怎么說的(words),還應包括林肯是怎么做的(deeds)。更準確地說,林肯作為聯邦政府的戰時總統和軍隊總司令,他的任務當然不是在象牙塔內撰寫一部“美國憲法解釋指南”,林肯解釋憲法的文本首先就是他“維護、保護和捍衛憲法”的政治行為。如同林肯研究的權威學者詹姆斯·麥克弗森教授所言,我們應當關注林肯是如何“以言行事”的。*可參見James McPherson, “How Lincoln Won the War with Metaphors”, in James McPherson,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3-112。就此而言,我們應采用一種“文本間主義”的解釋方法來理解林肯。*Akhil Amar, “Intratextualism”, 112 Harvard Law Review 747-827 (1999).這里的“文本間”,首先是指要將林肯的字面文本作為一個相互間融貫的整體來進行理解;其次,或許更重要的是,應當認識到林肯的總統行為也是憲法學要研究的另一種“文本”,觀察“words”和“deeds”之間是否有背離,又是如何取得統一的。簡言之,我們應當全面地而不是割裂地進入林肯研究。
但只要我們還停留在就林肯論林肯的邏輯里,我們就無法達到憲法學所要求的“全面”。前述作為憲法經典而存在的林肯文本,不是林肯在書齋里慎思明辨后的產物,而是誕生在政治的強力與偶然之中的,因此往往是知識人難以理解的文本。我們在今天去理解林肯的解釋經典,首先必須回到產生這些經典的憲法政治語境,特別是內戰這場憲法危機以及其來龍去脈。只有重新構建出早期憲法史上具體的、真刀實槍的解釋場域,我們才能發現林肯文本的憲法意義,否則的話,葛底斯堡演講永遠只能是慰藉知識分子心靈的政治美文而已。1848年,當林肯尚且只是國會眾議院內的年輕議員時,他就在國會圍繞著“內陸建設”(internal improvement)的辯論中談到過憲法解釋問題:“主席先生,有關憲法問題,我沒有太多可講。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當我站起來發言時,我就感到,若要嘗試任何原創的憲法論證,我就不可能也不應該得到耐心傾聽。早在我之前很久,那些最有能力也最具美德的人們就已經耕耘了這整片領域了。”*Mark Neely, Jr., The Fate of Liberty: Abraham Lincoln and Civil Liber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11.林肯作為一位釋憲者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從一開始,林肯就生活在本文所說的早期憲法文化的政法傳統內。在1860年當選總統之前,林肯是伊利諾伊州境內最成功的律師,耶魯法學院安東尼·克隆曼教授稱林肯為“法律人—政治家(lawyer-statesman)”的典范。*“我稱之為‘法律人—政治家’的理想。在美國法的每個時代,這種理想都能找到其杰出的代表人物。例如,林肯就是一例。在內戰之前的歲月里,當林肯在奮力尋找一條可以同時挽救共同體和民主的道路時,林肯并沒有可以指引他自己的公式。林肯也沒有任何技術性的知識,可以告訴他如何找到解決美國兩難困境的出路。林肯所能依賴的只有他的智慧——他審慎的平衡感,從而判斷應在何處達成原則與實用之間的均衡。”Anthony Kronman, The Lost Lawyer: Failing Ideal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在討論林肯時,我們不可脫離林肯本人就自覺意識到的建國憲法傳統的解釋譜系。
由此可見,我們不僅要在林肯的體系內全面理解林肯,而且要將林肯的文本放回到美國早期憲法歷史的發展脈絡里去。只有在美國早期憲法文化的語境內,我們才能知林肯是如何從他口中那些“最有能力也最具美德的人們”那里學習憲法解釋的。憲法解釋是一種代際之間的對話:如果我們將韋伯斯特在1830年對海因的答復視為對南卡州的第一次答復,將1832年杰克遜總統回應廢止危機的宣言稱為對南卡州的第二次答復,那么林肯宣布南方各州退出聯邦為違憲舉動的就職演說,就構成了對南卡州的第三次答復。最終,我們要建設林肯的“法律圖書館”:*關于“早期憲法史內的法律圖書館”,可參見Alison LaCroix, “The Lawyer’s Library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in Martha Nussbaum and Alison LaCroix, eds., Subversion and Sympathy: Gender, Law, and the British Nov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51-272。一方面,我們要在早期憲法史的坐標系內發現一個存在于字里行間的釋憲者林肯的形象;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發現林肯與早期憲法文獻之間另一種隱秘的“互文性”,不僅是要以早期憲法文化為語境去理解林肯自身,而且還是以林肯為方法去理解美國的憲法發展乃至普遍意義上的憲政實踐。
二、“兩次建國”與早期憲法史的路線之爭
在憲法史的敘事中“找回林肯”,當務之急并不是要梳理林肯總統曾面對的憲法問題,而后對這些問題逐一進行法律評析。*這方面的佳作是Daniel Farber, Lincoln’s Co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我們首先要思考作為憲法問題的林肯,而不是林肯的憲法問題,要將林肯作為我們提出問題的方法。也就是說,通過“林肯”,我們找到了進入美國憲法史的一種知識姿態、學術立場和思想方法。這是在憲法史中“找回林肯”的用意所在。
從“一部憲法史”的敘事方法來看,美國憲法所走過的兩百多年的漫長歷程,首先可以分為“林肯之前”與“林肯之后”兩個歷史階段。*關于“一部憲法史”的敘事方法,可參見田雷:《憲法穿越時間:為什么?如何可能?——來自美國的經驗》,載《中外法學》2015年第2期。以林肯1861年至1865年的四年總統任期為分水嶺,此前的歷史階段首先是一種“遙遠的過去”,*關于“美國憲法史作為一種遙遠的過去”,可參見[美]布魯斯·阿克曼:《我們人民:奠基》,汪慶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1頁。而在林肯之后,美國憲法的歷史就邁入了“當代史”的階段——每一代人都生活在林肯再造的新憲法秩序內。當然,“林肯之前”與“林肯之后”這兩個歷史階段并不是涇渭分明的。雖然“林肯之前”所定義的早期憲法史距今遙遠,但并不是僵死的歷史。林肯全部的政治和軍事努力,并不是以憲法革命的姿態消滅內在于美國建國憲法的奴隸制罪惡,而是通過憲法解釋來“挽救聯邦共同體”。“林肯之后”的憲法發展并沒有脫離建國者所規定的憲法之道,這種實踐也決定了美國早期憲法史與現代憲法史相互間的相關性。
若說“超穩定性”和“活憲法”是美國憲法的歷史與實踐呈現出的二元面向,*王希:《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4、45頁。那么以林肯為方法,我們可以發現這兩種在分析意義上相互沖突的面向在美國憲法歷史的實踐中是如何結合成一體的。在“活憲法”的敘事中,林肯是美國早期憲法史的終結者,結束了始終貫穿早期憲法史的兩種路線之爭,在林肯與世長辭之后,重建修正案實現了他所承諾的“自由的新生”。但更應看到的是,林肯的憲法改革并不是對建國憲法的“推倒重來”,他并沒有否定過去,而是用一場歷時四年的內戰解決了1787年制憲者建國的不徹底問題,在這一意義上,林肯是再造共和的“國之子”,是美國漫長建國時刻里“定于一”的釋憲者。*林肯作為“國之子”的傳記,參見Richard Brookhiser, Founders’ Son: A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Basic Books, 2014。因此,活憲法的敘事應當展開在超穩定性的歷史尺度之上。
林肯生于1809年2月12日,在1865年4月15日遇刺身亡,此時距離內戰結束未及一周。因此,一個基本的史實就是,林肯在其有生之年從來沒有看到過憲法文本的變動。1804年,第十二修正案增修進憲法,此時距離林肯降世還有五年的時間;當然林肯也未能活著看到第十三修正案寫入憲法,要等到1865年歲末,這條林肯力推的廢奴修正案才得到最終的批準。但憲法文本的穩定并不意味著這是一段波瀾不驚的憲法史。事實正相反,以1776年《獨立宣言》、1781年《邦聯條款》、1787年費城憲法這段“革命—制憲—建國”三部曲為歷史起點,*美國的憲法史究竟應當從何時起算,是從1787年費城憲法會議,還是以1776年《獨立宣言》為起點,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在本文論述可以回避的歷史問題。根據林肯的理解,美利堅民族誕生于1776年,因為林肯在1863年的葛底斯堡演講,開篇就指出國父在“八十七年前”創建了美國,由此可見林肯認為建國時刻是起始于1776年《獨立宣言》。當然,這個問題的復雜性遠非一個腳注所能處理,本文在討論林肯的聯邦觀時對此略有涉及,總體上是回避這個根本問題的。至1861年內戰爆發,這中間長達八十五年,前后綿延三代人的美國憲法發展歷程,就是本文所界定的美國早期憲法史,也構成了美國這個憲法共同體的漫長建國時刻。由于1787年制憲建國有其不徹底性,最根本的憲法問題在此階段內始終保持著面向未來的開放性,早期憲法史因此是一段“建國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歷史,只是司法中心主義的敘事范式未能發現早期憲法政治的舞臺,因此遮蔽了建國“八十七年以來”驚心動魄的憲法史。
遙想費城當年,建國之父們為了實現政治力量在最大范圍內的團結,在經歷百日的大辯論之后,向北美十三邦人民拿出了一部容納著若干重大妥協的建國文件。費城之所以出現“奇跡”,很大程度上在于制憲者們以妥協求團結的政治策略。*關于“費城奇跡”,可參見[美] 凱瑟琳·德林克·鮑恩:《民主的奇跡:美國憲法制定的127天》,鄭明萱譯,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關于費城會議的全程,可參見[美] 詹姆斯·麥迪遜:《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尹宣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在一場歷時更久、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全民大辯論之后,費城憲法草案得以“批準”,取代1781年《邦聯條款》成為“共同體(the Union)”的根本法。從法理上說,在《邦聯條款》治下的各邦仍保留邦國的原始主權,邦聯只是各主權邦之間的“友愛同盟”,但根據1787年憲法的序言,“我們合眾國人民”是這部憲法的制定者,當憲法草案根據第七條而得到邦聯共同體內九個邦的批準之后,新憲法生效。如果說1787年至1789年制憲有什么革命性,就體現在這種“九邦新造”、“合眾為一”的“建國”。
但革命并不徹底,建國原則也未能貫徹到底,曾有學者指出,美國憲法秩序在其源頭之處就包含著“兩次建國”,第一次建國起始于1776年的《獨立宣言》,終結于1781年獲得批準的《邦聯條款》,這次建國“創建了一個國家同盟(league of nations)”;而第二次建國則發生在1787年至1789年,這次政治發展的斷裂創造了一個“既有聯邦性也有全民性(partly federal but now also national)”的“復合共和國(compound republic)”,更準確地說,是在有限領域內具有全民性的聯邦政府。*Elvin Lim, The Lovers’ Quarrel: The Two Founding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這兩次建國在美國憲法秩序內部植入了兩種針鋒相對的共同體觀念,構成了自此后兩種憲法路線援引的源頭活水。而在本文看來,與其說美國有過兩次建國,不如說美國的建國憲制內包含著兩次制憲:第一次制憲形成了憲法正文的第一至七條,這是由聯邦黨人所主導的建國文件,旨在建成一個歐洲模式的“財政—軍事”國家;第二次制憲就是在費城憲法批準兩年后增修的前十條修正案,這一攬子寫入憲法的修正案,現在被稱為《權利法案》,但在內戰之前,更像是反聯邦黨人以及后來的州權派所主張的州權宣言書,是“主權在州”的憲法合約說的主要文本依據。*關于“權利法案”在內戰前作為州權文獻的存在,參見Akhil Amar, The Bill of Rights: Cre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由此可見,反聯邦黨人并不因“反”這個帽子而成為制憲時刻的政治異議人士,即便是在這個源頭處,他們也是可以同聯邦黨人相提并論的“另外的建國者”。*關于“另外的建國者”,參見Saul Cornell, The Other Founders: Anti-Federalism and the Dissenting Tradition in America, 1788-1828,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當然,無論是兩次建國,還是兩次制憲,在美國第一代建國者的政治實踐中都保持著對立的統一,構成了貫穿于美國早期憲法史內的兩種路線“相愛又相殺(lovers’ quarrel)”的矛盾根源。這種對立的統一在麥迪遜身上得到了最典型的體現:他既是建國憲法的設計師,同時也是“州權法案”的起草者,既寫過《聯邦黨人文集》內最重要的建國綱要,后來又在1798年撰寫了抗擊聯邦黨人暴政立法的《弗吉尼亞宣言》,終成早期憲法史上的州權文獻經典。在此意義上,越是典型的,就越是內在包容著兩種力量之間的張力。
建國憲法實現了“合眾為一”,但主權的合并卻未能實現憲法解釋的“定于一”。美國憲法斗爭的歷史并沒有隨著費城會議的結束而終結,正相反,當立憲政府在1789年開始運轉后,如何解釋建國憲法就構成了政治斗爭反復辯論的問題。因為制憲建國的不徹底,寫入憲法文本內的妥協實質上是將分裂性的政治議題留待未來解決,內戰前的政治辯論表現出了極大的開放性。既然憲法解釋的開放根源于建國的不徹底,那么早期憲法史上的學說之爭首先并不是解釋學意義上的法教義爭議,而是內在于建國憲法秩序的政治傳統之爭,其核心就表現在可以分別上溯至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的兩種路線的反復博弈、斗爭與妥協,直至1860年林肯當選美國總統,這兩種傳統再也無法繼續和平共處在同一秩序內,“于是,戰爭來了”。
如果說兩次建國是在制憲權意義上的斗爭,“不聯合,必定死”的地緣政治格局讓“合眾為一”成為了某種“必然法則”,那么在立憲政府的日常運轉中,兩種政治路線的斗爭就是在制憲權退場后形成的基于憲法的解釋之爭。縱觀美國內戰前的憲法史,兩種路線圍繞著如下三個問題展開了跨越三代人的斗爭。首先,如何理解建國憲法的性質,究竟是一部主權國家的最高法律,還是各個邦國間的國際條約;其次,如何理解這部憲法所創建成的“federal union”的法律性質,是統一不可分裂的單數,還是主權在地方的復數;最后,誰是憲法文件的權威解釋者,是代表全體人民出場的聯邦最高法院,還是作為憲法合約之締約方的各州。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發現,圍繞上述問題的路線之爭不僅是針鋒相對,而且始終一以貫之,在兩種路線內都形成了脈絡清晰的解釋經典。當然,由于執政者要做事,因此時常保持無言,而抗爭者卻需發聲,因此“州權學說”的傳統中涌現出更多的文獻,從1798年杰斐遜和麥迪遜分別起草《肯塔基決議》和《弗吉尼亞決議》以來,可以說是弦歌不絕,直至挑起內戰的南方叛亂分子的“退出”學說。相應,林肯起草總統就職演說時所用的參考文獻,就構成了由聯邦黨人所開啟的國家主義傳統內的解釋經典,如前所述,我們不妨將它們視為在漫長建國時刻對州權領頭羊南卡州的多次答復。
漫長的早期憲法史形成了可以稱之為早期憲法文化的政治心理結構,其至少有三個特點。首先是政治問題的憲法化,因為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著名論斷,我們對這一現象并不陌生,確實如此,內戰前的關鍵政治沖突都要轉化為憲法議題而得到“擺平理順”。*筆者特意用了“擺平理順”這個詞,因為訴諸于憲法并不等于問題即可得到解決。早期憲法史事實正相反,有些時候問題得到解決,但更多的時候只是暫時解決(妥協)或者通過憲法機制而回避問題,正是在此時期,憲法的功能就在于將某些分裂性議題排除在政治過程以外(“不爭論”),從而維持共同體的基本團結,參見霍姆斯教授對內戰前國會“閉嘴法案(gag rules)”的討論,Stephen Holmes, “Gag Rules or the Politics of Omission”, in Jon Elster& Rune Slagstad, eds.,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其次,在親歷費城會議的制憲者相繼辭世之后,我們現在所謂的“原旨主義”憲法解釋方法逐漸出現,成為解釋建國憲法的主流方法。*原旨主義在早期憲法史中的興起,參見田雷:《第二代憲法問題:如何講述美國早期憲法史》,載《環球法律評論》2014年第6期。最后,早期憲法文化是一種極具包容性的“守法”心理結構,美國內戰之前,南方和北方雖然對建國憲法形成了針鋒相對的解釋傳統,但雙方卻共享著同一種憲法文化,甚至1861年的南方叛亂者也還是要回到建國憲法來證明他們退出共同體的行為是合憲的。這種以守法為核心的憲法文化塑造了“以斗爭求團結”的憲政傳統。
林肯當然也不例外,在早期憲法文化的語境內,林肯的憲法解釋談不上原創性,也并未構建或嘗試構建完整周延的解釋體系。林肯之所以成為美國憲法最偉大的解釋者,是因為他出現在兩種解釋傳統再也無法和平共處而要訴諸戰爭的偉大時刻。在此時刻,制憲權重返舞臺,林肯終結了早期憲法史的漫長建國時刻,國家主義的解釋完勝“州權學說”的解釋。在此憲法文化中,林肯的解釋之所以可以“定于一”,并不是在一種理性的政治審議場域內完成了對“州權主義”的“說服”。事實上,林肯總統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兩種傳統究竟誰負誰勝出,這是內戰所提出來的憲法問題,當然要由戰場上的成敗來加以裁決。在此意義上,林肯的憲法實踐是一體兩面的,一方面,林肯是建國憲法秩序的正統解釋者;另一方面,林肯又是重建憲法秩序的奠基人。這種兩面角色也體現在葛底斯堡演講之中,一方面,這篇演講是美國建國“八十七年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另一方面,也是美國新憲法的隱藏序言。*葛底斯堡演講作為新憲法序言,參見George Fletcher, Our Secret Constitution: How Lincoln Redefined American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在林肯之前,建國憲法雖然寫下了不可動搖的立國之本,但立國之本應如何理解,卻始終是開放的,始終要在兩個路線斗爭場域內接受辯論,林肯總統正是此意義上的釋憲者;而在林肯之后,林肯對建國憲法的解釋就構成了美國新憲法秩序的根基,是不容常規政治過程加以挑戰、辯論和變革的。
三、林肯的聯邦(共同體)觀
(一)南部邦聯的“州權學說”
在早期憲法史的脈絡內,南方蓄奴州于1860年冬退出聯邦共同體,并不是歷史在林肯當選總統后發生了突然的轉向或斷裂,而是歷史的一種延續。從麥迪遜和杰斐遜在1798年反擊《外僑與反煽動法》時所提出的“干預(interposition)”說,到南卡州在1830年代初對抗聯邦關稅時的“廢止(nullification)”說,1861年的“退出(secession)”不過只是“州權學說”邏輯推演的必然結論。這是在州權邏輯上邁出的一小步(當然,也正是這一小步,完成從憲法框架內抗爭到踢開憲法鬧革命的性質之變,因此是跨越雷池的一大步)。*憲法不可能容納退出權,參見Cass Sunste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Secession”, 58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633-670, (1991)。自建國以來,共存于同一屋檐下的兩種制度在這時發生了根本的決裂。事實上,南方分裂分子甚至不難從《聯邦黨人文集》這部建國綱要中找到支持“退出”的只言片語,歷史的延續性由此可見一斑:
我們的政治制度立基于如下的公理:在任何可能發生的情形內,各邦/州的政府將提供充足的保障,制止全國政府的權力入侵公眾的自由。民選機構目光銳利,他們比普通人民更有能力識破掩藏在種種借口下的篡權陰謀。各邦議會將有更有效的信息手段。它們可以發現遠方的危險;由于擁有全部的政權機構,深受人民的信任,它們可以當即采用常規的反抗計劃,由此調動起社區內的所有資源。各邦議會之間還便于溝通,為了保護它們共同的自由而將它們的力量聯合起來。*還要指出,這篇出自最主張中央集權的漢密爾頓的手筆。參見[美] 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39頁。正文的引文對照英文原文在商務版基礎了進行上較大程度的調整。
更不必說,任何一篇“州權主義”脈絡內的解釋經典,在1861年都可以為南方分裂分子提供證明退出聯邦的國父指南。在內戰第一槍打響后,南部邦聯總統杰斐遜·戴維斯就闡述過一種極端的“州權學說”。根據這位“好戰叛亂者”的解釋,*James McPherson, Embattled Rebel: Jefferson Davis as Commander in Chief, Penguin Press, 2014.自1776年《獨立宣言》起,北美各邦結成了一個以抗擊英帝國為目的的“同盟協約”,經過1781年《邦聯條款》,進一步形成了一個各邦明文保留主權的“友愛同盟”。1787年制憲,誠然是“為了形成一個更完善的共同體”,但1787年憲法僅在批準憲法的邦內生效,就證明了這部憲法只是“一部在獨立各邦之間的合約”。憲法第十修正案也明文規定:憲法未授予合眾國、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這就是內戰前“州權學說”中主流的“合約理論”。根據合約論,憲法只是一部各主權州之間訂立的合約,因此那種認為這部憲法創設了一個“中央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的觀點,只是北方的異端邪說,“在北方人的心靈中,憲法原則已經遭到全盤徹底的污染”。林肯當選總統就意味著北方人“違約”在先,廢除奴隸制“會剝奪數十億計價值的財產”,正是因為北方在先的違約,南方各州才援引“自1798年以來的憲法信條”——“每一個州,作為最后的救濟,都是特別法官,判斷它所承受的不公以及可用救濟的模式和措施”;“顯而易見,根據萬國法,此原則是適用于獨立主權國家間關系的公理,包括那些根據憲法合約聯合起來的國家”。簡言之,美國的建國憲法,在戴維斯看來,不過只是主權國家間的合約,在此框架下,各邦在憲法生效后仍保留主權,正因此各邦在1787年可以合則來,當然在1861年就可以選擇不合則去。*戴維斯的論述,可參見戴維斯在1861年4月29日對南部邦聯臨時國會的咨文;戴維斯的副手、南部邦聯副總統亞歷山大·斯蒂芬斯,后又提出一個更系統的闡釋:退出是“邦國與生俱來的權利”,表現為自我宣布自此后不以任何方式受合約的約束,參見斯蒂芬斯的《近期國家間戰爭的憲法解讀》(A Constitutional View of the Late War between the States),參見Daniel Farber, Lincoln’s Co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77-78。
(二)林肯在總統就職演說中的回應
在1861年3月4日發表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林肯對南方諸州是否有權單方面退出的問題做出回答,萬眾矚目之下,林肯的答案是不容置疑的:聯邦共同體是“永續”的,各州在聯邦內并無主權可言(甚至除德克薩斯以外,各州從來就沒有過主權),單方面的退出就是踢開憲法鬧叛亂。回到早期憲法史的語境內,林肯的就職演說不僅是對南部邦聯分子在那個當下的回應,也標志著主要以南方為基地的“州權學說”最終走向崩潰的第一步。*內戰前,“州權學說”的大本營在南方,但并不完全如此,關于北方的“州權學說”,可參見劉晗:《民主共和與國家統一:美國早期憲政中的北方分離運動》,載《環球法律評論》2011年第6期。如果用現代法律解釋理論來分析林肯的文本,我們可以發現,林肯在論證南方無權單方面退出永續聯邦這個結論的過程中,至少采用了四種法律解釋的方法。
林肯總統首先訴諸結構解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推理是立基于“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和憲法”的。林肯一上來就開宗明義,宣布“各州之間的共同體是永續的”。或許因為林肯未能在憲法文本內發現載明“永續性”的條款,所以林肯在此部分并沒有直接引用憲法的具體條款,整個推理更多的是基于林肯所講的“普遍法則”,因此是一種結構性的論證。比如林肯講道:“在此可以有把握地說,任何一個正規的政府,在其組織法內都不曾有過規定其自身終結的條款。”換言之,制憲者通過憲法而建構起一個可統治的政府,其中不言自明的含義就是要讓這個立憲政府與世長存。而且,林肯的論證并沒有全部局限在美國憲法,而是擴展到了立憲政府的普遍原理:“永續性,在所有民族政府的根本法中,即便不是明文表達的,也是不言而喻的(implied)。”正是以此判斷,林肯希望向聽眾傳達出他沒有明文表達的言下之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美國政府的永續性隱藏在憲法文本之內。*[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81頁。
在此之后,林肯嘗試以歷史解釋來加強前述的結構論證:“我們發現,在法律思考中共同體是永續性的這一命題,也為共同體自身的歷史所確認。”如果說傳統上認為美國是一個因憲法而聯合起來的政治民族(也因此憲法在前,美國在后),那么林肯的論證則起始于一個有違常識的命題:“共同體要遠早于聯邦憲法(The Union is much older than the Constitution)。”林肯對這一反常識的命題進行了簡短的闡釋:
事實上,共同體是由1774年的《聯合條例》所組成的。通過1776年的《獨立宣言》,共同體得到延續并且臻于成熟。1778年的《邦聯條款》讓共同體更臻于成熟,當時參與的十三個邦都信誓旦旦保證共同體應是永續的。而最終,在1787年,憲法得以訂立,其所表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形成一個更完善的聯邦共同體”。*[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182頁。
由此可見,林肯將共同體的生成歷史理解為一個“四步走”的過程。共同體的誕生甚至可追溯至1776年之前——少為人知的1774年《聯合條例》,在此之后,從《獨立宣言》、《邦聯條款》,再到1787年憲法,每一部憲制性文件都代表著對這個誕生于1774年的“共同體”又一次的完善,由此勾勒出一種進步史觀的歷史敘事。而在這四步走的歷史過程中,最有說服力的環節存在于《邦聯條款》與聯邦憲法之間的關系。因為《邦聯條款》明文宣布“共同體是永續的”,而1787年憲法在序言內又開宗明義:我們人民制憲,首要目標就是要“形成一個更完美的(聯邦)共同體(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毋庸置疑,“更完美”顯然是要在“永續”基礎之上的更完美,因此由1787年憲法所創立的聯邦共同體就自然是永續的,否則“更完美”就是毫無意義的。
林肯所用的第三種論證是在實踐層面上對南方反叛者的警告,因此可歸為現代法律解釋中的結果主義/實用主義。其邏輯如下:如果共同體內的少數人確有退出的權利,那么少數人中還有少數人,從邏輯上講,少數人的退出權可以不斷延伸下去,直至共同體完全崩潰,分解為相互獨立的原子式個人。林肯反問南部邦聯:“正如當下聯邦的多個部分正在主張從聯邦退出一樣,一兩年后,新邦聯內部難道不會出現再一次退出的任性要求?”林肯的警告無疑是對南方謀求獨立的致命一擊:南方如果主張退出權,那么就必定要承認南方內部的少數人也有退出權,這樣的話,退出權會讓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如多米諾骨牌一樣崩潰,或者說,承認退出權的共同體是無法建立起有效政府的,林肯在演說中有句話直指問題之根本:“顯而易見,退出的核心思想本質上就是無政府。”*[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184、185頁。
最后,林肯訴諸地緣政治的論證來反對南方的分裂之舉。林肯在此部分指出:“就自然條件而講,我們不能分離。我們既不能把各自的地區分別搬開,也無法在它們之間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墻。夫妻可以離婚,然后分道揚鑣,再無往來;但我們國家的各組成部分卻做不到這一點。”*[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186頁。在早期憲法史的語境內,林肯的地緣主義論證接續了聯邦黨人關于美國為什么要通過憲法合眾為一的闡釋。直至1862年12月1日,林肯總統還在致國會的咨文內從地緣邏輯來解釋為什么美國不可分裂:“就它的一切適應力和自然傾向來說,只能聯合,不能分裂。事實上,不管分裂將會流多少血,損失多少財富,它總是非很快重新聯合不可。”*[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57頁。而地緣政治的憲法論證,其第一原則就是“不聯合,必定死”。
當然,林肯在演講中也特別回應了南方州權傳統一貫主張的合約理論。在林肯看來,即便承認合約論,認為聯邦政府不是一個適格的政府,而只是各州的合約聯盟,那么,“作為合約,非經全體締約方的同意,難道就能和平地取消嗎”?*[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81頁。換言之,南部諸州單方面退出共同體,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違約”乃至“毀約”。也許存在著合法的退出程序,但必定不是當時南方各州所進行的這種單方面退出。*在建國憲法框架內,是否存在著合法退出的程序,比如聯邦共同體內所有州都同意解散聯邦,則退出是否就是合法的,基于林肯文本的憲法分析,參見Akhil Amar,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American Union”, 200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109-1133 (2001)。
(三)解析林肯的聯邦觀
當林肯向南方邦聯分子論證退出違憲時,林肯表現出了內在于美國早期憲法文化的連續性。亨利·克萊是美國第二代政治家中的“三杰”之一,也是林肯畢生的政治偶像,林肯口中的“政治家的完美典范”,我們不難在林肯的憲法解釋中發現他與克萊之間的傳承。克萊生于1777年,1852年辭世,史稱“保全聯邦共同體”的1850年大妥協就出自于克萊之手。1850年2月5日,克萊在參議院引入他的一攬子妥協方案時曾發表演講——這是林肯起草就職演說時曾參考的解釋經典。在持續兩天、長達五個小時的演講中,克萊指出,十三個州最初之所以制定憲法,不僅是為了制憲那代人,而且是為了自此后無窮匱也的子子孫孫。憲法好比在私生活內不可解體的婚姻。“讓我們復述夫妻之間那些話:我們各自都有過錯;只要是人性的,就沒什么是完美無缺的;因此讓我們善待對方,寬容克制;讓我們生活在幸福與和平之中”。*轉引自Mark Neely, Jr., Lincoln and the Triumph of the Nation: Constitutional Conflict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p. 43。根據克萊所述,退出必定意味著戰爭,而且聯邦在南北之間的分離最終不會只是分裂為兩個“邦聯”,分離是一種開啟后就無法遏制的分裂過程,最終南方和北方邦聯也會各自分裂為更小的邦聯。北美新世界由此就步入歐洲舊大陸的戰國命運,這種政治格局將會帶來“某個愷撒或拿破侖”,摧毀聯邦分裂后各個地域的全部自由。*轉引自Fergus Bordewich, America’s Great Debate: Henry Clay, Stephen A. Douglas, and the Compromise That Preserved the Union, Simon & Schuster, 2013, p. 143。從林肯的就職演說中,我們可以找到克萊以及國家主義脈絡內的各位先賢的身影,林肯的命題及其論證并沒有原創性,當然如前所述,林肯也從未主張過自己的原創性。
如果說林肯在何處表現出對國家主義傳統的旗幟鮮明的突破,那么就是林肯突破了國家誕生于制憲這一主流敘事,而將共同體的形成追溯至1774年《聯合條款》。在兩年半后的葛底斯堡演講中,林肯用“八十七年前”的表述將美利堅民族的誕生回溯至1776年《獨立宣言》,這兩年的差距對于本文來說無關要旨,因為無論是1774年,還是1776年,都突破了國家主義學說將1787年至1789年理解為“統一憲政立國”的建國時刻的解釋。根據傳統的國家主義學說,1776年的《獨立宣言》只不過是宣布了13個英屬殖民地各自分別獨立為主權邦國,即便是1781年《邦聯條款》也不過只是創設了一個“聯合國在北美”的對外同盟,只有在1787年憲法得以批準生效之后,各邦才由主權邦變成了至少讓渡出部分主權的地方州,而且這種讓渡是一種不可逆的過程——一經讓渡,不可再收回。這種正統的解釋,約翰·馬歇爾曾在1824年吉本斯訴奧格登的判詞中有過闡釋:
有人曾提到在聯邦憲法形成之前各邦/州的政治處境。據說,它們都有主權,是完全獨立的,只是通過一個聯盟(league)才將彼此聯系起來。事實確實如此。但是,當這些聯合起來的主權將它們的聯盟轉變為一個政府(government)時,當它們將它們的大使會議(受委托就共同事務進行審議,并且建議具有普遍效用的措施)轉變為一個立法機關(授權就最令人關注的事項制定法律),各邦/州所呈現的整個性質就經歷了一次轉變。*Gibbons v. Ogden 22 U.S. 1 (1824),轉引自Akhil Amar, America’s Constitution: A Biography, Random House, 2005, p. 39。
馬歇爾曾親歷美國“革命—制憲—建國”的歷史,在聯邦黨已經解體的時期,他為下一代人提供了更準確的建國史敘述。相比之下,林肯認為合眾國各州從未享有主權地位,確實是與史不符的。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理解林肯總統聯邦觀的“錯誤”?生活在一個半世紀后的我們能否對之進行一種所謂“同情式的理解”?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將美國建國追溯至1776年甚至1774年,并不是林肯在闡釋美國憲法史時所犯下的唯一錯誤。如果我們用現代法律科學的標準來檢驗林肯的解釋,那么就可以發現林肯的解釋在很多地方并不周延,比如,在面對1781年《邦聯條款》時,林肯只抓住“永續性”條款,而對“友愛同盟”和“各邦保留主權”的規定置之不理。但問題在于,我們在今天旁觀這段一個半世紀之前的歷史,應當比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林肯看得更清楚:由于制憲建國本身的不徹底,由于兩條路線在早期憲法史上形成了傳統之爭,林肯的解釋是無法形成法律形式主義所要求的“科學性”和“中立性”的,換言之,如何解讀美國的早期憲法史,身處林肯所處的那個當下,并不是一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就能回答出來的問題。我們今天可以一眼發現林肯的“錯誤”,在此意義上,也是林肯所書寫的歷史添附在早期憲法史上的錯誤,正是林肯總統在兩條路線之間的“定于一”讓美國憲法發展走上了如今看起來進步的道路,也正是林肯總統在憲法實踐上的成功促成了他在憲法解釋上的“錯誤”。換言之,林肯上述的錯誤,是一個在兩百年憲法史的敘事結構內才存在的錯誤,身處林肯所處的那個歷史十字路口,尚且不成為錯誤,因為問題的答案尚不確定。
其次,林肯的憲法解釋并不是發生在以整全融貫為標準的學術場域,而是存在于一個事關聯邦共同體生死存亡的政治領域,因此具有一種回應當下問題的現場感。林肯總統的聽眾并沒有我們在一個半世紀后的從容和事不關己的超然。對于林肯的現場聽眾而言,他們對比的是林肯總統的解釋與另一位總統戴維斯的解釋,因此,有意義的問題并不是林肯的解釋是否符合美國建國的憲法歷史,而是林肯有沒有回答即將爆發的內戰所拋出的核心問題。就此而言,林肯的建國故事也許有他自己的視角偏差,但他關于各州從未享有主權的結論,在1861年的歷史關頭確實是一個正確的解釋,至少是比戴維斯所代表的南方道路更正確的解釋。
最后,我們還應當思考為什么林肯會形成這種“各州從未有主權,共同體先于憲法”的建國史觀。在這個問題上,阿瑪教授曾經給出過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解釋,林肯的憲法史觀形成于林肯所身處的政治環境,特別是其成長的經歷。做一簡單的對比,約翰·馬歇爾是親歷獨立戰爭的革命者,他來自初建聯邦共同體的十三州內最關鍵的弗吉尼亞,弗吉尼亞無可置疑地是先于聯邦共同體而存在的,因此確實是弗吉尼亞同其他十二個邦通過憲法創建了聯邦。“但是,從林肯所成長的地域來說,林肯所看到的是一個不同的國家及其歷史。聯邦共同體孕育出了林肯的家鄉州伊利諾伊以及印第安納,林肯到達印第安納時,正值其從聯邦領地成長為州的時刻,此后在那里度過了少年的大部分時光。正如林肯所見,‘共同體先于任何一州;事實上,正是共同體創造了作為州而存在的各州”。*Akhil Amar, America’s Constitution: A Biography, Random House, 2005, p. 275.就此而言,如果說馬歇爾的憲法建國史觀是原初十三州視角內的解釋,那么林肯的“共同體先于憲法”命題則是西部領地的憲法史觀。
四、林肯的民主觀
(一)從共和到民主
民主是個好東西嗎?自建國一代人到林肯生活的時代,這個問題的答案經歷了一場緩慢但深刻的變革,這是我們在討論林肯民主觀首先要進入的意識形態語境。在1787年那代人看來,民主是一種邪惡的政體,他們所創建的是一個立憲共和國,而不是純粹的民主制。“democracy”這個詞并沒有出現在1787年憲法的正文內,而憲法第四條第四款卻是“共和條款”,這一在內戰斗爭中至為關鍵但在今天卻被人遺忘的條款規定:“合眾國保證本聯邦各州實行共和政體(republic form of government)”。在建國之父的思想世界中,共和與民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
而到了1830年代中期,也是托克維爾出版《論美國的民主》的同時期,諾阿·韋伯斯特,這位《韋氏英語詞典》的編撰者,正因席卷共和國的民主浪潮而心生恐懼。韋伯斯特出生于1758年,此時已是近八十歲的高齡,他曾經這樣告訴身邊的助理,如果在美國革命時就可以預知民主在革命后的泛濫,那么他當初就不會參與愛國者的革命事業。更有意思的是,韋伯斯特這位“美國學術和教育之父”甚至設計了多種挽救共和國免于民主暴政的方案,包括將選民的投票年齡提高至45歲;按照年齡和財富將全體選民分為兩個階級,再由每個階級選出自己在國會內的議院。但韋伯斯特原本的警世恒言,在1830年代卻落得個無人問津的結局。這個故事選自《美國民主的興起:從杰斐遜到林肯》,歷史學家威倫茨以此歷史片段作為其鴻篇巨制的開篇,想必正是認為這則故事折射出了民主概念在代際轉換過程中發生的巨變。因不可抗拒之民主浪潮而心生恐懼絕望的,絕不是韋伯斯特一人,而是韋伯斯特所身處的那一代人的政治態度。1837年夏,詹姆斯·肯特(生于1763年)——《美國法釋義》的編者,被譽為“美國的布萊克斯通”——參加了一次老派紳士的聚會,與會者大談“數人頭民主和激進主義”的破壞力,那時候,平民總統杰克遜剛剛結束其歷時八年的任期,肯特對“杰克遜主義的恐怖學說及其影響力”可謂心有余悸。在威倫茨看來,肯特這代人正是托克維爾訪美年代時無法理解民主浪潮的“政治余孽(political relic)”。*See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p. 4.
而對于林肯這代出生于后革命時代的政治家來說,共和與民主之間的概念差異已經抹平,從林肯的政治演講中,我們無法感受到前一代人對民主如洪水猛獸般的恐懼,也看不到如何遏制民主浪潮以挽救立憲共和國的藥方。正相反,從林肯的演說文本中,我們可以發現,民主與立憲共和在林肯的思維中是完全可以等同的政體設計。1861年7月4日,國慶日,林肯向因內戰爆發而召開特別會議的第三十七屆國會發表演講,在此次演講中,林肯概括了這場內戰向美國乃至全人類的政治社會提出的一個憲法問題,林肯是這么表述這個問題的:“whether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or a democracy—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same people——can, or cannot, maintain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gainst its own domestic foes。”*Steven Smith edited,The Writings of Abraham Lincoln, edited by Steven Sm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37-338.在這里引用英文原文,首先是借用語法的約定俗成去發現林肯的思想世界,而對這問題所體現出的林肯民主觀則留待后文解讀。從英文的語法結構上,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兩點判斷。首先,林肯所理解的民主,就是“民有并且民治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same people),破折號可以清楚表明“民有并且民治的政府”是林肯對“民主”的基本定義;其次,在這里也更重要的是,林肯用“or”這個連詞來連接起“立憲共和國(constitutional republic)”和“民主”,由此可見,立憲共和國和民主這兩個概念在林肯的思考中是可以相互替換的,至少是功能等價的。
(二)有限多數決的原則
林肯將民主理解為“民有且民治”,但這并沒有回答到底什么是民主的問題,不過是將問題又以另一個方式重新表述出來。如要回答林肯民主觀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回到林肯的經典演說。事實上,同樣是在1861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林肯在論證了建國憲法不允許地方單元單方面退出之后,曾蓋棺論定地指出“退出的核心思想本質上就是無政府”。緊接著這一判斷,林肯進行了一段隱微的民主論述:
多數人——首先受到憲法分權和限權的制約,其次總是可以隨著民意和民情的審慎變化而輕松變換——是自由民族的唯一真正主權。無論是誰,只要它否定多數人的主權,就必定會滑向無政府或者專制統治。全體一致是不可能的,少數人的統治,如果作為一種永久的制度安排,也是完全不能容許的;正因此,只要否定了多數人原則,那么擺在我們面前的就只有無政府或某種形式的專制統治了。*[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85頁。
如何理解林肯的這段話,我們也許可以從后往前讀。首先在林肯看來,在美國這種“自由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全體一致”是一個可望但不可及的幻想。換言之,自由社會內必定會有意見的沖突,而且要容忍健康的異見。正如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內所論,共和體制無法擺脫黨爭,因為消除黨爭首先要消滅自由,但若是為了擺脫黨爭而限制自由,那么就如同為了防止火災而抽去空氣中的氧氣一樣,是荒唐地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既然無法做到全體一致,那么政治過程如何做決策,就是考驗民主原則的試金石。在林肯看來,少數人統治是不可容許的,不過也應看到,林肯為“少數人統治”加上了“作為永久的制度安排”的限定,至少從語義上理解,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某些例外情況下,少數人統治作為一種過渡性的安排是可以允許的。到此為止,林肯用一個否定式的表達給出了自己的結論,既然要有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無政府因此并不可取),同時少數人統治是一種專制主義,那么美國的民主政府要以“多數人原則”為基礎。
因此,林肯從一開始就指出:“多數人……是自由民族的唯一真正主權。”換言之,民主是一個“多數人說了算”的政體,但林肯民主觀的復雜性在于,即便是根據語言表述的表層含義,我們也可以看到,多數人并不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事務上都說了算的。林肯在原文中為“多數人”加了兩個后置定語,意在為多數人統治這一基本原則施加來自兩個方向上的限制,就此而言,林肯所理解的民主(也即立憲共和國)是一種有限多數決的原則。第一個限定是“受到憲法分權和限權的制約(held in restraint by constitutional checks, and limitations)”,也就是說,多數人并不是制憲權意義上的主權者,要受到憲法的制約,多數人民主的前提是立憲政治。這正體現了林肯將“民主”與“立憲共和國”相提并論的主要根據。在時間維度內,憲政是一種源自于過去的約束,是歷史上的立憲者對后來的每一代人的約束。第二個限定是“總是可以隨著民意和民情的審慎變化而輕松變換(always changing easily, with deliberate changes of popular opinions and sentiments)”。現在是多數,并不意味著永遠都是多數,多數人并不是僵化不變的鐵板一塊,隨著民意和民情的變化,多數人這個群體也會發生變化。如果第一種限定是來自過去因此不可輕易改變的規范制約,那么第二種限定就是要面向未來而保持開放,當然健康的民意和民情一方面不可能封閉僵化,另一方面也不可能瞬息萬變,如林肯所言,變化應是“審慎的”,而至于如何測度社會的民意或民情發生了審慎的變化,主要指標就是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在此意義上,總統所代表的那個多數人的政治授命也就是總統在選舉中所得到的四年授權。
回到林肯就職演說的語境,此時南北雙方雖然已經劍拔弩張,但內戰的第一槍還沒有打響,有限多數決作為民主原則的提出在這時就傳達出林肯總統一手硬、一手軟的政治策略。多數人原則首先表達出林肯強硬而不妥協的立場:既然林肯是全國選民選出的多數總統,那么南方蓄奴州就要承認自己在選票箱前的失敗,現在南方鬧退出,就是用子彈來替代選票,*在1861年國慶日對國會的演講中,林肯總統曾闡釋這一觀點:“現在是時候由美國人民向全世界證明,他們有能力組織起一場公正的選舉,也就有能力去鎮壓一場叛亂——選票將正當地并且和平地替代子彈;一旦選票公正地、合乎憲法地做出了自己的決定,就休想成功地訴諸子彈……這將是和平的一個偉大教訓:它教育人民,不能通過選舉而得到的東西,也休想通過一場戰爭而獲得——教育所有人,成為戰爭發起者是多么的愚蠢。”[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93頁。是對多數人原則的顛覆。四個月后,當內戰正式爆發之后,林肯也曾對國會講過,南方宣布退出是將自己變為民主國家的“內部敵人”,因此,退出不僅是違憲的,也是對民主的否定,會導向林肯所說的“無政府”。在此基礎上,林肯從兩個面向上限定多數人原則,目的就在于安撫南方,希望他們冷靜下來,三思后行:“內戰這一重大議題,現在全系于你們的手中……而并非掌握在我手中。政府將不會攻擊你們。只要你們自己不做侵略者,沖突必可避免。”*[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88頁。建國憲法是保護奴隸制的,而多數政府也無法突破憲法作為先定承諾的約束,這也就意味著林肯所曾多次講過的觀點——他既無權也沒有意圖去干預蓄奴州的奴隸制,既然如此,南方在退出時所主張的多數人廢奴暴政就是虛偽的——是站不住腳的。不僅如此,多數人也會隨民意和民情而變,任何一屆政府只是受到四年的委托,只是在四年內的多數。在就職演說中,林肯曾向南部邦聯拋出最后的橄欖枝:“通過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政府設計,美國人民巧妙地僅授予他們的公務人員以微乎其微的破壞權力;而且同樣智慧地規定了這一有限授權每隔很短的間隔就要回歸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人民可以保持他們的美德和警覺,沒有任何一屆政府,無論有多么邪惡或愚蠢,可以在短短四年期間對政府體制造成極其嚴重的傷害。”*[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87、188頁。言下之意,南方只要在共同體內再等四年,完全可以把共和黨以及他本人選下去,而不必在眼下訴諸內戰這種撕裂共同體的既違憲又反民主的行徑。
(三)民主的“致命缺陷”
林肯始終認為,美國的立憲民主政府是一場“試驗”。建國者成功地建立起了民有、民治的政府,而在建國者逝去后,當下這代人的任務就是要將他們所繼承的政府傳承下去,如青年林肯在1838年1月一篇演講的題目所示,要讓“我國政治制度永世長存”。*[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3-12頁。由此可見,林肯對民主政府之生命力的思考總是展開在一種代際交接的語境內。在赴華盛頓就職的火車巡回途中,林肯就這樣表述他所面對的問題:“這個國家的統一和自由能保持到最后一代人嗎?”*[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173頁。而那種“比華盛頓當年擔負的還更艱巨”的任務,就是“使憲法、聯邦和人民的自由傳諸永遠”。*[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177頁。可以說,如何在代際交接的過程中保存聯邦共同體,是林肯要探索的保持民主生命力的憲法之道。
之所以要思考民主政府的生命力這個問題,在林肯看來,正是因為內戰暴露出了立憲共和國的“先天性的致命缺陷”。自青年時代,林肯就認為,共和國作為自由的國家,其危險必定發生于內部:“如果危險果真來臨,它必定在我們內部產生,而不可能來自外部。如果毀滅是我們的命數,那么始作俑者必然是我們自己……作為一個自由人的民族,我們必須永世長存,不然就自殺身亡。”*[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4頁。而內戰就昭示著“自殺身亡”的危險,正是在此意義上,內戰向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民主國家提出了一個事關生死存亡的憲制問題,1861年國慶日,林肯面對國會議員表述出這個問題:“而這個議題所涉及的不只是合眾國的命運。它還向人類的大家庭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立憲共和國,一個民有并且民治的民主政府,是否有能力維持其領土完整,抵抗它的內部敵人。”*[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191頁。在葛底斯堡演講中,林肯也特別明確指出,這次偉大的戰爭所要檢驗的是,“我們的國家,以及任何奠基在自由和平等理念上的國家,能否長久存在下去”,還是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將會“從地球上消亡”。*[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278頁。
在林肯看來,國家是由領土、人民和法律所共同組成,而在國家的三元素中,領土是唯一具有持續性的那部分,“一代人逝去,另一代人降臨,但領土卻永遠存在下去”。*[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254頁。現在南方的政治訴求,事實上就是少數人在心懷不滿時即可任性地“分疆裂土”,若是此先例一開,那么民主政治就將包含著一個不可承受的自我分裂。也是在此邏輯上,林肯敏銳地意識到內戰的勝負將決定民主在世界范圍內的命運。林肯的多數民主理念是否可以成立,取決于聯邦軍隊在戰場上的勝負。聯邦取得勝利就可以建立起一個先例,也即少數人連同領土單方面退出聯邦,不僅是違反憲法的叛亂,還是任性的、反民主的少數人專制。反之,如果南方取得戰場上的勝利,就意味著少數人將劫持共和政體的主權——他們只要心懷不滿就會放棄憲法框架內的抗爭,而選擇踢開憲法鬧革命,這不僅是憲政的失敗,也是民主的失敗,也將宣告林肯所說的“人世間最后、最好的希望”*[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57頁。不過是一場噩夢而已。
“難道一個政府要么就必須強大到威脅自己人民的權利,要么就必定軟弱到無力維持自己的生存嗎”?*[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191頁。這是林肯在內戰伊始所提出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仍在求索的永恒且普遍的難題。
五、林肯的法治觀
(一)守法者林肯
林肯在還未當選總統時有過一句名言:“分裂之屋,無力自立。”而梳理林肯關于法治問題的論述,那么首先浮現的印象就是林肯也陷入了在“守法者”與“違法者”之間的自我分裂,而我們的問題就是這個看起來自我分裂的林肯是否可以自我站立起來。
守法者林肯的法治觀,在1838年的《我國政治制度永世長存》的演講中有一個完整的闡釋。做此演講時,林肯還未滿29歲,剛取得律師資格,面對著斯普林菲爾德青年學會的聽眾,林肯在演講中闡釋了新形勢下的新問題,展示了問題的解決之道。所謂新形勢,就是建國者逝去,而且獨立戰爭的革命經驗也漸成蒼白的記憶;正是因此,共和國內部出現了暴民政治的問題:人民的眼中越來越沒有法律,越來越以粗暴的情感來替代理性的法律,由于法律無法得到實施,人民不再愛戴政府——但在林肯看來,人民對政府的深厚感情,正是后革命時代共和制政府最堅強的堡壘。而林肯所提出的解決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讓憲法和法律成為自由民族的政治宗教:
讓每個美國人,每個自由的熱愛者,每一個子孫后代的祝福者,以革命的鮮血起誓,決不絲毫違反國家的法律,也決不容許他人違反法律。如同1776年的愛國者對《獨立宣言》的支持,每一個美國人也要用他的生命、財產和神圣的聲譽起誓,捍衛憲法和法律——每一個美國人都要記住,違反法律,就是踐踏父親的鮮血,就是撕裂他自己以及子女的自由人格。讓每一位美國母親,對在她膝上牙牙學語的嬰兒,灌輸對法律的尊重——讓法律在小學、中學和大學得到講授——讓法律寫進識字課本、綴字課本和歷本——讓法律在布道壇上布講,在議會廳中宣布,在法庭內執行。簡言之,讓尊重法律成為民族的政治宗教,讓男女老少、富人窮人、各種語言、膚色和階層的人們在法律的祭壇上獻身,永不停息。*[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8頁。
如果說以上是林肯動之以情的守法宣言,要以憲法和法律作為后革命時代共和國的理性支柱,那么林肯緊接著還有一段曉之以理的分析。在這段理性分析中,林肯探討了如何對待“壞法律”的問題。在林肯看來,嚴守所有法律并不意味著不存在壞法律。“雖然壞的法律——如果有的話——必須盡快廢除,但是在它們繼續生效的時候,為示范起見,還是應該嚴格遵守”。*[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第8頁。如果用現代法律理論的專業術語來說,林肯在這里的法律觀可以說是“惡法亦法”,由是觀之,林肯不僅是一位守法者,還是一位嚴格的守法主義者。
(二)違法者林肯
但林肯總統向來背負著違法者的惡名。在四年戰時總統的任期內,林肯做出了很多史無前例或打破先例的行為,最著名的包括:取消普通法傳統的人身保護令狀;在民事法院運轉的地區進行軍事審判;甚至解放者林肯是否有權發布《解放奴隸宣言》,也是一個眾說紛紜的“當代史”問題。根據近期譯成中文出版的《憲法專政》一書,林肯總統在內戰伊始所采取的一系列行為被認為“在美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后”,而且在綜合考慮后,“不容否認的是,他確實在推行一系列激進的、專政性的、具有違憲嫌疑的行動”。違法者林肯也因此有了一頂“憲法專政官”的帽子。*參見[美]羅斯托:《憲法專政:現代民主國家中的危機政府》,孟濤譯,華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頁。
不僅如此,林肯甚至親口承認過自己的行為有違憲法,這也許是后人在歷史法庭內指證林肯違反的最有利證供。1864年4月4日,林肯曾在信內這樣寫道:“根據一般法則,生命和四肢都必須得到保護。然而在很多時候,為了挽救生命,不得不把某個肢體切除;但是,如果為了保全肢體而付出生命,就是愚蠢之舉。我認為,有些措施,原本是違反憲法的,現在由于它們變成了保護民族并由此保護憲法的必需手段,因此變得合法。”*當然,林肯緊接著說:“對也好,錯也罷,我所采取的就是這種立場,現在公開宣布。”[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82、283頁。白紙黑字,林肯自己也承認他的有些措施“本來是不符合憲法的”,簡直不容后世人為其翻案!更何況,林肯建立在這種邏輯上的論述并非僅此一例。在答復塔尼大法官有關人身保護令狀的司法意見書時,林肯總統這樣指出:“把問題說的更直接些,為了防止一部法律受到侵犯,是否必須使這部法律以外的所有法律都無法得到執行,要使政府自身都分崩離析嗎?即便是在這種情形內,當我們相信無視這一部法律就有可能保住政府,現在卻任由政府被顛覆,這豈不是違背了總統誓詞嗎?”*正文這句話出自林肯1861年7月4日的國會咨文,商務印書館版《林肯選集》對這篇演講只是摘譯,其中未包括正文的句子,正文為作者自己根據英語原本譯出。
無需列舉更多,對于熟悉西方現代理論的讀者來說,一個施米特意義上的法外主權者的形象已經呼之欲出。在為自己辯護時,林肯首先一反常態地承認自己的行為確實有違形式法律,但在自證違法之后,林肯很快就引入了另一種合法性的論證資源,換言之,林肯承認他違反了白紙黑字的法律,也卻主張自己的違法是為了保全字里行間的法律。這種邏輯就是,內戰讓國家進入了事關生死存亡的例外時間,憲法乃至國家都隨時可能土崩瓦解,在此時刻就應該懸置憲法,至少不能讓憲法成為束縛政府打擊敵人之手腳的緊身衣,而在此危機時刻,最重要的法律義務就是保存國家和憲法,形式上的法律應當讓位于因果關系的必然法則。如林肯在答復為何他有權解放黑人奴隸時所言:“作為陸軍和海軍的總司令,在戰爭時期,我認為我有權采取可以最有效地克敵制勝的任何措施。”*[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40頁。換言之,只要可以克敵制勝,那么做任何事都是合“法”的。
(三)在實踐中的統一
為什么會出現前述兩個林肯,第一個林肯是虔誠的守法主義者,主張即便是如奴隸制這樣的惡法——只要仍是法律——就應當得到遵守;而第二個林肯則是結果至上的實用主義者,認為在國家危機時刻,在形式法律之上和之外還有保全共同體所必須遵循的“必然法則”。兩個林肯之間的緊張對立并不是我們后世學者“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且嚴肅的學者也不能以林肯對法治“口惠而實不至”這種膚淺的理由而回避問題。
在如何理解林肯的法治觀時,學者長期以來形成了兩種破題的思路。第一種思路并不遮掩林肯這位偉大的總統是一位違法者,甚至承認林肯的許多戰時作為是無法無天的,但是“那又如何”,換言之,林肯的違法者形象并未將他從美國憲法文化的神壇上請下來。第二種思路是施米特主義的,根據這種解釋,林肯違反的只是作為形式和手段的法律,以此為代價,林肯所遵循并且最終保全的是作為實質和目的的法律,正如林肯所言:“民族若是失去了,憲法是否還能得到保存?”*[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82頁。以上兩種思路看起來發生在不同的合法性理論脈絡內,但若回到美國早期憲法文化的語境內理解林肯,那么其深層邏輯卻是一致的,都是將林肯所面對的這部憲法理解為形式主義的法律——只要通過科學、中立、客觀的方法即可以得到正確答案的法律,在此意義上,施米特主義的林肯形象特別隱藏著一個形式主義的法律觀。問題在于,施米特的理論雖然為現代學者提供了一個可以貼在林肯身上的標簽,但這種信手拈來的標簽卻遮蓋了林肯身處的憲法傳統中法治的復雜性,并沒有充分挖掘林肯這個憲法現象所能提供的理論意義。在此,本文不揣淺陋,愿做拋磚引玉的思考。
首先,即便林肯的戰爭行為確實帶有施米特意義上的形式違法性,但林肯的戰爭行為以及他本人所提供的正當性說明,在早期憲法史中也是有一條清晰可見的脈絡可循的。聯邦黨人的費城制憲行為本身就是違反形式法律的,因此美國憲法秩序從其誕生之初就內含破壞性的基因,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40篇就這樣寫過:“在既存政府的所有重大變革中,形式應該讓位給實質;在此類情形中,僵化地死守形式,那么人民寶貴的至上權利——‘當發現政府完全可能影響他們的安全與幸福之時,廢止或改變他們的政府’——就成為了有名無實的空頭支票。”面對憲法草案反對派對費城會議違法性的苛責,麥迪遜這樣回應道:“設計的藍圖,將要提交給人民本身這個最高的權威,如果人民不批準,憲法草案就此完結;如果人民批準,那么此前的錯誤和違規,就此一掃而光。”因此,憲法之父即便是在為新憲法正名,所使用的也并不是純粹形式合法性的理論資源,麥迪遜對費城會議在形式上的“錯誤和違規(errors and irregularities)”,從不加以掩飾。*[美] 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03、204頁。1803年,就在被許多學者奉為美國憲政之開端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發生的那一年,素以嚴格解釋憲法而著稱的杰斐遜總統做出了路易斯安那購買的決斷。而在1810年,剛卸任總統的杰斐遜在私人信件內這樣為路易斯安那購買正名:
嚴格遵守成文法無疑是每位良好公民的崇高義務,但它并不是最高的義務。絕境之法、自我保存的法則、在危機之際挽救我們國家的法律,是更重要的義務。因為對成文法律的亦步亦趨,而失去我們的國家,其實是失去法律本身以及生命、自由、財產……因此是荒唐地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美] 托馬斯·杰斐遜:《杰斐遜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595、596頁。
我們引用杰斐遜的話,并不是要通過杰斐遜去證明林肯,而是為了簡單勾勒出林肯所生活在其中的憲法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正如林肯本人參考韋伯斯特、杰克遜和克萊的憲法解釋經典來起草自己的就職演說,林肯也自覺地體認到杰斐遜對自己的啟發。1854年,林肯就說過:“杰斐遜看到了我們的政府在處理密西西比河整個流域時所面對的必要性;雖然他承認我們的憲法并沒有授權領土購買的任何條款,然而他認為,情況的緊迫性將證明這一措施,因此做出了購買的決定。”*Mark Neely, Jr., The Fate of Liberty: Abraham Lincoln and Civil Liber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18.由是觀之,在美國早期憲法史內,林肯這位將國家主義路線寫入憲法,奠定美國新憲法秩序之基礎的歷史終結者,竟然同作為“州權學說”之源頭的杰斐遜之間存在如此隱秘的對話,由此可見早期憲法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在這種憲法文化內,林肯并沒有感受到我們現代法學者所預設的形式違法與實質合法之間的巨大緊張。
而且,即便從法律解釋的角度來看,林肯確實是美國最有權力的總統之一,程度至少前無古人,但這并非意味著林肯是在突破憲法乃至拋開憲法而執政。如憲法第二條規定,總統在就職時應做如下宣誓:“我莊嚴宣誓我定忠實執行合眾國總統職務,盡所能維護、保護和捍衛合眾國憲法。”在林肯的理解中,他的戰爭行為正是他“維護、保護和捍衛憲法”的職務行為。更準確的理解是,這部建國憲法為林肯的戰時大擴權提供了內在于文本的解釋空間:并不是林肯突破了憲法,而是林肯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前十五屆總統都未能充分運用的憲法授權。*Michael Stokes Paulsen, “A Government of Adequate Powers”, 31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991-1004 (2008);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and the Commander in Chief Power”, 40 Georgia Law Review 807-834 (2006).
這種對林肯擴權的解讀,在早期憲法史的解釋經典中也能找到文本印證。在1819年的“麥卡洛克訴馬里蘭案”中,約翰·馬歇爾這位轉業進入法院的建國之父就這樣寫道:“憲法旨在承受漫長歲月的考驗,因此必須適應人類事務的各種危機”,因此一部誕生于危機時刻并為未來危機時刻準備著的憲法,必定是一部包含著充分解釋彈性空間的文本。不僅如此,馬歇爾對憲法規范與政府權力之間的關系也表現出了一種不同于現代法律人的思路:“在廣袤的共和國,從科羅克斯海峽到墨西哥灣、從大西洋到太平洋,政府將征繳并且支出歲入,調遣同時給養軍隊。民族危機的關頭可能要求北款南調、西稅東流……難道我們的憲法解釋應該讓這些運轉變得困難、危險和昂貴?”至少從馬歇爾的判詞中可以看出,憲法規范誠然有約束政府權力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認其參與美國早期現代國家構建中所承擔的功能。最后,我們還應看到,關于何為合憲性的判斷,美國早期憲法史中存在著一種完全不同于現代法的尺度:“假如目的是正當的,處于憲法的范圍之內,那么所有適當的手段——只要與目的之間存在關聯,只要不被禁止、而是和憲法的文字與精神相一致,就都是合憲的。”*McCulloch v. Maryland, 17 U.S. 316 (1819).馬歇爾的合憲性標準或許會讓現代學者痛感內戰前美國的不法治,但無論如何,這都是林肯所繼承的憲法傳統,這種憲法文化塑造著他思考憲法問題的方式,乃至發現并且提出問題的方式。
如果全盤觀察林肯總統的憲法行動,我們也應看到,林肯雖然沒有荒唐地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任由成文憲法束縛其鎮壓內部敵人的手腳,但同樣,林肯也沒有簡單地主張合憲的目的即可以證明所有原本違法的手段,在形式與實質之間,林肯表現出了一位偉大政治舵手所需的平衡和審慎。就此而言,即便是在策略意義上,林肯也始終謹守總統“維護、保護和捍衛憲法”的文本授權,在建國憲法以及早期憲法文化的傳統內謀取戰時擴權的理論資源。事實上,沒有人會比林肯更切身體會到,若他真的成為建國憲法的懸置者,那么這場戰爭就將成為無源之水,而且陷入了一種無法自圓其說的吊詭處境:戰爭是為了鎮壓內部敵人從而保存憲法和國家,但現在為了戰爭的勝利,卻首先要懸置這部作為戰爭之目的的憲法,沒有成熟的政治家會這樣將道德高地拱手讓給政治和戰場上的對手,林肯當然更不會。
六、“林肯”:一種進入美國憲法史的方法
(一)林肯的“三觀”能合為一體嗎?
林肯只有一個,聯邦、民主和法治只是本文所設定的進入林肯憲法世界的三個維度,三步走的敘述結構首先是為了分析上的便利。但問題并不因此而自動消解,反而在行文至此時顯得更加緊要。林肯是否有一個內核,而我們前述的林肯“三觀”只不過是這個內核在三個面向上外向展示?或者說,在林肯具體的憲法解釋之上,是否還存在著林肯憲法的根本法,林肯所有的憲法言行都可以在此根本法的邏輯上得到統一而且融貫的解釋?更簡單地說,林肯——如果是一只“刺猬”——那么什么是他所知道的“一件大事”?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但至此卻不難回答,林肯的內核、根本法、所知的那件大事,就是“保存聯邦共同體”。
蓋棺論定,林肯總統解決了1776年至1787年的建國者遺留在憲法文本內的兩個根本問題。第一,林肯解放了黑人奴隸,實現了自由的新生;第二,林肯捍衛、守護同時也改造了聯邦共同體,將一個復數的聯邦變成了統一不可分裂的民族國家。正是在共和國的林肯時刻,內戰前綿延不斷的激進“州權學說”失去了政治生存的市場,當然,“州權主義”的傳統在內戰后并未完全覆滅,有機會總是會借尸還魂,但在林肯之后,“州權學說”已經失去了它在漫長建國時刻所具有的那種事關生死存亡的危險破壞力,已經不再可能對根本性的憲制結構造成沖擊乃至瓦解。*Sanford Levinson, “Twenty-First Century Rediscovery of Nullification and Secession in American Political Rhetoric”, 67 Arkansas Law Review 17-80 (2014).林肯挽救了聯邦,在挽救的過程中也在憲法上再造了聯邦共同體,如同林肯在其第一次就職演說中不斷援引的,林肯畢生的憲法功業就在于他建立了“一個更完美的聯邦”,在這一主題線索內,林肯同建國之父取得了高度的統一。林肯曾親筆寫道:“在這場斗爭中,我至高無上的目標就是要拯救聯邦共同體,而不是保全奴隸制或摧毀奴隸制。如果我可以拯救聯邦而不需解放任何一個奴隸,我愿意這么做;如果為了拯救聯邦就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隸,我也愿意這樣做;而如果為了拯救聯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隸,而保留另一部分奴隸,我同樣愿意這樣做。”*[美]亞伯拉罕·林肯:《林肯選集》,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37頁。正是在“拯救聯邦共同體”這個根本法則的邏輯上,我們才能發現林肯上述“三觀”的融會貫通。
首先,當林肯同南方分裂分子就何為聯邦而展開針鋒相對的論爭時,林肯所討論的問題也就是共同體為何。在內戰前的憲法實踐內,“federal”并不是一個分權問題,而是事關共同體之性質的根本法問題,而我們所講的“federalism”,更多的是早期國家建構的政治策略和技藝。正因此,在闡釋聯邦共同體的法律屬性時,林肯所身處的法律文化同我們當下的學術場域就存在著完全相對立的區別。我們目前對聯邦制的思考,根本的出發點就是一個聯邦制和單一制二元對立的光譜。在這個光譜所設定的思考中,單一制代表著更多的中央集權,而聯邦制則反其道而行之,意味著地方分權。在這種二元對立的邏輯中,我們往往是在進行概念的踢皮球:不是單一制的,就是聯邦制;反過來,不是聯邦制的,就是單一制,而從未從實踐意義上將這兩者講清楚。不夸張地說,正是聯邦制這個學術范式遮蔽了我們對美國“federalism”歷史和實踐的理解(甚至也使得我們并不理解中國憲法“單一制”),就此而言,我們需要從美國早期憲法史的實踐中挽救“federal”、“federalism”以及“federal union”這些概念。
在美國早期憲法史上,聯邦黨人首先是主張中央集權的政治家,制憲是為了“形成一個更完善的聯邦共同體”,是要建設一個更強大的中央政府,將美國建成一個漢密爾頓所向往的歐洲模式的“財政軍事國家”。在面對此任務時,聯邦主義就是聯邦黨人有所不為,而后有所為的國家建設的技藝。*1787年憲法與“財政—軍事國家”的建設,參見Max Edling, A Revolution in Favor of Government: Origins of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當林肯在討論聯邦制時,他所討論的就是共同體的憲法構成和結構問題,而他所闡釋的“共同體先于憲法”的民族歷史敘事,也成為在內戰中保家衛國的強有力的武器。
林肯所理解的民主要落實到一種有限的多數人統治。首先,多數人說了算;但任何一個當下時刻的多數人,一方面要受到來自過去的憲法規范的約束,另一方面也要立基于未來選舉所表達出的民情民意。作為內戰總統,林肯始終直面著民主政體的“致命缺陷”——只要當下時刻的少數人可以在不滿統治的多數人之時就可以任性地退出,那么共和國就無法自立,始終面臨“內部敵人”顛覆的危險。正是因此,葛底斯堡演講的主旨就是戰場上的勝負將決定美國以及任何共和國的政治命運問題,在戰士犧牲和鮮血的基礎上形成了美國憲法乃至任何共和國憲法的根本規則(無論是否可見于文本):不得退出。
而在法治問題上,守法者和違法者的對立,也只有在保衛聯邦共同體這一根本法之上才能得到統一。1838年,未及而立之年的林肯呼吁要尊重法律,將法律視為美國人的政治宗教,這是為了在建國者逝去之后找到共和國新的立國之本。而當林肯成為分裂國家的政治舵手時,他仍始終堅守著“維持、保護和捍衛憲法”的就職誓詞。如前所述,施米特不是林肯總統的憲法顧問,為林肯貼上施米特的標簽,只不過是思想的懶惰。林肯的憲法解釋始終發生在現實政治的場域內,這就要求我們回到美國早期憲法文化的語境內去發現林肯,從現有的各種理論潮流中挽救林肯。 就此而言,本文邁出了一步,但只是一小步。
(二)以林肯為方法重審早期憲法史
本文的學術努力,如標題所示,就是希望在美國早期憲法史的語境內“找回林肯”,這主要表現為一種從森林到樹木的視角,而在文章即將結束時,我們能否反轉視角,提出一個可供研討的問題:如果我們用林肯作為進入美國早期憲法史的姿態、立場和方法,那么能否豐富我們對美國憲法史的認識?
根據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講中所用的美國歷史“紀元”,美國早期憲法史跨越了“八十七年”的時間,就此而言,美國早期憲法史是很漫長的。站在一個半世紀之后,我們很容易將這八十七年的憲法史簡化為彈指一揮間的某種“時刻”。而且,如果在傳統的以法院為中心的憲法史敘事內,這八十七年的歷史更只是“自馬伯里案以來”司法審查一經創造也即陷入停滯的黑暗歷史。但如果我們以林肯為方法重新理解這“八十七年”的歷史,那么這就是一段跨越三代人的漫長歷史,由于建國尚未成功,三代政治家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相愛又相殺的政治博弈、斗爭和妥協,其豐富多彩和驚心動魄之程度遠非林肯之后的憲法史所能比擬。
在今天,中國人有必要認真對待這段歷史,原因是,若簡單類比的話,我們目前也正處在立憲共和國的“林肯時刻”:如果我們以中國憲法的1949年類比美國憲法史的1776年,那么我們現在所處的時刻也就大致等同于林肯發表《我國政治制度永世長存》的1838年(由此可見美國早期憲法史的漫長),在這篇演講中,林肯論述了在建國者已逝,革命記憶漸趨蒼白的新時代務必要重建法治,這同我們目前所要全面推進的依法治國也許并不只是顯白的巧合,而是立憲共和國在代際交接之后都會面對的隱藏命運。
美國早期憲法史雖然“漫長”,但并不因此而“蒼白”或“空曠”,而是一段長達八十七年的“擁擠”歷史。我所說的“擁擠”,首先是指這段歷史從來不乏精彩的人和動人的事,“一波還未平息,一波又來侵襲”;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在早期憲法史的舞臺之上,我們雖然可以以代際間隔區分出前后相繼的三代政治家,但他們并不是一代唱罷,另一代方才登場的,而是呈現出代際之間相互交錯的出場順序。由此所形成的“擁擠”感最鮮明地體現在小亞當斯身上。小亞當斯(1767-1848),在1825年至1829年擔任美國總統,是美國第二代政治家的代表人物,由于他曾陪同父親約翰·亞當斯在建國時代出使歐洲,所以曾同富蘭克林和杰斐遜在歐洲談笑風生,而在總統卸任后,小亞當斯以馬薩諸塞州眾議員的身份而重返國會,年輕的同事里就有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林肯。小亞當斯的政治人生不可謂不精彩,而他個人的政治生命中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因緣際會,也就要歸因于這種特有的代際政治所造就的“擁擠”憲法史。*Charles Edel, Nation Builder: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6.
這種既“漫長”又“擁擠”的憲法史,養成了前述的“以斗爭求團結”的憲法文化。憲法的團結功能,主要體現在憲法在建國者逝去后成為了林肯所講的“政治宗教”以及共和國政治的“堅強堡壘”,在早期政治的發展中,這部建國憲法成為控制黨爭不逾矩的根本法,也是兩種路線在斗爭之際共同訴諸并因此認同的“我們的法律”。但憲法如要成為團結的旗幟,那必定不能是僵死的。建國憲法要在一個多元而且劇變的社會內成為我們所共同的法律,這部憲法就要有與時俱進的彈性,要有面向未來的開放性,要提供一個在憲法秩序內競爭和妥協的規范空間。正是這種以斗爭求團結的憲法文化孕育了林肯總統這位偉大的釋憲者。
當林肯在1865年4月15日告別人世間時,如戰爭部長斯坦頓所言:“現在,他屬于千秋萬代。”林肯終結了美國的早期憲法史,接續了建國者所奠基的憲法秩序,開啟了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林肯之后”的新政治時代。對于每一個生活在今天的美國人而言,他們都生活在由林肯所創造的憲法秩序內,建國憲法的根本原則都必須融入林肯秩序內才可能得到貫通。不僅美國,甚至每一位現代共和國的政治公民們,也都生活在林肯的憲法遺產內。林肯這位政治舵手帶領美國這個憲法共同體渡過內戰的危機,由此回答了共和國為何可以與世長存的憲法道理。林肯的憲法,與我們對林肯的紀念一樣,與共和國的試驗相始終。
林肯已逝,林肯不朽。
(責任編輯:陳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