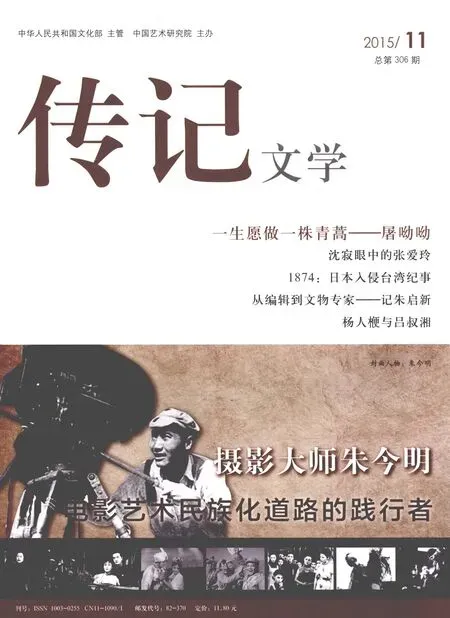還原一個真實可信的巴金
——讀陳丹晨《巴金全傳》
文 蒲宏凌
還原一個真實可信的巴金——讀陳丹晨《巴金全傳》
文 蒲宏凌
一
2014年,正值巴金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陳丹晨的《巴金全傳》修訂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事實上,早在1981年,陳丹晨就已經出版了《巴金評傳》。此后,他陸續出版了《巴金的夢:巴金的前半生》(1994)、《天堂·煉獄·人間:〈巴金的夢〉續篇》(2000)、《巴金全傳》(2003)、《走近巴金四十年》(2007)等。也就是說,《巴金全傳》修訂本這部近70萬字的皇皇巨著,是作者30多年來潛心寫作的最終成果,凝聚著作者多年來巴金研究的心血和汗水。
全書共分七編,分別以“革命的夢”、“文學的夢”、“生活的夢”、“天堂的夢”、“煉獄的夢”、“人間的夢”貫穿全文,勾勒出巴金“追夢”、“圓夢”的人生軌跡,探求了巴金憂國憂民、追求真理的心路歷程。陳丹晨認為,巴金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有了一個“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失”,他的一生就是在執著地追求這樣的夢想的實現。因此,從“夢”這樣一個獨特的視角切入,顯示了作者對于巴金生平的深刻理解。“無論怎么說,巴金的這些夢的的確確表現了他對人類世界強烈癡狂的美好渴求、憧憬和希望。有時,是在現實中未能實現,被移置在夢幻中來表現;有時,是因為他對生活過于理想化,執著于單純和善良的企求。”夢里有理想和企盼,也有幻滅和失望,有迷失,也有醒悟。
回顧巴金的百年人生,經歷了晚清、民國和新中國的時代更迭,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軍閥混戰、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其后的一系列運動,迎來了改革開放和繁榮穩定的新世紀。可以說,巴金的一生折射著20世紀中國的歷史風云。面對時代的大變亂和時局的大動蕩,面對個人命運的崎嶇坎坷和荊棘叢生,他內心也充滿了迷茫和苦悶,孤獨與痛苦,但他一以貫之的仍然是為改造社會而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精神。從對無政府主義的積極探索到對社會主義的堅定擁護,從激情四溢的文學青年到德高望重的文學界領袖,他的思想、精神、性格以及作品,為我們解讀百年中國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提供了一個極具代表性和豐富內涵的范例。
“寫傳就是寫史。”陳丹晨對此有著明確的認識,他本著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不虛美,不隱惡,對涉及巴金生平的疑難問題都做了正面回應與分析。比如,對于巴金早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作者基于對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的理論研究,從巴金對無政府主義的翻譯、著述及實踐,對這條思想線索做了清晰可見的梳理,既不回避,也不淡化。又如,對于上海解放前后巴金的思想變化,作者立足巴金著譯和書信,聯系當時的政治局勢,如實揭示了巴金“沒有應邀北上去解放區”和“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還存在一定的保留”的心態,以及隨著對新政權的互動和了解轉而擁護新政權并積極投身于新中國的建設。
二
現代傳記的特點之一就是傳記作者與傳主關系的改變。傳記作家在寫作的過程中,既尊重傳主的主體性,同時也充分發揮自身的主體性,平等對待傳主。正如法國哲學家雷蒙·阿隆所指出的那樣:“歷史展示出現在與過去的一種對話,在這種對話中,現在采取并保持著主動。”這是生命與生命的對話,正是因為傳記作家對傳主有著深刻理解的同時,還能夠保持獨立的反省意識和批判精神,才能與傳主進行心靈的溝通與交流。《巴金全傳》就是這樣一部內容深厚的傳記著作,陳丹晨作為一個老報人、老編輯,在占有翔實的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從宏通的歷史眼光和寬闊的學術視野出發,力圖“還原一個真切準確的巴金”。他說:“把巴金在這段歷史中坎坷不平的經歷,面對史所未有的嚴峻曲折的現實所發生的心態變化、靈魂浮沉、人格發展以至感情個性的揚抑……真實地描繪出來,希望借此略窺一點中國知識分子的某些側影,進而感受一點近代中國的歷史氣氛,這就是筆者寫作此書的初衷。”

《巴金全傳》書影
巴金曾經說過:“我在寫作中所走過的路與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無論對于自己或者別人,我的態度都是忠實的。”這句話引起了陳丹晨深刻的精神共鳴,他說:“無論對于社會歷史,還是對傳主巴老,我都應該采取忠實的態度,獨立思考,講真話;怎么認識,就怎么寫,不掩飾,不虛夸,力求真實準確地寫出巴老在這段歷史中的坎坷不平的經歷,心態變化,靈魂浮沉,人格發展,以及感情個性的揚抑。”在新版的“前言”中,陳丹晨再一次重申了他的寫作目的:“書寫巴金的一生命運,也就是探索和描繪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奮斗史、心靈史、思想文化史,寫出他們為社會改造而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這讓人想起羅曼·羅蘭,他因為不滿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社會,“鄙俗的物質主義鎮壓著理想,阻撓著政治與個人的行動。社會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類喘不過氣來”,先后創作“巨人三傳”(包括《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希望借助塑造健康偉大的人物形象,感召人們變革現實。他曾經寫道:“《貝多芬傳》絕非為了學術而寫的,它是受傷而窒息的心靈底的一支歌,在蘇生與振作之后感謝救主的,我知道,這救主已經被我改換面目。但一切從信仰和愛情出發的行為都是如此的。”曾為雪萊、拜倫、喬治·桑、雨果、巴爾扎克等著名作家立傳的安德烈·莫洛亞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撰寫傳記,這意味著要證實自己對人的信念……對我來說,傳記是反映歷史的主要形式之一,因為我認為,人不僅要服從于歷史規律的客體,而且也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也就是說,傳記寫作不僅僅是歷史事實的客觀記錄,而且也包含著傳記作者對于傳主的全面審視和深刻理解,抓住傳主的精神實質和性格特征,激發讀者對于偉大人格的景仰和對丑惡現實的憎惡。
這樣的傳記寫作理念,我們也可以聯想到20世紀初葉的梁啟超。當時,梁啟超在變法失敗之后,轉向思想啟蒙運動。他認為:“吾今欲極言新民為當務之急”,“然則為中國今日計,并非恃一時之賢君相而可以弭亂,亦非望蕗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文學史研究相埒,則外自不能為患,吾何為而患之?”他在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的同時,改革傳統傳記模式,“全仿西人傳記之體”,并創作了大量的名人傳記,宣揚偉大人格,激勵民族精神。此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把西方近代傳記的基本理論介紹給中國學者,他對中西傳記寫作比較研究之后認為,“吾國之傳記,惟以傳其人之人格;西方之傳記,則不獨傳此人格而已,又傳此人格進化之歷史”,因此主張學習西方傳記,揭示“人格進退之次第及進化之動力”,強調人格獨立、意志自由。這些都給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帶來深遠影響。
三
《巴金全傳》作為作家傳記,在很大程度上還具有文學研究的性質。對于這一點,陳丹晨也有著敏銳的學術自覺,他說:“個人的傳記本身就是社會歷史的組成。司馬遷的《史記》以至歷代的史書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物傳記。簡單地說:寫傳就是寫史。寫巴金傳就是寫20世紀中國歷史的某個側影。忽略或沒有寫出真實的歷史面貌,就不能成為一部稱職的傳記。我在新版修訂過程中,初衷不變,特別注意加強和補充這方面的敘寫,把傳主的心靈、思想、生活、情感和創作活動與歷史環境的變遷發展緊緊聯系起來。……它需要扎扎實實地掌握大量材料,從歷史事實出發,而不是隨心所欲地自以為標新立異取勝。反之,如果沒有對現實的深遠思考和對歷史的潛心研究,沒有對傳主的內心世界和文本的深入理解和探索,僅僅羅列材料也就不能真正認識傳主的真面貌真性情。”
傳記式批評的文學研究模式,美國學者韋勒克和沃倫也承認,“從作者的個性和生平來解釋作品,這是一種最古老和最有基礎的文學研究方法”,盡管它只是“文學的外部研究”而已。實際上,作家的文學活動都是與特定的文學環境、文學思潮和作家群體等多種因素發生綜合的關系,也正是在特定的文學環境中,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學史意義才能夠被凸顯出來。比如,陳丹晨通過史料的梳理,發現一個文學現象,即以出版社和巴金編輯的書刊為平臺,“在巴金的周圍不知不覺地慢慢地聚攏了一個沒有旗子也無宣言、不是社團也非流派、有影無形似無卻有的文學圈,巴金則是其中隱身的精神領袖”,因此明確提出巴金“文學圈”的形成和存在。僅以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時編輯的“文學叢刊”為例,曹禺、蕭乾、魯彥、劉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羅淑、嚴文井、陳荒煤、汪曾祺、黃裳、黃宗江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都是經巴金之手而得以問世,短短十幾年間,就有一百多種作品出版,充分展示了巴金杰出的文學判斷力和強大的感召力。
作家傳記的傳主,除了“作品的創造者”之外,他還在現實生活中扮演著豐富的社會角色,已經遠遠超出文學研究所能涵蓋的范圍。《巴金全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作者把巴金這樣一個復雜的生命個體,放在社會動蕩、思想交鋒的大背景下,進而觀照這一類文化人或者知識分子的進與退、浮與沉、得與失、喜與悲、遇與不遇的曲折人生及其復雜的心路歷程,引起讀者對于社會變革、文化重建等重大歷史命題的思考。比如,陳丹晨如實描寫了巴金在“十七年”初期的喜悅與激動,詳細敘述了之后的彷徨和矛盾、迷失和無奈,同時又充分說明了晚年巴金的嚴厲,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他不再唯上,也不再唯書;他從事實出發,反思歷史,也反思自己;他非常嚴肅認真地對待歷史和自己。他不再迷信盲從,更不能容忍流行了幾十年的假話,大話,空話……甚至到現在還在流行。”在《隨想錄》中,他超越了當時“傷痕文學”以及“暴露文學”等個人苦難的訴說,提出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他說:“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后也會在別處發生。”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講真話”都是永不過時的重要話題。
作者在“后記”中說:“這是一本文學性的傳記,也是一本普及性的學術讀物。我只是想把巴金的生平、創作、思想和心靈軌跡力所能及地描述出來,把我對他的認識和理解告訴讀者,盡量用平易的文字來表述,求得更多讀者的接受。”這部著作既有文學的可讀性和感染力,同時也有學術的嚴謹性和富于見地,20世紀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在作者的深情的敘述中徐徐展開,一代人的愛與恨、禍與福、歡樂與痛苦,如對目前,讓人不忍釋卷。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附有大量巴金的生活照片和手跡,圖文并茂,更具學術價值和歷史價值。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