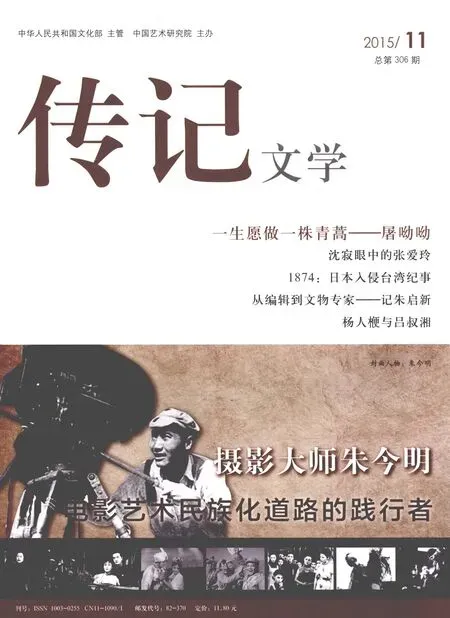沈寂眼中的張愛玲
——張愛玲辭世20周年祭
文 韋 泱
沈寂眼中的張愛玲——張愛玲辭世20周年祭
文 韋 泱
時下,健在的大陸作家中,見過張愛玲芳影的已經寥寥無幾。而與張愛玲早期有過多年交往者,則非上海老作家沈寂先生莫屬。筆者在給年逾九旬高齡的沈老先生撰寫年表時,斷斷續續聽他談及張愛玲,前后有八年之久,像打撈歷史的碎片,漸漸拼接出一段他與張愛玲不算太短的文緣軼事。今年適逢張愛玲(1920—1995)仙逝20周年,謹此為現代文壇前輩呈上心香一炷。
康樂酒家,首次見面
康樂酒家,坐落在上海靜安寺路上(今為南京西路北側,原美術館舊址),當年是一家頗為有名的高檔餐館。
1944年8月26日下午3時,由《雜志》社主辦,在這里舉辦了一次評論張愛玲及其小說集《傳奇》的座談會,《雜志》當年9月號以《〈傳奇〉集評茶話會記》為題,對座談會作了較為詳細的報道。沈寂作為“新進作家”,以谷正櫆的名字,也在邀請之列。當時按姓氏筆畫排列,他第一個出現在出席者名單中,接著是炎嬰、南容、哲非、袁昌、陶亢德、張愛玲、堯洛川、實齋、錢公俠、譚正璧、蘇青。《雜志》社出席的是魯風、吳江楓兩位,《新中國報》記者朱慕松作記錄。
座談會由吳江楓主持,他的開場白簡潔扼要:“此次邀請諸位,為的是本社最近出版的小說集《傳奇》,銷路特別好,初版在發行四天內已銷光,現在預備再版,因此請各位來作一個集體的批評,同時介紹《傳奇》作者張愛玲女士與諸位見面,希望各位對《傳奇》一書發表意見,予以公正的與不客氣的批評,在作者和出版者方面,都非常歡迎。”
作為座談會主角的張愛玲,這天涂著口紅,穿著橙黃色的綢底上裝,品藍色的衣裙,頭發在鬢上繞了一圈,長長地披下來,遮住了小半個臉,戴著淡黃色的玳瑁眼鏡,臉上始終露著微笑,可見這天她的心情之好。主持人話音一落,她便從座椅上欠了欠身,聲音低低地說:“歡迎批評,請不客氣地賜教。”接著大家自由發言,幾乎是一片贊揚聲。年方20的谷正櫆,直言不諱地說:“在中國封建勢力很強,對付這勢力有三種態度,一是不能反抗,二是反抗,三是不能反抗而將這勢力再壓制別人。若《金鎖記》里‘七巧’就有以上第三種人的變態心理,受了壓迫再以這種壓迫壓子女。”
一圈人發言下來,主持者請張愛玲“說幾句”。張愛玲有點故作謙虛地說:“我今天純粹是來聽話的,并不想說話,剛才聽了很多意見,很滿意,也很感謝。”座談會至此結束了。柳雨生本在邀請之列,因故未到,他特地把書面發言寄給了張愛玲,即轉到編輯手上,及時得以在報道中一并刊出。可見作者們對這次座談會的重視。
這是沈寂第一次見到張愛玲。雖然彼此沒有直接交談,但在一張桌子上,算是面對面了。
登門拜訪,以釋前嫌
其實,正式見面前,沈寂與張愛玲常常在紙上見面。1942年,時在復旦大學讀二年級的沈寂,創作第一篇小說《子夜歌聲》,在顧冷觀主編的《小說月報》刊出后,一發而不可收。第二年在周瘦鵑主編的《紫羅蘭》第7期上,刊發小說《黃金鋪地的地方》。而這一年,張愛玲從《紫羅蘭》第2期至第6期, 連載小說《沉香屑》。主編周瘦鵑“深喜之,覺得風格很像英國名作家毛姆的作品”。可以說,《紫羅蘭》是張愛玲最早贏得文名的刊物。同年,沈寂在柯靈主編的《萬象》第9、11、12期上,連續發表了《盜馬賊》《被玩弄者的報復》《大草澤的獷悍》三篇小說,得到柯靈的好評。在第9期“編后記”中,柯靈推薦道:“這里想介紹的是《盜馬賊》,細讀之下,作者自有其清新的風致。沈寂先生是創作界的新人,這也是值得讀者注意的。”而張愛玲的小說《連環套》,當年也在《萬象》上連載。她的《心經》,還與沈寂的《盜馬賊》同時刊登在9月號上。在柯靈的眼中,張愛玲與沈寂是《萬象》的重點作者,也是有發展前景的青年作家。
1943年底,在親友們為沈寂與女友朱明哲舉辦完訂婚宴的當晚,日本憲兵突然逮捕了沈寂。原因是沈寂的中學同學蔣禮曉僥幸出逃后,在其日記本上查到沈寂的名字。40余天的監獄生活艱苦難熬,包括上“老虎凳”。沈寂咬牙挺住,終因沒有確鑿證據,于1944年2月被釋放。沒過幾天,有人打電話給沈寂,輕聲說:“你進過憲兵隊,不宜再給《萬象》投稿,以免牽連刊物和柯靈,但可轉而為《雜志》寫稿。”果然不久,《雜志》編輯吳江楓寫信給沈寂,向他約稿。沈寂寄去小說《敲梆梆的人》,吳江楓說作品即可發排,但以后要改個筆名,不能再用過去的沈寂。兩人推敲一番,最后定名為谷正櫆。之后《王大少》《沙汀上》《挖龍珠》《淪落人》《大草原》等小說相繼刊出。當年8月,《雜志》舉辦一次筆談專輯:“我們該寫什么”,作者有疏影、譚惟翰、張愛玲、谷正櫆、朱慕松、錢公俠、譚正璧等11人。按來稿先后排序,張愛玲、谷正櫆為第三和第四,正巧登在同一版面上。可以說,這是他們“零距離”在一起,盡管,只是見名不見人。從《紫羅蘭》《萬象》到《雜志》,兩人紙上見面不算少呢!
但是,在康樂酒家所見的真人第一面,沈寂并沒有給張愛玲留下好印象。沈寂發言里有“變態心理”四個字,這正是張愛玲極為反感的字眼。她聯想到不久前看到的迅雨(傅雷)文章《論張愛玲的小說》(《萬象》1944年第11期),也批評她的《金鎖記》:曹七巧“戀愛欲也就不致抑壓得那么厲害,她的心理變態,即使有,也不致病入膏肓,扯上那么多的人替她殉葬”。張愛玲進而聯想到,有變態心理的作者筆下才會出現有變態心理的人物。這谷先生與迅雨先生,可是一個鼻孔出氣,串通好專門找她的茬兒。她越想越氣悶,就把這一想法悄悄與吳江楓嘀咕了一通。吳江楓聽后很是吃驚,覺得事情不妙。作為《雜志》編輯,又是那次座談會的主持人,他不希望張愛玲的情緒受到影響,如此,對《雜志》以后的編輯工作也無好處。吳江楓很快把張愛玲的想法轉告了沈寂。怎么辦呢?兩人商量時覺得,從刊物這邊說,張愛玲惹不得,她不但是《雜志》的臺柱子,更是上海灘當紅女作家。從沈寂這邊來說,一句老話說的是“好男不跟女斗”,應該消除張愛玲的誤解。從吳江楓這邊來說,張與沈都是他們重要的依靠對象,只能是“和為貴”。這樣,在吳江楓的建議下,沈寂決定登門解釋。

沈寂重溫編過的舊刊
一日下午,約好時間,沈寂跟隨吳江楓去了赫德路195號愛丁頓公寓(今常德路常德公寓),電梯直達六層樓。顯然,吳江楓是熟門熟路,可見他是這里的常客。張愛玲乍見吳江楓帶著谷先生進門,已心知肚明:何不給谷先生一個臺階下呢。張愛玲年長沈寂4歲,自然有大姐的姿態,舉止落落大方,這使心里有點忐忑不安的沈寂,很快消除拘謹,言談自如。三人東拉西扯,從座談會談到正在喝的咖啡味道,談到市面上的行情,前后坐了約一個小時。張愛玲由此曉得,谷先生常常以“沈寂”筆名發表作品,谷先生與迅雨的評論文章毫不搭界等等。作為女人,張愛玲敏感、小資、自視甚高,但她畢竟是才女,聰穎、得體,又善解人意,“到底是上海人”的張愛玲,的確“拎得清”。
在張府,沈寂見到了張愛玲的姑媽張茂淵。另外,還見到了瀟灑倜儻的胡蘭成,他穿著長衫,輕搖折扇。雖是一瞬間,沒有說上話,但證實了外界傳說的張愛玲與胡蘭成的關系。走出張府,沈寂不解地詢問吳江楓:看張愛玲的表情,似乎不太愉快。吳江楓一語道破天機:“她不愉快是因為不愿意我們在她家看到她的秘密男友胡蘭成。”
不久,有一次沒有成功的“義演”,也與張愛玲有關。吳江楓想以《雜志》名義,舉行一場義演,請電影導演費穆執導根據秦瘦鷗小說改編的話劇《秋海棠》,將收入全部捐給失學學生。劇中角色全由《雜志》作者扮演,譚惟翰飾秋海棠,張愛玲飾羅香綺,谷正櫆(沈寂)飾季兆雄,石琪(唐萱)飾一軍閥。吳江楓說,請大家來義演,不是科班演戲,而是文人粉墨登場,這是義演真正的“賣點”。第一次召集會的地點,就在康樂酒家。大家悉數到場,張愛玲戴一副茶色眼鏡,穿素色綴淺紅花點的旗袍,一聲不響地坐在后面。費穆給各位分配好角色,關照大家抓緊背臺詞后,就散會了。后來,又集中過一次,算是排演。導演石揮、白文也聞聽趕來。可是,張愛玲不知何故,沒有到場。這次義演,未知是否因張愛玲不太熱衷,最終不了了之。
1944年12月,張愛玲將中篇小說《傾城之戀》改編成話劇,由朱端鈞導演并首演于新光大戲院,沈寂好友舒適演范柳原,羅蘭演白流蘇。沈寂獲知演出信息后,特地買了一個花籃,題上祝演出成功的賀詞,當天購票觀戲并獻上花籃。第二天,吳江楓專門來電轉達張愛玲對沈寂的謝意。
抗戰勝利,仍有合作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沈寂除繼續創作外,還先后做過《光化日報》特約記者,在《辛報》編過“社會新聞”版,還主編過《民眾周刊》。后應環球出版社馮葆善先生之邀,應聘主編《幸福》月刊。又于1948年5月,接編《春秋》月刊。1948年,沈寂主編《幸福》。在任上海淪陷時期《雜志》(共產黨地下黨員袁殊負責)主編的吳江楓,寄來英國著名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說譯稿《牌九司務》,署名“霜廬”,沈寂編入10月出版的《幸福》第22期。
抗戰勝利后,社會輿論對張愛玲多有責難,皆因她與漢奸胡蘭成的婚戀關系。1945年11月,曙光書店出版發行一本小冊子,書名叫《文化漢奸》。書中列出柳雨生、張資平、胡蘭成、蘇青等17個文化漢奸,一一給予鞭撻揭露,張愛玲也在其中,被譴為“紅幫裁縫”。文中說張愛玲“愛虛榮,要出風頭去,被一群漢奸文人拉下水,又跟胡蘭成那種無恥之徒鬼混,將一生葬送了”!無奈之下,在大光明大戲院擔任外國原版影片“譯意風”(類似同聲翻譯)的姑媽,決意為張愛玲換個環境。這樣,她們搬出愛丁頓公寓。起先遷入靜安寺路梅龍鎮弄內重華新村,幾年后又遷往派克路(今黃河路65號)卡爾登公寓(今長江公寓)。期間,張愛玲埋頭寫作,從小說《華麗緣》《相見歡》,到電影《不了情》《太太萬歲》。但報刊上以張愛玲署名的作品已大為減少,還時遭退稿。這大大打擊了她的自尊。同時,這也意味著靠稿費生活的她,漸漸陷入困境。這些,沈寂頗能理解。本來,他是不敢輕易約張愛玲、蘇青這些人的稿子的。時至1948年底,沈寂正在革新《春秋》雜志,想辦得更純文學一些,在一時稿源匱乏之下,他想到了張愛玲,不宜用真名發表創作作品,就請她翻譯一些外國作品。張愛玲從圣瑪麗亞女校(今上海市第三中學)畢業,就讀過香港大學,有扎實的英文根底,又愛好外國文學,早年曾給英國《泰晤士報》和英文雜志《二十世紀》寫文章,翻譯對她來說輕車熟路。沈寂寫信約張愛玲寄稿,很快,張愛玲寄來了一篇題目為《紅》的文稿,約4000余字,未署名。沈寂看后,覺得是對毛姆原著的改寫,文字風格則是張式的。張愛玲說明道:因在創作劇本,沒有全部完稿,很是抱歉云云,同時把英國“企鵝版”毛姆小說原著附來。沈寂讀的是復旦大學西洋文學系,對外國文學自然爛熟于胸。他很快根據原文,譯完余下的三分之一文字,文末還寫上“本篇完”,編入《春秋》1948年第6期“小說”欄目,在內頁《紅》的題目處,沈寂請人配了題頭畫,中間留了空白,用何筆名,一時難定。后將曾譯過毛姆作品的吳江楓筆名“霜廬”代用在目錄上。卻因發稿時緊,疏漏了在正文標題中寫上此名。這樣,不看前面目錄,不知作者為誰,只是此文與魯彥的《家具出兌》、田青的《惡夜》等排在一起,給讀者造成這是一篇原創小說的感覺。刊物印出,吳江楓看到并不介意,之后繼續用他的“霜廬”筆名,再寄所譯毛姆的短篇《螞蟻和蚱蜢》,沈寂將此刊于《幸福》1949年第2期。張愛玲收到《春秋》樣刊后,自然喜出望外,內心感激著谷先生。張愛玲改寫毛姆作品未完,沈寂曾予續譯救場。作者與編者的默契合作,這實在是一則文壇軼聞。
半個世紀,再續文緣
很快,迎來上海解放。沈寂因香港永華影業公司買下他的小說《鹽場》《紅森林》版權,并邀請他出任該公司編劇,在獲得上海軍管會同意后,年底攜妻子赴港履新。1952年1月,沈寂因公司欠職工三個月薪水,代表職工與公司方談判未果。港方又因他參加進步團體“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組織的愛國活動,誣以“不受港督歡迎的人”,宣布將他終身驅逐出港。1952年4月,沈寂回到上海,進入剛公私合營的上海電影聯合制片廠。
而在上海的張愛玲,經主持上海文藝工作的夏衍同志提議,作為正式代表,出席了1950年7月召開的上海第一屆文代會。盡管已進入新社會了,但她的思想還停留在昔日的情懷中。她是一個對政治不感興趣的人。她度日如年。
亦是巧事。一日,在黃河路上開辦“人間書屋”的沈寂,去對面卡爾登公寓探望一個朋友,剛進大樓,與正從電梯里走出來的張愛玲撞個“滿懷”。張愛玲脫口而出:“谷先生嗎?”她習慣稱沈寂為谷先生,她已從報上知道沈寂因進步行為被驅逐出港。“是。張小姐多年不見,你好嗎?”聽這一問,張愛玲顯得無精打采:“還是老樣子,除了動動筆頭,嘸啥好做的。”他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著。沈寂看得出,張愛玲的情緒十分低落。是否見到從香港來的人,把她的思緒引到了香港,因為胡蘭成還在那里。正要告別,張愛玲說:“對了,最近正好出版了一本小說,送你看看。”說著,轉身上樓去取書。
這本書叫《十八春》,是張愛玲第一部長篇小說,相比以往的小說,《十八春》寫作的時間稍長些。她應《亦報》主編龔之方之約,寫這部小說,希望以連載形式吸引報紙讀者。小說署名“梁京”,從1950年3月至第二年2月,全部連載完畢。《亦報》趁熱打鐵,請張愛玲對全書再修改潤色,同年11月以“亦報社”名義,出版單行本。接著,《亦報》又連載她的另一部小說《小艾》。
1952年至今,63年過去了,沈寂一直保存著這本《十八春》。這是他與張愛玲在上海最后一面的見證。這次見面后過了大約三四個月,沈寂聽說張愛玲去了香港,不覺得驚奇,認為是順理成章之事,她不能適應現在的生活環境。又聽說,張愛玲滿懷熱望到了香港,卻見胡蘭成與佘愛珍(汪偽時期特務頭子吳四寶之妻)廝混在一起,并做著遠走高飛去日本的準備。張愛玲甚感絕望。此時經友人推薦,張愛玲在駐港美國新聞處謀得一職,并應《今日世界》之邀,寫作長篇小說《秧歌》《赤地之戀》。這兩部作品明顯帶有對大陸怨恨的“反共”傾向,與《十八春》《小艾》唱著另一調門。聞此,沈寂為同時代的文友深感惋惜。
時光轉到2009年,臺灣著名導演李安要執導張愛玲的《色·戒》,知道沈寂十分熟悉舊上海的一草一木,便聘請他擔任影片史實顧問。又聽說沈寂曾與張愛玲有過交往,高興地說:“邀您任顧問是請對了,增強了我拍攝《色·戒》的信心!”比如,張愛玲小說中的麻將戲,李安很重視,沈寂說那時的麻將不用塑料或木質,用的是牛骨。再比如,姨太太穿著黑披風,如何走路?沈寂說要走一字步,有一定的扭擺。影片上映后一炮打響。為喜愛張愛玲作品的“張迷”們,沈寂做了默默無聞的幕后英雄,更是續了他半個世紀前與張愛玲的文緣。

張愛玲贈沈寂的《十八春》書影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