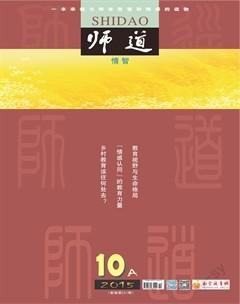鄉村教育該往何處去?
王淦生
高考結束后,高三老師便處于一種賦閑狀態。領導自然不會讓我們閑著,便將我們“打包發送”到一所位于城郊的普通高中去充任監考——那里今年設了一個中考的考點。
來這里考試的都是周邊地區的鄉鎮初中的學生。監考培訓會上,培訓人員一遍遍強調這里的考生素質之低、紀律之差,目的在于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承擔的任務的艱巨——仿佛那不是一場普通的監考,而是一場戰役;我們不是普通的監考老師,而是看守,是刑警。
到了接觸考生時,對我觸動最大的,不是這些孩子的“素質”和“紀律”,而是他們的神情——從這些十五六歲的少年身上,我看到的不是孩子應有的天真和稚氣,甚至也不是農村孩子常有的那種淘氣和頑皮,很多人都顯出一種與年齡不相稱的落寞、麻木甚至愚昧。他們看人時那種空洞的眼神和不屑的表情讓為人師、為人父的我內心深處有一種隱痛。
更為可悲的是,開考鈴敲響之后,考場中三分之一的人在填好考號、姓名后便趴到桌上呼呼大睡——他們甚至連作弊的欲望都沒有,你喚醒他便是懲罰他,因為兩個小時左右時間的枯坐對誰都會是一種折磨。所以,我們監考便是看著三分之一的考生睡覺,三分之一的考生枯坐。一個考場30名考生中認真答題的絕不會超過10人,稍好些的也就三兩人。
在與送考老師的交流中我得悉,如今的鄉鎮初中大多處在一種風雨飄搖的狀態中。學校規模日漸萎縮,教師和生源日見減少——優秀生源和優秀教師都被城里的學校吸走,剩下的學生大多是一些留守兒童和學習上有困難的同學,留守的老師也都是一些年齡偏大或教學水平平平的教師。在這樣的學校里,學生學習積極性普遍不高, 遲到、早退、曠課現象嚴重,更有甚者中途輟學,流入社會;老師固然有堅守崗位賣力苦干的,但更多的人則難免心灰意冷得過且過。如此,便使得鄉村教育呈現出 一種每況愈下的態勢。一個“混”字,足以概括出時下許許多多農村中小學學生、老師的生存狀態。從這樣的學校里走出的學生,且不論其學業狀況如何(其中很多人近乎文盲),單看其精神面貌、言談舉止,就很令人沮喪。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有識之士發展中國的鄉村教育,那時很多著名的學者、作家——諸如葉圣陶、夏丏尊、豐子愷、陶行知、晏陽初等人都曾是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當時,他們都是懷著一顆“救國”之心來發展中國的鄉村教育的,很多文學作品——如《倪煥之》《二月》中都曾有過紅紅火火而又如詩如畫的鄉村教育場景的描繪。至今讀來,依然令人心馳神往。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鄉村教育也曾有過如火如荼的階段,我大學畢業后就曾在一所鄉村中學整整待過10年。 彌漫在校園中的那種清新、純樸、向上的氛圍讓我在日后遇到種種挫折和坎坷時不時冒出“不如歸去”的念頭——可是,最近我才知曉,那所鄉村中學也已離關門不遠,其生源已不足以支撐其作為一所學校而存在。也就是說,“歸去來兮”對我來說已是一個永遠無法兌現的夢!而這,是不是現階段中國經濟不發達地區鄉村教育的一個縮影?
中國鄉村教育的式微應該說不完全是“錢”的問題。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和改革開放之初都不會比現在“有錢”。但為何我們的經濟總量上去了,我們的農村富裕了,我們的鄉村教育卻呈現出一種頹勢?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如今也愈來愈表現出對農村教育和農村學生的關注,比如在高校招生時重點高校要專門劃撥一定指標定向分配給農村學生。可是,我覺得與其劃撥指標給那些很少在鄉村中小學待過的農村優秀學生,還不如想方設法先將那些在考場上呼呼大睡的學子喚醒。因為沒有堅實的鄉村教育的根基,而靠劃撥一定數量的招生指標去照顧農村學生是無法帶動起我們的鄉村教育乃至整個中國教育的騰飛的。
當我們的鄉村教育能夠與城市教育相距不遠甚至平分秋色時,當我們的教師和學生不再想方設法逃離鄉村時,當我們的農村考生高考再不需要政策性照顧也能憑實力考進985高校時……我們才敢說我們的教育是公平的,成功的。
(作者單位:江蘇鹽城市亭湖高級中學 )
責任編輯 蕭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