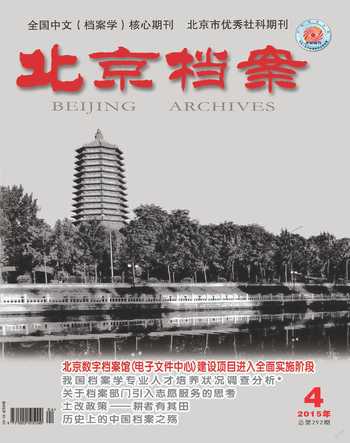民國時期北京中山公園社會功能初探
劉媛 姜秉辰 楊宇辰
公園是公眾消遣游憩的場所,是城市主要的公共空間,人們在此親近自然、娛樂賞玩,或參與文藝活動。中國最早的近代公園是建成于1868年的上海外灘公園(今黃浦公園),而開放于1914年的北京中山公園則是最早辟為公園的皇家園林。中山公園前身為明、清兩代皇帝祭祀土神、谷神的社稷壇,20世紀初的中國,正處于革故鼎新、兵燹馬亂之際,大勢已去、東山不復的清政府早已沒了祭天奠地的心思,終于在1912年宣告退出歷史舞臺,留下了“古柏參天,廢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間種苜蓿,以飼羊豕……渤溲凌雜,尤為荒穢不堪”[1]的社稷壇。1914年,時任內務總長的朱啟鈐鑒于“京師首善之地,人文駢萃,圜貴殷繁,向無公共之園林,堪備四民之游息,致城市之居囂闐為患,幽邃之區荒蕪無用”[2]的現狀,以解放思想,移風易俗為主要目的,倡導公園開放運動,并成功與前清皇室交涉,將曾經為皇家禁地的社稷壇開辟為中央公園,從此北京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園誕生。
早在中國還未有現代意義的公園時,黃以仁先生就通過對西方公園的考查研究,指出“公園匪特于國民衛生與娛樂有益,且于國民教育上,乃至風致上,有宏大影響焉”[3]。可見,公園不僅是百姓休閑娛樂的場所,更履行著重要的文化教育職能。公園的這一特點,在西方文化不斷涌入的民國前期顯得尤為突出。北京的中山公園不僅融合了東西方造園的不同特色,更承載著豐富的社會功能,其背后隱藏著的是北京迥乎不同的時代烙印和文化底蘊。
一、中山公園的休閑娛樂功能
毋庸置疑,供游客娛樂是公園建設的初衷,也是其首要職能。而前往公園的絕大部分民眾是去休憩游樂、釋放壓力、凈化身心。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一日不到公園,則精神混沌,理想污下。”[4]優美的自然環境讓游客神清氣爽,恬靜悠閑的氛圍又使游客得到心靈的安寧。
中山公園開園之初,僅有五色土壇和拜殿,實在不足一觀,因此,以朱啟鈐為首的董事會確立了“依壇造景”的建園方針,保留五色土壇、殿堂、城垣等古建筑,對園中盤根錯節、蒼翠蓊郁的數百株千年古柏進行保護,還廣植花木,尤以牡丹、芍藥、丁香、海棠最盛。每當繁花盛開之時,市民傾城出動,競相賞玩,甚至每天還有一列“觀花列車”從天津開來北京,專為天津游客來中山公園賞花之用。葉恭綽先生作《稷園觀牡丹詩》云:“萬人如海競相歡,勝似君王帶笑看。”可見當時的賞花盛況。中山公園不僅春花爭艷,夏秋冬三季也有花展。賞花的游客不禁慨嘆:“在北平提起菊花來,以中山公園最為盛名的。”1914年以后的數年間,在“清嚴偕樂,不謬風雅”的主旨下,新景點陸續添建,中山公園已從荒蕪的社稷壇到水木明澀、綠樹成蔭的公園,成為市民茶余飯后遛彎、賞花的佳選。中山公園是西風東漸的產物,自然就成為展示西方新事物的窗口。公園自開放后逐漸增添了照相館、咖啡館、西餐館、臺球房等配套設施,這些新鮮玩意兒吸引著市民們的目光,他們十分熱衷于前往公園親自揭開這些洋貨的神秘面紗,來園也就越來越頻繁,由此強化了中山公園的休閑娛樂功能。
二、中山公園的文化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
公園建設的初衷是希望在喧鬧嘈雜的城市中為市民提供一個舒適宜人的休息環境,但公園不僅僅是游憩賞玩的場所,還是一個多功能的空間,可以進行各種多樣的活動。在《中央公園開放章程》的第一條中明確規定中山公園的性質為“京都人士游息之所”,由此可見,中山公園是一處休憩場所,職能主要是使游客通過游園賞景獲得身心放松。然而,充滿時代特色的是,在時人眼中,文化教育職能和政治職能才是這座公園的主要職能。他們眼中的中山公園,不只是供大眾休閑娛樂的公共空間,更是一個文化的聚集地。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來中山公園的游客,有不少是專為茶座而來的。中山公園有各種類型的茶座,無論男女老少,上至總統,下至平民,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有人曾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頂好的地方是公園,公園中最舒適的是茶座。”[5]中山公園中受游客喜愛的茶座主要有四家,從時人的調侃中,我們便能看出四大茶座各自不同的特色。“來今雨軒是國務院”,因為政界要人們公余常在此碰頭,也常常能見到文化界名人、大學教授駐足于此;而“長美軒是五方元音”,這里的客人是三教九流,茶點引人垂涎,物美價廉;“春明館是老人堂”,老人們在此下圍棋、鑒賞古董,一坐就是大半天;“柏斯馨是青年會”,這里是洋派人物、摩登愛侶說情話的地方,賣的是西式茶點,即咖啡、荷蘭水、冰淇淋等。
中山公園的茶煙中,浮動氤氳著古都文化的氛圍。人們在茶座里品茶、聊天,但許多政界要人、文化名人與之有關的記憶卻更為豐富,他們眼中的茶座,其文化象征意義已遠遠超出了商業范疇。現今的我們僅能透過相關的記錄,想象當年的風華盛景。
茶座清靜雅致的氛圍,吸引了一批文人墨客,為他們提供了靈感的源泉。從中山公園建成開放后的十多年間,魯迅先生多次來園,僅《魯迅日記》中記載即達60次。最早來園的記載是1915年8月7日,此后,1916年1次,1917年5次,1924年8次,而從1926年7月6日至8月9日幾乎每天下午來園,一月之中來園多達28次。魯迅來園的目的多是飲茶、交談、閱報、參觀展覽、進行創作或翻譯小說,例如1924年5月30日的日記中記載:“遇許欽文,邀之至中央公園飲茗”[6],他們這次交談的就是討論小說創作問題。1926年后魯迅來公園,在來今雨軒的茶座中與齊壽山合譯荷蘭童話小說《小約翰》一書。張恨水也常常光顧來今雨軒的后院茶座,《啼笑因緣》便是創作于此。林徽因在其文學創作的高峰期更是經常來到這里。另外,朱自清、沈從文、老舍、齊白石等我國近現代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也都曾在這里留下身影。
中山公園深受市民的喜愛,游客數量眾多,從而吸引了大批演講者的到來。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勝利結束,教育總長特允各公立學校放假半天以參加慶祝活動,并在天安門附近搭建一高臺,供檢閱和演講之用。由于演講大受聽者歡迎,北大進而決定利用政府和教育部當月28—30日舉行慶典的機會,再次停課三天,在中山公園舉行第二次演講大會。1918年11月27日《北大日刊》頭版頭條刊載《本校特別啟事》,謂“本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為慶祝協約國戰勝日期,本校擬于每日下午開演說大會(地點在中央公園內外,俟擇定后再行通告),各科教職員及學生有愿出席演說者,望即選定演題,通知文牘處,以便先行刊印,散布聽眾。”[7]李大釗先生應征參與,著名演說《庶民的勝利》便由此而來。
此外,北京市檔案館的相關檔案中還記錄著曾有許多文人在此舉辦集會以及各學生團體的活動。如1925年滬案后,中華女子救國會請求將門票收入捐給滬案遇難同胞,清華等十四所學校請求在園內召開文藝匯演為滬案籌款等。
不僅文人墨客在日記中多次提及中山公園,胡適等一批北大教授也對這座公園表現出非同一般的青睞。在胡適任職北大期間,他經常來園,或與北大的同事結伴,或與學生同游。如“民國”十年九月十五日,這一天正是中秋前夕,《胡適的日記》中寫道:“作《章實齋年譜》,至夜八時,見月色撩人,就獨自去游公園,進園后,遇一涵、慰慈、文伯、淮鐘。同到水榭后石角上,喝茶高談。月色甚好,念明天是中秋,不知有此好月否?”[8]據《胡適與當代史學家》稱:“后來錢穆先生在北大教書時,也常去中央公園。”而錢穆先生的《師友雜憶》也有關于友人相會于中山公園的記載。謝興堯先生在其《中山公園的茶座》一文中記載了錢玄同先生與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公園喝茶的場景:“有兩位也時長在長美軒茶座上的,是錢玄同和傅斯年,不過他兩人比較特別,總是獨自一人,仰天而坐,不約同伴,不招呼人。”[9]為何北大教授們對這座公園如此情有獨鐘?主要原因有三:首先,當時北大的校舍分散于中山公園附近,且先生們也住在學校附近,為他們來園提供了莫大方便;其次,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文人集會的傳統,在此傳統影響下,北大的教授們課余之際常常在此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或討論學術問題,或共論國家命運;再者,民國年間大學教授的收入較高,屬于中產階級,故對于公園門票、茶座等費用也承擔得起。
在民國年間的知識分子眼中,中山公園的價值已經遠遠超過它的建造初衷。他們對中山公園寄予厚望,希望能通過這座公園向人民群眾普及先進的知識、科學的觀念,傳播西方的文化和藝術,啟迪民智,陶冶情操,激發他們的愛國之情和民族精神。而文學創作、商討國事、舉辦社團和展覽,是知識分子階層力所能及的振興民族、愛國報國的手段。名噪一時的文人在中山公園的活動是一道獨特而亮麗的風景線,極大地突出了中山公園的文化教育功能與政治功能。
三、結語
綜上可見,公園是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間,市民在此游憩賞玩。但它也是一個多功能的場所,履行著文化教育和政治等職能。中山公園與其說是一個公園,倒不如說是一個近代中國的人才聚集地,一個室外沙龍。其中諸多的文教活動、政治集會,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啟迪民智、救亡圖存的強烈愿望。它是知識分子的夢工廠,也是知識分子宣傳思想的平臺,大量的文學作品在此被創作,許多救國方案在此被討論出來;代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庶民的勝利》從這里走向全中國,一代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此被祭奠。不論是客觀發展,還是主觀期望,民國時期的中山公園成為塑造國民的重要教育空間,以寓教于樂的方式實現了化民成俗。
因此,以中山公園為代表的近代公園,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融,促進了市民生活方式的改變。由于當時的中國處于紛繁變革的時代,被“本土化”了的公園兼具著休閑娛樂、文化教育、政治等多重職能。公園不僅是游客賞玩休憩的場所,也是塑造新型國民的重要教育空間。公園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注釋及參考文獻:
[1]王煒,閆紅.老北京公園開放記[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51.
[2]朱總長請開京畿名勝[N].申報,1913-1-13.
[3]黃以仁.公園考[J].東方雜志,1913(9):2.
[4]梁啟超.新大陸游記[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42.
[5]謝興堯.中山公園的茶座[M]//王煒,閆紅.老北京公園開放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84.
[6]魯迅.魯迅全集(14)日記[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498.
[7]張世飛.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經驗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248.
[8]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胡適的日記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5:215.
[9]謝興堯.中山公園的茶座[M]//王煒,閆紅.老北京公園開放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