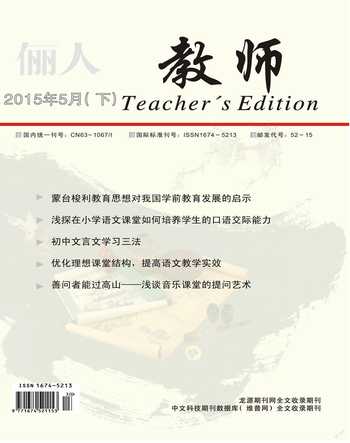《酒國》的文本互涉性研究
溫文華
【摘要】《酒國》是莫言眾多作品中的一個“意外”,是讀者的一個“驚喜”,也是莫言最愛的“美麗刁蠻的情人”,在該作品中有著明顯的文本互涉,是一種吸收,改造,更是推陳出新,有所創(chuàng)造。《酒國》中的文本互涉性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包括文本內(nèi)部的互涉、文本與其他文本的互涉。
【關(guān)鍵詞】莫言 《酒國》 文本互涉 敘事視角 吃人
《酒國》曾獲法國的外國文學(xué)獎,被稱為:“是一個空前絕后的實驗性文體,其思想之大膽,情節(jié)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結(jié)構(gòu)之新穎,都超出了法國乃至世界各國讀者的閱讀經(jīng)驗。”[1]我對這一評價深表贊同。《酒國》所虛構(gòu)的一個如此陌生,難以相信,而又無時無刻不讓人感到熟悉的世界。雖說它是一個用語言呈現(xiàn)的虛擬的文學(xué)世界,但不僅僅需要我們用意識去經(jīng)營的藝術(shù)世界,更是值得好好研究的文本。《酒國》中所體現(xiàn)的文本互涉性是明顯而特別的存在,是值得我們?nèi)ニ伎己脱芯康摹?/p>
一、文本內(nèi)部的互涉
(一)結(jié)構(gòu)框架上的推進
一部《酒國》主要由三大部分構(gòu)成:一是特級偵查員丁鉤兒辦奉命追查酒國食嬰事件始終,二是酒國市釀造學(xué)院勾兌專業(yè)的博士研究生、業(yè)余作家李一斗與小說中的作家莫言的書信往來,三是李一斗創(chuàng)作的關(guān)于酒國形形色色的描述,也就是特意寄給小說中的作家莫言的九個短篇小說故事。
《酒國》三條線索看起來是可以獨立的,都是敘述著自己本身的故事,而且發(fā)展要素齊全,尤其是九個短篇小說的故事,然而三者并不是簡單的單獨發(fā)展,而是并立而起,相互推進,穿插。文本內(nèi)部的互涉淺顯易懂地體現(xiàn)在內(nèi)容的互涉上,結(jié)構(gòu)框架的突顯是莫言《酒國》的一個特色之處。因為時空結(jié)構(gòu)的交錯,在文本中可以看得出有些地方的人物和時間是先后錯亂的,使得讀者產(chǎn)生錯覺,更是疑惑其中真假,恰到好處的“亂”和“互涉”。
(二)敘述視角的不斷變換
所謂敘述視角,即“一部作品或一個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體現(xiàn)為“一個故事敘事行為發(fā)生時誰在講故事、以誰的眼光講故事、講誰的故事和向誰講故事四方面的要素”[2]然而敘述視角的變換則可以造成達到文本世界的互涉,這是在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作品中常常出現(xiàn)的。
《酒國》的敘事視角不停在變換著,是以全知全能的視角作為主導(dǎo),其間還親自參與故事其中,以新身份或者借用故事中的某個角色來敘述,甚至是采用多個視角聚焦同一件事。故事中敘述者的身份一般有兩種:同一個人一是作為局外人來俯視整體,二是以劇中人的身份來分述部分情節(jié)。當(dāng)然《酒國》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李一斗給“莫言”的信及他的九篇短篇小說又有另外不同的視角。如:“他臉上的神情像個妖精,像個武俠小說中所描述的那種旁門左道中的高級邪惡大俠一樣,令我望而生畏。”“他蹲在那把能載著他團團旋轉(zhuǎn)的皮椅子上,親切而油滑地對我說”[3]。在這里是通過李一斗的感知來敘述,把“他”作為敘事的聚焦者來呈現(xiàn)內(nèi)容。
通過敘述視角的不斷變換,對人物進行了多點透視。簡單而言,就是書信中的敘述者也許就是上一部分中酒國市中的執(zhí)行者,不同時間地點出現(xiàn)的“同一個人”,讓我們在亦幻亦真的故事中越發(fā)深陷故事,這些超出了一般讀者的閱讀體驗。文本世界的互涉性在敘事視角的體現(xiàn)更是因為在《酒國》三線合一的結(jié)構(gòu)框架,二者渾然一體,經(jīng)營著“酒國”故事。
二、文本與其他文本的互涉
(一)《酒國》與《狂人日記》的互涉
張磊就以《百年苦旅:“吃人”意象的精神對應(yīng)——魯迅〈狂人日記〉和莫言〈酒國〉之比較》為題對新文學(xué)史上相隔大半個世紀的兩部以“吃人”文化為批判對象的小說進行了比較分析,起因是“發(fā)現(xiàn)兩者在文化背景、意義指涉等方面驚人地相似”。[4]魯迅《狂人日記》是精神上的“吃人”,而《酒國》確實實在寫肉體上的“吃人”,更準確來說是“食嬰”。這都是把吃這一動作發(fā)揮到極致,把國民性和社會黑暗面一針見血地指出。莫言的《酒國》除了思想主旨有一定的互涉性,在文本中隱隱約約能感受到《狂人日記》的隱形影響,是虛構(gòu)的場景和真實的細節(jié)共同為之。
莫言在小說中也談到“吃人”的構(gòu)思與魯迅傳統(tǒng)及《狂人日記》的間接關(guān)系。他在《酒國》中借小說中文學(xué)青年李一斗之口談出了創(chuàng)作動機:“立志要向當(dāng)年的魯迅先生棄醫(yī)從文一樣,用文學(xué)來改造社會,改造中國的國民性”。
(二)《酒國》與《西游記》的文本互涉
當(dāng)然《酒國》具有另一種特殊的激烈性,將“狂歡的宴飲轉(zhuǎn)化為吃人鬧劇”。相對比主題或是精神內(nèi)涵,在比較《酒國》與中國四大名著中文本互涉可以發(fā)現(xiàn),相比之下的《西游記》同《酒國》更為接近,因為在《西游記》中“吃人”的主題幾乎一直貫穿全文,最容易讓讀者直面的文本互涉是關(guān)于它們與《西游記》的“殘酷”和“妖精”的特點密切關(guān)聯(lián)。
在《西游記》中妖精千方百計要吃的唐僧肉既鮮美又能延年益壽,童子肉也同樣的讓各路妖精趨之若鶩,和《酒國》更有關(guān)的是《西游記》也多次提及了童子肉的鮮美,吃童子的心肝可以長生的說法是中國美食史上的重要組成部分。《酒國》中腐敗的官員們?nèi)绱藷嶂杂凇笆硧搿保l(fā)展成產(chǎn)業(yè)鏈,可謂是吃到了畸形的極致,文中多次提到了肉孩的神奇鮮美,“舌尖上的味蕾都跳動起來了”。不同的是,《酒國》中是出現(xiàn)了真正吃的行為和思想的不斷轉(zhuǎn)變,重點放在了“吃”之后一系列的行為發(fā)展,而《西游記》中著重的是“爭逐想要吃”這一過程的詳細描述,而不在于吃的行為動作。
結(jié)語
對于莫言筆下的《酒國》這個巨大而深刻的象征體,其“文本世界的真實來源于現(xiàn)實世界的真實,而文本的荒誕也來源于現(xiàn)實的荒誕。文本與現(xiàn)實形成互證的意義結(jié)構(gòu),使文本‘反思現(xiàn)實的價值凸顯出來”。[5]這的確符合小說文本與作家感知到的現(xiàn)實相關(guān)涉的實際。因為有了作者自我世界的感知,所以在文本中所包含的豐富性不言而喻。對于文本互涉性問題的討論,我們知道文本內(nèi)部、文本之間和文本與現(xiàn)實之間這三方面的互涉都是共同為了這個亦真亦幻的“酒國”而產(chǎn)生。來源文本,超越文本,只要讀者能從主體角度進行自我反思和社會反思,必然懂得個體與社會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兩個方面,既然無法抗衡社會的壓力,可以試圖在二者之間達到一種和解,并力圖去超越這種不合理。這就是文本互涉性研究所給予的一種勇氣和價值。
【參考文獻】
[1]張姣婧.論《酒國》的個性化創(chuàng)作特色[J].名作欣賞,2013.
[2]付艷霞.莫言的小說世界[M].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3]莫言.酒國[M].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
[4]張磊.百年苦旅:“吃人”意象的精神對應(yīng)——魯迅〈狂人日記〉和莫言〈酒國〉之比較》[J].魯迅研究月刊,2002.
[5]黃善明.一種孤獨遠行的嘗試——《酒國》之于莫言小說的創(chuàng)新意義[J]. 當(dāng)代作家評論,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