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作為觀念作為觀念……
梁舒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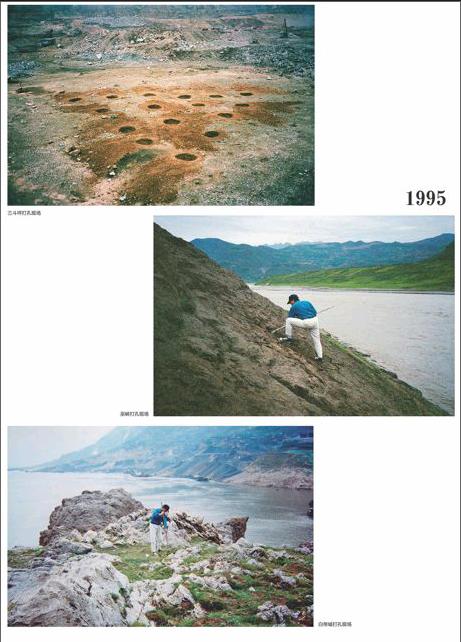
在面對云譎波詭、光怪陸離、不可名狀而又神秘兮兮的(或自詡的)“當代藝術”時,資深外行和資深內行們好奇與反思的也許是同一個問題—什么是“當代藝術”?或者說這種藝術和其他藝術區別何在?其實,旨在回答這一個問題的著述已然汗牛充棟,但越是這樣,反而越是助長了當代藝術的曲高和寡。其實,在諸特征中,有一點最為明顯又最易被忽略:與“傳統藝術”相比,“當代藝術”更容易被語言精確地描述(無法描述只能說明君還沒有找到此作的那個“點”)。例如,對于一件傳統的古典肖像畫,你盡可以用“雍容華貴、婀娜多姿、莊重典雅”等詞匯描述,可與此對應的圖像卻有多種可能;當代藝術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大冬天,有個人匍匐著不斷向地上哈氣。”君必能想出如此的一幅場景。因為“當代藝術”大都要表達某個想法,或者想用“藝術”的方式說點什么。為了實現這些作品傳達想法的初衷,是否還需舍文本之近,求物性之遠呢?《東方藝術·大家》的專題欄目“紙上展覽”也許能回答這個問題。
此欄目實現了理想的“策展”原理,即按照某個主題(例如“時間”“城市”“身體”等當代熱門話題)收錄、組織展覽,并圍繞這個既有主題對這些作品進行說明和初步的相關性闡釋。因此,“紙上展覽”展出的不是藝術家,不是作品,而是闡釋本身,因此才堪稱一個個有主題的“展覽”。這也許是純粹策劃理念唯一可能存在的方式(特別是在中國),因為圖片可以避免作品運輸、安裝等物質條件的限制,更不必考慮藝術家的代理關系、展覽契約、空間租賃等問題。稍等,當代藝術需要展覽空間嗎?一個藝術的行為和作品產生了,到底是產生在了彼時彼地,還是產生在了媒體的世界中?
如果非要在雞蛋里面挑骨頭,這個欄目的確也有一個問題:將不同時代和不同環境下產生的作品,用設定在前的“觀念”統攝起來,遮蔽了其原初的意義。作品與它的情境之間的關系被作品與欄目主題之間的關系所置換,這樣,作品們就自然而然成了概念們的服務生。但細思之,此舉也無可非議,因為闡釋本身也是一種關系,它會留下這個時代我們接受藝術的斑斑足跡。當然,這一切之所以可能,還是建立在一個前提的設定上—“當代藝術”一定是當代觀念的象征,同時我也想起了那句老話:“作為觀念的藝術本身也是一個觀念,循環不已(Art as an idea as an id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