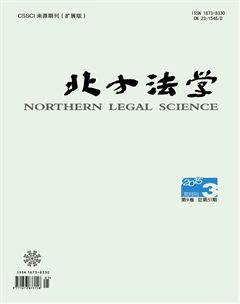誘惑偵查的是非之爭與規(guī)則細化
陳在上
摘要:盡管對誘惑偵查的爭論從未間歇,但深植其中的實踐理性與人權(quán)保障的終極目的使之生命力愈發(fā)頑強。我國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151條增設(shè)“有關(guān)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與“控制下交付”等關(guān)涉誘惑偵查的具體內(nèi)容將進一步提升偵查的法治化水準。然而,如此重要且倍受爭議的內(nèi)容卻用了及其簡略的法律條文,不僅難以消解人們對該制度存在的一貫爭議,而且極易導致其實踐“失靈”抑或“變異”。鑒于此,有必要從程序操作規(guī)范的角度對誘惑偵查的司法適用規(guī)則予以補充與細化,力促實現(xiàn)偵查主體法定化、案件范圍類型化以及判斷標準可控化等,并適時創(chuàng)設(shè)“后司法審查制度”,以促生該制度理性的最大化實現(xiàn)。
關(guān)鍵詞:誘惑偵查私權(quán)保障后司法審查制度
中圖分類號:DF7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330(2015)03-0072-07
誘惑偵查作為一種破案的手段可謂歷史悠久,具體實施的相關(guān)人員常被民眾冠以“智勇雙全”的美譽,但與此同時,對誘惑偵查的爭議亦從未間歇,并同樣被民眾不客氣地扣上“警察圈套”的帽子。如此一項令人“愛之深、恨之切”的偵查措施如何成為理性的制度,一直是各國立法者與實踐者夢寐以求的偵查法治化目標。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以下簡稱《新刑訴法》)第151條增設(shè)“有關(guān)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與“控制下交付”等類似于誘惑偵查的具體措施,①無疑對特定犯罪案件的偵查措施的法治化實現(xiàn)具有重大規(guī)范意義。然而,相關(guān)條文的闡述不夠詳盡,難以消解對該制度存在的一貫爭議,其制度價值理性難以付諸實踐。鑒于此,有必要對誘惑偵查是非爭論予以闡釋,論證其源于實踐的理論生命力以及私權(quán)保障必須之正當性根基,補充與細化相關(guān)立法規(guī)則,以生成該制度司法適用的可操作性。
一、是與非:對誘惑偵查從未間歇的爭論
(一)反對的觀點:警察不應追訴一個自設(shè)的犯罪行為
反對者認為,誘惑偵查要求具體實施偵查的人員隱蔽身份,甚至為了獲取與案件相關(guān)的訴訟證據(jù)而故意利用對方的欲望,這種具有欺騙性而且利用對方人性弱點的偵查措施,有人稱為“骯臟手段”,認為它損害國家威信,違背執(zhí)法、司法機關(guān)的道德責任,違反憲法和刑事訴訟法原則。②也有人認為國家應該防止犯罪行為的發(fā)生,但偵查機關(guān)及其工作人員作為國家的代理人參與犯罪活動無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他人實施犯罪,誘惑偵查產(chǎn)生了國家角色的失序。據(jù)此,日本學者西原春夫指出,此類偵查方法可能使人們對偵查方法的公正性失去信賴,也可能侵害國民的隱私權(quán)和人格權(quán)。③在以“正當程序”為標桿的美國刑事訴訟法中,誘惑偵查(Entrapment)是一種實體法抗辯,④即其與精神病抗辯、受脅迫抗辯、正當防衛(wèi)抗辯等抗辯事由一樣,如果被告人提出誘惑偵查之抗辯,且該抗辯具有充足的證據(jù)加以印證,被追訴人將會被無罪釋放。簡言之,一旦法院認定警察的行為屬于誘惑偵查,其法律后果不僅僅是要排除證據(jù),更重要的是,它將徹底阻止控方對被告人繼續(xù)追訴。⑤誘惑偵查之抗辯事由聚焦于警察不應該既制造又控告一個犯罪行為的觀點,對陪審團有很強的說服力。⑥即便是犯罪行為與法律規(guī)定一致,陪審團倘若對誘惑偵查的度不能接受,亦可以憑自己對司法正義的理解而做出無罪開釋的判決,即所謂的“陪審團費法(jury nullification)”。而且這種針對誘惑偵查的防御不是美國特有,英國、加拿大以及歐洲人權(quán)法院等司法體制都對此予以認可。究其原因,誘惑偵查蘊含著廣泛而又棘手且難以消弭的恒久性復雜問題,即刑事司法的目的、懲罰犯罪的重要性以及確保政府不使用過分的與不公正的方式去追訴犯罪行為。⑦
(二)支持的觀點:打擊特定犯罪行為需要特殊手段
支持者認為,刑事追訴中最為強烈的對抗無疑存在于偵查之中,其程度不亞于國家與被告人之間開展的“戰(zhàn)爭”,特別是在毒品犯罪、涉槍等案件中,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在實踐中常“短兵相接”甚至“直接交火”,難免造成魚死網(wǎng)破之下的“你死我活”之勢,這顯然迥異于審查起訴中的“和風細雨”,即便是法庭審判中的“唇槍舌戰(zhàn)”也無法與偵查活動中沖突對抗的強度與力度相提并論。組織化、智能化以及隱蔽化已然成為某些犯罪行為的顯著特征,被動型的偵查手段顯然無法適應有效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的現(xiàn)實要求。特別是針對無明顯被害人的犯罪、組織化程度高的犯罪以及在案發(fā)時間與地點有較強規(guī)律性的犯罪等情況,世界各國偵查機關(guān)紛紛調(diào)整思路,相繼采用跟蹤監(jiān)視、電子監(jiān)控、監(jiān)聽通訊、誘惑偵查等一系列主動型的偵查手段。⑧美國學者從打擊犯罪所需要的現(xiàn)實角度出發(fā),認為并不是一切犯罪行為都會公布于眾或者選擇報警,尤其是那些無明顯被害人的犯罪。而為了有效地執(zhí)行法律,維護社會秩序,就需要警察秘密參與其中才能有效實現(xiàn)對諸如此類的犯罪活動進行偵查以鎖定有效的控訴證據(jù)。因此,一名警察可能“合法”地購買可卡因以收集充分的證據(jù)去用于指控和起訴販賣毒品的人。⑨偵查程序與審判程序顯然存在較大差異,相同的訴訟手段和行為由于分屬于兩個不同的訴訟階段而獲得不同的價值評價和實效。例如,在證據(jù)集散地的審判程序中,由于偵查階段短兵相接的硝煙已經(jīng)散去,相對純粹的庭審程序雖充斥著控辯雙方的激烈對抗,但都在正當程序依法可控的范疇之內(nèi),威脅、引誘、欺騙等一些比較極端的調(diào)查手段和訴訟謀略在此難以被容忍或至少得以收斂,而偵查環(huán)節(jié)卻可能因為偵查程序獨有的殘酷本身而使之具有更高的容忍度進而被合法化。⑩面對狡詐、危險且常常是兇殘的犯罪嫌疑人,偵查人員的取證方式應當多元化且在最大限度上得到寬容和支持。因此,偵查實踐經(jīng)驗表明,特別是針對實施誘惑偵查的偵查人員而言,必然需要大為降低對其道德行為的評價,甚至對他們的“違法”行為也要理解和支持,更不能天真地期望實施誘惑偵查的偵查人員“像遵守道德和法律的公民在處理日常事務時所期待的那樣”B11模范地進行取證行為。刑事訴訟實踐也一再表明,針對特定類型的犯罪案件,唯實施誘惑偵查的人員才能出色地完成打擊犯罪的任務。
二、實踐理性與私權(quán)保障:誘惑偵查的正當性論辯
(一)實踐理性:偵查理性的必然要求
“理性”一詞似乎在各行各業(yè)中均備受青睞,因此,其在各個領(lǐng)域中被廣泛使用就不足為奇了,人們用它指代所具有的某種“能力”,也用它指代實踐活動以及創(chuàng)造活動中所體現(xiàn)的“精神”,甚至用它指代“人們在處理政治、經(jīng)濟、法律、道德等日常事務和社會實踐中表現(xiàn)出來的合理的態(tài)度”。B12實踐理性是指偵查機關(guān)及其工作人員在采取偵查方式時所具有的偵查理性,此處即是指采用誘惑偵查之時,偵查機關(guān)及其工作人員要綜合考量案件性質(zhì)、適用時的境遇、適用動因與目的等是否在合法的基礎(chǔ)上更具有合理性。B13博登海默認為,理性論證與判斷依賴積累的力量,而這些積累的力量是從不同但通常相互聯(lián)系的人類經(jīng)驗的領(lǐng)域獲取。B14而誘惑偵查措施的產(chǎn)生及其運行正是反映了刑事追訴的經(jīng)驗理性,亦符合刑事追訴的認識理性。
1.誘惑偵查反映刑事追訴經(jīng)驗理性
在美國,常從主觀標準與客觀標準兩方面分析誘惑偵查是否成立,前者著眼于被告人是否具有實施被指控的犯罪行為之主觀傾向,后者關(guān)注的則是警察的采證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guī)范。誘惑偵查抗辯的證明責任應當首先由被告人承擔,但證明存在非法誘惑偵查的標準達到優(yōu)勢證據(jù)證明的程度即可。當然,要求警察的行為構(gòu)成誘惑偵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quán)益,往往是指對嫌疑人憲法性權(quán)利的侵犯。接著,發(fā)生證明責任的轉(zhuǎn)移,由控方負擔證明責任且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證明被告人已然形成犯罪的誘因,即“無論何時機會一旦出現(xiàn),便即時且自愿去犯罪(ready and willing to commit the crime whenever the opportunity might be afforded)”。B15因此,“有關(guān)聯(lián)邦上訴法院對判決結(jié)果的研究表明:誘惑偵查的抗辯‘很容易提起,但是,要想在法律上證明它成立,卻極其困難”。B16無明顯被害人類型的犯罪行為常發(fā)生于特定人群之中,缺乏被害人報案這一常規(guī)案發(fā)機制和偵查線索,偵查機關(guān)及其工作人員若不采用諸如線人、誘惑偵查等謀略,實難偵破罪案、查獲罪證。例如,2012年8月29日的《檢察日報》就報道了曾經(jīng)是一名刑警的宋名揚(化名),為打進毒梟內(nèi)部臥底染上毒癮的凄慘遭遇。B17同樣,現(xiàn)代高隱密性、組織化的犯罪行為中,若偵查主體不積極主動出擊采用“臥底”、“誘惑”等潛行偵查謀略,很難查獲真正的主犯,更遑論斬斷犯罪的源頭,而只能徘徊于案外細枝末節(jié)的東西。B18據(jù)此,孫長永教授認為,對于特定隱蔽性特別強的犯罪行為,偵查機關(guān)常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滲透并參與犯罪的過程,引誘潛在的犯罪對象,獲得相關(guān)訴訟案件的證據(jù)并將其逮捕、起訴。B19由此可見,誘惑偵查措施的逐漸制度化并不斷完善的過程亦是刑事追訴經(jīng)驗理性不斷被接受的過程。
2.誘惑偵查符合刑事追訴認識理性
刑事追訴的過程本來存在一個歷史性悖論,打擊的都是過往或正在發(fā)生的犯罪行為,待到定罪量刑之時,裁判者只能憑借證據(jù)鏈去排除合理懷疑或達致內(nèi)心確信。對此等悖論的釋義體現(xiàn)為追溯證明的一系列活動,既要關(guān)切事實判斷,又要關(guān)注價值判斷,且刑事訴訟法所蘊含的人權(quán)保障的品質(zhì)正是源于價值判斷之上才得以不斷升華。一方面,刑事偵查工作的順利推進往往伴隨著紛繁復雜的偶然性因素;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刑事訴訟活動不可能無止境的開展下去,必然要求其在一定的期間內(nèi)終結(jié)程序追訴與實體懲罰,使其具有程序正當性與實質(zhì)必要性。
偵查活動需要在既定時間內(nèi)完成收集犯罪證據(jù),查獲犯罪嫌疑人的訴訟任務能否得以實現(xiàn)便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因素,畢竟刑事訴訟中的偵查活動顯然迥異于科學認識活動。首先,在目的上,刑事追訴的偵查目的在于收集證據(jù)證明案件事實,促成國家刑罰權(quán)的實現(xiàn),實現(xiàn)控制犯罪的目的;而科學認識的目的有“達到真理說、接近真理說、達到概率真理性說、解釋和改造世界說等不一而足”。偵查活動的目的相對簡單、明了且就事論事,而科學活動的目的卻顯得相對寬宏而且具有對于人類整體活動進步的普適性指導意義。B20其次,在對象上,偵查認識的對象是特殊的“事”——犯罪構(gòu)成諸要件;而科學認識的對象是普遍的“理”——客觀規(guī)律。B21雖然不能排除針對不同案件之偵查特定情況,把一定的客觀規(guī)律作為偵查的對象,例如對于一系列有規(guī)律地出現(xiàn)在特定時間、地點的搶劫案件的偵查策略的制定往往依據(jù)于該案的“客觀規(guī)律”,但是,針對個案的歸納之“理”畢竟是為偵破個案之“事”而服務的。而“科學的唯一的目的是發(fā)現(xiàn)自然規(guī)律或存在于事實中間的恒常聯(lián)系”。B22正是在這一點上,刑事個案往往表現(xiàn)為被特定時空所局限,而不具有普適性,盡管類似案件的作案手法與偵破方法極其類似,也很難把完全相同的偵查手段適用于同類刑事案件之上,而科學的發(fā)現(xiàn)往往是事實間的規(guī)律或者恒常聯(lián)系被發(fā)現(xiàn),可以用來具體闡述或者明示相關(guān)的實踐活動。再次,在結(jié)果意義上,偵查認識主要涉及到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利益,尤其是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乃至生命等利害攸關(guān);而科學認識活動的結(jié)果往往惠及人類生活的諸多方面。因此,偵查活動往往伴隨著偵查機關(guān)及其工作人員與犯罪嫌疑人的斗智斗勇,甚至流血犧牲的過程,而科學發(fā)現(xiàn)的過程往往表現(xiàn)為不同的多數(shù)主體,甚至是不同時空下的諸多主體齊心協(xié)力地形成合力努力拼搏才予以實現(xiàn)的過程。最后,在認識的求真屬性上,偵查活動要求在一定時效內(nèi)完成,迥異于科學認識活動的一絲不茍而且可以反復驗證。因為,隨著時間的流失,不僅取證越發(fā)困難,而且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法治秩序也得以逐漸恢復,追訴久遠的犯罪行為不僅取證相當困難,增加司法成本,而且對維護社會法治程序已無現(xiàn)實需要。正是源于此,針對特定類型化的刑事案件,如隱蔽性強、組織化程度高或者無明顯被害人的犯罪案件,偵查主體采取誘惑偵查措施,也是考慮到刑事追訴的認識理性所體現(xiàn)的認識活動的有限性理論,迥異于科學認識活動的無限性理論之特質(zhì),進而理性抉擇偵查措施的必然結(jié)果。況且,對上述誘惑偵查的案件范圍,倘若采取常規(guī)的偵查方式無異于打草驚蛇之舉,在無法鎖定嫌疑人犯罪證據(jù)的情況下,反復追訴、釋放也有悖于無罪推定原則與禁止雙重歸罪規(guī)則等諸多國際性條約所蘊含的法治化要求。
(二)私權(quán)保障:偵查理性的終極目的
任何社會均須有保護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而且社會必須有權(quán)逮捕、搜查、監(jiān)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這種權(quán)力運用適當,這些手段就是自由的保衛(wèi)者。B23社會秩序的和諧穩(wěn)定亦是國家對私權(quán)保障的最大出發(fā)點與歸宿,而作為特殊偵查措施的誘惑偵查行為的實施之緣由,正是考慮到相關(guān)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尤為嚴重,但又囿于取證的艱難,不得不采用蘊含一定欺騙性的誘惑偵查行為,以達致社會秩序的安寧,也從終極意義上實現(xiàn)私權(quán)保障的法治化。
早在1789年,法國《人權(quán)宣言》第4條即明確規(guī)定,“自由在于能夠做不損害他人的任何事情”;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導師恩格斯也認為,國家為了防止利益沖突者在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nèi)”。B24德國著名學者馬克思·韋伯也把保護個人與公共秩序作為國家的基本功能之一。B25盡管誘惑偵查與私權(quán)保障之間特別是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quán)利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與沖突,但是當國家唯此方能有效地保護社會良好秩序時,對特定類型的犯罪行為采取誘惑偵查的取證行為就具有維護社會秩序,進而保障大多數(shù)人的合法權(quán)益之正當性根基。從根本上說,偵查主體實施誘惑偵查最為直接之目的是為了獲得打擊某種犯罪行為的有力證據(jù),而基于犯罪行為人逃避訴訟的本能障礙以及案件證據(jù)難以恢復的事實障礙,唯有主動型的誘惑偵查行為的實施方能有效實現(xiàn)偵查之目的。也只有實現(xiàn)對犯罪行為的最終有效控制,才能實現(xiàn)社會良好秩序,并最終有效保障生活在其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的自由、平等等基本的權(quán)利。因此,誘惑偵查的采用在其終極意義上與私權(quán)保障的終極目的具有一致性。
三、補充與細化:誘惑偵查司法適用的完善
誘惑偵查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時也存在越界侵犯人權(quán)的隱憂。因此,謹慎且理性地對待誘惑偵查的態(tài)度是:一方面允許偵查機關(guān)對特定案件實施誘惑偵查手段;另一方面,法律也要為偵查主體采用誘惑偵查設(shè)置必要的底限,以確保誘惑偵查的程序理性。
(一)偵查主體法定性
鑒于誘惑偵查運行的特殊性,誘惑偵查的主體必須是法定偵查權(quán)的享有主體。《新刑訴法》第151條規(guī)定“可以由有關(guān)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表明實施隱匿身份偵查的主體既包括公安機關(guān)的偵查人員,也包括偵查機關(guān)指派的適宜進行隱匿身份實施偵查的其他人員。當然《新刑訴法》也規(guī)定了有關(guān)人員隱匿其身份實施偵查要“經(jīng)公安機關(guān)負責人決定”,以促進此類特殊偵查措施的行為理性。然而,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了享受偵查權(quán)的主體有公安機關(guān)、人民檢察院、國家安全機關(guān)、監(jiān)獄、軍隊保衛(wèi)部門,除此之外,任何機關(guān)和個人均不享有偵查權(quán)。即便如此,筆者認為,行使誘惑偵查的主體只能是公安機關(guān)、檢察機關(guān)、國家安全機關(guān),監(jiān)獄內(nèi)的犯罪以及軍隊內(nèi)部的犯罪行為不需要采用誘惑偵查措施。社會上廣泛存在的公民設(shè)置圈套、撲捉犯罪證據(jù)、向偵查機關(guān)舉報的行為,無論是出于“懲惡揚善”或者“領(lǐng)功請賞”,甚至是“排除異己”、“打擊報復”之目的,均不能承認并轉(zhuǎn)化類似的自發(fā)性誘導調(diào)查為合法的偵查取證行為,否則,便會導致一部分人甚至不擇手段地去引誘他人違法犯罪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例如排除商業(yè)競爭對手或其他“異己”),顯然這將與誘惑偵查打擊特定犯罪進而維護社會良好法治秩序的初衷背道而馳,并為法律所不容。在特殊個案中,偵查機關(guān)亟需授權(quán)非偵查人員具體參與誘惑偵查行為時,需要經(jīng)過嚴格的審查程序,可以規(guī)定由省級以上偵查機關(guān)負責人予以審批。《新刑訴法》第151條規(guī)定的“經(jīng)公安機關(guān)負責人決定”,也就是授權(quán)縣級以上各級公安機關(guān)負責人即享有批準權(quán)。也許立法的意愿是“這種偵查不同于技術(shù)偵查,不涉及公民有關(guān)權(quán)利,且這種化妝偵查,從偵查人員的安全角度考慮,知道的人越少越好”,B26然而,只有促進對偵查人員以外的“其他人員”實施誘惑偵查的審批監(jiān)管層次的提升,才會更加有利于案件偵破的理性得以順利實現(xiàn),并且對具體實施偵查的行為人的人身安全也是一種更負責任的態(tài)度,畢竟誘惑偵查所針對的案件高風險是公認的,刑事司法實踐中受過專業(yè)訓練的偵查人員尚且難以保證完成偵查任務,“其他人員”是否適宜擔當此任更須經(jīng)過審慎地甄別。
(二)案件范圍類型化
《新刑訴法》第151條規(guī)定:“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隱匿身份實施特殊偵查。“為了查明案情”只是一種目的性條件,所有刑事案件無不具有此種目的,關(guān)鍵是其必要性條件的限定問題,即在采用普通的偵查措施無法實現(xiàn)特定案件的偵查目的之時,即構(gòu)成了法定的“必要的時候”。然而存在一種兩難的情況:一是如果不對“必要的時候”加以具體化描述,“必要的時候”可能會因為偵查主體的理解差異而被泛化;二是如果對“必要的時候”加以具體化釋義成特定的罪名,可能又會因為個案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影響此類偵查措施的及時有效采用。權(quán)衡其利弊,將誘惑偵查的案件犯罪作類化限定而不是具體的罪名限定是符合“相對合理主義”的現(xiàn)實情況下的理性抉擇。首先,應當對適用誘惑偵查的案件范圍限定于無明顯被害人的犯罪、組織化程度高的犯罪以及在案發(fā)時間與地點有較強規(guī)律性的犯罪,這樣可使偵查機關(guān)采用此類偵查措施具有明確可控性。其次,對于特定情形下的個案采用此類偵查措施,規(guī)定審批監(jiān)管條件的層次提升即可,例如授權(quán)省級以上公安機關(guān)批準或同意方可實施。無明顯被害人的犯罪往往侵犯公共利益,例如毒品犯罪,偽造貨幣犯罪,組織、介紹賣淫犯罪等,在這些犯罪案件中,常常缺少被害人報案因素,致使案件證據(jù)難以固定,破案難度增加,唯誘惑偵查才可以成為打擊此類犯罪的有力手段。組織化程度高的犯罪往往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例如走私犯罪、黑社會性質(zhì)犯罪等,不借助誘惑偵查措施難以獲得有力的證據(jù)去懲治此類犯罪。對于案發(fā)時間與地點有較強規(guī)律性的犯罪也存在證據(jù)即時流失的問題,而借助誘惑偵查措施便能在獲得此類犯罪案件證據(jù)方面達到立竿見影之效。將誘惑偵查的案件范圍加以限定就能在有效打擊犯罪與防止權(quán)力濫用方面達到一個理性的均衡。顯然誘惑偵查倘若在偵查各類犯罪活動中被廣泛運用,就難免會傷及無辜公民的合法權(quán)益,而伴隨著偵查活動的逮捕、搜查、監(jiān)禁亦會被濫用。如果犯罪嫌疑人廣泛存在被誘騙進入“警察圈套”之嘆,自然會生出“上當受騙”的情緒,傷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尊心,使其抵制起訴與審判,也最終會導致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大為降低,反而會影響到社會法治秩序的和諧穩(wěn)定。
(三)判斷標準可控化
《新刑訴法》第151條規(guī)定,在實施隱匿身份偵查的過程中,“不得誘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fā)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來防范此類偵查措施的風險。“不得誘惑他人犯罪”主要是指不得進行“犯意誘發(fā)型”誘惑偵查,即不得誘使他人產(chǎn)生犯罪的意圖。“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發(fā)生重大人身危險的方法”是考慮到偵查人員實施誘惑偵查,將不可避免地打入犯罪分子內(nèi)部,有時候為了取得對方的信任,獲取相關(guān)犯罪證據(jù),不得不與犯罪分子一起實施一些違法犯罪活動。但參與違法犯罪活動有個界限,就是不得危害公共安全,不得造成他人重大的人身危險。然而,對此類判斷標準看似清晰,卻很難具體操作。試想一下,為了有效獲取有罪證據(jù),具體實施誘惑偵查的工作人員參與到違法犯罪活動之中具有實踐理性的同時,為了不過度危險地暴露自己,很難有效控制犯罪結(jié)果的指向性,畢竟實施誘惑偵查的人員只是參與而不是主導犯罪活動,有時候拒絕行為很可能導致誘惑偵查措施的失敗甚至危及到其人身安全。筆者認為,應結(jié)合主客觀兩方面的標準來判斷誘惑偵查的取證方式是否合法,予以抉擇誘惑偵查獲得的證據(jù)是否可采:一方面,主觀標準主要證明被告人是否具有實施被指控犯罪行為的傾向,證據(jù)可以圍繞案件發(fā)生的時間、地點等情形,以及被告人是否有相關(guān)犯罪記錄以及品格證據(jù)等;另一方面,客觀標準主要審視偵查人員的取證行為是否逾越了正當行使法定偵查權(quán)力的底限。在美國聯(lián)邦司法系統(tǒng)以及適用誘惑偵查主觀標準的州司法系統(tǒng)中,如果警察偵查行為的“受害人”原本具有實施被指控犯罪的傾向,那么,無論執(zhí)法官員的引誘或威脅行為(inducement and threat)多么極端,都不可能構(gòu)成誘惑偵查。但是,如果偵查行為確實令人震驚,那么,其也僅僅是“有可能”構(gòu)成違憲而需要有條件地啟動阻止對原本具有犯罪傾向的人進行刑事追訴的程序。在刑事司法實踐中,一般根據(jù)主客觀標準將誘惑偵查分為“犯意誘發(fā)型”與“機會提供型”兩種,后者較之前者而言,被告人更加具有犯罪故意的主觀傾向,偵查主體客觀上更加遵循公權(quán)力介入私權(quán)利的黃金法則——比例性原則的要求。主客觀標準思維下誕生并指導刑事訴訟實踐的規(guī)則對誘惑偵查的認定與評判提供了可控性的程序性支撐,既有利于實現(xiàn)打擊特定犯罪之目的,也有利于規(guī)范偵查主體的取證行為。因此,正是這種主客觀方面雙向被認可的誘惑偵查行為最大限度的平衡了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quán)的沖突,理所當然地被體現(xiàn)到越來越多國際公約與諸多國家的刑事立法、司法之中。
四、未盡的課題:創(chuàng)設(shè)后司法審查制度
鑒于誘惑偵查的具體實施主體常常是秘密地采取偵查行為,在某些特殊案件中,他們會具體參與違法犯罪活動,既有身不由己的無奈,又有義無反顧的豪邁,甚至有玉石俱焚的悲壯,稍有不慎,前功盡棄。因此,考慮到該項權(quán)力的具體操作過程可能會對私權(quán)利造成嚴重甚至不可挽回的影響,該行為具體負責行使的機關(guān)就不應當是該程序啟動之決定機關(guān),沒有了監(jiān)督制約的權(quán)力必然會被濫用。在我國現(xiàn)有的刑事司法體制下,偵查機關(guān)不宜既是該項權(quán)力的具體組織實施者,又是該項權(quán)力啟動的直接決定者,誘惑偵查啟動權(quán)的審查應當具有中立性,至少現(xiàn)階段應當盡可能地增加其中立化因子,才能保障其依法行使,進一步發(fā)揮其理性作用,否則對誘惑偵查的控制與監(jiān)督便淪為空談。
一般認為,理性的司法審查機關(guān)當屬中立的裁判機構(gòu)——法院。然而現(xiàn)階段,我國憲法以及刑事訴訟法均規(guī)定公、檢、法“平起平坐”(即“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性指導之下”),法官沒有高于警察或檢察官的權(quán)威,甚至在“審判機關(guān)承擔追訴職責”的現(xiàn)有情況之下,空談法院的審查中立性不僅于事無補,而且會引起無盡的爭論導致改革的無限拖延。B27而相較之下,作為法定監(jiān)督機關(guān)的人民檢察院不僅從現(xiàn)有的法律格局下容易理順,而且檢察機關(guān)亦有能力對實施誘惑偵查啟動的合法性予以適度審查,理由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人民檢察院作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guān)符合我國的憲法架構(gòu),具有監(jiān)督偵查權(quán)與審判權(quán)的憲法職能,檢察機關(guān)對誘惑偵查實施監(jiān)督契合現(xiàn)行法律對刑事訴訟國家專門機關(guān)之間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配置;另一方面,人民檢察院審查誘惑偵查的合法性更符合職業(yè)化的要求,能夠以最低的司法成本收獲最大的實踐效益,從而極大地降低制度的試錯成本。B28具體操作程序為:偵查人員認為需要實施誘惑偵查措施時,先將案件情況報至本部門負責人審批,同意后提交人民檢察院偵查監(jiān)督部門予以審查,最后經(jīng)檢察長簽字同意后方可實施。在一些特殊緊急的個案中,經(jīng)偵查機關(guān)負責人同意后可以先行實施誘惑偵查措施,事后應及時按照上述程序上報于人民檢察院并取得授權(quán)確認。
顯然,從檢察機關(guān)承擔控訴職責的角度看,此種監(jiān)督難以達致超然中立,盡管人民檢察院也屬于司法機關(guān),但此種行為也難以界定為理性的司法審查行為,畢竟需要控訴的本質(zhì)更使其對此種偵查行為及其獲取的證據(jù)均情有獨鐘,甚至愛不釋手。鑒于此,對上述弊端進行有效補救的措施即為,創(chuàng)設(shè)后司法審查制度。也就是說,在上述檢察機關(guān)適度審查的基礎(chǔ)上,在針對該程序的瑕疵進行程序性補救設(shè)置,以促進該項制度設(shè)計與運行的合理性。后司法審查制度的啟動與運行是以檢察機關(guān)監(jiān)督式樣的審批為必要條件,僅在權(quán)利人對由檢察機關(guān)審查批準決定的誘惑偵查行為以及獲取的證據(jù)的合法性存在爭議的情況之下,其才有權(quán)申請法院對相應的誘惑偵查行為及由此獲得的控訴證據(jù)予以審查,以取舍證據(jù)的可采性。
Abstract:Though the debate on entrapment investigation is ever lasting, its rationale of practice and ultimate purpos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erein is ongoing popular. The current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has added provisions in Article 151 that “relevant personnel conceals his identity to implement investigation” and “controlled delivery” related to the entrapment investigation, which has further improved the ruling of law. However, the pertinent provisions are not specific enough, which failed to eliminate the controversies and even led to “malfunction” or “deviation” in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upplement and refine applicable rules on entrapment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dural and operational norms, and to require the investigating subject to be statutory, the case scope to be categorized and the decision making standard to be controllable. Besides, the “pose-judicial review system” should be properly established to achieve the maximized effect of the rationale for this system.
Key words:entrapment investigationprivate rights protectionpost-judicial review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