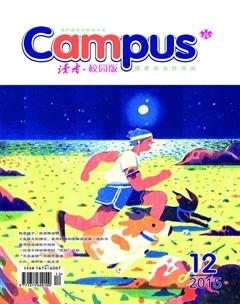青春期里的文藝病
葉子
1
文藝是一種病,很多時候就像沒吃藥。
一開始表現出文藝范兒的,是以桂綸鎂、安妮寶貝為首的一幫文藝青年。她們追捧音樂、電影、旅游,戴黑超眼鏡、穿棉布裙子、赤腳穿球鞋。
最早見識文藝范兒, 是我上小學的時候。學校的老師里有一個上海知青,教我們音樂。他的穿衣打扮、言行舉止,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非常有文藝范兒。想想吧,在全國人民一律穿布鞋、留短發、著裝以藍黑色為主的時代,唯獨他, 蓄著電影《追捕》里矢村警長的長鬢角,翻著潔白挺括的襯衣領子,常年一身素白。每次上課之前,他從長長的過道里款款走過來,神情冷峻,衣袂飄飄,幽暗的樓道成了他的背景,襯得他越發像一只仙鶴。
桀驁是要本錢的。“仙鶴老師”能演奏手風琴、笛子、揚琴、吉他等好幾種樂器。同學們在校園里玩耍時,能聽到從他家窗戶里飄出來的美妙樂聲, 惹得一幫孩子踮著腳尖,趴在他的窗臺上往里看,眼饞得不行。
那時候,媽媽跟“仙鶴老師”是同事,也不知怎么說動了他,“仙鶴老師”答應教我一樣樂器。那是個三伏天的晌午,校園里的蟬叫得很兇,媽媽牽著我的手,第一次走進“仙鶴老師” 的宿舍。消瘦的他坐在一片素白里,渾身散發出幽幽冷氣,招我近前,用鼻孔看了看我的眉眼, 又比量了一下我手指的長短, 這才吁了一口氣,從墻上摘下一把琴來。我是第一次看見那種樂器,肚子圓圓的, 脖子短短的,像吃胖了的吉他。他說:“這叫月琴,用一塊有機玻璃撥片撥弦兒,能彈出很好聽的曲子,評彈,你知道嗎?”我瞪著眼睛,一個勁兒地搖頭。
那年夏天天氣轉涼的時候,“仙鶴老師”突然回了上海,一去就再沒有回來, 媽媽替我惋惜。我那時不懂事,覺得學琴占用了我玩的時間,按弦兒按得我手疼, 學不成正好。
上中學后,因為愛看小人書,喜歡在書眉和頁角畫小人,美術老師認為我有藝術細胞,就極力攛掇我學畫。媽媽特別支持我,親自動手給我做了小畫板,買了顏料和畫紙。想著每天下午不用上自習課, 可以去畫室涂鴉兩個小時,跟玩兒一樣,我覺得挺美。
2
時間流水般過去,我稀里糊涂地混進了美術學院。大學里的頭一件事,就是扮藝術范兒。那時候流行扮披頭士,細腿褲配大褂。我穿3 7碼T恤剛剛好,偏買成42碼的,大到一不小心領口能從肩膀上掉下來。再用丙烯顏料,在大褂前襟畫上流血的傷口或萬箭穿心的玫瑰。我跟一個同學商量好,兩人買同款不同色的鞋子,彼此交換,一只腳一種顏色,在校園里招搖。外系的人這樣“夸”我們: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流浪的,仔細一看,是美術學院的。
畢業那年,學院外聘浙江美術學院的全山石老師輔導我們的畢業創作。全老師一頭銀發,白襯衣、灰長褲,腳上一雙布鞋,臉上一貫的淺笑。看到我牛仔褲上挖出的破洞問:“這樣會涼快些,是吧?”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回,全老師給我們上人體課,畫到一半時,那個老年模特突然嘔吐了,人體畫室是密封的,氣味難聞極了,同學們都跑到窗戶邊透氣。全老師放下畫筆,給模特披上衣服,蹲下身,試試模特額頭的溫度,詢問他要不要去醫務室。模特老人搖著兩只大手,說沒事。實在拗不過去了,他才低聲說:“院里要是知道我病了,我的模特工作怕就保不住了。”全老師握住老人的手說:“放心,先看病,有我呢。”
那一年,全老師的課結束后,同學們一改嬉皮頹廢的風格,重新變得干凈斯文起來。后來想想,以我們那時的淺薄和膚淺,一時還不能領悟全老師的高風亮節,但全老師那種使人如沐春風的學養和清氣,在潛移默化中我們隱隱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藝范兒。
3
亦舒說,女人有兩種:一種是打麻將的,一種是看《紅樓夢》的。文藝“未遂”后,我憋著一腔看《紅樓夢》的矯情,“撲通”一聲,落在升斗小民的麻將桌旁,讀過的書、學過的畫全都換了飯吃。當初逼著我學琴、棋、書、畫的老媽,徹底改弦更張,嫌我看書費眼睛,畫畫耗精神,全是四六不著調的營生,不如學著熬湯炒菜、養娃過日子正經。一粥一飯的小日子過下來,通身上下連文藝的皮毛都不剩了。
生活,斑駁了虛飾偽裝,讓真相水落石出。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只是文藝的形式和表象, 真正的文藝范兒,是感受和發現平淡中的詩意、庸常中的智慧,是發自內心的悲憫和善良, 是那些我們用手摸不著、用眼睛看不到,卻能用心感受到觸及我們靈魂和精神的東西。
諱疾多忌醫,文藝病人也忌諱別人說他文藝。某一天,朋友跟我說:“你吧,行事做人, 多少有點文藝范兒。”陡然被人揭了短,我惱羞成怒:“你才文藝呢,你們全家都文藝!”
(志墨摘自《時代青年·悅讀》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