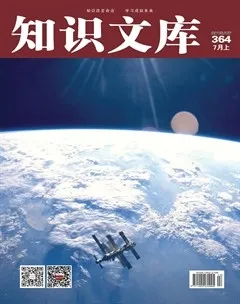梁啟超對民國初年“官場病”的批評

1915年,從政二十年的梁啟超流露出退隱之意,一個標志性的行動就是創(chuàng)辦《大中華》雜志。
梁啟超真正離別政壇,是在20世紀20年代,此時的暫時轉向,除了“政治與政治理想相去甚遠”(《〈大中華〉雜志發(fā)刊辭》),因而對現(xiàn)實政治的狀況失望外,他回國后與袁世凱合作,受到政界和知識界的批評以及1915年返粵遭暗殺威脅,也都是促發(fā)因素。不過,短暫的退隱,讓梁啟超可以稍稍拉開距離看待浸淫已久的晚清民初政壇。其反省固然包含個人的從政經(jīng)歷,而矛頭所指則主要是民初的“官場病”。所謂的“官場病”集中于兩個方面,其一是有知識的人熱衷于為官,其二是官場道德的敗壞。
在《吾今后所以報國者》中,梁啟超檢討了近20年參政之“敗績失據(jù)”。他說:“吾二十年來幾度之閱歷,吾深覺政治之基礎恒在社會,欲應用健全之政論,則于論政以前更當有事焉。而不然者,則其政論徒供刺激感情之用,或為剽竊干祿之資,無論在政治方面,在社會方面,皆可以生意外之惡影響,非直無益于國而或反害之。故吾自今以往,除學問上或與二三朋輩結合討論外,一切政治團體之關系,皆當中止。用到生平最景仰之師長,最親習之友生,亦惟以道義相切劘,學藝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論行動,吾決不愿有所與聞,更不能負絲毫之連帶責任。”關于今后的“報國之法”則謂“吾將講求人之所以為人者而與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國國民也,吾將講求國民之所以為國民者而與吾國民商榷之”。這其實是決定扮演以輿論影響社會的知識人角色。
梁啟超一向對于社會上有知識的人,亦即今日所謂中產(chǎn)階級,寄托著希望。他曾經(jīng)說:“大抵一國之中流以上之人士,必須有水準以上之學識,然后其國乃能自立于天地”。(《良知(俗識)與學識之調和》)
然而,在民國初建的二三年,他所看到的卻是有知識的人蜂擁入官場。這中間有晚清的老官僚,也是民初的新進,有海歸的留學生和國內各類學校的畢業(yè)生,無論何人都有一個共性,就是以當官為謀生的手段。
一般來說,引起社會上有知識者麇集于官場有兩個條件:一是社會的容量不足,不能吸納精英安身;二是官場中確有非同一般的利益,且提供名利雙收的機會。在民初,這兩個條件似乎都具備,民國從晚清繼承下來的龐大的行政系統(tǒng)仿佛可以容納一切有知識的人,而有知識的人擁入官場的直接動因,即梁啟超所說“夫官業(yè)所以最足歆動人者,則勞作少而收入豐也。”(《作官與謀生》)
梁啟超不是“小政府、大社會”的信奉者,但他發(fā)現(xiàn),有知識之人悉輳集于政治一途,卻未見政象有所好轉。他之所以只是規(guī)勸,而非嚴厲地指責,是擔心自己的指責一旦過度,會讓百姓對政治徹底地失望,從而遠離政治。(詳見《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
面對民初從政者為私心所縛,“奔兌傾軋者無所不用其極”,梁啟超的規(guī)勸顯得十分無力,他說:“吾以為恃作官為謀生之具者,天下作計之拙,莫過是矣。”(《作官與謀生》,下同)麇集于官場,讓有知識者既不能發(fā)揮個性,又因為供大于求,必有激烈之競爭,其間“雜以卑屈之鉆營,陰險之侵軋”。“故雖以志節(jié)之士,一入乎其中,則不得不喪其本來,而人格既日趨卑微,則此后自樹立之途乃愈隘”。
但梁啟超更關心的還是,這樣下去,社會被抽空,社會事業(yè)無人問津。缺了社會根基,不僅百姓會對政治多所不滿,而且政治人才也無從產(chǎn)生(參見《〈大中華〉雜志發(fā)刊辭》)。最終的結果則是,理想的政治生態(tài)無以形成,理想的政府形態(tài)也無以產(chǎn)生。
梁啟超喜歡講道德。晚清以降,受西方思想影響,他既講過公德,又講過私德,還講過官德。1910年3月,在《立憲政體與政治道德》中,梁啟超就強調官德的重要。他甚至認為,在政治領域,政治家的道德程度比知識程度重要得多。因為前者可以增益,而后者則未必容易提高。
然而,經(jīng)歷與袁世凱合作失敗的挫折,梁啟超親身體驗了政客政治權術的陰險。有關袁氏其人,在《袁世凱之解剖》中已經(jīng)有詳述,集中在一點,就是不講信義,這還是與官德相關。在另一篇文章《五年來之教訓》中,梁啟超說,袁氏乃一“好用權術而善用權術之人”,然“試觀古今史乘所載,以智機自豪之士,能全始終者究有幾人?”
老師與學生的區(qū)別,大約就是前者老成持重,而后者血氣方剛;前者收斂,后者不僅張揚,而且還喜歡替老師出頭。在批評袁世凱“尊孔”時,梁啟超的言論就遠不如其學生藍志先“海內人士讀之,多駭汗譙訶”(語出梁啟超)的《辟近日復古之謬》一文激烈;在批評官德不修時,梁的另一學生吳貫因激烈的程度也遠超其師。
吳貫因干脆把政治與道德二分,以為“政治家的道德與一般人的道德截然相反”。他列舉了六種官場道德,說明它們對進入官場的知識人的腐蝕作用,以警告那些清明而有操守之士慎入政壇。(參見《政治與道德》)
但此處的復雜性在于,潔身自好的知識人把政壇看做罪惡淵藪,固然有深刻揭示其本質的作用,但完全置之于不顧,則容易在客觀上促進后進者對官場惡德的認同感。好像凡入政壇者必須以厚黑為原則,否則無法生存。這樣下去,政治的理想就更不可能有立足之地。
梁啟超是在一個并不健全的體制下思考政治,因而他更多地以一己之經(jīng)驗,提倡政治道德,且以理想的道德標準來想像政治的理想狀態(tài)。實際上,政治道德與現(xiàn)實政治最大的不同,前者是政治理論家書齋里的討論,而后者則是一群熱衷于此的人的博弈。任何的政治都是以現(xiàn)實性為基礎的,利益的博弈,往往摻雜著個人因素和利益傾向,因此,政治本身都需要有體制的規(guī)范和制約。但即使如此,政治利益的內涵都不可能只有“私”而沒有“公”。在政治領域,公與私的界限不見得能夠截然分割,大多數(shù)時候只能是以“公”的面目和部分體現(xiàn)“公”的實質,實際上也摻雜著“私”的考量的樣態(tài)出現(xiàn)。
這樣說,也許陷入到了梁啟超理想政治或者說精英政治的想像之中。其實,現(xiàn)代政治與其他職業(yè)一樣,首先是一門職業(yè)。既然是一門職業(yè)就無須成為精英匯聚的唯一目的地。但作為職業(yè),它卻需要基本的職業(yè)操守和職業(yè)道德,這個操守和道德像超市收銀員面對顧客說“歡迎光臨”或者“歡迎下次再來”一樣,不一定發(fā)自內心,卻是必須執(zhí)行的,否則就應受到相應的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