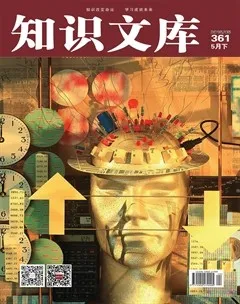守護留守兒童 鄉村教師當師又當“媽”
大石山區的夏悶熱難耐。天蒙蒙亮,趁著一絲涼意,韋春麗決定早點起來,把孩子們的午飯提前做上,把這僅有一個老師的學校和教室收拾收拾,一會兒,她的學生,23名一至二年級的孩子們就要陸續到校了,韋春麗簡單忙碌的一天便開始了。
弄為教學點位于廣西大化縣最偏遠鄉鎮之一的板升鄉弄勇村的弄為村組,學生來自本弄還有周圍山弄的適齡兒童。清晨,孩子們一大早趕到學校,有的要走1個小時的山路。中午韋春麗會為他們備好營養餐,下午4點孩子們放學。
周五放學后,韋春麗便徒步下山,從路邊老鄉家推出寄存的摩托車,30分鐘抵達板升鄉。那里有往返大化縣城的班車,在鄉間盤山公路再顛簸近3個小時后,韋春麗才能回到位于大化縣城的家。每個周日,韋春麗要經歷同樣的路線,天黑之前返回弄為教學點,并且帶回她和孩子們一周需要的糧食肉蛋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弄為村組位于國家級貧困縣大化縣西北部,離板升鄉十幾公里,距大化縣城100多公里,是瑤族聚居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區,聯合國糧農組織官員認為這里是“除了沙漠以外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
有條件的家庭通過城鎮化建設爭著搬出了大山,把孩子送到了城鎮學校讀書。但更多村民還生活在這個“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全鄉還有48個教學點,至少有48名如韋春麗一樣的老師,每天在大山深處孤獨寂寞地教授管理著近千名一到三年級的孩子們,他們大多數都是留守兒童。
從山下的鄉村公路徒步攀登40分鐘,轉過幾座大山,弄為村就處在兩座大山之間的山凹地帶,全村不過八九戶人家,弄為教學點就坐落在村口一塊不大的平地上。
村里依山谷可見不同年代的房屋,早已被煙熏黑的草房和木屋在石板混磚的新房中顯得沉悶破舊,村里基本見不到村民,一位上了歲數的老婆婆倚門坐在石板房的臺階上。學校教室側面一個10米見方的水塘,積水已經渾濁發綠,散發著腥臭的味道,幾只老母雞圍著水塘來回地踱著步子。教室門口的空地上,一只老狗懶散地躺在中央,眼皮微微顫動,沒有一絲生的欲望。
教室外,幾個學齡前兒童時而追逐從身邊走過的大公雞,時而踢一腳那只橫臥的老狗,更多的時候會攀上石塊趴在教室外的窗臺上,雙手托腮地望向教室,凝視一會兒正在上課的老師和學生們。
“小熊和小鹿,xiong、熊、熊,lu、鹿、鹿,nai、奶……”伴著韋春麗領讀課文的聲音,孩子們稚嫩清脆的讀書聲回蕩在深谷,回蕩在夏日的晨曦里。韋春麗一遍遍地糾正著孩子們的發音,一遍遍地拼讀示范……在這片貧瘠的大石山深處,鄉村教師就像一粒頑強的火種,堅守在落寞的鄉村,行走在崎嶇的山路,一遍遍點燃身邊這些懵懂孩子的希望。
凋敝山村里的讀書聲
“糟啦,都冒啦!”記者的到來,打亂了韋春麗平時一個人的有序狀態,教室旁邊的廚房里,給孩子們正在燜煮的米飯溢了一灶臺。
廚房角落里一只水管從窗外伸進來,正好流進窗下的水盆,水管連接著屋后老鄉家的集雨池。政府最新配備的電冰箱,和嶄新的包裝盒并排放在一起,占去了廚房不少空間。韋春麗指著灶臺上大大的電炒鍋以及電飯煲說,“這些都是新配的。以前給小孩們燒飯,鍋小,煮三鍋才夠吃。現在好啦,一個小時就煮好一鍋飯。”
“等下上完課再煮肉炒菜,現在很快的。”收拾好灶臺,韋春麗一邊擦手一邊來到教室另一側的宿舍,10平方米的房間,除了單人床和書桌,塑料衣柜正好擋住了門口的視線。收拾了床鋪,韋春麗抱起桌上批改了一半的作業走到教室,孩子們陸續已經開始了早讀。
“阿弟,回來上課嘍。”
“海華,昨天的作業很好。”
“邊浩,寫字要認真哦。”
……
8點10分,韋春麗一邊點評一邊發放孩子們的作業。學生們基本到齊,教室里一片嘈雜。幾個孩子發現記者在拍照,便跑過來在鏡頭前跳來跳去,甚至有頑皮的孩子開始搶記者手機要看個究竟……教室外,幾個咿咿呀呀的學齡前孩子擠在韋春麗的身后,互相推搡打鬧著。
“一年級的寫這個,邊浩、海龍、榮福……每個字寫4行。文豪,寫5行。”韋春麗指著剛剛在黑板一側寫下的生字說道。
布置完作業,上午的語文課就開始了,韋春麗在黑板的另一側寫上了二年級課文題目:《小熊和小鹿》,并且領著學生們開始朗讀。
習慣了“復式教學”的韋春麗忙碌有序。“早上兩節、下午兩節,語文教認字、拼音,數學也是按教學大[微博]綱的要求去教的。”課后韋春麗笑著對記者說。
教學對韋春麗來說不是問題,自己有多年“代課老師”的教學經驗,并且經過“河池市教師進修學校”的專業培訓,手里還攥著一張“函大”的文憑。
到弄為教學點當老師已經快2年,說“自己老了,需要鍛煉”的韋春麗44歲,看上去還很年輕,粉紅色的雪紡短袖衫映得臉頰紅彤彤的。
當初選擇到弄為,韋春麗是下了一番決心的,“我這個年紀到外面打工也很難的,后來參加了縣里教學點老師考試,我就來了,要不就等于放棄了教師資格。”
盡管在大化縣城買了商品房,但丈夫常年在廣州打工,兩個兒子,一個服兵役,一個在柳州讀大學。僅靠丈夫的打工收入,韋春麗一家還是很難維持日常的開銷。“還有三年房貸要還,每個月2000塊。”韋春麗伸出兩個指頭笑著,“在家里是一個人,在這里也是,還好吧。”
加上鄉村教師補貼,韋春麗每個月能拿到2000元。周末韋春麗都要下山回家,去購買自己和孩子們一周的生活必需品。
“這么高的山路,你怎么背上來?”記者剛剛徒步上山已累得汗流浹背。
“東西多我就叫學生下來接我,有時做工回來的村民也會幫我。”一般情況下都是她自己背上山。
除了用電有所保障,弄為沒有手機信號,在山下有信號的地方,韋春麗才能和家人通上一次電話。電視需要購買接收器,韋春麗索性買了一個平板電腦,周日回家,下載一些電視劇回來看,“哎呀,我那個平板也老壞的。”
教室里很多孩子看上去年齡很小,韋春麗說很多都不到上學年齡,但家長[微博]都愿意把孩子早早送過來,“當地人講瑤話,我們外鄉人也聽不懂。有些小孩子等上一年級還什么都不會,教起來很麻煩。他們提前送來,我都會收的。”這部分孩子屬于計劃外入學,韋春麗就想辦法替他們購買教材,甚至學會了網購,“這里家家都四五個小孩,父母又都外出打工,跟著爺爺奶奶在家,很多小孩都是沒人管的。我還有這能力,能多管就多管一些吧。”靦腆的韋春麗說起這些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兩節語文課后,韋春麗安排孩子們做作業,自己便返回廚房開始為孩子們準備中午的飯菜,一會兒,孩子們便可以享用他們的營養餐了。
老師就是你們的爸爸媽媽
大山遮蔽了夕陽,暴曬了一天的弄勇小學在晚飯后迅速涼快了。忙碌了一天的藍香利愜意地坐在操場邊的石凳上,因為每天的師生籃球大戰就要開始了。
“這些小孩打球打瘋了。”藍香利笑著對記者說,“每天下課都打,孩子嘛,正是愛玩的年齡,他們每天就跟著他們打。”藍香利指指幾個男老師,其中就有她的丈夫,教導主任覃任武老師。
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們長得并不高,和老師們比起來速度不慢。他們赤著腳板在粗糙不平的混凝土操場上奔跑,把一只只從老師手里搶奪下的籃球拋給同伴、拋向空中,或是直接砸向籃筐。“8:12”,操場邊,低年級的孩子們在小黑板上記錄比分,認真的樣子不亞于大賽裁判。教學樓的走廊上擠滿了看熱鬧的小女生,嘰嘰喳喳的。
從弄為教學點徒步下山,公路的盡頭就是弄勇小學。這里有227名一至六年級的小學生,寄宿率達到95%以上。孩子們的家分屬弄勇村下轄的不同村組,分布在方圓幾公里的大山深處。許多孩子們從家到學校單程往往需要走兩三個小時的山路,有的甚至更遠。寄宿上學成了大山里村級完小的普遍現象,周五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
2015年起,孩子們上學已基本不用花錢了,營養餐和免費寄宿讓山區的貧困家庭更愿意更安心把孩子送到學校去,“全包”成了父母雙雙在外安心打工的最好理由。
“這里基本上都是留守兒童,我們天天和他們在一起,比她們的媽媽爸爸和他們在一起的時間都長。”藍香利說。
弄勇小學有7名老師。藍香利是三年級班主任,每天負責全班71名孩子的全部課程和生活,藍香利的愛人覃任武同時兼顧著六年級的全部課程。夫妻老師在這所山村小學里有好幾對,因此,弄勇小學的教師隊伍比起板升鄉其他山村小學要相對穩定。
2004年,藍香利通過教學點教師考試,從距離大化縣城30公里的家鄉古河鄉來到大山深處的板升鄉弄頂教學點,2006年轉至弄勇小學,一待就是十幾年。“原來在古河鄉,由于城鎮化發展,學生越來越少,用不了那么多老師,我們就被清退了。”
“剛到板升時,日子非常艱苦,不通公路,到哪里全靠兩只腳。”那時藍香利一天掙不到20元錢,如果回趟古河鄉的家,往返路費就要60元。周末,從教學點到板升鄉趕一次集,徒步往返要近8個小時。“不敢回家,不敢搭車,那時候就是一天一天的挨日子。”
2006年,一直在家鄉打短工的丈夫覃任武通過考試來到板升鄉弄勇小學當老師,藍香利兩地分居的生活才算結束。
1994年藍香利從廣西都安師范進修學校畢業,由于是自費生,國家并不承認此學歷,藍香利只好一邊做代課老師一邊繼續函授大學的學習。后來,便認識了同為“代課老師”的覃任武,再后來兒子出生,兩人的收入難以維系家用,覃任武一度放棄“代課老師”。
“在木材加工廠,每天搬木頭、鋸木頭,都是體力活兒,非常辛苦。”閑了,覃任武還會繼續看書學習,完成函授課程。周圍的工人就取笑他,“覃老師,你讀了那么多書,有什么用,不是還和我們一樣在工地搬木頭嗎?”這件事以后,覃任武再也沒有回到過工地。
“現在我們能在一個學校一起工作,真的很好了。”如今,弄勇小學教學條件改善了很多,“國家投入很大,新建了教學樓、宿舍樓,新修了廁所,水池。”在板升鄉中學讀高三的兒子今年考上了大學,藍香利說,“希望他將來能自食其力。”
提起自己的一班學生,藍香利來了精神,“這里的孩子都像自己的兒子一樣,是看著長大的,真的有感情啊。”她總會對孩子們講,“老師就是你們的爸爸媽媽。”
藍香利說,很多剛入學的小孩不敢讓他一個人上廁所,“很危險,萬一掉進糞池呢?”老師們都是手把手地教低年級孩子生活必備的技能,“山里就是這樣,他們的爸爸媽媽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家里只剩下老人,也幫不了什么,我們老師就要多做一點啦。”
“很多家長不太重視讀書,總覺得學一點能出去打工就夠了。”藍香利說,在教學方面,老師們不敢怠慢,“如果學生成績都不好,我們也會覺得自己不合格。”
和記者聊了一會,藍香利跑回辦公室把電視機打開,孩子們愛看的少兒節目開始了,不大的辦公室里,擠進了20多個孩子。
教學樓旁邊的空地上停著一輛灰色的小汽車,是藍香利夫婦不久前購買的二手車,“2萬塊。”他們本來打算參加縣里教育局的集資建房,“太貴嘍,十幾萬元呢,哪有那么多錢。有了車,出門就省了車票錢。”
夜幕降臨,晚自習的鈴聲響起,藍香利招呼那些看電視、在操場玩耍、打乒乓球、籃球的孩子們回教室做作業。待會,檢查完作業,還要安排孩子們就寢,藍香利一天的忙碌才算結束。
山區教育的經很難念
“山區生產生活條件艱苦,盡管國家對外遷村民都有一定的政策補貼,但很多村民并不愿意搬出大山。加之越邊遠地區義務教育階段生源越多的現象,使得山區對于教師人數的需求越來越大。”一位當地負責人對記者說了實話。
據介紹,目前偏遠地區的村完小和教學點教師隊伍很成問題,“比如一個老師考到教學點,去了一年,家人有關系的就開始找人要挪啦,不想在那個地方,想到村完小,至少有幾個老師啊。教學點只有一個人,水又缺,當地語言又不通,條件很艱苦的,怎么安心工作。”
這位負責人表示,“從大化縣城到弄勇小學車程三四個小時,要是安排下鄉去板升,大家都會想‘能不能不去啊’,路真的很難走,都是在懸崖邊上轉。”感慨之后他說道,“哎,山區教育這本經真的很難念。”
就在記者發稿前,韋春麗打電話告訴記者,剛剛接到通知,自己將要結束弄為教學點的工作,到弄勇小學報到,“一位瑤族男老師接替我了。”
當記者告訴她,不久前國家出臺政策,提高對鄉村教師待遇時,韋春麗略帶緊張地說,“是的,收到啦,暑假里工資漲了八百塊,不少了,很知足啦。”然后才放松一些,“基層工作挺辛苦,但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我的付出也不算什么,談不上需要很多。”
記得那天結束弄為教學點的采訪,韋春麗從廚房出來送行,“慢慢走,我不送你們啦。”
“快去忙吧。”
“走了嗎?”剛剛那幾個趴在教室門口玩耍的學齡前兒童,學著普通話追過來問道。來了小半天,小家伙們已然熟識了我們,剛才還歡快地湊上來看我們拍照,對著鏡頭張大嘴巴……這會兒,一雙雙明亮的眼睛里卻透著茫然。
“走啦,再見!”
幽靜的大山深處,記者原路下山。繞過一座大山,伴著微微拂過的山風,耳邊忽然飄過一串稚嫩的聲音:“慢慢走……慢慢走……”在一處稍微平坦的崖邊回頭望去,那幾個只有四五歲的孩子,就這樣在距離我們50米的位置,默默地默默地跟了我們幾百米的路程,在我們即將轉過大山即將在他們面前消失時,孩子們學著韋春麗的樣子一邊向我們招手一邊大聲地呼喊著……
“快回去,快回去。”我們回應著,“不要跟了,快回去……”然而幾個幼小倔強的身影卻一直堅持站在原地。轉過一道山谷,便再也看不見他們,但孩子們稚嫩的送行聲卻始終回蕩在山谷,回蕩在下山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