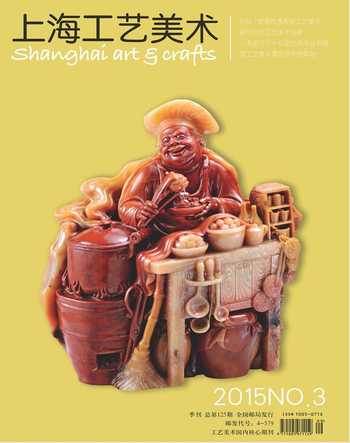程馟《顧繡》的文獻價值
徐勤


本文討論程馟《顧繡》的文獻價值,對萬歷-崇禎顧繡研究
已有的考證、解釋提出補充;探討以顧姬繆氏為代表的顧氏家族
女眷的工作模式及實用工藝繡的功能轉化。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literature value of Gu Embroidery authored by Cheng Tu, supplements the existing textural researches and explanations of Gu Embroidery of Wanli-Chongzhen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gains insights into work mode of Gu Familys members represented by Master Miao , as well a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practical craft embroidery.
程馟,字墨仙,工于文詞,明末清初休寧人。程馟《顧繡》全文不足五百言:“云間顧伯露,會余于海虞,兩月盤桓,言語相得。余時將別,伯露出其太夫人所制繡囊為贈。蓋云間之有繡也,自顧始也。囊制圓大如荇葉,其一面繡絕句,字如粟米,筆法遒勁,即運毫為之,類難如意而舒展有度;無針線痕,睇視之,莫知其為繡也。其一面,則白馬一大將突陣,一胡兒騎赤馬。二馬交錯,大將猿臂修髯,眉目雄杰,胡兒深目兕唇,狀如鷹顧;袍鎧鍪帶,鞍韉具備,錦襠繡服,朱纓綠縢,鮮熠炫耀。白馬騰躍,尾刷霄漢,勢若飛龍。赤馬失主,驚潰奔逸,神姿蕭索。一小胡雛遠坡遙望,一胡方騎馬赴陣,皆首蒙貂幞,毛毳散亂。光彩凌轢,有非漢物,窄袖裹體,蕃部結束,復有旗刀戟,布密森嚴,旛綴金牙,旗張云彩。蕃漢二屯,遙相持向。共計遠坡二,白、赤、黃戰馬三,大將、胡將及小雛四、戈戟五、云旗錦旛各一。界二寸許地,為大戰場,而中間空闊,氣象廖遠,不見有物。繡法奇妙,真有莫知其巧者。余攜歸,終日流玩。為記于簡。”1934年,劉大杰將其收入《明人小品集 · 雜文書信》;1949年以來,又先后被《明人小品選》、《藝術詩文》等專輯收錄。
云間顧伯露,為上海露香園創建者顧名世長子顧箕英(字匯海)嗣子。“伯露出其太夫人所制繡囊為贈”語境中的“太夫人”,應指萬歷-崇禎顧繡的杰出代表——顧伯露母顧姬繆氏;從“囊制圓大如荇葉”、“界二寸許地”等形制和尺度判斷,繡品或為荷包或香囊;“贈”,符合萬歷-崇禎顧繡的流通特征。
程馟《顧繡》對繡囊表現題材、人物塑造、動態沖突構成、構圖、色彩、繡技等進行的鞭辟入里分析,構成了文本可貴的文獻價值。
一、為萬歷-崇禎顧繡的考證研究提供補證
對以繆氏為代表的萬歷-崇禎顧繡特征的推斷,目前已掌握有不少文獻,但成文于明末繆氏顧繡同期的不僅數量極少,且因某些特定限制,不確定因素仍多。程馟《顧繡》有條件為顧繡這一時期的考證研究補充新證。
1.對文獻的補充
現有萬歷-崇禎顧繡研究的明末文獻證據主要是萬歷譚元春“顧姬繡佛歌作”及初刻于崇禎三年(1630)、增刻于崇禎四年的《松江府志》。
譚元春己未年得轉贈顧姬繡佛一件,欣喜作歌記識:“上海顧繡,女中神針也。己未(萬歷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十一日與雨若相見,蔣謝適有貽尊者二幅,舉一為贈。時地風日,往來授受,皆不知為今生。乃為歌識于二幅上(正文見注釋)[1]。譚元春“顧姬繡佛歌作”善于提煉“顧婦”刺繡立意、神韻、技藝特點;但作品客觀面貌描寫簡略。
崇禎四年《松江府志· 卷七· 風俗》載:“顧繡,斗方作花鳥,香囊作人物,刻畫精巧,為他郡所未有。”崇禎四年《松江府志》為以繆氏為代表的顧繡發端期研究留下了寶貴的“稱謂(顧繡)、體裁種類(斗方、香囊)、與體裁對應題材(斗方作花鳥、香囊作人物)、主要特點(刻畫精巧、他郡所未有)”等信息,體現了志書精準簡約的文范。限于規模和志體特點,不見對顧繡具體作品的狀物形容。
程馟《顧繡》對上述文獻的補充貢獻是:第一,又增顧繡研究明代史料一件。第二,提供了以顧姬繆氏為代表的萬歷-崇禎顧繡在繡佛以外其他人物題材刺繡實記;第三,提供了“香囊作人物”如何“刻畫精巧”的詳細字證。第四,“云間顧伯露,會余于海虞,兩月盤桓,言語相得。余時將別,伯露出其太夫人所制繡囊為贈”,提供了萬歷-崇禎顧繡通過饋贈走向社會的豐富信息,例如:饋贈對象性質(程馟,明末清初知名文人),授受雙方互動程度(“兩月盤桓,言語相得”),贈品規模等級(顧繡能手顧伯露母精制繡囊),贈品后續體驗價值(“余攜歸,終日流玩。”)等,可與譚元春“顧姬繡佛歌作”中顧繡在文人圈“往來受授”的記載形成飽滿的文獻響應。第五,“蓋云間之有繡也,自顧始也”,可以被看作程馟對伯露所贈繡囊的價值“考”,可以讀出“伯露太夫人”以顧氏家族貴的時風,不經意間,也旁證了彼時云間刺繡的勃然。
2.對傳世作品鑒定的支持
上海博物館藏《竹石人物花鳥合冊》十開中有“繆氏瑞云”絲繡朱文方印的《枯木竹石》,是目前所知顧繡作品中唯一具繆氏名款者,也被公認為唯一沒有疑問的繆氏原作。故宮博物院張瓊先生以《枯木竹石》為標度對比研究后推論,同冊中《昭君出塞》、《文姬歸漢》、《蘇李泣別》、《李廣靖邊》等六開與《枯木竹石》的品格、工藝水準最為相近,尤其人物面部及神情的處理,擘絲僅一絲,運絲出神入化,大有生韻,極有可能也是顧姬繆氏所作[2] 。
程馟《顧繡》對上述傳世作品鑒定的支持是:第一,程馟所述繡囊的歷史故事題材,人物造型、面部及神情處理,擘絲、運絲特色均與《竹石人物花鳥合冊》中四開人物相近。第二,上述四開人物繡的物象造型、色彩設計、構圖要素也與程馟繡囊相關要素極為相近。雖然迄今仍無繆氏人物繡的確鑿傳世實物,但程馟繡囊描述從歷史文獻角度支持當代《竹石人物花鳥合冊》中四開人物為繆氏繡作的推論:程馟繡囊人物題材圖像幾乎就是縮微的繆氏人物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