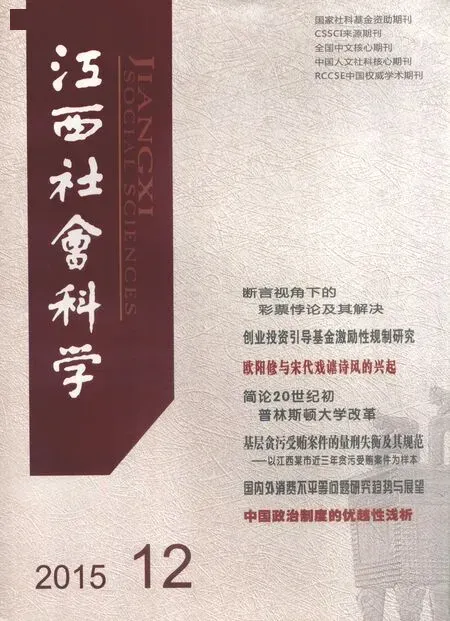市場發育與糧食危機:以抗戰時期重慶市為例
■楊國山
在抗戰時期,糧食是最主要的國防資源和民生資源。后方的治安,前方的軍心以及物價的漲落,都以糧食問題為核心、為決定點。[1](P1)糧食問題是戰時中國的一項重要議題,值得深入研析。關于抗戰時期中國糧食問題的研究,海內外學界已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既有研究,就研究主題而言,多側重探討田賦征實政策①、戰時糧食危機及政府的管制舉措②。就研究視域而論,多聚焦于四川、廣東、江西等省份。③學界對于作為抗戰時期中國首都的重慶市,尚未予以足夠的關注。實際上,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頒行的諸多糧政措施,都須從重慶糧食市場尋找源頭。
重慶市是華西重鎮,市厘繁盛,貿易發達,“為四川糧食調劑之中心地點”。抗戰爆發后,政府西遷,工廠內移,重慶一變而為全國軍事政治經濟之中心。因人口頓增,消費增大,重慶成為后方糧食消費的主要市場。且前方軍糧之供應,后方民食之接濟,又多以重慶為轉輸中心,形成糧食集散轉運的主要樞紐。所以時人認為,重慶糧食市場 “為整個四川糧食問題之代表寫照”[2],“足反映后方戰時糧食問題之真相”[3]。 此外,重慶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國民政府唯恐其因糧食恐慌而出現社會問題,有礙國際觀瞻。[4]汪偽政權下的宣傳系統也緊緊抓住重慶市的糧食問題,大做文章,對重慶政權展開反面宣傳。緣此,重慶政府對于重慶糧食市場格外重視,一切管制措施,均含有嘗試性質與示范作用。從這個層面看,重慶糧食市場可視為抗戰時期全國糧政的試驗田,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以原始檔案及時人調查等一手資料為基本依據,對抗戰時期重慶糧食市場的市場分布、糧食來源、糧食組織與交易方式、糧價波動等諸多面相予以初步探討,藉此管窺抗戰時期后方糧食問題之演變。
一、市場分布及糧食來源
抗戰時期重慶市為長江上游最大商埠,握川省各支流之樞紐,四川糧食的進出口均須經過重慶。故重慶糧食市場既為消費市場,同時也兼具集散市場的性質。重慶下游的涪陵、萬縣、云陽、奉節、巫山等地產米不足,多向重慶采購補充。宜昌、沙市一帶缺米時,也常由重慶輸出接濟,每年約三四萬擔。抗戰前兩三年內,因湘米豐收,行銷宜昌、沙市的川米,已大為減少。且由于川米歉收、軍糧急需等原因,外省的米糧也由重慶轉運入川。[5](P3)總體而言,各種糧食輸入后再輸出者,為數不多,均在40%以下[6](上冊,P21),絕大多數糧食在重慶市內消費。
重慶市民主要食糧以米為大宗,“鮮有食用雜糧者”。[7]當時重慶米糧市場可分為山米市場與河米市場兩種。山米市場也叫“小米市”,共有米亭子、金馬寺、紫霄宮、龍王廟及黌學街五處(俗稱五大米市),其中以米亭子為最大。所售糧食以米為主,間有雜糧。山米多由肩挑負販經營,由米販到重慶四鄉或鄰縣收購黃谷加工,或收購熟米直接運渝出售,也有農民直接運至市場或街頭出售。河米依其來源,分為大河(長江)米與小河(嘉陵江)米。大河上游運來米糧,洪水時泊濫泥灣,枯水時停菜園壩。大河下游來渝糧船,枯水時泊朝天門,洪水時泊麻柳灣。小河運輸米船,多泊曾家巖碼頭。此外磁器口、千廝門及兜子背等碼頭,也常有糧船停泊待售。故在沿江糧船停泊之處,即有河米交易市場:大河以菜園壩、朝天門為主,小河則以曾家巖、臨江門為主。交易地點均在江邊茶館內舉行。河米市場的交易是批發整售,而山米市場多為零星出售。自實施糧食管制以后,國民政府為便利管理,將山米市場與河米市場集中于米亭子,并由糧政機關常川派員監督。[7]
相應地,重慶市的米糧來源,主要有三種途徑: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重慶四郊。長江及嘉陵江流域運來的米,由水路輸入,為河米。其中,沱江、綦水、岷江沿岸各地所產之米,稱為大河米;涪江、渠河、巴水各地所產之米,稱為小河米。重慶四郊由陸路運來的米稱為山米。其來源主要是重慶市方圓100里內外的縣份,如江北、巴縣、璧山、綦江等地。山米在重慶市場上的地位不甚重要,其輸入量視年歲豐歉及渝市米價高低而定,平均每年十萬市石。據稻麥改進所調查,1938年輸入量為102 270.12市石。1939年根據四川省糧食管理委員會駐渝處統計山米輸渝為107 084市石,僅占該年總輸入額的10%。重慶市的米糧約有80%以上來源于長江流域與嘉陵江流域。鄉村的米糧要運抵重慶市場,需經過多種不同性質的市場周轉。大致而言,米糧先由產地集中到鄉鎮市場,再由鄉鎮市場集中至集散市場,然后運達消費市場出售。例如江油龍泉鄉米糧要運銷到重慶,需先由農民在趕場日擔至龍泉鄉售于米販,米販運至中壩售于米商,米商運至江油售于運商。江油運商再運至泰和鎮出售。泰和米商則售于合川或重慶采購商人或逕運重慶出售。糧食市場的層級性較為明顯。
就糧源渠道而言,抗戰時期重慶的糧食來源并不穩定,時常發生糧荒。其原因固然紛繁復雜,但以下兩點尤為突出:第一,糧食分流至長江上游各地。抗戰爆發后,資中、內江一帶農作物種植結構改變,農民改種經濟效益更好的甘蔗,糧食種植面積減少。自流井增產井鹽,榮威增產煤鐵,工人陡增,加之眾多高校內遷成都,糧食消費日增。導致宜賓、瀘縣等糧源地,均改而向上述各地輸出糧食。重慶糧食進口因此大受影響。[3]第二,各糧源地為自保起見,經常發生“阻米出關”的舉動。戰前,遇有突發事變或年歲不豐,上游各縣也時常禁止糧食出境,導致重慶糧食來源斷絕。[8](P89)抗戰開始后的頭兩年內,糧食迭告豐收,重慶的糧食來源較為穩定。[2]但從1940年3月起,糧價開始不合理地上漲。渝市糧商,紛赴各糧源地競購,“地方政府,紛紛封倉,阻關禁運”,致重慶米糧缺乏來源,形成糧慌。1941年的軍糧采購由各縣分攤,地方政府擔心本地糧食外流,不易采購,均實施封倉,市場糧源斷絕。雖然政府嚴令禁止,各地仍施行如故。[9]糧食流通渠道的人為堵塞,加劇了重慶糧食市場的糧源緊張程度。
二、糧商組織及交易方式
(一)糧商組織
糧商是指從事糧食運銷業務的商人。抗戰時期重慶糧商可分為運商、行幫、買幫(零售商、加工廠商)、米棧商及斗幫等種類。運商可分坐地運商與水客兩種。坐地運商,即重慶市的運商,隨時派人至產糧各地采購運渝。水客即外埠運商,亦稱“米船主人”,自各地運糧來渝。二者通常稱為賣幫,是河米的主要經營者。賣幫多為兼營,流動性很大。買幫是向賣幫買進,然后轉售于市內消費者。買幫分為零售商與加工廠商兩種。零售商買進熟米或磧米,直接轉售于消費者。加工廠商,則購進黃谷磧米或小麥,經加工制成熟米或面粉后,然后轉售于消費者。買賣兩幫交易須經中間人從中撮合。中間人俗稱 “行戶”或“經紀”。
重慶各類糧商數量,時有增減。歷年糧商之消長可大致顯示重慶市糧食市場營業概況。抗戰前重慶糧商規模不大,1936年運商有10余家,行商僅4家,加工廠商10家。抗戰開始后,重慶糧食消費量劇增,糧商規模亦隨之迅速膨脹。1938年孫醒東曾調查重慶糧食市場,糧商達800余家,依運銷性質,可分為7大類,如表1所示。紀等的糧商,共計1416家。到1944年12月,全市有機器碾米廠108家,每月承碾公私米糧93 000市石。[11]當然,上述各類糧商的劃分也并非絕對,其內部也偶有交叉重合之處,例如行商有時兼辦外地購糧,充當運商,其他行業商人也會兼營糧食。
(二)交易方式

表1搖1938年重慶糧食市場運銷商統計表
表1所顯示的糧商數量,相較于1936年,呈現出明顯的遞增趨勢。1940年糧價高漲之后,糧商規模進一步擴大,行商增至28家。1941年1月,米糧販運業公會統計,全市共有經紀行戶28家,販運商485家,零售米店556家,囤船102家,機器碾米廠17家,碾房194家。[10]1942年,重慶市糧政局舉辦糧商登記,全市從事糧食購銷、加工、經
當時重慶糧食市場的交易方式,大致可分為直接交易、間接交易與委托交易三種。直接交易,即米糧交易不經過中間人介紹,直接出售給買者。間接交易指米糧成交須由經紀從中斡旋。委托交易,即外埠糧商或糧戶不隨糧來渝,將運到重慶的糧食委托渝市熟識糧商或經紀代售。委托交易是間接交易的高度發展形態。
山米的交易多屬直接交易,交易手續較為簡單。農民或米販擔米入市后,即排列市場上,等候顧客,買方看貨談價,現錢交易成交后由賣方代為送至家中。路途近者,不收取送力。若路途過遠,每挑2老斗米糧就加送力5角至1元。由于山米在重慶糧食來源中所占份額甚低,所以直接交易并非重慶糧食交易的主要形式。
河米交易多為間接交易,偶有委托交易。1940年2月米市未經管制以前,河米交易方法較為繁雜。主持交易的中心為糧行,販運米商在糧食運到后,即帶貨樣前往素有往來的糧行接洽交易。由糧行報告最近交易狀況與可售價格,征得賣方同意后,即代為尋找買主,買方一般是米店、碾米廠、碾房等。每次成交數量最低為20市石,糧行每市石取傭金4角,由買方出1角5分,賣方出2角5分,同時賣方出過斗之斗息6分,防空捐2分,共計每市石的交易費為4角8分,賣方擔負3角3分,買方擔負1角5分。統制市場以后,自1940年12月1日起,重慶市糧食管理委員會為管理市場起見,將全市28家糧食行商,組成一個食糧業經紀行商聯合辦事處,負責統一糧食交易,辦事處設于米亭子米糧業公會內,凡買賣雙方,不論購進或售出,均由其分配管理。[10]
(三)交易陋習
糧食市場的交易陋習古已有之,重慶糧食市場承襲舊規,因沿積習。在米糧收購、裝袋、過秤、出售等各環節,存在著袋里藏假、以次充好、改變量器等諸多弊端。糧商們“舞巧弄技,花樣百出。非身歷其境,具有實際經驗者,莫能辨識”。最為普遍的陋習就是在米糧中摻水摻雜。

表2搖1938年重慶市各月糧食存儲數量(市石)
糧商在米糧出售前,將其攤開,直接潑水;或在出售前夜,“先取十分之二三,浸之以水,然后混入其余米中攪勻,非仔細觀察,不易發覺”。摻雜是在糧食中摻拌品質較劣或破碎米糧,重慶糧商故意在米中摻入稻谷、黃谷,或將熟米中摻以1/3的碎米。有些米店專門向碾米廠或糧戶收購糠秕碎米,然后混入好米中;更有甚者直接在米中摻入泥沙渣滓。此外還有造假現象,即在米中加入漂白劑,有的碾房將石膏灰與米合碾,“使米之顏色漂白,以冀獲高利”。摻水摻雜不僅出現在糧食市場的出售環節,在糧食收購地,此種惡習也是層出不窮。摻水后的米糧如不設法盡快通風曬干,就會發熱霉壞。有人指出抗戰時期重慶的平價米,“非谷即稗,非糠即碎,非霉即壞”,均為摻水摻雜的結果。[3]摻雜陋習嚴重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1944年議員李奎安在重慶市臨時參議會上控訴重慶平價米 “為意想不到之壞”,“品質甚劣,或摻水霉爛,臭氣熏人,或谷多于米,難以進口”,“其原因當以人為的關系最為重要”,建議政府革除市場陋習。[12]
三、糧食存儲與糧價波動
糧食價格穩定與否,與一地有無大型倉儲設施,成正比例關系。“大凡無倉庫設備之市場,糧價多不穩定,且易發生谷賤傷農之害,又易造成糧商操縱投機的弊端。”[6](上冊,P94)重慶市內地勢高低不平,易生火災,故市區積谷倉數量甚少。該市最大的近代化倉庫是八省積谷倉(贛、閩、鄂、湘、粵、浙、晉、陜),該倉庫屬于義倉,于1858年由川東道尹責成八省會館設立經營,以備荒歉之用。該倉歷次存儲至30 000石,平糶20余次,到辛亥革命時仍剩余19 000余石。然而民國以后,政局紛亂,該倉所余田產積谷“或被吞蝕倒賣,或被軍隊提食,此挪彼借,現余無幾”[8](P89)。該倉的積谷備荒功能已有名無實。
堆棧也是存儲糧食的重要場所,然而,重慶市內的堆棧皆由私人設立,其辦理主旨,“非以囤積謀利為目的,即以擴展業務為要旨,即偶有一二義倉設施,亦以儲存農產品之數量無幾,安足以言救濟備荒平糶種種要務”,根本無力應對社會急需。[6](下冊,P186)重慶市的米棧與積谷倉甚少,故存米不多。從表2可略窺重慶存糧之一斑。
表2顯示,1938年重慶市各月糧食存儲量,最多為68 186市石,最少為14 432市石,平均存底不過二三萬市石。若就重慶市每月消費米15萬市石計算[13],則所存儲的米僅可供4—6天的食用,若一星期內,米因故未能運到,不但米價會高漲,而且有發生米荒的危險。[2]針對重慶存糧嚴重不足的問題,時人提出建議:“如重慶市這樣一個消費市場,不論在平時或戰時,對于食米,應該要有相當的儲備,始能使價格安定,甚至不致發生米荒”,在戰時,重慶應在各消費區分設10座3萬市石一所的糧倉,以此儲備3個月的米糧。[14]然而,由于經費短絀等種種因素限制,重慶市倉儲建設并未好轉,直到1941年重慶市政府仍稱:“本市原有積谷倉厫,數目無多,容量甚小,年代久遠,大多朽壞。”[7]倉儲設施事關一地糧食安全體系的建構。重慶缺乏大型倉儲設施,存貯能力有限,故而一遇青黃不接、販運失調等突發事件,該市糧價就大受影響,起伏不定。
此外,落后的運輸工具延緩了糧食的運轉效率,增加了糧食運銷成本,刺激了糧價的上漲。重慶為川省第一大商埠,水陸交通比較便利,公路汽車可達成都、簡陽、南充、廣安等地,但其糧食運輸仍主要依靠水運。除忠縣、涪陵及洪水期間長江上游各產地可用輪船外,其余各地,以帆船為主要運輸工具,每船容量大小不一,多者可載五六百石,甚至1000石。少者僅百余石。
重慶糧食輸入所需運費因運程之遠近、交通之難易而不同。江水的大小對于糧食運輸影響很大,每年夏季6—9月江水陡漲,長江浪猛灘險,運輸經常受阻,甚至安全發生問題,致使商運不盛。一二月間,水位降低,嘉陵江河窄水淺,船只載重量過少,運輸所需時日增加,人工伙食費用增高。故重慶米糧的輸入,在這兩個季節非常少。尤其是六七月間,江水溫度極高,米糧散裝于船中,受濕氣蒸潤,容易發熱霉爛。相較于陸運,水運雖成本較低,但耗費時日,宜賓等地的糧食運抵重慶,需耗時一周之久,效率較低。一旦重慶缺糧,緩不濟急,極易發生恐慌,引起糧價暴漲。
抗戰時期重慶市糧價上漲迅猛。以中等河米躉售價格為例,1927年每市石僅為5.09元,此后便漸趨上漲,至1931年,為抗戰前重慶米價最高一年。在該年6月青黃不接時,每市石售價至17.86元,達戰前歷年指數最高峰。因當時劉文輝駐軍宜賓、江津一帶,長江上游之米,無法運抵重慶。而陳書農又駐軍合川,嘉陵江上游米糧也斷絕來源,造成重慶市米糧空前恐慌。[15]1931年以后,世界銀價高漲,中國物價低廉。四川米價,亦隨之跌落,更加連年豐收,供過于求,糧價低微。1936年至1937年春,四川旱魃為災,收成大減,米價頓高。抗戰爆發后,1938年與1939年重慶米價每市石分別為7.78元、8.22元,相較于1937年的10.76元/市石,未漲反跌,主要是因為這兩年四川米糧迭告豐收,較常年增收一成五,形成糧食過剩的恐慌。1940年重慶市因敵機轟炸,糧船多受損失,糧商裹足不前,米糧來源緊張,更加6月中旬,宜昌失守,湘米濟川因此受阻,糧價陡漲至46.78元/市石。1941年以后,糧價更如脫韁野馬,難以遏制。1942年每市石河米高達341.97元,比1937年上漲了30余倍。糧價高漲嚴重影響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下級市民及薪俸收入者大感痛苦”[16]。政府的限價政策并未達到抑制糧價的效果,反而糧價被越限越高,黑市猖獗,連陶行知這樣的名流也抱怨在重慶 “有時不論你花多少時間,市場上有錢竟買不到米”[17](P101)。
四、結語
抗戰開始的頭兩年內,大后方因無重大自然災害,糧食連年豐收。糧價未增反降,個別地區甚至出現了“谷賤傷農”的現象。1939年下半年開始,糧價逐漸上漲;1940年7月以后,糧價進入猛漲時期。糧食危機的持續發酵,引起朝野內外的一致關注。蔣介石在全國財政會議痛陳:“如果目前糧食問題不能解決,不僅是有關于抗戰與建國的問題,而且是社會問題亦無從解決。”[18]1942年有學者指出:“在目前, 中國最嚴重的事態,莫過于糧食恐慌問題了。”[19]
糧食危機的成因,固然錯綜復雜,諸如糧食減產,消費增加,通貨膨脹,囤積居奇,政府行政執行力低下[20]等,皆為重要原因。概而言之,論者多是從供給與需求、政府管控等方面分析糧食危機的成因。其實,糧食恐慌的直接誘因是糧食流通不暢。糧食市場作為糧食流通的載體,其自身發育完善與否,應是分析糧食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
抗戰時期重慶糧食市場體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發育。糧商規模擴大,糧食市場的交易主體更為多元化,有較為固定的糧食交易場所。然而,重慶糧食市場的運轉機制并不完善,在糧食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缺乏大型倉儲設施,糧食儲備能力有限,突發事變下的糧食危機應對能力薄弱。在糧食運輸工具方面,落后的運輸工具延緩了糧食的運轉效率,刺激了糧價的上漲。在糧食交易方面,中間人層次眾多,除經紀人外,尚有斛手、斗戶、躉販商、零售商等,層層抽取一定的傭金、手續費,這些費用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糧食經過中間商的多次周轉,糧價易被其操縱。[6](下冊,P186)戰時大后方各地糧食市場均不同程度的存在發育不完善,運轉不靈活的情況。此為戰時糧食危機產生的制度性因素之一。
注釋:
①陸民仁:《抗戰時期的田賦征實制度》,《近代中國》1991年第83期;侯坤宏:《抗戰時期田賦征實的實施與成效》,《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期;郝銀俠:《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田賦征實制度之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②金普森、李分建:《論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的糧食管理政策》,《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陳雷:《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糧食統制》,《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1期;郝銀俠:《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應對糧食危機策略研究》,《民國檔案》2013年第2期。
③何友良:《抗戰時期江西糧食征供情況考察》,《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2期;霍新賓:《市場機制與政府行為——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糧食市場管理的個案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2期;許秀孟:《國家、社會與糧食:抗戰時期四川省臨時參議會有關糧食政策的討論》,《國史館館刊》2012年第31期。
[1]饒榮春.糧食增產問題[M].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
[2]郭榮生.重慶市米糧供需實況與統制方策[J].軍事與政治,1941,1,(3).
[3]于登斌.重慶糧食市場研究[J].新中華,1944,2,(7).
[4]為電力廠工人因米價高漲主張結隊請愿謹將調查實況簽請鑒核由[Z].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號:11—2—3063.
[5]平漢鐵路管理局經濟調查組.重慶經濟調查[M].漢口:光明印刷商店,1937.
[6]四川省糧食管理委員會.四川省廿六市場糧食運銷概況調查[M].成都:誠達印書館,1938.
[7]重慶市糧食管理委員會三十年度行政計劃[Z].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號:11—2—2390.
[8]九年來之重慶市政[M].重慶:內部刊物,1936.
[9]于登斌.重慶糧價變動之原因及其影響[J].財政評論,1943,10,(4).
[10]陳敬先.重慶之米市[J].經濟匯報,1941,3,(11-12).
[11]張光旭.重慶市民營電機碾米廠概況調查[J].糧政季刊,1945,(1).
[12]請市政府轉請糧食部飭主管機關改進陪都民食供應案[Z].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號:11—1—9489.
[13]重慶市糧食管理委員會工作報告[Z].重慶:重慶市檔案館,檔案號:64—8—80.
[14]胡昌齡.重慶市米供需與米市場之檢討[J].農本,1940,(34).
[15]文先俊.重慶米糧價格調查與分析[J].建設周訊,1938,4,(12).
[16] 包 華 國.重 慶 市 的 物 價 與 平 政 [J].經 濟 匯 報,1941,3,(3-4).
[17]橋本學.重慶的抗戰[A].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重慶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Z].重慶:內部發行,1988.
[18]蔣介石.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訓詞[J].財政評論,1941,6,(1).
[19]病馬.從解除糧食恐慌說到振興農業[J].新東方雜志,1942,6,(2).
[20]黃雪垠.政府史視野下抗戰時期國統區糧食危機原因再探析——以四川省為中心的考察[J].江西社會科學,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