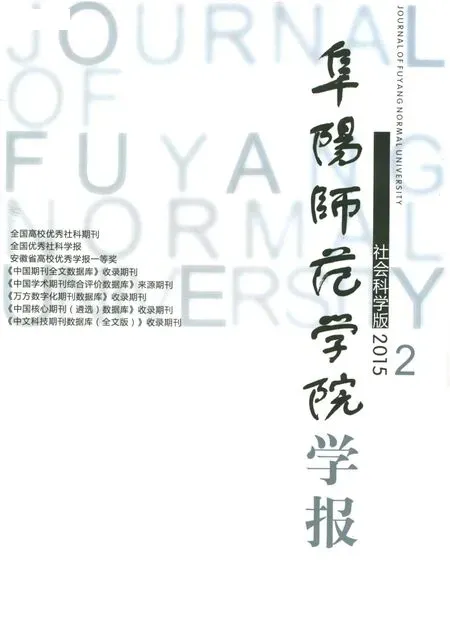露跡:新生代小說中的元小說敘事手法
趙映環(1.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2.福州大學人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2)
露跡:新生代小說中的元小說敘事手法
趙映環1,2*
(1.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2.福州大學人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2)
“露跡”是最重要的元小說敘事手法之一,也是先鋒小說家們常用的寫作策略。“露跡”手法的使用是新生代小說對先鋒小說多元化創作的一種繼承。但新生代小說家們將“露跡”手法納入了更為合理的范疇,擺脫了先鋒元小說創作中“形式大于內容”的怪圈。
元小說;敘事手法;先鋒小說;新生代小說;露跡
英國小說家戴維·洛奇曾給元小說下過一個個簡明扼要的定義:“有關小說的小說,是關注小說虛構身份及其創作過程的小說。”[1]
元小說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使得一大批不愿走傳統小說套路的作家們趨之若鶩。西方的元小說創作大規模興起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了一大批經典文本,如博爾赫斯的《小徑交叉的花園》、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等等。這些文本中元小說敘事手法的應用,革命性地顛覆了傳統小說的敘述方式與手法。
80年代中期,以馬原為代表的先鋒作家群大膽地借鑒了博爾赫斯等人獨特鮮明的元小說敘事手法,自覺地形成了一股元小說的創作高潮。90年代的新生代小說家們當然也不會放棄這些能夠借以達到解構傳統敘事、消解中心意義目的、帶有鮮明后現代特征的元小說敘事策略,于是也出現了一大批使用元小說的敘事手法進行創作的新生代小說文本,如,林白的《說吧,房間》、荊歌的《鳥巢》、李馮的《16世紀的賣油郎》、韓東的《扎根》等等。
一
元小說的敘事手法是多種多樣的,帕特麗夏 ·沃就列舉了作者介入(也稱露跡)、戲仿、拼貼、任意時空、文類合并等等近 20種。其中最主要的、最廣泛使用的元小說的敘事手法則是“露跡”(或稱為作者介入、作者闖入、打破框架等),也就是作者講故事的同時將虛構的痕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僅宣稱小說就是虛構,而且在文本中堂而皇之地討論自己使用的種種敘述技巧。這種敘事人故意暴露敘事虛擬性的行為,被認為是元小說最為鮮明的外在特征。“露跡”包括:作者直接指出故事是虛構的;在創作中挑明構思的過程;討論敘事的技巧;在文本中對話讀者;甚至自己以小說的某個角色出現在文本中等等。
元小說暴露虛構的“露跡”手法,戳穿了統治小說理論幾百年的“再現真實”神話。引發人們對于“真實”的思考,并以此引導“真實觀”的更新。因此,“露跡”手法的出發點和終極目的都是意義非凡的。80年代的先鋒小說家們也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小說的手法和語言形式上都進行了革命性的嘗試。然而,隨著創作實踐的深入,先鋒小說的“露跡”手法不僅陷入了泛濫的境地而且面臨著重重的危機。先鋒小說家們在元小說的創作進程中,越來越重形式輕內容,將形式看成小說的最終目的,普遍傾向于單純地移植與借用西方元小說獨特的敘事技巧和不確定的形式,我們在閱讀時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刻意模仿這些敘事手法留下的痕跡。在他們那里,虛構導致了現實世界一文不值,小說創作自然也就墮入了暴露虛構的狂歡陷阱之中。文本中充斥著大量的評論性話語甚至不著邊際的批評,破壞了小說敘事的流暢性和完整性。他們甚至將小說當成是一種純粹的、個性化的、炫耀敘事技巧的語言游戲,那些匪夷所思、前后矛盾、甚至拗口的語言使得小說文本變成了純粹的形式與技巧的展示。這就給多數讀者的閱讀造成了一定的接受障礙。如果說“露跡”使用之初,給讀者帶來了新鮮的閱讀感受,吸引了一批有著一定的閱讀積累和鑒賞能力的讀者,但到了此時,過分形式化的復雜文本導致了審美的疲勞,使讀者困惑并且無所適從,當然也就無法引起共鳴,最后的結果一定是敬而遠之的。
二
90年代的新生代小說中,“露跡”仍然是一種極為常用的寫作手法,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敘述過程中作者的故意暴露,公然在敘述故事的間隙突然插入自己的設想、故事情節的發展、創作手法的介紹等等,或解釋說明、或評論總結,目的就在于提醒讀者注意故事的虛構性,體現出顯而易見的超現實色彩。例如,李洱的《花腔》的開篇:
它是由眾多引文組成的。我首先要感謝……他們……講述了這段歷史……他們的講述構成了本書的正文部分。其次我也要感謝……等人。作為本書的副本部分,他們的文章和言談,是對白圣韜等人所述內容的補充和說明。
讀者可以按本書的排列順序閱讀,也可以不按這個順序……正文和副本兩個部分,我用“@”和“&”兩個符號做了區分……您可以按照自己對故事的理解,重新給本書劃分次序。[2]
作者一開始就將自己的寫作方法、文本結構、各種技巧明明白白地展現給讀者,并且告訴讀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理解文本,甚至可以按自己的理解來編排順序。這不僅告知讀者故事的虛構性,也給了讀者介入文本的途徑。
荊歌的小說《時代醫生》中:“以上是人物表,共有男女人物十三人(含筆者在內)……他們大抵都會在以后的行文中出現。當然,也許僅僅是走過場……你不要以為這個人物表僅僅是小說前可有可無的索引,它其實是小說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事實上,原先我曾有這樣的打算,那就是在完成這個人物表后,我就不再繼續往下寫了……現在只是因為意猶未盡,才有了以下的章節——或許它們才是可有可無的。”[3]這段話很明顯地改變了傳統小說作者隱藏在幕后的情形,跑在了幕前與讀者進行的交流。在交流中,作者明白地告訴讀者,自己也是文本中的一個人物——“含筆者在內”。接著,作者還交代了自己構思創作的過程——他原先的打算和后來的結果。
李洱、荊歌在與讀者交流的同時,也都在刻意地暴露和強調著小說的虛構性。他們打破了傳統的敘述框架,違反了情節發展的邏輯性,將紀實與虛構融合在了一起,意義的不確定性也由此產生了。但是,作者暴露文本虛構性的過程卻也是讓讀者好奇心得到滿足的過程,使讀者更能體會到閱讀的快樂。同時,這種以暴露敘事,將故事的虛構性坦誠地告知讀者的手法,不也是一種對“真實”的追求嗎?
三
新生代小說家采用的“露跡”手法,無疑是對先鋒小說家多元化創作的一種繼承。然而,新生代小說家們顯然是看到了濫用“露跡”所導致的重重危機,其中包括讀者群的喪失。因此,他們在采用這一敘事手法時,并非一味地模仿和抄襲。相對于先鋒小說家們“天馬行空”的創作,他們對“露跡”手法的運用則回歸到了更為合理的范疇。
在他們的創作中,既適當合理地保留了元小說獨特的“露跡”敘事手法,也保持了傳統小說對情節和內容的重視。一方面,作者文本中不時傳達出“故事是虛構的,敘述是不可靠的”這一信息,讓讀者意識到敘事成規對文本理解的限制,鼓勵他們去質疑所謂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另一方面,新生代小說家使用元小說敘事手法不是為了強調敘事技巧的重要性,更不是為了進行單純的語言游戲。“露跡”手法在他們那里是構建文本的元素之一,是表現情節和內容的手段之一,它可以反映出作者豐富的想象力和扎實的寫作功底。更重要的是,“露跡”手法的應用在新生代作家那里還是吸引讀者的方法之一。“自我暴露”消解了傳統小說作者的居高臨下的主體地位,淡化了作家、讀者、故事人物的角色。作者不僅將讀者視為文本創作過程的參與者,而且還把故事中的人物也上升到可以與作者進行平等交流的地位。這一手法不僅可以打破作者專斷的敘述,而且在敘述過程中,作者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傳達出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讀者對文本意義的理解,使讀者更接近小說家的創作初衷,降低對作品誤讀的幾率,同時也協調了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審美情趣。而對讀者而言,人類天生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也使得“露跡”這一新鮮的元小說敘事手法必然沖擊著讀者陳舊的閱讀思維模式。與此同時,小說中作者、讀者與人物之間“近距離感”更是提高了讀者參與其中、探究其文本的興趣,小說家也就此可以引導讀者反思小說與現實的關系。因此,新生代小說中“露跡”手法的應用不僅豐富了敘事文本的藝術手法和內容,而且拉近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
其特點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對話讀者成為最重要的“露跡”形式。新生代小說家比先鋒小說家重視讀者的閱讀接受,作品較先鋒小說而言,更具可讀性。他們對“露跡”手法的應用擺脫傳統小說的俗套,在表達對傳統“真實觀”質疑的同時,更多是為了創造陌生化的語境吸引讀者,而不像先鋒小說家那樣玩弄語言游戲,為了形式而形式。因此,在“露跡”的各種形式中,他們特別看重的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例如,作者常在敘述過程中暴露自己的同時,采用和讀者商量的語氣來引發讀者的興趣,讓讀者參與到文本當中并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
例如:“停一停,透透氣吧。這一段寫蘇林醫生與黃鱔,也許寫得太緊密了,令你生厭了吧?我們說點別的吧,比方說女人。”[4]
有時,作者還提示讀者故事的發展進程:“這一切看起來和林黛無關。事實也正是如此。……上面的接口是:在日漸透明的秋季里,我差不多不再想起林黛了。現在我接著往下說。”[5]
在這樣的敘述狀態下,讀者對作者這種平等的相互磋商的姿態會產生一種親切感,閱讀的過程也成了讀者參與的過程,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到達故事尾聲,產生一種回味無窮的感覺。
作者甚至還會讓讀者直接出場,在韓東的《去年夏天》這篇小說中,作家寫道:“也許讀者朋友會對我說:‘喂,老兄,你不能就這么把這篇小說結束了!我們花了錢(買雜志)和時間(閱讀)。’……他們大度地說:‘我們做了什么倒無所謂。但你至少得告訴我們常義的生死呀?……既然如此我就讓常義那小子活著。”[6]此處讀者直接出場與作者對話,小說中人物的命運也因此產生了新的變化。作者、讀者、故事人物混為一體,真實與虛構的交融使得文本的空間變得更為豐富。
(二)“露跡” 與故事融為一體。先鋒小說在使用“露跡”時,作者常常只關注小說創作本身,拋開小說的內容強調形式的創新。馬原們任性地玩弄著語言形式的游戲,要么頻頻進行侵犯性的插入評論,要么大段大段地討論敘事策略,賣弄自己敘事技巧,顯現了文本創作的人為操作性。敘事行為本身明顯重于敘事的內容,甚至在有些文本中,敘事內容似乎成了敘事行為的工具。文本的主題被消解,情節被淡化,人物面目模糊不清。此類文本破壞了傳統小說內容的完整性,打斷了情節的連續性,消解故事的邏輯性,留給讀者的很可能只是主題、情節、人物皆無的技巧游戲。小說本該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沒有形式的小說,其內容的深度很可能被掩蓋;但離開了敘事內容的形式技巧就失去了靈魂所在,其文本的晦澀難懂必然使讀者退避三舍。部分先鋒小說在運用元小說的敘事手法時,正是陷入了這樣極端的形式主義的誤區。
而新生代的小說在運用“露跡”這一元小說的傳統敘事手法時,對之進行了一定的改進。他們改變了典型“露跡”手法為了讓讀者關注小說創作本身,頻頻引入敘述者使得小說文本支離破碎。將一系列評論性的敘述加到故事發展的邏輯中,讓它們與小說的故事情節融為一體。“露跡”在此只是小說的一個元素,而不是目的。因此,讀者在閱讀時,面對著作者的介入不會覺得突兀和生硬,更不會影響讀者對小說情節的理解。我們來看荊歌的《鳥巢》中的一段話:“這些,其實已經是這個故事外的事情了。又是發生在很久以后,我把它提到前面來,語無倫次地說了一通,實在是對不起。……在這一段有關柳鍵和純思結婚的文字之前,我所說的大河馬被無罪釋放,其實也是一段后話了。要是按部就班順流而下地記敘,還輪不到說大河馬呢。……”[7]此處,作者直接出面暴露了寫作的狀態、小說的構思、情節發展的線索等等。似乎偏離了故事情節的正常軌道,但接下來,作者沒有繼續就敘述而敘述,而是馬上回到正常的情節發展上來:“剛才說到我們在車站送大河馬回家休養……”[7]這樣一來,讀者在不中斷閱讀的情況下,不僅很容易理解小說的故事情節本身,還可以體悟作者對敘述這一概念的理解,對小說創作自身的理解、還有當前這個文本構成的機理以及創作的過程。“露跡”手法的使用與小說故事發展融為一體,小說中敘述和評論的混合,不僅使故事情節發展的脈絡一目了然,還使讀者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作者的存在,增加了小說的趣味,調動了讀者閱讀的興趣。
在新生代小說中,“露跡”手法有時不但不是小說內容的破壞者,反而有利于故事情節的銜接與發展。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就是個非常好的例證。在第三章中,寫到自己失學的經歷時,林白寫道:“我知道,在這部小說中,我往失學的岔路上走得太遠了,據說這是典型的女性寫法,視點散漫、隨遇而安。讓我回到母親和故鄉的話題上。”[8]114接著就進入了對母親和故鄉這一話題的敘述。上下文之間加入對敘事的技巧的評論,篇幅短小,不僅完全不影響下文對母親和故鄉的講述,而且使得上下文的銜接更為自然。
再如:“讓我接著本章的開頭,敘述我的路途。”下文寫了“我”的“漫游”,并且對之進行了評價:“這個詞我一直覺得用得不太準確,漫,這個字令人聯想到神仙般的從容,想起一蹬腳就能騰云駕霧的形式。”[8]117這些明顯的作者介入痕跡的元小說敘事手法的運用,都提醒著下文情節的發展,預示著“我”之后不幸的旅程——不僅沒有“神仙般的從容”,而且有的還充滿了“恥辱和悲憤”。
類似于此類情節的銜接中“露跡”手法的運用,在新生代很多作家的文本中都大量存在。它們雖仍然在強調文本的虛構性和故事性,但是它們以一種打破傳統的“陌生化”的方式,聯系著上下文,促進著情節的發展,也表達了作者的創作態度。不僅沒有破壞文本的完整性,反而引領著讀者的閱讀。
總之,新生代作家們將“露跡”這一代表性的元小說敘事手法納入了合理的使用范疇。“露跡”與文本相結合,將之融入故事情節并注重與讀者的對話,這一手法的運用使得文本在達到陌生化的同時也縮小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并且保證了小說敘事的完整性。這更符合一般讀者的審美情趣和閱讀期待。但“露跡”的運用依然打破了讀者們固有的、傳統的閱讀習慣,使得讀者在閱讀的同時也關注到了文本的敘事行為。新生代小說家對“露跡”手法的合理應用,擺脫了先鋒元小說創作中“形式大于內容”的怪圈,然而文本中“露跡”所揭示的“虛擬性”依然可以傳達出“小說的主題意義不全然是對現實中客觀存在著的某些本質規律的揭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它是經由敘述生產出來的”[9]這一事實。文本因此達到娛樂與審美的雙重效果。
[1]胡全生.英美后現代主義小說敘述結構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32.
[2]李洱.花腔[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1.
[3]荊歌.中國小說50強1978年-2000年?八月之旅[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56.
[4]荊歌.《短篇王》文叢?牙齒的尊嚴?口罩遮顏[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167.
[5]荊歌.《短篇王》文叢?牙齒的尊嚴?手指上的漩渦[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202.
[6]韓東.我們的身體?去年夏天[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223.
[7]荊歌.鳥巢[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141.
[8]林白.一個人的戰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9]余向軍.小說反諷敘事藝術[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198.
Exposure: Narrative Approache to Metafiction in the New Novel
ZHAO Ying-h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Fujian)
Expos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tafiction narrative technique, which is also a writing strategy commonly used by mordem pioneer novelists. To the new novel, the use of “Exposure” approach is an inheritance of the pioneer novel’s pluralistic creation. But the new generation of writers subsumed the “Exposure” approach into the more reasonable scope and get rid of the vicious circle of “Form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ntent” in pioneer novel creation.
metafiction;narrative technique;pioneer novel;new novel;exposure
H05
A
1004-4310(2015)02-0046-04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2.011
2015-01-07
福州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語境視域中的中國新時期小說語言研究”(14SKF59)。
趙映環(1973—),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福州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修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