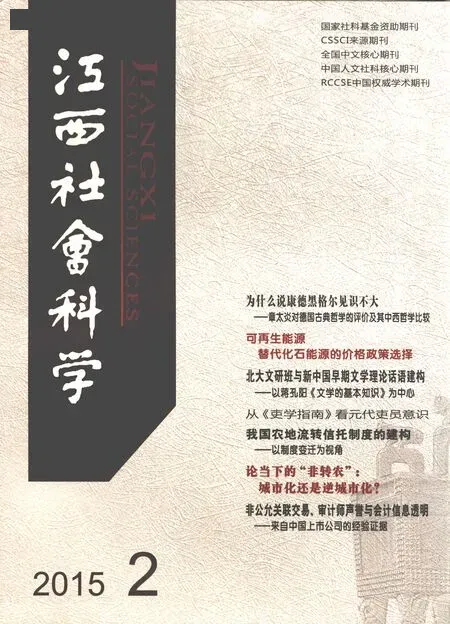從“獨白”走向“對話”:當代道德主體話語的范式轉換
龍溪虎 王誠德
從“獨白”走向“對話”:當代道德主體話語的范式轉換
龍溪虎 王誠德
道德是一種“自我”與“他者”相融合的存在,具有“工具性”與“價值性”等多重意義。道德主體話語的范式主要有“獨白”和“對話”兩種。當前道德主體話語陷入了“人”的遮蔽、“善”的迷失、“言”的缺場等“獨白”式困境。道德主體實現“對話”式訴求,使“人”的遮蔽轉向“人”的復歸、“善”的迷失轉向“善”的確證、“言”的缺場轉向“言”的出場,是當前道德主體從“獨白”走向“對話”的話語轉換的可行路徑。
道德主體;主體話語;范式轉換
龍溪虎,江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博士生,南昌工程學院教授;
王誠德,華南理工大學思想政治學院博士生,南昌工程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江西南昌 330099)
“范式”(Paradigm)概念來源于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的“科學共同體”思想,本意是“共同顯現”,也被稱為“模式”、“范型”、“范例”等。道德主體話語作為一種話語形態,既非一蹴而就,也非浮空設想,而是一種話語實踐。它在特定的時空場域中往往表現出相對穩定的價值取向與話語方式,基于一定時期與一定理論指導下呈現的共同特征則稱之為道德主體話語的“范式”,它可分為“獨白”式和“對話”式兩種道德主體話語范式。在快速變革的社會轉型期,當代道德主體話語未能實現成功的范式轉換,而是呈現出“人”的遮蔽、“善”的迷失、“言”的缺場等“獨白”式困境。基于道德主體話語的“對話”式訴求,探索當代道德主體話語從“獨白”走向“對話”[1](P103)的轉換路徑,是當前理論與實踐必須做出的理論思考。
一、當代道德主體話語的“獨白”式困境
從古希臘提出的“認識你自己”到近代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經黑格爾“理性的狡計”的升華,“自我”在一步步的承認中高揚、抬頭,卻陷入了將“他者”無意識化、將“外界”客體化的困境。道德主體話語亦在此進程中呈現 “獨白”式的特點,即以“述謂式”代替“交互式”,否認不同意識在真理問題上的平等權利、否認在它之外有另一種意識存在,出現了“話語失真、理解歧義、審美疲勞等”[2](P29)障礙,從而走向“我就是我”的自大狀態,具體表現為“人”的遮蔽、“善”的迷失、“言”的缺場。
(一)“人”的遮蔽
繼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米歇爾·福柯喊出“人之死”。“人之死”的吶喊莫過于以最深刻的悲憫透視當下“人”的遮蔽。關于“人”的思想歷程,大致經歷了自我的放大至他向的束縛。自“人”的主體性發現,“人”之主體被一步步抬高,然而陷入自我的主體從未與外界相融,而是高喊“我就是我”的霸道法則,進而陷入“我是誰”的迷思。隨著科學技術的推進,“他者”專權的誤區不斷顯現,“人”的影子漸漸遁入“物”的籠罩之下,進而陷入“唯他是從”的幻想。道德教育從根本上是關乎“人”的教育,是挖掘“人的存在和存在著的人類本性特征”[3](P10)的教育。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本是在思想達乎語言。語言乃本是之家。人居住在語言的寓所中。運思者和作詩者乃這個寓所的看護人。”[4](P366)人的存在則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在對話中尋求意義的過程。然而,不論是自我的放大或是他向的束縛,主體間都無法進行對話,而是在獨白中遮蔽人存在之本身,道德教育亦在此過程中呈現 “見物不見人”的景象。
“人”的遮蔽在道德主體話語實踐中具體表現為:首先,人是目的變為人是手段。道德教育是一種人對人的活動,是以人本身為目的的活動,“人”既是實踐活動的中心,也是教育的宗旨。然而 “獨白”式的形態將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都置于評判體系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缺乏平等的對話與共通意義的生成,受教育者從“人之為人”的目的變為“人被器物化”的手段。其次,人的完滿變為人的抽象化。正如馬克思所說:“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5](P60)道德教育作為一種教育實踐,是從具體的、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出發,推進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各類社會關系的完滿,將人形塑為豐富的、完滿的個體。然而“獨白”式的形態將人的精神關系、物質關系、社會關系都符號化、模式化、單一化,將人抽象化為無生氣的、被灌輸的工具化個體。最后,人之生成變為人之預成。正如后現代主義代表人物多爾所說:“世界的知識不是固定在那里等待被發現的;只有通過我們的反思性行為它才能得以不斷的擴張和生成。”[6](P136)道德主體的人應是在對話和反思中不斷發現的、生成的“大寫的人”,然而“獨白”式的形態將教育的軌道預定程式化,教育的過程僅僅是預設的目標與內容被動轉化與累積的線性化過程,將人之生成的動態性變為人之預成的定格化。
(二)“善”的迷失
“善”內蘊價值之所尋、真理之所至。道德教育是尋求“共同善”的實踐活動,是在“自我”與“他者”的融合中經歷平等、對話、交流、協商后達致“善”之共識的教育活動。然而,在自我的放大至他向的束縛下,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秉持一端或被預定的軌道所規劃,教育者將受教育者視為客體,否認不同意識在真理問題上的平等權利、否認在它之外有另一種意識存在,進而導致“善”的迷茫、迷失。
“善”的迷失在道德主體話語實踐中具體表現為:一是價值模糊而無方向。現代化進程不僅是經濟的現代化,更是人的觀念、價值理念的現代化。席勒提出這是一個“價值缺席”的時代,馬克斯·韋伯則提出這是一個 “祛魅走向世俗”的時代。然而,“價值缺席”、“祛魅走向世俗”并不是無價值之聲,而是主流價值在聲音的嘈雜中 “被缺席”。當前,國內各種思潮與主流價值不斷發生碰撞與沖擊,道德主體要在不同聲音的交流、對話中找尋“共同善”、尋求主流價值之根基。然而,“獨白”式的話語形態阻礙了不同聲音之間的碰撞與回響,進而走入價值模糊而無方向的窘境。二是意義混沌而無根基。道德教育是在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對話中意義生成的過程。“獨白”式的話語形態使其意義始終在自我的世界里逗留,在無法尋找到自我的疑惑中困頓,呈現出意義混沌而無根基的狀態。三是價值的分歧而無共識。面對價值的分歧,胡塞爾提出“主體間性”理論,即跳出主客二分的思維,提出主體與主體間的對話、協商以尋求不同“善”的共識。然而“獨白”式的話語形態囿于自我的思維領地,尋求的是自我的法則,執迷于主客二分、非此即彼的計算邏輯,否認“他者”的合法性,未能與“他者”尋求融合與對話,從而呈現出價值有分歧而無共識的境況。
(三)“言”的缺場
審視哲學發展史,古代哲學向近代哲學發生認識論轉向,近代哲學反省人類意識及其與世界的相互關系,在轉向的歷程中人的主體性不斷高揚。在這一進程中帶來的是近代哲學物質與精神、事實與價值、主觀和客觀的二元對立,二元對立預設的則是主客體的不平等,在道德教育的具體活動形態中主體則化身為絕對的權威,對客體強加“填鴨式”或“灌輸式”的獨立語言,進而呈現的是教育主體的 “自我獨白”與客體的 “緘默不語”,或者是客體的“眾聲喧嘩”與主體的“旁觀旁聽”,整體景觀則呈現出“言”的缺場。“言”的缺場,其實質是在認知理性、先驗理性主導下主客二分的教育實踐活動呈現的樣態,它是一種 “我它關系”的不對等交流而非“我你關系”的平等對話。
“言”的缺場在道德主體話語實踐中具體表現為:一是受教育者的集體失語。道德教育應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對話,是主體與主體之間通過平等對話、真誠交流、敞開心扉、暢所欲言,以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主體間關系促成的合奏交響樂。然而“獨白”式的話語形態將受教育者客體化,主體間的關系變成主客關系,“我—你”關系變成 “我—它”關系,受教育者被預設的目標、知識、內容所規約,優劣評價均以此為標準,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則是受教育者不需主動參與,而是按固定的要求來執行,在教育的交流中則是集體失語狀態,這是當前道德教育效不佳的重要原因。二是事實與價值的二元對立。在以技術理性與唯效率論的指導下,人類患上了工具理性癥,使工具理性優于價值理性,事實與價值呈現了二元對立的現象。道德教育作為一種現代時空背景下的話語實踐活動,同樣沒有跳出事實與價值二元對立的框架,“獨白”式的話語形式使教育停留于既定的效率、理性、目的,而脫離了價值的本質內涵,脫離了“人之為人”的真實屬性。三是權威支配下的被動式接收。對話活動是說者與聽者以交替論證的方式互構而發生的,支配與從屬、原因與結果、本源與派生、主動與被動、構成與被構成以及實體與屬性等傳統的對立范疇都失去作用,并最終導致消解關系雙方的實體性存在和作為純粹關系本身的一種所謂 “之間”范疇。然而“獨白”式的話語將“它”視為支配者,“我”定格為“從屬者”,“學生對教師必須保持一種被動狀態”[7](P294)。“言”的缺場使學生只能在權威支配下被動式接收,主體性、主動性、參與性均被剝奪了。
二、當代道德主體話語的“對話”式訴求
道德教育是“自我”與“他者”融合、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和洽的“對話”式教育。當前道德主體話語盡管表現為“人”的遮蔽、“善”的迷失、“言”的缺場等“獨白”式困境,但其“對話”式訴求從未中斷。道德教育主體的“對話”式訴求不僅是道德教育的內在要求,也是達致本真人格的一種必然、生成民主素養的一種途徑、強化責任意識的一種方法。
(一)“對話”:達致本真人格的一種必然
“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道德教育不僅傳授知識,更是塑造個體的本真人格。“獨白”式的道德主體話語以自上而下的權威式導引,以統一的精英式標準規約每一個個體,其實質是一種“失真”的教育(雅斯貝爾斯語)。道德教育的目的分為兩種:有限的目的與無限的目的。有限的目的,即使受教育者具有與外部世界期待相符的外在目的;無限的目的,即“超出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發展”[8](P19)。有限的目的僅僅是手段與方法,無限的目的才是教育的本真與內在訴求,其實質即是對本真人格的要求。“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在達致本真人格中的價值具體表現在:一是“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推進本真的找尋與理解;雅斯貝爾斯將精英式的權威化、統一化、刻板化教育稱之為“失真”的教育,實質是指出“失真”的教育使人成為工具、手段,而丟失了其目的、失去了其本真。“對話”式的道德主體話語使人真正從權威、統一、刻板中解放出來,走向真實的自我,在平等的交流、自然的對話中尋求本真,因此它有助于推進本真的找尋與理解。二是“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促進人格的培育與塑造。人格的培育與塑造首先在于平等,人與人之間不對等無以形塑健全與真實的人格。[9]“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跳出主客二分、彼此對立的思維,強調主體與主體之間的對等。道德教育傳授對政治、紀律、道德等知識的理解,但其更根本的目的則在于人格的培育與塑造,而這離不開平等的、真實的 “對話”。[10]本真人格中蘊含獨立、平等、真實,而“對話”則是達致人格的一種必然,倘若沒有“對話”,只有僵硬的框框或自上而下的權威,則只能培育極少數的精英與大多數的“道德偽道士”。
(二)“對話”:生成民主素養的一種途徑
自近現代民主成為各國爭相標榜或實行的政治制度以來,何為民主、何為民主的實質、何為民主的精神等問題均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有學者提出,民主是一種程序政治;有學者認為,選舉是民主的前提;還有學者認為,協商是選舉民主的更高級形式,等等。綜觀各種關于民主的理解,不難發現,民主本身離不開“對話”,逃離“對話”本身,既無法理解民主,也不可能實現民主。民主素養是當前理解并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必備素質,“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在生成民主素養中的價值具體表現在:一是“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促進對民主的理性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不同于西方式的民主,倘若以西方式的民主裁剪式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則必然會產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誤讀與曲解。“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需要在民主的教育形態中促進對民主的理性認識,深刻理解民主實現形式的多樣化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必然性與優越性。二是“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推進民主的制度安排。民主不是一句空口號,民主的運轉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等制度安排得以運轉的,每一項制度安排都需要相應的民主素養,也需要民主教育來增強對制度本身的理解。道德主體話語內蘊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當前道德主體話語在生成民主素養中的價值體現都是以 “對話”式的道德主體話語為要求,在話語形態上要求民主式的話語。民主式的話語不是“灌輸型”或“專制型”話語,而恰恰是溝通、理解、對話、協商式的平等參與型話語,因此“對話”是生成民主素養的一種途徑。
(三)“對話”:強化責任意識的一種方法
康德說:“每一個在道德上有價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擔,不負任何責任的東西,不是人而是物。”[11](P6)馬克思提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時,其實質也是指出人在社會關系中所承擔的責任。責任本身有兩個維度:一方面是對他人的義務的承擔;另一方面是對自我過失的擔當,它們是道德責任的一體兩面。“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在強化責任意識中的價值具體表現在:一是“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提升對責任的省思。人的社會關系決定了人是社會性的動物,責任是人之為人不可逃避的內在要求。“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有助于個體在價值虛無與價值爭吵的混亂中明晰自身的職責,提升對責任的擔當意識。二是“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促進理解責任的邊界與限度。道德責任既不是強加的,也不是無邊界的,對惡的責任則是縱容錯誤,因此認清責任的邊界與限度亦是不可或缺的。責任的邊界與限度直接影響道德的適當尺度,道德主體話語以正義為核心內容,在教育的推進中可以促進理解責任的邊界與限度。責任意識的培養是在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中產生,對話是責任意識產生的通途,道德主體話語也只有以“對話”式形態展現才是強化責任意識的一種方法。
三、當代道德主體話語的范式轉換路徑:從“獨白”走向“對話”
基于當前道德主體話語呈現的“人”的遮蔽、“善”的迷失、“言”的缺場等“獨白”式困境,回應道德主體話語的“對話”式訴求,提出“人”的遮蔽轉向“人”的復歸、“善”的迷失轉向“善”的確證、“言”的缺場轉向“言”的出場,是當前道德主體話語從“獨白”走向“對話”的轉換路徑。
(一)“人”的遮蔽轉向“人”的復歸
在經歷了自我的放大至他向的束縛的思想變動期后,主體間性視閾下的道德教育逐漸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主體間性思想的本質內核要求跳出主客二分、彼此對立的二元化思維,主張主體與主體之間的平等、對話,尋求價值引導與主動建構的共通性。主體間性視閾下的道德教育從“人”的發展角度,也指向了“人”的遮蔽轉向“人”的復歸。具體來說,“人”的遮蔽轉向“人”的復歸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重拾人的目的本身。馬爾庫塞曾針對發達工業社會時期人類技術奴役的狀態,深刻批判了人類在技術奴役下成為“單向度的人”。“單向度的人”從另一深層次解讀即是將人是目的變成人是工具。因此,應挖掘人的本真力量,重拾人的目的,使人真實地成為現實性的特定人格的人。二是回歸人的完滿本身。馬克思曾對人的存在狀態作出三個階段的劃分,即“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的人的依賴性狀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狀態”、“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狀態”,馬克思在對人的存在狀態的不同層級描述中透視出人的發展漸趨于完滿的狀態。人是社會關系的存在,人也是豐富多元的存在,既有政治人的屬性,也有道德人、信息人[12](P70)的屬性;既要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也要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的復歸就是要回歸人的完滿本身,進而在人的發展中趨近于自由狀態。三是理解人的生成特性。人的發展不是固定不變的預成式,而是通過反思行為不斷生成的,一切的“程式”與“定式”都不可能將人本身完成預制與規劃,投射在道德教育上則要求將德育的目標設定為 “流動”式,德育的過程設定為“生成”式,德育的評價設定為“形成”式。道德教育不是簡單的單方面傳授,而是通過受教育者的認知、體驗和踐行把知識內化為信念并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的過程。簡言之,“人”的復歸是道德主體話語從“獨白”走向“對話”的基礎,是“對話”道德主體話語的本質要求,也是其最終要達到的重要旨歸。
(二)“善”的迷失轉向“善”的確證
道德教育本質上是蘊含價值的教育、是導向“善”的教育,“對話”式的道德主體話語是在協商、對話、溝通的情境中以尋求“共同善”,因此其內在要求從“善”的迷失轉向“善”的確證。具體來說,“善”的迷失轉向“善”的確證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確定主流意識形態的指引。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多元社會思潮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居于主導地位。當前面對各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應予以堅決的還擊,并有力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二是提升主流價值的吸引力。在價值泛化的時代,主流價值的吸引力遭到削弱,求新、求異的“獵奇”式思維逐漸成為一代又一代病態價值的征兆。主流價值是先進文化的代表,當前面對各種不同的聲音,面對各種分歧與爭論,應提升主流價值的吸引力,并在公平正義的尋求中、在多方的協商對話中達到對主流價值的理性共識,確證何為“善”與為何“善”。三是回歸生活世界中找尋意義之根基。在生活世界中教育更能走向其本真,進而傾聽并找尋意義之根基,在意義的找尋中走向“善”的確證。“善”的確證是道德主體話語從“獨白”走向“對話”的關鍵,是“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的內在意旨,也是其最終以期達至的價值訴求。
(三)“言”的缺場轉向“言”的出場
“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從表現形態上必然是“言”的出場,缺乏“言”的話語只能是“獨白”式或“沉默”式。“言”的缺場轉向“言”的出場不是混雜的爭論或各抒己見的固執,而是在言說的語境中碰撞、交流、溝通,進而達成共識。具體來說,“言”的缺場轉向“言”的出場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話語目標堅持事實與價值的統一。“言”的出場不是隨意性的指向,而是一定目標指令的出場。“言”的出場必然要求堅持事實與價值的統一,兼顧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由此言說的情境則能跳出狹隘的利益沖突并進行真誠的溝通與對話,從而形成悅耳的和諧之音。二是話語方式從單向灌輸轉向平等對話。正如學者提出:“灌輸的弊端在于無視人的價值內涵和精神品性,漠視了發展中的個體作為潛在的或顯在的道德活動的主體所應有的人格尊嚴。”[13](P26)“言”的出場需要在話語方式上從單向灌輸轉向平等對話,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價值內涵與精神品性,尊重每一個個體的潛力釋放與話語表達。不可否認,在特定的場合與特定的意義上灌輸具有其正面意義,然而隨著主體性的不斷高揚,單向灌輸可能帶來的風險與弊端愈加突顯,因此應在充分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基礎上實現平等對話,推進真實的、對等的“言”的出場。三是話語過程從單向訓導轉向雙向交往。從“獨白”轉向“對話”,運行于具體的教育過程中,則需要改變傳統的單向訓導式,轉變以往的將受教育者置于被動接受的地位。“對話”式道德主體話的實質是互動交往的過程,在交往中尋求“同情的了解”,在交往中注重人的情感、理智、直覺、意志、信念等多種要素的和諧統一、做到“情緒關注與理論整合”[14](P161),在互動、交往、理解中營造共通的“精神場”,從而在知、情、意、行等各層面達到教育之“無限的目的”。總之,“言”的出場是道德主體話語從“獨白”走向“對話”的環節,是“對話”式道德主體話語的必要過程,也是其最終達至的話語生態。
[1]龍溪虎,汪榮有,王誠德.從獨白走向對話: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轉向[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4,(6).
[2]馬忠,李雙根.思想政治教育語言研究現狀及其前瞻[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1).
[3]弗洛姆.自為的人[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
[4](德)海德格爾.路標[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美)多爾.后現代課程觀[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
[7]張煥庭.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8](美)羅伯特·格拉澤.教學心理學的進展[M].楊琦,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9]馬冰星,林建成.道德雙重人格和道德重建[J].學術探索,2012,(1).
[10]楊偉濤.中國道德理性主義文化傳統中的道德自我訴求[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
[11](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代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王誠德.“信息人”:一種新物種的起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4,(9).
[13]肖川.主體性道德人格教育:概念與特征[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3).
[14]龍溪虎,汪榮有.情緒關注與理論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對話的主體性需要[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7).
【責任編輯:龔劍飛】
B82-02
A
1004-518X(2015)02-0034-06
江西省“十二五”重點學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培優項目“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對話論”(14yb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