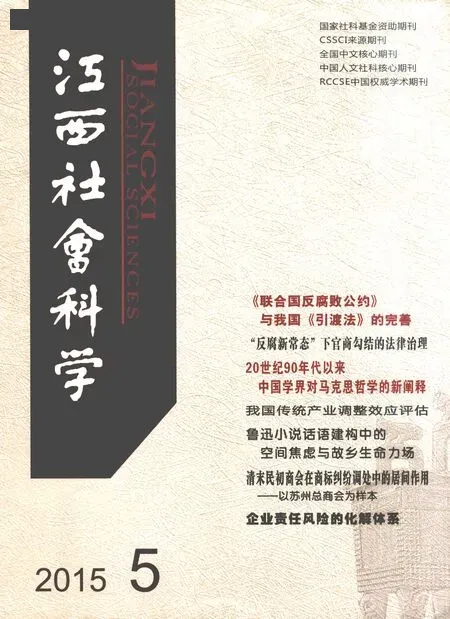蘇軾的曠達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趙延彤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蘇軾可謂迄今難以逾越的高峰:其文于唐宋八大家中堪稱翹楚;其詩與黃庭堅并稱“蘇黃”,代表了宋詩的最高成就;其詞開創豪放派先河,與辛棄疾并稱“蘇辛”而雄視百代;其書法位列“蘇黃米蔡”四大家之首,被同時大家許為“本朝善書當推第一”;他還開了宋代文人畫的濫觴,其畫技被稱為 “玉局法”。蘇軾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既是趙宋王朝社會土壤滋養的產物,更是他這樣一位曠世奇才曠達胸襟、超邁個性的文化披露和心靈綻放。通觀蘇軾一生,其自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歲入仕,至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十六歲致仕(卒于是年),歷經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在四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既有“入掌書命,出典方州”的榮耀,也遭遇了三起三落、身陷囹圄、屢遭貶逐的困頓屈辱。在崎嶇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蘇軾“達觀一視”吟嘯徐行,以超然樂觀的態度對待政敵的打擊和生活的磨難,從容不迫地走過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成為不朽的歷史人物。
后人把蘇軾的這種態度稱為曠達。解析其曠達有助于認識以蘇軾為代表的宋代士人的思想結構和心靈趣向,進而更準確地解讀其文學品格。
一、蘇軾曠達的思想來源
(一)儒家思想是形成蘇軾曠達的精神基石
儒家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其主調是積極兒童用世精神。但當政治主張不被君主接納時,它又講“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兩方面的結合便形成封建士大夫事君立身行事的基本信條。在專制社會里,君主的喜怒無常、黨派之間的劇烈傾軋,隨時都可能給封建士子的政治命運帶來榮辱生死的遽變,因而如何對待仕途進退就成為他們人生中的重大課題。蘇軾的曠達正是這種矛盾的產物。
何為曠達?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作如此描述:“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煙蘿。花覆茅檐,疏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1](P12)《晉書·裴頠傳》中將其闡釋為:“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蘇軾推崇曠達,他在《論修養帖寄子由》①中提出,人生應當“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又在《與傅維巖秘校》中鄭重指出“仕無高下,但能隨時及物,中無所愧,即為達也。”可見,曠達,作為一種品格,表現為無掛礙于紅塵俗世的超脫、飄逸;作為一種人生態度,則表現為心胸開闊,無所執著的一種達觀超越。而在蘇軾看來,“達”是與“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一種政治態度,從政者在仕途上不論職位高低升遷罷黜,都應“隨時及物”勤于政事憂民惠民,做到心中無愧方好。這就決定了蘇軾的曠達是與那種以不問世事、嘯然塵外高自期許而實為逃避矛盾、消極避世的高人隱士精神大相徑庭的。蘇軾自鑒判鳳翔入仕起就始終未脫離仕途,在他所經歷的五位君主中,仁宗賞識他,神宗理解他,高太后重用他,這種為封建文人士子所企羨的君臣際遇使蘇軾深感 “蒙恩尤深”(《答王定國》),每每形諸歌詠,溢于言表:“畢命驅馳,未嘗萬一,懷安退縮,豈所當然。”(《杭州謝表》)蘇軾“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忠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宋史·蘇軾傳》),這都說明,蘇軾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充滿積極用世熱情的。
但蘇軾的政治命運不幸而多舛。熙寧年間他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被貶離朝廷,元豐二年又被權要以 “謗訕新政”罪名投入監獄幾至喪命。在其后劇烈的黨派傾軋中更因秉性耿直、不能隨時俯仰而大吃苦頭,以垂老之年遠放嶺海幾乎不能生還。這種仕途摧折使蘇軾悲憤不已,欲仕不能、欲隱不忍:“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羨君欲歸去,奈此未報恩。”(《寄題梅宣義園亭》)蘇軾反復流露了這種復雜矛盾而又痛苦扭結的心情。對此,蘇軾的解脫之道是運用儒家“可處而處,可仕而仕”、“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的精神來處理與君主仕途之間的矛盾,超脫名韁利鎖的羈絆,對個人的升沉榮辱亦坦然不以為懷,從而形成了蘇軾特有的一種忠而不愚、貶而不頹的從政風格,從其奏論文章中很可看出這個特點。比如蘇軾認為身為大臣就應當“以義正君”(《大臣論》),不能卑論趨時茍合取容。但他并不贊許“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的所謂“忠臣義士”(《霍光倫》),而主張在遭遇挫折時要“忍”與“待”:“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這樣才能在復雜險惡的政治斗爭中既可保全自己,又能實現尊主澤民、濟世安邦的理想。
蘇軾更用儒家的中庸思想為之提供理論根據。他提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于饑飽而已。”(《張氏園亭記》) 這就是說:“必仕”即盡愚忠,很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必不仕”又不合乎臣子的義分,也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士大夫應處于仕與不仕之間,既不要過分執著于功名進取,又不要脫離仕途,更不能走向消極無為,一切以中庸為度,只要“隨時及物,中無所愧”,盡到自己的職責即可。蘇軾的政治智慧,或者說他在仕途坎坷中體現出的高明之處就在于把入世與出世打成一片、熔為一爐。在他看來,入世即出世,出世即入世,“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既然出入一樣、仕隱無異(等無有二),那么“此心安處是吾鄉”、“塵心消盡道心平,江南與塞北,何處不堪行”(《臨江仙》)的曠達態度就是順理成章的了。蘇軾正是秉此心態從政,在朝則“以義正君”,大義凜然,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赴之,禍福得喪付于造物;但另一方面,他又“未許朱云地下游”,并不學漢代的朱云那樣折檻死諫。當與秉軸者意見不合、發現自己處于“位非用事之地”時,就選擇“乞外任避之”,借以遠害全身,并在職守內力行善政,盡力于朝廷。在多次貶居期間,蘇軾能做到“胸中淡泊,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而且積極有為于逆境,不以升沉榮辱為意,真乃進退裕如、蕭然自得,充分體現他曠達超邁的政治襟懷。
(二)濡染佛老思想是形成蘇軾曠達的主要因素
宋代士大夫對待佛老的態度大致可分三類:一種是以“辟佛”、“辟老”者自居,站在儒家正統立場對佛老嚴加批判大力排斥;一種是在遭遇挫折后用它來排遣失意的情懷,作為精神寄托情感撫慰;一種是利用佛老義理和思想資料來創建新的理論體系。但在宋代這些矛盾的態度往往會在同一個人身上呈現出來。比如,王禹偁上書力主 “澄汰僧尼”、“罷度人修寺”(《東都事略》卷三十九),但晚年謫居時,他則“焚香默坐,消遣世慮”[2](P14-15)。司馬光力主“辟佛”,但其《家法》中寫定:“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說郛》卷三十九);歐陽修撰寫《本論》,對佛老大加撻伐,但“自致仕居潁上,日與沙門游”(《佛祖統紀》卷四十五);改革家王安石罷相后,晚居鐘山信仰高僧瞿曇,并著《楞嚴經疏解》闡釋佛理,甚至舍家為寺;至于宋代理學家們一面斥佛老為異端,一面又吸收佛老精義來豐富營造自己的學說,更是廣為后人所知的事實。這些情況表明,出入于佛老而歸宗于儒,以儒修身,以禪治心,已在宋代士林中蔚成風氣。蘇軾走的正是這條路子,只不過他不像政治家王安石那樣“雜于禪”為的是“欲明圣學”,也沒有像思想家朱熹、陸九淵那樣借用佛老思想元素去建構理學、心學一類的思想體系,而是用來處理仕途上的進退行藏,借以應對當時風云變幻錯綜復雜的黨派斗爭,這正好促成了蘇軾的曠達。
同歐陽修、王安石等人一樣,蘇軾對佛老的態度也有個變化過程,可以烏臺詩案為界劃為前后兩期。前期的蘇軾“奮厲有當世志”,從朝廷利害出發,對佛老那些“虛無淡泊之言”、“猖狂浮游之說”及其無為出世主張予以嚴厲批判,直指佛老對當世政治經濟社會的消極影響。同時,蘇軾也意識到佛老思想中存在的有益因素,可使那些 “不得志于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放心而無憂”(《韓非論》),他自己也與方外之人結交,“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常常“頌詩往來”(《東坡志林》卷二)。這是蘇軾日后一度“歸誠僧佛”的緣憑。但可看出,此期蘇軾對佛老思想的論斷批判并未有超越前人的理論深度,他的方外交游也主要是受風行于世的禪悅風氣影響所致。蘇軾真正開始汲取佛老思想中的有益因素,與自己固有的儒家思想進行融合,進而內化為一種曠達的生活態度來對抗仕途險阻,是從貶居黃州開始的。烏臺詩案后蘇軾被貶黃州,這是他政治上屢遭挫折的起點。紹圣年間又遠貶惠州,繼貶儋州。政敵的打擊接踵而至,生活上越加窘迫,加之往昔朋友因畏牽連而與之絕交,使他幾陷絕境,此時他亟須解除精神危機獲得心靈寄托,這無疑從客觀上加速了他“歸誠佛僧”的步伐。烏臺詩案后,一種塵緣盡捐飄然欲舉的氣氛充盈在蘇軾的思想中,飄逸在他的詩文里。他甚至堅持五年“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黃州安國寺記》)的參禪活動。他殷切關照友人說:“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他自己則常“默坐反觀,瞑目數息”以養生(《答劉貢父》)。其實蘇軾平生多次表示對佛老那一套 “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的“超然玄悟”之說是誨謾不信的。他臨終前留下的詩篇更是宣稱:“平生笑羅什,神咒真浪出。”(《答徑山琳長老》)這表明蘇軾雖好佛老,但并沒有像那些虔誠的善男信女一樣成為佛老思想的俘虜。正如他所言:“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得其所似,不為無害。”(《答畢仲舉書》)他對佛老采取的態度是以“智慮臆度”之,即對其中有益的妙理玄言參考借鑒以 “期于靜而達”,這才是蘇軾濡染佛老的旨趣所在。
佛學自東漢末年傳入后,即與中國的老莊之學一起作為儒學的對立補充,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塑造產生極大影響,許多個性鮮明的歷史人物無不出入三教各得所歸。但在蘇軾眼中,學佛老如陶(淵明)王(維)者近乎懶,劉(伶)李(白)者似乎放,蘇軾不贊成學佛老而走向懶與放,進而“嬉游人生”,而是追求一種“靜而達”的境界,其目的在靜以待變,達以處難。蘇軾正是運用佛老思想中的空無觀念和齊榮辱、等生死、乘運委化、因任自然的生命主張來看待生活磨難和仕途榮辱,并收安心之效:“升沉何足道,等是蠻與觸”,“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與楊元素》)。在佛老主張的價值觀面前,人世間的一切煩惱痛苦沉浮榮辱都已變得微不足道不必執著了,由此形成的心態恰可為蘇軾承受政敵打擊和生活重壓提供精神支撐,使他臨深履薄而泰然自若,心胸豁達而應緣無礙,談笑生死之際,超然不改其度,而且始終沒有喪失對生活的興致。雖傾心佛老卻未厭棄世事,納交方外而不遁入空門,好而不溺,學而通變,曠而不頹,達而不放,這就是蘇軾借助佛老思想形成的獨具特質的曠達。本質上空無無為消極遁世的佛老思想在蘇軾身上顯現出理性的光輝。宋初名臣王禹偁指出:“夫禪者,儒之曠達也。”(《小畜集》卷十七)他從自己的身心體驗出發,精準地道出了宋代士大夫濡染佛老的目的所在,也正可說明佛老思想在蘇軾身上發生的效應。
(三)樸素的辯證思想是形成蘇軾曠達的認識論基礎
蘇軾在對許多具體事物的認識上含有唯物思想并富于辯證色彩。蘇軾認為運動與變化是事物的根本屬性。他在《御試制科測》中指出:“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在《墨妙亭記》中提出:“凡有物必歸于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化。”闡發了作者對自然萬物運動、變化、發展規律的認識。蘇軾還看到事物總是在相互矛盾對立的狀態中互為依存:“有成而后有毀,有廢而后有興”[3](P288);“必嘗去也,而后有歸;必嘗亡也,而后有得,無去則無歸,無亡則無得”[3](P105);“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者兩之,通者一之,不能一則住者窮于伸,來者窮于屈也”[3](P291)。同時,他又看到事物總是在相互矛盾的運動過程中互相轉化,指出 “否極泰至”是 “物理之常然”(《量移廉州表》),“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墨妙亭記》)。人事之理如此,自然萬物也是這樣,“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變化往來,有逝無竭”(《天慶觀乳泉賦》)。在蘇軾看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事物都在“興廢成毀,相尋于無窮”(《凌虛臺記》)的運動中變化著,一切事物都要經歷盛衰興亡的過程,沒有什么可以“恃以長久”不變的東西。由是觀之,蘇軾能夠辯證地看待問題,盡管他的辯證思想是樸素的經驗性的,但當他用來看待和處理人生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時,便顯得識見通達、襟懷超邁。
既然人世間的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交替轉化,就不必過于膠著個人的榮辱得喪:“知哀樂之不可長,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游恒山記》)由此出發,蘇軾從“不務雷同以固祿位”,而是“下視官爵如泥淤”“芒鞋不踏利名場”,表現出對功名利祿的淡泊。對社會上那種“士所志于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張君寶墨堂記》)、“處者安于故而難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茍安之弊”(《張氏園亭記》)的奔競逐利之風,蘇軾表示甚為鄙夷。對此,蘇軾的解決之道是,“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王君寶繪堂記》),即人不要被物欲役使成為物的奴隸,方能擺脫俗世利害關結的羈絆,從而解除精神枷鎖獲得心靈自由,達到無住不樂、無往不暢的境界。由此,蘇軾深慕“陶謝之超然”,屢屢以早退閑適的白居易自況,稱頌歐陽修見機而退為“有道者”,贊許王安石“進退之美,雍容可觀”,肯定韓琦、張方平等大臣在仕途受阻后,或“退默深居”,或“寓形于醉”“毀譽不動,得喪如一”的風度。他自己也正是這樣踐行的,所謂“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死生窮達,不易其操”(《韓魏公醉白堂記》),其識見之超邁,胸懷之曠達實為古今難儔。
形成蘇軾思想的文化根源比較駁雜,其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墓志銘》中指出:“(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有“得吾心矣”之嘆,“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墨,博辨無礙,浩然不見其涯矣”。這說明蘇軾既信奉正統儒學,還探涉佛家,研讀老莊,因而使其思想呈現出復雜的面貌。但蘇軾的思想并非是糅合各家思想的大雜燴,而是以儒學為正宗,以佛老為輔翼,經過獨立思考熔鑄而形成的。蘇軾的曠達正是其復雜的思想通過自身特殊際遇而形成的產物。蘇軾奉儒為正統,因為有儒家思想做根基,才使他雖曾一度“歸誠佛僧”而終未遁入空門,走向消極頹靡、游戲人生;蘇軾好佛老,這對仕途多舛的東坡來講,有助于他處理仕途上進退行藏的矛盾,消遣他政治失意的苦悶,不致被政敵打壓和生活的困絕摧垮;蘇軾識見圓通,心胸豁達,這使他能夠于逆境困頓中不失積極用心,未忘為政為民為文,給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蘇軾的曠達實際上反映了宋代社會在三教合流日益成為思想界的普遍趨勢下,士大夫“修身以儒、治心以釋”(《閑居編》卷十九)的精神走向,而蘇軾無疑是這一風尚的典型代表。
二、蘇軾的曠達在其文學創作上的體現
蘇軾的曠達當然地為其文學創作提供了高標獨立的視界,鋪設渲染遼遠濃烈的背景氛圍,決定著他的創作主張,形成個性鮮明的藝術風格。
(一)曠達與蘇軾的藝術風格
蘇軾興情曠達,天才宏放,是高產多能的大家,在詩詞歌賦書畫諸方面都有極高成就。國學大師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斷言:“三代以下詩人,無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4](P26)將其列入中國詩歌史上文才人格兼備的四大家。這里,王國維把高尚偉大之文章與高尚偉大之人格掛鉤,點出了文學創作的一個深刻規律,文學亦人學,人格即文格。蘇軾文學成就的獨創性和難以復制性,根源于他鮮明獨立的個性。蘇軾也表明自己的文藝主張說:“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書朱象先畫后》)達心適意,正可宣泄其個性襟懷。杰出作家的創作風格無不是其個性胸臆的展現。人們賞讀蘇軾,常常嘆服于他在作品中層層推出的警言妙理,敬服于他發自心肺的浩然正氣,折服于他舒卷自如、無施不可的筆力,波瀾橫生、變化多端的章法,才思洋溢、觸處生春的詩思,搖曳多姿、行云流水般的文風,殊不知這正是蘇軾曠達胸襟的藝術宣泄和心靈綻放。
(二)曠達與蘇軾創作的境界
1.以理馭情,清妙超脫
蘇軾乃智慧型詩人,其寫作活動往往與生活打成一片,他常以詩人的敏感發現提出生活中的詩意和矛盾,又以哲人的睿智掃滅情累,以理安懷,終歸于曠達,這種情調在蘇軾的作品中是非常突出的。如《超然臺記》,開篇即發超然之意,然后入事,敘事過程中忽及四方之形勝,忽入四方之佳景,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闡發了作者超然物外則“無所往而不樂”的人生哲理。《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上片先寫心情的扭結郁悶:“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對天國神往與對人間眷戀的矛盾使作者悵惘不已,但轉念想到“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也就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祝福中和月光下開懷自釋、痛飲達旦了。千古名篇《赤壁賦》,入筆即景生情,因情生悲,又以理遣情,回悲為喜,結之以曠遠,兩賦氛圍清泠、意境高妙、思緒超然,充分顯示作者高超的藝術腕力和善于從矛盾中解脫的曠達襟懷。
2.搜研物情,理趣深邃
蘇軾提出詩文創作要善于“搜研物情,刮發幽翳”(《祭張子野》)這有助于詩人深掘意境、深化詩意、創造新的文學形象。蘇軾曠達俯視,洞幽燭微,眼光超邁流俗,常常于人情物理中發他人之所未見未言者,吟出富含哲理的警言妙語。最為人熟知的《題西林壁》,寫觀賞廬山者角度不同,收入眼底的美景也是各異,觀山如此,觀世間萬物也一樣,提醒世人跳出局限超越利害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全貌。《慈湖夾阻風》寫“且并水村欹側過,人間何處不巉巖”,暗示世人坎坷無處不在,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應對風雨。《浣溪沙》“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是人生應該樂觀的吟唱。《琴詩》則表達了主觀意志與客觀條件相統一方能取得成功。蘇軾一生沉浮不定,一貶再貶,世事無常令他慨嘆不已:“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爾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和子由澠池懷舊》)對生命的體悟化為氤氳的禪意和雪泥鴻爪留給后人去品鑒。《泛穎》一詩寫得別開生面,形象新穎富有情趣,是所謂人人意中有而語中無者:“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蘇軾貢獻了一批這樣的理趣詩,劉熙載說“蘇詩長于趣”即在此,理趣詩經蘇軾而廣大,這是他對宋詩的開辟貢獻,后人繼寫,成為宋詩優于唐詩的一個特點。
3.任性宣情,宏肆奔放
蘇軾一生如其自述,“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生死之際”(《與李公擇》),如此血性至情,發為詩文,施之筆墨,自然形成蘇軾任性宣情、宏肆奔放為主導的多樣化藝術風格。對此沈德潛形象地指出,蘇軾創作如“天馬脫羈,飛仙游戲,窮極變化,而適如意之所欲出”(《說詩晬語·卷下》),正道出了蘇軾任性宣情而無不合乎法度的創作個性和杰出成就。這在蘇軾各種文體創作中有淋漓盡致的體現。
在詩。蘇軾一生寫詩兩千七百多首,可謂包羅宏富精彩迭見。葉燮《原詩·卷一》指出:“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蘇詩關心政局直陳得失,表現了他率真的秉性和為政操守。蘇詩語言以自然奔放博洽無礙見長,他是天才的大學問家和語言大師,經史子集、佛老道藏、俚諺俗語到其筆下“皆歸熔鑄”,任其自由驅使。蘇詩兼能各體而尤善七言七古,長于在這類恢宏闊達的篇制中揮灑才情縱橫古今施展腕力。試讀其名句名篇,用典無礙如“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流利酣暢如“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磅礴跌宕如“公昔騎龍白云鄉,手抉銀漢分天章”,以及《百步洪》《登州海市》《雪浪石》《煙江疊嶂圖》等七言長篇,均顯示了坡公“波瀾浩大、變化不測”(《詩人玉屑》卷十七)的筆力和奔放性情。誠如評論大家趙翼在悉數唐宋優秀詩人的創作后所言,蘇軾“以文為詩……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為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甌北詩話》)。
在詞。蘇軾對詞體創作的最大貢獻是,一掃詞壇倚紅偎翠的青樓形態,突破婉約傳統,開創豪放詞風。這顯然與其任性宣情的超曠個性和文學主張是一致的。傳世蘇詞約三百五十篇,比當時專業詞人柳永還多。詞至柳永一變,初加開拓,使之從青樓華筵走向市井羈旅。詞至蘇軾而大變,他有意抗衡柳永,清切婉麗為宗的標準被打破,廣闊豐富的社會人生成為詞的表現舞臺,為以后辛詞再變樹立了先導。蘇軾對詞的創變革新空前擴大了詞體的廊廡和表現范圍,突破了傳統詞體題材表現的狹窄面。在蘇軾筆下,舉凡名勝、鄉愁、閨怨、政治、友義、田園、邊關、情愛等等,皆可盡情書寫,以至于“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5](P108)。 蘇軾更以豪邁的氣勢和雄健的筆力一洗綺羅香澤之態,為詞苑貢獻了一批前所未有的藝術形象。如《南鄉子》寫“帕首腰刀是丈夫”的英武將軍,《江城子》寫“老夫聊發少年狂”的太守欲挽強弓射天狼,《沁園春》寫“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青年報國豪氣干云。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作者更用交錯時空、縱橫古今的手法,描繪了儒雅將軍于亂石崩云、驚濤拍岸的兇險環境中輕松打敗強敵的英雄形象,這在詞史上屬首創。與此相應,蘇詞語言亦盡辭軟媚脂粉氣,讀之但覺其“挾海上風濤之氣”撲面而來。如《八聲甘州》的“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滿江紅》的“江漢西來,高樓下,葡萄深碧,猶自帶岷峨雪浪,錦江春色”等篇章,激昂排蕩,氣象清雄。蘇詞正如南宋愛國詞人劉辰翁所譽:“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辛稼軒詞序》)
在文。蘇軾文章尤可印證顯示其曠達超邁的個性和自然奔放的藝術風格。他在《自評文》中快意地宣稱:“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主張寫作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隨物賦形,姿態橫生。蘇軾一生筆耕不輟,于文章用力尤勤。他的政論文,包括早期的應制及史論、進策、奏議等,大都寫得議論英發、雄辯無礙、剴切誠直,見解超邁流俗,承繼了漢臣賈誼、陸贄的文風,也可看出縱橫家的筆法和莊孟、《戰國策》的影響。如其《大臣論》《平王論》《留侯論》等。蘇軾的小品文,包括題記、書札、隨筆、序跋等,往往特見精彩,或天機湊泊情趣晶瑩如《記承天寺夜游》,或見解新穎慧眼別具如 《日喻》,或不加修飾洞見肺腑如《上梅直講書》《答參寥書》等等,揮灑寫作與不經意之間,最能顯示作者智慧開朗的人格魅力。蘇軾的文章以記游敘事類的散文成就為高,釋德洪《跋東坡 懷允 池錄》指出,“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描繪了蘇軾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宏肆奔放的寫作風格。其名篇佳構流布廣遠,如《潮州韓文公廟碑》議論高絕,此碑一出而頌韓之文“眾說盡廢”。《韓魏公醉白堂記》贊賞廉于取名、嚴于責己的重臣風操以激勵朝堂。《石鐘山記》寫景奇寒,逼真狀物令人毛聳。《赤壁賦》則把議論抒情寫景熔為一爐,展示了隨物賦形,搖曳生姿,汪洋恣肆的藝術表現力,蘇軾文章可謂爐火純青。繼文壇領袖歐陽修之后,蘇軾把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推向高峰并取得成功,代表了北宋詩文的最高成就。蘇軾一生的文學創作鮮明地印記著他曠達超邁的胸襟個性,研讀蘇軾可以體悟,東坡之創作絕非拘拘如轅下駒者可學,也絕非邯鄲學步者可步的。
三、結語
蘇軾,是“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余秋雨語),也是世界級的大作家。2000年,法國《世界報》舉行了名為“千年英雄”的評選,“選出1001—2000年間的全世界12名杰出人物。蘇軾成為入選者中唯一的中國人[6]。這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中國文化的光榮。蘇軾一生給后世留下了豐富珍貴的精神遺產,他“忠君愛國”的從政操守,曠達超邁的胸次襟懷以及傲視困難、逆境不沉、積極有為的精神,早已化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因子向后衍展。今天我們學習借鑒蘇軾的精神遺產,對培養健康堅強的人生觀,提高民族文化素養,乃至豐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
注釋:
[1](唐)司空圖,等.詩品二十四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
[2](宋)王禹偁.小畜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22.
[3](宋)蘇軾.東坡易傳[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4]王國維.王國維文集(第1卷)[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5](清)劉熙載.藝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元波.蘇東坡是大英雄[J].西南航空,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