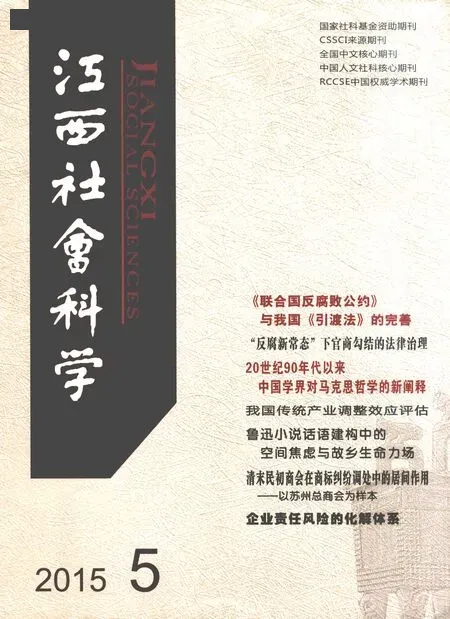傳記文學的表現范式與創作反思
■韓春萌
傳記文學是以文學手法記述人物的生平事跡、描寫人物成長歷史的一種文學樣式。《中國大百科全書》這樣定義:“記載人物的作品稱傳記,其中文學性較強的作品即是傳記文學。”[1](P1312)這種獨特的文學樣式,深受讀者喜愛。然而,縱觀當前的傳記文學創作,盡管作品數量眾多,但水平參差不齊,有不少作品存在媚俗化傾向。為了更好地發揮傳記文學的社會教育功能,有必要對傳記文學的文體特征和創作方法作進一步探究。
一、“以人為本”的表現范式
中國文聯副主席仲呈祥在“‘風雅頌’杯當代優秀傳記文學作家評選”頒獎活動上說:“現在提倡以人為本,傳記文學特別‘以人為本’,人是放在第一位的,傳記文學作家都有豐富的人生體驗和感悟,他們從人切入歷史,折射出人類的智慧。”[2]在傳記文學的創作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在敘述角度、結構藝術、人物塑造等方面,把傳主放在中心位置來考慮。
(一)以傳主為中心的結構方式
以傳主為中心人物,以中心人物為視角來結構作品,這是傳記文學的基本方法。縱觀當今許多傳記作品,尤其是長篇作品,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傳主 “出生——成功——去世”的過程。這種平鋪直敘的敘事方法,難以達到引人入勝的效果。如《賺錢之神邱永漢傳》按邱永漢所從事的職業和經營的業種分章,敘事平淡而不吸引人。再如南方某出版社的 《梁羽生傳奇》洋洋30萬字中只有第一部分“名士風流”寫了他的生平事跡外,其余六個部分都是他具體作品的評述,人物的性格和傳奇色彩不足。
在傳記文學創作中應當將傳主擺在最重要地位,圍繞傳主的人生經歷,選擇其一生中充滿故事性的重要事件,來反映傳主的人生軌跡。通過這些有意義的人生故事,起到教育人、激勵人、啟迪人的作用。優秀的傳記文學往往能夠圍繞人物來選材和結構作品,不僅有很強的可讀性,而且還能夠突出傳主在整部作品中的中心地位。例如被評為全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的《開國領袖毛澤東》《梅蘭芳全傳》等,就具有這些特征。
以人物生平為中心線索來結構作品,要盡量避免敘述平淡,可以變換敘事方法。可以像《邁克·泰森:我的王朝》那樣適當運用倒裝敘述和交錯敘述,使傳記文學在結構上更加跌宕起伏。人物傳記也可以學習傳奇故事寫法,多留懸念以避免敘事平淡。除了在敘事方法上要有變化,對傳主的生平材料的處理也非常重要,必須學會剪裁。以傳主的生平為結構線索,并不是將傳主的什么事情都堆上去。為了克服 “流水賬式”的平淡敘述,還應當考慮敘事角度的變化,必要時可以轉換人物的敘述角度。
(二)“踵事增華”的立傳原則
中國有以人為史的傳統,先秦兩漢史傳文學確立了“踵事增華”的原則。南朝蕭統在《文選序》指出:“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3](P1)這種“以事物由簡單趨向繁復,由質樸趨向華麗的普遍發展規律而推及文學的發展規律, 蕭統的看法是難能可貴的”[4](P84)。所謂“踵事增華”,就是要在真實性的基礎上再進行文學化,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動感人。適當虛構無關痛癢的某些細節,符合“踵事增華”的原則。
傳記文學要為傳主樹碑立傳,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必須是真實的人物形象。遵循“踵事增華”的原則,其前提應當是真實性,因此避免不講“度”的虛構。“傳記可以寫得如小說一樣生動有趣,同時并不放棄對事實的追求。”[5]傳記創作中有一種叫“死無對證”的方法,就是對已故的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進行隨意虛構。因為傳主已逝,所以死無對證。例如根據歷史照片,虛構照片上人物的對話和故事。盡管此事“死無對證”,但這種方式是不足取的,傳記文學不能因為傳主已作古就胡編亂造。
有人認為:“新時期傳記文學已逐漸擺脫了臉譜化、順序化和高大全的單一寫作模式。人們對傳記文學已產生了高層次的審美訴求。”[5]這種更高的審美訴求,當然主要是藝術上的,那就是要加強傳記文學的文學性問題。總的來說,還是必須遵循“踵事增華”的原則,在人物塑造上把握文學化的“適度”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再提高傳記文學的審美層次。
(三)典型化與傳主個性彰顯
很多傳記作者注重于傳主人生傳奇的描述,故事性寫得較強,有一定的可讀性。但是這樣處理,作為“寫人的文學”,對傳主的人物個性沒有彰顯出來。這就使得傳主形象模糊,不是獨特的“這一個”。傳記文學作家王朝柱指出:“傳記還叫傳記文學,要強調文學性,強調個性,只有個性才有文學性。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以前人們認為不好看,這里面就存在創作者的一個誤區,就是人物個性不突出,共性的東西太多。”[6]
傳記文學的人物塑造,需要運用典型化手法,才能血肉豐滿。有的傳記作品由于作者選材和剪裁時缺乏“性格”意識,典型化手法不夠,由此個性差異不明顯,形象沒有“立”起來。如《香港四大天王》共四本傳記,只是描述了傳主的部分人生經歷和演藝生涯,沒能突出傳主的個性特征。根據“典型化”理論,要彰顯人物的性格特征,人物的性格必須有形成發展的過程,同時要盡力突出人物性格的復雜性。當前一些傳記作品的人物塑造,還停留在“類型化”的手法上。
傳記文學是寫人的文學,塑造人物要盡量寫出人物的個性特征。筆者在寫《拳壇教父唐·金》和《武林奇俠黃飛鴻傳》時,有意突出唐·金狡詐、黃飛鴻低調的性格特征,并描繪了他們性格發展的歷程。如《拳壇教父唐·金》這本書中的主人公在獄中寫信給阿里,說“黑人應該互相幫助”,出獄后找到阿里,拼命鼓吹“咱們黑人也應該有自己的經紀人和拳賽推廣人”、“我們黑人應該幫黑人”[7](P24-28), 最終成為阿里拳賽的推廣人。從語言和細節上,力求寫出唐·金的狡詐個性。《黃飛鴻正傳》中有一處寫到黃飛鴻退隱江湖,有人上門來拜他為師,他就故意說自己是黃飛鴻的哥哥,弟弟出門了。[8](P166)寫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目的是為了突出黃飛鴻為人低調這一個性特征。
二、美丑轉化的審美模式
藝術美源于現實生活,作為“以人為本”的傳記文學,與人物的生活歷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審美與審丑,同是文學藝術的功能之一。要將生活丑轉化成藝術美,必須遵循傳記文學的審美原則。
(一)關于傳主的選擇
傳記文學肩負著為人樹碑立傳的使命,傳記作品具有勵志和警示作用。傳主的創業傳奇和成功的人生歷程,對現在正在奮斗的青年人有激勵作用。正因如此,傳記圖書大受歡迎。除了傳記圖書,受歡迎的還有不少專門的人物傳記雜志,如《名人傳記》《人物》《傳記文學》《人物春秋》等。就連中學語文教材中也選了不少傳記課文,竺可楨的《哥白尼》、侯仁之的《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記》和楊振寧的《鄧稼先》等。要充分地發揮傳記文學的社會教育作用,就必須選擇好傳主。
縱觀當今的傳記文學,傳主大多是名人明星、商業精英、領袖人物和傳奇人物。市場上有不少反面人物傳記,如《蔣介石大傳》《希特勒全傳》《林彪傳》《汪偽特工李士群》《汪精衛傳》等等。反面人物能不能成為傳主?這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問題。應該盡量少選擇反面人物為傳主,即使要寫也是站在批判的立場上來寫。
反面人物不是不能成為傳主,但為他們立傳時一定要有立場。正如惺園退士的《〈儒林外史〉序》所說:“余惟是書善善惡惡不背圣訓,先師不云乎:‘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讀者此意求之《儒林外史》,庶幾稗官小說亦如經籍之益人,而足以起觀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云爾。”[9](P624)描寫“善”、“惡”的目的在于提供借鑒,讓人們引以為戒。
(二)虛美與溢惡的處理
大多數人寫傳記,都是站在“虛美”的角度。所謂“虛美”,是指傳記作者對所寫的傳主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在寫作過程中很容易喜歡上這個人物,因此帶有某種傾向性,都往好的地方寫。“虛美”現象是傳記文學創作中的一大缺陷,不利于傳記文學發展,例如一些作品有意美化古代的一些皇帝、忠臣,過分夸大他們反貪、廉政、愛民的一面,像《少年包青天》《一代廉吏于成龍》等就存在虛美現象。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歷史上有幾個真正的開明皇帝?正直的清官是有的,但真正的“清官”也是很有限的。包拯、海瑞、于成龍等不可能像文學作品中描寫得那樣鐵面無私。既然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作為傳記文學的描寫對象,就應該力求真實。
在創作過程中也有少數人會有 “溢惡”傾向。所謂“溢惡”就是暴露傳主丑惡的一面。報載曾有作者給香港富豪立傳,寫傳主與他的秘書搞同性戀。結果鬧得打起了官司,雙方不歡而散。還有不少傳記作品,如《汪精衛傳》《希特勒大傳》等,傳主本身就是個反面人物,創作過程中不能不寫到陰暗面和人性的丑惡。如果作者過分渲染丑惡的東西,難免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要處理好“虛美”與“溢惡”問題,就要對傳主有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傳主是好人還是壞人,不是用簡單的公式能概括的,人都是有雙重性的。可以借鑒《史記》的互現法,立傳時要重點突出哪一方面,就圍繞它來選材。在處理有關反面材料時,如果一時難有明確的答案,就更應當客觀公正地處理。在寫到反面人物的丑惡人生時,可以采用“評傳”的方式,必要時進行點評對讀者加以引導,這樣可以對青少年讀者有警示作用。
(三)美丑轉化的方式
傳記文學通過作品所塑造的傳主形象,或鼓勵人們以傳主為榜樣,或警示人們以傳主為戒。優秀的傳記作品能夠起到影響人、鼓舞人和警策人的作用。既然人們對反面傳主的丑惡人生也感興趣,市場有需求,就不可能禁止以反面形象為傳主的傳記文學出版。那么,如何克服反面形象作傳主帶來的負面影響,讓傳記起到“引以為戒”的警鐘作用,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研究課題。
傳記文學作家應當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在描寫丑惡人生中注意方法和尺度,在批判丑惡的人生的同時將生活丑轉化為藝術美。“在原來現實丑的基礎之上加上了審美創造者的審美情感和真實化、典型化的藝術表現技巧的光環,從而形成了雙重的審美效果——丑感+美感。”[10](P131)從審美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努力將生活丑轉化為藝術美。
從生活丑向藝術美的轉化,需要經過傳記作家的創作。傳記文學的審美性特征要求我們將生活丑變成藝術美,也就要求傳記文學作品在對丑惡人生的描寫過程中帶有批判色彩。對傳主丑惡的人生事跡要有“點評”,要有明確的是非觀念和愛憎觀念,要有鮮明的態度和立場。此外,傳記文學在塑造反面形象的同時,也可以在作品中適當塑造一些正面形象。只有這樣,才能讓讀者受到教育,才能更好地發揮傳記文學的社會教育作用。如果反面人物被塑造成世人敬仰的偶像,即使描寫生活丑的水平再高,也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美。
三、當前傳記創作的反思
當前的傳記文學創作還存在不少問題,諸如真實性問題、“麥當勞化”問題以及媚俗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出現有著復雜的原因,商業化中的趨利行為是其主要原因。深刻反思當前傳記文學創作中存在的這些問題,有利于推動傳記文學創作的向前發展。
(一)戲謔化與虛構問題
以歷史人物的生平為原型的影視文學作品,本來也應是傳記文學的一部分。像《戲說乾隆》《鐵齒銅牙紀曉嵐》這類搞笑作品,大量戲謔化手法的運用,使其“戲說”的成分太重。歷史人物傳記中的戲謔化情節,大多取材于野史或民間傳說,這些材料本身就不太真實。為了使搞笑的成分更濃厚,還有不少情節是作者虛構的。像《黃飛鴻笑傳》這樣的戲謔化作品,不能算是真正的傳記文學。
戲謔與虛構是傳記文學的天敵,因為它違背傳記文學真實性的原則。歷史學家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所用史料,在腳注中多注名資料來源。姚雪垠的《李自成》雖以真人真事為依據,但虛構的成分超出了限度,只能當成歷史小說。傳記文學理論家趙白生強調“傳記事實”的重要性,他認為“傳記事實是一部傳記的生命線”[11](P14)。
從另一方面看,還有的傳記作者為了追求傳記文學的真實性,通過想象來設計故事情節,通過虛構“逼真”的細節來刻畫人物,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激情·原色——舒淇》被批評正是如此。真實性是傳記文學的生命線,因此必須守住“真實性”這一創作底線。戲謔化和虛構帶來的后果,必然使傳記文學失真。失真的傳記文學作品,有損于傳主的形象,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和官司,同時極易給喜愛傳記文學的讀者造成誤導。所以在傳記文學的創作過程中,一定要把握好文學性與虛構之間的關系。嚴格遵循真實性原則,既不虛構也不戲謔化。
(二)“麥當勞化”問題
“麥當勞”理論來自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喬治·里澤爾的著名社會學暢銷書 《麥當勞夢魘——社會的麥當勞化》。麥當勞是美國著名的快餐企業,所謂“麥當勞化”,指的是快餐店的規則逐漸主宰美國社會的諸多方面乃至世界其他地域的過程。這個過程由于極強的高效性、商業性和可復制性而主宰了世界,然而在這種理性的引導下,社會衍生出了非理性。克隆化、快餐化的傳記作品大量涌現,正是這種“麥當勞化”帶來的問題。什么人的傳記好賣就出什么書,這就是“麥當勞化”的表現。
文學商業化過程中,這種“跟風書”現象可謂屢見不鮮。因為要搶時間,書的質量得不到保障。出書“短、平、快”自然不能避免內容雷同、裝幀類似、克隆化、快餐化。當紅影星和體育明星的書重復出,商界巨子的傳記滿天飛,內容都是大同小異。最典型的就是有關李嘉誠的傳記,上網搜索至少有十幾種。如《李嘉誠傳》《李嘉誠自傳》《李嘉誠全傳》《香港超人李嘉誠》等等。面對傳記文學的“麥當勞化”現象,我們不能不考慮傳記作品的質量問題。如果創作和出版的傳記文學都是這樣質量不高的作品,將來誰還讀傳記文學?傳記文學如何生存與發展?
(三)趨利與媚俗化問題
媚俗化是傳記文學的一大詬病,它是商業社會趨利帶來的不良后果。市場上什么內容吸引人,哪怕是迎合某些人低級趣味的東西,依然有人去寫。《十大土匪惡霸》一書中的《美艷女匪首千青》,寫傳主15歲在家洗澡時被強奸,后來多次描寫與她那對“曾引以為驕傲的大奶子”相關的情節。這種迎合低級趣味的描寫,就有媚俗之嫌。
如何才能避免媚俗?這就要求在材料處理上有所剪輯和選擇,突出不同的重點。媚俗與否,關鍵在于怎么寫。同是寫東北女土匪張淑貞的,《十大土匪惡霸》中的《東北女匪首張淑貞》寫她18歲與長工偷吃禁果,逃婚時在一客店被十幾個日本兵輪奸,而后又被店主賣到妓院做妓女,在此遇到嫖客匪首大龍,上山當了女匪……電視劇《煙花女駝龍》則把重點放在張淑貞悲慘命運和抗日斗爭上,傳主雖然相同,但這個形象的意義完全不同,電視傳記中張淑貞這個人物的積極因素更突出。
以上本文作者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對傳記文學的創作模式、審美特征進行探討,對當前這一文體創作中的一些問題進行反思。當前傳記文學創作中的問題,涉及作家的創作方法、作品的審美觀、出版界的行規等。針對傳記文學創作中所存在的這些問題,有必要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在探討中不斷提高當代傳記文學的創作水平。
[1]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2]葉永烈等10位作家當選“當代優秀傳記文學作家”[N].大河報,2005-10-17.
[3](梁)蕭統.昭明文選[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4]薛寶生.論“踵事增華”的三種實現方式[J].湖南第一師范學報,2009,(2).
[5]李健.中國新時期傳記文學理論研究綜述[N].文藝報,2006-12-21.
[6]張體義.寫傳記文學,他們最優秀[E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5-11-4.
[7]韓春萌.拳壇教父唐·金[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8]韓春萌.武林奇俠黃飛鴻正傳[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9]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10]景旭.美丑關系新認識[J].社會科學輯刊,1995,(2).
[11]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