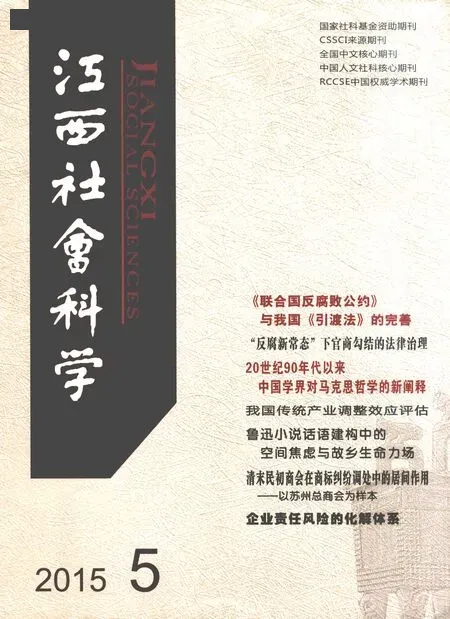史鐵生作品中的神性理想及詩意建構
■鄧齊平
一
在當代中國新時期作家中,史鐵生是對國外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借鑒吸收得較為圓熟的作家。在史鐵生的創作中,我們看不出像馬原、余華、格非、蘇童等作家早期創作中明顯的模仿痕跡。在《命若琴弦》《禮拜日》《一個謎語的幾種簡單的猜法》《中篇1或短篇4》《關于一部以電影作舞臺背景的戲劇之設想》等帶有濃厚的形式主義探索意味的作品中,我們仍然能感受到史鐵生扎根于現實土壤之中的鮮活的生命體驗。
史鐵生的這種圓融自在,來自于他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透徹理解。康定斯基談到由點、線、面所組成的現代形式主義藝術說:藝術最終通向的是人的靈魂的“內在需要”[1](P45)。史鐵生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解也是如此。他是從人的靈魂的經驗事實來理解現代主義的。如對博爾赫斯的理解,史鐵生說:“我理解,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是指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他強調的其實不是時間,而是作為主觀的人的心靈,這才是一座迷宮的全部。”[2](P76)迷宮存在于人的靈魂深處,史鐵生把現實世界看作是心靈的迷宮。時間的交叉,空間的并存,是心靈的感應。所以,在史鐵生的文學世界里,感覺是可以錯位的,思緒是可以顛倒的,印象是可以混淆的。史鐵生對普魯斯特的理解也是獨特的。他說:“普魯斯特在吃瑪德萊小點心時,一瞬間看遍了自己的一生。如普魯斯特一樣的感受,幾乎我們每個人都有過。”[3](P326)史鐵生把普魯斯特瞬間即永恒的生命體驗理解為整體性的審美體驗,即使是對美味的品嘗,也是一種全身心的審美感受。這和史鐵生對加繆的西緒福斯神話的體驗一樣,他認為只有在審美過程中的體驗,才會感受到生命真實的存在。人所占空間有限,瑪德萊娜小點心所占空間更是微乎其微,但它能承載整個生命真實存在的感覺信息,它連接著一個人整個一生的漫長經歷,它牽動著個體鮮活生命的萬千思緒,它所超越的時間和空間是無限度的。
作為審美主體,對往事的回憶,普魯斯特強調的是確證生命真實存在的喜悅,說明他是現實的;而史鐵生看到的卻是“脫離現實勞役進入藝術的欣賞”的詩意和美感,這說明他是抒情的。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命若琴弦》中的無字藥方、《毒藥》中的泡泡糖毒藥、《務虛筆記》中的寫作之夜、《我的丁一之旅》中的戲劇之夜等,都是可以連接起無限渺茫的宇宙人生的那一個 “奇點”,或者說是“起點”,猶如普魯斯特審美視野里的馬德萊娜小點心。作為藝術符號的象征物,它所喚起的是人的生命整體性的記憶和印象。所以,它能在人生的某一個時刻,突然喚醒一個人的全部生命活力和激情,甚至激活整個僵化的、死氣沉沉的現實世界。所以,史鐵生特別強調文學藝術把握的是每一個個體人的獨具的心魂,它連接著紛繁復雜的萬千世界。
使個體獨具的心魂映現出無限浩渺的現實和歷史,史鐵生的整體性審美經驗的表達必然會選擇象征或隱喻的寫作技巧,即:以部分象征整體,以具象隱喻抽象。無論是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還是普魯斯特“瑪德萊娜小點心”、加繆的西緒福斯神話、伍爾芙的“心靈漩渦”等,史鐵生強調的都是對情感的激發和對靈魂的捕捉。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史鐵生把這種混沌的情感或靈魂稱之為“行魂”①,后來又把它概括為“虛真”。在“虛真”里,包孕著人的善、惡、美、丑等等人性中各種復雜的因素,人的獸性、神性、魔性都存在。因此,在“虛真”的心魂世界里,充滿著林林總總的人生疑難和悖謬,給人帶來無窮無盡的困惑。史鐵生的寫作,就是試圖探秘、揭示“熱氣騰騰、變幻莫測的心靈漩渦”[4](P177)的奧秘,解開那令人困惑的疑難和荒誕。史鐵生說:“寫作從來就是去探問一個謎團。靈魂從來就是一個謎團。這一個‘謎’字有兩個解:迷茫與
迷戀。”[5]對“行魂”、“謎團”、“心緒”的把握,實際上就是對“空”(“虛真”)的把握。史鐵生說:“宇宙誕生前與毀滅后,都不是無,而是空……空不是無,空是有的一種狀態。那么死也就不是無,死是生的一個段落。作為整體的人類一直是生生不息的,正如一個音符一個個跳過,方才有了音樂的流傳。”[4](P172-173)與中國道家哲學的“空”“勢”“造勢”“道”等概念相結合,“虛真”也就是靈魂存在的可能性,這也是一種真實。人作為個體性的存在,必然要匯入人類整體之中才能“永恒輪回”地存在下去。“虛真”既是指個體心緒的真實,也是指與整體的人類連接在一起的向上、向善、向美的愿望或理想的真實。在人類整體存在的背景下,對個體心魂的捕捉,也就是以無限召喚有限、以神性引領人性。相對而言,具體的個體是有限的,作為整體的人類是無限的。有限是殘缺,無限是圓滿。于是,人的殘缺和神的圓滿就成了史鐵生創作思維中的兩個極點,人與神既對立又統一的世界就成了史鐵生文學世界的基本架構,立足于人的殘缺眺望神的圓滿,同時又以神的圓滿燭照人的殘缺,從而形成了史鐵生文學創作中獨特的審美視野。
二
在史鐵生的文學世界里,人與神既對立又統一,但對立是絕對的,統一是相對的。史鐵生認為人與神之間、有限與無限之間、相對與絕對之間存在著永恒的距離,而這種距離由于是殘缺與圓滿之間的相互觀照而形成一種審美關系,因此,它是一種審美心理距離,是一種具有詩意的審美距離感。無論站在哪一個端點上去觀照另一個端點,都是審美的觀照、詩意的觀照。又由于兩個端點的絕對存在和不可能重合,使得兩個端點之間相互觀照的符號化表達,成為二者相互之間的象征或隱喻,即以人顯神或以神喻人。以人觀神,使史鐵生充滿對自然宇宙和社會人生的敬畏之情,同時也使史鐵生看到人世間造人為神的悲劇和鬧劇;以神觀人,使史鐵生充滿對人世間的悲憫情懷,同時也使史鐵生看到造物弄人給人類造成的災難和人類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命若琴弦》《毒藥》《死國幻記》等作品直接采取寓言的形式,在人與神、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之間造成一種審美張力,從而使有形的琴弦和無形的目的、有形的毒藥和無形的生命意志以及無聲無息的“死靈”和溫暖嘈雜的“光明”之間形成一種審美關系,并涵養出各自的審美境界,使具體的物象 (無字藥方、毒藥、死靈)各自具有抽象的象征和隱喻的豐富內涵,創生出獨特的過程美學的審美意義。史鐵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談到西緒福斯神話時說:“有回我走上一條名為西緒福斯的路,那地方才叫荒誕呢!我們從早到晚地把石頭推上山去,石頭又滾下來,我們從早到晚地再把石頭推上山去,石頭又滾下來……直到有一天我從落日中看見了西緒福斯的身影,從天幕中讀出了一個美麗的注釋,那條路途也才變得美麗起來……”[6](P367)人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上帝只管交給你這樣一個現實,要你從無奈中找出一個美麗的價值,在人與神之間的緊張關系中建構人生的意義。
在神人沖突和神人融合的審美張力之間,史鐵生找到了理想人性的合理限度。理想人性即神性。但由于人永遠也不可能成為神,理想人性永遠只能是虛擬的真實,即“虛真”。神或神性只是人在自我完善過程中的想象或虛構。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可人還活著,史鐵生宣告上帝活著,但上帝永遠在天上,上帝只是作為神靈運行于人世間,上帝活在人的心中。人神分裂是現實,人神同一是理想。史鐵生說:“有限與無限的對立,殘缺如人與圓滿如神的永恒距離,惟此一條是原版的神說,因其無需人傳,不傳也是它。絕對的命令就聽見了。”[7]這種“聽見”是看不見而信的信仰。
樹立神的標準和對神的召喚,源自于史鐵生對自然人性的不信任。在與神的圓滿的對照中,人的殘缺的直接表現就是人性惡。史鐵生認為真正的人性惡就是人與生俱來的追求和占有權力的欲望本能。他認為人有一種“控制異體”[8](P136)的古老恨怨,它使人不斷地追求無限的世俗權力和精神權力,造成人與人之間無休止的血腥暴力和精神虐殺。他說:“人性中,原是包含著神性與魔性兩種可能,浮士德先生總是在。”[9]人的自然欲望本身無所謂善惡,但它更傾向于受惡的引誘,更容易陷入獸性或魔性的泥淖。所以,在現實生活中,神性對人性的監督和引領是必不可少的。
人性解放的創作模式以揭露現實丑惡,張揚自然人性的合理性為鵠的。從 “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中解放自然人性,有它的歷史合理性。但是,沒有神性指引的自然人性并不一定走向真善美,也有可能走向假惡丑。史鐵生特別強調神性對人性的方向性指引。他說:“中國的文藝復興,全是人性的解放,沒有神性的沖動。‘人性解放’這四個字可不全是褒義呀。人性還有惡呀,全由著人性來,就糟糕了。”[10]樹立起人性解放的大旗沒錯,但矯枉過正也需要警惕。史鐵生看到人性解放的負面后果,始終警惕人性被獸性和魔性所控制,擔心它使人只追求實利,及時行樂,使人成為行尸走肉。如果人性被魔性控制,出賣靈魂,為虎作倀,或控制他人、征服他人,就將導致極權專制、暴力、霸道等,傷害人類自身。《文革記愧》《她是一片綠葉》《鐘聲》《務虛筆記》《記憶與印象》《我的丁一之旅》等涉及“文革”的作品,展現的大多是這一時期人性荒誕丑陋的一面,都與史鐵生對控制異體的權力意志的批判聯系在一起。
既然神人沖突是絕對的,神人融合是相對的,人與神之間有著永恒的距離。那么,人就不可能篡改神意,人就不可能僭越神位。史鐵生說:“世界是一個整體,人是它的一部分,整體豈能為了部分而改變其整體意圖?這大約就是上帝不能有求必應的原因。這也就是人類以及個人永遠的困境。”[11]神的“整體意圖”不可改變。在神的“整體意圖”中,人只能是丑弱、殘缺的。因此,在史鐵生的創作中,沒有偉岸崇高的英雄人物形象,丑弱的人、殘缺的人的生命形態成為史鐵生傾注全部熱情來加以表現的主要對象。如《命若琴弦》中的大、小瞎子,《毒藥》中的自殺者,《原罪·宿命》中被“種”在病床上的截癱者,《鐘聲》中的“古典派肖像畫”似的姑父,《關于一部以電影做背景的舞臺戲劇之設想》中死了七天的酗酒者,《務虛筆記》中的自殺者教師O、一夜白頭的醫生F、殘疾人C、Z的異性姐姐M、葵林里的女人,《死國幻記》中的眾多死靈,《記憶與印象》中的人形空白的姥姥、姥爺和顫抖的二姥姥、恐懼的老姑娘,《我的丁一之旅》中的姑父等等。我們可以把這種類型的人物形象概括為受難者形象。
史鐵生筆下受難者的形象是一群受苦受難的弱者形象,他們的原型是《圣經》中的約伯和圣子耶穌。如《奶奶的星星》中的奶奶,《山頂山的傳說》中的瘸子,《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和小瞎子,《我之舞》中的十八、世啟、老孟和路,《原罪·宿命》中的莫非和十叔,《中篇1或短篇4》《務虛筆記》《我的丁一之旅》《兩個故事》中的叛徒、流氓,《關于一部以電影作舞臺背景的戲劇之設想》中的酗酒者A,《老屋小記》中的B大爺、U師父,《記憶與印象》中的老姑娘、二姥姥、人形空白的姥爺、叛逆的大舅,《老好人》中的老好人等。還有一批是處在父母親情和自我愛情選擇的兩難境地之中的受難者形象,如《老屋小記》中的小三子,《務虛筆記》中的導演N和醫生F、殘疾人C、詩人L等。
在所有受難者形象中,史鐵生尤其對叛徒形象的心魂世界予以非同尋常的精細描摹,表現出史鐵生對叛徒的深切同情。在史鐵生看來,世俗的對叛徒的憎恨和貶斥,表現的正是人性的虛偽和殘酷。在神性的視野里,史鐵生沉痛地反省有關叛徒的話題,解構的是千萬年以來人類歷史上最為野蠻、殘酷和虛偽的一面,為叛徒呼吁人道意義上自由、平等的權利,從而使叛徒形象成為史鐵生表達神性理想的重要符碼。
被損害、丑弱、殘缺的受難者形象,在史鐵生的創作中不是主要人物的陪襯,更不是插科打諢的小丑,他們本身就是作品中呈現出來的主要審美對象,是史鐵生建構自身文學世界的核心要素,他們的出現不僅標志著史鐵生創作的重大轉變,同時也標志著新時期文學審美風尚的重大轉變。
三
雨果在《〈克倫威爾〉序》中說:“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與惡并存,光明與黑暗相共。”[12](P30-31)雨果把美丑既對立又統一的觀念看作是浪漫主義文學和古典主義文學相區別的標志。他說:“正是從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優美的典型這兩者圓滿的結合中,才產生出近代的天才,這種天才豐富多彩、形式富有變化,而其創造更是無窮無盡,恰巧和古代天才的單調一色形成對比;我們要指出,正應該由此出發以樹立兩種文學真正的、根本的區別。”[12](P32)雨果的這一宣言,在文學史上具有開天辟地、開辟蒙荒的意義和價值,此后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王爾德的《莎樂美》等,開始直面人類精神的黑洞,揭示人類魔性的恐怖,表現現實多樣化的真實,從此開啟現代審美的基本范式。
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與雨果有著大致一致的說法。他說:“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諸多苦難給這人間,你也可以為消滅種種苦難而奮斗,并為此享有崇高與驕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會墜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沒有了苦難,世界還能夠存在么?……就算我們連丑陋,連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們所不喜歡的事物和行為,也都可以統統消滅掉,所有的人都一樣健康、漂亮、聰慧、高尚,結果會怎樣呢?怕是人間的劇目就全要收場了,一個失去差別的世界將是一條死水,是一塊沒有感覺沒有肥力的沙漠。”[13]史鐵生的這段文字與雨果一樣,也是對單極化的崇高美的否定和對世俗化的美丑并存的現實真實的肯定。所不同的是,雨果借此而肯定了“滑稽丑怪”作為美的存在的合理性,而史鐵生則進一步地確立了殘缺作為美的存在的基礎性地位,從而宣告了對于完美、圓滿的古典美的追求幻象的破滅。既然美人、智者、英雄、佛祖只能相對于丑女、愚氓、懦夫、眾生而存在,離開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完美和圓滿就只存在于虛幻的想象之中,現實生活中永遠也不可能單獨地存在完美和圓滿。
如果說雨果顛覆的是古典主義時代的審美規范,那么,史鐵生解構的則是英雄時代的神話。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在審美領域里發現被遮蔽的殘酷的現實真實,即“丑的美”②。丑或者殘缺美的出現,標志著現代審美意識從先驗觀念向經驗感性的轉變,也標志著人類審美意識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史鐵生文學創作的意義和價值就在于他在經歷“文革”之后的當代中國實現了這種轉變,從而使他成為當代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代表性作家。
殘缺美是史鐵生以生命為代價感悟和體驗到的美感經驗,具有觸及靈魂的深度和廣度。但是,當有學者用“殘疾主題”、“自卑情結”和“宿命意識”來解讀史鐵生的創作時[14],卻遭到了史鐵生委婉的否定。他說:“‘殘疾’問題若能再深且廣泛研究一下,還可以有更深且廣的意蘊,那就是人的廣義殘疾,即人的命運的局限。”[15]“人的廣義殘疾,即人的命運的局限”,說的意思是:殘疾是人的抽象本質,殘缺指的是人命運的局限性。后來,史鐵生更明確地說:“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殘疾。”[9]從病理學的殘疾中剝離出來,抽象地觀照人性,史鐵生發現人的局限性是客觀存在的,完全不受限制的存在就只有造物主即神的存在。因此,只有在神的視野里,殘疾作為人的抽象本質方能與神的圓滿形成對照,從而形成審美距離感,產生審美效果。
用神性燭照人性,史鐵生看到的是人性中的獸性和魔性,是人性惡,是人性的殘缺,比如造人為神、極權專制、控制異體、人定勝天等等。與受難者形象類型相對應的,在史鐵生的創作中還存在著可怕者類型的人物形象。在這些可怕者人物形象身上,史鐵生看到的是人類可怕的獸性和魔性的膨脹。在《奶奶的星星》《務虛筆記》《記憶與印象》《想念地壇》《我的丁一之旅》等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是那個可怕的孩子的形象。可怕的孩子特別擅長于拉攏、打擊、孤立對方,擅長于奇跡般地抓住人的弱點加以無情的攻擊。他能抓住戰神阿喀琉斯的“腳后跟”,在古典意義的爭斗中,能致他人于死地。可是,在現代社會中,人的弱點恰恰是人性的表現,攻擊他人的弱點、缺陷乃至殘疾是極不人道的表現。與斗爭哲學相反,神性的關懷恰恰表現在對弱勢群體、對人自身的弱點、缺陷和殘疾的尊重和呵護上。可怕的孩子的形象是20世紀以來極權專制者的雛形。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史鐵生說:那個可怕的孩子獲取權力的途徑,是“人之罪惡的最初范本”,更令人恐懼的是“那個可怕的孩子已然成長得無比強大,已然漫漶得比比皆是,以致人間的一切歧視、怨恨、防范與爭戰中,都能看見他的影子”[6](P88-89)。 這是詩人史鐵生的敏感,那個可怕的孩子形象已經不是自然意義上的小孩,而是詩學意義上的幽靈,它已經飄蕩在人世間,成了征服者的象征,也成了炫耀某種神秘力量(如權力、魔力、戰爭等)的幽靈的象征。
與此同時,史鐵生也看到了人性中引人向上和向善的力量。即使是上帝弄人,那也是上帝對人的考驗,是神性對人性的檢驗。比如西緒福斯神話、受難的約伯、受難的圣子耶穌、瞎子的無字藥方等等。盡管人性的根基是欲望,但欲望既有可能使人成為魔鬼的代言人,也有可能使人成為上帝(神)的代言人。所以,史鐵生一再強調:“人與神有著永恒的距離,因而向神之路是一條朝向盡善盡美的恒途。”[4](P156)“神即是現世的監督,即神性對人性的監督,神又是來世的,是神性對人性的召喚。……神性的取消,恰是宣布惡行的解放,所以任何惡都從中找到了輕松的心理根據。”[4](P49)
維護人與神之間的永恒距離,使神性既是人性的監督,也是人性的牽引。史鐵生的寫作既否定人欲望叢生的魔性,也否定造人為神的人的權力欲望的無限膨脹。史鐵生認為:“人的價值是神定的標準,即人一落生就已被認定的價值。想來,神的標準也有上下線之分,即‘下要保底’——平等的人權,‘上不封頂’——理想或信仰的無限追求。所以,人除了是社會的人,并不只剩下生理的人,人還是享有人權的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人。”[16]這就否定了君權神授的狂妄和造人為神的虛偽,也拒絕了人對以社會價值作為衡量標準的所謂成功人士、社會精英的無原則的贊頌。站在神性的高度審視人性,使史鐵生對人類獸性、魔性的洞察,異常敏銳,對由于人性的殘缺所帶來的人的命運的局限,也看得更為清晰。同時,他也對由于神性的牽引所產生人類奇跡,更是驚羨不已。如《命若琴弦》《毒藥》《死國幻記》等。
注釋:
[1](俄)康定斯基.論藝術的精神[M].查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2]史鐵生.隨想十三[A].史鐵生散文選[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史鐵生.記憶迷宮[A].史鐵生作品集(第3卷)[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4]史鐵生.信與問[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8.
[5]史鐵生.地壇與往事[J].十月,2008,(2).
[6]史鐵生.我的丁一之旅[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7]史鐵生.給王朔的信[J].收獲,2012,(1).
[8]史鐵生.私人大事排行榜[A].史鐵生散文選[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9]史鐵生.病隙碎筆2[J].天涯,2000,(3).
[10]史鐵生,等.史鐵生:扶輪問路的哲人[J].黃河文學,2010,(6).
[11]史鐵生.病隙碎筆1[J].花城,1999,(4).
[12](法)雨果.《克倫威爾》序[A].雨果論文學[M].柳鳴九,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
[13]史鐵生.我與地壇[J].上海文學,1991,(1).
[14]吳俊.當代西緒福斯神話:史鐵生小說的心理透視[J].文學評論,1989,(1).
[15]史鐵生.寫給本刊編輯部的信[J].文學評論,1989,(1).
[16]史鐵生.日記六篇[J].江南,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