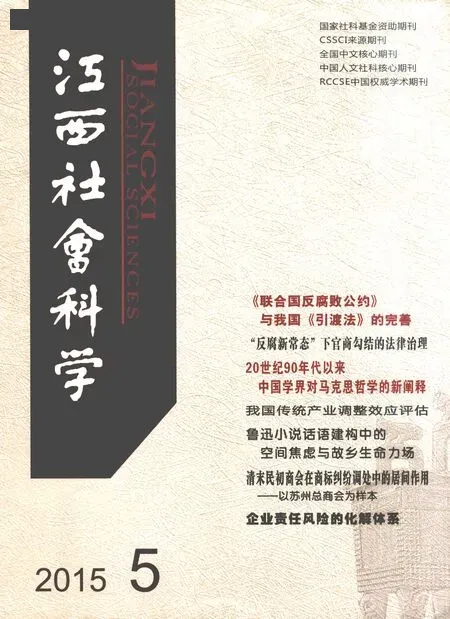政治經濟學研究與人本主義邏輯的解構——重新認識《評李斯特》的歷史地位
■馬 曦
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形成的過程中,有一個文本即《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以下簡稱《評李斯特》)起到了重要的過渡作用。然而,在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這一文本卻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注。今年正值《評李斯特》寫作170周年,重讀這一文本,充分挖掘并科學評估這一著作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可以為當下進一步推進對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啟示。
一
1843年《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實現了哲學立場的第一次轉變,即由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轉向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而在1844年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實現了政治立場的轉變,由原來的革命民主主義轉向了哲學共產主義。因此,馬克思此時要做的是為無產階級革命尋找內在依據,這一政治立場決定了馬克思第一次經濟學研究的目的不是對經濟學本身進行理論分析,而是為其政治目的服務。這就決定了,此時馬克思必然會站在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上以人本主義的哲學話語來全面批判和否定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這種批判,從實質上來看,就是用費爾巴哈的自然唯物主義來否定古典經濟學的社會唯物主義,用前者的人本主義邏輯來否定后者的客觀現實邏輯。[1](P169-170)這一點在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得到了明確體現。
在《手稿》中,馬克思直接以否定私有制為預定前提,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在他看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雖然探討了私有制的各種規律,但對私有制本身的合理性問題卻只字未提,而它們的一切論斷都是以私有制為前提的,并把它看作是符合人類本性的永恒規律。這種觀點必然會遭到馬克思的嚴厲批判和否定,但由于受此時經濟學水平的限制,決定了他不可能從經濟學本身的內在邏輯來揭示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矛盾,而只能跳到政治經濟學之外,援引人性的立場,借助于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邏輯來揭露和批判私有制的反人道本質。這種批判的確體現了他的睿智性,但同時也迷惑了他的雙眼,使他無法甄別出古典經濟學所蘊含的科學成果,而是把它與資產階級的狹隘性一同拋棄了[2](P330-331)。由此可見,古典經濟學所蘊含的社會認識論并沒有真正影響到當時的馬克思。雖然《手稿》中也存在一個客觀現實邏輯,但這一邏輯始終作為一種否定性因素屈從于人本主義邏輯的光環之下,無法從總體上改變人本主義邏輯的權力話語的霸權地位。
到了《神圣家族》時,馬克思也試圖在批判鮑威爾等人的自我意識哲學時,闡明一種和唯心主義不同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但由于他仍未真正領悟古典經濟學的社會唯物主義思想,歷史運動的最終動力還沒有歸結于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而依舊是用人類不變本性(應該)和違反這種本性的外部現實 (是)之間的沖突來說明。在這種情況下,對共產主義的論證,歸根結底還是像《手稿》中一樣訴諸抽象的人性原則。這種認知絕不可能是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總結,而只能是一種脫離歷史現實的、帶有一種倫理批判的邏輯推論,根本不具有現實性;更重要的是,此時馬克思根本無法依據這一理論,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現實可行的道路。
為了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馬克思又重新回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來,寫下了《布魯塞爾筆記I》《評李斯特》《布魯塞爾筆記II》①。就像他后來描述的那樣:“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后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里繼續進行研究。”[3](P412)因此,通過對《評李斯特》的深入研究,能夠為我們準確把握馬克思思想邏輯的轉變提供重要啟示。
具體而言,這種轉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對古典經濟學認知態度的轉變。作為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斯密開啟了一種新的社會哲學,即不再像洛克、霍布斯等人那樣用政治來注解社會,而是相反,將社會的根基推進到經濟的層面,用經濟自身的演進來完成對社會的理解,并堅信市民社會的自然演進必然會解決社會中所存在的問題,為事物帶來秩序。
這是一個極其了不起的貢獻。如果說在前期馬克思對這種社會唯物主義的思想還是有意拒斥的話,那么現在馬克思對這一認知邏輯已經有所領悟,并有意識地承襲了這一思路,為后來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提供了理論資源。其次,前期那條屈從于人本主義邏輯之下的客觀現實邏輯已經明確地凸顯了出來,成為馬克思邏輯布展的主導尺度。在《評李斯特》中,雖然原來的雙重邏輯仍然交織在一起,但它們的歷史地位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客觀現實邏輯已經逐步成為馬克思話語布展的理論中軸,而前期的居于主導地位的人本主義邏輯已經開始被解構了,這預示著一個新的格式塔式的轉變。它清晰地記錄了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真實軌跡和動態發展過程,有效填補了從《神圣家族》到《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邏輯缺環,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政治經濟學研究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說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作為批判對象存在的,那么,在《評李斯特》中,這種語境已經發生了重要轉變,成為馬克思批判李斯特的重要理論支撐。
在馬克思看來,作為德國資產階級利益忠實代表的李斯特,是以漫畫式的小丑形象登上歷史舞臺的,他所謂的國民經濟學,實質上不過是 “在工業的統治造成的對大多數人的奴役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的”情況下,企圖在德國建立資產階級社會,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時代的反動,所以,他不得不“追求財富而又否定財富”,創造一種 “與世俗的法國和英國的經濟學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經濟學,以便向自己和世界證明他也想發財是有道理的”,企圖用理想的唯心主義的詞句來掩蓋資產階級的真實意圖,來為德國資產階級驗明正身,因此,他“必然要反對那種無恥地泄露了財富的秘密并使一切關于財富的性質、傾向和運動的幻影成為泡影的法國和英國的經濟學”[4](P241)。結果,“自斯密以來的經濟學的全部發展”在李斯特那里喪失了所有的意義[4](P241)。針對李斯特的這種刁難,馬克思指出了這種言論的荒謬實質,認為李斯特對英法經濟學的這種“否定”,從本質上來講,就是對現實性的一種否定,即他不愿意承認英法經濟學所描述的市民社會已經走向沒落的客觀事實,而是相反,用一種唯心主義的理想化的詞句來予以裝點、粉飾這個已經“陳舊腐朽的”市民社會,并把它當作未來美好的社會目標予以歡欣雀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逆流。所以,在馬克思看來,這兩種經濟學的對峙表面上是兩種不同的經濟主張的對峙,但實際上體現的是兩種不同哲學觀的對峙,是觀念與現實、唯心主義的主觀邏輯與社會唯物主義的客觀邏輯之間的對峙。
在李斯特那里,不是現實高于觀念,而是相反,是觀念統領現實。他把市民社會自然演進的客觀邏輯消融于主觀愿望的旋渦之中,結果,“整個國民經濟學不外是在研究室中編造出來的體系”,而不是“同社會現實的運動聯系在一起的”[4](P242)。對此,馬克思非常氣憤,對李斯特展開了激烈批判,肯定了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價值,實現了對古典經濟學認知態度的轉變。他指出:“如果說亞當·斯密是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那么他的實際出發點,他的實際學派就是‘市民社會’,而對這個社會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可以在經濟學中準確地加 以探討 。”[4](P249)以此來看,此時馬克思已經不再把古典經濟學作為批判和否定的對象,而是開始有意識地肯定它的認知思路,并借助于這一邏輯來解構李斯特的主觀邏輯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邏輯了。在這里,馬克思已經認識到“市民社會”在古典經濟學中的積極意義。此時他在批判和否定古典經濟學政治立場的同時,積極肯定了它的合理內核,并將后者視為一門科學,以此來建構自己的社會理論。后來在《布魯塞爾筆記II》中,馬克思通過對布阿吉爾貝爾著作的摘錄②,進一步肯定了古典經濟學的邏輯:經濟的邏輯是可以自我揚棄的,“事態即市民社會的自然進程應該給事物帶來秩序”[5](P48)。以此來看,此時馬克思正是沿著斯密所開創的道路前進的③。這是馬克思第二次經濟學研究的理論成果,也是人本主義邏輯解構的重要原因之一。
馬克思說:“對這個社會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可以在經濟學中準確地加以探討。”[4](P249)這句話無疑道出了一個更具體的研究思路:從李斯特的觀念邏輯回落到古典經濟學的市民社會固然重要,但對市民社會這個歷史現實本身的分析才是更為關鍵的,這正是后來歷史唯物主義的真實基點。一旦馬克思開始著手分析市民社會的演進歷史時,一種全新的哲學革命就將到來了,屆時,縈繞在他頭腦中的人本主義邏輯必然會全面退去,開啟一種全新的哲學范式。而這恰恰是在后面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完成的。在后一文本中,馬克思指出:“真正的市民社會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6](P211)也是由此出發,馬克思建立了自己的歷史觀。然而,此時他顯然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他還不具備對市民社會本身進行歷史性分析的能力,而只是認識到這一點而已。就此而言,《評李斯特》在總體上只具有過渡性意義。
三
隨著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知態度的轉變,他的理論布展邏輯也開始發生轉變。一開始時,馬克思似乎還是像前期那樣,用一種人本主義的邏輯來批判資產階級社會。他指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由勞動”,實際上是一種“間接地自我出賣的奴隸制”,“工人是資本的奴隸,是一種商品,一種交換價值”,“他的活動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現,而毋寧說是把他的力量售賣給資本,把他片面發展的能力讓渡 (售賣)給資本,一句話,他的活動就是‘勞動’”,資產者不是把無產者看作人,而是將無產者變成了物,勞動力僅僅是一種物的生產力,所以,馬克思認為,整個資產階級制度其實就是一種卑鄙的“人為物而犧牲的反人制度”[4](P261)。因此,當他看到李斯特還在空談那種用愛國主義精神連接成那種脫離現實的理想化勞動時,必然會非常憤怒。他指出,那種“談論自由的、人的、社會的勞動,談論沒有私有財產的勞動,是一種最大的誤解”[4](P254)。 這一觀點不僅是對李斯特的批判,同時也包含著馬克思的自我批判,他在《手稿》中就是以“自由自覺的勞動”為參照系來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的異化勞動的。這也表明,此時馬克思已經洞悉,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所謂的自由勞動,“‘勞動’,按其本質來說,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會的、被私有財產決定并且創造私有財產的活動”[2](P254-255)。 此時馬克思同樣要廢除這種非人的勞動,也同樣要廢除私有財產,但他已經不再運用《手稿》的人本主義邏輯了,而是試圖把它建立在現實的邏輯之上。馬克思說,要廢除非人的奴役狀況就要廢除私有財產,而要廢除私有財產只有被理解為廢除 “勞動”,并且“這種廢除只有通過勞動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說,只有通過社會的物質活動才有可能,而決不能把它理解為用一種范疇代替另一種范疇”[4](P255)。
在這里,馬克思的價值指向是非常明確的,就是為無產階級革命尋求現實的可行性。在他看來,那種用“一種范疇代替另一種范疇的”思想革命在現實中是根本沒有出路的,它不會對現實的生產關系造成任何觸動,現實的狀況只有通過現實的物質力量來摧毀。此時馬克思的思路已經由原來的“應該”回落到現實的“是”了,人本主義的邏輯就此被解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轉換。
那么,這個現實的物質力量是什么呢?在馬克思看來,就是工業實踐[7]。因此,接下來,他緊緊地圍繞著工業實踐展開了理論分析。他指出,只要人類能夠把工業從現實的資產階級環境中解放出來,就能夠為廢除這種奴役勞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一旦這種轉變完成,也就意味著,“消除人類不得不作為奴隸來發展自己能力的那種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的時刻已經到了。因為一旦人們不再把工業看作買賣利益而是看作人的發展,就會把人而不是把買賣利益當作原則,并向工業中只有同工業本身相矛盾才能發展的東西提供與應該發展的東西相適應的基礎”[4](P258)。這樣,我們就能把“工業喚起的力量同工業本身即同工業給這種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條件”區別開來,用工業自身的力量來打破那些束縛工業發展的社會羈絆——資產階級社會的狹隘限制。
此時馬克思已經明確地將工業與工業的存在形式區分了開來,要求用工業的自身力量來打破工業的資產階級形式。他指出:“打破工業的羈絆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擺脫工業力量現在借以活動的那種條件、那種金錢的鎖鏈,并考察這種力量本身。這是向人發出的第一個號召:把他們的工業從買賣利益中解放出來,把目前的工業理解為一個過渡時期。”[4](P259)這是馬克思向資產階級社會所作的一種歷史宣判。
雖然此時他還在借用“人”的口號,但這里的“人”顯然已經不再是《手稿》中那種從未存在過的理想化的“人”了,而是一種從事歷史活動的真實主體;同時,對異化勞動的批判也不再是依靠前期的人本主義邏輯,而是轉換為工業發展所引起的客觀矛盾運動。此時馬克思的布展邏輯已經出現了重大轉變,即從前期那種對社會主導因素的探討轉向了對社會歷史存在基礎的探討,從大寫的人學辯證法轉向了客觀的歷史辯證法[8](P96),實現了從人本主義邏輯向現實客觀邏輯的轉變。
于是,無產階級革命不再只是一種理論訴求了,而且也是現實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共產主義終于在現實中找到了這個阿基米德點。馬克思說:“工業用符咒招引出來(喚起)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對工業的關系,同無產階級對工業的關系完全一樣。今天,這些力量仍然是資產者的奴隸,資產者無非把它們看作是實現他的自私的(骯臟的)利潤欲的工具(承擔者);明天,它們將不斷砸碎自身的鎖鏈,表明自己是會把資產者連同只有骯臟外殼 (資產者把這個外殼看成是工業的本質)的工業一起炸毀的人類發展的承擔者,這時人類的核心也就贏得了足夠的力量來炸毀這個外殼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現出來。”[4](P258-259)這已經是在社會歷史發展的真實進程中來確認走向共產主義的現實道路了,客觀現實邏輯已經不再像前期那樣僅僅作為一種否定性因素屈從于人本主義邏輯之下,而是從總體上推翻了后者的主導地位,成為此時馬克思邏輯運演的新軸心,這是他邁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關鍵一步。
但是,如果僅僅以此為依據就將其指認為新世界觀的誕生地,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為什么呢?相對于《手稿》而言,此時的轉變無疑是一個重要進步,但我們決不能過分放大這一著作的歷史地位,我們必須看到,此時馬克思還存在著一些無法克服的難題。他指出:“德國資產者是事后登上歷史舞臺的,他不可能把英國人和法國人詳盡闡發的國民經濟學再向前推進,正象后者大概也不可能對德國哲學運動作出什么新的貢獻一樣。”[4](P249)這表明其時馬克思還沒有真正領悟古典經濟學的哲學意義和黑格爾哲學的經濟學意義,市民社會的自然進程和黑格爾哲學的那種歷史感還沒有真正地結合在一起。這種歷史感的缺失,使他對矛盾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幾何平面上,還無法深入到現實歷史運動的內在矛盾之中,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而只是停留在用一種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力來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的抽象層面。因此,此時馬克思所得出的結論絕不是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客觀總結,更不是科學主義的世界觀。這一點決定了《評李斯特》不可能是馬克思成熟時期的理論著作。但我們決不能因此來貶低這一文本的歷史地位,它至少為馬克思后面的哲學革命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這正是《評李斯特》一文所具有的理論意義。在此后不久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從物質生產出發,科學詮釋了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運動,準確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建立了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從而實現了哲學史上一次重要革命。這也再次證明,《評李斯特》無疑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過渡性文本。
注釋:
①馬克思的《布魯塞爾筆記》一共有兩個:1845年2月馬克思先寫下了一批摘錄筆記,共3冊,稱為《布魯塞爾筆記I》,接下來馬克思開始寫作《評李斯特》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在5-7月,馬克思又寫下了一批摘錄筆記,共4冊,稱為《布魯塞爾筆記II》。
②馬克思對布阿吉爾貝爾著作的摘錄,原來被指認為《巴黎筆記》的內容(見《馬恩列斯資料研究匯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版,46—52頁)。后經過認真鑒定,確定這一摘錄屬于《布魯塞爾筆記》II的內容,因此,從寫作時間上來看,馬克思的上述結論應該是在《評李斯特》之后,這也恰好印證這一文本的過渡性。
[1]張一兵.回到馬克思[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2]孫伯 鍩癸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馬恩列斯研究資料匯編(1980)[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孫樂強.西方實踐哲學傳統與馬克思實踐觀的革命[J].江西社會科學,2014,(8).
[8]張一兵.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