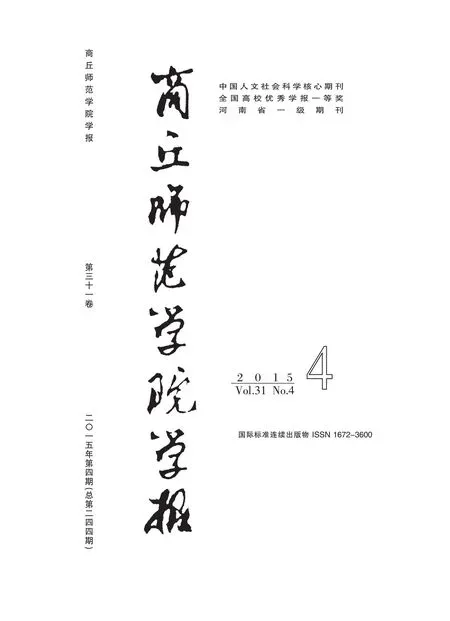從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到朱熹的“天理論”
趙 廣 志
(四川師范大學 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8)
從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到朱熹的“天理論”
趙 廣 志
(四川師范大學 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8)
董仲舒是漢代經學大師,“天人感應說”是其思想體系的根本基石。朱熹是宋明理學理論體系的主要奠基者,是繼董仲舒之后最重要的經學家。“天理論”是朱熹以儒家倫理為本位吸收佛、道兩家的本體論及思辨性而建構起來的。從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到朱熹的“天理論”似有貫通之處。
董仲舒;天人感應;朱熹;天理論
馮友蘭在其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中,將儒家思想的歷史分為董仲舒之前的子學時代及之后的經學時代。在這個意義上,董仲舒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一個經學家,而朱熹則是繼董仲舒之后最重要的一個經學家。如果說孔子是承繼三代優秀文化結晶的“六藝”之學而創立了儒家學派,董仲舒則是根據漢朝的時代需求,對儒家思想作了第一次大修正,建構起了漢代新儒學。而朱熹則根據宋朝的時代需求重新詮釋儒家經典,完成了中國哲學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次儒學創新。朱熹與董仲舒處于不同時代,然而他們在探求“儒家倫理”的本源時所提倡的“天理論”與“天人感應說”卻有相似和貫通之處。
一、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
為了實現政治上的大一統,既要樹立皇帝的權威,又要限制皇帝的私欲,董仲舒采用了天人感應的理論形式來實現這兩方面的功能。皇帝的權威已經樹立,能夠授命于皇帝的天是指什么? “天人感應”又是怎樣限制皇帝的私欲呢?
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要處理好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關系。與生產力及科技水平相關,在古代,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主,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內部的人際關系逐漸占據重要地位。黃開國認為,天人感應的“天”,正體現了“哲學從重點探究人與自然的關系,向重點探索社會內部人際關系的轉變”[1]。“天人感應”中的天,殷周傳統天命論雖然經過春秋末期“兩個二分化”[2]6、荀子的批判乃至秦始皇不信天,但在社會上仍然有很大的影響[3]。在董仲舒的哲學中,“天”是最高的哲學范疇,而不是“元”[4]。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較之于之前的論證更加嚴密、更為成熟。在廣泛吸收、借鑒西周以來天人感應相關論述的基礎上,以儒家的政治倫理學為基點,吸收了當時比較流行的陰陽五行說等觀念,主要是以類合、以數偶為基本方法論[5],把儒家思想中的倫理、治國原則抬高到天的位置,使自然之天重新具有了神靈之天、宗教之天的意味,并賦予了天以儒家倫理的色彩,最終使皇權限制在儒家之天的權威之下。
大一統的關鍵點在尊王。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需要約束,所以董仲舒搬出了被儒家倫理化的天。天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皇帝只是上天在人間的代理人,皇帝所做的事情,只是、也只能是按照天的意思去做。而天到底是什么,卻“任憑”儒家去解釋。對儒家“天”的解釋,則出自于儒家的經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儒術”被“獨尊”,儒家之天成為天下人的“天”,儒家的經典也成為天下人的經典。大一統的確立客觀上要求“獨尊儒術”,“儒術獨尊”則“儒經獨尊”,乃勢之必然。
二、朱熹的“天理論”
“天理論是朱熹哲學最重要的理論,體現了理學乃至宋學的本質特征,也是其經典詮釋的形而上的根據。”[6]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的提出,以春秋公羊學為基點,充分融合了儒家倫理及當時流行的陰陽五行等學說。與董仲舒相似,朱熹“天理論”的提出及哲學體系的建構,也是通過對儒家經典作了反映時代發展新要求的新詮釋而提出來的,“最終完成了自宋初以來,思想家們致力建立一種直接把哲學本體論、思辨性的哲學形式與儒家政治倫理統一起來的哲學體系的嘗試”[6]。雖然中國古代存有哲學思想,但是仍然需要對這一時期的“哲學思辨性”進行界定:朱熹時代的“哲學思辨性”是指援佛家的心、性本體論及道家的道本體論入儒,進而建構起系統的、完整的以“天理論”為核心的理本論思想體系[7]。
唐朝經學在“注不違經”、“疏不破注”的信條下發展,至孔穎達奉命修《五經正義》,一方面使經學“參考書”出現統一的權威定本,另一方面也使儒學的發展停滯。唐朝時期,佛道大盛,儒學在佛道宗教的挑戰面前,理論上難以回擊,從而使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有所動搖。儒家思想在理論上強調倫理政治、修身入世,但卻沒有哲學上的本體論,道、玄有道本體論,佛家有心、性本體論,儒家在其理論根基上是相對粗糙的“天人感應說”,無法回擊玄、佛、道的挑戰。在經學時代,儒家經學是“天上之法”、是“天子”之父,故儒家理論的解決必須堅持以“儒家理論”為本位,歷代的經學家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終于至朱熹而建構成相對嚴密的儒家“理本論”哲學體系。“朱熹提出并論證了中國哲學的一系列范疇、命題和重要理論,使得哲學本體論與儒家倫理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其中天理論是論證的中心,朱熹在理論的完備性、精致性方面進一步發展了二程的天理論哲學,并以太極論發展了理本論哲學。”[6]朱熹通過闡發儒家經典《周易·系辭》的太極說,將太極等同于天理,將太極升格到本體論的哲學范疇,同時,“天理”也具有了“本體論”的高度。朱熹通過對《易》學的研究,對經作出了新的解讀,解決了儒家思想中無本體論的問題。
三、從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到朱熹的“天理論”
經學時代,新思想的提出、建構一般是通過注經的形式,朱熹和董仲舒也不例外。其原因在于:自從政治上的大一統被人民普遍接受之后,為大一統作論證的“天人感應”說自然被接受。皇權在人間是至高無上的,至高無上的皇權是被天授命的,授皇權的天是儒家經典所界定的——形成了三個至高無上的權威——至高無上的皇權,至高無上的天,至高無上的儒家經典。董仲舒以至高無上的天樹立至高無上的皇權,又用儒家經典界定、規范至高無上的天,故儒家經典的地位是“天上之法”。“天上之法”,一方面要適應時代潮流的發展以解決“天下之事”;另一方面,其建構的新理論體系在被封建統治者能接受的同時,能夠最大程度地實現儒家德政、治世等使天下有序的政治理念,這是經學在封建時代存在、延續和發展的普遍法則。
朱熹是宋代經學集大成者。宋學就是以講義理為主的宋代(后延續到元明,亦包括清代宋學)經學的流派,而與漢唐重章句訓詁、煩瑣釋經之學相區別。以偏重訓詁及偏重義理來界定漢宋之學,是對漢唐時期及宋明時期經學發展大趨勢的概括,而每個思想家身上又具有特殊性。比如,董仲舒是漢代經學的開創者之一,卻以《公羊春秋》為文本成為建構漢代新儒學的主要開創者之一。而朱熹,雖屬于以己意說經、偏重于義理闡發的宋學時代,但他本人兼重義理和訓詁,并對“宋學的流弊加以修正,由此影響到后世的考據學”[8]。朱熹在對其“天理論”等諸多問題的論證上都是以注經的形式進行的。因此,當我們從總體上去了解整個經學歷史的趨勢時,可以簡單以“漢宋之學”來概括,而具體到時代、思想家的思想時,則要根據時代、思想家個人的情況具體分析。畢竟無論是“漢學”還是“宋學”,只是對“訓詁”和“義理”有所偏重,這至少說明兩點:其一,治經學需要訓詁、義理兼顧,明白經典文本本身含義的訓詁學是基礎,闡發義理以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是目的和歸宿;其二,對“義理”或“訓詁”的“偏重程度”該當如何計量,以文本的數量、思想的主張還是其他?這個“偏重程度”是很難計量和評判的。故“名”之以“漢宋”是為論述之便利,得“漢宋”“名”下之“實”之時,需放棄漢宋之“名”。
董仲舒作為漢代新儒學、經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其思想以儒家經典《公羊春秋》為本位,“根據大一統政治的需要,精心營建了一個嚴整的以陰陽五行為理論骨架、以天人感應為核心、以儒家思想為主體而統和諸家的理論體系”[9],切實地解決了漢代的實際問題,使“儒學”由“諸子之學”成為“天下之經”。朱熹以對《周易·系辭傳》的新注解而闡發太極哲學,使太極等同于天理。通過將太極升格成本體論范疇的途徑而使“天理”成為理本論的核心。朱熹以理本論為注經的形而上根據,傾四十年精力而成《四書章句集注》,不僅解決了來自佛道“本體論”思潮的挑戰,而且使“四書”學代替“五經”學的地位而成為南宋以后朝廷科舉考試的參考書。
宏觀論之,朱熹的“天理論”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都解決了屬于他們那個時代的難題,他們解決的途徑都是通過對儒家經典本身并結合時代發展的新闡釋而建構起新儒學。董仲舒開創了經學的“五經”時代,朱熹開創了經學的“四書”時代。時下,人們更是將“四書五經”作為儒家思想甚至國學的代稱,董仲舒、朱熹的影響可見一斑。
微觀論之,董仲舒吸取當時先進的 “陰陽五行”說而創立的“天人感應說”等理論,使儒家倫理具有了與天等同的位置,符合那個時代發展的需求。隨著佛教進入中國及逐步儒學化,魏晉時的以玄釋儒、隋唐時期的佛道大盛,致使玄學、道家道本論的思想、佛教心性本論等本體論思想深入人心。特別是自唐初《五經正義》頒布之后,儒家經學發展僵化,對佛道在本體論等方面的挑戰不能作出及時的回應或無法給予有力的回擊,儒學日益衰微,因此,自韓愈、李翱起,儒者已開始作相關的理論建構的探索,直到朱熹“天理論”哲學體系的建構才得以最終解決。朱熹“以儒學為母體,吸納佛教的思辨結構,利用道教的宇宙生成圖式”[9],建構起以天理論為核心的“理本論”思想體系。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為實現政治大一統、尊王的需要,樹立了儒家經典“天上之法”的權威地位,使“自然之天”具有了“授命之天”的意義。朱熹的“天理論”,將董仲舒的“天”置換成“天理”,使其具有與“太極”本體相等同的位置,將至高權威性的“天”結合時代的需求而演化成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天理”,將儒家倫理與天理等同。可見,二者確有貫通之處。
[1] 黃開國.天人感應論本質上是社會倫理政治哲學[J].社會科學研究,1988(1).
[2] 黃開國,唐赤蓉.諸子百家興起的前奏——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M].成都:巴蜀書社,2004.
[3] 周桂鈿.我為什么研究董仲舒[J].中國文化,2010(10).
[4] 黃開國.董仲舒“貴元重始說”新解[J].哲學研究,2014(4).
[5] 李宗桂.論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義[J].天津社會科學,1990(5).
[6] 蔡方鹿.朱熹理學與經學[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
[7] 蔡方鹿.經學理論化的意義[J].河北學刊,2009(1).
[8] 蔡方鹿.朱熹經學與宋學[J].社會科學研究,2003(5).
[9] 李宗桂.思想家與文化傳統[J].哲學研究,1993(8).
【責任編輯:李安勝】
2014-10-11
趙廣志(1985—),男,河南濮陽人,碩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研究。
B234.5;B244
A
1672-3600(2015)04-005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