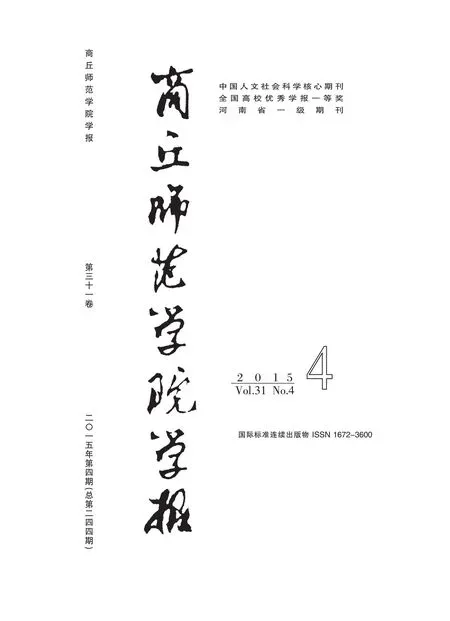從解構文論到政治批評
——《哈姆萊特》還是《塔爾瑪》
辛 雅 敏
(鄭州大學 文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從解構文論到政治批評
——《哈姆萊特》還是《塔爾瑪》
辛 雅 敏
(鄭州大學 文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在莎士比亞評論領域,解構主義并沒有形成聲勢浩大的批評陣營,但卻為其他莎評流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方法。20世紀80年代以后,莎士比亞評論越來越明顯地帶有“左傾”政治色彩,解構主義莎評也順勢從單純的文本批評向政治批評過渡。著名莎評家泰倫斯·霍克斯對《哈姆萊特》的解讀就是這種過渡的典型案例。霍克斯先對《哈姆萊特》進行了細致的文本解構,但隨即轉向對歷史上一位著名莎評家的政治立場的解讀,這看似不連貫的邏輯背后正體現了解構主義莎評的政治化傾向。
哈姆萊特;解構主義;政治批評;霍克斯;莎士比亞
20世紀60年代,由于受美國的新批評和英國的實用批評這些本土形式主義批評的強大影響,在法國異軍突起的結構主義批評作為另一種享有國際聲譽的形式主義文學理論幾乎沒有能夠在莎士比亞批評領域掀起任何波瀾。不過到了70年代,同樣來自法國的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在保爾·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羅德·布魯姆和杰弗里·哈特曼等幾位耶魯教授的倡導下開始進入英美文學批評,而且這種影響也開始逐漸撼動新批評等傳統形式主義批評在莎士比亞批評中的地位。眾所周知,消解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主要任務。在耶魯學派那里,解構主義文論還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文本理論。但是,解構主義文論的開放性和破壞性卻使它很快被新歷史主義和女性主義等其他新興批評陣營所借鑒,變成了傳統批評的真正破壞者和顛覆者。
因此,解構主義文論對莎士比亞評論發展的貢獻主要是理論和方法。“解構主義莎評”作為一個批評陣營持續的時間很短暫,它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但進入90年代以后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以至于到了2004年,當一位莎評史家在選編當代莎評文選時,甚至沒有將解構主義莎評列入其中,并聲稱“雖然有一些詞匯和原則勢不可擋地進入了其他形式的批評閱讀,但真正的解構主義對莎學的影響很小,也很少有莎學家自稱為解構主義者”[1]12-13。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莎士比亞評論集體向左轉的大潮中,解構主義莎評很快便融入其中,但迅速出現又迅速自我消解。英國著名莎學家泰倫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教授對《哈姆萊特》的評論就體現了解構主義從文本理論向政治批評的過渡,因而具有標志性的意義。
一
在一篇名為《塔爾瑪》(Telmah)的文章中①,霍克斯教授從解構主義視角出發,將“哈姆萊特”(Hamlet)的名字倒寫成“塔爾瑪”(Telmah),以此來暗示《哈姆萊特》中不斷被破壞和倒置的線性結構。但與此同時,他也把政治因素納入考察范圍,將文學批評與政治聯系在一起,強調用解構主義批評方法對《哈姆萊特》進行顛覆性解讀對社會秩序所帶來的破壞性,從而體現了20世紀80年代西方莎士比亞評論集體“向左轉”的傾向。
在這篇文章中,霍克斯首先指出在《哈姆萊特》里開頭和結尾有大量的對應關系,首尾相連形成循環,而不是線性發展。比如此劇以沉默的士兵開始,又以沉默的士兵結尾;開始時國王的死亡和戰爭的威脅籠罩著丹麥,結尾時另一位國王死去,新來的挪威君主再次使丹麥戰云密布。甚至具體文本也有對應,比如開始時勃那多對霍拉旭說:“怎么,霍拉旭!你在發抖!臉色這樣慘白②!”(第一幕第一場)結尾時哈姆萊特則說道:“此時你們這些發抖且臉色慘白的人們……”(第五幕第二場)因此,對《哈姆萊特》這個故事而言,在某種意義上首就是尾,尾就是首,傳統的線性敘事結構被完全破壞。
其次,霍克斯認為此劇在主題上也與線性結構相悖。比如戲還沒演到一半,就有五位父親死去,即老王福丁布拉斯、老王哈姆萊特、波洛涅斯、普里阿摩斯以及《捕鼠機》戲中的貢扎古公爵,其中前三位的兒子都進行了復仇行動。相同的地方還在于,老福丁布拉斯死后,他的弟弟繼任挪威王位,并試圖使小福丁布拉斯重新融入社會;而老哈姆萊特死后,克勞狄斯對哈姆萊特做了相同的工作;而且,在波洛涅斯死后,克勞狄斯還像叔父一樣對待雷歐提斯。因此,“叔父”功能是本劇主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它不僅與替父報仇的主題形成對比,也是全劇和諧結構的破壞者。總之,在倒置的《哈姆萊特》——《塔爾瑪》中,哈姆萊特的叔父克勞狄斯才是全劇的中心人物。
另一個打破線性結構的特征體現在文本中的大量回述上,劇中人物在情節向前推進時,走一步停一步,不斷地“向后看”,不斷重述、追憶以前發生的事。比如開場人物不斷提到的“兩次”看到同一可怕景象,直至霍拉旭重述以前福丁布拉斯的故事;然后進入第一幕第二場,克勞狄斯再次重述以前的事;再后來,鬼魂又給哈姆萊特回述了謀殺發生的情境。于是,此劇給人的印象就是,劇中的不同人物不斷地重述歷史。而且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視角“修正”過去發生的事。
霍克斯進而指出,劇中有這么一段對白最能體現這種不斷重述所表現出的似是而非的解構色彩:
哈姆萊特:你看見那片像駱駝一樣的云嗎?
波洛涅斯:哎喲,它真的像一頭駱駝。
哈姆萊特:我想它還是像一頭鼬鼠。
波洛涅斯:它拱起了背,正像是一頭鼬鼠。
哈姆萊特:還是像一條鯨魚吧?
波洛涅斯:很像一條鯨魚。(第三幕第二場)
不過,霍克斯認為,所有這些對線性結構起到破壞作用的重述和倒置中,戲中戲《捕鼠機》才是高潮。這場戲不僅是“戲中戲”,而且是“回放中的回放”(replay of a replay),因為它用行動回放了鬼魂對自己被謀殺過程的回述。戲中戲是全劇的轉折點,正如哈姆萊特向克勞狄斯解釋戲中戲的時候說的:“這是一個比喻的名字”(第三幕第二場),這里比喻用的是“tropically”一詞,其原型詞“tropic”既有比喻的意思,又有環形回歸線的意思。所以霍克斯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過去被融入未來,全劇由此正式進入倒置的《塔爾瑪》。
看完這樣的分析,我們不禁要問,尋找“塔爾瑪”的意義何在?霍克斯指出,對于我們所熟知的經典文本《哈姆萊特》來說,“塔爾瑪”一詞暗示了一種永恒的挑戰和矛盾。“在這種意義上,‘塔爾瑪’與‘哈姆萊特’以一種我們認為不可能的存在方式共同存在并且相互毗鄰。我們被教導說,一個事物不可能既是這個又是那個。但是,這正是‘塔爾瑪’所挑戰的原則。”[2]58霍克斯認為,歐洲中心論所傳承下來的“意義”(sense)、“秩序”(order)、“在場”(presence)乃至“視角”(point of view)等觀念能夠使一個闡釋者從不同角度闡釋《哈姆萊特》,甚至把它解讀為倒置的塔爾瑪,但卻不會承認兩者為同一體。也就是說,這個作品不可能既是《塔爾瑪》,又是《哈姆萊特》,因為這會違背我們根深蒂固的同一性視角及其背后的“權威”和“作者”觀念,但霍克斯的解讀正是要用解構主義原則顛覆這一傳統觀念。換句話說,《哈姆萊特》就是《塔爾瑪》。
二
不難看出,霍克斯借“塔爾瑪”來顛覆的事物的同一性的背后仍然是解構主義所批判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而且他的這種解構主義論調和耶魯學派的希利斯·米勒等人對莎士比亞的解讀簡直如出一轍。然而,霍克斯強調的是解構主義解讀給文本帶來的多重含義和破壞性。因此他并沒有停留在單純的文本分析,而是將這種分析與莎評史上的一場爭論聯系在一起,進而又與當事人的意識形態背景和政治立場相關聯。
1917年,著名莎學家、新校勘學派的代表人物格雷格(W.W.Greg,1875 - 1959)寫了一篇名為《哈姆萊特的幻覺》(Hamlet’s Hallucination)的文章。在此文中格雷格同樣把研究的重點集中在戲中戲,并指出,哈姆萊特用戲中戲《捕鼠機》試探國王克勞狄斯,但這個戲中戲有一個啞劇前戲,謀殺國王的全過程在這個前戲中已經被演了一遍。然而,克勞狄斯在觀看這個前戲之后沒有任何反應,這就說明哈姆萊特的試探計劃有問題,進而說明鬼魂可能并未向哈姆萊特完全吐露實情。格雷格認為這個情節上的小插曲破壞了以哈姆萊特這個人物為中心的情節結構,其結果是提升了克勞狄斯的形象,因而也顛覆了我們對此劇的傳統認識乃至對莎士比亞本人的看法。格雷格這樣的解讀顛覆了哈姆萊特和鬼魂的形象,其實正是把《哈姆萊特》變成了霍克斯所說的《塔爾瑪》。對此,他本人的結論是:“要么不能繼續將莎士比亞看做是一位理智的作者,要么放棄對《哈姆萊特》這個故事的既有看法。”[3]102
對某些人來說,這個結論是無法接受的,它激起了另一位著名莎評家多佛·威爾遜(John Dover Wilson,1881-1969)的強烈不滿。當年威爾遜在從利茲到桑德蘭的火車上看到了格雷格的文章,他一口氣讀了六遍,并意識到自己必須予以反駁。這個動機成就了后來著名的《〈哈姆萊特〉中發生了什么?》(What Happens in Hamlet?1935)一書③。不過,威爾遜到底反駁了什么并不重要,在這里我們主要來看霍克斯對這一陳年舊事的分析。
霍克斯關注的是威爾遜的身份和政治立場。1917年11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了決定勝負的緊要關頭,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更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的動蕩。當時的威爾遜受雇于英國教育委員會,是一名教育巡視員,在戰時還常常兼任軍需部門的巡視員。在威爾遜眼中,《哈姆萊特》這樣的經典文學作品體現的是一種民族思想,是英語教育和英國生活方式的核心組成部分,甚至是聯系各階級和階層的紐帶。所以,對《哈姆萊特》任何形式的顛覆都是不能接受的。霍克斯同時還發現,威爾遜在早年的文章中同情俄國貴族制度,支持沙皇統治,因而他認為十月革命爆發后,威爾遜很可能感到了一種逐步迫近的危機,那就是英國也有可能步俄國的后塵。因此,這些因素結合起來,霍克斯認為,威爾遜在格雷格的文章中讀出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味道。
于是,一場看似簡單的文學批評爭論就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意義:
多佛·威爾遜1917年在通往桑德蘭的火車上對格雷格的回應是一個文學解讀與政治社會關懷相聯系的完美例證,在我們的文化中,這種聯系一直存在但卻常常不為人知。要使它公之于眾就要發掘格雷格閱讀中的真正的顛覆性。因為他在一個被英語文化認為具有核心意義的不朽文本中發現了一種令人不安的一致性與穩定性的缺失。[2]57
三
那么,霍克斯自己對《哈姆萊特》情節結構的分析和他對威爾遜的評析又是什么關系?我們不難看出,這其中的內在聯系便是一種破壞性和顛覆性。以往的批評家對《哈姆萊特》有一種所謂的正統觀念,這種觀念認為,《哈姆萊特》有一個井然有序的線性結構,所有有悖于這種觀念的解讀都會被視為具有顛覆性。格雷格的解讀就具有這種顛覆性,因而激起了威爾遜這個保守派的不滿;同樣,霍克斯自己的解讀強調的就是這種顛覆性。在為《劍橋莎士比亞研究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Studies)寫的介紹性文章中,霍克斯就曾評估過解構主義方法對莎劇文本以及傳統莎士比亞批評的破壞力:
對莎士比亞文本的解構主義解讀會試圖破壞布拉德雷派批評視為前提的人物性格和作者思想的假象,它還會拒絕和顛覆結構主義在文本中發現的對立和張力模式,并宣布這些都是從外部強加于文本的方法,會妨礙文本潛在的無限的意義生產。在試圖證明所有的寫作都在暗地里拒絕被簡化為單一“意義”,以及當擺在讀者面前時,這種意義不可能從單一文本中產生時,解構就會最終破壞現代校勘者們試圖制造統一的莎士比亞文本的努力,而且還會將所有的此類努力視為西方思想縱容專制劃界的標志。[4]292-293
這段文字把矛頭指向以往的性格分析和形式主義莎評,充分強調了解構主義對包括校勘研究在內的傳統莎學的破壞力。解構主義方法在這里完全成了傳統的破壞者。不過,在認識到解構主義閱讀給文本帶來的破壞性的基礎上,霍克斯進一步認識到了從意識形態和政治角度解讀文本的重要性。因此,他提議“將文本視為一個充滿潛在的矛盾和對立解讀的場所(site)或區域,沒有個人或群體有權在這個場所宣稱‘內在的’卓越性或‘固有的’權威,這個場所本質上帶有意識形態性質,并受制于外在的政治和經濟決定性因素”[3]117。于是,《哈姆萊特》與政治和意識形態被聯系在一起,而這種聯系才是霍克斯的本意所在。
我們分析霍克斯的這篇文章,就是因為它體現了解構主義批評與左翼批評的融合。20世紀后期,當馬克思主義在文學批評領域再次成為顯學,文化研究開始侵入文學研究,莎評界乃至整個文學理論界流行著一種觀點,就是認為解構主義的非政治傾向是一種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唯物主義等派別一擁而上,以左翼知識分子的姿態在20世紀80年代迅速占據了莎士比亞批評的大舞臺。在這些批評家眼中,解構主義更是一種可以加以利用的方法,而不是一個具體的批評陣營。新歷史主義莎評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就曾指出,當代理論對文學批評的沖擊就在于它顛覆了文學審美脫離社會文化語境和意識形態的自治傾向。這種顛覆不僅來自馬克思主義,也同樣來自解構主義。“因為解構主義在文學意義中不斷發現的不確定性動搖了文學與非文學之間的界限。這種生產文學作品的意圖不能保證一個自給自足的文本,因為能指會不斷地越界進而破壞意圖。”[5]164
耶魯學派的解構主義文論打破了文學與非文學之間的樊籬,于是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一樣進入了批評家的視野。但在格林布拉特那里,解構主義的破壞力還不夠大,他認為解構主義還需要再向前進一步:“解構主義的閱讀會輕易地和不可避免地滑入虛無。在實際文學實踐中,真正的困難不是純粹的、無拘無束的悖論(aporia),而是某種特定歷史遭遇中的局部策略。”[5]164在格林布拉特眼中,解構主義是一種有價值的方法,但他堅持認為,在用解構方法揭示文本的不確定性、挑戰學科界限的同時,特定的時空背景和意識形態傾向不能被拋棄④。這一認識在20世紀80年代逐漸成為莎士比亞評論領域的共識。于是,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霍克斯對《哈姆萊特》的解讀應運而生,他不僅充分強調了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批評方法的破壞力,也試圖將政治批評融入其中,雖然這樣的融合在邏輯上有些生硬,但畢竟為解構主義進入莎士比亞批評領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注 釋:
①此文最初出現在1983年四月的《偶遇》(Encounter)雜志上,名為《〈塔爾瑪〉與多佛·威爾遜》(Telmah & J.Dover Wilson)。1985年經過修改和擴充后被收入莎評文集《莎士比亞和理論問題》(Shakespeare and the Question of Theory)一書,1986又被收入霍克斯自己的文集《那個莎士比西亞小調》(That Shakespeherian Rag: Essays on a Critical Process)中。
②本文中所有莎士比亞引文均出自《莎士比亞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部分引文有改動,不再在參考文獻中另行注明。
③格雷格與威爾遜之間的爭論以《現代語言評論》(Modern Language Review)為媒介,持續了近20年:1917年10月,格雷格在《現代語言評論》上發表了《哈姆萊特的幻覺》一文;1918年4月,威爾遜在同樣的刊物上發表《〈哈姆萊特〉中的平行情節:回復格雷格博士》(The Parallel Plots in “Hamlet”: A Reply to Dr W.W.Greg),首次反駁格雷格;1919年10月,格雷格發表《鬼魂重入:回復威爾遜先生》(Re-Enter Ghost: A Reply to Mr.J.Dover Wilson),回應威爾遜的反駁;1935年,威爾遜舊事重提,出版了專著《〈哈姆萊特〉中發生了什么?》,并將此書題獻給格雷格;1936年4月,格雷格仍在《現代語言評論》上發表《〈哈姆萊特〉中發生了什么?一封公開信》(What Happens in “Hamlet”? An Open Letter),再次回應威爾遜。
④格林布拉特這幾段評論解構主義的文字作為《莎士比亞和驅魔人》一文中的一部分,只出現在《莎士比亞與理論問題》這本論文集中,在格林布拉特自己的專著《莎士比亞的協商》于1988年出版時,這段話被刪去。
[1]Russ McDonald ed.Shakespeare: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 1945-2000[C].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2]Terence Hawkes.Telmah & John Dover Wilson, in Encounter[J].April 1983.
[3]Terence Hawkes.That Shakespeherian Rag: Essays on a Critical Process[M].London: Routledge, 1986.
[4]Terence Hawkes.Twentieth Century Shakespeare Criticism: The Tragedie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Studies[C].Stanly Wells 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5]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 and the Exorcists, in Shakespeare and the Question of Theory[C].Patricia A.Parker, Geoffrey H.Hartman ed.London: Routledge, 1986.
【責任編輯:郭德民】
2015-02-10
辛雅敏(1983—),男,河南鄭州人,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博士,鄭州大學英美文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英美文學及西方文學理論研究。
I106
A
1672-3600(2015)04-007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