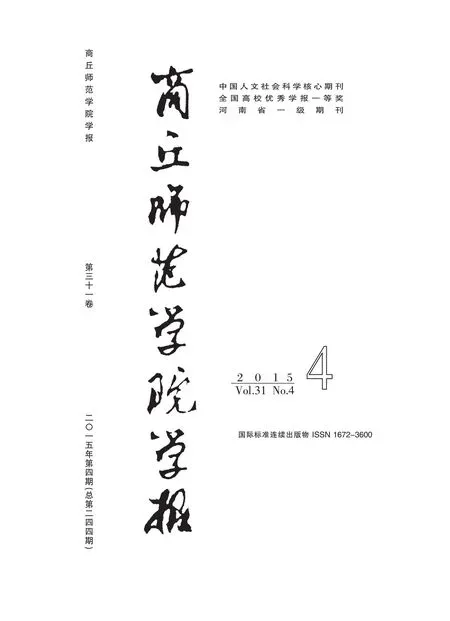民國高校學(xué)術(shù)群體與文物保護(hù)事業(yè)論析
江 琳
(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 100006)
民國高校學(xué)術(shù)群體與文物保護(hù)事業(yè)論析
江 琳
(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 100006)
民國時期是中國現(xiàn)代文物保護(hù)事業(yè)的形成時期。從20世紀(jì)20年代開始,一批從事文物調(diào)查、研究和考古活動的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在高校內(nèi)建立。它們不但開展了實(shí)地調(diào)查和田野考古工作,積極籌備建設(shè)高校博物館,發(fā)起文物維權(quán)運(yùn)動,還借助高校平臺支持官方的文物保護(hù)工作,推動了民國時期文物事業(yè)的發(fā)展。
民國高校;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考古發(fā)掘;文物主權(quán);博物館
20世紀(jì)20年代,南京高等師范學(xué)校(東南大學(xué))、北京大學(xué)、清華大學(xué)、中山大學(xué)、廈門大學(xué)等高校都提出,要在史學(xué)研究中重視實(shí)物資料和引進(jìn)西方考古學(xué)新方法,一些高校還成立了專門從事考古研究的機(jī)構(gòu)或團(tuán)體。這些學(xué)術(shù)群體不但開展了實(shí)地調(diào)查和田野考古工作,積極籌備建設(shè)高校博物館,發(fā)起文物維權(quán)運(yùn)動,還借助高校平臺支持官方的文物保護(hù)工作。對民國時期高校的文物保護(hù)和考古工作進(jìn)行系統(tǒng)論述,將有利于拓展近代文物保護(hù)的歷史研究,并客觀評價高校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在近代中國文物事業(yè)中的作用。
一、重視文物調(diào)查和考古發(fā)掘
20世紀(jì)初,中國境內(nèi)相繼有敦煌文書、殷墟甲骨等一系列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促使中國學(xué)界開始注重面向社會搜集文化的物證,走上了借助考古資料開展古史研究的新道路。1920年5月,南京高等師范學(xué)校首先成立史地研究會,提出要仿照西方史學(xué)會,通過“采訪古跡,掘地發(fā)藏,調(diào)查統(tǒng)計”,來“增加和保存史料”[1]。研究會創(chuàng)辦的《史地學(xué)報》刊登了大量的考古學(xué)文章,提倡“古史之較證與開拓,必需掘地發(fā)藏,非合群力不能進(jìn)行”[2]。不過南京高等師范學(xué)校雖提倡考古學(xué)較早,或許因其更重視古器物的史料價值,所以在搜求古器物時主張“或仿造之,改作之”[3],也未在校內(nèi)組建考古團(tuán)體。
最早身體力行組織高校考古團(tuán)體的是北京大學(xué)國學(xué)門。1920年10月,北京大學(xué)在確定整理國學(xué)計劃時,就將“收購”、“購地攫取”和“求贈”設(shè)定為搜求古器物的重要途徑[4]1440。1922年國學(xué)門成立后,沈兼士首先將古物調(diào)查與發(fā)掘作為發(fā)展重點(diǎn)[5]。1924年馬衡擔(dān)任國學(xué)門考古學(xué)會主席后,決議“用科學(xué)的方法調(diào)查、保存、研究中國過去人類之物質(zhì)的遺跡及遺物”[6]1500。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成立后,也將出土文物的搜集和實(shí)地考察作為獲取史料的重要途徑。梁啟超在《學(xué)問獨(dú)立與清華第二期事業(yè)》一文中說:“希望清華最少以下三種學(xué)問之獨(dú)立自任”,其中就包括“史學(xué)與考古學(xué)”[7]。研究院提出:“欲研究吾國古代之文明,人類進(jìn)化之程序,典籍以外,尤必藉于實(shí)物及遺跡之考察也。”[8]為了搜集地下史料,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與歷史系聯(lián)合設(shè)立了考古學(xué)陳列室,由李濟(jì)負(fù)責(zé)征集工作。
除北大、清華外,還有部分高校將古物古跡調(diào)查和文物考古作為發(fā)展國學(xué)研究的基礎(chǔ),并設(shè)立了考古學(xué)會。1926年10月成立的廈門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院在籌備時就指出,要“采集中國歷史或有史以前之器物”,“或國外佚書秘籍,及金石、骨甲、木簡文字”為考證之資料[9]。成立大會上,院總秘書林語堂提出了“一面調(diào)查閩南各種方言社會以及民間一切風(fēng)俗習(xí)慣,一面發(fā)掘各處古物”的計劃[10]。從組織結(jié)構(gòu)上看,廈門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院傳承了北大國學(xué)門的體例,也設(shè)立了考古學(xué)會。研究院的中堅力量、原北大考古學(xué)會成員顧頡剛為《廈門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院周刊》撰寫了《緣起》,其文就有“我們要掘地看古人的生活”之語[11]。國立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研究所在成立之后,也推舉了徐信符、商承祚、黃仲琴主理廣東古跡調(diào)查一切事宜[12]。1928年成立的中山大學(xué)考古學(xué)會,由商承祚擔(dān)任主席,原北大考古學(xué)會主席、時任中山大學(xué)教授的馬衡擬定了從事實(shí)地調(diào)查、搜集和發(fā)掘工作的發(fā)展計劃[13]。根據(jù)計劃,中山大學(xué)首先開展兩粵古代城市宮室墳?zāi)惯z址的搜尋,并認(rèn)為“西南各省的發(fā)掘事業(yè),尤應(yīng)該本所來擔(dān)負(fù)”[14]。中山大學(xué)閩學(xué)會成立之初,雖不能開拓發(fā)掘事業(yè),但也強(qiáng)調(diào)對于古跡調(diào)查和古物記述要“隨地進(jìn)行”,“提倡保存,免付損毀,或售外人,以留后本研究的資料”[15]。
民國時期高校考古團(tuán)體開展田野實(shí)踐活動以仿古、調(diào)查為主。從1924至1930年間,北大考古學(xué)會先后組織或參與了數(shù)次田野調(diào)查活動。其中,北京大學(xué)獨(dú)立組織的田野調(diào)查活動有:由徐炳昶、李宗侗主持的西郊大覺寺大宮山、小宮山調(diào)查,陳萬里、顧頡剛、劉榮貴參加的圓明園、文淵閣遺跡調(diào)查,1924年調(diào)查洛陽北鄺山漢晉太學(xué)遺址及漢魏氏石經(jīng)出土情形,1929年馬衡、傅振倫和常惠參加的易縣燕下都調(diào)查。合作的考察包括:1925年陳萬里參加的華爾納中亞考察隊敦煌洞窟調(diào)查,1927年徐炳昶、黃文弼等參加的中瑞西北科學(xué)考察團(tuán)敦煌古跡調(diào)查。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成立后,也曾派研究室主任李濟(jì)和地質(zhì)調(diào)查所袁復(fù)禮一起考察了山西西陰村,發(fā)現(xiàn)大片史前陶片。后來,研究室還曾到河南、甘肅等地考察和搜集文物。1928年暑假,中山大學(xué)研究所曾派商承祚、容肇祖赴粵北韶州搜求古物[16]。廈門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院成立后,顧頡剛、陳萬里等數(shù)次前往泉州訪古[17]。燕京大學(xué)史學(xué)會也重視實(shí)地考察,設(shè)立了參觀股,經(jīng)常組織會員考察各地文物古跡。學(xué)會短期考察多在北京城內(nèi)和周邊,如圓明園、妙峰山、周口店等地。長期的考察主要利用假期進(jìn)行,曾調(diào)查了河南的洛陽、開封和安陽、河北正定龍興寺和大名崔東壁故里、山東泰山、大同云岡石窟等地。
多數(shù)高校還積極尋找機(jī)會,開展田野考古活動。但總體看來,各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開展的考古發(fā)掘數(shù)量少,而且規(guī)模較小。高校中率先開展考古發(fā)掘?qū)嵺`工作的,是李濟(jì)領(lǐng)導(dǎo)的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考古學(xué)研究室。1926年3月,在清華校長曹云祥和教務(wù)長梅貽琦的大力支持下,李濟(jì)組織考古隊于10月15日至12月發(fā)掘了山西西陰遺址,獲文物76箱[18]26。北京大學(xué)國學(xué)門雖然成立時間早,考古發(fā)掘活動卻較清華為晚。1929年10月,北大考古學(xué)會派傅振倫和日本學(xué)者原田淑人的學(xué)生水野清一發(fā)掘了中國大學(xué)(清鄭王府)內(nèi)的唐仵欽墓,是為“北京第一次考古發(fā)掘”[19]。1930年,考古學(xué)會與河北省教育廳廳長沈尹默約定以河北省為學(xué)會的發(fā)掘基地,與古物保管委員會、北平研究院合組燕下都考古團(tuán),由馬衡率領(lǐng)在河北易縣展開燕下都老姥臺遺址發(fā)掘[20]。中山大學(xué)唯一一次實(shí)地考古發(fā)掘是在1928年4月,由戴季陶、傅斯年、容肇祖組成專家教授組,發(fā)掘番禺縣員村鄉(xiāng)晉代古墓,共獲得晉磚20余塊[21]。
民國時期高校考古發(fā)展緩慢既有大學(xué)教育體制局限使然,也與機(jī)構(gòu)本身力量脆弱,經(jīng)費(fèi)困難有直接的關(guān)系。高校教師多有教學(xué)任務(wù),學(xué)生每年要完成學(xué)業(yè),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很難長期組織大量人力集中開展考古發(fā)掘活動。傅斯年也認(rèn)為,與研究院相比“大學(xué)中因有學(xué)生作為助手的便利條件,適宜開展規(guī)模較小的研究工作”[22]。經(jīng)費(fèi)短缺也是阻礙高校開展科學(xué)考古活動的障礙之一。中山大學(xué)創(chuàng)立初,考古學(xué)、人類學(xué)、民俗學(xué)、語言學(xué)的調(diào)查費(fèi)及特別研究的準(zhǔn)備金僅每月800元,不可能支持稍具規(guī)模的田野調(diào)查。1929年中山大學(xué)語史所考古學(xué)會的考古發(fā)掘費(fèi)只有1000元[23],而1930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田野工作經(jīng)費(fèi)是每年1萬元[24]。兩者相比,考古經(jīng)費(fèi)差距非常明顯。廈門大學(xué)國學(xué)院經(jīng)費(fèi)則依靠陳嘉庚經(jīng)商支持,國學(xué)研究經(jīng)費(fèi)遲遲不能落實(shí),考古發(fā)掘的計劃自然無法實(shí)現(xiàn)。
為解決考古經(jīng)費(fèi)的問題,高校較大規(guī)模的田野考古工作多采取與其他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或博物館合作的方式開展。北京大學(xué)早在沈兼士組織考古學(xué)研究室時就擬定組織“考古學(xué)研究會”,打算待“古物之搜求和研究有一定之計劃”后,與本校史學(xué)系及“校外古物學(xué)會等機(jī)關(guān)聯(lián)絡(luò)”開展工作[25]1442。后來考古學(xué)會與河北省政府、古物保管委員會組織的燕下都考古發(fā)掘團(tuán)就是采用這種合作模式。廈門大學(xué)國學(xué)院制定考古學(xué)計劃時曾擬加入東方考古學(xué)協(xié)會,并組織發(fā)掘團(tuán)在安陽發(fā)掘,可惜此計劃因國學(xué)院解體而夭折。燕京大學(xué)史學(xué)會的考古活動也有不少是和校外機(jī)構(gòu)合作的,如與哈佛大學(xué)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xué)社,在1933年4月組織了哈佛燕京考古團(tuán),赴正定考察龍興寺。
高校倡導(dǎo)文物調(diào)查和考古發(fā)掘推動了中央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的田野考古工作,其考古團(tuán)體或機(jī)構(gòu)成員成為官方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開展考古發(fā)掘的重要力量。1927年,馬衡曾派北大國學(xué)門考古學(xué)會事務(wù)員董作賓持函到上海謁見蔡元培,請組織發(fā)掘殷墟及漢太學(xué)遺址,以探掘甲骨刻辭及漢魏石經(jīng)。可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殷墟發(fā)掘亦不能不追溯國學(xué)門推導(dǎo)之功。后來董作賓被傅斯年任命,率先在河南安陽開始了殷墟的試掘工作。清華國學(xué)院考古學(xué)研究室主任李濟(jì)后來擔(dān)任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學(xué)室主任,主持了數(shù)次殷墟發(fā)掘工作。1936年8月,為“獎勵學(xué)術(shù)研究”,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決議批準(zhǔn)“對于考古有相當(dāng)設(shè)備及人才”的私立大學(xué)參加采掘古物發(fā)掘活動[26]。由此,更多的民國高校加入到了文物考古活動當(dāng)中。
二、重視文物保護(hù),維護(hù)文物主權(quán)
通過開展訪古和考古發(fā)掘?qū)嵺`活動,高校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進(jìn)一步認(rèn)識到文物保護(hù)的迫切性,開始通過發(fā)表研究成果、舉辦展覽等方式廣泛宣傳,以期引起社會重視文物古跡保護(hù)工作。如顧頡剛在考察蘇州保圣寺后,專門撰寫了考證文章,陳萬里也發(fā)表了攝影作品,呼吁保護(hù)保圣寺唐代塑像,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終使之獲得大學(xué)院專批的1萬元作為保護(hù)資金。
1924年,北大考古學(xué)會為禁止載洵拆毀大宮山的玄同寶塔,維護(hù)大宮山古跡,在《申報》發(fā)表宣言。其文曰:
茍國人不急起阻止,則今日失一古跡,異日即失一史料,其事似微,而所關(guān)茲大,長此以往,西山古建筑將積漸受其摧殘,史料缺遺,后來學(xué)子,考索無從,我國文化將有淪亡之懼、不亦悲哉。本會有志考古,無力挽救,瞻企文化,惄焉興憂,所望邦人君子,群起力爭,則慶幸者,非徒考古界矣。[27]
高校內(nèi)的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也試圖通過官方力量,推動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強(qiáng)文物古跡保護(hù)工作。1922年4月,北大國學(xué)門考古學(xué)會成員沈兼士、馬衡,以及沈士遠(yuǎn)、單不庵、馬玉藻、朱希祖、錢玄同、周作人等北大教授聯(lián)名發(fā)表啟示,要求國民政府制止清室盜賣《四庫全書》,并擬請北京大學(xué)致函教育部,收回《四庫全書》,籌設(shè)“古物院一所,任人觀覽”[28]。1922年,北大國學(xué)門顧頡剛、陳萬里考察蘇州保圣寺后,顧頡剛致函國學(xué)門主任沈兼士,建議“與歷史博物館主任商酌公呈內(nèi)務(wù)部,請為運(yùn)京保存”為妥[29]。后來,顧頡剛、陳萬里還被聘為教育部“甪直唐塑保存會”委員[30]。北大考古學(xué)會主席馬衡在考察新鄭孟津古物之后,為避免古物流失,建議北京大學(xué)呈請國務(wù)院令地方將古物撥歸中央保管[31]。 1924年2月,國學(xué)門給山西、河南省長發(fā)去公函,請保護(hù)太原天龍山及大同云岡、洛陽龍門及鞏縣石窟寺,并提出“如有愿捐資修理者”,希望隨時通知該會選派專家“襄同辦理”,以免修理不當(dāng),“失原像真相”[32]。
高校還通過購買流散文物的方式,保護(hù)了部分古物。1927年1月,在發(fā)現(xiàn)山西商人擬秘密將57箱興化寺壁畫出售給外國人謀取厚利時,北大國學(xué)門 “一面磋商價買此五十七箱,一面點(diǎn)請省長飭屬保存其未剝各畫。議價再三,始以四千元得之”[33]。中山大學(xué)考古學(xué)會主任商承祚在調(diào)查員村鄉(xiāng)古物時,也設(shè)法購回了一些散佚的陶俑和器蓋[34]。
此外,高校學(xué)術(shù)群體還重視維護(hù)中國文物主權(quán),通過限制外國借助考察之名掠奪中國文物資源,開展平等基礎(chǔ)上的中外學(xué)術(shù)合作等方式,促進(jìn)了中國自主文物保護(hù)工作的開展。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文物維權(quán)活動就是由高校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開展的。1925 年初,美國人華爾納受哈佛大學(xué)之委托準(zhǔn)備組織中亞考察團(tuán),進(jìn)入中國西北考察,并邀請北大國學(xué)門派人參加。考古學(xué)會的陳萬里受國學(xué)門委派加入考察隊。鑒于1923 年華爾納在華考察期間曾有剝離敦煌壁畫的劣行,陳萬里在考察過程中嚴(yán)密監(jiān)視華爾納的行動,并將考察隊擬剝離壁畫的計劃及時報告了地方政府。在活動結(jié)束時,華爾納被迫同意了國學(xué)門提出的不帶走所采掘文物的條件,開創(chuàng)了中國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反對西方文物掠奪的成功先例[35]136。
李濟(jì)主持的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考古學(xué)研究室與美國佛利爾藝術(shù)館的西陰村考古發(fā)掘合作,也是以維護(hù)中國的文物主權(quán)為基本條件的。在西陰村合作發(fā)掘協(xié)議中,最重要的條款就是“所得古物歸中國各處地方博物館;或暫存清華學(xué)校研究院,俟中國國立博物館成立后永久保存”[36]34。二者成功的合作實(shí)踐也為中國學(xué)界維護(hù)考古文物主權(quán)樹立了榜樣。1927年由“中國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協(xié)會”與斯文·赫定合組的中瑞西北科學(xué)考察,就是中外合作考古最成功的范例。這次西北考察,從談判協(xié)議到組團(tuán),都是以北京大學(xué)和清華大學(xué)兩高校為主要力量。北京大學(xué)地質(zhì)系教授李四光、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教授袁復(fù)禮和李濟(jì)為談判代表。從組團(tuán)情況看,考察團(tuán)的中方人員除歷史博物館照相員龔元忠和華北水利工程師詹蕃勛外,其余9位成員都來自北大和清華[37]序言①。根據(jù)“中國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協(xié)會”與斯文·赫定簽訂的協(xié)議,外方“不得有任何借口,致?lián)p毀關(guān)于歷史、美術(shù)等之建筑物”和“以私人名義購買古物”,采集品“關(guān)于考古學(xué)者,統(tǒng)須交與中國團(tuán)長或其委托之中國團(tuán)員,運(yùn)歸本會保存”[38]260。協(xié)議充分反映了學(xué)術(shù)界維護(hù)文物主權(quán)的意識和堅持學(xué)術(shù)獨(dú)立性以及學(xué)術(shù)平等的觀念,是“中國學(xué)術(shù)界成熟并形成社會力量之一的標(biāo)志”[39]6。
1935年,古物保管委員會頒布了《外國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或私人參加掘采古物規(guī)則》,就中外合作發(fā)掘條件作出相關(guān)規(guī)定,要求外國人員“不得超過本國學(xué)術(shù)機(jī)關(guān)團(tuán)員之半數(shù)”;“外國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或私人,應(yīng)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所派人員之監(jiān)察”。外國合作方“須俟本國主持采掘之學(xué)術(shù)機(jī)關(guān)正式發(fā)表后始得發(fā)表”工作報告或文字宣傳[40]633。這些條款,從國家法制層面結(jié)束了外人任意在中國境內(nèi)考古、掠奪中國文物的歷史。這一成果,與民國時期高校內(nèi)文物考古群體的不懈努力是分不開的。
三、建設(shè)高校博物館
20世紀(jì)20至30年代,各高校文物團(tuán)體通過收集古物、組建博物館保護(hù)了部分出土文物,并在開展文物調(diào)查和考古過程中為學(xué)生提供了實(shí)踐機(jī)會,培養(yǎng)了文物研究和博物館的專門人才。
早在北大國學(xué)門初建時,沈兼士在《國學(xué)門建議書》中即提出,希望以各學(xué)會為基礎(chǔ),“擴(kuò)而充之,即可成一大學(xué)附屬之博物院,各學(xué)系均可于此取資參考。將來與各國間成績之交換,物品之贈借,均可規(guī)定一圓滿之辦法,共圖東方學(xué)術(shù)之發(fā)展”[41]。1923年11月,國學(xué)門還曾建議將河南新鄭發(fā)現(xiàn)的古物交歸中央,劃撥北大保存,以作為“大學(xué)考古系陳列館”的基礎(chǔ)[42]。到1925年,北大考古學(xué)陳列室已擁有藏品3502件[43],1930年達(dá)到3695件[44],為充分展示考古成績,學(xué)會設(shè)立四所陳列室,展示馬衡、徐炳昶、李宗侗、陳萬里等所采集的金石、甲骨、陶器、玉器等文物。還另辟專室,展示藝風(fēng)堂等處拓本12000余件。陳列室對校內(nèi)開放,文物供學(xué)生參觀和研究,并備校外專家參考。因此,曾任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會助教的傅振倫認(rèn)為,“考古學(xué)會實(shí)是具有博物館性質(zhì)的組織”[45]820。從建制上來看,國學(xué)門考古學(xué)會的古物陳列室也比較完備,設(shè)有石刻室、照相室、傳拓室和庫房,基本配備了博物館的各職能部門[46]263②。
北京大學(xué)還參與了官方的博物館建設(shè)工作。1928年,考古學(xué)會常任干事陳垣帶領(lǐng)北大學(xué)生協(xié)助查點(diǎn)故宮文物。故宮博物院成立時,沈兼士擔(dān)任董事會理事、文獻(xiàn)館副館長,李煜瀛為第一屆董事會、理事會的董事和理事長,李宗侗為董事會理事、秘書長,馬衡擔(dān)任古物館副館長,顧頡剛、徐炳昶為文獻(xiàn)館專門委員,袁同禮為圖書館副館長[47]46-47,76-77。可見,故宮博物院的建設(shè)與北大國學(xué)門考古學(xué)會的參與分不開。此外,北京大學(xué)與教育部歷史博物館也有很深的淵源關(guān)系。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后,歷史博物館恢復(fù)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平歷史博物館舊名后,任命北京大學(xué)余遜兼任主任。1947年9月,國立北京大學(xué)博物館專修科主任韓壽萱兼任了歷史博物館館長。1948年,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無力顧及歷史博物館,也將其事務(wù)交北京大學(xué)代管[48]40。
李濟(jì)在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工作期間,對博物館建設(shè)尤為重視。1926年6月,李濟(jì)建議英國庚款會調(diào)查團(tuán)支持中國建立一“設(shè)備齊全之博物館”,作為國立機(jī)構(gòu),此館將成為全國一切考古學(xué)及人類學(xué)工作之“結(jié)算中心”[49]154。雖然李濟(jì)在建議書中并沒有將此博物館與清華建立聯(lián)系,但從其設(shè)定的博物館活動和研究領(lǐng)域來看,是與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發(fā)展方向相一致的,即除展覽外,尤為重視考古發(fā)掘和人類學(xué)測量工作。從后來他與美國佛利爾藝術(shù)館簽訂的考古協(xié)議看,曾有考察古物可“暫存清華學(xué)校研究院,俟中國國立博物館成立后永久保存”一條[50]34,似可看出李濟(jì)有將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考古學(xué)術(shù)研究與國家博物館業(yè)務(wù)相結(jié)合的打算。1926年6月,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議決由研究院與歷史學(xué)系合辦陳列室,作為收集和研究古物的場所[51]。當(dāng)時陳列室每年的經(jīng)費(fèi)預(yù)算有六七千銀圓,可見所受重視不同一般。李濟(jì)從西陰村發(fā)掘回來的古物,后來都保存、陳列在這個室內(nèi)。據(jù)《國學(xué)論叢》記載,“中外學(xué)者多來此參觀。唯以件數(shù)過多,整理困難,故現(xiàn)陳列于考古室者尚不足十分之一”[52]。
中山大學(xué)在籌備考古學(xué)系的時候,就計劃投入6萬元作為博物館的先期開辦費(fèi)[53]。后來語史所通過購買和考古工作充實(shí)了藏品,并于1929年1-3月舉辦了展覽會。從展覽會的說明書看,古器物部陳列了殷墟古禮器、戈、劍、斧、弩機(jī)、銅權(quán)、鏡、造像以及石范、陶器等,還制作了不少古器物的模型[54]10-16。1929年1月,商承祚以史語所原有古物不足供考古之用為由,特會同顧頡剛商準(zhǔn),由校長核撥專款赴北平購置古物,預(yù)算的古物征集費(fèi)用每月達(dá)到1000元[55]。5月,語史所在北平搜得商周秦漢魏晉隋唐宋明之甲骨、金石、陶瓷等古器物,共200余種,“其中不乏精絕奇異之品”,這些古物都收藏在史語所的古物陳列室[14]。1926年秋季,廈門大學(xué)也設(shè)立了文化古物陳列所,并于10月舉行了第一次古物展覽。陳列室展出有魯迅所藏拓片、六朝隋唐造像、陳萬里所藏大同云崗?fù)仄⒍鼗拖嗥约昂幽下尻栆粠С鐾恋墓盼锖蛯W(xué)校商科所藏古錢[56]。通過收受外間捐贈并自購風(fēng)俗物品,廈大國學(xué)研究院還設(shè)立了風(fēng)俗物品陳列室,作為風(fēng)俗博物館之初步[57]。
四、結(jié)語
綜上所述,民國時期高校內(nèi)的文物團(tuán)體在開展文物調(diào)查、考古、研究,維護(hù)文物主權(quán),組建博物館等方面都作出了不俗的成績。北京大學(xué)國學(xué)門“延攬中外考古學(xué)家,組織古跡古物調(diào)查會,以搜羅考古學(xué)之材料,設(shè)博物館以為系統(tǒng)之陳列,立研究室以行科學(xué)之研究”[58],在近代中國文物保護(hù)事業(yè)中具有重要影響,亦作出了表率。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積極開展考古活動,為中國學(xué)界開展科學(xué)考古活動之先導(dǎo)。二者在發(fā)展文物保護(hù)事業(yè)上的開創(chuàng)之功、教導(dǎo)之力不容忽視。20世紀(jì)20至30年代,各高校建立文物團(tuán)體多有仿照北大、清華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的組建方式和研究理念而來,如建制上設(shè)立考古、語言、歷史、民俗學(xué)會,發(fā)展規(guī)劃中重視文物征集,并以組織實(shí)地考古作為團(tuán)體發(fā)展的目標(biāo)。高校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開展的文物考古工作帶動了一些民間文物團(tuán)體,一些高校內(nèi)還成立了民間文物研究團(tuán)體,比如容庚在燕京大學(xué)內(nèi)成立考古學(xué)社,雖以古器物學(xué)研究為學(xué)社主旨,但同時還強(qiáng)調(diào)古器物學(xué)者要與考古學(xué)者分工合作,并使科學(xué)考古的“風(fēng)氣普遍和認(rèn)識”[59]。
高校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開展文物保護(hù)和考古工作,對近代中國文物保護(hù)事業(yè)發(fā)展具有很大的促進(jìn)作用。高校學(xué)者站在教學(xué)和科研的前沿,了解國際的文物考古和保護(hù)理念,他們通過組織文物考古活動,在文物維權(quán)、考古規(guī)范制定等方面都獲得了有益的經(jīng)驗(yàn),從而組成了官方文物管理機(jī)構(gòu)的智囊團(tuán)。在1928年成立的大學(xué)院古物保管委員會中,委員會成員多半來自于高校內(nèi)的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其中馬衡、顧頡剛、沈兼士、李宗侗、李石曾、徐炳昶等都曾分別在北京大學(xué)國學(xué)門、清華大學(xué)考古學(xué)研究室、中山大學(xué)語史所等高校考古團(tuán)體中任職。此時期國民政府出臺的各種文物政策和方針亦多出自各高校知名學(xué)者之手。所以,考察民國時期高校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的文物調(diào)查、考古、文物保護(hù)活動,對于研究政府的文物保護(hù)思想和政策發(fā)展脈絡(luò)也不無裨益。
注 釋:
①考察團(tuán)分三隊,北隊有北京大學(xué)的丁道衡、黃文弼參加,中隊由北京大學(xué)的教務(wù)長徐炳昶負(fù)責(zé),南隊由清華國學(xué)院袁復(fù)禮帶隊。
②日本侵華戰(zhàn)爭拖延了北大博物館建設(shè)的步伐,直到1948年,北大才正式籌備博物館,由韓壽萱出任館長。據(jù)《北京大學(xué)博物館概要》(北京大學(xué)博物館編,1949年版)記載,至1949年9月,北京大學(xué)博物館有文物3700件,照片2508張。
[1]陳訓(xùn)慈. 組織中國史學(xué)會問題[J]. 史地學(xué)報:第1卷第2號,1922.
[2]中國之史學(xué)運(yùn)動與地學(xué)運(yùn)動[J]. 史地學(xué)報:第2卷第3號,1923.
[3]國立東南大學(xué)國學(xué)院整理國學(xué)計劃書[J].國學(xué)叢刊:第1卷第4期,1923.
[4]國立北京大學(xué)研究所整理國學(xué)計劃書[M]//王學(xué)珍,郭建榮.北京大學(xué)史料(1912-1937):第2卷·中.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
[5]研究所國學(xué)門懇親會紀(jì)事[N]. 北京大學(xué)日刊:第1337號,1923-11-10.
[6]研究所國學(xué)門開會紀(jì)事[M]//王學(xué)珍,郭建榮.北京大學(xué)史料(1912-1937):第2卷·中.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
[7]梁啟超. 學(xué)問獨(dú)立與清華第二期事業(yè)[J]. 清華周刊:第350期,1925-09-11.
[8]研究院紀(jì)事[J].國學(xué)論叢:第1卷第1號,1927.
[9]廈門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院組織大綱[J].廈大周刊:第156期,1926-09-25.
[10]國學(xué)研究院成立大會紀(jì)盛[J].廈大周刊:第159期,1926-10-16.
[11]顧頡剛. 緣起[J].廈門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院周刊:第1卷第1期,1927-01-05.
[12]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事務(w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jì)錄[J].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30期,1928.
[13]馬衡.本校籌備考古學(xué)系之計劃[J].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10期,1928.
[14]顧頡剛,余永梁.本所計劃書[J].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62-64期,1929.
[15]陳錫襄.閩學(xué)會的經(jīng)過:續(xù)[J].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8期,1927.
[16]容肇祖.韶州調(diào)查日記[J].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39期,1928.
[17]張陳兩先生調(diào)查泉州古跡及關(guān)于中外交通史料之報告[J]. 廈大周刊:第165 期,1926-11-27.
[18]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diào)查[M]//李光謨.李濟(jì)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1994.
[19]傅振倫.傅振倫自述[J].北京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北京文史資料:第54輯,1996.
[20]傅振倫.燕下都發(fā)掘報告[J].國學(xué)季刊:第3卷第1號,1932.
[21]本所大事記[J].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62-64期,1929.
[22] 孟真.改革高等教育中的幾個問題[J].獨(dú)立評論周刊:第4期,1932.
[23]考古學(xué)會十八年度進(jìn)行計劃書[J].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101期,1929-10-16.
[24]李濟(jì).安陽[M]//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李濟(jì)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5]研究所國學(xué)門第一次會議紀(jì)事[M]//王學(xué)珍,郭建榮.北京大學(xué)史料(1912-1937):第2卷·中.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
[26]奉行政院令據(jù)內(nèi)政部呈據(jù)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呈為國內(nèi)私立大學(xué)應(yīng)準(zhǔn)參加發(fā)掘古物工作以獎勵學(xué)術(shù)研究等情請鑒核施行一案仰知照等因令仰知照[R].江西省政府公報:607期,1936.
[27]北大擬掘京西大宮密窟:續(xù)[N].申報:18478號,1924-08-07.
[28]為清室盜賣四庫全書敬告國人速起交涉啟[J].北京大學(xué)日刊:第1005號,1922-04-20.
[29]顧頡剛致沈兼士函[J]. 北京大學(xué)日刊:第1065號,1922-07-22.
[30]陳彬和.保存唐塑運(yùn)動之經(jīng)過[J].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70期,1929.
[31]北大要求保存古物:新鄭孟津古物送京[N].晨報,1923-10-06;北京大學(xué)研究所國學(xué)門調(diào)查河南新鄭孟津兩縣出土古物紀(jì)事:續(xù)[N].晨報副刊:第277號,1923-10-21.
[32]研究所國學(xué)門致山西河南省長公函[J].北京大學(xué)日刊:1401號,1924-02-22.
[33]馬衡.壁畫考語跋[J]. 北京大學(xué)研究所國學(xué)門月刊:第1卷第1號,上海:開明書店,1927.
[34]商承祚.調(diào)查員村鄉(xiāng)發(fā)現(xiàn)晉代古塜始末記[J].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30期,1928.
[35]陳萬里.西行日記[M].北平:樸社,1936.
[36]西陰村史前的遺存[M]//李光謨.李濟(jì)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1994.
[37]徐炳昶.西游日記[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38]中國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協(xié)會與斯文赫定博士所訂合作辦法(原文)[M]//徐炳昶.西游日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39]斯文·赫定.亞洲腹地探險八年[M].楊鐮,代序.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40]外國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或私人參加采掘古物規(guī)則[M]//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二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41]國立北京大學(xué)研究所國學(xué)門經(jīng)費(fèi)計劃書[J].國學(xué)季刊:第1卷第3號,1923(7).
[42]研究所國學(xué)門懇親會紀(jì)事[J].北京大學(xué)日刊:第1337號,1923-11-10.
[43]國立北京大學(xué)研究所國學(xué)門報告[J].國學(xué)季刊:第2卷第1號,1925.
[44]傅振倫.北大研究所考古學(xué)會在學(xué)術(shù)上之貢獻(xiàn)[J].北京大學(xué)周刊:第1卷第2期, 1930-12-17.
[45]傅振倫.記北京大學(xué)考古學(xué)會[M]//傅振倫文錄類選.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1994.
[46]李淑萍,宋伯胤.博物館歷史文選[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
[47]那志良.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jīng)過[M].臺灣: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1957.
[48]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80年[M],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1992.
[49]致英庚款會調(diào)查團(tuán)(1926-6-5)[M]//李光謨.李濟(jì)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1994.
[50]西陰村史前的遺存[M]//李光謨.李濟(jì)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1994.
[51]研究院紀(jì)事[J].國學(xué)論叢:第1卷第1號,1927.
[52]研究院紀(jì)事[J].國學(xué)論叢:第1卷第2號,1927.
[53]馬衡.本校籌備考古學(xué)系之計劃[J].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10期,1928.
[54]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國立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展覽會說明書目次[Z].1929.
[55]本所預(yù)算表[J].國立第一中山大學(xué)語言歷史學(xué)研究所周刊:第62-64期,1929.
[56]國學(xué)院第二次學(xué)術(shù)講演[J].廈大周刊:第168期,1926-12-18.
[57]廈門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院發(fā)掘之計劃書[J].廈大周刊:第158期,1926-10-09.
[58]北京大學(xué)對于保存新鄭孟津發(fā)現(xiàn)之古物之提議[J].教育雜志:第11期,1923.
[59]劉節(jié).考古學(xué)社之使命[J].考古:第2期,1935.
【責(zé)任編輯:劉圓圓】
Academic Community and Relic Protection in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Lin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Beijing 100006)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modern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20s, some academic groups engaged in cultural surveys, research and archaeological activities, and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university.They not only carried out field surveys and archaeological field work, actively prepar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museums, launched heritage campaign,but also with aid of university’ platform support, promoted the government work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cademic groups;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sovereignty of Cultural relics;museum
2014-12-16
江琳(1971—),女,北京人,副研究館員、博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史和博物館學(xué)研究。
K26
A
1672-3600(2015)04-00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