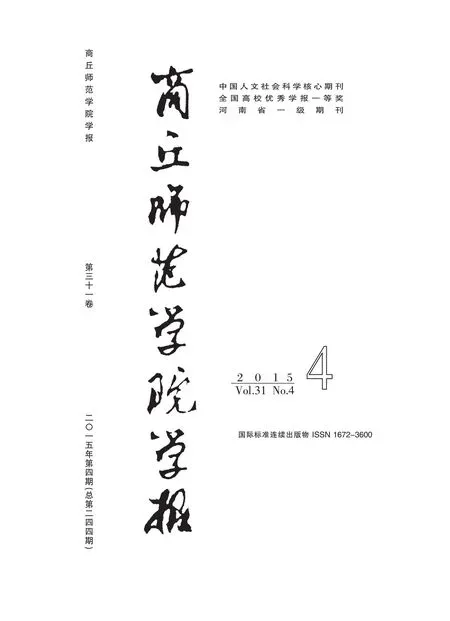論秦直道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線
王紹東 鄭方圓
(內蒙古大學 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論秦直道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線
王紹東 鄭方圓
(內蒙古大學 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對于昭君出塞的路線,林干認為是經秦直道北上的。近年來,山西地區的部分學者認為昭君出塞所走路線為途經山西地區的通塞中路。從歷史資料來看,秦直道仍然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線,因為這條道路最便捷、最安全;呼韓邪單于在迎娶昭君之前,就沿著這條道路往返于漢朝與匈奴之間。秦漢時期,秦直道得到了很好的維護,秦皇、漢武都曾走過這條路線。在昭君出塞之時,秦直道的通行環境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昭君出塞自然不會選擇其他路線。昭君出塞沒有經過秦直道的理由尚不充分。
昭君出塞;秦直道;呼韓邪單于
一、關于昭君北上匈奴單于庭路線的爭議
關于昭君出塞的行走路線,史書上并沒有明確記載,最早提出昭君可能的出塞路線的,是著名的匈奴史研究專家內蒙古大學的林干。1979年,林教授在《昭君與昭君墓》一書中就指出:“昭君出塞時所經路線,史無明文,但線索不難找出。史載呼韓邪單于在宣帝甘露三年(前51)第一次從漠北入漢時,漢朝派兵在他經過的七個郡沿途護衛,并表示歡迎。據《資治通鑒》卷27胡三省注的考訂,那七郡就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后由馮翊直至國都長安。若以當時各郡治所為準,則所經約今內蒙古的包頭、杭錦旗、東勝、陜西榆林、甘肅慶陽,而至陜西西安。呼韓邪從漠北第一次入漢既經由這條路而來,那么,他在公元前33年入漢及后來偕同昭君返回漠北,也是取道這條道路,是很自然的。”[1]581986年,林教授在《內蒙古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發表長文《試論王昭君藝術形象的塑造》,進一步申明了自己對昭君出塞路線的研究,“經過近一二十年來我個人的研究,現已初步探明,呼韓邪和昭君一行北歸漠北單于庭時,由漢朝派遣各級官員領兵護送出境,一則表示禮儀,一則為了警戒和防衛。史書記載呼韓邪于公元前51年(宣帝甘露三年)二月第一次北歸時,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及車騎都尉韓昌,率領一萬六千名騎兵護送。這次有昭君公主出塞同行,按理護送的兵馬自應較前更多。沿途所經路線,共歷七郡,即從漢都長安(今陜西西安)出發,先過左馮翊(屬三輔,在長安東北),然后經過北地(今甘肅慶陽)、上郡(今陜西榆林)、西河(今內蒙古東勝)、朔方(今烏拉特前旗),而至五原(今包頭;以上各地,以當時郡治為準),從五原郡再往西行,至朔方郡臨河縣(今內蒙古臨河縣東北,靠近烏加河南岸),渡北河(今烏加河),向西北方向出高闕(今石蘭計山口),越過長城,便算離開漢地(出了塞),進入匈奴所轄地區”。
林教授提出昭君出塞的這一路線后,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同。近年來,山西省的部分學者又提出了昭君出塞所走的不是秦直道,而是秦直道東的通塞中路,也就是經山西雁門關—平城(大同)—武州(山西左云)—雁門郡(山西右玉)—殺虎口—云中郡—五原郡—單于庭的路線。較早主張這條路線的是山西大學的靳生禾,他在《昭君出塞與蹄窟嶺芻議》一文中認為:“昭君與呼韓邪由長安至單于庭的路線,是東渡黃河北上,循涑水、汾河、桑干河三河河谷一線,經蹄窟嶺至殺虎口出塞,是蹄窟嶺、紅沙巖口實屬很可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與可資開發的旅游資源。”[2]靳先生的觀點提出后,得到了山西省特別是左云縣一些學者的響應,左云縣文聯的劉志堯[3]、左云四中的劉溢海分別發表文章[4],肯定昭君出塞是經過雁門關、大同、左云、殺虎口出塞至匈奴龍庭。
二、經秦直道北上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線
由于《漢書》、《后漢書》等原始文獻都沒有直接記載昭君出塞的行走路線,所以我們的研究只能根據相關的史料進行考訂、判斷。如果拋開其他因素,純粹對相關史料加以綜合運用與解析,似乎可以得出結論,經直道北上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線。
1.秦直道是秦、西漢時期中原王朝連接塞北地區的最便捷通道
秦朝統一后,秦始皇進一步對周邊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軍事擴張,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征服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5]。匈奴人地處塞北草原,他們“逐水草遷徙”[6]1879、胡服騎射,機動性強,“倏來忽往,云飛鳥集”[7]3304。為了打擊匈奴,秦朝需要修筑一條與北方地區溝通便捷、可以快速調集軍隊、運送軍事物資、傳遞軍事情報的道路。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陽,塹山堙谷,直通之”[6]256。對于秦直道的行經路線,盡管學術界仍有爭議,但從各地對秦直道的實際考察結果來看,秦直道的修筑嚴格遵循了“塹山堙谷,直通之”的要求。如國家文物局秦直道課題研究組與陜西省旬邑縣博物館的《旬邑縣秦直道遺址考察報告》就指出,辨認子午嶺山區秦直道的六大要素是:(1)看是否南北的大致走向。(2)看是否沿山脊或高地選線。(3)看是否有塹山堙谷的痕跡。(4)看是否線形順直,彎道很大。(5)看路面是否寬闊平緩。(6)看沿線是否有與秦直道配套的設施,如秦漢行宮、兵站、關隘、烽火臺等遺址,如果六點全部符合即為秦直道無疑[8]。楊澤蒙考察鄂爾多斯境內秦直道遺址時也發現:“鄂爾多斯境內目前可確認的秦直道遺跡,北起達拉特旗高頭窯鄉吳四圪堵村東、南到伊金霍洛旗的掌崗圖四隊,南北縱貫鄂爾多斯高原中部,地圖上的直線距離近100公里。秦直道遺跡途經的地區,今天多屬高丘陵地區,地勢延綿起伏,高差較大,溝壑縱橫。直道遺跡在這一地區沿約190度的方向直線南行,絕無彎道。為了減少道路的起伏高差,凡直道所途經的丘陵的脊部,絕大多數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開鑿,置身直道分別向南、北眺望,均可看到一線相通的數個由于開鑿而形成的位于丘陵正脊部位的豁口,或位于脊背部位的半豁口。……凡直道途經的丘陵間的鞍部,絕大多數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填墊,……,填墊部分的路基底部最寬者約60米,頂部寬30-40米,殘存最厚的墊土現今仍達6米以上,足可見當初工程之艱難。”[9]歷史文獻與考古勘察都證明秦直道是連接秦漢時期中原王朝的統治中心關中地區與北方蒙古高原地區最便捷、最暢通的道路。
2.昭君出塞時,秦直道仍在使用并得到了很好的維護
直道修通后,整個秦、西漢時期都成為從關中地區進入北方河套地區的最重要通道。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死在了沙丘平臺,秦二世、李斯、趙高等人一方面隱藏了秦始皇的死訊,同時仍然按照秦始皇生前制定的巡游路線,繞道秦直道從九原返回首都咸陽。秦始皇的巡游隊伍浩浩蕩蕩、規模龐大,選擇從直道返回首都,說明秦始皇三十七年直道已經基本完工,粗可使用。到秦二世時繼續對直道進行加工修繕,使工程得以竣工。直道修成后,整個西漢時期一直得到了有效的維護和使用。司馬遷到北方邊境地區,曾經親自考察過秦直道,并留下了“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見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故輕百姓力矣”[6]2570的感慨,也體現出秦直道是“適北邊”的最便捷道路。漢武帝時期北擊匈奴,秦直道的戰略地位進一步得到了強化。元封元年十月,漢武帝親率大軍,“行自云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余里,威震匈奴”。漢武帝率領十八萬軍隊從秦直道來到河套地區,表明這時的秦直道有著良好的通行條件。半年前,也就是元封元年四月,漢武帝在登封泰山后,“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10]189。秦皇漢武都使用直道,說明整個秦漢時期秦直道是官方公認的、使用最普遍的連接關中與塞北河套地區的便捷通道。西漢時期,漢朝在北地郡設直路縣、除道縣,顯然是為了維護直道而取名的。
秦直道的兩端,在秦漢時期連接的是兩個最重要的地區。秦直道的南端起始于云陽的甘泉宮,對于甘泉宮的重要地位,辛德勇在《秦直道研究與直道遺跡的歷史價值》一文中進行了深入論證。其北端的九原郡,在整個秦漢時期的重要性亦不可小覷。秦漢王朝與匈奴的和戰關系不僅牽動著全國力量,甚至影響著整個政局,而九原郡處于最前沿的地區,無論是和是戰都會對那里產生重要的直接影響。為了鞏固北方邊疆,秦皇漢武都曾往這里大規模移民,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使這里成為秦漢時期經濟開發的新區。漢武帝元狩四年,山東發生大范圍水災,國家無法賑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應劭對“新秦中”的解釋是:“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10]116說明到漢武帝時期,九原郡所在的河套地區已經具備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優越的開發條件,不僅作為國家轉移災民的目的地,而且遷移到這里的人們還有機會成為“新富貴者”,其繁榮富庶的程度,時人已經把那里與經濟最發達的“秦中”地區相比擬了,因此也就有了“新秦中”之稱。直道的南北兩端,連接這樣兩個經濟地位、軍事地位、戰略地位都如此重要的地區,沒有理由不進行很好的維護。
秦直道并不只是一條南北通行的大路那么簡單,為了保障直道的暢通,發揮聯通南北的各種功能,圍繞秦直道修筑了行宮以及兵站、驛站、關隘、烽燧等軍事防御設施與信息傳遞設施。如對旬邑縣秦直道石門關附近的建筑遺址進行考察,“可以判斷石門關南峰是一處秦代行宮,漢時仍然沿用的皇家住所。石門村東邊大片農田上應為較大的居住區,除官吏的住房和軍隊的營房外,還有驛站、商業、民居等設施。印證史料,可以推測,石門關關前關后的常住人口可能有數千。《史記·秦始皇本紀》又載秦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石門關是秦直道必經之地,若沒有如此規模,不可能接待運送秦始皇靈柩返回的龐大隊伍。”[8]秦直道與周邊道路、城鎮、兵營等構成了立體的、“一方有難,八方馳援”的防御體系,從而保證了在直道上行走的安全。這樣看來,從秦直道出塞,不但最便捷、順暢,也不存在所謂的安全隱患。
3.呼韓邪單于在甘露三年選擇秦直道往返長安與塞外之間
對于昭君出塞的路線,史無明確記載,但昭君是隨呼韓邪單于一同離開長安回到了塞外的單于庭,則是有明確的史料證據的。《漢書·元帝紀》載:“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儀,既伏其辜,虖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愿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為閼氏。’”由此可見,昭君嫁給呼韓邪單于,是在單于來漢廷朝見時決定的,昭君極有可能是隨單于一同返回匈奴故地的。值得關注的是,呼韓邪單于并不是第一次來到漢庭。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通過五原塞向漢朝表達修好愿望,經過討論,漢朝決定“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以隆重禮節接待單于。據《資治通鑒》載:“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胡三省注曰:“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后至長安也。”[11]漢紀十九這里明確記載了呼韓邪單于是經過秦直道的沿線七郡來到長安的。在長安留住一個多月后,“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愿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11]漢紀十九。呼韓邪單于從五原郡來到長安,走的是秦直道路線,返回的路線,自然不會變更,況且護送者是同一個人騎都尉韓昌。說明韓昌經常在秦直道上往來,應該非常熟悉沿途路程。
呼韓邪單于朝漢事件,從漢朝皇帝到百官大臣都極為重視,必然選擇最安全、最暢順、最便捷的路線。《資治通鑒》明確記載這條路線就是秦直道。那么,18年后的竟寧元年(前33),呼韓邪單于迎娶昭君,自然仍會選擇這條路徑。在這段時間里,沒有秦直道通行環境惡化的因素,也沒有從關中到五原郡新修更便捷道路的記載與可能性,如果相信《資治通鑒》的記載,就沒有懷疑昭君出塞走秦直道的理由。也許有人說,《資治通鑒》及胡三省的注釋是宋元時期所作,距離昭君出塞的時代已經久遠。實際上,《資治通鑒》的記載所依據的是《漢書》的相關記載。《漢書·匈奴傳》記載:“明年(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兩千騎,為陳道上。”至于《資治通鑒》所補充的部分是否可信,可以從司馬光及寫作《資治通鑒》的過程與態度進行推測。司馬光及其團隊用了19年的時間編修《資治通鑒》,他們首先對相關史料進行詳細排列,寫成叢目,然后在此基礎上完成初稿,最后經過認真考證,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完成最后的定稿工作。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還編成了《資治通鑒考異》,說明取舍材料的依據和理由。司馬光及其團隊以及《資治通鑒》的注釋者胡三省等人的史學素養極為深厚,寫作態度極為嚴謹認真。他們利用當時能夠看到的史料寫呼韓邪單于往返長安與九原的行走路線,應該是有充分依據的。至少在找到新的、更可靠、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之前,難以否定《資治通鑒》的相關記載。
4.昭君出塞經雁門關之說史料依據尚不充分
山西學者靳生禾、劉志堯、劉溢海等主張昭君出塞路線為雁門關一線的通塞中路,而不是秦直道,其史料依據主要是詩歌、戲曲等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其中,劉溢海在《昭君出塞路線考》一文中引證的最早的資料是唐李白的《王昭君》:“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唐上官儀的《王昭君》:“玉關春色晚,金河路幾千,琴悲桂條上,笛怨柳花前。”唐無名氏《王昭君變文》(說唱):“單于:憶昔辭鑾殿,將相出雁門。”劉先生認為,“單于庭既在北方而不在西北方,那么,以李白為代表的‘玉門關說’肯定是錯誤的。否定了玉門關說,那么,昭君出塞之路線也只能是經陜北的直道與經山西的通塞中路了。可為何文學作品中找不出經直道的路線呢?在多數作者的認識中,秦直道是一條山高谷深,又多河谷與沙漠的艱險之路。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因此,文學作品的許多作者就為昭君出塞選擇了經山西雁門關的路線。經雁門關的這條道路相比之直道來,也確實要安全得多”[4]。實際上,文學作品中的描寫,許多是虛擬性描寫,而不是寫實性記述。在唐代,玉門關與雁門關的軍事地位極為重要,人們往往把這兩個關作為出塞的標志。因此,不管是李白等人寫昭君經玉門關出塞,還是無名氏的寫昭君從雁門關出塞,都是虛指昭君出塞之事。劉先生認為李白對匈奴所在方位認識錯誤,玉門關之說不能成立,實際上,無名氏所寫的雁門關,也不具備寫實性的地理坐標性質,而只是泛指昭君出塞之事罷了。至于明清以后的文學作品的描寫,包括地方志中記載的民間故事和傳說,更不具備有力的證據作用。如同許多昭君故事和傳說一樣,它們只是“昭君想象”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人們出于對昭君的熱愛、敬重、同情、歌頌、贊美的心理,希望昭君與自己的故鄉發生聯系,從而創造了各種有關的故事。這些故事,反映的往往不是歷史的真實,更多表現的是人們心靈的期冀與情感的表達。昭君從雁門關出塞的傳說是這樣,山西部分學者主張的昭君出塞走通塞中路之說又何嘗不是這樣的心理呢?另外,劉溢海等所說如果走秦直道路線,匈奴內部不同的勢力可能危害昭君一行的安全,況且秦直道路線的氣候條件惡劣,難以成為昭君出塞的選擇路線等,也都經不起嚴格推敲。對此,王子今在《關于王昭君北行路線的推定》[12]一文中已經進行了辯駁,此不贅述。總之,從目前的相關資料來看,尚不足以推翻昭君出塞走秦直道說。
[1]林干.昭君與昭君墓[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2]靳生禾.昭君出塞與蹄窟嶺芻議[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9(6).
[3]劉志堯.昭君經武州塞出塞考釋[J].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2010(3).
[4]劉溢海.昭君出塞路線考[J].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2012(6).
[5]王紹東.秦始皇北擊匈奴的若干問題辨析[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3(1).
[6]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7]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8]國家文物局秦直道課題研究組、旬邑縣博物館.旬邑縣秦直道遺址考察報告[J].文博,2006(3).
[9]楊澤蒙.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秦直道[J].內蒙古文物與考古,2005(2).
[10]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1]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6.
[12]王子今.關于王昭君北行路線的推定[C]//昭君和親路線專家研討會論文集.湖北昭君旅游文化發展有限公司,2014.
【責任編輯:劉圓圓】
The Theory That Qin Straight Road was Still the Most Possible Route by Which Zhaojun Departed for the Forntier
WANG Shaodong ZHENG Fangyuan
(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of Tourism,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1)
For Zhaojun’s walking route, Mr.Lin Gan thought that it was by Qin Straight Road to the north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in Shan xi considered that Zhaojun’s walking route was Tong-sai road in Shan xi.From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Qin Straight Road was still the most possible route for Zhaojun to the Hun district because it was the most convenient and secure route that the king of Huhanye once used to make contact with Han Dynasty before he married Zhaojun.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Qin Straight Road was protected well and Emperor Qin Shihuang and Emperor Wu of Han have used it.The environment of Qin Straight Road did not changed very much until Zhaojun left Han Dynasty so they had no other choices of routes.Therefore there were no sufficient reasons for the idea that Lady Zhaojun did not go abroad by Qin Straight Road.
Zhaojun Outside the Frontier ;Qin Straight Road;The King of Huhanye
2014-07-31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多維視角下的內蒙古地區戰國秦漢長城研究”(編號:13BZS020); 內蒙古大學本科生國家創新基金項目(編號:201310126010)。
王紹東(1964—),男,內蒙古寧城人,教授,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
K234
A
1672-3600(2015)04-00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