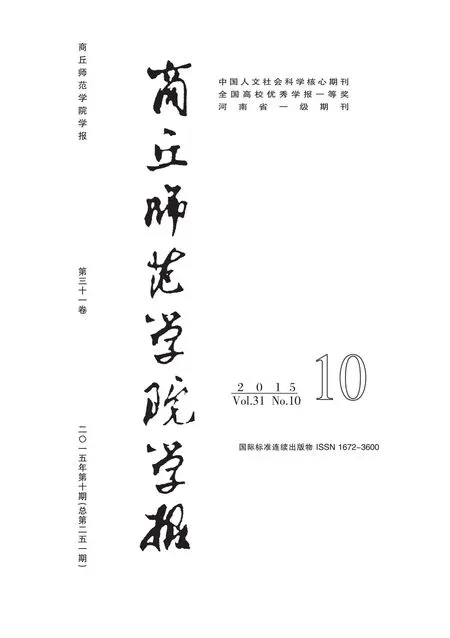沖突與整合
——“國(guó)家法”與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在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中的博弈
廉 睿
(中央民族大學(xué) 管理學(xué)院,北京 海淀100081)
沖突與整合
——“國(guó)家法”與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在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中的博弈
廉 睿
(中央民族大學(xué) 管理學(xué)院,北京 海淀100081)
在構(gòu)建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的進(jìn)程中,需要妥善處理好“國(guó)家法”與本土資源之間的關(guān)系。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作為本土資源的典型代表,具有自身的特點(diǎn)和價(jià)值。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中的部分內(nèi)容與“國(guó)家法”所倡導(dǎo)的精神具有一致性,這體現(xiàn)為兩者之間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良性互動(dòng)上。但與此同時(shí),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與“國(guó)家法”之間也存在著沖突的一面。因此,在建構(gòu)社會(huì)主義法制體系的過(guò)程中,仍需要“國(guó)家法”對(duì)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有效整合。在沖突中尋求整合,在整合中解決沖突,方為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和諧社會(huì)的有效路徑。
“國(guó)家法”;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互動(dòng)模式;整合
一、問(wèn)題的由來(lái)
新中國(guó)成立至今,中國(guó)的社會(huì)形式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各種思潮和思維模式伴隨著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不斷輸送到我國(guó)。作為一把雙刃劍,現(xiàn)代化一方面塑造出了嶄新的社會(huì)面貌,并對(duì)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現(xiàn)代化也給我們帶來(lái)了無(wú)盡的困惑和不解。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律一詞,淵源于歐陸,并伴隨著歐風(fēng)美雨的洗禮和市場(chǎng)化的進(jìn)展而入駐我國(guó)。當(dāng)然,在構(gòu)建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和現(xiàn)代法律體系的過(guò)程中,我們必須借鑒外來(lái)經(jīng)驗(yàn),重視現(xiàn)代化的立法和立法文化,這是毫無(wú)疑問(wèn)的。但與此同時(shí),我們必須對(duì)根植于中國(guó)本土的各種民間法和民間法律文化予以足夠的人文關(guān)懷[1]112。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作為我國(guó)的本土法律資源之一,也就是從這個(gè)層面上開(kāi)始進(jìn)入公眾視野。在“國(guó)家法”所主導(dǎo)的現(xiàn)代法律體系中,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命運(yùn)如何?它是否還有生命力和生存的土壤?假如有,那么它又怎樣同“國(guó)家法”進(jìn)行博弈?這正是我們所要關(guān)注的問(wèn)題。
二、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基本理論
作為典型的“地方性知識(shí)”,我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種類繁多,內(nèi)容豐富[2]2,幾乎各個(gè)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地區(qū)都有習(xí)慣法或者習(xí)慣法文化的分布。因此,要想給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下一個(gè)統(tǒng)一的定義,的確是有難度的,但大體上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gè)角度來(lái)理解我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
(一)民族性
作為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民族性毫無(wú)疑問(wèn)地成為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首要特征。不同的少數(shù)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之間的民族法文化當(dāng)然也不盡相同。無(wú)論從法律內(nèi)容還是糾紛解決機(jī)制上看,各個(gè)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比如,在摩梭族的社會(huì)中,走婚制是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即“一妻多夫”是合乎摩梭人習(xí)慣法的,具有合法性[3]22;但是,在苗族人的世界里,普遍提倡“一夫一妻”,一個(gè)丈夫和一個(gè)妻子才是他們理想的婚姻模型,假如出現(xiàn)了多夫或多妻的現(xiàn)象,不但會(huì)遭受輿論與社會(huì)的譴責(zé),而且還會(huì)遭受苗族習(xí)慣法的制裁。當(dāng)然,我們?cè)谶@里無(wú)須對(duì)各個(gè)民族習(xí)慣法內(nèi)容的優(yōu)劣進(jìn)行評(píng)判,并且這種評(píng)判也是毫無(wú)道理的。因?yàn)椴煌贁?shù)民族的習(xí)慣法都體現(xiàn)了本民族特有的民族特征和文化習(xí)慣,從這個(gè)角度而言,它們已經(jīng)演化為某種“民族符號(hào)”,也就都具有了正當(dāng)性。
(二)自發(fā)性
與“國(guó)家立法”所采用的人為建構(gòu)模式相比,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是自發(fā)形成的,無(wú)過(guò)多的人為參與。在法律史上,習(xí)慣法先于制定法產(chǎn)生,并且是現(xiàn)代制定法的法律淵源之一[4]。據(jù)史料記載,我國(guó)早在商周時(shí)期就存在著大量的“祭祀”習(xí)慣之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被統(tǒng)一遵守且統(tǒng)一適用,在后期逐漸演化成一套關(guān)于“祭祀”的習(xí)慣法文化。從這個(gè)典型的演化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反復(fù)使用的習(xí)慣構(gòu)成了習(xí)慣法的主要內(nèi)在要素。但無(wú)論是習(xí)慣還是習(xí)慣法,都是在人們的社會(huì)交往過(guò)程中自發(fā)生成的,自發(fā)性也就成為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另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
(三)本土性
本土性,有時(shí)候也可稱之為“鄉(xiāng)土性”。正所謂“一方水土,一方風(fēng)情”、“一方水土養(yǎng)育一方人”。即使是同一個(gè)民族,由于聚居的區(qū)域不同,導(dǎo)致其民族習(xí)慣法的內(nèi)容和形式也不盡相同。比如,對(duì)于聚居于南方水澤之鄉(xiāng)的廣大回族群眾而言,他們的民族習(xí)慣法中鮮有水利灌溉的管理與使用原則的規(guī)定,這是由自然因素所決定的。但對(duì)于聚居于青海和甘肅一帶的回族民眾來(lái)說(shuō),水是極其珍貴的,因此他們的民族習(xí)慣法中出現(xiàn)了大量涉及灌溉及生活用水的習(xí)慣法規(guī)定。由此可見(jiàn),各個(gè)民族的習(xí)慣法在一定程度上都體現(xiàn)著本區(qū)域的自然特色和自然條件。本土性成為考量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一個(gè)重要視角。
(四)形式和內(nèi)容的多樣性
傳統(tǒng)的法學(xué)研究認(rèn)為,少數(shù)民族的習(xí)慣法是不成文的,其實(shí)這是學(xué)界的一個(gè)誤區(qū)。就我國(guó)目前各個(gè)民族的民族習(xí)慣法存在形式而言,雖然大多數(shù)是靠口頭相傳或故事傳說(shuō)等方式而得到延續(xù),但也不乏用文字記載或者制定條文等成文形式而獲得傳承。比如,生活在我國(guó)西南的瑤族群眾,就樂(lè)于用“石牌”的形式記錄他們生活中的習(xí)慣法。所謂“石牌”,就是指把習(xí)慣法用文字的形式刻在石碑上,然后把石碑屹立于村中,便于為村民知曉。而我國(guó)貴州地區(qū)的侗族民眾,則用《約法款》的形式記錄他們的習(xí)慣法。《約法款》的形式主要表現(xiàn)為“款條”,而“款條”又分為兩種形式:款碑條,即一種特定石碑;款詞條,把約法編成歌詞,世代吟唱,口口相傳。至于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涵蓋的生活領(lǐng)域和生活范疇,可謂豐富多彩。就整體而言,大概覆蓋了生產(chǎn)與分配、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債權(quán)、人身權(quán)、婚姻家庭和社會(huì)組織領(lǐng)域等,所調(diào)整的范圍涉及民事、刑事以及事后程序等多個(gè)方面。
總而言之,就我國(guó)現(xiàn)存的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而言,大多與現(xiàn)代化的“國(guó)家法”具有互補(bǔ)性,即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不足之處恰恰構(gòu)成了“國(guó)家法”的優(yōu)勢(shì)特點(diǎn),而“國(guó)家法”的弱點(diǎn)恰恰又成為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過(guò)人之處”。比如,由于國(guó)家法的立法周期較長(zhǎng),因此不能以較快速度覆蓋新出現(xiàn)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但是,對(duì)于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而言,即使出現(xiàn)了新生社會(huì)關(guān)系,它也能內(nèi)化為原理或原則的方式而解決糾紛。在這一點(diǎn)上,習(xí)慣法具有了判例的某些性質(zhì)。再比如,國(guó)家法體系清楚、內(nèi)容確定,它可以很快識(shí)別糾紛,解決爭(zhēng)端。但是,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由于多采用不成文形式,且內(nèi)容瑣碎,因此想要利用民族習(xí)慣法來(lái)快速解決糾紛,是有一定難度的。
三、當(dāng)今社會(huì)中“國(guó)家法”和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互動(dòng)模式
在依照現(xiàn)代社會(huì)制度和現(xiàn)代法律體系所構(gòu)建的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中,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仍然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是在今天仍能發(fā)揮作用的“活法”、“行動(dòng)中的法”。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比照法的形式,參照法的符號(hào),并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群眾的實(shí)際生產(chǎn)生活中產(chǎn)生出法的功效。在我國(guó)廣大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實(shí)際上存在著兩大法律系統(tǒng):一套系統(tǒng)是由現(xiàn)代國(guó)家立法所主導(dǎo)的現(xiàn)代法律秩序,它是一套“顯性”法律體系;另一套則為各種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以及其他鄉(xiāng)土性規(guī)范所組建的“隱形”法律秩序。當(dāng)這兩套不同的話語(yǔ)體系共同匯聚在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區(qū)之時(shí),便會(huì)因其互動(dòng)模式的不同而體現(xiàn)出不同的社會(huì)治理效果。
(一)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與“國(guó)家法”之間的良性互動(dòng)
此種互動(dòng)模式體現(xiàn)在兩個(gè)層面上。第一個(gè)層面即為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與“國(guó)家法”所呈現(xiàn)出的一致性。在這個(gè)層面上,“國(guó)家法”與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可以為社會(huì)治理共同發(fā)揮作用,兩者體現(xiàn)出某種程度上的默契性。第二個(gè)層面則為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對(duì)“國(guó)家法”的補(bǔ)足與優(yōu)化。由于現(xiàn)代性法律所能調(diào)整的社會(huì)領(lǐng)域和社會(huì)范圍是有限的,這就為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留下了足夠的生存空間。在這個(gè)層面中,“國(guó)家法”與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分而治之”,互不打擾,實(shí)現(xiàn)共贏。
1.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與“國(guó)家法”的一致性
作為正式立法的法律淵源之一,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與“國(guó)家法”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親近關(guān)系。這種親近關(guān)系充分體現(xiàn)為習(xí)慣法與“國(guó)家法”的一致性。具體而言,這種一致性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一是目的的一致。現(xiàn)代法治精神的突出特點(diǎn)就是對(duì)于公平正義等基本社會(huì)價(jià)值的追求,由于是隨著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民族國(guó)家而生,所以現(xiàn)代法治所追求的價(jià)值與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所倡導(dǎo)的公平正義精神是吻合的。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雖然產(chǎn)生的歷史已久,但同樣充滿著對(duì)公平與正義等基本價(jià)值的渴望。無(wú)論是活躍在北國(guó)草原地區(qū)的蒙古族的民族習(xí)慣法,還是生活在南海之濱的黎族民眾的民族習(xí)慣法,都不乏諸如懲處犯罪、尊老愛(ài)幼等內(nèi)容,這充分體現(xiàn)出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對(duì)于公平價(jià)值的追求。對(duì)正義和公平的追求,構(gòu)成了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永恒價(jià)值取向。二是內(nèi)容的一致。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形式多樣、內(nèi)容繁多,其中有相當(dāng)部分之內(nèi)容與現(xiàn)代國(guó)家立法具有重合性。例如,我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大概可以劃分為涉及民事婚姻的實(shí)體習(xí)慣法、涉及刑事犯罪的實(shí)體習(xí)慣法、涉及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的實(shí)體習(xí)慣法、涉及糾紛解決的程序習(xí)慣法等。這大體上與現(xiàn)代法律體系中的民法、刑法、經(jīng)濟(jì)法、訴訟法相對(duì)應(yīng)。再就具體內(nèi)容而言,如對(duì)于殺人、強(qiáng)奸等暴力行為,無(wú)論是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還是“國(guó)家法”,都普遍將其定性為嚴(yán)重的犯罪行為,認(rèn)為此種行為嚴(yán)重破壞了社會(huì)秩序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應(yīng)該給予嚴(yán)懲。
2.補(bǔ)足性
伴隨著現(xiàn)代社會(huì)分工的日益細(xì)化和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飛速發(fā)展,對(duì)“法律萬(wàn)能主義”的迷信已經(jīng)被逐漸破除。作為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的理性人,大家普遍認(rèn)識(shí)到法律并不是萬(wàn)能的,法律所能調(diào)整的社會(huì)領(lǐng)域和社會(huì)關(guān)系是極其有限的,諸如情感、友誼等社會(huì)關(guān)系并不適宜用“國(guó)家法”來(lái)予以規(guī)范,即使是“國(guó)家法”對(duì)此種社會(huì)關(guān)系作出硬性規(guī)定,也難以獲得有效執(zhí)行,反而損害“國(guó)家法”的尊嚴(yán)。而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則大不相同,它雖然不具有“國(guó)家法”的外在形式,但由于其根植于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且多為“不成文”的表現(xiàn)形式,所以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反而具有了正統(tǒng)的“國(guó)家法”所不具備的優(yōu)勢(shì),這表現(xiàn)在它具有相當(dāng)程度的靈活性與適應(yīng)性。對(duì)于“國(guó)家法”所不能覆蓋到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和社會(huì)空間,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反而能迅速進(jìn)入,并從中獲得生存機(jī)會(huì)。就這個(gè)角度而言,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在一定程度上對(duì)“國(guó)家法”有著天然的補(bǔ)足性。
(二)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與“國(guó)家法”之間的機(jī)制沖突
1.糾紛解決機(jī)制的沖突
就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guó)家法”而言,審判模式與“國(guó)家法”的適用相匹配,成為當(dāng)今社會(huì)的主要糾紛解決機(jī)制。雖然在“法律多元”思維模式的指導(dǎo)下,現(xiàn)代“國(guó)家法”也逐漸開(kāi)始從其他社會(huì)規(guī)范中借鑒了諸如調(diào)解、仲裁、和解等糾紛解決機(jī)制,并將其統(tǒng)籌為“ADR”(替代性糾紛解決機(jī)制),但我們應(yīng)該看到,這些替代性糾紛解決機(jī)制在現(xiàn)代“國(guó)家法”所營(yíng)造的法律帝國(guó)中,其所發(fā)揮的作用是有限的。比如,這些機(jī)制只適用傳統(tǒng)的民商事法律關(guān)系,而在嚴(yán)重的刑事犯罪領(lǐng)域,“國(guó)家法”仍禁止替代性糾紛解決機(jī)制的進(jìn)入。即便是在允許替代性糾紛解決機(jī)制介入的法律領(lǐng)域,它所發(fā)揮的作用也遠(yuǎn)不及傳統(tǒng)的審判模式。
相比而言,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不但關(guān)注糾紛的有效解決,而且同樣關(guān)注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恢復(fù)。因此,如何用適當(dāng)?shù)姆绞皆诮鉀Q糾紛的同時(shí)又有利于受損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盡快恢復(fù),便成了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所特別關(guān)注的主題。在這樣的視角下,調(diào)解與和解便成為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中所運(yùn)用的主要結(jié)案方式。在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話語(yǔ)邏輯中,調(diào)解與和解不但可以為處理傳統(tǒng)的民事糾紛和民事案件所運(yùn)用,甚至在刑事案件中,也不乏調(diào)解與和解的影子。比如在我國(guó)青海和西藏的廣大藏區(qū),歷史上對(duì)殺人罪實(shí)行的是賠命價(jià)制度,即加害方只需在中間人的斡旋下賠付受害人家屬一定的財(cái)物,案件便可以了解,雙方家族之間的恩怨也將一筆勾銷。
2.實(shí)體內(nèi)容的對(duì)抗
在實(shí)體內(nèi)容上,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與“國(guó)家法”的沖突,無(wú)論在傳統(tǒng)的民事領(lǐng)域,還是在刑事領(lǐng)域,都有所體現(xiàn)。筆者僅從以下三個(gè)方面對(duì)此問(wèn)題進(jìn)行論述。
在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方面,一些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所規(guī)定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主體極其富有特色。在這些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中,一般認(rèn)定集體或者家族作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主體。相反,個(gè)人一般不被認(rèn)定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主體,因此在這些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視野中,個(gè)人也不能單獨(dú)行使財(cái)產(chǎn)的支配權(quán)。這與現(xiàn)代“國(guó)家法”所認(rèn)定和保護(hù)的個(gè)人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在我國(guó)四川涼山地區(qū)的彝族村落中,森林和果樹都被認(rèn)定為整個(gè)村落共同所有,即使是位于自家門前的果樹,也可以供村民隨意采摘食用而不被認(rèn)為是盜竊行為。
在民事婚姻領(lǐng)域,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普遍禁止某些特定家族之間的通婚,并且仍然保留有“近親結(jié)合”的傳統(tǒng),而且對(duì)婚姻成立的實(shí)質(zhì)性條件也有著自己獨(dú)特的規(guī)定,一般只要經(jīng)過(guò)特定的儀式之后,便可認(rèn)為婚姻關(guān)系已經(jīng)締結(jié)。例如,在彝族的習(xí)慣法文化中,白彝與黑彝之間是不允許通婚的,他們之間的婚姻是不被雙方親屬和廣大彝族社會(huì)所接受的,而且,“儀式婚”在廣大彝族地區(qū)仍然普遍存在,只要經(jīng)過(guò)“儀式婚”,婚姻關(guān)系便由此締結(jié),而無(wú)須去國(guó)家民政部門登記[5]121。這與“國(guó)家法”對(duì)于婚姻關(guān)系的種種法律規(guī)定顯然不相符合。
在刑事處罰領(lǐng)域,各個(gè)少數(shù)民族對(duì)于各種嚴(yán)重的刑事犯罪行為的處罰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在廣大的苗族地區(qū),規(guī)定對(duì)于故意殺人者,可以對(duì)其進(jìn)行活埋,被害人家屬也可以對(duì)殺人者本人或者家屬進(jìn)行血性復(fù)仇,并可掠奪其家庭全部財(cái)產(chǎn)而作為對(duì)被害人的補(bǔ)償。由此可見(jiàn),在苗族習(xí)慣法中,對(duì)于殺人行為的處罰不但手段多樣,而且相當(dāng)嚴(yán)厲。這與“國(guó)家法”中對(duì)故意殺人罪的規(guī)定是大為不同的。
四、“國(guó)家法”對(duì)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有效整合
在構(gòu)建現(xiàn)代法治國(guó)家的進(jìn)程中,需要理性處理國(guó)家法和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之間的關(guān)系,這將是一個(gè)復(fù)雜且敏感的過(guò)程。因此,如何在維護(hù)“國(guó)家法”尊嚴(yán)的同時(shí),最大限度地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法”與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之間的良性互動(dòng),有效建構(gòu)二者之間的和諧關(guān)系,將會(huì)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duì)的重大命題。但無(wú)論具體模式如何建構(gòu),我們都應(yīng)該把握好這樣一個(gè)原則:在照顧本土資源的同時(shí),必須堅(jiān)持國(guó)家法制的統(tǒng)一。毫無(wú)疑問(wèn),在現(xiàn)代國(guó)家體系的建構(gòu)中,法律起到了獨(dú)一無(wú)二的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時(shí)期,哲人亞里士多德就對(duì)法治給出了以下定義:“已經(jīng)成立的法律得到大家的普遍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本身必須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6]29。由此可見(jiàn),法律的普遍使用性是法治社會(huì)的必然要求,任何拒絕現(xiàn)代“國(guó)家法”進(jìn)入的方式和手段都是不可取的。但與此同時(shí),現(xiàn)代法治體系的建構(gòu)并不意味著對(duì)本土資源的絕對(duì)否定,對(duì)優(yōu)質(zhì)的本土資源,我們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和尊重,這方為對(duì)待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理性態(tài)度。
(一)“國(guó)家法”通過(guò)立法形式對(duì)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進(jìn)行吸收
在“國(guó)家法”的制定中,有必要對(duì)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中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作出充分且全面的考察,吸取其合理成分,用立法的方式對(duì)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合理內(nèi)容進(jìn)行確認(rèn),給予其法的符號(hào),授予其法的尊嚴(yán)。任何法律制度的存在,都必須有堅(jiān)實(shí)的社會(huì)基礎(chǔ),否則,法律將失去其賴以生存的土壤。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所規(guī)范的內(nèi)容涉及少數(shù)民族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與少數(shù)民族群眾有著天然的親密感,并成為鄉(xiāng)民所遵從的一套傳統(tǒng)話語(yǔ)體系。“國(guó)家法”在傳統(tǒng)的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中獲取資源,有助于拉近與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生活距離,從而最終有效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立法之目的。比如,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中的眾多內(nèi)容涉及日常生活、鄰里關(guān)系等民事關(guān)系,用現(xiàn)代“國(guó)家法”的法律邏輯來(lái)考察的話,這些領(lǐng)域?qū)儆诘湫偷摹八椒ā狈懂牎6椒ㄋ駨牡氖滓瓌t即為意思自治。早在古羅馬時(shí)期,意思自治就被認(rèn)為是私法自治的首要表現(xiàn)。只要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中的這些規(guī)定不違背社會(huì)的公序良俗,不對(duì)國(guó)家利益構(gòu)成危害,就應(yīng)該通過(guò)國(guó)家法的方式對(duì)其進(jìn)行確認(rèn)和整理,以期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法”對(duì)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有效整合,從而構(gòu)建起一套為廣大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群眾所熟知的話語(yǔ)體系。
(二)“國(guó)家法”留給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適當(dāng)?shù)纳婵臻g
對(duì)于不適合現(xiàn)代“國(guó)家法”所調(diào)整的社會(huì)領(lǐng)域和暫時(shí)無(wú)法覆蓋到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國(guó)家應(yīng)認(rèn)可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在這些領(lǐng)域所發(fā)揮的替代性作用,從而留給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一定的生存空間。“法律萬(wàn)能主義”和“法律虛無(wú)主義”作為兩種極端的法律思潮已經(jīng)逐漸被現(xiàn)代社會(huì)所拋棄。對(duì)此,我們應(yīng)該理性地看到,即使在積極構(gòu)建現(xiàn)代法治國(guó)家的話語(yǔ)邏輯下,法律自身的弱點(diǎn)仍難以掩飾。由于“國(guó)家法”的立法周期偏長(zhǎng),對(duì)于日常生活中新出現(xiàn)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和社會(huì)領(lǐng)域,不能進(jìn)行及時(shí)地覆蓋,這就造成了所謂的“時(shí)間差”,即新出現(xiàn)的社會(huì)關(guān)系更加需要法律予以規(guī)范和調(diào)整,但法律對(duì)這些領(lǐng)域的覆蓋卻要等到下個(gè)立法周期才能完成,而下個(gè)立法周期中仍然會(huì)不斷出現(xiàn)新型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如此周而復(fù)始,循環(huán)往復(fù)。這顯然為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生存和發(fā)展留下了剩余空間。我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區(qū),多處于邊遠(yuǎn)地帶,自身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育尚不完善。而我國(guó)的漢族地區(qū),自改革開(kāi)放后經(jīng)過(guò)近40年的發(fā)展,已初步構(gòu)建起相對(duì)完善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系。“國(guó)家法”正是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背景下發(fā)育壯大起來(lái)的,其所覆蓋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也涉及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這就導(dǎo)致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社會(huì)關(guān)系與漢族地區(qū)社會(huì)關(guān)系的“不吻合性”,這種“不吻合性”恰恰為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留下了適用空間。對(duì)于現(xiàn)代法不進(jìn)入或無(wú)法進(jìn)入的社會(huì)領(lǐng)域,可以使用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對(duì)其進(jìn)行調(diào)整,這種情形并不會(huì)破壞國(guó)家法制的統(tǒng)一,也不會(huì)弱化“國(guó)家法”的地位。
(三)“國(guó)家法”應(yīng)借鑒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所倡導(dǎo)的調(diào)解機(jī)制
在法的實(shí)踐層面,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guó)家法”有必要對(duì)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中的糾紛處理機(jī)制進(jìn)行借鑒。在司法和執(zhí)法階段,要根據(jù)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實(shí)際情況,選用合理的處理模式,以便達(dá)到法律效果和社會(huì)效果的統(tǒng)一。具體言之:一是在處理刑事案件時(shí),如果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不認(rèn)為是犯罪,而現(xiàn)代“國(guó)家法”又認(rèn)定為犯罪的,我們需要謹(jǐn)慎處理。因?yàn)椤皣?guó)家法”的強(qiáng)制介入有可能會(huì)損害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不利于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社會(huì)秩序的穩(wěn)定。對(duì)此,筆者認(rèn)為,當(dāng)這種行為不具有顯著的社會(huì)危害性時(shí),“國(guó)家法”可以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zé)任。同理,當(dāng)有些犯罪行為被“國(guó)家法”認(rèn)定為重罪,而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認(rèn)為是輕罪的,則國(guó)家司法機(jī)關(guān)要遵從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處理習(xí)慣,對(duì)犯罪人減輕處罰。當(dāng)然,這種“國(guó)家法”的弱化形式的適用前提是不損害國(guó)家法制的統(tǒng)一。二是注重國(guó)家習(xí)慣法中對(duì)調(diào)解機(jī)制的有效運(yùn)用。調(diào)解作為一種與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相配套的糾紛解決方式,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得到了民眾的普遍認(rèn)可和尊重。與冷冰冰的“國(guó)家法”的審判模式相比,調(diào)解模式顯然溫情了許多。它在處理糾紛、化解矛盾的同時(shí),又不破壞既有社會(huì)的人情關(guān)系,因而在廣大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被廣泛采用。例如,在我國(guó)涼山彝族地區(qū),任何社會(huì)糾紛的解決首先依靠的是“博古”的調(diào)解,這種習(xí)慣在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習(xí)慣法中也多有體現(xiàn)。因此,當(dāng)“國(guó)家法”以強(qiáng)勢(shì)姿態(tài)適用到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時(shí),尤其要善于借鑒這種相對(duì)柔情的糾紛處理機(jī)制,以期在化解糾紛的同時(shí)又不破壞既有的社會(huì)關(guān)系。
總之,通過(guò)整合來(lái)構(gòu)建“國(guó)家法”與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之間的和諧關(guān)系,是在廣大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構(gòu)建社會(huì)主義法治體系的關(guān)鍵步驟。當(dāng)然,整合并不意味著對(duì)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漠視,在整合中解決沖突,在沖突中尋求整合,方為“文化多元”視野下對(duì)待少數(shù)民族習(xí)慣法的理性態(tài)度。
[1]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
[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4.
[3]費(fèi)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1999.
[4]廉睿.現(xiàn)代化背景下的少數(shù)民族發(fā)展[J].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xué)報(bào),2015(3).
[5]高其才.中國(guó)習(xí)慣法論[M].北京: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8.
[6]亞里士多德.政治學(xué)[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3.
【責(zé)任編輯:李維樂(lè)】
2015-07-18
廉睿(1987—),男,山西臨汾人,博士生,主要從事法律政治學(xué)、憲法學(xué)原理研究。
DF2;DF35
A
1672-3600(2015)10-008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