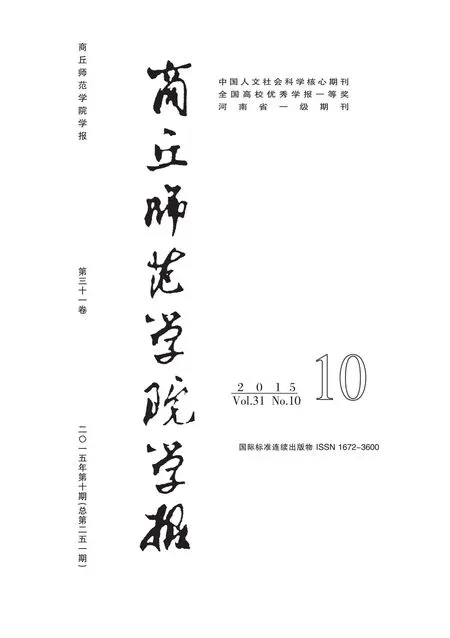論上清道之自然性、非人格性和虛空性
[加]詹姆斯·米勒
(加拿大女王大學 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安大略省 金斯頓市)
論上清道之自然性、非人格性和虛空性
[加]詹姆斯·米勒
(加拿大女王大學 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安大略省 金斯頓市)
作為中國道教獨具特色的一支派系,上清道教從4世紀到14世紀,曾經盛行千年。上清道教宗承襲由四十五代嗣法宗師親自傳授的上清經箓。雖然現今上清道教已鮮見公開的教團組織形式,但它所尊崇的教義已被主流道教傳統融合、吸收并影響至今。所以,它是連接萌發于東漢(25—220)的早期有組織宗教和元代(1279—1368)后逐步形成的各種道教近當代形態的重要紐帶。
上清道教創建自一系列修真得道后法力無邊的“真人”神諭。源自這些“真人”的口授之誥被記錄成文,內容多描述他們所居住的天宮玉闕,那里瑞氣紫霧,金殿銀鑾,琪花瑤草,仙樂飄飄,真人們過著仙童玉女服侍左右、極致奢侈、安逸逍遙的生活。神諭指明眾道士得道升入“上清天”的途徑首先是遵循這些“真人”昭示的修行過程,即存思諸神,神就會安置其身。存神會出現在某個特定的時刻或地點,廣袤神秘宇宙的某種力量會促成人神的感應。
在存思過程中,神再次彰顯其造化力量,將修行道士的肉身轉化成與最初向其呈現天境奇觀的真人一模一樣。道士的身形從此永遠不死,并化成另一種狀態達到永生,白日升天,不留一絲塵世的痕跡。那些無法達到這一境界的道士則死去,但通過真人的救賒,他們會在天庭獲得再生,成為“仙”①。這些“仙人”在天庭獲得一個比“真人”低的階位,從此不必遭受那些因罪孽深重被迫下地獄的人所經歷的苦難。而那些不幸的人將在由天、地和水所構成的三層階系中受到殘暴役吏的百般折磨、審判和懲罰,以此洗刷他們身上累積的罪行,而且他們將永世與朋友及家人分離。在修行道士眼中,這樣的情形是不惜任何代價也要避免的②。
據此可知,上清道教義認為人是居住在介于地球和群集各類超自然力量的天界兩者之間的空間里。在宇宙的級系中,人的地位優于動物界,但在天界之下。鑒于自然法則被視為一種具有造化力量的法則,上清道道士相信宇宙的造化力量可以改變人的根本質性,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從擁有塵世身份的人變成擁有天庭地位的神仙。值得注意的是,不管這種改變是確有其事還是比喻意義上的,這樣的轉化超越了通常所理解的以獻身方式獲得的升天。由于天界也如其他造物主創造出的秩序一樣由同一自然法則管轄,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種轉化并不是一個超自然過程。雖然肉體的升天十分罕見且令人驚嘆,但它仍只是被認為是人的肉身完全自然的轉化。這種轉化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修習道義并立志獻身施行經箓中所記載的詳細修行法術的道教信徒身上。
自然界的神靈
為了更深入理解為何上清道教將神靈齊聚的天庭視為自然界一部分,而非超自然現象,有必要對上清道教進行進一步梳理。理解這一觀念的關鍵在于在西方傳統中,神靈的世界及天堂是超自然的,也就是說,是超越自然法則管轄的。在上清道教中情形卻并非如此:無論是神還是人都受制于同一個自然法則,即“道”。經典的亞伯拉罕宗教教義與上清道正好相反,在他們看來,上帝是超然存在于自然之外的,是上帝創造了自然界的狀態,無論這個自然界是希伯來《圣經》中神圣的“話語”(Word),還是《約翰福音》神學中的“邏各斯”(Logos),抑或是伊斯蘭教中世紀經院哲學的自然哲學。但在道教傳統中,自然界不是神創造的。
更確切地說,自然界其實是人類對自然過程的某種觀察。這樣的觀察為神學想象提供了可參考的模板。因此自然界生物過程和天庭過程兩者間并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割裂。神靈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他們比凡人更能體現自然界生物過程的抽象本質③。
不過,中西關于神學和自然界關系大相徑庭的觀點會導致另一個結論:上清道中的神仙并不具備顯著的人格性。盡管上清道也有諸多化為人形的神,不過它不像希伯來經卷或希臘神話那樣通過神自身的歷史和行為來描述神祇。在歐洲和西亞宗教傳統里,不同的神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他們具有像人一樣的性格特征。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體現人的品質和性格。神可以是慈愛的、公正的、憐憫的、睿智的、忠誠的,也可以是嫉妒的、喜怒無常的、權力強大的和奸詐的。總之,他們是類人的,盡管擁有超人的力量,但他們完好地保持著人的性格特征。在上清道教中,神并非因為與人相似而重要,而是因其與自然相似而變得重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清道教中真人和神仙最顯著的特性是具備類似自然界的非人格性和冷漠無情。神的階位越高,他就變得越抽象、越冷漠和越無人性。道教經書的眾多例子都表明,神絕不是因為慈愛或善良而重要,神的重要性在于他們是“道”的化身,以及他們不得不無情地遵循宇宙的基本法則和運行方式。
要準確理解這一點需要考察上清道中教禮和自然法則的關系。首先要區分道教傳統中兩種明顯不同的觀點,即官僚神學傳統和個人神人相遇觀。上清道教融合了上述兩種觀念。楊曦在描寫最初的神靈啟示時將其描述為類似婚姻一般親密的關系。不過,隨著道教的發展和演變,官僚神學傳統觀念中與神仙相遇方式的觀點逐漸占了上風。本書討論的上清道經文中很清晰地指明道士與神仙相遇是一種正式的、官方的,而不是一種個人的、親密的溝通方式。以下是一則《中央黃老君八道秘言章》所描述的典型例子:
以立春日,正月甲乙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云者,是為太上三元君三素飛云也。其時三元君乘八輿之輪,上詣天皇太帝,子候見是三色云。當心存叩頭自搏,心存四再拜,自陳乞曰:“曾孫某甲,少好道德,修行九真,沐浴五神,并為天帝、帝君所見記錄,今日有幸,遇三元君出游,乞得侍給輪轂。任意祈祝矣。”若三見元君之輿者,則白日升仙,不須復他存思,千百所施為也。八道所行祝拜之辭,亦如此。此所謂八道秘言者矣,非有仙錄者不得聞也。
該段中不少有趣的地方在文中都有很詳細描述。鑒于本文討論目的,有必要指出文中描寫的儀式與宮廷儀式極為相似。此次神人意外相遇的最終目的是道士在青天白日之下升天成仙獲得永生。這一目的是要通過天庭派出“祥云”坐騎將修行道士載回天庭才得以實現。“祥云”坐騎出現的前提條件是道士要有機會與一位階位較高且擁有派出“祥云”坐騎權力的神仙相遇。在這一過程中,道士必須臣服于神仙,用正式的宮廷式語言向神仙祈求,并且相遇的所有細節要正式記錄在案。在上清道經典中有許多經文都反映了類似的宮廷主題。道士向神仙所作的祈求好比臣民向皇帝作的祈求。道士要稱神仙的官銜以示尊敬,這就如同一介平民如想從官員那得到幫助需要畢恭畢敬地尊稱他們一樣。神仙身著華麗的宮廷服飾,居住在奢華宮殿,侍從時刻服侍左右。顯然,上清道教旨是借用進入天界宮廷后變得高貴以及讓道士獲得特定神仙官銜的方式來象征其修煉成仙獲得永生。
從上述分析可清晰看出,上清道的天庭(也即上清天)類似皇家宮廷。神仙就是皇帝,教禮就是宮廷禮儀。如果這一比喻是成立的,那么可以更為合乎情理地認為上清道的世界是一個典型的人類社會,也就是說,是一個人際和社會的世界,而遠非一個充滿自然法則和宇宙力量的世界。事實上,這恰恰是很多道教研究者在嘗試討論《道德經》中自然哲學與道教官僚體系、法治與神仙世界的關系時難以逾越的障礙。在我看來,解決這一難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看待道教中的神仙。如果神仙是類人的,神人的溝通類似人際交往,那么就很難將上清道與《道德經》中的自然法則相聯系。我認為,事實上上清道教正是通過道教官僚神學傳統與自然法則建立直接聯系。隨著道教在中國南方興盛發展,其教義越來越主張將神視為自然力量而不是具有人格特征。
這一觀點不是要低估在上清道仙真告授集如《真誥》中所描寫的與人格化的神親密相遇所起的作用。很顯然,這類個人相見也扮演極其重要角色,因為這類相見有助于推進修行道士死后登升之事的進程,因此可以大致被視為是一種社交和個人的關系。然而,我們不應忽視上清道教義中另一個同等重要方面,那就是從非人格化視角來看待人神相遇,因為正是這類正式相遇才能促成宇宙的全面繁榮興盛。在本書所討論的上清道修行中,即便那種人神間個人的和社會的交往也是為了達到超自然和宇宙的目的,這種目的超越了世俗世界關于生和死的看法④。
首先,看一下肉體升天這一宗教儀式的目的。肉體升天指通過改變人的屬性以達到最終的徹底轉化。盡管這一行為是對質性的根本性改變,但它仍被看做是在自然界內的行為。這種轉化過程與通過精煉和攝入自然物質尋求肉身長生不老的煉丹術傳統密切相關。在這個意義上,升天不是對道德行為的賞賜:不是所有品行高尚的“道德”之人都會得到獎賞升入天庭。
在這里,升天是一種行為結果。這種行為包括與住在天庭的神仙建立密切關系以及祈求獲得許可加入他們的行列。總之,上述段落在描述自然的造化力量時使用了宮廷慣例和程序化語言。換言之,升天的過程不能理解為一種在社會范疇內發生的“自然”意義上的轉化,否則就會對上清道士的行為產生類似涂爾干社會理論式的誤解⑤。在上清道士眼里,宮廷意象是宗教儀式中隱喻化的符號,它所指向的深刻現實是自然的造化力量。在上清道教義中,自然并不象征某些深刻的社會或精神現實,而是通過宮廷意象來象征性地體現其造化的力量⑥。
因此,盡管上清道教禮也關注世俗世界的社會、法律和政治秩序,它更旨在建立一種更高層次的宗教篤信。這種篤信主要建立在永恒不變掌控著人類生死過程的自然力量之上。雖然登升過程的教規教禮與儒家宮廷儀式類似,但很顯然,其最終目的并不體現儒家理念,而是具有濃厚的道教色彩,因為其完整的宗教儀式關注的是人類與自然界力量的互動。
其次,有必要更仔細地考察宮廷場景中對神仙的描寫。在上清道經箓中,關于神仙的描寫是相當詳細的——他們乘著不同座駕,騰云駕霧,身著各式各樣錦緞的艷麗彩袍。顯然,這樣的描寫根本不是個性化的描寫,相反,它們都與神仙的官職有關:這些神仙不是普通個人,他們是官僚。類似地,宮廷式教禮也不是普通個人間的交往,而是一種官府往來的形式。神仙不是用各自的名字來稱呼的,他們也沒有個人居所或者個性特征。他們都擁有官銜,居于各自的官殿,身著官服,處理各自官職范圍內的事務。事實上,即便他們有一些個性特征,他們是誰也無關緊要,唯一關鍵重要的只是他們作為官員的職能。
在這里,神仙與自然的聯系變得更為明顯,因為區分一個人的官員能力和其個人能力的辦法就是看他是否必須被迫依據他作為其中一分子的官僚體系法則行使官員職能。離開了這一體系,他就不具有官員能力,那樣的話,他就僅僅是一個“普通的人”。但正是由于他將自己的個性特征納入了他的官員職能之中,使其成為“無臉譜”(faceless)的人,他才可以不用以“普通人”身份行事,并依此獲得官員能力。
上清道士一般不使用名字稱呼神仙。他們在向神仙祈禱時也不會稱其為“天上的父”,他們是用神仙的官銜比如“天帝”或“元始天尊”稱呼神仙。雖然虔誠宗教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信徒和神之間的親密相會,也就是說,信徒以神的名字稱呼神,見到神的面容,并基于愛確立與神的關系。但是,這恰恰也是上清道教所不推崇的,上清道教所追求的是官府的、正式的神人相遇。道士最不希望見到的是神仙以個人善意和恩惠來行使他們的職責。如果神仙基于隨心所欲或個性特征行使職責,那么整個宇宙就會變化莫測,反復無常。這時,宗教也就無異于其他一些比如賭博前祈求神帶來好運這樣頗受歡迎的民間信仰了。沒錯,在上清道教中,神仙們是超越人類的,但他們很大程度上屬于非人格化的、無個性的以及無感情的超人類群體。他們不像佛教中完全個性化的菩薩,不會基于同情和憐憫,對終有一死痛苦不已的人類施展法力。
再仔細研讀一下在上述引用段落中道士祈求“遂愿”的方式。他沒有請求神仙垂憫或給予特殊待遇。他僅僅是請求神仙看到他已經做了要求做的事情:他已經修煉身形,凈化心靈,并且時刻存思。他之所以作出如此請求的基礎是他取得了正式資格,并得到了合法的獲得永生的認可。這種請求不是祈求神靈給予恩惠,而是祈求神靈看到并且肯定道士行為的合法性。在升天過程中,神仙是別無選擇的,因為他只是作為天庭仙官在一定范圍內行使他的官職而已。他不得不滿足道士的要求,因為那樣的要求是依據法定提出的。不過,不像世俗世界官僚只能執行代表統治階級意志或者民主體制中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天庭體系中仙官執行的是“道”的法則。這一法則不代表神仙的意志,而是一種自然法則。自然法則是宇宙力量的體系,正是這一體系管轄著道教信徒和天庭之間的一切事務。
這里我們看到了中國神學和西亞神學的本質差別。在西亞神學體系中,《圣經》和《可蘭經》中的神通過自己的意志體現其神圣力量。在《舊約》的前五卷律法中,神之所以選擇成為以色列人的神,僅僅是因為他選擇了他們,然后頒布了相應律法。以色列人因此有幸成為神的子民。作為回報,以色列人必須遵守這些律法。在《可蘭經》中,信徒也必須嚴格服從神的意志,通常這些意志由神通過啟示口授給先知。然而,在上清道教中并不存在類似的自愿主義(voluntarism)⑦。上清道教中有律法,但沒有律法制定者;有創造,但沒有造物主。因此,在這樣的一個體系中,盡管神靈可能擁有人的外貌并且以一種正式的交往方式與人類溝通,但管轄神靈的深層法則不是人格或人道,而是非人格性的宇宙體系中的自然法則。
如前所述,這種“非人格性”還未能全面描述上清道傳統教義中的人神相會⑧。上清道綜合了中國南方各類宗教教義,包括道教對自然和官僚神學的看法,因此也融合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修行方法。但是,在歷史發展中演變而成的道教融合體系中,非人格官僚傳統一直占據主導地位。那種親密的神人相遇,比如楊曦與上清道神仙的相遇本身并不具有精神上的終極意義。至上清道宗師朱自英(976-1029)為《上清大洞真經》作序之時,這一官僚體系觀念已經深深根植于道教非人格玄學理論之中。
通過使用一整套復雜的宮廷禮儀和法定語言,上清道教達到了與宇宙的重要力量溝通以及在宇宙力量范圍內發生轉化的目的。不過,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首先需要確立相應宇宙觀,即宇宙的力量依據某種法則或原理來運轉;其次,宇宙法則自身應包括人類世界與宇宙相互溝通或關聯的概念。如果說使用法定語言的原則有助于增加與宇宙終極力量有效相遇的可能性——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力量傾向于對人類活動作出回應;那么,使用宮廷禮儀的原則有利于建構與宇宙各種力量的相會場景。這樣的場景不是類似松散的民間信仰那種臨時性的活動,而是一種程序化的、系統的會見場合。
上述兩種原則構成了上清道教禮產生的條件和基礎。也就是說,它們形成了道教與神仙相會時通用的宗教禮儀。上清道教禮嚴格規定了道士和神仙之間通靈溝通的基本禮儀或規范。這類交流溝通是一種正式的相會。教禮的正式性或者說程序化的屬性是極為重要的概念,因為它確保了神仙的人格特征與靈性轉化過程是完全不相干的。這一主張與近現代西方宗教“人格靈性”觀點正好相反。在西方傳統中,個體的信仰和道德情感是成功宗教生活之關鍵。但對于上清道教而言,個體的信仰和感情從屬于系統化的各式教禮力量。這些教禮的具體屬性會在后面的行文中討論,目前我們關注的是這一觀點如何揭示了上清道對于自然概念的理解。
上清道關于“自然儀式”的觀點并不是將自然看做各類物體集合體,而是各種力量的聚合體,這些力量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或“道”施加影響。早些時候已經討論過液體和固體的關系。道教一般都認為流動性是自然界得以形成的基礎。這一基礎通過兩分的節奏即陰和陽來運作。陰陽即一種永恒不變的相互作用,其概念可追溯至中國古代周朝《易經》一書。基于這一設想,宗教儀式就可以被視為一種宇宙萬物之間流動性溝通的途徑。但陰陽概念為何是自然界流動性中至關重要的方面呢?《黃帝內經·素問》中關于陰陽的闡述有助于理解這一兩分法。
“故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
以上引文表明,陰和陽既不是物體,也不是力量,而是活動的方式。文中把“陽”解釋為“萌動”,而陰是“靜止”,意思是當我們考察行為動態性時通常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動態,即從外部施加影響或力量;一種是靜態,即接受外部的影響并將其內在地吸收。靜態在這里并不是說完全停止,相反它指的是沒有外部力量作用。當某物處于“陰”時它就進行自我完善,這時的“自我完善”指的是吸收和加工接收到的外部影響。
當人們扔一塊石子到池塘,泛起的漣漪就是水對石頭的回應,這就是“動態”,就是“陽”。隨著時間推移,漣漪平息,水又回到了原先的常規狀態,這就是“陰”。我們也可以通過呼吸來觀察陰和陽。陽是呼氣或吐氣,陰是吸氣或者吸入。陽(即呼氣)的本質是化生,陰(吸氣)的本質是構成形體。將陰與陽相結合就能看出自然界是一種動態過程,即各類影響或外力源源不斷地被向外排出和向內收納。這種持續過程或者說能量的互換就產生自然界,也就是變化旋轉的流動世界。自然界因此可以看做是回應溝通和化生,這就類似官僚道教傳統中神仙和道士通靈相遇時的宗教儀式。
由于自然具有可視性且是持續動態轉換的結果,這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在上清道世界中溝通的重要性。沒有溝通——即施加影響和接受影響的機制——那就沒有動態性可言。沒有動態性,就沒有生命。從這一定義出發,生命就可以理解為一種轉化,即互相溝通的物體之間不間斷的能量運動以及通過這一過程發生的形體轉化。
此外,對于上清道士而言,自然之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所構成的任何特殊形體,即任何具體有形的物體,而在于有形物體內及不同有形物體之間的空間。換言之,是施加和接受影響的不同方式及相互轉化的媒介促成了自然界的動態性。也就是說,存在于物體之間的空間使溝通和轉化成為可能。沒有空間,就只有內在的運動,或者“僵體”(dead stuff)。有了空間,就有了溝通、交互和轉化的可能。
虛空的自然界
在考察上清道自然哲學時,我們需要將視角從普通現象界透過隱藏的溝通渠道最終聚焦于宇宙轉化力量的核心,也就是“道”。貫穿上清道經典的一個不斷重復的主題就是將虛或虛空作為轉化發生的處所。例如,上清道紫陽真人周義山登真獲得仙界官銜時曾宣講:
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也。山腹中空虛,是為洞庭。人頭中空虛,是為洞房。是以真人處天、處山、處人,入無間,以黍米容蓬萊山,包括六合,天地不能載焉。
這一宣教表明,空間屬性以及“無”與“虛”的關系是成為真人后首要關注的問題。佛教玄學從本體論和心理學角度看待“虛”,但上清道玄學教義中的“虛”更關注空間具有的存在和處所兩種屬性。天界、山岳和人體的空間都是相似的。它們都具有相同的“無”的特性,而真人即居于“無”之中。
因此,紫陽真人對“道”的體悟即是與“無”的相遇,而這種相遇是在“虛”中發生的。山的空虛使他有幸遇到了為其親授秘要經文的神仙,身體的空間則讓他看到鎮守身體各部位的神。道教的“無”或“虛空”的本質就是它無處不在,或正如經文所記載:“以黍米容蓬萊山,包括六合,天地不能載焉。”因此,虛空是一種相互連接的空間,它促成了宇宙萬物溝通交互并最終發生轉化。
在《上清大洞真經》序言中有針對虛空創造屬性之重要性的論述。盡管序言的大部分是對道與神諭關系的哲學反思,但其首段就對虛無的重要性展開了論述:
夫道生于無,潛眾靈而莫測;神凝于虛,妙萬變而無方,杳冥有精而泰定發光,太玄無際而致虛守靜,是之謂大洞者歟。
該序言為上清教派第二十三代宗師朱自英親自撰寫,他用三個關鍵特征來定義“道”:無(nonbeing)、虛(emptiness)和玄(mystery)。理解這三個意象是很重要的。在某種意義上,朱自英用這三個意象表明虛空性是自然界萬物的本原。
為人所熟知的道教虛空性概念源自《道德經》,其第11章提供了關于“無”的最廣為人知和全面的描述: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這些意象都指向虛空和裝載物體的關系。物體的形狀,也就是它的“作用”取決于虛空的部分。不過,漢斯·喬治·穆勒(Hans-Georg Moeller)指出,這一“結構模型”取決于包圍的概念,即環繞著虛空部分的某種有形物體。這就在比喻意義上指出了“旋轉”的概念。有形物體實際或者比喻性地包圍或繞著虛空部分旋轉。借用車輪的意象可清晰地解釋這一點:輻條圍繞著中空的車轂“旋轉”。在器皿中,黏土圍繞著拉坯輪“旋轉”,而在房屋中是墻壁圍繞著虛空部分“旋轉”。
穆勒在中國學者龐樸(1995)論述基礎上討論了宇宙論的術語“玄”。傳統上人們把“玄”解釋為“神秘”或“奧妙”。龐樸認為這一術語最初是指“旋轉”,這可以從其漢字字形中很形象地看出來。如果這一詞語用于描述水向下旋轉的漩渦就指的是“暗處或隱藏的深淵”。將這兩種見解綜合起來,我們就可以逐漸看到道的本原類似某種呈向下趨勢緩慢旋轉的虛空(swirling void),圍繞著虛空之處就衍化出世間萬物。
參照朱自英有關玄學的論述,可以大致從三個維度解讀這種“旋轉的虛空”。第一,道是“體”,即“有”(being)是建立在圍繞著“無”(nonbeing)的旋轉之上。一切存在的“有”都以本體“無”的存在作為前提。
第二,這種本體的“無”(absence)包含了一個處所的“虛”(emptiness)。也就是說,“無”包含了宇宙中虛空所體現的具體的“形”。在上清道教中,這些“虛空”是神仙們用來溝通的媒介。神仙居住在這些“真空”之中,而宇宙中暗藏的力量就在各種空隙、空洞以及大腦空腔中施展它們的造化能力。沒有“虛空”,就沒有生機勃勃,就不會產生靈性的轉化和創造。
第三,有與無關系、實與虛關系被稱為道的“太玄”(great mystery)或“巨大的宇宙旋轉”(vast cosmic swirling)。“太玄”將平靜與壯麗,黑暗與光明歸為一體,這也就是朱自英所使用的術語“大洞”(Great Grotto)或“大彌漫”(Vast Pervasion)的含義。這種彌漫包容了一切的“形”:所有的“有”都是建立在同一的“無”之上,所有的“實”都是建立在同一的“虛”之上,所有的“形”都是建立在同一的“空”之上。虛空包含所有的“有”,并將它們一起組成“太玄”,即深不可測的、旋轉的、虛空的“道”。因此,道是宇宙的本原,是一切“有”參與的“空”,形形色色的宇宙萬物在其中不斷交換能量和孕育轉化。
(本文系詹姆斯·米勒節選其著作《上清道:中古中國的自然、存思及神諭》。)
注 釋:
①在道教傳統中,術語“仙”(immortal)的具體含義在不同的宗教運動和歷史時期出現過較大爭議。在本書所論及的上清道經文中,該術語主要從等級森嚴天界中不同類別的“仙人”的階位角度出發討論,“仙”一般被認為等級次于“真人”。
② 不同于道教天師派特別詳細闡述地獄的功能,許多上清道經書更多強調天庭生活的益處(見羅賓奈特,1984:1.66)。關于中古中國早期來世觀念演化以及它們與佛教死亡和轉世概念關系的詳盡討論可參見伯肯坎姆(2007)。
③這有助于解釋為何與基督教《圣經》中的《創世紀》或《吉爾伽美什史詩》不同,道教從未產生一種強大的創世紀的敘事經典。鑒于神靈不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之外或超越自然界過程,因此,道教認為沒有必要去解釋神靈如何創造自然世界。出于這一原因,很多人在討論“道”——宇宙的最終創造過程時,都把“道”視為一種內在的過程,而不是一種超然的過程,由此與西方宗教傳統中超自然的神形成鮮明的對照。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說,所謂的超然性和內在性是不適用于解釋道教的宇宙概念的,因為這類表述本身暗示了有某物存在于自然界之外或超越自然界。甚至說“道”的屬性是內在的也暗含著“道”與自然界的差異。這類觀點在道教的概念體系中是無法接受的。
④對上清道教中的社會世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伯肯坎姆(2007)。
⑤為進一步解釋這一概念有必要區分道教儀式和儒家儀式。在中國傳統中,儒家宮廷儀式一直占據重要地位。對于儒家儀式的理論家,比如荀子,人類文明世界最重要的是社會的習俗約定。人類交往是通過語言和文化進行的,而語言和文化的方式是完全任意的和獨立于自然力量及趨勢的。荀子曾使用無論人們祈禱與否雨都會下的現象清晰地例證這一點。也就是說,在荀子看來,宗教世界和儀式是絕對不同于自然法則的。在這方面,他的觀點與近代歐洲神學家一致,他們認為上帝的護佑和慈愛不是因為要對人類救贖歷史進行某種干預,而是因為上帝安排了宇宙的法則使得人類繁衍興盛。因此,在荀子的觀點中,宗教和宮廷儀式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影響了天界讓其更能滿足人類的特別需求,而是因為它以一種卓有成效的方式將人類社會連接在一起。在這個方面,他的觀點可以與涂爾干主義相比較,對于涂爾干理論而言,宗教的最終對象不是一般認定的神或神祇,而是人類社會自身。
⑥此處引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何上清道的道士認為有必要用這些術語建構和幻想他們最終的宗教目的呢?答案需要從上清道道士的社會歷史現實世界中尋找。
⑦事實上,如果擁有個人意志是神性定義的一個必要條件,那么在上清道教中我們并不是在討論神,也就是說,“神學”這一概念并不適用。然而,這種對神強烈的人格主義和自愿主義的解讀并不是唯一一個解讀諸神,尤其是亞伯拉罕的神的方法。兩者的差異在于,盡管自愿主義在西亞神學中是合法的神學選擇,在上清道教中卻完全不是這樣。
⑧關于上清道教的通靈更多屬于親密神人相會的規范之討論,可參見卡羅爾(1996)和伯肯坎姆(1996).
[1]Bokenkamp, Stephen R.1996.“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 [C]//InReligionsofChinainPractice, edited by Donald S.Lopez, J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179.
[2]2007.AncestorsandAnxiety:DaoismandtheBirthofRebirthinChin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Miller, James.2008.TheWayofHighestClarity:Nature,VisionandRevelationinMedievalChina[M].Magdalena, NM: Three Pines Press.
[4]Moeller, Hans-Georg.2007.Daodejing(Laozi):ACompleteTranslationandCommentary[M].Chicago and La Salle, I⒏L: Open Court.
[5]Pang Pu 龐樸.1995.“Tan xuan” .談玄 [Discussing Mystery].inYifenweisan:Zhongguochuantongsixiangkaoshi[M] .一分為三:中國傳統思想考釋 [One Becomes Three: Examin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henzhen: Haitian Press:284-294.
(譯者:梁燕華,廣西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留英博士。)
【責任編輯:高建立】
2015-06-28
詹姆斯·米勒,加拿大女王大學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研究專家。
B956
A
1672-3600(2015)10-0032-06
——自然界動物們的大遷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