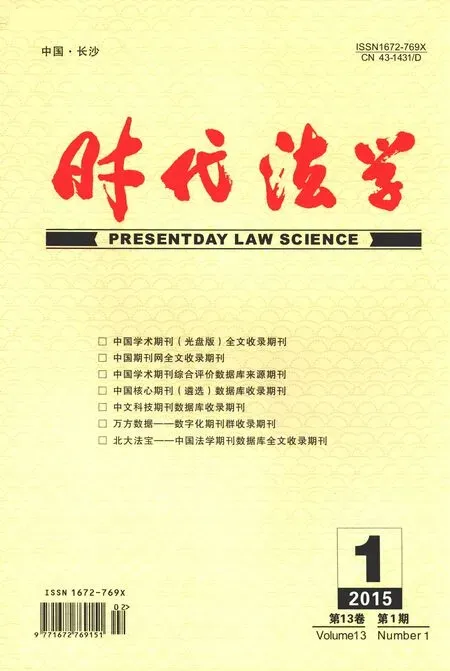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
朱學磊
(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1)
引言:當“權利時代”遭遇“管制時代”
進入21世紀以后,伴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越來越多的公民開始敢于主張自己的權利。受教育權、勞動權、人格權等傳統上不受重視的權利,在公民權利譜系中的地位逐漸得到提升①例如,近年來國家對隨遷子女異地高考的回應,《勞動合同法》的制定和實施以及國家對公民隱私權等人格權保護措施的加強等,都表明傳統上不被重視的公民基本權利正在從理論轉化為現實。。因此,有學者描述我們正處在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②夏勇.走向權利的時代[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而另一方面,隨著“風險社會”的來臨③[德]烏爾里希·貝克.從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上)(下)[J].王武龍編譯.馬克思主義理想與現實,2003,(3)(5).、社會資源短缺以及法律面對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的滯后性,越來越多的領域需要政府進行必要的管制。所以,當下又是一個“走向管制的時代”。當不斷膨脹的公民權利與無處不在的政府管制行為在同一時空下相遇時,必定會發生關于二者的“矛盾之爭”。
管制性征收正是這種“矛盾之爭”在公民財產權領域的集中體現。為了維持社會正常運轉,政府需要利用自身擁有的警察權對經濟社會諸領域進行管制。當政府的管制行為超過必要的“度”時,就可能形成對公民財產權的不適當限制,構成應予補償的征收行為。在這種情形下,公民可以根據法律的規定針對政府管制行為提起訴訟,從而發動一個“自下而上”的征收行為。所謂請求權基礎,是指“可供支持一方當事人得向他方當事人有所主張的法律規范”④王澤鑒.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50.,它在本質上是一種思維分析方法,通過這種方法可以避免我們在具體案例中圍繞空洞的概念進行討論,從而使得法律的適用變成一個有跡可循的過程。請求權基礎對于公民是否能夠在管制性征收案件中得到法律救濟具有決定意義。本文通過界定管制性征收的概念并指出其作為“反向征收”的基本特征,試圖說明請求權基礎對于管制性征收的重要意義,最后結合美國與德國在管制性征收請求權基礎上的法律規定與司法實踐,探討我國現行法律中存在的有關管制性征收請求權基礎的相關規定。
一、管制性征收的出現和發展
一般認為,“管制性征收(regulatory taking)”概念起源于美國1922年的“賓夕法尼亞煤炭公司訴馬洪”案(以下簡稱“馬洪案”)⑤Pennsylvania Coal Company v.Mathon,260 U.S.393(1922).。該案被認為是確立“管制性征收”制度的“奠基之作”。在本案中,對于同一塊地皮,被告馬洪根據合同擁有對地表以及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權,而原告賓夕法尼亞煤炭公司擁有開采其地下無煙煤的權利。賓州政府于1921年頒布實施《柯爾勒法案》(Kohler Act),根據該法案,如果挖掘無煙煤可能導致地表的塌陷,那么這種挖掘開采行為將被禁止。因此,馬洪主張煤炭公司的權利在事實上已經不存在。賓夕法尼亞煤炭公司最終將案件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這一法案實際上是對本公司所擁有合法財產權利的征收,并要求獲得公正補償⑥Ibid.,at412.。
霍姆斯大法官傳達的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認為:首先,為了促進和保證公共利益,政府擁有規范和管制社會經濟活動的“警察權”(police power);其次,個人擁有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權利,但這種權利有一種隱含的限制(implied limitation),并且須服從于警察權;最后,當州政府行使警察權對個人權利進行管制時,需要保證因此造成的公民財產權利的縮減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一般認為,公民個人權利需要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管制,但如果政府的管制行為走的太遠(goes too far),那么就可能構成對公民財產的征收。”⑦Ibid.,at415.
通過這個并不復雜的案例可以看出,所謂“管制性征收”是指政府在對經濟和社會進行調整和管制的過程中,因為管制行為過分限制了公民的財產權,導致公民經過訴訟程序自下而上發動的一種征收形式。管制性征收在本質上是一種征收行為,但是這種征收行為在被法院判決認定之前,是以政府合法管制的形式出現的。在法院判決宣告之前,這種行為是合法的、無需向公民提供補償的;在法院判決宣告之后,這種行為則有可能被認定構成法律上的征收,需要向公民作出補償。
管制性征收的概念起源于美國,但其所指代的具體現象卻是在不同國家都存在的普遍性問題。隨著我國對社會主義公有制認識的不斷深入,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與保護公民合法財產收入之間的矛盾逐漸被消解⑧李惠斌.重讀《共產黨宣言》——對馬克思關于“私有制”、“公有制”以及“個人所有制”問題的重新解讀[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8,(3).。財產權作為一項公民基本權利的地位也得到了憲法和法律的認可。根據我國2004年修正以后的憲法第13條之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此后,國內學術界對于“征收”、“征用”等問題的探討逐漸升溫。但是,由于管制性征收的出現依賴于公民自下而上發動訴訟程序,而請求權基礎的缺失又導致公民很難成功發動此類程序,因此它并未成為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只是到了最近幾年,“對財產權的過度限制”作為管制性征收問題的“中國形式”,才引起學者零星的重視⑨董彪.論財產權過度限制的損失補償制度[J].當代法學,2009,(3);張卉林.論我國的所有權過度限制及立法改進[J].法學論壇,2013,(3);劉連泰.確定“管制性征收”的坐標系[J].法治研究,2014,(3).。但是實際上,管制性征收問題在我國已經廣泛存在于社會生活中的多個領域⑩例如,以2003年湖南省長沙市頒布《長沙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城區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為起點,全國多個城市開啟了一場“禁摩運動”,這場運動事實上導致許多合法擁有摩托車的市民無法上路而失去摩托車基本價值,因此有構成管制性征收的嫌疑;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對車輛限行的管制措施也曾引發關于此行為是否是對公民財產變相征收的討論。此外,我國在文物古跡保護、土地規劃利用以及治安管制等領域,均不同程度存在對公民財產過分限制的問題。參見房紹坤,王紹平.公益征收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47-51.。因此,認識和理解管制性征收的基本問題,明確作為其請求權基礎的相關法律規定,對于完善公民權利救濟途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作為“反向征收”的管制性征收
與傳統的征收方式相比,管制性征收的最大特點在于它是由公民“自下而上”發動的,因此也被稱為“反向征收”(inverse condemnation)[11]房紹坤,王紹平.公益征收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31.。在一個完整的管制性征收案例中,政府首先基于自身享有的警察權對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進行管制,作為相對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政府的管制行為超過了必要的限度而形成對自己財產的過分限制,在無法從政府那里得到公正補償的條件下,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向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對政府管制行為的合法性與合憲性進行審查;如果法院經審查后認定政府管制行為缺乏法律依據或者不具有合理性,那么將判定政府行為構成應付補償的征收行為,此時政府管制行為就可以被稱為管制性征收。
從上述管制性征收的發生軌跡來看,請求權基礎對于管制性征收的發生以及公民面對管制性征收的權利救濟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在請求權基礎缺失的情況下,政府的管制行為始終是單向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無法依法提起訴訟而只能被動接受政府的管制,政府管制將被默認為是正常的管理行為,是合法的、無需補償的,此時管制性征收就不可能發生;另一方面,沒有請求權基礎,也意味著公民無法通過司法部門維權,因為在缺乏法律明文規定的條件下,我國法院很難認定相對人具有提起訴訟的資格,更遑論判決政府管制行為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明確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具有保證政府管制行為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以及保護公民財產權的雙重意義。
在管制性征收案例中,政府的管制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以議會立法方式進行,本文將其稱為“立法型管制性征收”。第二種是以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包括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的方式進行,本文將其稱為“行政型管制性征收”。因此,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既要針對議會立法,也要針對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只有如此,才能為公民財產權提供最全面的保護。
三、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美國與德國的經驗
相比較法治發達國家,管制性征收目前在中國還是一個新問題,我們對于管制性征收的認識和理解仍處在剛起步的階段。因此,參照美國與德國這兩個不同法系的代表性國家在管制性征收請求權基礎問題上的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既有助于完善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也可以為我國處理管制性征收相關問題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
(一)美國:“正當程序條款”、“征收條款”抑或其他
傳統上,美國法院審查政府征收行為的法律依據有兩條:一是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序條款”——“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二是同屬第五修正案的“征收條款”——“非有恰當補償,不得將私有財產充做公用”。正當程序條款——主要是作為其理論分支的“實體性正當程序”理論,主要被用來判斷政府行為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等理念[12]張千帆.西方憲政體系(上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267-270.,違反該條款的法案可能被法院直接宣告無效;征收條款并不解決政府法案是否違法、違憲的問題——法院在根據該條款作審理案件時,往往已經預設了政府管制法案的有效性[13]張千帆.“公共利益”的困境與出路——美國公用征收條款的憲法解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法學,2005,(5).,并主要解決政府是否需要賠償的問題。
在理論上,“正當程序條款”和“征收條款”分別作為公民的請求權基礎似乎具有合理性,公民既可以依據前者請求法院確認政府行為因違反基本的公平正義理念而無效,也可以依據后者請求法院要求政府作出補償。但是,隨著“實體性正當程序”在美國的沉浮和管制性征收理論的崛起,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問題在美國學界和法院內部曾引起較大爭論。
“經濟正當程序”曾在20世紀40年代之前成為法院審查政府管制行為主要標準[14]Lochner v.New York,198 U.S.45(1905).,但這一理論被聯邦最高法院在“西濱旅社案”中放棄[15]West Coast Hotel Co.V.Parrish ,300 U.S.379(1937).。之后,管制性征收理論崛起,并逐漸將“正當程序條款”和“征收條款”融合在一起,審查政府管制行為的合憲性。但是這種融合似乎造成了一種混亂:它要求法院在審查政府行為時采用比實體性正當程序更加嚴格的標準,使得法院成為居于議會之上的“二次立法機關”——而這正是“新政”之后法院所力圖避免的現象,也是實體性正當程序被放棄的根本原因。針對這種指責,有學者認為,將正當程序條款和征收條款融合在管制性征收理論之下并無不可。理由在于: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是針對聯邦而非各州政府的,它只有經過第14修正案的“吸收”才能將“征收條款”的規定適用于各州,因此這種“吸收”勢必會造成“征收條款”與“正當程序條款”的融合;再者,這種融合也有利于為公民財產提供保護。因為,在征收條款之下,即便法案被認定為無效,公民仍然可以獲得補償[16]First Lutheran Church v.Los Angeles County,482 U.S.304(1987).。然而,這似乎同樣對法院的角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必須能夠“因時而動”,非常清楚地知道何時應該維持政府法案而要求補償,何時應該徑直宣布政府法案違憲。因此,支持將二者融合的學者,仍然要求法院發揮較強的司法能動性,并沒有真正回應批評者所指出的上述問題。
由于“洛克納時代”留下的慘痛教訓,法院成為各種爭議的核心與焦點,這讓其在管制性征收問題的判斷上顯得頗為尷尬。而在聯邦最高法院最近的判例中,法院似乎也正有意識地弱化自己在這場爭論中的角色。它所采取的策略,就是一方面回到比實體性正當程序更為古老的“合憲性推定原則”那里去,給予政府管制法案盡可能的尊重——除非它犯有如此明顯的錯誤以至于法院對其審查不會引起任何異議;另一方面,則將審查的重點放在公民財產權受到的不利影響上,為公民財產權提供更多的保護。如此一來,法院在面對管制性征收問題時,其理想的路徑選擇便是首先基于“合憲性推定原則”尊重政府的管制措施,然后根據其在司法實踐中發展出具體判斷標準[17]奧康納大法官曾在“琳格爾訴美國雪鐵龍有限公司案”中詳細討論了自“馬洪案”以來美國關于管制性征收的判斷標準之發展,See Linda v.Chevron U.S.A.Inc,544 U.S.528(2005).劉連泰.確定“管制性征收”的坐標系[J].法治研究,2014,(3).,考察公民受到的損失,最后做出政府是否需要補償的決定。
最高法院的這種政策選擇是否意味著公民只能放棄“正當程序條款”而依據“征收條款”請求補償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首先,法院的政策選擇并不能剝奪公民獲得救濟的權利;再者,“合憲性推定”原則也并非意味著法院在任何時候都不對政府管制法案的合憲性進行審查。因此,公民在提起訴訟時,既可以依據“正當程序條款”也可以依據“征收條款”請求法院進行司法審查。
1)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高于城市。據“五普”、“六普”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安康市農村、鎮出生人口性別比遠遠高于城市(表2)。從人口普查數據斷定,20世紀80年代以來安康市出生人口性別失衡主要表現在農村出生人口性別的失衡,即農村男性人口數量遠遠超過女性。而當年出生的人口到現今都已到了婚配時期,由于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而導致的農村男青年婚戀困難問題也日漸凸顯。
(二)德國:公民請求撤銷還是請求賠償
德國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問題是和其對征收概念的界定緊密聯系的,而德國對征收概念的界定,與其《基本法》第14條第3款的規定相關。該款規定:只有為了實現公共福祉才可允許剝奪財產權。對財產權的剝奪只能通過和依據規定了財產補償方式和程度的法律進行……[18]孫謙,韓大元.世界各國憲法·歐洲卷[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180.。該條款被國內學者稱為“一攬子條款”或“唇齒條款”[19][德]漢斯·J.沃爾夫,奧托·巴霍夫,羅爾夫·施托貝爾.行政法(第二卷)[M].高家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407.,它對征收概念進行了規范界定:征收只能依法進行,且法律在規定征收同時必須規定補償。這意味著,德國法中的征收,只能是“依法征收”。因此,征收只能通過法律(合法征收)或根據某項法律(行政征收)才能進行,這些法律也規定了補償的方式與程度。當有關的征收法律沒有規范補償,或者當它所確定的補償與《基本法》第14條第3款的規定不符時,那么它就是違憲的法律,法官也無權將其作為有效力的法律來適用,或者通過某項充分的補償措施來彌補其缺陷。法官的主要義務是依照基本法第100條將案件上交至聯邦憲政法院處理[20][德]康德拉·黑塞.聯邦德國憲法綱要[M].李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353.。然而,這一原則的發展也并非順利,它是在德國聯邦普通法院與憲政法院的“交鋒”過程中被確立的。
在德國聯邦普通法院看來,管制性征收一類的行為,可以被稱為“準征收侵害”[21][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總論[M].高家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69.672.,此類行為可以適用《基本法》第14條第3款的規定,將其視為征收而給予補償。同時,聯邦普通法院并沒有否認當事人可以基于法律違憲而提出撤銷法律的請求權。因此,對于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問題,聯邦普通法院的觀點是,《基本法》第14條第3款可以作為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公民有選擇權,可以依據該條款的規定,請求法院撤銷這種財產侵害行為,也可以選擇接受這種行為,然后起訴并要求補償。
聯邦普通法院的這種觀點在“水砂判決”中遭到了聯邦憲政法院的批評和反對。水砂判決的基本案情是:原審原告在其不動產范圍內經營采砂,因為工地位于一個水利設施的保護區內,可能危及地下水,原告為采砂所需要的水法許可申請被駁回。原告以征收性侵害為由要求賠償,聯邦普通法院后將案件移送至聯邦憲法法院。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基本法》第14條第3款之規定只能被適用于征收行為,如果沒有補償規則,設定征收的法律就是違憲的,以其為依據采取的征收措施也是違法的。因此,該條款不能被適用于所謂的“準征收侵害”,原告只能訴請法院撤銷征收行為,并不存在請求撤銷和補償之間的選擇權問題[22][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總論[M].高家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69.672.。該判決明確了征收性侵害補償制度之適用范圍的幾個標準。“準征收侵害”不包括規范性違法——即有關財產內容和范圍限制的法律規定違反過度禁止的要求,實際上具有征收的效果,但不構成《基本法》第14條第3款規定意義上的征收。在這種情況下,聯邦普通法院不得以補償的方式彌補法機關懈怠的錯誤,公民應當選擇訴諸憲法申訴[23][德]漢斯·J.沃爾夫,奧托·巴霍夫,羅爾夫·施托貝爾.行政法(第二卷)[M].高家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423-424.。
由此,在“水砂判決”之后,對于德國的財產所有人來說,在一個可能涉及管制性征收的案件中,他(她)只能發起針對管制法案或者管制行為的憲政申訴,以達到使其因違憲而無效的效果,而無法直接請求法院認定政府行為構成對自己財產的征收并進而要求補償。
(三)美、德管制性征收請求權基礎之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美國,公民至少可以依據“正當程序條款”和“征收條款”,請求法院確認政府管制行為構成對財產的征收,進而要求政府補償;在德國,如果公民對政府管制行為有異議,認為構成對自己財產的征收,那么只能向法院請求撤銷該管制法案,并不能直接起訴要求補償。美國與德國的這一差異根源在于兩國對“征收”概念的不同界定,具體表現為兩國的憲法規范對征收的不同規定。
在1875年的“科爾訴美國案”之后[24]Kohl v.United States,91 U.S.367.,美國聯邦政府獲得了廣泛、獨立的征收權。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只有征收行為才應該支付補償[25]張千帆.“公共利益”的困境與出路——美國公用征收條款的憲法解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法學,2005,(5).,但是美國憲法中的征收概念遠沒有德國《基本法》中征收概念的規范性強。因此,美國憲法的這種表述這并非意味著補償條款成為決定政府法案是否構成征收的條件。在一些沒有補償條款的法案中,法院同樣可能依據“征收條款”將政府管制法案定性為征收行為。由此,公民在管制性征收領域的請求權基礎并未受到限制,如上文分析的那樣,公民可以依據“正當程序條款”請求法院確認政府行為過分限制的公民財產權而構成征收,然后依據“征收條款”要求政府支付補償。在德國,“征收”概念已經受到《基本法》的規范限制,且普通法院沒有權力審查決定不符合規范限制的政府管制法案是否構成征收以及是否需要補償。因此,針對管制性征收,公民請求救濟的唯一方式是依據《基本法》第14條之規定,發起憲政申訴,請求聯邦憲政法院確認政府管制行為違憲并予以撤銷。
四、中國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
如果將我國有關管制性征收請求權基礎的法律規定與實踐中出現的過分管制現象相對照,不難發現,我國公民目前面對管制性征收行為的請求權基礎是非常模糊的。這種請求權基礎的模糊性,既與我國憲法不能進行司法適用的現實相關,也與行政訴訟中“以合法性審查為原則,以合理性審查為例外”的基本原則相關。上文提到,管制性征收主要可以被分為立法型管制性征收和行政型管制性征收,因此與之相關的請求權基礎也需圍繞著這兩大類型來進行。
(一)立法型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
立法型管制性征收的存在本身已經說明,公民只有獲得挑戰法律合憲性的資格,才能真正發動這種“自下而上”的征收形式。否則,這種征收形式只可能存在于理論中而不具有實際意義。
以我國在槍支管理領域發生的爭議為例:1996年10月1日,新的《槍支管理法》開始實施,該法規定于當年10月1號以后換發新的持槍證件,凡不符合新法規定的持槍條件的一律予以收回。該法將合法的公民個人持槍范圍限定在獵區的獵民、牧區的牧民——這就意味著其他地區居民所持槍支必須無條件上繳,否則即為違法。在“楊某訴淅川縣人民政府案”中,楊某所持獵槍被公安機關收繳。楊某不服公安機關收繳其獵槍的行為,認為雖然依據《槍支管理法》其確實不再具有合法的持槍資格,但是公安機關收繳其槍支之后,應該支付補償。楊某經過兩審之后最終敗訴。勝訴的行政機關認為,原告不具有繼續持槍的資格,因此沒有對其核發新的持槍證件,并且,《槍支管理法》中也未規定需要對這種情況下原告的損失予以補償,行政機關屬于依法辦事[26]王玉信.一支藏槍引出法律空白[N].經濟日報,2003-11-13.。
在上述案例中,行政機關抗辯的理由之一是“《槍支管理法》中也未規定需要對這種情況下原告損失需要補償,行政機關屬于依法辦事”。從依法行政的角度來看,行政機關的確是在依法辦事,并無違法行為。但值得追問的是,作為行政機關辦事依據的《槍支管理法》本身是否合憲?我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如果楊某認為該法沒有規定對公民的補償違反了憲法規定,楊某是否可以依據憲法第13條發起一個質疑《槍支管理法》合憲性的訴訟?轉化成一般性的問題就是:我國公民個人是否具有在法院挑戰法律合憲性的資格?在我國目前的法律合憲性審查機制中,并不存在由公民直接發動的審查程序,因此在類似的情形中,“自下而上”的管制性征收不可能發生,公民的財產權也無法得到最全面的保護。
上述分析似乎表明,中國公民面對立法型管制性征收是無能為力的,只能任憑國家藉由一紙立法將自己的合法財產收歸公有。事實上,克服這種尷尬現象的路徑有兩條:第一條,提高人大立法的民主性與科學性,保證人大立法在規定對公民財產進行各種管制的同時,明確規定救濟途徑;第二條,允許公民提起憲法訴訟,挑戰人大立法的合憲性。比較來看,第一條路徑更加符合我國的法制現狀,它所要求的變動也是最小的。第二條路徑則要求憲法的司法適用,同時賦予公民提起憲法訴訟的原告資格。鑒于管制性征收“自下而上”的發動方式,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時不可能準確預見某部法律是否會引發管制性征收問題,因此第二種路徑似乎更加合理。
(二)行政型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
政府行政部門對公民財產的過分限制可能以兩種形式出現:行政立法即所謂的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相比較立法型管制性征收,由于部分行政行為具有可訴性,公民申訴救濟渠道也相對較多,因此行政型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相對更明確。
首先,如果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過度限制了公民財產權,那么公民可以依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除此之外,該法第11條和第12條還對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作出規定。這些條款一起構成了公民針對由具體行政行為引發的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
其次,倘若公民認為某項行政立法過分限制了自己的財產權,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該公民似乎無法直接請求補償,因為我國行政訴訟的基本原則之一的是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27]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1.。根據《立法法》第90條的規定,如果我國公民認為各種行政立法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因此,公民享有的只是一種“審查建議權”,并且這一過程注定是漫長低效率的,也就很難對公民的財產權進行及時有效的保護。因此,通過修改《行政訴訟法》,適當增加法院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權,可以進一步完善對公民財產權的保護。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管制性征收的特點之一在于,它對公民財產權的侵犯是無形的,基本不會發生行政機關對公民財產的物理性侵入。在很大程度上,管制性征收是法院對政府限制公民財產權是否合理的一種判斷。因此,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標準和強度成為公民能否獲得權利救濟的關鍵。一般認為,我國行政訴訟采取“以合法性審查為原則,以合理性審查為例外”的審查標準,除了行政處罰行為,其他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很少會受到法院直接的審查。因此,管制性征收問題的出現就要求我國修改這一原則,將政府行政行為的合理性納入到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至于司法審查的強度問題,因為管制性征收涉及范圍較為廣泛,很難直接給出一個明確的強度標準,需要在司法實踐中逐漸探索總結出針對不同領域的審查強度標準。
五、余論:走向權利與管制的統一
作為法治發達國家,美國和德國在管制性征收領域已經發展出具有各自法系特色的請求權基礎理論,既保證了政府可以在風險社會來臨時進行有效管制,又為公民財產權提供最大程度的保護。而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各種利益錯綜復雜,政府既要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及時進行反饋和處理,又要防止過分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何實現權利與管制的統一,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作為由公民“自下而上”發動的反向征收,管制性征收是國家警察權與公民財產權矛盾的一個集中體現。要實現權利與管制的統一,就要保證國家在行使警察權對社會諸領域進行管制時,公民能夠對政府管制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面對強大的政府管制,為了維護合法權益,公民應當獲得通暢的訴訟救濟渠道,應當在出現法律爭議時獲得較為明確的請求權基礎。由于訴訟資格的缺失,我國公民在面對立法型管制性征收時目前還沒有有效的救濟途徑。在行政型管制性征收中,除了具體行政行為,公民在面對由行政決策和抽象行政行為導致的過分限制財產權等行為時,同樣面對較大困難。綜合以上分析,為了完善我國公民面對管制性征收的請求權基礎體系,走向權利與管制的統一,本文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第一,提升各級人大立法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擴大管制性立法中的公眾參與,在相關立法中規定出明確的公民權利救濟途徑。
第二,探索公民監督法律合憲性的制度性渠道,允許公民獲得挑戰法律合憲性的資格。
第三,適當擴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將部分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領域。
第四,將行政訴訟“以合法性審查為原則,以合理性審查為例外”的基本原則修改為“以合法性審查為主,以合理性審查為輔”,允許法院就行政行為的合理性進行司法判斷,允許將比例原則、正當程序原則等作為法院判決的依據,同時注重法院的判決說理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