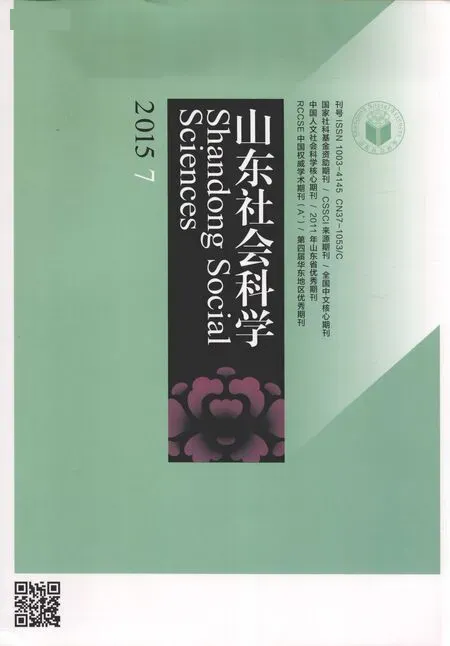對日本文藝諸概念的反思與再認識
——概念編制與評價史的視角
[日]鈴木貞美撰 黃彩霞譯
(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 京都6101192;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學術主持人:王升遠)·
對日本文藝諸概念的反思與再認識
——概念編制與評價史的視角
[日]鈴木貞美撰 黃彩霞譯
(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 京都6101192;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無論隨筆或小說,都有在不同地域、規范及價值觀的作用下相應發展的歷史。以往因為國際視野的缺失,人們一般不關注平時使用的術語、概念及其相互間的關系,一直以來顛倒錯亂的“日本文學”觀被說得煞有介事。“私小說”常被當作日本獨特的類型,或被稱作平安時代以來“日記文學”的傳統。實際上被稱為日本獨特類型的是隨筆形式的“心境小說”,且所謂“平安女流日記文學”類別是在1920年代才開始出現、屬個人記錄的各種文章的總稱。即使在明治末期狹義“文學”確立后,女流日記、紀行文及隨筆類仍未明確分類。日本三大隨筆觀有可能是在二戰后隨著國語教科書的輔助教材或考試參考書的普及才得以傳播的。此類問題既是類別概念的問題,也是評價史的問題。
日本文學;概念編制;日記;隨筆;日記文學;私小說;心境小說
一、概念編制與評價史因何重要
“日本文學”這一概念至明治中期才開始出現。前近代的“文學”意味著以儒學為中心的漢詩世界,和歌與物語都未被稱為“文學”,無論從何種意義看都不存在與近代“文學”相對應的概念。在此,筆者將談一談“日記”“隨筆”“日記文學”“私小說”“心境小說”等“日本文學”的下位類別概念。
“日本文學”最初是參照歐洲各國整個19世紀逐步形成的“國民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這一概念被提出的,是指那些與基督教神學(關于神的語言領域)相對、用母語進行創作的從屬人類優美語言領域的人文學(the humanities)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曾被當作人們讀寫的范本和知識階層應當背誦并掌握的東西。但是,新提出的“日本文學”是基于日本文化傳統的作用,包括宗教書籍、用漢語(漢文)書寫的書籍,還包括近松門左衛門的戲曲及曲亭馬琴的讀本等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
之后,至1910年前后,歐洲19世紀末形成的以詩歌、小說、戲曲為主要類別、用文字來書寫的語言藝術(literary art)的“純文學”[尤其是德語中與“Wissenschaft Literature”(知性文學或“科文學”)相對的“shōne Literature”(美文學)]傳入日本,狹義的“文學”(literature)在知識分子階層中扎根。在前近代泛指所有技藝的“藝術”(廣義)一詞,在日本明治初期成為作為英語“fine art”的譯詞而出現的“美術”一詞的同義詞①北澤憲昭:『眼の神殿―「美術」受容史ノート』,ブリュッケ2010年版。,用來指今天我們所說的“藝術”(中義)整體,而特指繪畫與雕刻的狹義的“藝術”則是1910年由文部省使用的,同時用文字來表現的狹義“文學”概念也作為平行概念被固定下來。但廣義的“文學”概念直至二戰結束前一直都在使用。②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學」概念』,1998年版;鈴木貞美:『「日本文學」の成立』,2009年版。
向20世紀過渡時期,在歐洲興起的象征主義藝術——浪漫主義中積極運用發達的象征技巧的流派——因吸收了被基督教視為異教、邪教的民族宗教等信仰,染上了一種宗教色彩,而未被日本接受。因此,已滲入日本古典中的神道、儒學、佛教、道家思想等要素未被排除,而且“能樂”等宗教藝能的詞章也作為狹義的“文學”,沒有任何違和感地被研究或教授。①鈴木貞美:『入門日本近現代文蕓史』,平凡社新書2013年版。
為什么要談這五種類別或范疇呢?那是因為它們之間關聯密切,如果僅考察其中的一種類型,有些地方會解釋不明白。以第一人稱的角度講述作家親身體驗的“私小說”是國際上20世紀小說的主流,其代表作家如詹姆斯·喬伊斯、馬塞爾·普魯斯特、弗朗茨·卡夫卡、威廉·福克納、亨利·米勒、羅伯特·穆齊爾……不勝枚舉。這與藝術領域中印象主義向象征主義的轉變有關,也與向20世紀過渡時期興盛的“意識哲學”的變化有關。日本的一位作家曾預言全世界各國小說最終都將會變成此類形態,此人即是巖野泡鳴。②鈴木貞美:『入門日本近現代文蕓史』,平凡社新書2013年版。
但是,“私小說”常常被認為是日本獨特的類型,甚至被認為是平安時代以來“日記文學”的傳統。實際上被稱為日本獨特類型的是指在中國及歐美未被列入小說范疇的隨筆形式的“心境小說”。而且,“平安女流日記文學”這種類別其實是在“私小說”“心境小說”盛行的20世紀20年代才開始出現的,在此之前并無此分類。
以往因為國際視野的缺失,人們一般不關注自己平時使用的術語、概念及其相互間的關系(概念結構或編制),因此一直以來顛倒錯亂的“日本文學(史)”觀被說得煞有介事。今天,《枕草子》《方丈記》《徒然草》被稱為日本三大隨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至今連此種結論究竟是在何時、依據何種價值觀作出的都尚未弄清楚(好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因此,關于“日記”“隨筆”“日記文學”“私小說”“心境小說”這五個概念要相互關聯著考慮。關于各個類別的作品,我們有必要追溯前近代的概念與評價在近現代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概念編制的改編與評價的變遷。此時,我們要注意“文學”的近代概念帶來的關于古典的性質方面的各種偏見。例如,“歷史物語”這一概念是在向20世紀過渡時期出現的。讓我們以此為例來看一下評價古典的觀點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例如《太平記》(編纂時間推定為14世紀中期—1370年前后)描寫的是天皇家南北朝分裂、中世戰亂時期的內容,其讀本被稱為“太平記読み”,至江戶時代仍被廣大民眾所喜讀。著眼于“讀物”這一特征,兵藤裕己出版了《太平記〈閱讀〉的可能性》(1995),另外,著眼于《太平記》在民眾的政治觀形成中所起作用的研究也在進行。《太平記》將楠正成等土豪以“忠臣”形象來書寫有著作者的意圖,直至二戰結束前都給日本人的歷史觀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當今的歷史學上將其視為歷史敘述。
在今天的某部文學事典中這樣評價《太平記》:“通過戰亂悲劇強調了人類道義,表達了與始終貫穿政權爭奪的政治相抗爭的民族的哀嘆,作為這樣一部文學作品,有著空前的價值。”此評論雖亦映射了日本戰敗的影子,但評論者從《太平記》表達了向往“太平”的“民族的哀嘆”的角度,將其作為一種感情表達,或作為一種以文字記述的語言藝術意義上的狹義的“文學”,對其進行了高度評價[釜田喜三郎“太平記”,見《新潮日本文學小辭典》(1968)和《新潮日本文學辭典》(1988)]。
在“國文學”領域將《太平記》等中世的戰記稱為“軍記物語”并視其為狹義的“文學”形式之一,始于19世紀末芳賀矢一的《國文學史十講》(1899)。讀其序可知,在此之前的“日本文學史”是“以全體學問為對象”的(實際上這是日本的人文學的范圍——引者),但芳賀矢一認為“文學就是被制作的美術品”,可稱為“美文學”。之所以稱為“美術品”,是因為在19世紀末以前詩歌、小說、繪畫、音樂、舞蹈等都被統稱為“藝術”或“美術”。根據這一思想,故事性亦即藝術性,于是出現了一種用近代文學的基準來評價古典的姿態。
歷史敘述主張將直面歷史事件的人們的心理或感情融入作品,如《源氏物語》“螢之卷”,既可比正史更加詳細地記載歷史事實,還可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這里的“物語”指的是從中國傳入的“章回小說”的形式,每一章回都有標題,故事情節也具有連續性。正因物語具有這樣的特點,隨著藤原政權的發展,繼《榮華物語》(11世紀)之后誕生的《大鏡》(平安后期)、《今鏡》(平安末期)、《水鏡》(鐮倉時代)、《增鏡》(南北朝時期)等“四鏡”也采用了這種形式,不僅運用了對話,還加入了圍繞史實評價的論述。相對于用漢文記載的皇家“正史”,“四鏡”可謂是用日語書寫的另一部“正史”。《榮華物語》“鶴之林”章中有將藤原道長的死比作光源氏的記述。歷史敘述中可用虛構的故事事件作比喻,這在中國的“史”書中是絕不可能出現的。
中國的“正史”是由下一朝代的史官整理前代王朝的歷史記錄。而在日本,沒有王朝的更迭,用漢文記載的皇家“正史”(六國史)的記載中斷后,在藤原政權時出現了用物語形式書寫的“史”。從此,歷史敘述開始呈現多樣性。平安時代中期開始,日本在向中國尋求范本的同時,也開始出現向日本獨特性發展的傾向。在二戰期間此種傾向被稱為“國風文化”,歷史上曾提出停派遣唐使的菅原道真也得到贊賞。但今天我們認為當時之所以停派遣唐使,其原因在于當時日本已經可以與中國進行各種物資貿易,因而已沒有特意派遣國使的必要。而且,現在菅原道真以及作為當時“國風”文化擔當者的紀貫之等人的高深的漢詩素養也正在被我們重新認識。原本“國風”的原意即是地方特色的意思。
兵藤裕己還指出了《太平記》中作者有意模仿《平家物語》而增加了作品趣味的地方,如交戰場面等。在引經據典中體會其變化的樂趣,這大概與和歌的“本歌取”(一種引用古和歌的詞句或趣向來創作和歌的方法)的創作方法相類似。物語形式會喚起人們脫離史實的自在感吧。
盡管《榮華物語》與《太平記》中包含感情表達或愉悅讀者的各種要素,但這兩部作品都不是作為芳賀矢一所說的“美術”或“藝術”被創作的。關于對中國“史”的概念的受容應另當別論①鈴木貞美:「歷史的歷史」,『「日本文學」の成立』,2009年版。,但以近代的“藝術”觀來評價處于歷史敘述與感情表達未分化狀態的古典顯然不合適。要想避免用近代的評價標準對古典進行判斷及其帶來的誤解,必須要了解各個概念的成立情況。概念是當時的知識階層都了解的意思或用法。
首先談一談“日記文學”,它是1920年代新出現的一種概念,然后按照“日記”“隨筆”“私小說”“心境小說”的順序對各概念史進行略述。關于各概念相互間的關聯,即概念間的結構或編制,首先從大致上進行把握比較重要,之后再逐漸對細微處進行修正。在此先聲明,尤其關于“隨筆”部分目前尚處于研究之中。另外,在前近代,文章的分類概念,除了參考中國的“經、史、詩、集”,還參考了類書的分類。13世紀前葉根據事實編寫的故事集《古今著聞集》中使用了“神祇”(神道)、“釋教”(佛教)、“文學”(漢詩文)等帶有日本特性的概念編制,雖然這些概念編制在發展過程中也發生過各種變化,但一直延續到了幕末。作為明治政府的國家事業進行編纂的古籍《古事類苑》就是在其傳統概念的基礎上又參考了西洋的分類概念。
二、“日記文學”的形成
首先,關于“日記文學”這一類別,主要以所謂的“平安女流日記文學”為對象來談。例如,紀貫之的《土佐日記》(935)一般被認為假托女性口吻而寫,還有平安時代中期的《蜻蛉日記》(975年前后)、《紫式部日記》(1010年前后)、《和泉式部日記》(推定為1004年)、菅原孝標女的《更級日記》(1059年以后)、《贊岐典侍日記》(推定為1109年)等。
《土佐日記》是紀貫之結束在土佐的任期返京途中寫的記錄,將本來應該用漢文來書寫的每天的記錄(即日次記)假托女性的口吻并使用多為平假名的和文來書寫。內有和歌57首,包括和歌在內,所記內容并不會使人認為作者是女性,任何人一讀便知,其實只是一種設定的假托而已。此種假托在漢詩中早就存在。《文華秀麗集》(818)中巨勢識人與嵯峨天皇的“長門怨”相呼應,以女性的口吻慨嘆獨宿的孤獨。另外,慈圓《早率露膽百首》(1188)的題詞中寫道,此詩為常誦俱舍論的比叡山的幼兒所做。另外,《土佐日記》起首的“男もすなる日記といふものを女もしてみむとて”可以理解為“男子寫的日記,作為女子的我也不妨一試”,但這句話中并不帶有“我是女子中第一個嘗試寫日記的”這種強烈的含義。
《源氏物語》的注釋書《河海抄》成書于室町時代初期,其中引用了醍醐天皇皇后穩子的日記。穩子為關白藤原基經之女,入宮之后的日記都是用平假名記述,但在朱雀天皇即位其本人當上皇太后之后的日記都改用漢文記述。穩子的這兩種日記都早于《土佐日記》的執筆時間。大致可以推測為,穩子本人對宮廷的各項活動做的記錄用平假名,而當上皇太后之后即由專門負責記錄的人用漢文來記錄了。
《土佐日記》出現之前也有一些帶有日期的宮廷儀式或祭典當天的記錄,以及斗詩會、和歌會的記錄。比如,陽明文庫所藏《類聚歌合》卷17的“和歌合抄目錄”中有“延喜13年(913)3月13日亭子院歌合”一項,下面寫著“參照伊勢日記”。另外,尊經閣文庫所藏《歌合》卷1的和歌會記錄一般認為也是取自《伊勢日記》。這些“和歌會日記”都是關于和歌的記錄,所以都用平假名書寫,但不一定都是女官所記。此類情況下的“日記”很可能只是當天的記錄的意思。還有和歌詩人藤原隆房記錄后白河法皇50壽誕慶祝儀式的《安元御賀日記》亦是如此。
藤原道綱的母親寫的《蜻蛉日記》共包含261首和歌,前半部分描寫的是對丈夫的怨恨,后半部分則采用游記的形式描寫了參拜寺院的內容。起首有這樣一句話:“我擁有普通人沒有的經歷,將我的經歷寫成日記,應該會有人對它感興趣吧”①『日本古典文學大系20』,巖波書店1957年版,第109頁。。從“日記”就是將某一時期的事情記錄下來這個意義上來看,“日記”一詞的意義已被挪用,即使非日次記,記錄人亦非公職人員,也都可稱之為“日記”。安和2年(969)的一段日記中,在寫完西宮左大臣的事情之后附了這樣一句話:“雖然不應該在原本只記錄我自己生活的日記中寫入這樣的事情”②『日本古典文學大系20』,巖波書店1957年版,第175頁。。對此,玉井幸助在《日記文學概說》中作如是評論:“相對于一般的日記,‘只記錄我自己生活的日記’是極其特殊的日記”③玉井幸助:『日記文學概説』,國書刊行會1983年復刻版,第245頁。。確實如此,遠離公文的女性記錄超出規范的“日記”并普及開來,應屬后來所說的“平安女流日記”。
《紫式部日記》又叫《紫式記》,并非日次記,是一些和歌的記錄或某種情況的隨手記錄之類,可能本來就不是為了讓別人閱讀而寫的,一般認為其中使用了比書信更接近于口語的書寫方式。
直至江戶時代,《和泉式部日記》又叫《和泉式部物語》,以帶有章回題目的物語形式記錄了某“女子”對戀愛經歷的回憶以及新戀情成功的經過。《更級日記》的前半部分主要記錄了從上總(現千葉縣)到京都的游記,后半部分則主要是對遁入佛門之前的經歷的回憶,其中對夢境的大量記述很有特色。
鐮倉初期藤原為家的側室阿佛尼寫的《十六夜日記》(成立于1283年左右)記錄了阿佛尼為領地糾紛訴訟而從京都去鐮倉途中的旅行紀實和在鐮倉滯留期間的生活。另外還有記錄藤原經子13年宮廷生活回憶的《中務內侍日記》。
今天,包括《土佐日記》在內的這些作品被冠以“日記文學”的名稱,被視為日本文學中一種獨特的類型,但是這樣一來,對于這一形式和內容都各不相同的作品群,無論進行怎樣的細致分析與深刻研究都不可能了解其特質了。因為當時那個時代人們不可能擁有除了私人記錄以外的其他的共同規范意識。
江戶時代后期,塙保己一編纂的《群書類從》是對本朝古書的整理,分為神祇部、帝王部、補任部、系譜部、傳部、官職部、律令部、公事部、裝束部、文筆部、消息部、和歌部、連歌部、物語部、日記部、紀行部、管弦部、蹴鞠部、鷹部、游戲部、飲食部、合戰部、武家部、釋字部、雜部,屬于“國學”系統,從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近乎正式的分類意識。將漢詩列入“文筆”部,在“物語”部與“管弦”部之間設立“日記”部,內收《和泉式部日記》《紫式部日記》《宗長手記》等八篇,“紀行”部中以《土佐日記》開頭,下列《海道記》《東關紀行》等十四篇。《土佐日記》雖是日次記,但被歸為紀行類。紀行文開始是由遣唐使等人作為公務報告而寫的,可能早就有了將其視為一種類型的意識。在中國古代,為與上表文等正式公文相區別而稱私記類,在這里亦可將“日記”看作是對中國古代用法的一種沿襲吧。
實際上,始于明治時期的“日本文學史”中并沒有提及“日記文學”這一范疇。堪稱“日本文學史”嚆矢的三上參次、高津鍬次郎編的《日本文學史》(1890)雖然在編寫時參考了歐洲近代的文學類別概念,但如前所述,此書編寫的是日本的“人文學”、廣義“文學”的歷史(其態度也出現過些許動搖。《日本文學史》總序中寫道:“漢文全部未采用。但與國文學相關之處自然要使之明確”④三上參次、高津鍬次郎合著:『日本文學史』上巻,金港堂1890年版,第11-12頁。。實際上,上卷率先登載了《古事記》《日本書紀》以及用萬葉假名書寫的歌謠之類,顯示出對語言藝術的尊重,但《出云國風土記》中的國引神話一節(原文漢文)卻使用了和漢混同體,而下卷(鐮倉時代以后)則重視儒學,又引用了新井白石的漢文。上卷和下卷在結構與文體上稍有不同。據推測,此書是由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歷史學科的三上參次教授進行整體構思,當時在讀碩士研究生的高津鍬次郎執筆上卷,三上執筆下卷),編者在第三篇“平安朝的文學”的第四章“日記及紀行文”中寫道,日記、紀行、隨筆“這三者之間很難界定明顯的界限”⑤三上參次、高津鍬次郎合著:『日本文學史』上巻,金港堂1890年版,第298頁。。因此,關于“隨筆”我們也需要多加注意。
綜上所述,無論媒體形式如何變化,對于時政新聞來說,優質的新聞主體內容仍舊是新媒體時代的核心。因此,在新時代背景下,廣播新聞采編人員要創新模式,不斷提升專業能力,強化綜合素質。只有掌握較強的新聞采編技巧,融合新媒體元素,創新采編形式,才能更好地適應新媒體時代的發展要求,推進廣播事業快速發展。
在芳賀矢一的《國文學史十講》的第五講、中古文學之二“假名文字散文”中同時寫了《源氏物語》《枕草子》《紫式部日記》《和泉式部日記》《蜻蛉日記》的內容,其內部并未細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被廣泛閱讀的簡明文學史——藤岡作太郎編寫的《國文學史講話》(1901),顯示出一種縱觀美術動向的文化史的姿態,其中談道:“枕草子為清少納言之作,盡管當時也出現了紫式部日記、和泉式部日記等很多類似作品,但都得給此書讓步”,之后便進入與《源氏物語》的比較。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確定,即使在明治末期狹義“文學”確立之后,女流日記、紀行及隨筆類仍未進行明確分類。
哥倫比亞大學的鈴木登美已在研究中指出①鈴木登美:「ジャンル·ジェンダー·文學史記述―『女流日記文學』の構築を中心に」,載ハルオ·シラネ、鈴木登美編『創造された古典―カノン形成·國民國家·日本文學』,新曜社1999年版,第104頁。,今天,“日記文學”一詞最初出現在書名中是池田龜鑒的《宮廷女流日記文學》(1928),首次出現應是池田龜鑒《自省文學的歷史性展開》(《國文教育》1926年11月號)中的“圍繞‘日記’與‘日記文學’概念的筆記”,“日記文學”的目的在于“作者心境的漂白”。池田龜鑒在《自省文學的歷史性展開》中寫道:今天的“自省文學的全盛時代”“帶來了可以通過新視角去解釋國文學的時機”,可將這些作品列入“直接講述自己真實經歷的懺悔、告白與祈禱文學系列”,與“陶醉、沉迷于現在”的抒情詩不同,它們是“對過去的思索與反省”,并“伴有一種叫作‘鄉愁’的寂寥”。②池田龜鑑:『日記·和歌文學』,至文堂1969年版,第56頁。今天所謂的“自省文學的全盛時代”,應該是指“私小說”與“心境小說”盛行的時代。但實際上,與主要面向文學青年的“文壇小說”相對,當時攜手歌頌勤勞大眾的、被稱作“時代もの”或“髷物”的“歷史小說”和“偵探小說”——“大眾文學”(取材于當代風俗的“通俗小說”曾被當作“文壇小說”,1930—1935年也被納入“大眾文學”)以及“無產階級文學”興起,“私小說”“心境小說”則隱形遁世。因此,毋寧說當時是一個圍繞“私小說”“心境小說”激烈爭論的時期。關于那些爭論如何姑且不論,下面僅談一談有關“日記”概念變遷的基本情況。
三、日本的“日記”概念
首先,我們今天使用的“日記”概念未見于前近代的漢語,據說現在中國使用的“日記”概念是20世紀通過日本的教科書之類傳到中國去的。雖然中國古代也有“日記”一詞,但與今天的“日記”概念相差甚遠。據玉井幸助的《日記文學概說》(1944)第一章“概觀”可知,在中國“日記”一詞最早可見于東漢王充《論衡》第13卷“效力篇”,論及“文儒之力”示于文章時指出“上書日記”并立可見,王充認為優于“上書”者如效力于漢成帝的谷子云,優于“日記”者如孔子。換言之,《春秋》等五經即被視為古代“日記”。相對于上奏給皇帝的奏本,個人每天書寫或收集、編集的文章等都可稱為“日記”。總之,“日記”就是用來指在每天的生活中所做的所有與寫文章相關的事情。玉井還寫道,到后來一般通用的也還是此意義上的“日記”,“日錄”“日鈔”“日抄”“日疏”等詞可看作“日記”的同義詞,即古漢語中的“日記”僅僅是“私人記述”,不屬文學類別。
北村季吟等人論及紀貫之的《土佐日記》時將“日記”定義為“記錄每日事”,同時又把非“記錄每日事”的《篁日記》等與其列為同類。對此,玉井幸助在《日記文學概說》第二篇“我國的日記”中進行了質疑。也就是說,日語中的“日記”在江戶時代“記錄每日事”這一詞義已基本固定下來,但仍有傳統意義的殘留,從而導致了使用上的波動。但是,即使傳統意義上的“日記”也仍與古漢語中的“日記”有所差別。玉井幸助談道:現存文獻中“日記”一詞最早見于《類聚符宣抄》中的弘仁12年宣(821)。內有“自今以后、令載其外記于日記”一文,意思是“自今以后,律令要由外記載入日記中”。“外記”就是位于記錄宮廷儀式的少納言之下的史官及其所做的記錄。因此,在日本,史官所作的帶日期的公家記錄(可能是按日記錄)也被叫作“日記”。
作為今天所說的“日記”的起源,經常會提到中國皇帝的言行記錄“起居注”。由史官記錄,后作為“實錄”修撰,其中有大家熟知的漢武帝的“禁中起居注”。史官名從周代開始有“左史”“右史”,但據說漢代作為官職名的“起居注”尚未得到確認。從晉朝起設置“起居令”“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專門官職,此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滅亡。③受清華大學王中枕教授的啟發。另外,眾所周知,《日本書記》神功皇后攝政第66年的部分有對《晉起居注》的引用。
現存最早的“起居注”為中國唐代的編年體史書《大唐創業起居注》,但之后留存下來的較少。據說是因為下一朝代對前朝的“正史”進行編纂時被扔掉了。清朝的“起居注冊”目前保存在臺灣的國立故宮博物館。無論哪一朝的“起居注”都是經史官之手記錄的。
在日本,內記負責相當于起居注的皇宮記錄,外記則負責宮廷儀式記錄。記錄中使用了“日記す”“日記せしむ”這樣的動詞。此外,還有一些貴族或官吏記的個人記錄。在中國一直沒有發現有關宮廷儀式的個人記錄,可能宮廷儀式的個人記錄是被禁止的吧。
天皇的日記有“三代御記”,即現存最早的《宇多天皇御記》(寬平御記)以及《醍醐天皇御記》、《村上天皇御記》。皇族日記有醍醐天皇第四皇子重明親王的《吏部王記》等,高級貴族的日記有藤原忠平的《貞信公記》、藤原實賴的《清慎公記》、藤原師輔的《九歷》(九條殿御記)等。取名“歷”是因為此記錄是使用具注歷記錄的。另外,正倉院文書中發現了天平年間以來的國司業務記錄以及一些使用了具注歷余白、紙背的記錄。
具注歷最初是古代日本為了支配或統治國家的時間而由朝廷向地方行政機構頒布的。據平安末期的《本朝世紀》可知,由于新抄紙及重抄紙不足等原因,10世紀時此制度遭到了破壞。另外,有學者認為,10世紀時貴族及寺院依靠歷博士或歷生來制作、書寫具注歷已成慣例。或者也可以說具注歷的一半用途是用來書寫日記的吧。據說最初是藤原攝關家接受了具注歷的進獻,但具體時間不詳。現存最古的親筆歷記中有藤原道長的《御堂關白記》,其大部分都是按照日語的語序書寫并適當使用了漢字詞。可能連漢文讀寫水平很高的藤原道長都覺得使用正規的漢文記述太麻煩了吧。
也就是說,日本前近代的“日記”有兩種:①是指正式“公文”以外的個人記錄的所有文章,②鈴木貞美:「日々の暮らしを庶民が書くこと―『ホトヽギス』募集日記をめぐって」,佐藤バーバラ編『日常生活の誕生―戦間期日本の文化変容』,柏書房2007年版。是指宮廷史官所做的帶日期的記錄。①中又混合了三種用法,即用具注歷記錄的文章、個人記錄的日次記,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文章。隨著時代的發展,到了江戶時代,屬于舊中間層的理發店或商家,出于寫各種報告的需要,形成了以上述①中的第二種形態即以日次記的形式做記錄的習慣,但其書寫樣式各不相同。在第一章中曾談到的自平安中期開始至鐮倉、室町時代由女性創作,被冠以“日記”之名,并于1930年代前半期被歸類為“平安女流日記文學”的作品群,應屬①中第三種用法,即為個人記錄的各式各樣文章的總稱,這一點再次得到了確認。
四、“日記”概念的近代化
在歐洲相當于“日記”的概念有“journal”和“diary”兩種,前者是指所有附有日期的記錄類文章,后者是指記錄預定計劃或備忘錄的帶有印刷的年、月、日的筆記類。但日本的“日記”概念并未受到此概念的影響而發生改變。
明治后期,正岡子規創辦的俳句雜志《杜鵑》曾于1900年10月至1903年9月(4卷1號—12號、5卷2、4、8、10、12號)征集、選拔并刊登過“每周日記”和“每日日記”。眾所周知,正岡子規致力于短歌、俳句及“敘事文”的近代化革新,此征集活動正是“敘事文”(所謂的“寫實文”)改良的一次嘗試。俳諧本是作為百姓的一種游戲而普及、固定下來的,因此應征者多是平民階層。看其所錄用的日記就會發現,“每周日記”的投稿首先是各種業務的記錄,由此可以看出此種習慣在民間早已深深扎根。在日記的空白處寫一點感想,這與古代朝臣個人記錄的日次記差不多。文體基本也是從江戶時代開始就在百姓中流行的名詞結尾、“コト”結尾、用言終止形結尾、表過去或完了的“た”形結尾的口語文體。
一般認為明治時期的“言文一致”文體改良運動是將文語體改成口語體,但這只是對知識分子階層而言。對平民階層而言僅僅是將上述口語體(“する、した”體)的句子結尾處統一改成“だ、である”而已。在小學教育階段只要經過訓練很容易就能轉變過來。通過《杜鵑》征集的日記明顯能看出這種轉變。②
1895年創刊的引領社會輿論潮流的博文館的綜合雜志《太陽》,接受各界讀者投稿,不限制執筆者文體使用的自由。比較該雜志的文體變化情況就會發現,在對“だ、である”體的使用方面,平民百姓比善用文語的知識分子更容易習慣。在《太陽》的署名投稿中,政治類文章的文語體殘留現象較多,大部分文章都使用“だ、である”體是在1905年前后。另外,正岡子規在《杜鵑》中引導人們重點描寫印象深刻的事情,其效果在“每日日記”中尤為可見。①鈴木貞美:『日本語の常識を問う』,平凡社新書2012年版,第3章。
日次記形式的“日記”發生的大變化在于,記載的內容不再僅僅以事件記述為中心,也可圍繞自己的思考內容、感想來記述。比如,記錄美國哲學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生前思考點滴的日記(journals)在其死后被分為2冊出版。有可能受此影響,國木田獨步于1893—1897年間圍繞戀愛心情而寫的心理記錄《欺かざるの記》在其死后也被出版了(前部1908年,后部1909年),凈土真宗改革派的清澤滿之晚年的內省記錄《臘扇記》等被讀者當作“修養書”一樣去讀,這些都為日記的變化奠定了基礎。之后,阿部次郎以新文藝的方法提倡“精神生活的如實描寫”,出版了非回憶的、記錄彷徨內心的《三太郎的日記》(1914年,第二1915年,合本1918年),本間久雄在《日記文的寫法》(新文章速達叢書,止善堂,1918)中作為范本刊載了尾崎紅葉的記錄式日記以及樋口一葉的感想日記,并收錄了新潮社系新進作家們的隨筆風格的日記。這些改變大概也刺激了中學生或女學生、高中生們的日記寫作,學生中間也逐漸形成了作為內省記錄的日記習慣。1920年代,尊重兒童自發感情表達的情操教育風潮(以大正生命主義的北原白秋的《童謠》理念為代表)在小學教師中間席卷開來,于是作為作文教育的一環記錄每天生活的日記形式固定了下來。
前章介紹的池田龜鑒在《自省文學的歷史性展開》中始創“日記文學”一詞并提出“日記文學”的目的在于“作者心境的漂白”,如果說這一學說的提出是以隨筆形式的“心境小說”的興盛為文學史背景的,那么我們就要了解這里指的應該是更廣義的文化史的背景。
五、關于“隨筆”的概念
下面,我想簡單追溯一下“隨筆”一詞的歷史變遷。《新潮世界文學小辭典》(1966;增補改編版為《新潮世界文學辭典》,1990)中擔當“隨筆”一詞解說的福原麟太郎這樣解釋:“縱觀中西文化,漢語中‘隨筆’一詞的出現始于南宋洪邁的《容齋隨筆》(1180年公開發行,之后還著有《容齋續筆》乃至未完成的《容齋五筆》)。在日本,第一部以‘隨筆’冠名的書籍是室町中期一條兼良編撰的說話集《東齋隨筆》。與東方的起源相對,英語中‘隨筆’的概念是由英國作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受法國隨筆開山鼻祖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的《隨筆集》(Essais,1580,1588)的影響,將古羅馬時期新斯多葛派的哲學家小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e,公元前3—公元65)的書簡也包括在內,將‘隨筆’的范疇擴大,使其變成一種既包括理智又包括情感、書寫形式自由的文學形式。”該辭典中還規定“隨筆”是“內容多樣的小品散文樣式”,并順便提到“我國的私小說類作品在英國被算作散文的一種”。
蒙田的《隨筆集》描寫了在舊教和新教的宗教戰爭面前,人類對自身倫理道德的懷疑和反省。讀了此書的培根,會想起塞涅卡的書簡及文章一點都不奇怪。一度隨心所欲生活的塞涅卡一邊隨時等待著皇帝派來的死亡使者登門,一邊在日常瑣事中對人性進行觀察,在文章中直抒胸臆地吐露自己對道德根本進行的思考。
在19世紀的英國,查爾斯·蘭姆的《伊利亞隨筆》常被稱為隨筆文學的巔峰。其含義是感受富含人類機智和洞察力的文章帶來的快樂。雖然設定了伊利亞這個敘述者,但其中也含有很多自傳性元素。福原麟太郎之所以提到“我國的私小說類作品在英國被算作散文的一種”肯定是受到《伊利亞隨筆》的影響吧。另外,“我國的私小說”中特別限定為“我國的”,大概是為了與歐洲的“自敘體小說”相區別,是指作家的形象不直接表現在作品中而以隨筆形式陳述自己心境的、被稱為“心境小說”的那種“私小說”而言的。
總之,不是以一般人信奉的宗教世界為對象,而主要以人性為對象對倫理進行考察的態度及其文章的妙趣構成了歐洲隨筆的根本。可以說,由此人們才會喜歡上像諷刺詩中表現出來的那種被認為“說得妙”的奇特構思和新穎的表達。“隨筆”正是在這種人文學的基本發展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至于擴大到“內容多樣的小品散文樣式”與報業的發達有密切的關系。
無視上述歷史變遷,直接將“隨筆”定義為“內容多樣的小品散文樣式”,并強加在中國及日本古典文學上的態度是有些危險的。雖說一條兼良編著的說話集取名為《東齋隨筆》,但當時在日本“隨筆”一詞是否被理解為“內容多樣的小品散文樣式”還有待考究。而且,“我國的私小說類作品”不論是在英國、法國還是中國都不被算作小說的情況也沒有被考慮在內。無論隨筆類還是小說,都有在不同的地域、在不同的規范及價值觀的作用下相應發展的歷史。正因如此,才有必要追究諸概念之間的關系,即概念構成或編制的歷史變遷。
《容齋隨筆》的自序中說明了“隨筆”的含義,即“意之所至,隨即記錄”。此書匯集了各種內容的筆記,從題材來看,以經史為首,諸子百家、詩文、方術,甚至民間信仰,資料豐富,涉及范圍廣泛,確是“內容多樣的小品散文樣式”。此書對史料記載的評議或典據的考察都非常確切,向來以對“文字”的考證精確而著名。①大西陽子:「『容斎隨筆』に見る表現形式―読者との係わりの中で」,『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1987年第6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推其為南宋說部之首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這種將各種內容的筆記編纂成冊的書籍早在11世紀就已出現,如沈括的《夢溪筆談》、吳曾的《能改齋漫錄》等。可將二者視為同一類型。究其成書背景,在唐代,不拘泥于規范的文章的自由寫法(肆筆)就已十分盛行,②高橋文治:「〈肆筆〉の文學―陸龜蒙の散文をめぐって」,荒木浩編『中世の隨筆―成立·展開と文體』竹林舎2014年版。出版物在民間大量流傳,其中尤以經書、史書類注疏(注釋書)為盛。長期擔任史官的洪邁,博覽群書,經世致用,對塵世的“淺妄”多予以嘲笑。洪邁的考證范圍極其廣泛,自“經、史、子、集”到佛教批判、人物評、地志等無不有所涉及。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之為“議官”出身的“雜家者流”。意思是說洪邁不是“稗官”“小說家”。洪邁評價過主張三教一致論的白居易的詩歌,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容齋隨筆》是以寫“經、史、子、集”的內容為根本規范,雖然也有超出此規范的內容,如當時的街頭軼事、人物傳聞等,但作者并非要去寫故事,畢竟洪邁不屬于以著有《呂氏春秋》的呂不韋為代表的百科全書派那樣的流派吧。
有一類文章,不像《容齋隨筆》這類書籍是關于史實考證或評論的,也不是寫社會事件或傳說的,其開創者應該是明代的作家袁弘道。袁弘道非常擅長花道技藝,同時也對飲酒的方式頗有心得。他曾經寫過關于花道的《瓶史》和指導人們如何愉快地飲酒的《觴證》。說袁弘道的文章開創了一個新的流派也不為過吧,在中國,各類體裁的“史”書都習慣在“正史”中編寫,“花道史”卻是一個例外。但袁弘道能夠創作出與“經”“史”都無關的著作,大概可以歸結為他年輕時與其弟一起師從1930年代被稱為“陽明學左派”的李贄(李卓吾)的緣故吧。在李贄那里,袁弘道學到了“解放欲望,達到‘圣人’境界”的思想,養成了自由發揮思想的風格。袁弘道與其兄弟一起反對擬古、復古的詩風而推崇清新的詩風,由于出生于湖北省公安縣,世稱“公安派”。清代袁枚等學者繼承了袁弘道的文風,提倡文章要自由表現個人性情,開創了“性靈派”的詩風。袁枚還著有關于烹飪技巧的書《隨園食單》,并效仿李贄提倡婦女文學,甚至公開刊行了《隨園女弟子詩選》一書,因此遭到了朱子學派的非難和抨擊。
中國的雜文在不斷地發展,自明代的“古文辭派”開始,至清代則流行對事物的由來等進行考證的形式。而且,這些“雜文”都是正式的文言文體,不是講義、講話、問答時用的“白話文”。
相對于中國的“雜文”,日本最早以“隨筆”冠名的書籍是《東齋隨筆》。此書為一條兼良從已有文獻中摘錄了78則民間故事和傳說編撰而成的,內容分為音樂、草木、鳥獸、人物事件、詩歌、政治、佛法、神道、禮儀、好色、游玩等11個部分。室町時代后期又出現了“連歌師”荒木田守武編著的《守武隨筆》,此書大概是效仿《東齋隨筆》而命名的。
雖然《東齋隨筆》被命名為“隨筆”,但不像中國宋代的雜文集那樣,多選擇一些詩文對其進行論述、整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東齋隨筆》命名為“東齋漫錄”應該更合適。那么為何取名為“隨筆”呢?現在還不能確定“隨筆”一詞是否被賦予了特定的意思。與中國宋代的雜文集相比,《東齋隨筆》的顯著特色在于其內容選取的對象并非“經、史、子、集”,而是日本前代的故事和傳說。當然,在此書之前已有著述前代傳說的先例,但在此沒有必要追溯到平安初期的《日本現報善惡靈異記》。12世紀的《今昔物語集》的編纂動機也不詳。
從《東齋隨筆》中分類的情況來推測,此書有可能受到13世紀前期鐮倉時代由橘成季編著的《古今著聞集》的影響。有關《古今著聞集》的編寫目的,如其序文中所說,是為了補充“實錄”。所謂“說話”一般都基于事實,而且很多都涉及朝廷的規章典制或者當時那個年代的事件。因此,橘成季的為了補充《實錄》的說法亦可理解。在此之前,13世紀初,精通典章制度的源顯兼編著的《古事談》共有王道后宮、臣節、僧行、勇士、神社佛寺,亭宅諸道等六卷,被稱為皇族、貴族、僧人的奇談或秘聞集,此書在編寫時可能也帶有輔助《實錄》的目的性。但是,在此之前的說話集中是否也伴有類似的意識?而且《古事談》的書名中使用“談”字是否是因其內容為傳說?這些我都不能判斷。在中國,“語”和“語錄”傾向于用于白話文,但在記錄講說的內容時也有使用“筆談”的情況。因此可以推測,《古事談》中的“談”也可能是一種比喻用法。這一點姑且不論,將以民間故事為主要材料編纂的《古今著聞集》作為《實錄》編纂的補充這一在中國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之所以能夠發生,并且書中根據中國的類書進行分類的做法,都是因為日本當時正處于中世這樣一個價值規范混亂的時期。當時,公家政權的官僚階層欲用現成的材料拼湊出僅形式上符合中國式規范的東西,來支撐勉強延續下來的王朝。
《古今著聞集》分為神祇、釋教、政道忠臣、公事、文學、和歌、管弦歌舞、能書、術道、孝行恩愛、好色、武勇、弓箭、馬藝、相撲強力、圖書、蹴鞠、博弈、偷盜、祝言、哀傷、游覽、宿執、爭斗、興言利口、怪異、變化、飲食、草木、蟲魚鳥獸等30篇。顯然,此種分類仿照了中國的類書,但也有不符合類書的地方。現參照初唐時期歐陽詢編纂的較有代表性的類書《藝文類聚》(624)來加以對照。卷頭有“天”2卷、“歲時”3卷,接著是“地”“州”各1卷、“山”2卷、“水”2卷。至此處相當于“天文”“地文”,以下為“人文”。接下來是關于帝王受命于天的“符命”1卷、“帝王”4卷、“后妃”1卷、“儲宮”1卷、“人”20卷、“禮”3卷、“樂”4卷、“職官”5卷、“封爵”1卷、“治政”2卷、“雜文”3卷、“武”1卷、“軍器”1卷、“居所”4卷、“產業”2卷、“衣冠”1卷。另外,“鳥”“獸”“魚貝”,甚至“靈異”等也都收入其中,最后一卷是“災異”,共46部727個子目。徐堅編撰的規模較小的類書《初學記》(727)共23部313個子目,其基本構成與《藝文類聚》大致相同。可以說,這些類書,尤其在平安前期的漢詩文繁盛時期,作為詩文的文典被廣泛使用。
雖說《古今著聞集》借用了類書的分類,卻沒有“天、地、人”的大分類,將“神祇”“釋教”置于開頭,這是與中國類書不同的顯著特征。這可以看作是《日本書紀》以來日本正史中所體現出的日本式意識的表現。漢文被歸于“文學”部。此外,出于對世事的關心進行了諸如“孝行恩愛”“好色”“博弈”“偷盜”等非常精細的分類,這一點也值得關注。
但是,《東齋隨筆》與《古今著聞集》的順序顯著不同。大概《東齋隨筆》沒有補充《實錄》的意識吧。而且,《東齋隨筆》的編寫方法與鴨長明的《發心集》中基于特定主題編寫佛教傳說的做法也不同。有人推測《東齋隨筆》將“音樂”置于開頭可能是為了表達對儒家古流派的“樂”的尊重,但“草木”緊接其后的理由卻不得而知。因此,《東齋隨筆》編纂的動機不詳。
與此相對,《守武隨筆》可以看作是連歌師收集的滑稽故事集。與概念或分類意識不同,在研究中世的所謂隨筆類的評價史時,俳諧連歌所起的作用非常大。
進入江戶時期,漢詩文與和漢混同體盛行,比如山鹿素行的著作中沒有以“隨筆”來命名的,而是用“論”或“紀”來命名。但是,荻生徂徠學習中國明代的古文辭派,強烈批判朱子學,并把通過對伊藤仁齋古義學的批判而獨自開創古文辭學的他的著作題名為《萱園隨筆》。萱園即為徂徠的號。
眾所周知,參加中國明代遺臣活動后流亡日本的朱舜水以水戶藩德川光國的修史事業(后命名為《大日本史》)為開端,相繼輔助其完成了各種事業,并為日本古代的考證(稱和學或本朝學,明治前期統稱為“國學”)創造了契機。在此潮流中涌現了諸如本居宜長《玉勝間》那樣收錄了各種筆記的書籍,內容涉及諸多領域。是否有意所為不得而知,或許是在模仿先前談過的《容齋隨筆》等“雜家流派”的形式。
在中國清代,各地都在編纂地志。受其影響,日本民間也進行了地志編纂。隨著時代的發展,有關江戶時代的風俗或傳承方面的考證隨筆大量刊行。19世紀初,僅就文化而言,出現了大量著名的廣搜文獻并配有插圖的考證書籍,如曲亭馬琴的《燕石雜志》、柳亭種彥的《還魂紙料》、山東京傳的《古董集》等。都是大開本,比讀本、劇作類高級,可能當時已意識到這些作品屬于一個類別吧。之后,紀行類、中國清朝時期盛行的地志也大量編纂,其中有完全屬于民間愛好者的鈴木牧之模仿別人編寫的《北越雪譜》。編纂過程中,與山東京傳、曲亭馬琴商量過,但因未能具體化,最終由山東京傳的弟弟山東京山制作出版,受到民間的好評。原本計劃按季節出續編,最終因鈴木牧之逝去而未能完結。以前我曾提到過,關于雪這一氣象的考察明顯有參考寺島了庵《和漢三才圖繪》(1712)的痕跡,在這里充分體現了“天、地、人”“三才”的區分法。①鈴木貞美:『生命観の探究―重層する危機のなかで』,作品社2003年版,第4章11節6。
另外,江戶后期曾頻繁使用“隨筆”一詞。在蘭學學術圈的協議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一條要求提交“隨筆”(考證的報告)②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日蘭関係史をよみとく―蘭學を中心に」(2012年12月8-9日)”研討會上,從上野晶子(北九州市立自然史·歷史博物館學藝員)的報告中得到的啟示。。由此可看出,清朝考證學已經影響到了民間。
明治時期,各種散文也開始進行改良。前面已經談到過,由德富蘇峰主編的《國民之友》有一段時期采取以《史論》為“文學”核心的方針,但是這里的“文學”相當于歐洲人文學(但日本的“文學”包括宗教教義書、漢文這類異語言作品、民眾文藝,這一點與歐洲不同)范疇的“文學”,此“文學”概念直至明治末期一直都是主流。1895年博文館創刊的商業綜合雜志《太陽》,在目錄中引入了“史傳”與“隨想”。“史傳”就是“史”與“傳”的意思。“隨想”應該是“エッセイ”的翻譯,是指與“評論”相對而不明確發表見解的文章。
向20世紀過渡時期,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比如,曾于19世紀中葉游歷法國的俄羅斯貴族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所著的《獵人日記》(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1852)中使用英譯題目A Sportsman's Sketches;德富蘆花受到由外光派轉向印象派的繪畫的影響,對“寫生”的興趣大增,在韻律和聲調等方面下足功夫,寫出了充滿散文藝術氣息的作品《自然與人生》;國木田獨步參考二葉亭四迷翻譯的《獵人日記》中的“幽會”(《國民之友》1888年初出版;《かた戀》,春陽堂,1896年收錄①鈴木貞美:『入門日本近現代文蕓史』,平凡社新書2013年版,第88、152頁。)出版了《武藏野》(1901)并引起關注;正岡子規提倡以“描寫世間存在的事物(不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寫出有趣文章之法”來寫“敘事文”,倡導“將事物按照其客觀存在的狀態或看到的狀態進行臨摹”(報紙《日本》附錄周報,1900年1月29日),并在《杜鵑》雜志上向讀者征集日記,指導大家以印象深刻的地方為焦點來寫日記,對地方城市中那些對俳句感興趣的人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②鈴木貞美:「日々の暮らしを庶民が書くこと―『ホトヽギス』募集日記をめぐって」,佐藤バーバラ編『日常生活の誕生―戦間期日本の文化変容』(柏書房2007年版)及『日本語の「常識」を問う』(平凡社新書2012年版)。。
人們在論及此事時常常與“言文一致體”的問題聯系在一起,但是德富蘆花的《自然與人生》就是文言文體,這與文體的問題無關,也與作品類別無關。總之,非考察性的、情景描寫或印象再現、以興趣為中心的文章流行了起來。例如,一種被稱為“寫生文”的短小散文,還有一種被叫作“小品”體裁的文章,如夏目漱石的《永日小品》(1990),它從江戶時代的漢文世界擴展開來,并容許加入虛構成分,也被用于雜志投稿。
在日本,“隨筆”作為一種文學類別名稱被廣泛使用,是在1920年前后綜合雜志、女性雜志大量涌現,“雜文”類作為一種不同于評論、可輕松閱讀的文章被廣泛接受之后的事情。自此,“小品”的名稱基本被驅逐。1923年菊池寬創刊的《文藝春秋》的成功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芥川龍之介連載的警句《侏儒の言葉》以及直木三十五的文壇閑話等在當時都很暢銷。菊池寬則未使用“隨筆”,一直使用“雜文”一詞。③鈴木貞美:『「文藝春秋」とアジア太平洋戦爭』武田ランダムハウス講談社2011年版,第2章第1節。同年12月、中戶川吉二在水守龜之助以及牧野信一等人的協助下,以追求強烈藝術性的“隨筆文學”為目標而創刊的《隨筆》雜志并未持續多長時間。而1930年代內田百間(后改為“閒”)摻雜對夏目漱石的回憶,包括關于朋友關系、對金錢的信念之類的文章,以輕妙灑脫的文風寫就的《百鬼園隨筆》(1933)等卻再版發行。我們今天所說的不問材料與形式、能讓人輕松閱讀的雜文意義上的“隨筆”的用法,應該是1920—1930年代固定下來的。
六、“私小說”與“心境小說”
最后,談談“私小說”與“心境小說”的問題。“私小說”受到德語“Ich Roman”(I novel)的啟發,并受到歐洲浪漫主義小說形式的影響,通常是指以作家的親身經歷為題材,以第一人稱(有時也用第三人稱)來講述的小說。以歌德自身的戀愛經歷為題材而寫的《少年維特之煩惱》(1774)被公認為“私小說”的開端。雖然小說的主人公維特因失戀而自殺,但歌德卻活了下來且寫了這部小說,因此僅憑這一點即可以說《少年維特之煩惱》是虛構的。在法國19世紀初葉,夏多布里昂以在美國與當地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的經歷為原型,用流麗的文筆寫了小說《勒內》(1802),描寫了回到巴黎的青年的憂愁,開拓了“近代憂愁”的表現手法。自由主義政治家本杰明·貢斯當也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名作,其中,《阿道爾夫》(Adolf,1816)細致地描寫了主人公對于愛情的倦怠以及被女人吸引時的心理,被譽為心理分析小說的杰作。
但是,在以野史小說、傳奇小說為發端的東方小說傳統中,不會將自身體驗虛構化,即使在江戶時代發行的大量戲劇作品中也沒有一個這樣的作品。明治時期,用各種口語體來書寫一般文章的習慣早已在江戶時代的平民百姓中得以普及,小說類多以“なり、たり”結句的文語體來書寫,在這些所謂的“言文一致體”小說的嘗試中,雖然有幾部作品是以第一人稱視角來寫的,但并非以作家的自身經歷為題材寫就的。
因此,田山花袋將其與女弟子之間實際發生的事情為題材而寫的《棉被》(1907)被看作日本最早的“私小說”。作品描寫了主人公“我”對女弟子抱有的情欲,被稱作“自然主義”。然而,這部小說用一種讓世間作家感到滑稽的方式描述了一副道學家的面孔,達到一種自我嘲諷的效果。
田山花袋在創作時應該意識到了約翰內斯·弗爾凱特(Johannes Volkelt)在《美學上的時事問題》(Asthetisce Zeitfrangen,1895)中所說的“揭露深奧、神秘內心世界的‘后自然主義’”。弗爾凱特看到原本呈現“自然主義”風格的作家們開始傾向于神秘童話等象征主義時說道:雖然大家都說“自然主義結束了”,但自然的“揭露深奧、神秘內心世界的‘后自然主義’與象征主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且近代人“神經質”的特質使人們比起“現實的感覺”越來越注重“空想的感覺”。森鷗外把這個翻譯成《審美新說》并作了介紹(《柵草子》1898—1899年連載,1900年出版發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田山花袋在《小說中的象征諸派》(《早稻田文學》1906年2月號)中指出:梅特林克、于伊斯芒斯、易卜生們“欲在自然主義的核心下創出新意”,因此可以斷定田山花袋應該讀過《審美新說》,而且他一定也想創造出自己的新意。但是,隨著片上伸的“人生觀上的自然主義”(《早稻田文學》1907年12月號)的提出,“自然主義”被當作性欲的代名詞,這也成為“自然主義”在1910年衰退的原因。
實際上,隨著“私小說”的方法傳播開來,在德田秋聲一派,即在所謂的“自然主義”作家中間流行起來,他們還寫出了類似于身邊雜記的一些作品。因向往法國浪漫主義而立志成為作家的宇野浩二也寫了與諏訪市藝人之間的愛情為題材的“私小說”,但在小說《甘き世の話》(1917)中寫道:“近來小說界的一部分作品”,不介紹容貌、職業、性格等情況,“突然冒出來一個不知所以的‘我’”,“盡寫一些奇奇怪怪的感想”。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使人們誤認為“‘私’小說”的創作就是把作家自身的經歷原封不動地寫下來,這也給周圍的人帶來了麻煩。這里所說的沒有小說樣的小說,指的是以志賀直哉的《在城崎》(1917)為代表的隨筆形式的作品,是從它與起源于歐洲自敘體小說的“私小說”不同這個意義上來說的。
志賀直哉年輕時寫過以描述自己內心活動為主的《某個早晨》,有一天寫稿時在筆記本上注上了“非小說”字樣。1920年前后在《新潮》等刊物上,包括小說講述者是否使用“我”來講述等問題成為當時討論的話題。擔任過《新潮》編輯的作家中村武羅夫在“寫實小說與心境小說”(《新小說》1924年1月號)中,將“心境小說”與俄羅斯的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1865—1869)等歐洲的長篇大作相比較,并進行了批判。盡管是對宇野浩二提出問題的誤解,但文中對“心境小說”作出了說明,即“作者直接出現在作品中的小說”,“專門講述作者心理的小說”,這明顯是在指隨筆的形式。
我們知道,前面提到的池田龜鑒在《自省文學的歷史性展開》中提出的“最直接地講述自己真實的內心”的說法也是基于此說。即“心境小說”是指無需客觀地介紹作家情況,以講述自己內心世界為主的作品。
久米正雄在《‘私’小說與‘心境’小說》(《文藝講座》1925年1、2月)中主張:不論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還是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都只不過是“偉大的通俗小說”,“真正的‘私小說’同樣必須是‘心境小說’”。這其中包含了俳句中所說的“腰のすわり”以及一種東方的求道的思想。“通俗小說”是相對于“歷史小說”而言的,指當代風俗小說,但在這里有著強烈的面向大眾的意味。后來,久米正雄認為寫“心境小說”的作家生活會難以為繼,因此又倡導了“純文學余技說”(1935年4月)。
另外,宇野浩二在《‘私小說’之我見》(《新潮》1925年10月號)中,在講述了自己曾經關注過“白樺”派的“自我”哲學的問題后,對葛西善藏的《柯樹葉》《湖畔手記》(1924)用隨筆形式記述面臨落魄、毀滅的心境以及接觸大自然后得以慰藉的心境的價值給予了肯定,承認了“心境小說”雖然“在形式上超乎尋常”,但確是一種“私小說”。同時宇野浩二還談道:“我們不能期望日本人寫出巴爾扎克式的正規小說,同樣也不能期待西方人創作出芭蕉或善藏那樣的藝術。”宇野浩二也開始考慮所謂符合日本人的小說的寫法了。久米與宇野兩人的學說都是文化相對主義時代的產物。
佐藤春夫則不同。他在“關于自敘體小說”(1926)中談到了真實告白的困難及反社會性,在“‘心境小說’與‘正規小說’”(1927)中,將“私小說”比作建立在作家自身基礎上的浮雕,將“心境小說”說成是散文敘事詩一樣的“變態”小說,是生活在狹小文壇中的“早老者的詩”。這里的“變態”與宇野浩二所說的“超乎尋常”應屬同義,因為隨筆形式在歐洲并不被承認是小說。
佐藤春夫的《田園的憂郁》(1919)是一部“心境小說”,作品描寫了在城市受傷的神經對田園生活的興致以及由于神經患病而感受到的美,在當時的文學青年中掀起了一股熱潮。不過,由于故事講述者的生活狀況也被寫在內,之后這也成為了“私小說”和“心境小說”在形式上的區別變得含混不清的原因。
佐藤春夫在將《病了的薔薇》(1918)改寫成定本《田園的憂郁》的過程中,把故事講述者(主人公)只知道作一些平庸的俳諧來消遣改寫成了沉浸在松尾芭蕉的世界里。但作者在小說的結構上并未做改動,仍將自身境遇比作親手精心培育的、被蟲蠶食了的薔薇,最后以一句“你是患了薔薇病了吧”的感嘆來結尾。明治末期,蒲原有明在象征詩集《春鳥集》的序言中介紹歐洲象征主義時,以松尾芭蕉的世界為范本,展示了日本人如何用簡單的語言展現高深的意境,在象征詩人中掀起了再評價之風。
佐藤春夫在“《〈風流〉論》(《中央公論》1924年4月號)中寫道:在天地自然間感受“悲愁”和“喜悅”融為一體的感動以及“宇宙與永恒似乎相連的那種真實的閃光的瞬間”,“渴望能設法將其變成永恒”,并想把此愿望留在作品中,此乃藝術的根本要求,而且,人的意志從中世的“物哀”即“無常觀”中脫離出來,完全與宇宙融為一體,達到心神合一,將那種瞬間的感覺表達出來的正是松尾芭蕉的藝術,松尾芭蕉的藝術與波德萊爾等的頹廢美學有共通之處。同時,佐藤春夫還主張將其視為判斷一部作品能否從極度關注人類思想矛盾與沖突并構成審美藝術的近代小說(以巴爾扎克為代表的近代小說)中脫穎而出的標準。這也表明了一種文藝上的“近代的超克”的意識。
1935年,東京帝國大學國文科出身的作家舟橋圣一,大概受到池田龜鑒命名的自省文學作品群的影響,借橫光利一的《純粹小說論》和小林秀雄的《私小說論》的對戰,在《關于私小說和主題小說》(《新潮》10月號)中提出了“私小說傳統”的觀點。舟橋圣一說:“今天的私小說”是平安時代女流日記文學“殘留的尾巴”,而“隨筆文學”的淵源是鴨長明的《方丈記》(1212)①根據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項目研究員石川肇氏提供的材料。。
正是在這種爭論的背景下,人們越來越分不清小說和隨筆的區別了。志賀直哉很早就開始寫《某個早晨》(1908)、《到網走去》(1910)等短篇小說,從內心世界挖掘自我意識的細節變化。前面談到過,志賀直哉在撰寫《某個早晨》的底稿時在筆記本上留下了“非小說”的字樣。但是,比如他曾把刊登在雜志的隨筆欄中的《偶感》(1924)編入創作集《雨蛙》(1925)中,1927年又把接到芥川龍之介自殺的訃告后寫成的回憶文章《沓掛にて——芥川君の事》(后改為《沓掛にて——芥川君のこと》)編入了短篇小說集。關于這一點,他在《續創作余談》(1928)中明確指出:也許應將追悼文編入追悼文集,但是,用心寫的文章或明確表達自己心情的文章也可視為一種“創作”,對此不作明確區分。志賀直哉不區分虛構與非虛構的區別,可謂之思想犯。
志賀直哉隨筆形式的作品《在城崎》,描述了作者經歷交通事故后前去城崎溫泉療養,在那里目擊了三個昆蟲或小動物的死而深切感受到了生死無常的一種心境。志賀直哉在《創作余談》中寫道,《在城崎》是按照實際經歷寫的“描述事實的小說”,“即便所謂心境小說,也是由余裕中誕生,并非心境”②『志賀直哉全集6』,巖波書店1999年版,第208頁。。這里的“所謂心境小說”是在當時人們紛紛議論俳句、議論余裕有無的語境下而言的。
另一方面,新潮作家崛辰雄也在隨筆《嘉村先生》(1934)等作品中談道:“無論是實際存在的、還是實際發生的,抑或是自己想象的,都是自己意識內的事情,在這一點上都是一樣的”。如此一來,隨筆與心境小說的區別愈發模糊了。
此外,在1920年代的“隨筆”全盛期,岡田三郎把由法國的民間傳說、寓言之類發展而來的“幽默小故事”介紹到了日本。比如沙爾·波德萊爾的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Charles Baudelaire.Le Spleen de Paris.1869年死后刊行)中即含有類似幽默小故事的成分。法國象征詩巨匠斯特芳·馬拉美不僅研究希臘神話,還研究了印度民間故事,他將收集到的印度民間故事都整理在《印第安人·幽默故事》(Contes Hindienne)中。在打破定型韻律詩規范的散文詩這一新類別的形成時期,民間傳說、民間故事、寓言類相互交叉,“幽默小故事”與之結合在一起傳入日本后,就與諷刺幽默、輕巧的“小噺”(小笑話)摻雜在一起,獲得了強勁的發展。眾所周知,川端康成將其命名為“掌篇小說”并進行了大量的創作。但是其中很多作品都沒有與“隨筆”相區別。因此可以說,自由書寫自己所思所想的“隨筆”與將作者意識里的東西進行再創作的20世紀小說的創作方法之間的區別并沒有被人們所在意,一直模棱兩可地發展至今。
安德烈·紀德寫過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論》或長篇小說《偽幣制造者》(1905)。其中,《偽幣制造者》采取了作品中小說家艾杜瓦的日記與故事情節同時展開的方式,艾杜瓦的日記中記錄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是當時在場的各式各樣的人物來講述的,讀者可以通過艾杜瓦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得知《偽幣制造者》小說情節發展的情況。紀德在作品中把唯一的“浪漫”稱作“純粹小說”。受到紀德作品的啟發,1935年,橫光利一在《純粹小說論》中指出:要想將以復雜的現代社會為舞臺的風俗小說采用第一人稱視角的“私小說”的形式來創作,有必要充分利用偶然性來引起讀者的興趣,抑或使用除主人公=作者的第一人稱視角之外的“第四人稱”(即作家統率小說世界的思想)。對此,小林秀雄在“私小說論”中談道:不能只模仿外國作品的形式,“私小說”之所以能在日本盛行是因為實證主義沒有在日本扎根,并且“多余的舊肥料太多了”。“多余的舊肥料”指的是俳句。這是小林秀雄出于知識分子應該對滿洲事變后的社會積極關心的態度而提出的。①鈴木貞美:『入門日本近現代文蕓史』,平凡社新書2013年版,第3章第3節。
此次爭論中,久米正雄提出了“純文學余技說”,菊池寬在“日本的現代小說”中也提出:“私小說或者身邊小說”就是描述“與俳句所表現的達觀相似的平靜心情和在非社交性的自我本位世界中的生活的作品”,是“日本文學的特色”②鈴木貞美:「菊池寛『日本の現代小説』―近代文學史観を狂わせた元兇」,『Japan To-day研究―戦時期「文藝春秋」の海外発信』,作品社2011年版。。此次爭論帶來了不小的影響。其中有舟橋圣一的《關于私小說和主題小說》(《新潮》10月號)。舟橋圣一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文科,在學期間接受過藤村作的指導,可能受到池田龜鑒命名的自省文學作品的影響,提出了“私小說傳統”。舟橋圣一認為:“今天的私小說”是平安女流日記文學“殘留的尾巴”,而“隨筆文學”的淵源是鴨長明的《方丈記》(1212)③根據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項目研究員石川肇氏提供的材料。。另外,“主題小說”受到了菊池寬的影響,他主張小說的主題即是“作家想要表達的東西”④鈴木貞美:『「文藝春秋」とアジア太平洋戦爭』,武田ランダムハウス講談社2011年版,12第2章。。
江戶時代,雖然各種通俗文學盛行,可沒有人把自己的內心活動以小說的形式寫出來,也沒有出現任何與“私小說”類似的作品,隨筆也傾向于考證。如果沒有來自西洋的刺激,無論是“私小說”還是隨筆都不會誕生。正是由于對這一點的忽略,人們才會去談論平安時代以來的“私小說”傳統的問題。戰后,在說法上也有人稱為“私小說的風土”。
七、研究仍將繼續
舟橋圣一的意見中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隨筆文學”的淵源是鐮倉時代鴨長明的《方丈記》。很明顯,他不承認平安時代中期清少納言的《枕草子》是隨筆。自江戶時代起《枕草子》即因其題名被稱為放在枕邊的隨手筆記,而不被視為“隨筆文學”應該是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文科的主流意見吧。
今天,《枕草子》《方丈記》《徒然草》被稱為日本的三大隨筆。《枕草子》是隨筆形式的作品,卻明顯表現出了對文體的關心。可能正因如此,《枕草子》得到了藤原定家的高度評價,后被北村季吟繼承,而且即使按照西歐的隨筆標準來看也會得到好評。
那么,鐮倉時代末期的兼好法師的《徒然草》又如何呢?此作品發行后約百年未引起世人的關注。后來,在連歌師中得到好評,至江戶時代成名。這也是作品的風格或作家的姿態讓我們覺得有趣的地方吧。《徒然草》是從《枕草子》中得到啟發創作的,作品中出現了名字,在江戶時代已有相關論述,據說在江戶時代就已出現將《徒然草》稱為“隨筆”的文章。但是,塙保己一的《群書類聚》卻連“雜”部都未將其收錄其中。
明治時期,在三上參次的《日本文學史》下卷中,對《方丈記》有如下評價:“說是隨筆又像日記,說是日記又像隨筆”,居于《枕草子》之下,基本可與《徒然草》并列。從此評價來看,三大隨筆說的出現好像也較為合理。芳賀矢一的《國文學史十講》中將《枕草子》和《方丈記》稱為“隨筆”,但藤岡作太郎的《國文學史講話》中卻未將《枕草子》視為“隨筆”。似乎三上參次的觀點并沒有得到普及。而且,《方丈記》的風格與其他兩部截然不同。
那么,《枕草子》《方丈記》《徒然草》被作為日本三大隨筆的觀點是何時形成、又如何得以廣為流傳的呢?我推測可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國語教科書的輔助教材以及考試參考書的普及得以廣泛傳播的。此類問題既是類別概念的問題,同時也是評價史的問題。研究仍將繼續。
(責任編輯:陸曉芳)
I0-03
A
1003-4145[2015]07-0074-13
2015-04-12
鈴木貞美(1947—),男,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名譽教授,國際知名學者,曾獲日本大眾文學研究獎,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近代文學。
譯者簡介:黃彩霞(1978—),女,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吉林華橋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近現代中日文學、文化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