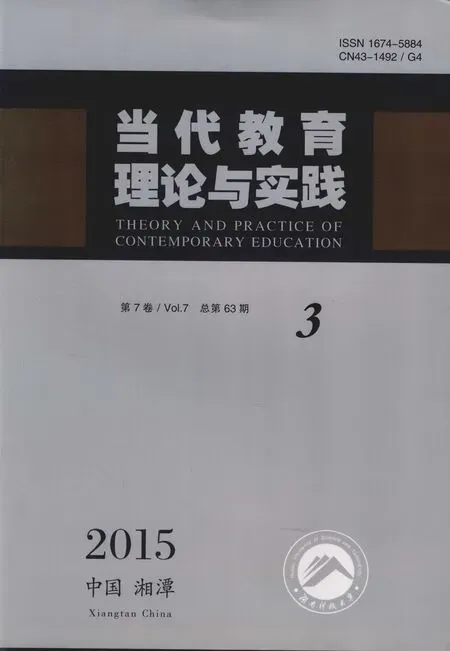安德魯·馬維爾詩歌對宮廷愛情傳統的繼承與反叛
侯夢縈
(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長沙410000)
學術術語宮廷愛情(amour courtois)最早出現于法國學者加斯頓·帕里斯(Gaston Paris)1883年發表的文章中。這一術語在學術界引起了十分熱烈的討論,百年來也無法達成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宮廷文學表達愛情的形式花樣繁多,不同作者所強調的主題內容也大不相同[1]451。實際上,根植于宮廷的社會構想體系中的這種愛情往往被認為是只存于詩人想象中的一種烏托邦式社會空想。這種追求完美的社會理想體現在宮廷文學(尤其是宮廷詩歌)中對宮廷禮儀、宮廷美德的強調上。所以,盡管宮廷愛情的主題內容大相徑庭,但總體上強調的是能體現宮廷禮儀的為女士效勞的概念,追求的是理想而不可得的完美愛情。
彌爾頓1653年2月21日寫給約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的關于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的就職推薦信上說,從1642年起,馬維爾在歐洲大陸游學4年并熟悉了法語、西班牙語、荷蘭語和意大利語。這4年間,他接觸到了這些國家的精英文化與獨特傳統[2]19。此外,英國文藝復興時期,伊麗莎白一世復興了埃莉諾(Eleanor of Aquitaine)12世紀帶到英國的宮廷愛情理想,鼓勵侍臣們追求、侍奉她。西德尼(Philip Sidney)、斯賓塞(Edmund Spenser)甚至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都寫過相關作品。到了17世紀,也有騎士派詩人濫用宮廷愛情詩歌風格來引誘女性的詩歌和玄學派詩人刻意嘲弄這一文學傳統的作品出現。所以馬維爾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宮廷愛情傳統的影響。
在馬維爾的抒情詩歌中,不僅可以找到他對宮廷愛情文學傳統的繼承,也不難發現這個曖昧的(ambiguous)政治家、曖昧的詩人,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展現出與宮廷愛情相悖的風格。總體來說,馬維爾對宮廷愛情傳統的繼承與反叛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部分。
1 為女士效勞與引誘女性
被認為影響了宮廷愛情詩歌發展的奧維德(Ovid)曾說過:“所有墜入愛河的人都會像戰士一樣為自己的心上人效勞。”[3]18在其詩集《愛的藝術》(Ars Amatoria)第二卷中,說到了如何具體實施這種效勞:“如果你正在鄉下,而她托人送信,信上書寫的是‘請君速來’,請馬上動身吧,因為阿漠爾總是憎恨行動遲緩的家伙。此時,即使沒有車馬,也應拔腳就走。無論是雷雨、酷暑還是霜雪,都不應成為你前進路上的阻礙。”[4]185實際上,奧維德提出這些建議是為了嘲諷那些號稱為了愛情做出這樣荒唐行徑的人。然而后來,這些行為卻成了宮廷愛情的行為準則[5]6。
一般來說,敘事文學中通常以騎士驕人的戰績、功勛和競技業績來為女士效勞。傳奇故事《蘭斯洛特》中騎士蘭斯洛特和亞瑟王之妻格溫娜維爾(Guinevere)的感情可以說是宮廷愛情的典范。在營救格溫娜維爾的過程中,蘭斯洛特在劍橋(sword bridge)上九死一生,路途中經歷幾次決斗并在最后關頭聽從格溫娜維爾的話停止與敵人的決戰。游吟詩人(troubadours)則以贊美她們的詩篇來為女士效勞[1]454。受埃莉諾資助的著名游吟詩人旺塔多恩(Bernart de Ventadorn)曾為諾曼王后寫到:“我無法真實的描繪她/她氣質典雅,形容甜美。”①原句為“Si.n voli’esser vertaders,/Tan es cortez’e ben estans”,從克萊恩(A.S.Kline)的英譯版轉譯。游吟詩歌中總是抒發對冷漠無情的女士炙熱的類似宗教般的崇拜之情。這種感情常常表現為諂媚、忠誠和對女士外貌過高的贊揚上。
在馬維爾為數不多的詩歌中,這種恭維、崇拜的主題時有出現。以詩歌《畫廊》(The Gallery)為例。敘述者在想象中邀請摯愛克羅拉(Chlora)來參觀他腦海中的畫廊。畫廊里陳列著千萬幅她的肖像畫。通過動態地展現其中5幅畫,詩人描繪了兩對截然不同卻同樣驚艷的女性形象。她們在吸引畫廊主人的同時給了他無盡的折磨。克羅拉既是一個美麗的殺手——以自己冷漠的“黑眼睛”,性感的“紅唇”,狂野的“卷發”作為武器;又是一個誘人卻無情的女巫——挖出愛人的腸子用來占卜自己容顏的限期,爾后殘忍地將之拋棄給貪婪的禿鷹。
同時,她還是純潔的宗教形象——曙光女神奧羅拉(Aurora),愛與美的女神維納斯(Venus)。她慵懶地躺在東方的天空上,伸長“雪白的大腿”。馬維爾在此連用了多個宗教意象來體現對女神克羅拉宗教式的崇拜。如“清晨的唱詩班”“天賜之糧(manna)從天而降”和“求偶的白鴿”。同時,使用帶來祥和寧靜(halcyons)的嗅覺意象“龍延香”的氣息,營造了一個人間天堂。
最后說話人帶我們參觀了位于畫廊入口的那張他最愛的畫像:“柔情的牧羊女,秀發/在風中恣意飄散,/青山上采來的野花,/為她加冕,捧于心間。”[6]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克羅拉的畫面,也是他陷入愛戀的那一瞬間。畫中,她站在山間,發舞飛揚。最后一句,馬維爾謙卑地用花環替她加冕。即使克羅拉變化無常,讓敘述者倍受折磨,在他的內心深處,仍愿意讓她做自己的女王,任其差遣。
再看《致羞怯的情人》。詩中講述者用了宮廷愛情詩歌最傳統的方式來贊美情人:“我可以用上整整一百個年頭/來凝視你的面龐,贊美你的眼睛,/用兩百年來愛慕你的酥胸,/用三萬年來崇仰你的全身;/你的每根頭發都得愛一個世紀,/待世界末日才窺視你的芳心。”[7]
乍看之下,這是用宮廷式的禮節來追求情人,以長足的耐心來為她效勞。但若注意到開篇的虛擬語氣——“假若”(Had)我們有足夠的時間空間,就能發現這看似忠誠的效勞:去恒河為她尋找紅寶石,從洪水②《舊約·創世紀》中記載的大洪水。前十年就開始耐心地愛慕追求她,慢慢展開戀愛過程,都只是虛擬的。這長篇大段只不過是為了引誘情人放下矜持、縱情享樂的三段論(syllogismos)中的第一步而已。
詩歌的第二部分從“但是”開始,語氣急轉。用焦急地語氣寫出時間的緊迫(“時間的飛輪正匆匆逼近”),并通過“沉寂的永恒”“蛆蟲”“灰燼”“墳墓”等黑暗的意象,大膽描繪殘酷場景:“那時只剩下蟲豸蠹蛆/來品嘗你長久保持的童貞。”[7]從心理上擊潰情人,放松她的防線。
詩的最后一部分也嚴謹地遵照三段式的措辭,用“所以”一詞引出這一部分及時行樂(carpe diem)的結論:“能歡娛之時讓我們盡情歡娛,/就像一對相親相愛的飛鷹。”[7]至此,達到了勸服情人收起羞澀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17世紀,宮廷求愛方式常與源于賀拉斯(Horace)的及時行樂主題相結合,被騎士派詩人用于引誘保守的女士享受情愛的歡愉。而從《致羞怯的情人》中夸張的語言風格、露骨大膽的措辭,不難看出馬維爾對被濫用的宮廷愛情傳統的嘲諷。
2 無回報的精神愛戀與靈肉合一
“精神戀愛是宮廷—騎士愛情的最高形式,這種看法源自這樣的觀念:只有當男人的情欲沒有得到肉體的滿足時,才能發揮愛情的凈化和升華作用。”[1]459由于中世紀對真愛的不可滿足的性質的強調,法國、德國的游吟詩歌中充滿了對無結果的愛戀的哀嘆。12世紀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仿效奧維德《愛的藝術》所著的關于宮廷愛情游戲規則的《愛情論》(De amore)第二卷中也提醒淑女們,難以獲得的愛情才最珍貴:“愛情越易得到越沒價值;難以獲得才更可貴。”[8]185
除此之外,中世紀貴族社會大多因為利益、政治原因結姻。夫妻之間幾乎不可能產生愛情。于是,愛情只能在婚外生存:常發生在騎士、廷臣與其所侍奉的主人的妻子之間。然而追求這樣一份美好愛情(fin’amor),對處于封建社會、被嚴格管轄在丈夫城堡中的貴族女士來說是致命的。這便使得宮廷愛情必須保密,也難以圓滿。
宮廷愛情的這一特征在意大利文學作品中得到充分發揮。在但丁的《新生》(La Nuova Vita)以及《神曲》(La Divina Commedia)中都描述了他對貝雅特麗齊(Beatrice Portinari)的單戀。同樣,彼特拉克(Petrarch)也在十四行詩中抒發了他對勞拉(Laura)的愛。這份無望的愛逐漸在他詩歌中轉化成不可解的傷痛:“我的全部戰爭已然結束,卻無法平靜;/我懼怕著、希望著,我燃燒著卻凍結成冰。”③彼特拉克《歌集》第134首,從托馬斯·懷特(Sir ThomasWyatt)的英譯版轉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受彼特拉克影響很深的詩人西德尼和斯賓塞也寫了許多抒發類似情感的詩句。
有別于前輩們在詩中大書對得不到的愛戀的悲痛之情,馬維爾處理這個題材時,更著力于描述這樣一份愛情的本質。在《愛的定義》(The Definition of Love)中,詩人以“我的愛”(my love)開篇,不對自己的愛人(my love)訴說,卻在描述我的愛的本質。它萬分“珍貴”“神圣”,目標“獨特而崇高”。從“絕望”中孕育而生,超越一切“不可能”。“獨特而崇高”(strange and high)一詞說明這份愛情本質上是純粹的、唯一的、神圣的。與“絕望”“不可能”相結合,暗示著愛人的地位也是“獨特而崇高”的。“唯有這慷慨的絕望/方可向我展示如此神圣的事”[6],而“希望”不能。這說明無望的愛才使其更加動人,無法被滿足激情才使其出奇珍貴。
為什么敘述者的愛情如此的絕望?是因為“命運”(Fate)嫉妒他倆結合,將他與戀人放置在地球的兩極,讓他們就像兩條平行線,永遠無法相遇相擁。唯有以毀掉整個地球為代價,使天堂坍塌、大地震裂,將地球壓扁成一個平面(cramped into a plainisphere)他們才有可能在一起。更進一步分析這個奇喻,不難看出馬維爾在此詩中更傾向于無回報的精神愛戀而非肉體的結合。“整個愛情世界”(love’s whole world)被比作地球,這對完美的戀人被比作地球的兩極。分離時,愛情得以長久維系(“愛情世界圍繞著我們運行”)。一旦相結合,愛情便崩塌。
在詩歌的最后一節,馬維爾又強調了命運的無情離間,總結這份愛的本質——身體相隔心卻相連。
然而,馬維爾想強調的并不完全是這種“純粹的愛”(“pure love”)(卡佩拉努斯提出的不包含肉體結合的愛,與“混沌的愛”(“mixed love”)相對應),而是柏拉圖在《斐德羅篇》(Phaedrus)中提到的,與“性快感”(“sexual pleasure”)相對應的“激情的愛”(“passionate love”)——強調精神與身體的融合。這在他的詩作《科羅琳達與戴蒙》(Clorinda and Damon)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詩歌開頭部分,科羅琳達試圖用“及時行樂”的論調說服牧羊人戴蒙“抓住稍縱即逝的快樂”,同她一道去他們常去的人跡罕至的洞穴中共享歡愉。戴蒙卻堅定地拒絕了這曾經誘人的邀約,轉而說到“道德”“靈魂”與“天堂”。由此可以看出,在這首對話體詩歌對話的兩派中,科羅琳達代表了肉體、歡愉、罪惡和女性;戴蒙代表著靈魂、道德、信念和男性。對話在相互對立的對話者中展開。
戴蒙之所以拒絕了科羅琳達,是由于他遇見了天神潘(Pan)后就只為他唱贊歌了。潘有兩種不同的形象:一是希臘神話中長著羊角的男性生殖神,他掌管著牧人、牛羊、森林與草原;另一個是好牧人(Good Shepherd④好牧人是《約翰福音》第十章十一到十二節中給耶穌基督的稱號。)耶穌基督,將羊群領到青草地上。彌爾頓的詩《圣誕清晨贊美詩》(Hymn on theMorn-ing of Christ’s Nativity)中也用過“偉大的潘”(“themighty Pan”)來指代耶穌。在此,潘是一個既情色又純真的形象。
對話雙方在結尾合唱部分達成了和解:無論潘激發了身體或是靈魂都不重要,因為全世界都是潘的唱詩班(all the world is our Pan’s choir)。正如潘看似對立卻兼容的雙重形象,代表肉體的科羅琳達和代表靈魂的戴蒙,在最后得到了融合,共同為潘高歌。
3 結語
在這樣一個動蕩時期,為了發出新時代的聲音,反叛舊有傳統、建立新興傳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即使如此,無論自愿與否,舊有傳統都不可避免的留有痕跡。在馬維爾以及其他玄學派詩人甚至騎士派詩人身上,我們不難看到他們對像宮廷愛情一樣的古老傳統的繼承。然而,承受著前輩詩人帶來的焦慮感,他們只能盡量反叛。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永遠留在文學史冊上。
[1]約阿希姆·布姆克.宮廷文化:中世紀盛期的文學與社會[M].何珊,劉華新,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
[2]Birrell Augustine.Andrew Marvell[M].London:Macmillan & Co.Ltd,1905.
[3]Jestin Charbra Adams,Katz Phyllis B.Ovid:Amores,Metamorphoses:Selections[M].Mundelein:Bolchazy-Carducci Publishers,2000.
[4]奧維德.愛的藝術[M].寒川子,譯.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
[5]Lewis C S.The Allegory of Love: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M].Oxford:Oxford U.P.,1936.
[6]Marvell Andrew,Rogers Henry.The PoeticalWorks of Andrew Marvell:With Memoir of the Author[M].London:Alexander Murray,1870.
[7]曹明倫.外國抒情詩賞析辭典[M].北京: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1.
[8]Capellanus Andreas.The Art of Courtly Love[M].Trans.John Jay Parry.New York:Columbia U.P.,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