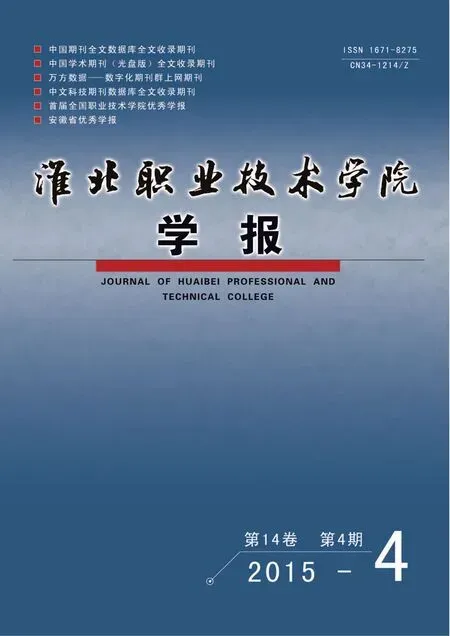莊子《理想國》芻議
·哲學與政治研究·
莊子《理想國》芻議
李慶寶
(淮北市委黨校,安徽 淮北235000)
摘要:莊子所崇尚的理想國不過是部落社會的幻景而已。但是,處于戰國時期的亂世之中,莊子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前景感到恐懼,看不到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因而只能主張回到人類的嬰兒時代,回歸人類文明的元點——部落式洞穴文明時代。莊子式的恐懼與反叛,其實正代表著早熟的中華文明所遭遇的成長中的煩惱。
關鍵詞:理想國;至德;原始部落
收稿日期:2015-06-19
作者簡介:李慶寶(1966-),男,安徽淮北人,淮北市委黨校教授,研究方向為哲學、公共管理。
中圖分類號:B2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275(2015)04-0001-02
部落文明時代并不是人類最為理想的社會,這是顯而易見的。莊子所崇尚的理想國不過是部落社會的幻景而已。但是,處于戰國時期的亂世之中,莊子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前景感到恐懼,看不到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因而只能主張回到人類的嬰兒時代,回歸人類文明的元點——部落式洞穴文明時代。莊子式的恐懼與反叛,其實正代表著早熟的中華文明所遭遇的成長中的煩惱。通讀整部《莊子》,我們分明能感覺到,莊子所勾畫的理想國圖景其實就是對原始公社、部落社會理想化生活的懷念與向往,同時也是對強權暴政下王權專制主義社會的控訴。
一、“至德之世”是莊子追求的夢想
春秋戰國時期,幾乎每個思想家都有他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國”,莊子亦不例外。那么,莊子所構建的理想國圖景是什么呢?“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游。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1]。所以,在上古人類天性保留最為完善的時代,百姓行動從容,目光專一。那時候,山上沒有路徑和通道,水面上沒有船只和橋梁;萬物共生,不分鄉里,比鄰而居;禽獸成群,草木茂盛。因此,禽獸可以讓人用繩子牽著游玩,鳥鵲的巢窠可以任人爬到樹上窺探。在那人類天性保留最為完善的年代,人類跟禽獸雜居,與萬物共處,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天真而無知,就不會離開原始的狀態;樸實而無欲,就叫做純真實在。能夠保持純真實在,人類的天性就不會改變了。
那么,“至德之世”存在于哪里呢?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1]。在那個時代,百姓靠結繩的辦法記事,把粗疏的飯菜視為美味,把樸素的衣衫視為美服,把純樸的風俗視為歡樂,把簡陋的居所視為安適,鄰近的國家彼此相望,雞鳴狗叫的聲音也相互聽得到,而百姓直至老死也互不往來。像這樣的時代,就可說是真正的太平治世了。
莊子認為,在堯舜禹以前就有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這十二個時代是“至德之世”。然而,到了堯、舜、禹時代,中國人的純真本性逐步喪失,一切都開始改變了。在《莊子·應帝王》篇中,莊子認為,中國人在伏羲氏時代是完全擁有天賦本性的,而到了舜的時代,中國人的天賦本性就快要進入“非人”化的時代了——天賦本性已經到了不能再失去的時候了。舜的時代正是中華文明歧路開始出現的地方。歧路之后又有歧路,人類的天賦本性損而又損,中國人終于走入了春秋戰國那樣一個萬劫不復的歷史深淵。
莊子眼中的“至德之世”,就是人類天性最為純真的時代。因而,莊子的理想國亦即人類最為原始狀態的文明時代。
二、“至德之世”是基于部落文明的“泛愛”理論
莊子為什么如此向往原始部落社會?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原始部落社會與王權專制主義社會究竟有著怎樣的不同?
關于人類史前時期的原始部落社會究竟是一種什么狀況,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難有定論。我們可以避開那些導致爭論的關于部落社會的具體化描述,如原始部落社會是否實行原始共產主義制度,有沒有私有財產等,我們可以人類文化發生發展史的角度來探索人類史前時期在漫長的原始部落社會里的生存景況。
原始部落社會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人類對客觀世界缺乏認識,個體無法獨立生存,人們在一定地域形成了相對集中的群體性組織。這種組織以天然的血緣關系作為基本紐帶。一個部落可以分化為若干不同的部落;不同的部落之間也可以組成部落聯盟。部落之間可以相互合作,也有可能發生戰爭。現代人類學理論研究表明,原始部落社會有多種組織形式,不能僅僅從財產是否公有、部落成員之間是否平等方面來定性。部落成員可以集體生活,也可以分散生活,部落甚至可以成為村社式的分散性社會組織。部落社會的規模可以很小,也可以大到一個王國。在這種原始共同體社會里,由于面臨諸多外部壓力,如洪水猛獸以及來自其他部落的挑戰等,資源和產品可能接近于最低水平的平均分配。換句話說,由于剩余產品較少,如果存在大量的不平等現象,就會有相當一部分部落成員因為缺乏生存所需要的物資而死亡。實際上,由于血緣關系等基本紐帶的存在,也相應保證了部落社會最起碼的公平與平等關系的長期存在。因而,在這種社會更需要有一定能力的人來主導部落內部的財產分配與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動,這種人可以是長者或是部落(國)王,亦可為祭司。
雖然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平等,但在這種原始部落社會里,人們擁有共同的生活區間、共同意志與共同的價值取向。而這種低水平、低層次的公平與平等正是莊子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在“至德之世”,人們生活自然而任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們共同勞動,共同面對生存威脅;部落成員之間平等相待,對于不該得到的財產無私無欲;部落神是每個成員心中共同的崇拜對象,神的權威神圣不可侵犯;人立身于天地之間,與大自然和諧共存,像花兒一樣自然綻放,像嬰兒一樣純樸自得。
然而,在中國的中原地區,這種文明形式注定是要被打破的。部落之間的戰爭頻繁發生著,弱小的部落總是在兼并中消亡,直到出現更大規模的相對獨立的文化集團。歷史上的中國正是從“萬國”走向“一國”。
古代中華民族最為重要的有三大文化集團,即:華夏、東夷、苗蠻文化集團。據考證,華夏民族的活動地區始自西北(今陜甘地區),逐漸向今河南及山西境內拓展;東夷民族的活動地區主要在渤海沿岸,今山東地區,擴展于淮水沿岸。至于江漢及其南方,則為苗蠻民族的活動地區。三大集團的活動地區,體現出中國歷史上殘酷的部落兼并的基本軌跡。
與世界其它民族文化發生發展史相比,中華文明最為本質的特征是,中國中原地區的部落文明徹底走向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以家族歷史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的王權專制主義社會制度。表面上,這種文化仍舊以人類母體文明中的血緣關系為基礎,但最大的不同是,部落文明中可以在更大范圍存在的“泛愛”徹底消失了,社會上只能存在著家族/家庭式的“私愛”,西周時期開始形成的表面上溫情脈脈的禮樂文明就是以這種狹隘的“私愛”為基礎的。
那么,部落式的“泛愛”與家族式的“私愛”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部落文明時期,人類文化有一個相對完整的共同區域,人們在這個區域內可以擁有共同的愛,即“泛愛”;而部落文明消亡之后,人們所能表達的愛只能存在于家庭之中,即“私愛”。進一步說,部落文明與家族文明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區別呢?
部落與家族同是“洞穴”,從部落文明走向家族文明,雖然只是從一個“洞穴”跳到另一個“洞穴”,但洞穴所能承載的“愛”,其性質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們所“愛”的范圍大大縮小,人們原本共同擁有的廣場被不同的家族分成若干不相連的相對獨立的整體。具體地說,在“中國”這個大“廣場”上,遠古時期相對集中的部落文明可能有“萬國”之多,中國人在家族式血緣之愛的基礎上,還可以表達上萬種共同的部落式“泛愛”;但這種文明消亡之后,中國人只能表達家族式的小小“私愛”了。
從堯舜禹時代開始形成的家族/家庭式的私有制,實質上就是一種“天下”的私有化運動。從此,“天下”被瓜分,權貴成了惡狼,而人民卻只能淪為王權專制主義制度下的羔羊了。莊子清醒地認識到,無休止的人欲主導下的強權暴政改變了人類的天性,而這正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出現大亂的根源。
三、結束語
部落文明時代并不是人類最為理想的社會,這是顯而易見的。莊子所崇尚的理想國不過是部落社會的幻景而已。但是,處于戰國時代的亂世之中,莊子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前景感到恐懼,看不到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因而只能主張回到人類的嬰兒時代,回歸人類文明的元點——部落式洞穴文明時代。莊子式的恐懼與反叛,其實正代表著早熟的中華文明所遭遇的成長中的煩惱。
由此,我們得出結論,莊子所勾畫的理想國圖景就是對原始公社、部落社會理想化生活的懷念與向往,同時也是對強權暴政下王權專制主義社會的控訴。歧路正是出現在中國人從洞穴文明走向廣場文明的起點上,中國人選擇了一條并不完美的道路。這不由得讓我們想起歷史傳說中的“楊朱泣歧”故事。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跬步而覺跌千里者夫!’”[2]。也就是說,這是那錯誤地跨出一步后就已覺察走錯千里的地方吧!
參考文獻:
[1]包兆會.莊子[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林宏星.荀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張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