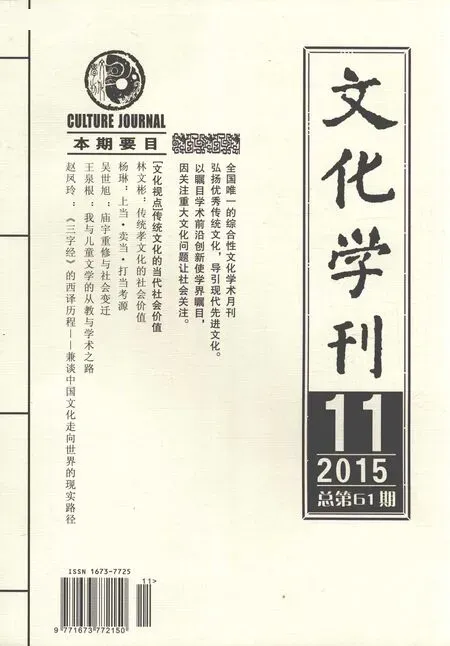海南政治格局的歷史變革與文化發展
段會冬
(海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海南 海口 571158)
長期以來,海南文化研究對宋元時期的貶官及明清時期有“濱海鄒魯之風”稱號的文化發展歷史的關注程度明顯高于隋唐之前的歷史。倘若上述兩個時期是海南文化同中原文化的兩次重要碰撞的話,那隋唐之前上萬年的歷史則是海南文化同中原文化的第一次碰撞。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階段,政治的動蕩雖然影響了海南文化的發展,但海南文化最終同中原文化逐漸建立起了密切聯系,并且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點。而這個過程中,冼夫人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隋唐之前國家的遙領與海南文化的緩慢發展
百萬年前,海南并非孤懸海外的小島,而是與雷州半島相連的大陸南端,然而,地殼運動使海南最終成為一個獨立的海島。[1]在交通尚不發達的時代,地理的隔絕對人類的進化與發展勢必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根據目前海南考古發現可知,在海南與大陸地理分離后的百萬年間,海南并沒有早期人類活動的痕跡。許多學者認為,這實際上表明海南島上的早期人類文化源自島外先民遷徙入島的歷史進程。[2]距今大約兩萬年的昌化江信沖洞遺跡和距今一萬年的三亞落筆洞遺址被視為海南先民最早的痕跡。這兩處文化遺存與大陸的越文化等文化遺存間存在的密切關聯,表明早在兩萬年前,海南島便已存在與大陸文化的相互交流,然而,史料和考古材料的匱乏使我們難以描述彼時海南與大陸間文化交流的清晰狀況。
公元前214 年,海南與中原政權的關系掀開了新的一頁。統一嶺南諸地的秦始皇卓有遠見地設置了象征一統皇權的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實現了中央王權對海南的“遙領”。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平定南越之后,漢武帝在海南版圖內設置了珠崖郡和儋耳郡,這標志著中央政權對海南直接統治的開始。《三國志·薛綜傳》記載:“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指使學書,使驛往來,觀見禮化。”[3]郡縣的設立,為中原與海南之間的人員流動創設了更為直接的政治條件,中原與海南的互動也成為影響海南發展的不容忽視的因素。
統治者對海南奇珍異寶與異樣風俗的過分關注,直接激起了海南先民的反抗。面對千里之外邊民的反抗,究竟是否要派兵進剿毒瘴蔓延的海島之亂,成為漢代統治者一個兩難的選擇。據《漢書·賈捐之傳》記載,自漢武帝初設郡縣至漢元帝始元年間在位的數十余年,海南大規模“叛亂”就有九次之多。[4]漢昭帝時,雖然將儋耳郡并入珠崖郡,但并未改變“叛亂”頻仍的局面。而彼時關東大地主兼并土地導致的民不聊生,使農民不得已揭竿而起的狀況動搖了漢朝統治的基礎。面對動搖根基的關東之亂與孤懸海外的海南之亂,漢元帝采用謀臣賈捐之的建議,罷棄珠崖郡。自此以后,海南文化的發展不僅失去了同中原文化進行交流的政治基礎,也開啟了此后數百年間海南郡縣廢立不斷的“常態”。在這種中原政治統治難以介入的歷史狀態下,海南文化的發展只能在相對封閉與隔離的狀況下緩慢前進。官方文化介入的微弱與不確定的民間文化交流的孱弱成為當時海南文化發展最為直接的寫照。總之,政治力量的動蕩帶來的近似真空的狀態使一海之隔的地理狀況對文化發展的限制作用被無情地放大。
二、冼夫人作為代理人的政治新格局與中原文化向海南的快速傳播
隨著歷史的發展,冼夫人的出現使隋唐海南與中原政權的關系有了新的歷史形態。冼夫人雖不是海南人,但在海南與中原政權的互動中卻扮演著重要角色。其確切的生卒年代正史中并未詳述,學界普遍認為,冼夫人生活的時間大抵為南朝梁武帝天監年至隋文帝仁壽年間,前后大約歷時九十年。這個時期恰是中原地區由戰亂紛紛向全國一統邁進的歷史時期。然而,在當時中原政權“遙領”嶺南的狀況并未根本改變。嶺南自古為越族的生活之地,《譙國夫人傳》記載,高涼冼氏“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余萬家”。[5]當時,作為世家豪酋的冼家在嶺南的影響絲毫不遜于中原政權派駐嶺南的地方官吏。這一點通過馮冼兩家聯姻的歷史事實可以得到證明。
冼夫人的丈夫名為馮寶,根據王興瑞的考證,馮氏祖先馮跋曾建立北燕政權。馮跋的弟弟馮弘趁馮跋病危之際襲取王位。由于政權勢力不足,因此北燕最終為北魏所滅,馮弘只能率國人投奔高麗國,然而與高麗王的矛盾使馮氏在高麗也無法久住。無奈之下,馮弘只能派遣其子馮業率眾人投奔南朝宋,自此不僅在嶺南安家,而且被朝廷委以郡守州牧之類的官職。[6]嶺南之地古越族部落眾多,各部往往據險而守,中原政權派遣的官員對各部落各自圈定領地的做法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馮氏家族雖未守牧也不例外,而作為嶺南俚人豪酋之家,冼家在嶺南本來就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再加之冼夫人對本宗之人嚴加戒約,即便是她的兄長冼挺,也在冼夫人的勸誡下收斂恃強凌弱的姿態。冼夫人的聲望在嶺南頗高,連海南先民的首領也紛紛歸附。為改變“號令不行”的局面,馮融決定為馮氏家族選擇一門重要的婚姻,即與俚人豪酋冼家結親。馮冼聯姻使馮家在當地的話語權陡然提升,“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7]
馮冼兩家的政治聯姻反映了馮氏家族的政治智慧,也反映了冼氏家族在嶺南的顯赫地位,更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魏晉至隋唐時期嶺南之地的政治現實。雖然隋唐中原政權強盛,但對這個邊陲之地的統治仍力所不及,因此,冼夫人與馮冼家族的存在使中原政權對海南的統治有了另一種治理方式。隋朝初年,冼夫人奉詔平亂的事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借助代言人實現統治的方式。
隋朝初年,番州總管趙訥貪虐過度,激起嶺南諸俚獠部落的紛紛反抗。冼夫人上書陳述趙訥的罪狀。面對大范圍的少數民族反叛,隋高祖并未派兵進剿,而是下詔委冼夫人以招慰叛亂之責。根據《譙國夫人傳》的記載可知,冼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余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可以說,冼夫人出色完成了隋高祖交付的平叛重任,然而,隋高祖以一封詔書以應對此事,究竟是一種“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高明決策,還是一項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當時,隋高祖派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南,但韋洸“逡巡不敢進”。直到冼夫人派人迎接,韋洸才到達廣州,嶺南之地才才算平定。由此可知,一方面,隋王朝的統治力量尚未改變嶺南的權力結構;另一方面,雖然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少數民族豪酋在嶺南掌握更大話語權的現實,但中原王朝已欣然接納了冼夫人的歸附,這成為當時海南與中原政權關系的另一種重要的歷史形態。
在冼夫人生活的時代之前,雖然海南已納入中原政權的版圖,但郡縣廢立不斷使海南文化發展長期處于缺少中原政權實質性介入的狀態,冼夫人的出現,使原本力有不及的中原政權擁有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治理海南的代言人,從而使海南文化發展獲得了穩定的政治局面,也使中原文化實質性介入海南。隨著統治力量的深入,海南文化的發展不斷注入外來因素。如在唐至五代時期,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相繼傳入海南,并獲得長足發展。閻根齊等海南文化研究專家根據唐史研究等相關文獻認為,海南島上最早設立的孔學也應在唐初;[8]佛教和道教建筑在海南最早于唐朝建立的史實也證明唐朝時期,海南道教與佛教獲得長足發展;[9]唐高宗時期,來自西亞和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和來自廣州等地的傳教士也將伊斯蘭教帶入海南。[10]因此,可以說冼夫人的出現,不僅結束了海南政治動蕩數百年的尷尬局面,也開啟了海南文化與中原文化全方位互動的歷史。
三、海南文化特征的初步形成
第一次文化碰撞,給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冼夫人“治而不獨”的國家意識。毫無疑問,冼夫人作為一個完全有能力在海南稱王的嶺南實質意義上的控制者,其維護國家統一與地方安定的決心的確令人稱道。周恩來稱其為“中國巾幗英雄第一人”也正是看重冼夫人對國家統一的巨大歷史貢獻。然而,冼夫人不僅是維護國家統一的民族英雄,也是開啟海南文化發展的關鍵人物。
在冼夫人之前的漫長歷史時期,雖然海南與中原地區的民間文化交流時有發生,但是,政治動蕩所造成的消極影響的確極大限制了海南文化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海南先民在長久缺失中原政權力量實質介入的情況下,逐漸形成了自己對國家的理解。無論是那些逃難至此的移民,還是久居此地深受動蕩、蟲瘴之苦的先民,他們對中原政權更迭的關注度遠不及其對冼夫人的認可,因為正是冼夫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終給他們帶來了和平與發展。換言之,與其說當時的海南民眾認可冼夫人本人,倒不如說他們認可冼夫人代表的和平與發展的文化符號。他們并不關注究竟誰坐擁天下,但他們著重關注自己能否安居樂業。這種淳樸的民本思想是海南先民在經歷了長久的政治動蕩、經濟發展滯后和蟲瘴頻生的惡劣環境后逐漸形成的對國家的認識。
不僅如此,當時海南先民對冼夫人的認可并沒有阻礙他們對其他文化的傳入。雖然唐朝時期,海南先民便給冼夫人建廟祭拜,但是,他們對中原地區傳入的其他宗教和文化并沒有采取拒斥的態度。不僅如此,從冼夫人治理嶺南為海南地區引入大量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方式開始,到隋唐時期大量中原先進文化的傳入,海南先民也并沒有孤島自封,而是懷有開放心態接納了這些“外來”文化。而之所以接納這些文化,不獨尊冼夫人文化,其背后的原因也十分簡單,只要能為生活的改善提供幫助,為自己尋找到生活的精神寄托,他們愿意接受來自各方的文化。閆廣林教授認為“海南文化信仰的關鍵在于神能否保佑他們順利、平安、丁旺、救苦救難、恩澤子孫,是直接的功利主義。”[11]這種帶有鮮明實用主義的開放心態,成為此后海南文化發展的重要特點。而功利主義與民本思想的疊加,恰是第一次文化碰撞中逐漸形成的海南文化發展的關鍵性特征。
[1]王俞春. 海南移民史志[M].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22.
[2]閻根齊.論海南古代文明的起源[A]. 海南歷史文化[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32-42.
[3]陳壽.三國志·吳書·薛綜傳(卷五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55.
[4]班固.漢書·賈捐之傳(卷六四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997-1998.
[5][7]魏征.隋書·列女傳·譙國夫人傳(卷八十)[M].北京:中華書局,1973.1800-1801.
[6]王興瑞. 冼夫人與馮氏家族[M]. 北京:中華書局,1984.17-21.
[8][9]閻根齊,劉冬梅.海南社會發展史研究[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174.175-180.
[10]符策超.海南文化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55-57.
[11]閆廣林.海南島文化根性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