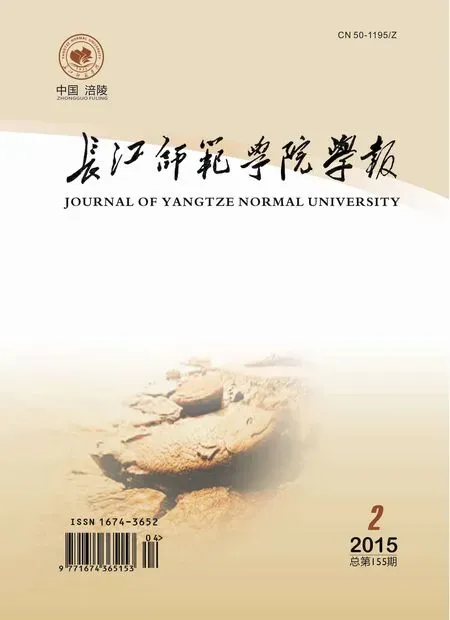文學如何“虛無”歷史?
文學如何“虛無”歷史?
魏巍,馬玥玥
(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中國文學研究所,重慶400715)
[摘要]2014年1月1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組筆談,就當前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一些討論。之后,《文學評論》在2014年第2期再次發起了“文學不能‘虛無’歷史”的筆談,就這一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對于當前的某些文學創作現象進行剖析,在我看來,這樣的討論無異于一個偽命題,文學雖然與歷史相關,但無論如何,文學畢竟不是歷史,而歷史也不是文學。
[關鍵詞]文學;歷史;文學“虛無”歷史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652(2015)02-0090-04
[收稿日期]2014-12-15
[作者簡介]魏巍,男(苗族),重慶酉陽人。博士,博士后。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少數民族視野下的沈從文、老舍比較研究”(13YJC751061)。
2014年1月1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組筆談,就當前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關系進行了一些討論。之后,《文學評論》在2014年第2期再次發起了“文學不能‘虛無’歷史”的筆談,就這一問題進行深入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引起我們興趣的,并不是因為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問題,而是《人民日報》“開欄的話”與學術界之間話語的錯位問題。
在“開欄的話”中,主持人這樣寫道:“文藝創作雖然活躍,當代文學主體理論建設卻嚴重滯后,對一些重要的文學原點問題的認識模糊,文學批評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導致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等現象滋生蔓延,對于文學創作和受眾鑒賞水平的提高產生消極影響。”[1]顯然,開設欄目所要討論的初衷是文學批評界的問題,可是,所有參與討論的人卻都把矛頭對準了文學創作,這不能不說是認識價值的錯位。
張江認為,“文學與歷史是分不開的。文學以自己的方式參與歷史建構和傳承。這不僅適用于歷史題材創作,而且也適用于一切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2]他的這一觀點后來得到了重申,在《文學不能“虛無”歷史》中,他強調說,“任何進入載體和介質的文學作品,也都在書寫歷史,文學與歷史互文互證。”[3]如果說論者所針對的現實生活中的穿越劇、宮廷劇、抗日神劇等文化現象,這種說法當然是站得住腳的,并且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說把這個觀點推而廣之兼及文學創作,則明顯超出了文章所能把握的理論范圍。在張江所言中,文學與歷史具有某種同構作用,我們不否認文學與歷史之間的緊密關系,但是,這兩者間的關系并沒有到共存亡的程度。我們只能說,在某種程度上,歷史會成為文學創作的題材,但是,并非所有的文學創作都與歷史相重合。除非能夠證明白流蘇這樣的女人與范柳原這樣的男人結婚,必須要以一座城池的陷落作為代價(張愛玲:《傾城之戀》)。那么,什么是文學?什么又是歷史?文學與歷史之間究竟有著什么樣的界線?在這樣的追問下似乎就沒有論者所強調的那么嚴重了。
事實上,文學不會“介入”歷史——如果說“介入”是指干預的話——歷史終究已經成為過去,從這一點來看的話,無論文學如何“介入”,都不可能改變歷史的真相。論者并非不清楚這一層,他們所擔心的,是文學通過“改造”歷史進而“介入”現實。“用主觀概念切割歷史,用虛擬想象來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傾向,甚至政治傾向”[4]。矛盾的是,論者旋即又改變了這樣的主張,認為“文學‘虛無’歷史,是在歷史和現實的關系上預設了一個前提,即認為歷史以脫離現實而存在,如何處理歷史與現實無關”[5]。不
管論者強調多少次文學“虛無”歷史,這種理論的“緊張”都多少讓人莫名其妙。
文學是作者意識形態的表達,或明或隱地闡述了作者的立場。正如王堯所言,“毫無疑問,文學在處理‘歷史’和‘事件’時從來都有其意識形態性。”[6]這樣的文學理論相信早已為人熟知,伊格爾頓早就說過,“文學,就我們所繼承的這一詞的含義來說,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它與種種社會權力問題有著最密切的關系。”[7]這一清楚明了的文學理論常識,不僅是外國人的認識,也是中國文學的教材接受的常識,張江怎么能夠說文學在如何處理歷史的問題上與現實沒有一點關系呢?
接下來的表述,就更讓人覺得有些夸大其詞了,“這種行為的危害就是,它拒絕了歷史提供的各種文化進入現實的可能。歷史被封存、消費,它所攜帶的經驗和智慧也隨之消散,人類發展進步就失去了根據,一個國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體失憶,進而迷失前行的方向。更關鍵的是,現實失去歷史的邏輯支撐,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成為懸而無著、飄搖無根的浮萍。”[8]張江的擔憂當然是有道理的,如果對歷史進行肆意篡改的話,真實就會被永遠遮蔽。但是,這樣的推斷是建立在文學與歷史同構的基礎之上的,只有把每一部文學作品都當作歷史書籍來對待,我們才能建構起文學與民族集體記憶之間的關系。
把文學等同于歷史顯然是理論上的謬誤。文學可以虛構歷史,但是歷史本身卻要求真實。文學的虛構是對想象的再現,而歷史則是對事實的再現。因此,從理論上來說,文學天然具有虛構的特權。虛構遠不是一種立足現實而又超越現實的創作方法,它還意味著對現實規約的回避,同時也意味著對規約力量的某種反抗。文學可以作為為宣傳機構服務的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工具,但是,它也可以反過來具有某種顛覆性功能。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虛構為文學的繁榮發展提供了途徑。
文學只是弱者的武器,是弱者最后的表達,而強者自有歷史為他們樹碑立傳。正如魯迅所言,“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8]。在這種情況下,文學以虛構的筆法,曲折地表達出作者的想法。于是文學可以“紀實”,可以用還原歷史的筆法來重寫過去。但是,就算如此,文學也沒有完全歷史化的義務,至少沒有承載與歷史同構的任務。歷史故事的內容要求真實可信,要求真正發生過的事情,而非想象性的建構。歷史的這種本質要求劃分了它與文學之間的差別。同時,進入歷史,將人物與事件歷史化就意味著他們本身的超越時代性,或推動或阻礙了時代的發展。從這方面來說,小人物是根本沒有進入歷史的權利的。這是一個充滿悖論的話題,我們常常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推動者,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的主體,但是,翻開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誰能夠在里面找出他的主體地位?如果他們真的創造了歷史,那么,他們在歷史教科書中的缺席又意味著什么?
歷史不會關心云普叔(葉紫:《豐收》)一家是否有飯吃的問題,也不會關心許三觀為何賣血(余華:《許三觀賣血記》),當然,更不會關心強拆與房價等問題,這些問題除能夠被新聞短暫性關注之外,最適合讓他們進入“歷史”的或許也只有文學。因此,從某方面來說,正是文學彌補了歷史的這一缺憾,被歷史忽略、遺忘的那些“歷史的主體”只有在文學中才得以重現。
但是,歷史上的農民是否都像云普叔一樣吃不上飯?則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是湖南人的沈從文在寫到家鄉的鄉民的時候,至少在他的小說中,是從來不擔心他們沒有飯吃的,湘西人民在“邊城”中活得有滋有味,那種重義輕利、純潔樸實、樂善好施的民情民風,至今仍讓諸多游客對“湘西”流連忘返。那么,在葉紫與沈從文之間,誰的書寫才真正符合歷史呢?如果按照論者們的“歷史”邏輯,這種兩極化書寫至少表明有一個作家是會受到“歷史”審判的。同樣的現象幾乎出現在所有作家身上。當我們的研究者反復強調老舍沒有直接書寫滿族生活,是因為限于其時的政治環境,害怕被拉出去重打五十大板的時候,老舍卻在《正紅旗》中書寫著滿族之于漢族和回族人的心理優勢。那么,這中間究竟是研究者對歷史的過度闡釋?還是因為老舍對于歷史的“虛無”?
參與“虛無歷史”話題的研究者都認為,文學負擔著歷史的功能。至少,它有輔助我們了解,認識歷史的功能。“脫離‘文學’去談歷史,也只是枯燥無味,甚至會被所謂的歷史來愚弄。”[9]問題是,文學的存在并不僅僅只是為了讓我們更準確的去把握歷史,文學可以具有輔助讀者了解,認識歷史的功能,但絕
不僅僅只具有這一功能:文學從來都不是歷史的仆從,它所要解答的不是“歷史”的問題,而是當前讀者的審美與精神需要問題。
事實上,在讀完有關“虛無”歷史的文章之后,我們也很難理解,文學是如何“虛無”歷史的?陳眾議把“虛無”論概括為,“歷史虛無主義的‘藝術’表征,簡而言之,一謂‘戲說’,二謂‘割裂’,三謂‘顛覆’。”[10]這三點只能算作是文學創作的一般方法,它也并非為某一派別所獨有。而張江等論者的論點則更讓人如墜五里云霧,“在歷史題材創作中,什么是歷史真實,它與藝術真實是什么關系,也有一個正本清源的問題。有人簡單地認為,只要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的事情,就是歷史真實;還有人認為,文學需要虛構,于是就可以無所顧忌,率性而為,用細節代替歷史。這都是錯誤的。”黨圣元則補充說,“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并不等同于歷史真實。我們所說的‘歷史真實’是指合規律性的本質真實,而不單單指事件真實或者細節真實。這是因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些事件雖然確有發生,但是,它代表不了歷史的本質,有時候甚至與歷史主流相悖逆。”簡而言之,他們所要求的歷史題材文藝創作,“最終要追求的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有機統一。”[11]這里重要的已經不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而是要“合規律性的本質真實”。在這種以一種本質取代另一種本質的論述中,論者們巧妙的以一種社會進化論的“虛構”理論取代了文學上的“虛構”理論。這種“合規律性的本質真實”論把歷史理解為某種線性發展的階段,把歷史理解為某種必然,一切事情在發生之前似乎就已經由上天注定,換句話說,命當如此。這種觀念顯然不是唯物史觀,而是徹頭徹尾的唯心論。他們自以為掌握了歷史發展的玄機,只要順應這種潮流,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按照既定的歷史軌跡前進。這樣,文學在書寫歷史的時候,也只能書寫這種歷史發展的主流,而忽略這期間發生的支流。
這可不是什么好現象,因為每個個體在這個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更何況,主流也是眾多的支流匯合而成的。對支流的漠視,多少會影響我們對歷史原貌的認識。
歷史可以只顧及主流,因為歷史本身就是已經發生之后的故事總結,但是,文學是否應該也如此?則又另當別論。文學在書寫歷史事件的時候,它面對的不僅是過去,更重要的是,它必須面向將來。歷史當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話誠然不假,但是這種“不假”也只是說歷史的一種理想狀態,是就“事實”而言的,至于歷史的細節以及對歷史的價值判斷,這本身就是任人打扮的結果,不存在單一化的統一認識。同時,還應注意兩個方面,其一是寫誰的歷史?其二是誰在寫歷史?有沒有被拔高了的歷史?有沒有被埋沒了的歷史?這樣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借用福柯的話來說,“誰在說話?在所有說話個體的總體中,誰有充分理由使用這種類型的語言?誰是這種語言的擁有者?誰從這個擁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權地位?反過來,他從誰那里接受如果不是真理的保證,至少也是對真理的推測呢?這些個體享有——只有他們——經法律確定或被自發接受的講同樣話語的合乎規定的傳統權利,他們的地位如何?”[12]沒有人追問歷史,卻總有人追問文學。在責備“虛無”歷史的文學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不應該疏忽忘記另外一種追問:那些被遺忘、被忽視的非文學的歷史事件是怎樣進入到文學創作領域中去的?它們為何引起了作者的注意?在這個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些什么?
這不是質疑歷史,而是質疑那種認為歷史都是實有其事,或者就算歷史上沒有的事件,只要“符合歷史規律”,也可以創造出來的觀念。因為正是這種觀念,滋生了這樣的想法:文學也應該如歷史一樣,以紀實的手法去實錄其事,而歷史也可以不拘小節,就算細節失真,也不影響社會發展的“規律”。這種謬誤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們把這條標準衡量文學,那么,一切童話故事,一切武俠小說都沒有了存在的根基。
從實證的角度來看,那些穿越時空、往返古今的表現方式,就跟童話故事中那些騎著掃把的巫婆一樣顯得荒謬絕倫。但是,既然我們能夠寬容童話的存在,那么,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包容當前的某些文學創作傾向呢?實在來說,這只不過是文學的一種創作方法罷了。
有論者認為,以人性論來重塑歷史人物,造成了對歷史的顛覆。這樣的論點似乎又讓我想起了沈從文,以及魯迅與梁實秋之間關于“人性論“的論爭,沈從文的小說不正是對湘西優美人性的發掘嗎?在某些特定的時期,文學固然有階級性,但是,從長遠來看,既然我們書寫的是活生生的人,那么,他們就不可避免地會有著某些普遍的“人性”,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標志。因此,不管是賣國賊還是人民英雄,或
多或少都有著在歷史教科書上不為人知的一面,重點并不在于我們是否突出了人性,而在于我們是否尊重了歷史的結局。至于其是非功過,本來就是留待后人評說的。那么,為什么一定要反對對于“人性人情”的書寫呢?又何必去擔心“如果用‘文學’的筆法,以人性人情味主綱去書寫歷史的話,那將會影響我們對于歷史規律和本質的探尋,是對本質真的歷史的歪曲乃至顛覆。”[13]
歷史是事實判斷,而文學是價值判斷。兩者具有天然的差異,這種差異也印證了論者們的擔心,但是,這種擔心首先需要建立在讀者們都是蘇珊·格巴所謂的“空白之頁”的理論之上的。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讀者,也不是如論者們所認為的那樣,是可以任人涂抹的“空白之頁”。
長期以來,文學被賦予了太多的責任,在國家貧弱的時候,它是救民于水火的工具,道德、宗教、政治、風俗、學藝、乃至于人心、人格等一切,都指望著小說去救命;在戰爭期間,它是匕首投槍,是文藝上的軍隊;在經濟社會大潮之下,它是挽救道德衰亡的救生衣;而今天,它又成了拯救歷史知識的稻草。只要評論家們愿意,或許有一天,文學還會變成抵抗霧霾的防毒面具,甚至變成維護世界和平,拯救人類的諾亞方舟,誰知道呢?前些年,我們剛剛討論完文學的生死問題,認為文學已經死了的人大有人在,似乎它已經窮途末路到了不值一文的地步,可轉眼之間,文學又被賦予了如此神圣的“歷史”義務。它似乎什么都是,就像萬金油,但實在的說,它又什么都不是,就像一塊狗皮膏藥,貼完一天兩天就會被撕下來隨意扔掉。
在我看來,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這樣的討論都是一個偽命題,猶如隔靴搔癢。文學代替不了歷史,而歷史也代替不了文學,文學僅僅只是文學,而歷史也僅僅只是歷史。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我們沒有必要一看到涉及歷史的文學就拿去與歷史相比照,這不是閱讀文學的做法,更不是文學批評的做法。文學批評要做的是,在這種差異性中去洞察作者的創作心理,以及它帶給讀者怎樣的審美感受?至于那些想要了解歷史的讀者,還是請他們自己去讀《史記》吧!
參考文獻:
[1][2][10][11]張江,等.文學不能“虛無”歷史[N].人民日報,2014-01-17(24).
[3][4][5]張江.文學不能“虛無”歷史[J].文學評論,2014(2).
[6]王堯.當代文學的“歷史”沉浮[J].文學評論,2014(2).
[7] [英]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M].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1.
[8]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M]//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36.
[9][13]商金林.文學的邊界和本質[J].文學評論,2014(2).
[12] [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M].謝強,馬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7:54.
[14]魏巍,馬玥玥.少數民族視野下的東西方文化沖突與民族國家建構——以沈從文與老舍為中心[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4(1).
[責任編輯:黃志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