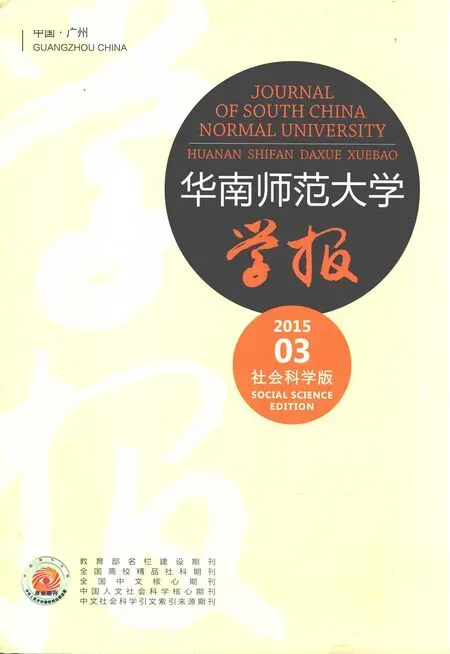黃遵憲的文化姿態與思想經驗
左鵬軍
清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05年3月28日),杰出思想家、外交家、愛國詩人黃遵憲在家鄉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因肺病逝世。在他僅57年的一生中,除了在政治改革、維新變法、外交事務等方面作出的執著努力和杰出貢獻外,還留下了可以代表近代中國人了解和認識日本最高水平的《日本國志》,以及收錄在《人境廬詩草》與《日本雜事詩》中的1 100 多首詩歌。貫穿于黃遵憲政治活動、外交活動、學術活動、文學活動之中的,則是以頗為深邃的思考、相當廣闊的視野為基礎,探尋世界發展大勢與西方列強及日本發達強盛的奧秘,追問清朝政治腐敗、國貧民弱、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原因,求索中國走向開明法治、富裕強盛的道路。這是黃遵憲一生為之執著奮斗、無怨無悔的核心所在,也是他留下的最大精神財富。在這一艱難的精神探索、思想變革和心靈歷程中,黃遵憲的文化姿態與思想成果、詩歌創作與傳承變革,留下了處于時代前沿、具有深刻啟發性、至今猶可深長思之的豐富思想經驗。
一、當代認同與歷史影響
黃遵憲一生所追求的主要并不是詩,正如他自己感慨的“窮途竟何世,馀事且詩人”①黃遵憲:《支離》,見《人境廬詩草箋注》卷八,第773 頁,錢仲聯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梁啟超也說他“不屑以詩人自居”②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24 頁,舒蕪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在經過多年的外交生涯,在政治改革、維新變法上遇到失敗、面臨窮途末路之后,他卻只能成為一個詩人。無論如何,詩,都是黃遵憲的最大成就之一,也是他倍受當時各界及后人關注和評價的一個主要方面。黃遵憲生前身后,詩名綦盛,影響及于多個方面和多個時期,可謂廣泛而深遠。這首先是因為人境廬詩以其廣闊而深入、穩健而創新、特色而兼容的方式處于時代詩壇之高點,取得了具有突出時代性、標志性意義的思想藝術成就。與此同時,也與多位著名人物的評論贊譽從而贏得了關注、擴大了影響密切相關。在并不漫長卻相當復雜的政治經歷中,黃遵憲與李鴻章、張之洞、陳寶箴等多位重要政治人物熟識并多受提攜。又由于人境廬詩具有縱橫自如、牢籠百變、大氣包舉的思想內涵與藝術氣度,從而與一般所謂同光體、中晚唐派、西昆體及其他詩人文士多有交往唱和且多受認同。黃遵憲與張蔭桓、鄭藻如、何如璋等多位嶺南籍官員及其他人士聯系密切,又曾與大河內輝聲、石川英、重野安繹、岡千仞、宮島誠一郎等多位日本詩人文士交往密切。這種情況一方面反映了黃遵憲在當時國內各界、日本等地受到的關注和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派別人士之間密切交流、互相影響的文學史事實和中國近代文壇創新發展、復雜多變的面貌。
就詩歌創作而言,黃遵憲與多位維新派政治家、文學家的關系最為密切也最為深摯,這不僅僅在于詩歌主張與詩歌創作方面的一致性,而且在于政治主張、文化觀念上的相通性。現有史料可以證明,梁啟超的“詩界革命”主張曾經直接而深刻地受到黃遵憲詩歌觀念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影響啟發;另一方面,梁啟超的持續關注和高度評價,也對黃遵憲其人其詩廣為人知、聲名日隆起了關鍵作用;甚至可以說,黃遵憲及其詩歌的廣泛影響和地位確定,首先是從梁啟超的積極鼓動、大力號召開始的。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載并產生顯著影響的《飲冰室詩話》中給予最充分評價并引為“新派詩”和“詩界革命”的同道者就是黃遵憲,這部詩話中關注最多、評價最充分的一位詩人就是黃遵憲。梁啟超曾說:“公度之詩,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公論不容誣也”①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24,63 頁。;“公度之詩,詩史也”②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24,63 頁。。他后來還說過:“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為,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③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82—83 頁,朱維錚校注,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盡管梁啟超對清代詩壇的整體評價在今天看來可議之處甚多,對于金和、黃遵憲和康有為的贊譽之詞過多夾雜了個人好惡和主觀隨意色彩,但是以這些言論與評價姿態為導引,黃遵憲及其詩作受到一批政治上、文學上同道者的普遍贊揚,并對其后多年的黃遵憲研究及近代詩歌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
黃遵憲其人其詩還受到其他具有相近政治傾向或文學主張的多位人士關注和贊揚。康有為說:“自是久廢,無所用,益肆其力于詩。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公度豈詩人哉?”④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見《康有為詩文選》,第101 頁,舒蕪、陳邇冬、王利器編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不僅對黃遵憲及其人境廬詩多有理解之同情,而且融入了自己的政治觀念和文學主張,可見康有為對那個時代文學創作的認識。蔣智由也感慨說:“公才不世出,潦倒以詩名……才大世不用,此意誰能平?”⑤蔣智由:《挽黃公度京卿》,見《飲冰室詩話》,第117 頁。對黃遵憲未能實現政治理想、只能以一個詩人終老而深為感慨,當然也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感受。另一位維新派人士狄葆賢也評論說:“黃公度先生,文辭斐亹,綜貫百家。光緒初元隨使日本,嘗考其政教之廢興,風土之沿革,泐成《日本國志》一書,海內奉為環寶。由是誦說之士,抵掌而道域外之觀,不致如墮五里霧中,厥功洵偉矣哉!先生雅好歌詩,為近來詩界三杰之冠。”⑥平等閣主人(狄葆賢):《平等閣詩話》卷二,第1,3 頁,(上海)有正書局宣統二年版。主要從黃遵憲《日本國志》的思想政治價值、對當時中國的啟發借鑒價值方面進行評價,深得黃遵憲進行日本研究并撰寫研究論著及相關詩歌的主旨。他在得知黃遵憲去世消息之后作的挽詩五首同樣滿懷感慨同情。其一云:“竟作人間不用身,尺書重展淚沾巾。政壇法界俱沉寂,豈僅詞場少一人?(近得先生正月粵中書云:‘自顧弱質殘軀,不堪為世用矣。負此身世,負我知交。’不意竟成讖語。)”其二云:“悲憤年年合問誰?空馀血淚化新詩。微吟踏遍傷心地,不見黃龍上國旗。(庚子秋,余夜過威海衛,見英國兵艦云屯,電光燦爛。口占志感詩有‘靈風徹夜翻銀電,不見黃龍上國旗’句。嗣見先生游香港詩,亦有‘不見黃龍上大旗’一語。)”其五云:“奇才天遣此沉淪,湘水愁予咽舊聲。莫問傷心南學會,風吹雨打更何人?(先生官湘臬時,與陳佑民中丞、江建霞、徐硯父兩學使,皆為南學會領袖,今諸君俱下世矣。)”⑦平等閣主人(狄葆賢):《平等閣詩話》卷二,第1,3 頁,(上海)有正書局宣統二年版。將有關史實的敘述與對逝者的懷念融會于一,將個人感情與國家局勢聯系起來,從不同角度對黃遵憲的政治建樹與傷時憂國、歷史貢獻與失望遺憾表達得充分而真摯,表達了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心聲。黃遵憲之弟遵楷也曾指出:“其詩散見于宇內者,輒為世人所稱頌。以非詩人之先生,而使天下后世,僅稱為詩界革命之一人,是豈獨先兄之大戚而已哉?”⑧黃遵楷:《人境廬詩草跋》,見《人境廬詩草》卷末,第1 頁,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將黃遵憲的詩歌成就與未竟事業聯系起來評價,中多感慨遺憾之音,反映了家族后人的復雜認識和深切感受。這種對黃遵憲生不逢時、壯志未酬的感慨同情影響了許多人,延續了許多年。時過多年之后,鐘叔河也指出:“黃遵憲首先是一位維新運動家,一位啟蒙主義者,一位日本研究專家,然后才是一位詩人。他是一位學術型的政治人物,他的詩,也主要是學術的詩,政治的詩。”⑨鐘叔河:《中國本身擁有力量》,第29 頁,(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1989年版。按:鐘叔河在《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說:“黃遵憲首先是一個維新運動家,一個啟蒙主義者,一個愛國的政治人物,然后才是一位詩人;他的詩,也主要是政治的詩。”第390 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黃遵憲的詩歌理論觀念和創作實踐中始終帶有“馀事且詩人”的特點,這是認識和評價其人其詩時必須注意體會并有所踐行的。
黃遵憲的文學觀念和詩歌創作還深刻影響了五四一代新文學家。更準確地說,當時年輕氣盛、充滿激情卻又內涵不豐、準備不足而又躍躍欲試的一群活動家和文學家們,從黃遵憲的文學觀念與詩歌創作中找到了自己所欲鼓動倡導新文學與新文化所迫切需要的思想資源,產生了如遇前代知音的精神感受和思想認同。胡適曾從倡導白話新詩、新文化運動的角度出發高度評價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主張,簡單主觀、一廂情愿甚至不惜損害論斷的科學性、合理性地稱之“很可以算是詩界革命的一種宣言”①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第116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位領袖人物周作人也不止一次地表示欽佩黃遵憲的思想和見識,并從現代新詩、新文學創建的角度稱贊“其特色在實行他所主張的‘我手寫我口’,開中國新詩之先河”②周作人:《詩人黃公度》,見陳子善選編:《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326 頁,岳麓書社1988年版。,顯然也是就其與現代新詩的相通性進行評價。鄭振鐸指出:“欲在古舊的詩體中而灌注以新的生命者,在當時頗不乏人,而惟黃遵憲為一個成功的作者”③鄭振鐸:《文學大綱》,“民國叢書”第四編五十四冊,第2047 頁,上海書店1992年影印本。,并盛贊“這些山歌確是像夏晨荷葉上的露珠似的晶瑩可愛”④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第456 頁,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朱自清也曾贊揚黃遵憲的“新詩”成就及其對五四新詩運動的啟迪:“清末夏曾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詩界革命’的志愿,他們所作‘新詩’,卻不過撿些新名詞以自表異。只有黃遵憲走得遠些,他一面主張用俗語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試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詩。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于民七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的影響。”⑤朱自清:《導言》,見《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卷首,第1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時間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后,鄭子瑜還曾專門撰文論證黃遵憲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⑥鄭子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黃遵憲》,1989年7月鄭子瑜教授寄示筆者之論文手稿復印件。按:鄭子瑜先生已于2008年6月30日在新加坡去世,特記于此,以志懷念。。這些言論或觀點顯然都是從現代白話新詩及新文學的淵源與發生、創新性與合法性等方面進行考察并得出結論的;而且這種思考方式、評論角度和基本觀點產生了至今猶在的深遠影響,在某些歷史時期甚至成為一種話語壟斷和思想霸權。從近現代詩歌變革歷程與相關文獻史實提供的實證可能來看,這樣的認識與其說具有充分的學理依據和學術價值,不如說主要體現了這批新文學倡導者、思想家、嘗試者的主觀愿望和文化態度。在這里,新文學運動的倡導、新文化思想觀念的宣傳顯然占據了主導地位,以致于明顯傷害了立論的可靠性和結論的允當性。也就是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及其后的多種論著對于黃遵憲詩歌創作與現代白話新詩關系的解讀,攙雜了過多的先驗觀念和主觀色彩,政治性、思想性和實用性占據上風的生硬論斷與相關史料、客觀事實和學理判斷之間存在著明顯矛盾,產生了尖銳的沖突。這種矛盾沖突已經日益明顯地限制和影響著近現代詩歌與文學思潮及相關領域的研究進展,這是研究者需要清醒明辨并注意鑒戒的。
從接受史的角度來看,黃遵憲的深刻影響還表現在另一個重要方面,即與新文學、新文化相對或相反的方面。近現代以來,在政治理想、文化態度、文學觀念上進化/發展、變革/革命觀念持不同立場、相異觀點的一批人士則從另外的角度對黃遵憲及其詩歌進行考察和評價,認識其詩歌創作的局限性、可商榷處,得出了一些與上述見解頗不相同甚至針鋒相對的認識。胡先骕指出:“黃公度、康更生之詩,大氣磅礴則有之,然過欠剪裁,瑕累百出,殊未足稱元氣淋漓也。”⑦胡先骕:《讀鄭子尹〈巢經巢詩集〉》,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附錄,第1305 頁。又說:“五十年中以詩名家者甚眾,決不止如胡君所推之金和、黃遵憲二人。然胡君一概抹煞,非見之偏,即學之淺,或則見聞之隘故也。黃氏本邃于舊學,其才氣橫溢,有足多者。然其新體詩,實與其時之政治運動有關……可見當時風氣,務以新奇相尚。康有為孔子改制之說,譚嗣同之《仁學》,梁啟超《時務報》《新民叢報》之論說,《新民叢報》派模仿龔定庵之詩,與黃遵憲之新體詩皆是也。黃之舊學根柢深,才氣亦大,故其新體詩之價值,遠在譚嗣同、梁啟超諸人之上。然彼晚年,亦頗自悔,嘗語陳三立:天假以年,必當斂才就范,更有進益也。”⑧胡先骕:《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人境廬詩草箋注》附錄,第1306 頁。這顯然是針對梁啟超所說“金和、黃遵憲、康有為,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①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83 頁。而發,可見品鑒趣味與見識的明顯差異,更反映了評價角度和文化觀念的明顯矛盾。從黃遵憲詩歌創作及其與新派詩關系、當時詩壇狀況的角度看,胡先骕所論特別啟人深思的是:倍受胡適推崇②按: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這個時代之中,我只舉了金和、黃遵憲兩個詩人,因為這兩個人都有點特別的個性,故與那一班模仿的詩人,雕琢的詩人,大不相同。”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過:“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為,元氣淋漓,卓然稱大家。”胡適此觀點顯然受到梁啟超直接影響。的金和、黃遵憲在詩家眾多、詩派林立的近代詩壇的合理地位與恰切評價究竟如何;所謂“新派詩”或“新體詩”的理論導向和創作實踐與當時政治運動的密切關系應該如何認識評價;在黃遵憲的詩歌創作中,政治態度與文學觀念、創新嘗試與舊學根柢的關系及各自作用當如何體會等,都是許多論者認識不清或根本沒能意識到的。徐英說得更加激烈:“金和、黃遵憲、康有為之詩,謬戾乖張,丑怪已極。而梁啟超謂其元氣淋漓,卓然大家,阿其所好,非通論也。”③徐英:《論近代國學》,見《人境廬詩草箋注》卷末詩話,第447 頁。同樣是針對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的有關言論而發的。通過對深受梁啟超推崇的金和、黃遵憲、康有為之詩的批評,表達了持重保守的文學觀念,反映了對當時總體文學與文化走向的認識,其中對以政治改革和輿論宣傳為主要目標的“詩界革命”中的確存在的急躁草率、追逐新奇現象提出的嚴厲批評尤具啟發性。這樣的話雖然出自數十年以前,但對今天的近代文學及相關研究領域的治學方法、學術方式、考察角度與文化觀念仍然具有深刻的啟發性。從黃遵憲研究與近代詩歌變革、現代新詩倡導的理論內涵和學術史經驗來看,這些與新文學和新文化立場迥然不同甚至明顯對立的認識,以另一種文學批評方式提出了近代詩歌變革中產生的新現象、出現的新問題,也是黃遵憲及其詩歌創作引起出自不同流派、具有不同觀念的詩歌批評家關注并產生顯著學術影響的有力證明。對于這樣的聲音,不應該采取有意回避或進行簡單地批判,而應當從更廣闊的文學與文化視野、從更深切的理論思辨和更豐富的創作實踐中具體考察、深入體會,汲取其中具有啟發性、前瞻性的內容。④按:關于此問題,拙文《近代文學研究中的新文學立場及其影響之省思》嘗有討論,載《文學遺產》2013年第4 期。
面對多年來黃遵憲詩歌及近代詩歌變革如此矛盾叢生、難以統一的評價,在黃遵憲研究方面用力甚勤并以《人境廬詩草箋注》享譽學界的錢仲聯曾指出:“人境廬詩,論者毀譽參半,如梁任公、胡適之輩,則推之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為疵累百出,謬戾乖張。予以為論公度詩,當著眼大處,不當于小節處作吹毛之求。其天骨開張,大氣包舉者,真能于古人外獨辟町畦。撫時感事之作,悲壯激越,傳之他年,足當詩史。至論功力之深淺,則晚清做宋人一派,盡有勝之者。公度之長處,固不在此也。”⑤錢仲聯:《夢苕庵詩話》,第161—162 頁,齊魯書社1986年版。主要從黃遵憲詩歌評價的矛盾現象和不同結論著眼進行分析并試圖尋求其中的共同點,著重強調人境廬詩在繼承詩歌傳統基礎上著意創新的遼闊廣遠、雄渾遒上氣象,對近代政治歷史事件、國家民族命運有意紀錄表現的詩史價值,頗有化解消彌以往觀點分歧、融會綜合見解異同的用意。但是從黃遵憲及近代詩歌研究的學術歷程及其經驗的角度來看,關于人境廬詩歌及相關問題評價出現的分歧,固然有著不同詩歌流派、評價角度、品鑒趣味、個人好惡等差異性、矛盾性因素,但更深刻也更值得關注的應當是這種矛盾現象所表現的關于新舊文學的不同文學觀念、文化觀念,所反映的關于近代以來詩歌變革、文化變遷的成敗利鈍及其經驗教訓的基本認識,也透露出中國詩歌與文學批評在中西古今、文白雅俗、新舊取舍之間探索出路、尋求可能、不斷嘗試過程中不得不面臨的困境與艱難。這已經是一個有必要冷靜面對、深刻思考并尋求合理方案與最佳可能的具有廣泛思想文化意義的問題。因此,錢仲聯基于深入細致的文獻功夫做出的推動黃遵憲研究的有關論述,提出了引人深思的學術觀念和思想方法問題,但尚未真正找到會通統一黃遵憲及其詩歌評價的關鍵,也未從理論觀念與學術變遷角度觸及產生這些分歧的深層原因并將問題的探討引向深入,也可以說將這一問題留給了后來的研究者。
將上述關于黃遵憲其人其詩的種種矛盾認識、不同評價視為一種思想史和學術史現象,則應當看到,無論基于何種文學標準或文化觀念,這些出自不同時期、不同人物的言論都是特定思想觀念、學術條件、政治環境、文化背景下的產物,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時代和評論者個人的觀念印跡,都是學術貢獻與局限、思想價值與缺失共生并存的,其中的得失成敗、經驗教訓、啟發遺憾也可以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學術史話題。從總體上看,以往對黃遵憲的研究評價在揭示若干文學史事實、得出一些有價值結論、充分顯現其當世價值和歷史貢獻的同時,也留下了一些明顯的缺失或遺憾,尚待彌補糾正或豐富完善。
二、詩歌取徑與詩學觀念
嚴羽嘗說:“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①嚴羽:《滄浪詩話校釋》,第26 頁,郭紹虞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此語頗為流行,對明清時期許多詩人的文學觀念、創作實踐乃至詩歌整體發展走向產生了深刻影響。盡管清人鐘秀曾經提醒地批評說:“嚴儀卿曰‘詩有別才’,千古定論。又曰‘非關學也’,斯言一出,貽誤后人不小,不得謂非語病。雖然,滄浪斯言亦為宋人以議論為詩者對癥發藥,其所謂‘非關學’者,殆謂學詩者不在著力,非謂學詩者不必讀書,第恐后人誤會其意,所關非淺也。”②鐘秀:《觀我生齋詩話》卷一,見《滄浪詩話校釋》,第27頁。但是,明清以降的文學史上,在詩歌創作中過多倚仗才情而輕視讀書學問者大有人在,以致于形成了一種頗具影響力的詩壇風尚并一直影響到近代詩壇。在這種詩壇風氣之中,黃遵憲對于詩歌創作中才情與學問、感悟與讀書等關系的理解和處理,顯示出相當高明的見識和應對能力。他并未僅僅依靠過人才情使詩歌創作走向以情韻獨勝的道路,而是保持著對創作根柢、門徑、內涵的尊重,對讀書、學問給予足夠關注、多所用心并有意運用。從當時的詩壇狀況和傳統詩歌面臨的文化環境而言,無論從理論觀念還是從創作實際來看,這種選擇路徑和處理方式都顯然更有合理性,從而能夠在創作中將才華與學問結合得非常緊密,取得兼顧其長而兼得雙美之效,由此造就了人境廬詩的獨特思想深度和藝術風貌。
在許多詩人都不能不面臨和處理的通俗與雅正、淺白與古奧的關系問題上,黃遵憲采取的依然是綜合兼顧、取其優長的認知方式和處理方法,從中獲得廣闊包容的理論空間和豐富多變的創作可能。黃遵憲對中國語言文學中的通俗化、白話化傳統非常熟悉,包括客家山歌民謠、淺易樸素的詩詞曲、通俗小說戲曲的表達方式和語言形態,甚至關注日本小說戲劇、民間文學中的通俗因素,從而使自己創作的一部分作品具有突出的通俗曉暢、淺白明快的思想特征和語言特點。黃遵憲文學思想與詩歌創作中的這一側面正是被后來的多位研究者高度關注并推崇的,被認為開啟了近現代文學語言通俗化、白話化的先河,甚至被認為是五四白話新詩、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這種思考方式和評價方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占據著主導地位,至今仍為部分研究者所堅持。從有關文學史實和學術史經驗來看,不能不承認,這樣的認識和評價固有一定根據,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學性。
但是,至今可見的豐富文獻史實和大量詩歌也在有力地證明,黃遵憲的文學思想和詩歌創作中同時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傾向,即更多地從中國詩歌的典雅端莊傳統出發,有意守護和追求淵雅正統、講究古奧深邃的傾向。這既是黃遵憲文學修養、詩歌品位、創作能力的重要體現方式和實現途徑,又是作為詩人的黃遵憲以學養功夫、創作實力獲得當時由官員名士構成的主流詩人、正統派文學家及有關政治人物關注認同的必經途徑。以往的研究者對融入主流詩壇之于黃遵憲詩歌創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意義關注無多、認識不足,而經常過于片面、簡單地強調其詩歌創作通俗化、淺易化傾向的意義和價值。這既不符合黃遵憲及其詩歌創作的文獻史實,又不符合黃遵憲與各派詩人聯系交往、與近代詩壇保持復雜關系的實際情況。這主要是不顧豐富的文學史事實,將某些既無思想深刻又無科學價值的既定主觀政治觀念和思想邏輯強加于復雜的文學現象進行主觀駕馭、強行解釋的結果,從而將紛繁復雜的文學史現象引向了概念化、簡單化道路,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使學術研究走向了明顯的非學術化方向,甚至形成了一種思想習慣、言說方式和基本認識。這是當下的黃遵憲及近代詩歌相關研究中應當充分注意并深入反思的。
從個人選擇、創作態度與當時文學運動、詩歌派別、文壇風氣的關系來看,黃遵憲與所謂“新派詩”和“詩界革命”在新與舊、名與實之間也留下了值得認真清理、深入反思并清醒認識的文學史和學術史經驗。就與“新派詩”的關系而論,黃遵憲在早年詩作中寫下的“我手寫我口”①黃遵憲:《人境廬詩草箋注》卷一,第42 頁。和在中年詩作中寫下的“讀我連篇新派詩”②黃遵憲:《酬曾重伯編修》,見《人境廬詩草箋注》卷八,第762 頁。,本來只是詩歌創作中即興的有感而發或酬答友朋時隨手寫下的普通詩句,并未進行過深刻的理論思考或嚴謹的邏輯闡述,也沒有其他論述的有力支撐或明顯證明,因而其本身并不帶有任何成熟的理論意識、思想內涵或倡導詩歌變革的主觀意圖。一系列詩歌創作也在有力地證明,黃遵憲并不反對所謂“新派詩”,還創作了若干首具有革新色彩的詩歌。但應當清醒地看到,這絕不是黃遵憲詩歌創作的全部,也不是其詩作的主導方面。頗令人覺得奇怪的是,這樣兩句表現出一定詩歌觀念和理論意識的詩歌,在后來的許多年中、在許多研究者那里卻被當成了黃遵憲主張詩歌創新變革、倡導“詩界革命”的有力證據,并進行了種種大膽分析和過度解讀。而且,“新派詩”③按:與“新派詩”概念密切相關的另一概念“新學詩”的成立與否,更需要進行認真的史實文獻清理并對以往的研究方式、基本認識與有關結論進行清醒反思。筆者以為,“新學詩”是一個較“新派詩”更加無根據、無法自圓其說的生造概念,相關研究中存在著更加嚴重的觀念與方法問題。此不具論。這一概念是否能夠在嚴格的學術意義上得以成立、它與舊派詩或傳統詩歌的關系究竟如何,既尚未找到充分的文獻根據,也未進行足夠深入的理論闡述,許多研究或只是人云亦云、姑枉用之而已,或仍停留在對非常有限的材料進行過度闡述、強行論證的水平上,因而顯得強詞奪理、捉襟見肘。這是目前的黃遵憲與“詩界革命”、近代詩歌變革研究中應當認真反思的重要問題之一。
在近六七十年來已經形成的近代詩歌必須朝著新詩化、通俗化、現代化的方向改革、“詩界革命”代表著近代詩歌變革發展正確方向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框架之下,黃遵憲儼然成了“詩界革命”的倡導者之一,也是最成功、最具有標志性的實踐者,是一面革新創造的旗幟。其實,在現有相關文獻資料中,還找不到黃遵憲在理論上有意倡導、在實踐上主動參與“詩界革命”的直接證據,當然也未發現他明確表示反對“詩界革命”的相關材料。結合黃遵憲的詩歌理論主張、創作實踐及其與“詩界革命”鼓動倡導者梁啟超等人的關系,只能說他與“詩界革命”保持著一種不即不離、矜持而認同的態度。這種姿態既符合黃遵憲基于豐富的創作經驗形成的文學觀念和詩歌主張,也與他一貫中和穩鍵、樸質堅忍、務實求新的政治立場、學術文化觀念、處世態度等明顯相關和一致;更與梁啟超1899年在《夏威夷游記》中、1902年起在《新民叢報》連載的《飲冰室詩話》中正式鼓動并積極倡導“詩界革命”之際黃遵憲的政治處境、思想轉變、詩歌創作和人生經驗密切相關。也就是說,黃遵憲對于“詩界革命”的真實態度和具體做法是他政治態度、思想特點、學術觀念、處世原則、生活經驗在文學觀念、詩歌創作上的表現。黃遵憲對“詩界革命”及與此相關的輿論鼓動的態度,既不同于年輕氣盛的梁啟超等人的簡單浪漫、焦躁冒進和急于求成,也不同于同時代更多注重延續傳統、保守謹慎的主流派文人和正統派詩家,而是在因革通變、揚棄取舍之間保持著一種穩妥合和、理性持重的文學姿態與文化態度,其中蘊含著頗為深刻的世變道理和辯證智慧。就當時傳統詩歌的生存處境和面臨的變革來說,這種處理方式也更具有思想方法、創作原則上的建設性和啟發性。從中國傳統詩歌面臨的中西古今選擇、傳承創新難題來看,這種態度也更符合近代詩歌繼承優秀傳統、因時而變、適當求新的發展方向。無論是從近代詩歌、近代文學研究的角度還是從近代學術、思想文化的角度進行反思,都應當看到,這也是黃遵憲留給后人值得記取的思想經驗。
三、文化態度與思想調適
黃遵憲生活的晚清時期,盲目自守、閉關鎖國的局面已在外國列強各種方式的強迫下、在清政府不得做出的種種應付中被愈來愈徹底地打破,代表世界文明水準、價值標準和發展方向的西方文明正在日益充分地展現在中國人面前。這已經是一個不得不打開國門、無法不面對西方文化、不能不對古老的中國文化進行重新思考進而尋求出路、謀求變革的前所未有的時代。而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歷經日本、美國、英國、法國以及英屬新加坡等地的外交官僚屬經歷和積極考察、主動學習西方文化的行動、心態及一系列詩歌創作與著述文化活動,又使黃遵憲受到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的直接沖擊和巨大影響,也為他提供了深切體察、準確認識外國文化的良好機會和客觀條件,可以在比較真切的中外文化關系、異同對比中思考和探尋中國文化的出路,顯示了個人思想的先進性與時代要求的進步性之間的某種契合,也反映了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化發展變革的一個主導趨勢和必然方向。
在這一幾近全新的文化沖突、思想變革過程中,黃遵憲的文化心態總體上是以比較健康、積極主動的姿態去面對異質文化的沖擊和挑戰的。這在作為他首次出國經歷、出使日本期間的諸多文化感受、內心矛盾及自覺進行的自我疏導、自覺調適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在同期所著的《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及其修改過程中、在創作的《櫻花歌》《西鄉星歌》《不忍池晚游詩》《都踴歌》《赤穗四十七義志歌》等多首關于日本政治、歷史、文化的詩歌作品中得到了集中展現;而與日本多名文學、文化與政治人士的交往對于黃遵憲日本觀、世界文化觀的形成也產生了重要作用。這些文學、學術、外交活動及日常生活使黃遵憲比較平穩地度過了始料未及的文化心理和價值信仰危機,積累了珍貴的文化交流經驗;而且,這種豐富而親切的日本經驗成為黃遵憲接觸和認識外國文化的思想基礎,對于他后來出使歐美國家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后來在出使美國、英國、法國以及英屬新加坡的時候,黃遵憲的內心感受、文化態度不斷發生顯著變化,再次經歷了內心的文化困惑和思想矛盾。這一方面是由于歐美文化與日本文化的巨大差異性、當時清政府與美國、英國、法國外交關系的復雜與艱難及其對于黃遵憲思想觀念上造成的深刻影響,一方面也是由于黃遵憲本人知識結構、認識能力、思想觀念、內心感受所帶來的明顯限制,特別是對于歐美文化的明顯陌生感和疏離感,造成了預想不到的內心困難與思想矛盾。這在他寫下的一些詩作如《海行雜感》《紀事》《倫敦大霧行》《登巴黎鐵塔》《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等作品中也有著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反映。但是,由于在日本期間已經具有豐富的對外國文化經驗、形成了良好的對待外國文化、異質文明的情感態度和文化姿態,加之政治經驗、文學修養、文化見識、人生閱歷等的豐富提高,黃遵憲在總體上能夠比較恰當地處理各種思想矛盾和現實問題,以頗為平和穩健的態度和方式比較順利地度過各種困難。這些經歷和努力,使黃遵憲在最初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外交人物當中保持著先行者的地位,為中國人和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作出了積極探索和突出貢獻,也積累了至今仍然值得關注并體會、汲取的文化史經驗。
另一方面,黃遵憲在接觸和面對外國文化的過程中也表現出復雜深刻的內心矛盾和價值沖突,面臨著難以找到正確方向、合理答案與可行出路的文化難題和價值困惑,這同樣是值得充分注意的。黃遵憲也像當時的許多儒士文人一樣,認為雖然西方先進文化應當學習吸收,但需要根據中國文化傳統和當時的需要進行具體分辨與取舍。他在日本時曾說:“近者土風日趨于浮薄,米利堅自由之說,一倡而百和,則竟可以視君父如敝屣。所賴諸公時以忠義之說維持世教耳。”①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第232 頁,(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年版。保守的思想傾向表現得非常明顯。他還說:“形而上,孔孟之論至矣;形而下,歐米之學盡矣。論當今之事者,不可無此見解也。”②岡千仞:《觀光紀游》十三,明治十七年八月一日(光緒十年六月十一日)日記,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八冊第五帙,第178 頁,杭州古籍書店1985年影印本。又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自上古以來,逮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所發明者備矣;形而下者,則自三代以后,歷漢魏晉宋金元明,猶有所未備也……舉一切光學、氣學、化學、力學,咸以資工藝之用,富國也以此,強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實有其可重者在也。中國于工藝一事,不屑講求,所作器物,不過依樣葫蘆,沿襲舊式……今萬國工藝,以互相師法,日新月異,變而愈上。夫物窮則變,變則通。吾不可得而變革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凡關于倫常綱紀者是也;吾可得而變革者,輪舟也,鐵道也,電信也,凡可以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者皆是也。”③黃遵憲:《日本國志》卷四十《工藝志》,第1—2 頁,光緒十六年羊城富文齋刊本。他認為可以變革的方面總體上應當限定在能夠直接有利于國富民強的器物、技術等物質文化層面;對于國家法律、政治制度等文化的中間層面則應當采取比較審慎的態度,可以學習借鑒的主要是日本、英國式的國家制度和政治體制,對于美國式的共和制度則多有批評,認為不可效法;至于一般所謂文化的最深層即道德倫理、思想觀念、價值體系、精神信仰等方面,則基本上不需要學習西方,也就不存在借鑒效法的問題。這種中體西用、變器而不變道的觀念困擾了黃遵憲一生,也是同時代許多文人面臨的最深刻的文化難題和價值困惑。①按:關于黃遵憲的政治觀念和對于西方文化的認識,拙文《黃遵憲晚年思想三題》(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黃遵憲的中西文化觀與文化心態》(載《炎黃文化研究》第三輯,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曾有具體討論,此不贅述。
以明末西方傳教士入華為主要標志的西學東漸思潮,在經歷了清代前中期的種種艱難曲折之后,至近代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無法避免的巨大力量,西方(包括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文化對中國的滲透影響日益深入充分。雖然其間幾經反復、多有波折,但西學東漸、學習西方的總體趨勢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在這一空前深刻的文化變革轉換歷程中,中國人始終未能解決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中西文化的體用關系、西方文化價值觀念對于中國的適用性和適用度、中國文化傳統的轉化延續及其近現代價值問題。在這一思想史背景下,黃遵憲也曾深受當時頗為流行、后來仍頗受認同的西學中源論的影響。他在日本時曾說過:“余考泰西之學,墨翟之學也。尚同、兼愛、明鬼、事天,即耶穌十誡所謂‘敬事天主’‘愛人如己’”;“《韓非子》《呂氏春秋》備言墨翟之技,削鳶能飛,非機器攻戰所自來乎?古以儒、墨并稱,或稱孔、墨,孟子且言天下之言歸于墨,其縱橫可知。后傳于泰西,泰西之賢智者衍其緒馀,遂盛行其道矣”;“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書。第我引其端,彼竟其委,正可師其長技”②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原本第五十一首自注,光緒五年同文館集珍版,第23—24 頁。。直到晚年鄉居時,西學來自中學的基本觀念仍未發生轉變且有所深化,認為:“舊學中能精格致學者,推沈夢溪,聲、光、化、電、力、氣無一不有。其使遼時,私以蠟、以泥模塑地圖,即人里、鳥里之說,亦其所創也,他日必有人表而出之”③黃遵憲:《黃遵憲全集》,第434,428 頁,中華書局2005年版。筆者對原校點有所調整并省略作者原注。。還認為:“吾讀《易》,至泰、否、同人、大有四卦,而謂圣人于今日世變,由君權而政黨,由政黨而民主,圣人不啻先知也……而謂圣人之貴民、重文明、重大同,圣人不啻明示也(大象明之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自天佑之。系辭曰‘履信、思順、尚賢’,非民主而何?)。所尤奇者,孔子系辭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此非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說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非猴為人祖之說乎……達爾文悟此理于萬物已成之后,孔子乃采此理于萬物未成之前,不亦奇乎?”④黃遵憲:《黃遵憲全集》,第434,428 頁,中華書局2005年版。筆者對原校點有所調整并省略作者原注。非常肯定地認為不僅西方自然科學的許多方面早已大備于中國古代典籍之中,而且西方近代社會人文科學內容、當時傳入中國的新觀念也早已略備于中國傳統思想之中。從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當時流行一時并持續較久、包括一向被視為走向世界的先進中國人黃遵憲在內的許多文人堅信不疑的西學中源論,雖然對中西文化關系包含著明顯主觀故意成分的誤讀;但作為一種文化心理現象,體現了中西文化接觸碰撞、交流融合過程中最深層、最內在的矛盾沖突,反映了中西文化交融的沉重步伐和艱辛歷程,也表明中國近代文化變革的演進與深化,有其存在的社會文化背景、人文心理環境和一定的合理性,也是那一代文人彌補巨大文化失落感、消解無法消除的文化心理焦慮的一種補償形式。
黃遵憲及其時代人士所面臨的思想矛盾、價值困惑,特別是他們為解決這種前所未有的矛盾困惑所做出的積極回應、努力調整,是真切深刻且具有文化史意味的。從近代思想史的邏輯演進和近代知識分子心態調適完善的角度來看,黃遵憲那一代先進中國人未能解決的矛盾困惑,并非僅僅屬于他們自己,實際上已經考驗了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及其他有識之士。這種文化困惑和思想矛盾是中西文化關系中一個極有深度的根本性問題,并不是黃遵憲及其同代人所能解決的(其間的缺陷和遺憾當然也不應當僅僅由他們那一代人承擔),因而留給了后來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更多的中國人。從文化態度、思想觀念與時代氛圍、文化變遷總體趨勢的關系來看,黃遵憲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之間的權衡、取舍與選擇,具有鮮明的個人特點和突出的時代特色,留下了內容豐富、價值獨具的思想史經驗,直至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因為,從近代走到今天的我們,仍然在中西古今、通變揚棄、傳承創新中艱難求索、奮力前行,其間留下的仍然是前景與困惑、進步與缺憾、經驗與教訓交織雜糅的思想歷程和心靈印痕。從這一角度來看,已經逝世110 周年的黃遵憲的思想情感、理想信念與探尋中國富裕強盛、民族復興道路的后來者們是一脈相承、息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