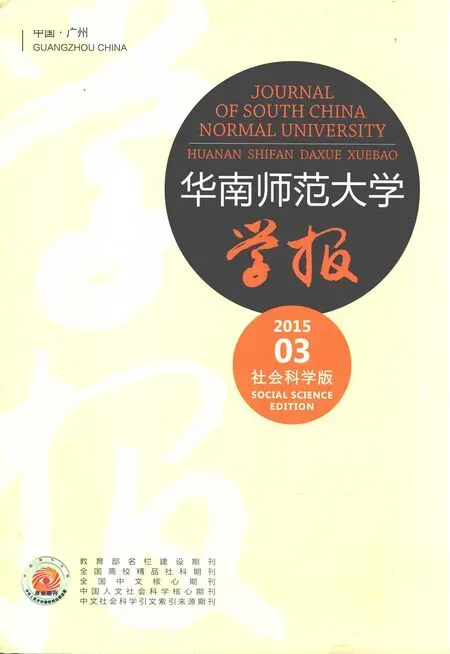秦帝國統治思想的狹隘性與局限性
李禹階,趙昆生
秦帝國二世而亡,除了實行商、韓法家思想,嚴刑峻法、苛暴虐民外,其國家統治思想及意識形態的狹隘性與單維度化所表現出的局限性亦是一重要原因。秦帝國的建立標志著古代中國政治上、地域上的一統。但是,在統一六國后,秦的統治思想以及相應政策沒有及時從軍事軌道向和平時期轉化,因此缺乏在新的歷史時期對于國家政權的合法性論證以及政治思想上的建樹。對于秦王朝來說,依靠刑治手段,全面秉承法家“農”“戰”思想使其取得了戰爭的巨大成功,這也使其比較盲目地相信了強權、暴力乃至秦君臣主觀作用的力量,而缺乏對于國家統治思想建構必要性的認識。因此在建立全國政權后,秦王朝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國家統治思想及政治意識形態,仍然是赤裸裸的刑治主義和暴力對抗,是君臣之間的利益角逐,是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斗爭。它所主張的政治價值與信仰、理念,亦是法家理論主張的君主專制下的刻薄寡恩、苛暴無情,由此使其在統治思想及國家意識形態方面缺乏對于關東地區固有的宗法文化的包容與懷柔。這樣,秦在統一中國后,其政治思想及強調軍功、農、戰的戰時價值理念,就呈現出狹隘與單維度的特征,而不能適應統一后中國社會的需要。
秦帝國統治思想的狹隘性與單維度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秦帝國在軍事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對其戰爭力量和主觀作用的深信不移和盲目夸大,以致未能及時調整“馬上”與“馬下”治天下的攻守異勢的統治思想及其政策、策略。秦國在全國統一后,其政治思想與意識形態理論仍然停留在戰爭軌道上,缺乏對于全國各個階層有效的思想上、理論上的整合。秦統一后,出于對自己戰爭能力和主觀作用的深信不移,一味依靠刑治理念治國,沒有認識到由馬上取天下,而不能由馬上治之的道理。這種單純依靠刑治精神進行的社會控制,就使之成為歷史上以重刑著稱的朝代。它使人們重“利”、重“力”而忽略社會倫理道德的規范、信念,使人欲不斷被膨脹、放大。這在西秦時期宗法血緣基礎薄弱的軍事戰爭軌道上是有效的,但是當它延續到戰爭結束后的和平時期,沿用在關東各國的社會整合與“文治”中,就不那么有效了。歷史正是證明了這一事實。
在帝國建立之初,面臨復雜的政治局面,秦王朝沒有使政府權能部門迅速由戰爭軌道下的軍事職能轉變為戰后恢復社會經濟的和平職能,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去適應、包容關東諸國宗法血緣的社會文化、風俗,通過王朝政策的調整,達到秦、齊、楚等幾大不同地域的社會整合。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也采取了一系列鞏固統一的措施,例如推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制度,但是這些制度主要是以秦國制度為標的,由此來完成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的全方位統一。而且十分重要的是,秦在帝國的社會控制與整合的政策措施上,仍然采取了西秦時期法家嚴刑苛政的國家治理思想,并將這一統治舉措延伸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試圖以此將帝國政治、軍事、經濟資源運用到中國廣大地域中去。這種對于國家政治思想及文化制度的考量,在當時紛紜復雜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沖突中,是缺乏其適應性的。
事實上,秦帝國統一六國的過程,也是一個秦專制政治制度及其法家思想、刑治精神在統一戰爭局面下不斷強化、膨脹的過程。秦的統一,一方面使秦朝君臣在主觀上過分相信軍事機器的強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實行統一的過程中,秦國實行的戰時政策、措施強行推進、深入到帝國各個階層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使西秦社會在法家思想的一統下去完成政治上、文化上的整合。尤其在秦嬴政時期軍事上的摧枯拉朽,使秦帝國君臣過分相信了帝國軍隊與法家刑治主義的力量,所以當秦消滅了六國政權,完成國家統一后,其君主集權及官僚政治也就到達其頂點。秦始皇這種無限的自我膨脹,以及對自己戰爭力量和主觀作用神威性的深信不移,致使他蔑視天下蒼生,一切自以為是,把自己推到了孤家寡人的位置上。例如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登之罘山,就刻石稱:“大圣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義誅信行,威憚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①《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249 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大肆宣揚自己“光施文惠”“奮揚武德”“烹滅強暴”等天下蒼生救世主的功績,武斷地決定以法家理論來應對一切的裁斷。在秦始皇看來,專制皇權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遍天下”②《史記》卷87《李斯列傳》,第2546—2547 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③《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249 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始皇不僅擁有國家最高立法權,同時亦擁有最高的思想裁斷權,君主的言論、意志就是天下法律的源泉和行為的規范,由此開中國封建時代專制君主所具有的法律制定權、思想裁斷權、制度施行權的先河。
始皇高高在上,俯視蒼生,以自己的意志為標準進行社會分層,并強行以西秦制度來規定不同社會階層應遵循的社會規范。他自稱:“端平法度,萬物之紀……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④《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249 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按照人治社會中的君主之法,要求不同社會階層應嚴格遵守該階層的規定和規范行事,不能僭越自己所在階層的規定。秦代法律對不同社會階層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規范制定得非常細致和具體,其條文甚至細致到對人們具體行為方式的量上的精確規定。《秦律》現已佚失,但我們可以從“承秦制”的漢初法律中看出。如1983年至1984年在湖北江陵張家山247 號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共有竹簡527 枚,包含了27 種律和1 種令,共28 種。它的發現既完善了我們對于秦漢法律文獻的認識,也看出秦法的內容包羅萬象的情況。在《二年律令》里,不僅有殺人及傷人罪、經濟犯罪、官員瀆職及失職罪等刑事罪刑,也有以孝入律的不孝罪等倫理罪刑,還有對人口商業農業等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漢初是繼承秦法并且有所增刪而來,因此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秦代法律制定是十分完備的,其實施也是無所不入的。這樣,一方面秦帝國將社會各階層具體的一言一行都納入了政權控制的爵制與法律框架之中,使君主極權縱深地延續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層面,表現出了君主極權的強大和無所不在。另一方面,法律條文過于具體化、細節化、生活化,除了條文自身反映的法家刑治主義的嚴刑峻法外,也使得各個階層的社會行為運作缺乏余度,沒有因時而變的空間和時間。尤其是在除了秦關西地域的其他中國廣大土地上長期實行宗法血緣“親親”“尊尊”制度的社會中,其基層社會在過去往往是依靠宗法制度的族規、家法在統治,依靠祖宗血緣崇拜的精神紐帶維系著社會的倫理規范和道德信念。這種宗法制度的存在,往往是在嚴酷的專制集權政治對于基層社會的壓迫中起到了一個中間層次的社會壓迫減震器作用,使嚴酷的壓迫在宗法血緣的“親”“尊”中得到部分消融。現在一旦缺失了基層宗法社會這么一個社會壓迫減震器,國家的統治及嚴苛、刑律直接展露在民眾面前,其嚴酷殘暴的刑治精神在習慣于宗族“親”“尊”原則及其宗法規范統治下的人民大眾面前暴露無遺。所以,西秦嚴酷的法律規范在全國不同風俗、文化的地域的頒布實施,在基層民眾社會中的延伸、深入,使廣大民眾處在國家極權政治和刑治精神的高壓下,自然不能達到社會整合與控制的效果;而只能適得其反,引起當時楚、齊、韓、魏等各國舊貴、士人、民眾的強烈不滿與反抗。“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就是這種專制統治的政治反映。所以,陳勝、吳廣等人所面臨的戌邊“失期”懲罰,對于長期習慣于秦國軍律的西秦民眾來說,應該是能夠忍受的。但是對于習慣于宗族“親”“尊”原則的關東舊六國民眾而言,就是一種極其殘酷的律法。所以漢初陸賈曾就“攻守異勢”的問題規勸高祖劉邦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①《史記》卷97《酈生陸賈列傳》,第2699 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正是這種不同歷史時期與社會文化特點決定了秦始皇以嚴刑峻法來進行社會控制的統治思想的局限性與狹隘性。
其次,是秦帝國在意識形態、政治價值觀上的極端功利化特征。在秦統一四海過程中,隨著君主專制政體的建立,與其相適應的政治與權力的價值觀也延伸到四海之域。以法家思想為核心的專制王權理論,隨著帝國建立而逐漸推向全國。商鞅到韓非理論的演進軌跡,即是秦專制王權在理論與實踐上不斷發展、擴充的行進歷程。從戰國后期到秦帝國的統一,正是秦專制王權從理論到實踐迅速演進、擴大的時期。與韓非同時代的呂不韋,曾經從政治實踐中認識到專制王權乃是實現大一統的重要因素,要有效整合與控制中國古代社會,就必須建立統一的君主集權政治。他認為,“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②冀昀主編:《呂氏春秋·謹聽》,第262 頁,中華書局線裝書局2007年版。故“國之一,在于君”,“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③冀昀主編:《呂氏春秋·執一》,第403 頁,線裝書局2007年版。。于是,在呂不韋等官僚、宰輔的推波助瀾下,秦以君主集權和以軍功顯榮的權力價值論,對帝國現實地建立君主專制的官僚體制,促進官吏的選拔與流動、人才擢用都起到極大作用。同時,權力價值觀的發展,使秦國士農工商各階層打破既有的傳統分工格局,無不以其軍功和“技”能來獲取富貴顯榮。正因如此,秦國家從帝王、官吏到普通士人,其不擇手段,僅為功利目的的投機思想泛起,官員政治價值觀也顯得十分窄化。在底層社會及民間,價值觀轉變更是使人目不暇接,而為官之德更加無從談起。據史料記,當時關東陳勝、吳廣起義,杰俊相立,兵至鴻門。丞相李斯見情勢危急,多次欲當面向秦二世勸諫,二世不許。后來秦二世不耐煩了,對李斯加以責問說:“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何?”④《史記》卷87《李斯列傳》,第2553—2554,2553—2554,2539—2540 頁。大意是貴有天下的帝王,豈能夠像奴才一樣苦形勞神,過著仆役般的生活。圣賢的帝王之有天下也,專以天下之物來滿足自己的人生欲望,如果于自己身體欲望都不能滿足,又將以什么來治理天下哉!因此我的人生愿望就是肆意極欲,窮盡奢侈,長享天下而無害。秦二世公開地引用韓非的話,視天下為己物,以奢侈享受為人生目的。這種治國者的政治價值觀,充分體現出秦王朝上層統治者的自私、狹隘,也充分體現出秦王朝從帝王到官吏政治思維的功利性、局限性、陰暗性。正是在這種政治思維的影響下,秦二世提出了“以人徇己”或“以己徇人”的問題:“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⑤《史記》卷87《李斯列傳》,第2553—2554,2553—2554,2539—2540 頁。由此發出了以嚴刑苛政治理社會的概嘆。正是在這種極端自利的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下,秦王朝國家治理與社會控制處于空前的暴戾與殘酷之中。
秦帝國政治信仰的功利性狹窄化,已經成為帝國君臣上下一種普遍現象,它隨時表現在朝廷官員投機性的政治價值觀中。例如秦丞相李斯,其人生觀與價值觀就具備十足的投機性。李斯曾經由小吏而出將入相,其心理態勢則是:“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⑥《史記》卷87《李斯列傳》,第2553—2554,2553—2554,2539—2540 頁。將富貴功名視為人生目的,而其富貴與尊榮均下注于君主身上,這也是封建化過程中一些官僚、士人權力價值觀的發展趨勢。這種權力價值觀充分表現出官僚、士人對新的封建制度中仕途開放的干政激情和與此相關的對專制王權的依附性。
這種權力價值觀趨向,使傳統的商、韓思想延續了下來。以“強力”、軍功、政績而不以宗法統緒取富貴,已成為秦代的一種時尚。本來以軍功、政績攝取富貴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但是當其片面強調這個方面而忽視道德倫理的作用時,就容易使帝國上下形成一種刻薄寡恩、重刑酷法、以利相競的風氣。這種風氣使得秦帝國內部的官僚機制和對于基層社會的整合、控制在帝國一統初期就存在失效的危險。例如在秦帝國宗室內部的宗法關系上,就表現出極其的刻薄寡恩、利益至上的傾向。早在秦帝國誕生的前夜,這種情況就開始出現。如秦始皇就把本家族的成員排斥在權力結構之外,不給同姓宗室子弟以政治實權。秦始皇死,秦二世就用陰謀手段奪取皇位,并且與心腹宦官趙高密謀對付宗室兄弟姊妹的策略。趙高聲稱:“今時不師文而決于武力”,主張以武力和強權對待宗室兄弟姐妹。于是秦二世大開殺戒,“誅大臣及諸公子”,“六公子戮死于杜”。當時,公子將閭弟兄三人被囚禁于內宮,秦二世派人對公子將閭說:“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閭質問:“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愿聞罪而死!”使者說:我不知道,我只是奉旨行事。將閭仰天長號:“天乎!吾無罪!”兄弟三人拔劍自刎。這種對傳統“親親”原則的否定,不僅使得本來就已孤獨的皇帝失去了宗法、家族的人倫溫馨,更使皇族內部在權力興替上始終處于血腥的不穩定狀態,形成漢初人所評價的“激秦孤立亡藩輔”而“亡秦孤立之敗”的局面。
皇帝在朝廷上失去了同宗室子弟的輔佐,趙高指鹿為馬的現象隨即出現。這種情況,根本是秦上層統治者在窄化了政治信仰及相應的權力價值觀念后,使得秦代君主專制的強權政治潛伏著異常險惡的風險與危機。本來,秦帝國的軍功等級爵位是為建立良好社會秩序,更好地進行社會整合而設立的,但它的政治名分與財富占有相結合的本質,又向人們披露了一個事實,即:等級越高,權力越大,土地財富的占有越多。在極端的封建君主專制下,皇帝高踞于權力金字塔頂端,俯視、監視著他的臣民;百官大臣和子民百姓則匍伏在他的膝下顫顫兢兢,誠惶誠恐地揣度著帝王的意旨,并準備承受突然降臨的雷霆;君臣之間的防范、猜疑更加深了雙方的冷淡,擴大了權力的距離。因此,在一個缺乏相應的社會道德倫理分野的政治局面下,對于皇帝個人來說,越是集權,越是大權在握,其所面臨的來自皇室與官僚階層的離心力就越大。這種離心力,有來自皇室內諸王對于帝位的爭奪;也有來自手握軍政大權的權臣對于皇權的窺視,同時亦有內臣近侍的變亂。加上帝王久居宮廷,這種離心力使等級之間距離日益擴大,加大了帝王和臣子之間的權力距離。這種擴大使君臣之間、群僚之間的宦海風波波詭云譎,并且使權力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地發生轉移。在秦二世執政的短短數年間,秦王朝政權由二世而趙高而子嬰,幾易其手,卻沒有受到官僚群體的集體制約與反對。所以,政治思想與信仰體系的功利性窄化與結構性缺失,是秦帝國政治整合與社會控制不能有效實行的原因之一。
再次,是秦王朝統治思想中政治哲學的低級化及單一化。秦過分崇尚武力和戰爭能力的結果,是使其在全國統一前夕,并沒有做好統一后的理論準備,而是簡單套用西秦政治思維模式以及戰國時期的宗教理論,使其統治理論存在重大缺陷。
秦王朝在統一全國前后,對于當時關東國家和關西社會的價值觀念體系的極大差異并沒有充分重視,也缺乏足夠的統一后的理論準備,這尤其表現在其理論的核心部分——政治哲學方面。從史料看,秦建立全國政權后,除了依靠法家思想治國外,其論證國家合法性以及政治等級制度的政治哲學,主要是戰國時期在東方齊地流行的“五德終始”學說,和來自民間的原始宗教的山川泛靈崇拜。
“五德終始”學說是以戰國時齊地思想家鄒衍為代表提出的一種以自然界五種物質元素(金、木、水、火、土)來解釋宇宙規律與歷史發展的一種政治與文化學說。《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以“五德終始”說解釋歷史演變規律,揭示朝代更替背后深層次的內容,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民眾能夠接受的一種朝代更替理論。由于時代局限,普通知識分子和百姓對社會發展、朝代更替的規律和原因不可能有深刻認識,但又迫切想知道隱含在朝代更替背后的必然性因素。自然界五種物質元素(金、木、水、火、土)作為戰國以來的一種逐漸流行的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一種對于宇宙與社會規律的認知工具,其五行相生相克、相互作用的道理淺顯易見,因而容易被人們接受。戰國時,鄒衍提出的“五德終始”說已在齊地廣為流傳。而秦相呂不韋在試圖為統一后的秦帝國建立“文治”之具時,就將”五德始終“說納入其政治視野中。《呂氏春秋·應同》篇曾記曰:“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這說明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已經被《呂氏春秋》較完整地采用和保存。秦統一后,由于秦當時政治理論準備的薄弱,就采用這個現成的哲學理論來作為其政治哲學的主要基石,一方面希望從法理上解釋秦朝統一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權威性,由此標示秦統一和朝代變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為統一后的秦帝國建立一種具有理論依據的文化整合模式,來統一當時六國“不同風”局面下的文化思想,進行制度建構。據《史記·封禪書》記,當公元前221年秦剛統一六國后,立即就有人出來以“五德終始”說獻計獻策。“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蚓)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周人之德是“火”,秦人之德是“水”,“水”克“火”,所以秦人取代周人統治了天下。“五德終始”學說雖然是東方齊地興起的學說,但是由于“五德終始”學說在當時秦政治思想理論匱乏的情況下能夠相對合理的闡明秦朝代更替的合法性,于是秦始皇毫不遲疑地把這一套拿過來,為新王朝的政治合理性服務。《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以秦始皇之口宣布秦替周而立,其水德屬性不可置疑。從文獻中也可以看出,秦采用“五德終始”說作為其政治哲學的本體,并沒有經過統一前后長時間的探討、研究,而是在建國初采用了部分官僚或者士人之說。①從《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載:“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可以看出,提出這個建議的,很可能不是顯官貴戚,而是普通官僚或者士人,尤其可能是東方齊地人氏。自此,秦就以“五德終始”的思想作為國家大一統的合法性論證,并且將之推向帝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層面,并以之來改正朔,易服色,完成帝國的政治與文化制度的改造大業。
秦始皇宣布采用“五德終始”說作為其政治哲學的基點后,就不僅大力神化和宣揚“五德終始”說,而且還將“五德終始”說的抽象說教進一步社會化,將其延伸到國家政治活動和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具體細微的人們社會生活中的規范、行為來體現“五德終始”說的無所不在。例如在政治與文化制度方面,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后合五德之數。”黑色成為秦國崇尚的顏色,“六”成為吉祥數字。分天下三十六郡,正好是六的六倍;銷毀天下兵器,鑄金人十二尊,遷徙天下富豪十二萬戶于咸陽,皆是六的二倍;甚至“三公九卿”亦與“六”暗合。將人們崇拜并以此為生的黃河改為“德水”,將嚴刑苛法也與五德之數相合。由此,帝國的政治與文化體制在“五德終始”說的基礎上建立了起來。這種做法,對于統一天下習俗風尚、價值取向起到了整齊劃一的作用,使人們在黑色的迷戀、“六”吉祥數的追述中體會到皇權的神圣性和秦專制統治的合理性,從而認同秦的統治。
但是,“五德終始”說又是一把雙刃劍。“五德終始”可以說是秦用來建立或者彌補其政治思想及國家意識形態缺失的一種論證手段,但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理論學說或者一種完備的政治信念。它雖然能對秦王朝的建立和統治給予神圣、合理的解釋,也同樣能給人們心理上一種潛在的暗示:朝代間的更替將永遠進行下去。秦取代周是合理的,因為“水”滅“火”,但“水”仍會被“土”替代。秦為了保證水德的長存與穩定,必須小心翼翼,從周的滅亡中不斷吸取經驗教訓,重視實際統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秦王朝并沒有記住這一點,最終被其他政治勢力所取代。
在遵從“五德終始”說的同時,秦始皇還大搞多元的泛靈性山川神靈崇拜。山川神靈崇拜是一種史前原始宗教崇拜。史前對自然山川神祭祀的內容甚多,表現在天、地、日、月、山林、川谷、丘陵、星辰、寒暑諸多方面。人們可以根據不同自然現象的功能,把它視為與人的禍福相關的禁忌與預兆。《禮記·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左傳》昭公元年記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史記·五帝本紀》記黃帝在位時,“順天地子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莢”。《管子·封禪》則云伏羲、炎帝、黃帝時的封禪情形:“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司馬遷《史記·封禪書》其說同。伏羲、神農、黃帝封泰山未必實有其事,但它說明這些酋長兼巫師循守泛靈禁忌這一傳統規則以趨福避兇的情形。這種泛靈性山川神靈崇拜自春秋戰國就一直流傳下來,成為當時基層社會流行的一種民間宗教信仰,并且沿用至秦。秦時,出于從思想上進行社會整合與控制的需要,帝國上下均采用了這種泛靈性山川神靈崇拜的方式。從秦朝廷來看,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就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的第三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秦始皇借向上天稟告改朝換代而要求他的臣民子孫“遵奉遺詔,永承重戒”,并且將這種訓誡用封禪刻石記錄下來,展示給國民,如刻石上所曰“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后世,順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圣志”等等。就在這次巡行途中,秦始皇經過彭城時“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秦王政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出巡到云夢,又“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秦始皇還沿用了秦國傳統的郊祀雍四畤上帝的活動來祭祀天地鬼神。秦二世時候的情形大抵也是如此。太卜官曾評論說:“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而秦帝國由于信仰的多元性與泛靈性,始終沒有將國家宗教上升為一種一統國家所需要的統一神袛的一神教宗教,而是始終使其僅僅具有民間的原始宗教的山川神靈泛靈崇拜性質。這使它與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統一宗教以及統一神袛的一神教宗教具有十分重大的區別。所以,秦帝國在政治信仰及社會價值觀上,由于缺少其國家意識形態重新構建的基本要素,不得不用傳統的自然界多神崇拜來作為其國家進行社會控制的思想信仰。這樣,當世俗化的政治理論不能完成對于全國民眾思想統治的功能時,宗教又處于一種在原始宗教層面的低級狀態。它使秦帝國政治思想與意識形態缺乏對于各個階層人們的政治價值觀和社會等級次序、規范的相關論證,缺乏對于社會行為的約束和道德倫理的提倡,由此也就使完成戰爭功能的秦國家機器始終還在軍事性的運轉軌道中,各級官吏仍然依靠戰爭時期的刑治手段來進行社會控制,由此使秦帝國先天存在著一種理論上的結構性缺陷,這確實是十分可悲又作用有限的。
所以,由于秦王朝過分重武輕文,在全國大一統前期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而在全國一統后,又沒有及時調整國家政治思想理論,僅僅依靠適應于戰爭狀態的法家刑治主義來進行和平時期的思想統治,它就使秦王朝的統一缺乏穩固的思想基礎。事實上,在秦完成統一后,帝國廣大官吏們的思想信仰和國家治理理念并沒有轉化,奉行強權政策和皇權至高無上的思想路線,采取的是以刑治精神為主導的嚴刑峻法、刻薄寡恩的社會控制方法。這在當時社會基礎與文化模式都十分不同的關東六國舊地,必然會缺乏統治的根基,并產生極其負面的影響。事實上,這正是秦王朝在社會轉型重建中不成熟的內斂機制與大一統社會整合中的秩序失范的必然結局。如果僅僅從時間段上看,秦對于全國統一是呈摧枯拉朽之勢的。盡管秦統一六國有著長期的戰爭能力準備,但在具體的最后統一過程的時間段是相對較短的。秦始皇從公元前230年起,僅僅花費了10年左右時間就兼并了山東六國,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在統一的國家政權有機體中,如何不斷地修正、調整自己的統治方式,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大問題。秦政權社會整合與控制失效的重要虧缺就在于社會環境從戰亂轉型到統一安定中,沒有實現統治思想與政策的調整,缺乏在和平局面下有效的自我反省和內斂機制,并且在其狹隘的功利性價值取向下,橫征暴斂、無所顧忌。這就使得一大批舊貴族以及廣大士人在統一以后找不到更多獲取利益的途徑;而廣大百姓在嚴刑酷法下,也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條件和生命保障。由此觀之,秦王朝的失誤就在于沒有完成國家治理和社會整合中政府權能及職責的及時調整,以及安寧局面下的規范化和秩序化。其結果,必然是天下洶洶,民不聊生進,進而激起全國民眾的反抗。秦朝的速亡正與此有著極大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