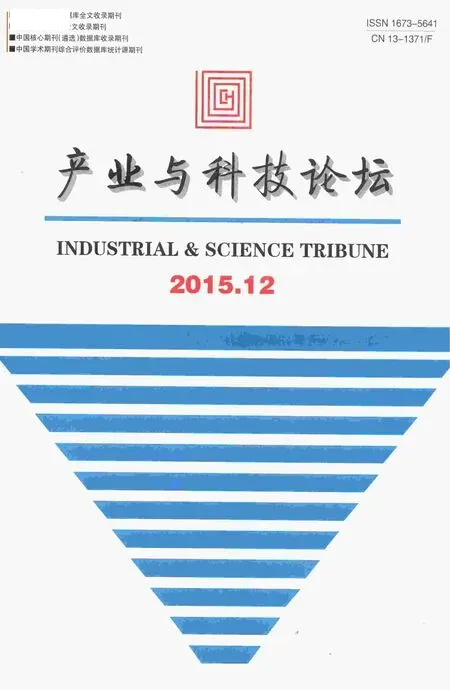基于人類語言起源的古代漢語語言學價值研究
□ 呂文科
一、人類語言起源
(一)人類語言起源的歷史研究。當今世界紛繁復雜,不同國家、人種、地區乃至同一個國家的不同民族、地區之間人類的語言都可能存在極大的不同。因此,關于人類語言起源的學說,在不同國家或不同學術圈子之間都存在很多不同觀點。著眼于過去和現在,雖然其中很多學說尚未形成體系,但依然給我們語言研究者以啟迪。這些說法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語言是神授的。在西方近代世界和傳統中國的少數民族中,一系列的神話和傳說告訴我們語言是上帝賦予人們的,人們一生下來就已經掌握了講語言的本領。神授說的代表作有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克拉底魯篇》和被奉為基督教佛學經典的《圣經》。前者告訴我們語言來自于天上各路神仙對各種事物制定名稱的使用,而后者則用人類祖先亞當制造出來時就已經會說話的事例告訴我們是上帝創造的語言。
2.摹聲說。此學說認為,人類的語言來源于人類對自然世界聲音的模擬和效仿,比如中國語言中的“布谷鳥”之所以為此名是因為它叫聲似“布谷”,此學說持有者的代表人有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與海岱爾。
3.勞動號子說。還有學說認為,最初的語言來自于人們勞動時的用力呼號,持此學說的學者們認為,勞動不僅解放了人類的身體,還給了人們可以說話的生理基礎,另外,人們在勞動時需要語言與彼此溝通,所以最初的語言由此產生。
4.感嘆說。感嘆說認為最初的語言起源于人類的生理反應,比如幼兒最初不會說話時用“啊”、“呀”等表示自己的疼痛,高興時則又有另外的聲音。
5.手勢說。此學說把語言看作由人類身體符號系統轉變而來的另一種符號系統,由法國學者孔狄拉克提出。
(二)人類語言起源的單源性。從上述角度觀察人類語言的起源,每一種學說都有其道理,也有其弊端。如神授說實際混淆了物質世界與人類主觀能動性的聯系與區別,這種學說過于強調神的力量,而忽視了人類改造物質世界、提升自身能力的實際。另外如勞動號子說,雖然勞動對人的生理發聲器官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促進作用,但把人類最初的語言形式完全歸結于勞動本身不免犯了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錯誤。
哲學的發生學原理告訴我們,無論一個事物發展到后期其基本形式有多么復雜,這種事物的起源總是簡單的。這種知識否定了一些學者妄圖把上述學說合而為一體解釋語言起源的想法,告訴我們人類語言起源必定具有單源性,即源頭單一。這種單一并不是指語言發展的形式固定而唯一,只是強調人類語言初期形態的簡單性。
人類最初的語言學家大多數為哲學家出身,這種現象告訴我們,人類在開始思考世界之初,便已經開始了語言源頭的探索之路。語言起源研究至今,不同的結論五花八門,不少學者甚至開始主張除了人類的其他動物也有語言。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而愚蠢的,語言能力是人類在動物群體中獨有的溝通手段。
(三)人類語言的產生。有些學者認為,語言是在人類發展的一瞬間產生的,如德國學者洪堡特認為人類語言其實是一種“突現”,即某一時刻人類突然掌握了語言能力;我國的王士元先生也在后來計算機輔助的語言學研究中證明,人類語言確實為“突變的”爆發。根據“生物重演律”,我們在兒童語言中研究“突現”現象,最終發現兒童語言習得過程對人類語言的濃縮性重演也告訴我們語言發生之初確實是“瞬間”的。另一方面來說,我們都知道語言與思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正是因為思維人類才有了發展和產生語言的可能性,同時語言的發展又促進著思維的進步,從思維產生的角度對語言起源進行研究,我們發現在語言的雙詞句階段,指稱代詞與陳述代詞兩分,名詞、語法和動詞的語言三要素也在此時同時“瞬間”產生。
“語言突現”說雖然已經得到了大部分學者的認同,但尚有探討的余地。然而換一個角度發現語言,如從有著五千年歷史的中國語言的最初形式——古代漢語范疇考證原始語言特點,我們會發現古代漢語的研究在這一課題領域極其有價值,古代漢語的特點更是從側面佐證了原始語言的“突現”和其他特點。
二、古代漢語的語言學價值研究
(一)古代漢語與人類原始語言的關系。關于中國古代漢語與人類原始語言的關系,不少西方學者早有猜測,這些猜測與論述雖然過于感性,但仍有極大的啟迪意義。施萊哈爾作為語言譜系研究的鼻祖型學者就曾經提出,人類的語言發展必定是經過類似于漢語那樣的簡單而孤立的狀態,通過后期的粘著變化,才能夠變成最后屈折語言的高級形式。由此論述,語言學開始分化人類語言為孤立語、粘著語和屈折語三大形式,漢語即為孤立語的代表性語言,即最接近人類原始語言的語言形式,而屈折語即語言發展的晚期形態代表語言為印歐語。另外,古代漢語語言距今幾千年,原始語言距今也只有上萬年,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古代漢語是我們研究原始語言形式與語言起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國古代漢語語法形式簡單保守,與人類最初的思維形式對應程度高,因此古代漢語即為現代語言中最接近原始語言的語言形式,可以作為人類原始語言的“活化石”進行對比研究。
(二)語言起源角度的古代漢語語言學價值研究。無論何種民族語言或是同一民族語言的不同時期,其語言形式必定為個性與共性的統一體,即它既有自身民族的語言特性,又兼有世界語言的共同特征與階段特點。由此觀之,我國古代漢語既有漢民族在古代時期的語言特性,同時又代表著一定的原始語言特性。語言學和哲學大家薩丕爾曾經說過,“語言學視野所及,從拉丁語到俄語的演變過程,其實是大致相同的,盡管最近時期的人類書市地形可能有所改變。接著發展到英語階段,人們會發現語言的大山的山形走向好似有所歪斜,但是大致走向我們依稀能認得出來,但是好像到了漢語這里,我們發現連語言山頭頂的天都變了。”這些話指出了古代漢語與其他語言的明顯具有極大的不同,同時也告訴了我們古代漢語的獨特性與在世界語言類型學與發展研究問題上的獨特性。
三、結語
縱觀世界語言,只有古代漢語在類型上如此特別,也只有古代漢語是人類現有語言中最接近人類語言原始形態的語言類型之一,相比于世界其他語言,在人類語言起源角度,古代漢語研究具有更大更重要的意義。同時,漢語是人類語言中歷史資料最豐富的語言,古代漢語傳承至今不得不說是世界語言叢林中的一大奇跡,可以說是活著的語言中可考歷史最長的語言,因此,加強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不僅對于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研究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對中國語言學乃至世界語言學的研究都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1]姚舟.人類語言的起源與古代漢語的語言學意義[J].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
[2]李無未,李遜.漢語現代語言學理論體系的最初構建——日本《現代中國語學》(1908)的意義[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1
[3]任曉彤.論語言學理論在“古代漢語”教學中的運用[J].教育與教學研究,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