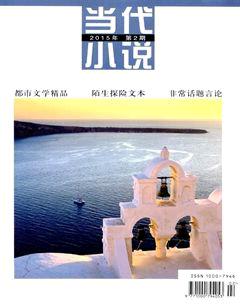后巷
劉玉明
立春后的這場(chǎng)雨把小城湮沒在蒙蒙的水汽之中。軟白的水霧在小城的上空凝聚盤旋,再慢慢流淌下來,繾綣在青瓦屋面上、深巷淺胡同里。冬天里灰白的瓦草、青石板罅隙里枯死的青苔緩過氣來,把一身淡淡的綠在不起眼處招搖。春雨下了整整十天,把這座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小城溶在綿密的細(xì)雨里,慢慢發(fā)泡變軟。
春雨貴如油。但林慕華回想起1944年春天的這場(chǎng)細(xì)雨,總覺得有很大一部分時(shí)間在雨水里漚爛了,壞掉了。透過這部分壞掉的時(shí)間,林慕華依稀看見陳亞蘭站在被歲月剝蝕的舞臺(tái)上,她低吟淺唱,她揮動(dòng)白色的水袖,她滿是青春的眼睛……林慕華對(duì)妻子西鳳說,這個(gè)人,我一輩子也放不下。他說這句話的時(shí)候,西鳳正安靜地躺在他的懷里。身患絕癥的西鳳伸出干枯的手摩挲著林慕華的臉,說,這一輩子,我最放不下的還是你。
好想再回后巷去看看。臨死前,西鳳說。
林慕華的眼睛濕了,淚光中,他看見21歲的林慕華撐著黑布傘走過李子園舞廳,走過西街,走進(jìn)后巷那條斜斜的青石面街道。
林慕華撐著黑布大傘來到后巷的祥福林茶館的時(shí)候,鄧福林正在和幾個(gè)茶客閑聊。“趕得上梅雨季節(jié)了,啥東西都長(zhǎng)了白毛。”鄧福林抄著手說。
“西鳳,西鳳,你們家掌柜說東西都長(zhǎng)白毛了,你長(zhǎng)了沒有?”一個(gè)茶客笑嘻嘻地對(duì)正在續(xù)水的西鳳說。
“問你姐姐去。”西鳳說。幾個(gè)茶客發(fā)出放肆的笑聲。
鄧福林嘿嘿地笑。透過模糊的玻璃窗,鄧福林看見林慕華站在朱紅斑駁的柱子前小心翼翼地收起傘。水霧飄蕩的街面上,走過一條神情懨懨的狗,走過披著蓑衣戴著斗笠的挑夫,走過打著油紙傘的小腳女人。林慕華抬頭看了看懸在屋檐下的紅燈籠,燈籠被雨水打濕了,滴下淡淡的紅染料。
“林先生來了。”西鳳對(duì)鄧福林說。鄧福林打了個(gè)哈欠,看著西鳳。西鳳嘟囔著說:“我去看看水開了沒有。”
林慕華踏進(jìn)茶館,鄧福林就迎了上去。林慕華不太喜歡鄧福林。鄧福林看起來有些猥瑣。鄧福林說:“林先生,可把你等來了,你老好久也沒有來喝茶了。我家里的唱片機(jī)壞了,老是唱不響,正想找你看看咋回事呢……”小城里的人喜歡把留聲機(jī)叫做唱片機(jī)。
西鳳提著水壺出來,說:“唱片機(jī)有啥好聽的,只有聲音又看不見人,壞了扔掉算了。”
“你懂個(gè)屁。”鄧福林說,“我這個(gè)唱片機(jī)還是托人從上海買回來的呢,全縣城就只有幾個(gè),說扔了就扔了?”他一面說著話,一面讓林慕華上了樓。
留聲機(jī)是好的。林慕華笑著對(duì)關(guān)門的鄧福林說:“你的板眼兒真多。”
鄧福林走到留聲機(jī)前,很熟練地取下唱針,從中空的唱針管里取出一卷紙片。“很快就要壞了。”鄧福林說著話,把紙片卷成小卷放進(jìn)林慕華的傘柄里。“龍公館的張副官認(rèn)識(shí)吧,他明天會(huì)去廣東會(huì)館聽?wèi)颍堰@個(gè)交給他。”
“我都成了你們的信使了。”林慕華說,“你和張副官很熟,自己去不就行了?”
鄧福林用舌頭頂著牙花子,慢騰騰地說:“日本人做夢(mèng)都想搞掉重慶,你是曉得的吧?”
林慕華說楊先生早就告訴我了。“我只是一個(gè)賬房,不是郵差。”林慕華說。
鄧福林定定地看著他,“你不是一個(gè)中國(guó)人?日本人快要打到我們家門口了。”鄧福林咄咄逼人的目光和平時(shí)判若兩人。林慕華有點(diǎn)泄氣,“你和張副官是一伙的?”
“他和你一樣,都是有血性的人。”鄧福林說。
“我都做了很多次了,啥時(shí)候才能加入你們?”林慕華鼓起勇氣說,你們是共產(chǎn)黨還是國(guó)民黨?
鄧福林看了林慕華一會(huì)兒,嘿嘿一笑,“你已經(jīng)加入了。”
林慕華有些失望。鄧福林無疑是個(gè)很狡猾的家伙,林慕華想。其實(shí),關(guān)于國(guó)民黨和共產(chǎn)黨——這類政治上的事情,林慕華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他也不愿意去搞清楚。林慕華對(duì)自己現(xiàn)在的生活很滿意。他能夠成為兆豐米廠的賬房先生,完全得益于父親的朋友楊先生幫忙。
父親林子峰對(duì)于林慕華來說,既熟悉又陌生。林慕華從小就和母親生活在鄉(xiāng)下。在兒時(shí)的記憶里,父親總是來去匆匆。也許在睡夢(mèng)中親過自己的額頭,但這些猶如水面的浮萍,留不下根腳。林慕華在鄉(xiāng)下的學(xué)堂里讀完初小后,父親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了。
在一個(gè)暮色蒼茫的傍晚,楊先生來到鄉(xiāng)下。那天晚上,母親打發(fā)林慕華早早睡下,便和楊先生說話。“他是一個(gè)很了不起的人,到死也沒有說出該說的話。”楊先生說。母親低低地啜泣,讓林慕華感到那個(gè)曾經(jīng)在睡夢(mèng)里親過自己的男人像煙霧一樣消散了。
楊先生留下了一摞銀元,帶走了林慕華。他對(duì)林慕華說,你父親希望你繼續(xù)讀書。林慕華說,我父親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是一個(gè)工人。楊先生的回答充滿了可疑,正如父親給林慕華留下的印象一樣。
工人就是像米廠里的那些挑夫一樣,有什么事情能讓他連命也沒了?
他是一個(gè)有血性的人。楊先生說。這句話不但陪伴著林慕華走過10年的光陰,也讓林慕華為此付出了一生。
楊先生說,我會(huì)好好地照顧你。
林慕華沒有選擇繼續(xù)讀書,他進(jìn)了兆豐米廠。在他的印象里,父親林子峰應(yīng)該就是兆豐米廠里的一個(gè)工人。楊先生履行了他的承諾。精通算術(shù)的林慕華成了賬房先生——這無疑是一個(gè)很輕松的活路,而且每個(gè)月能夠領(lǐng)到一筆在鄉(xiāng)下人看來很是豐裕的錢。
林慕華很快熟悉了這個(gè)小縣城。楊先生開始介紹一些人給他認(rèn)識(shí)。這些人好像和他的父親很熟,但都不太愛說話。他們讓他捎帶東西,有時(shí)候是一包大前門的煙,有時(shí)候是一張裹著蠟的丸子,或者是一張寫滿莫名其妙數(shù)字的紙片——對(duì)于林慕華來說,這都是順便的事。他做這些事頗有天賦。而且,能夠順便得到一點(diǎn)小費(fèi)畢竟是件很快樂的事情。“和他父親一樣能干。”楊先生感嘆說。
林慕華從不問為什么要捎帶這些東西,至于后來東西送給了什么樣的人,更與他無關(guān)。楊先生說過,你只管把東西送到就行了。
我父親是不是也和我一樣?林慕華問楊先生這句話的時(shí)候,剛過20歲生日。3年的時(shí)間足以讓一個(gè)人變得成熟。
楊先生沉默半晌,說是。
他就是給你們帶東西送了命的。林慕華感到一絲恐懼。
你害怕了?楊先生笑瞇瞇地問。
這個(gè)城市里有國(guó)民黨和共產(chǎn)黨,我父親是哪一個(gè)黨的?林慕華突然問道。
楊先生一怔,好一會(huì)兒才說,日本人的飛機(jī)都飛到重慶了,還什么黨不黨的!
楊先生是一個(gè)秋天里離開小城的。他告訴林慕華,今后沒事兒就去后巷的祥福林茶館喝喝茶。林慕華很快就淡忘了這件事。他一直不喜歡喝茶。直到西鳳來柜臺(tái)買米結(jié)賬的時(shí)候,說起祥福林茶館才把林慕華沉睡了許久的記憶喚醒過來。那天,他把西鳳給的零頭爽快地減掉了。
我會(huì)到茶館來喝茶的。他對(duì)西鳳說。
西鳳看著他,抿著嘴淺淺地笑。
林慕華認(rèn)識(shí)了鄧福林。鄧福林像老熟人一樣,親熱地稱他林先生。鄧福林和楊先生是一伙的。林慕華想。
鄧福林把唱片機(jī)轉(zhuǎn)了幾圈,阮玲玉綿軟的聲音便彌漫在整個(gè)房間里。“好聽嗎?”鄧福林問,林慕華不言聲。“我如今千般苦耐心受忍,把性命比鴻毛不足重輕。明天是陳亞蘭的《魚藻宮》,老么子串編的川劇本子。可惜我看不成了。”鄧福林嘆了一口氣說。
林慕華疑惑地望著鄧福林,這個(gè)形容猥瑣而又卑微的茶館老板到底是一個(gè)什么樣的人?他沒有問鄧福林,因?yàn)樗嘈胚@個(gè)疑惑遲早有解開的一天。
看著邁出門口的林慕華,鄧福林突然說:“你覺得西鳳這個(gè)孩子咋樣?”
林慕華默默地看了一眼鄧福林。“我怕有一天我走了,沒有人照顧她了。”鄧福林眼睛里流溢出莫名的哀傷。
鄧福林恭恭敬敬地送林慕華出門,走到街面上的時(shí)候,林慕華才透了一口氣。天色很陰暗,空氣卻很清新。祥福林茶館和鄧福林一樣,顯得有些沉悶。這種感覺很微妙,林慕華一時(shí)間說不上來。他回頭看了看祥福林茶館,鄧福林已經(jīng)進(jìn)去了,只有西鳳拎著茶壺,靠著門口朱紅剝落的柱子,眼睛里起了一層水霧。
位于城東的廣東會(huì)館建于咸豐末年,歇山式牌樓拖著兩邊廂房,順著西廂房旁的走馬轉(zhuǎn)角樓拾級(jí)而上,便是古戲樓。戲樓上的雕梁綴著布滿灰塵的蜘蛛網(wǎng),隱約能夠看見鎏金的顏色。這座古老的建筑曾是廣東鹽商在小城的落腳點(diǎn),如今卻成了舵把子程丹九的私產(chǎn)。
林慕華走進(jìn)會(huì)館的時(shí)候,陰云被風(fēng)攪亂了,水霧也收斂了不少,有些要放晴的意愿在空中流轉(zhuǎn)。廂房?jī)膳缘淖呃壬献鴿M了看戲的人。張副官和程丹九坐在西廂房走廊的前排聊得正歡。后臺(tái)的鑼鼓有一搭沒一搭地敲響。林慕華好不容易在走馬轉(zhuǎn)角樓處找了個(gè)位置坐下,把雨傘靠在身旁的板凳上。便有伙計(jì)倒了茶水,上了一盤葵花籽。
人多眼雜,張副官身份又太特殊,如何才能把雨傘里的東西交給張副官?林慕華正在思索,聽得后臺(tái)一片鑼響,幕布徐徐拉開,戚夫人已經(jīng)款款站在臺(tái)上。戚夫人挽個(gè)水袖,把幽怨的眼神拋灑下來。林慕華只覺得心里被人揪了一把。四下里一下子仿佛沒了聲息,瞬間便又爆出蓬勃的叫好聲來!
這個(gè)“戚夫人”便是陳亞蘭。
陳亞蘭這個(gè)女人是個(gè)尤物。兆豐米廠的總管劉麻子曾經(jīng)流著口水對(duì)林慕華說。劉麻子說他玩過一籮筐的女人,就是沒有和陳亞蘭那樣漂亮的女人睡過,太不值得了。“還是程丹九老狗有福氣,天天摟著這個(gè)嫩娘們兒睡。”劉麻子說這句話的時(shí)候,唾沫和酒氣噴了林慕華一臉。身為國(guó)民黨川西北駐小城情報(bào)站的負(fù)責(zé)人,劉麻子在小城解放的第二年便被槍斃了。
劉麻子死的時(shí)候保持了長(zhǎng)期潛伏的穩(wěn)重,他雙腿盤坐在地面上,冷眼地看著群情激憤的人們。透過一張張血紅的面孔,他看見陳亞蘭弱不禁風(fēng)地靠在林慕華肩膀上。林慕華仿佛在對(duì)著他說話,又仿佛在對(duì)著陳亞蘭低低地絮語。劉麻子長(zhǎng)嘆一聲,他把目光從林慕華和陳亞蘭身上收回來的一剎那,他看見一顆子彈呼嘯著奔向自己的眉心。
劉麻子死前的那一聲嘆息,是為了自己一輩子的事業(yè)終于結(jié)束的解脫還是到死也不知道林慕華就是潛伏在自己身邊的敵人?林慕華無從知曉,他已經(jīng)無暇去想這些了。他扶著搖搖欲倒的陳亞蘭從人群中走出來的時(shí)候,天空異常的藍(lán)。在他倆的身后,是押解他們的便衣。
劉麻子是特務(wù),身份明確;但林慕華的身份卻很可疑,沒有人能夠證明他的身份。在以后的歲月里,林慕華一直在記憶里搜索能夠證明自己身份的人,但這些人都已經(jīng)不在人世了。陳亞蘭不能證明他的身份,因?yàn)樗橇帜饺A的妻子。身份可疑的林慕華和妻子陳亞蘭在劉麻子被槍斃之前便被關(guān)進(jìn)了一個(gè)偏遠(yuǎn)山村的麻風(fēng)病醫(yī)院。這所醫(yī)院四面高墻,連鳥也飛不出去。參觀完劉麻子被槍斃的后一年,活在恐懼中的陳亞蘭終于被懷疑感染了麻風(fēng)病而死去,林慕華看著她像麻袋一樣被拖上卡車?yán)吡恕D且惶欤谔炜诊h蕩的白云里,林慕華依稀看見陳亞蘭青春的臉龐、青春的眼睛。
就是這一張臉龐和青春的眼睛讓林慕華無法自拔。林慕華看著臺(tái)上的陳亞蘭,忘記了喝茶,忘記了吃瓜子,忘記了此前來的任務(wù),時(shí)間在他的背后倏忽而逝。他盯著臺(tái)上的戚夫人,這個(gè)曾經(jīng)把劉邦迷得神魂顛倒的女人,現(xiàn)在又哭哭啼啼尋死覓活。
大幕徐徐閉上,戚夫人不見了,陳亞蘭也不見了。一個(gè)老生上臺(tái)咿咿呀呀地唱著繞口令似的詞句。他一句也沒有聽進(jìn)去。直到卸了妝的陳亞蘭從樓梯上下來,碰倒了他搭在凳子上的雨傘。
“先生,是你的傘嗎?”陳亞蘭俯身拾起傘問他。
林慕華慌忙起身,桌子上的茶杯被他的慌亂掀翻了,茶水流了一地。他怔怔地看著眼前明艷照人的陳亞蘭,一股自慚形穢的東西緩緩涌了上來。
“是……不是……”林慕華結(jié)結(jié)巴巴地說。
陳亞蘭撲哧一笑,眼前這個(gè)憨厚帥氣的年輕人顯然被自己迷住了。陳亞蘭對(duì)自己的美貌很自信。
張副官和程丹九走了過來。林慕華仿佛撈著了一根救命草,他說:“傘是……是長(zhǎng)官的。”
“哦,張兄帶了傘來么?”程丹九看了一眼已經(jīng)開始放晴的天空,意味深長(zhǎng)地說。
張副官把林慕華掃視了一眼,“春寒勤穿衣,出門記帶傘嘛。”張副官說,“剛才來的時(shí)候順手扔在這里了,小兄弟不說,我倒是忘記了。”
陳亞蘭把傘遞給張副官,依偎在程丹九身邊。林慕華嘴里泛出一絲酸澀的味兒。
程丹九陪著張副官走出會(huì)館,陳亞蘭始終挽著程丹九的胳膊。林慕華看著她的背影,悵然若失。“這個(gè)小伙子人不錯(cuò)。”林慕華隱隱聽見程丹九說。
程丹九說這句話的時(shí)候,輕輕拍了拍陳亞蘭的肩膀。林慕華有一種想沖過去打程丹九的念頭,但他很快打消了這個(gè)愚蠢的念頭,因?yàn)殛悂喬m回過頭對(duì)他輕輕地笑了一下。林慕華突然覺得地面很柔軟,自己正在慢慢地陷落下去。
林慕華開始迷上了看戲。沒有陳亞蘭上臺(tái),林慕華就會(huì)覺得生命里缺少什么似的。這期間,鄧福林的留聲機(jī)壞了幾次,但都是讓西鳳來找林慕華去修的。這給祥福林茶館里喝茶的人們留下了一個(gè)很好的印象——米廠的賬房林先生對(duì)西洋的玩意兒很有一套。
林慕華開始對(duì)鄧福林的把戲感到厭倦。他已經(jīng)沉浸在對(duì)陳亞蘭的迷戀之中了,印象里的父親是如何死去的疑惑開始在他的生活里漸行漸遠(yuǎn)。鄧福林開始感到一絲憂慮。“一個(gè)有血性的人”的回答對(duì)于林慕華來說,已經(jīng)開始失去了誘惑力。紅顏禍水啊,鄧福林感嘆說。
鄧福林的話語里充滿對(duì)林慕華的不滿,他準(zhǔn)備放棄林慕華,對(duì)于一個(gè)迷戀女人的男人,是相當(dāng)危險(xiǎn)的。“他一點(diǎn)也不像他的父親。”鄧福林說。
鄧福林的話語里頗有恨鐵不成鋼的意思。
鄧福林說這句話的時(shí)候,是在一次相當(dāng)隱秘的聚會(huì)上。程丹九也在場(chǎng),沒有人會(huì)懷疑一個(gè)掌控著幫派的黑社會(huì)頭目——至少不會(huì)懷疑他是一個(gè)共產(chǎn)黨員,劉麻子不會(huì),因?yàn)樗统痰ぞ旁谝黄鸷染啤㈡渭说臅r(shí)間不下五十次。黑社會(huì)頭子程丹九有他的生存之道,他是連接官方和民間的橋梁。劉麻子很信任程丹九,這一點(diǎn)不容置疑,在1939年女子中學(xué)串聯(lián)游行事件無法收拾的情況下,程丹九動(dòng)用了非常手段把事件平息了。女子中學(xué)一個(gè)教員被程丹九的手下打得癱瘓?jiān)诖玻肽旰蟛抛叩脛?dòng)路。對(duì)此,程丹九還狠狠責(zé)罵了手下的弟兄:“你們平時(shí)嫖女人的干勁到哪里去了?!”
劉麻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程丹九喜歡抽鴉片玩女人,但他從來不做走私鴉片、開院子的買賣。劉麻子曾經(jīng)問過他,這么賺錢的買賣您咋就不插一腳呢?
程丹九噴出一口煙霧說,我怕呀,怕我的兄弟賣命的時(shí)候要吸了鴉片玩過女人才使喚得動(dòng)。程丹九是靠賺挑夫的錢發(fā)達(dá)的,最近他還把全城倒夜香的活路霸占了來做。
劉麻子大笑。程丹九是一個(gè)不要命的人,更是一個(gè)胸?zé)o大志的人。沒有危險(xiǎn),值得利用,這樣的人也值得拉攏。在劉麻子的指示下,縣政府給了程丹九不少好處。程丹九用全城半個(gè)月的屎尿錢盤下了廣東會(huì)館。
劉麻子做夢(mèng)也沒有想到,程丹九會(huì)是一個(gè)共產(chǎn)黨員。
黑社會(huì)頭子程丹九在解放后就被拉到當(dāng)?shù)匾蛔苡忻纳缴咸帥Q了。告發(fā)他的人正是女子中學(xué)的那位被他手下打斷腿的教員。程丹九沒有辯解的機(jī)會(huì),忙著追趕國(guó)民黨殘余部隊(duì)的解放軍敢死隊(duì)沒有時(shí)間去核實(shí)一個(gè)黑社會(huì)頭目提供的證詞。程丹九閉上眼睛,等待死亡的召喚,他想起自己的女兒——陳亞蘭——那個(gè)他和戲子生下的私生女,有林慕華這樣忠厚的人照顧,再也沒有什么可以顧慮的了。
“這個(gè)小伙子不錯(cuò)。”這是程丹九第一次見到林慕華對(duì)女兒陳亞蘭說的一句話。
聽完鄧福林的話,程丹九皺著眉頭,說:“可是他畢竟是林子峰兄弟的兒子呀。”
鄧福林說:“敵人會(huì)利用他的弱點(diǎn),這難道不是很危險(xiǎn)的嗎?”
程丹九想了想,說:“難道要讓林子峰絕后?”
鄧福林痛苦地閉上雙眼。
程丹九堅(jiān)決不同意鄧福林的意見,他用自己的女兒來保全了林慕華,“亞蘭調(diào)查過了,這個(gè)小伙子很不錯(cuò)。”程丹九說。這一點(diǎn)無疑很感性化,很快遭到鄧福林的反對(duì),鄧福林說:“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guān)。老程,我怕你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到頭來把女兒也搭上了。”
程丹九說:“你們可以懷疑我,但不能懷疑林子峰,他到死也沒有說出我們的事來。”
這場(chǎng)關(guān)于林慕華去向的爭(zhēng)論最終不歡而散。
“但愿你沒有看錯(cuò),他是一棵好苗子。”鄧福林對(duì)程丹九說。
林慕華與死神擦肩而過。正如鄧福林期望的那樣,他出色地扮演著線人的角色。這項(xiàng)危險(xiǎn)而有趣的工作能夠讓他暫時(shí)忘卻思念一個(gè)女人的痛苦。直到日本人的飛機(jī)光臨了小城,他的工作才暫時(shí)告一段落。
距離重慶不到四百公里的小城顯示出無比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日本人的飛機(jī)從這一年的夏天便頻頻光顧。丟下炸彈、機(jī)槍掃射——那些讓人恐慌的機(jī)器在天空肆意妄為。小城籠罩在硝煙之中。
轟炸持續(xù)了一個(gè)多月。米廠無法正常開工,林慕華開始閑了下來。沒有人知道那些長(zhǎng)著翅膀的怪物什么時(shí)候會(huì)飛來。整個(gè)城市亂成了一鍋粥。
后巷的祥福林茶館遭遇了滅頂之災(zāi)。那天,西鳳正在茶館后院里燒水,她聽見天空中響起嗡嗡的聲音,像蝗蟲飛過一樣。一顆炸彈挾著風(fēng)聲落了下來。
鄧福林正在房間里擺弄著他的留聲機(jī)。炸彈不偏不倚地落在祥福林茶館中間,兩層高的小樓轟的一聲就塌了。飛濺的瓦片雨點(diǎn)一樣拋落在西鳳的腳下,西鳳尖聲驚叫。
那是一顆沒有爆炸的炸彈。淡綠色的彈身冒著青煙,地面起了一個(gè)大坑。驚魂未定的西鳳扔掉手中的茶壺,在騰起的煙塵中尋找鄧福林。
鄧福林躺在一堆瓦礫之中。西鳳把他刨出來的時(shí)候,他手里緊緊地抱著留聲機(jī)。一個(gè)茶客的半截膀子搭在他的身上。
鄧福林對(duì)淚流滿面的西鳳說:“城里不安全,你……你還是回鄉(xiāng)下去吧。”西鳳咬著嘴唇。鄧福林口鼻里涌出的鮮血讓她手腳無措。爆炸的聲響震顫著大地,鄧福林長(zhǎng)長(zhǎng)地吐了一口氣,他想努力閉上眼睛,卻怎么也不能,西鳳撕心裂肺的哀嚎在炸彈的巨響聲中愈來愈遠(yuǎn)。
西鳳沒有回鄉(xiāng)下,她抱著留聲機(jī)在街面上游蕩。小城在飄蕩的硝煙和燃燒的火焰里哭泣。四處奔逃的人們像炸了窩的兔子,找不到方向。咒罵和凄厲的哭聲讓她感到彷徨無計(jì)。
在廣東會(huì)館外面,西鳳發(fā)現(xiàn)了林慕華。光著一只腳的林慕華從奔跑的人群里擠出來,布滿血絲的眼睛四下里搜尋,仿佛丟失了最重要的東西一樣。西鳳跑過去,喊,林先生,我們掌柜的死了。
林慕華沒有聽見她的聲音,他在人群里尋找陳亞蘭。西鳳手里抱著的留聲機(jī)硌疼了他的肋骨,他才停下來。
西鳳,你怎么來了?他說。
我們掌柜讓房梁壓死了。西鳳哭著說,天上落了一顆炸彈,沒有爆,把房子壓塌了,鄧掌柜從樓上跌下來,讓房梁壓死了。
林慕華覺得腦子里一片空白。他看了看天空中升騰的黑煙,說,西鳳,你先到我那里去吧。
在這個(gè)令人恐慌和煩悶的夏天,西鳳的到來,完全打亂了林慕華的生活。逼仄的房子除了廚房、廁所,剩下的空間就很小了。林慕華說,西鳳,你明天還是回鄉(xiāng)下去吧,鄉(xiāng)下安全一些。
西鳳撥弄著鄧福林留下的留聲機(jī),眼神很憂郁。林慕華訕訕地說,我去買點(diǎn)菜回來。
林慕華徑直去了廣東會(huì)館的戲院,里面空無一人。透過昏暗的門洞,林慕華仿佛看見程丹九和陳亞蘭從里面走出了,他們有說有笑,神態(tài)親昵地穿過林慕華的眼眸,穿過林慕華的身體。
林慕華的心慢慢涼了下來。幽暗里,低低高高的哭聲傳進(jìn)他的耳膜。他走進(jìn)后巷。鄧福林和被壓死的茶客的尸體已經(jīng)被拉到化人廠去了。只留下了一片廢墟。那顆沒有爆炸的炸彈靜靜地佇立在廢墟中間,周圍被拉起了紅線。
林慕華突然感到孤獨(dú)。楊先生不在縣城,鄧福林又死了,一直做著的事情戛然中斷了,心里有說不出的滋味,不知道是悲傷,還是輕松。林慕華怔怔地看著那顆炸彈。殘破的燈光映照在炸彈上,發(fā)出綠瑩瑩的光。
晚上,林慕華才回到寓所,屋子已經(jīng)被收拾過了,雜亂的衣物裝進(jìn)了箱子,放在床底下。油膩的玻璃上被舊報(bào)紙遮蓋了。家具挪動(dòng)了地方。屋子看起來寬敞了許多。床也重新清理了,林慕華瞟了一眼,心里跳了一下。
西鳳做好了飯菜,在等他。
林慕華伏在桌子上睡了。早上起來的時(shí)候,臉色有些灰。他對(duì)西鳳說,我們?nèi)ベI一張長(zhǎng)椅子。
買合起來是椅子,拆開就是床的那種。西鳳把手鐲褪下來遞給林慕華說。
米廠很快建起來了。地址就在后巷祥福林茶館后面。祥福林茶館里那顆炸彈被拖走了,地面被平整了起來,修了一排低矮的鋪面。林慕華站在鄧福林被壓死的地方,鼻子里有些酸楚。
“后巷這個(gè)地方是寶地。”總管劉麻子說,“其它地方落下的炸彈都炸了,就這地方的炸彈沒有炸。”劉麻子建議把廠址選在后巷,并不是這個(gè)地方風(fēng)水好,而是這里偏僻,不會(huì)引人注意,對(duì)于自己所要從事的事業(yè)是絕佳的地方。不久,縣警備大隊(duì)的監(jiān)獄也在米廠后面建了起來。
除了和警備大隊(duì)的人打得火熱之外,劉麻子還認(rèn)識(shí)一些地方的頭面人物。畢竟是米廠的總管,免不了要混一個(gè)臉熟。在林慕華的眼里,劉麻子大大咧咧,喜歡拿女人說事。這樣的人自然很俗氣,林慕華不想和他走得太近,但為了解決住房的問題,他還是咬牙請(qǐng)劉麻子下了館子。
“屋里有個(gè)女人是好安逸的事情,搬出來做啥?”劉麻子說。
“她不是我的女人,是我的妹妹。”林慕華抿著杯子里的酒說。劉麻子吧嗒著嘴說,祥福林茶館里那個(gè)西鳳是你妹妹?不是老哥我說你,放著屋里的女人你都不消受,簡(jiǎn)直就是浪費(fèi)嘛。
林慕華給劉麻子夾菜,強(qiáng)調(diào)說,真是我妹妹。
劉麻子噴著酒氣說,沒睡一起?操,要是老子早把個(gè)女人干了。林慕華把筷子放下就走。“回來,回來。”劉麻子說,“我不是說著玩兒的嘛,你走了誰結(jié)賬?不就是一間房子嘛。”
林慕華在米廠鋪面里的小閣樓住了下來。每天,西鳳送飯過來。日子過得很平和。
劉麻子似乎很喜歡林慕華,沒事了就踱到鋪面上來,除了看看賬面,便是和林慕華聊天,話題里總是少不了女人,自然提到了陳亞蘭。自從西鳳搬過來那天,林慕華去過廣東會(huì)館一次,就再也沒有見到陳亞蘭了。
陳亞蘭唱得好戲,人又漂亮,可便宜了程丹九這個(gè)老狗。劉麻子說。
會(huì)館里好久都沒有唱戲了。林慕華說。
上一次日本人丟炸彈把人丟怕了,還敢去看戲?劉麻子淡淡地說,陳亞蘭的東西又不是鑲了金子的,誰舍得把命搭在里頭?說不定陳亞蘭已經(jīng)被炸死了呢。
林慕華很想一巴掌打在劉麻子的胖臉上。“最近學(xué)生鬧騰得厲害,你要在意一些,免得那一幫猴崽子把米店掀翻了。”劉麻子慢騰騰地說。
劉麻子說得沒錯(cuò)。中午西鳳送飯來,臉色有些蒼白。“學(xué)生都不在學(xué)堂里念書了,全在街上喊話呢。”西鳳一邊從盒子里拿飯,一邊說,“好些男娃娃不穿衣服,光著個(gè)膀子。那些女學(xué)生也不要臉,跟著后面瞎鬧騰。”
林慕華撲哧一笑。我說錯(cuò)啥了?西鳳一臉疑惑地說。
鋪面的生意冷清。林慕華關(guān)照小伙計(jì)看著鋪面,到大街上去看學(xué)生游行。游行喊話的隊(duì)伍從林慕華身邊走過去,每一張臉都紅彤彤的。街邊上站滿了人,或目光呆滯,或神情興奮。有發(fā)放傳單的女學(xué)生過來,都剪著短發(fā),很精神。人群像進(jìn)了水的油鍋,爭(zhēng)搶著去抓傳單,便有人抓住了女學(xué)生的手不放,鬧哄哄亂成一團(tuán)。林慕華有些陰郁地站在街邊的樹陰里。
陳亞蘭后來說,我看見你了,你就像一棵樹一樣站在那里。
“不做亡國(guó)奴!”一個(gè)學(xué)生揮舞著拳頭高喊。
“打倒日本帝國(guó)主義!”聲音此起彼伏。
“讓日本人滾回他姥姥家去。”一個(gè)人在人群里尖聲尖氣地喊。引得眾人轟然大笑。
林慕華甚覺無聊,在轉(zhuǎn)身要離開的一瞬間,他看見了陳亞蘭。林慕華對(duì)西鳳說,要是那個(gè)時(shí)候沒有看見她,情況就變了。
她會(huì)來找你。西鳳說,連我也沒有想到。
站在木樓窗戶旁的陳亞蘭雙手環(huán)抱,神情有些慵懶。
游行的隊(duì)伍已經(jīng)遠(yuǎn)去,林慕華還呆呆地站在樹下。
她還活著。林慕華想。
洞房的那天晚上,林慕華對(duì)陳亞蘭說,我以為你被日本人的炸彈炸死了,你知不知道,我到會(huì)館找了你。
陳亞蘭沒有說話,她緊緊抱住林慕華。
學(xué)生鬧騰了十多天,便有報(bào)名上前線抗日的,各界紛紛擁護(hù),并倡議義演捐款。街頭上也貼了海報(bào),上面赫然有陳亞蘭的清唱。林慕華收了工便到女子中學(xué)大操場(chǎng)去,早已經(jīng)是人山人海。操場(chǎng)四面拉滿了橫幅,一律白底黑字。林慕華也覺不出扎眼。
夏風(fēng)吹送,氣氛很好。義演的節(jié)目也都很有斗爭(zhēng)氣息,讓人感覺自己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陳亞蘭清唱了一段,贏得滿場(chǎng)喝彩。程丹九上臺(tái)捐了五百個(gè)大洋。林慕華掏了掏包里,只有一張紙幣,有些不好意思,捏了捏便又放回去。他開始埋怨沒有多帶點(diǎn)錢出來。陳亞蘭已經(jīng)飄然下臺(tái)了。
林慕華從人群里擠出來,風(fēng)從斜仄的街巷吹過來,撩動(dòng)掛在屋檐下的橫幅,燈籠里的光搖搖晃晃,投下無數(shù)怪異清冷的影子。林慕華踩著地上的影子,窗戶里有女人輕輕責(zé)罵丈夫的聲音流淌出來。林慕華驀地感到一絲溫暖,西鳳在干什么呢?
如同天上的流云,形勢(shì)變得不可捉摸。日本人投降了。小城里駐扎了部隊(duì)。金圓券也變得不值錢了。劉麻子許久不來鋪面上察看賬目,也不和林慕華聊天了。廣東會(huì)館的陳亞蘭也沒再登臺(tái)了,一個(gè)叫紅妹的戲子火爆了起來。有人說,紅妹是程丹九從李子園挖過來的,是程丹九的女人。這些都無法激起林慕華的興趣,謎一樣的陳亞蘭憑空消失了。雙手環(huán)抱、神情慵懶的陳亞蘭會(huì)時(shí)時(shí)浮現(xiàn)在林慕華的腦海中,這是陳亞蘭留給他最近、也是最鮮活的記憶。
在一天傍晚,劉麻子突然出現(xiàn)在鋪面的賬房里。“今晚上我請(qǐng)你去李子園喝酒。”劉麻子用白色的皮鞋跟磕著地面說,“聽說里面來了幾個(gè)重慶過來的妹子,模樣兒還不錯(cuò)。”
林慕華沒有拒絕。劉麻子說,昨晚上死了幾個(gè)人,聽說是共產(chǎn)黨。現(xiàn)在太亂了,做什么不行非去做什么共產(chǎn)黨呢?
林慕華摸著下巴上的胡須說,我先去刮刮胡子。
還是西鳳每天給你送飯么?在李子園里,劉麻子問。林慕華看著酒杯里漾動(dòng)的紅酒,低沉柔媚的音樂聲里,許多人攬著細(xì)腰在燈光里浮動(dòng)。
我怎么看你越來越像共產(chǎn)黨了。劉麻子說。林慕華不自覺地抖了一下,“我像么?”他說。
“放著屋子里的女人都不用,不是一般人才有的定力。”劉麻子說。林慕華摸著身邊的一個(gè)女人小玉說:“今晚上,你跟我睡,好不好?”林慕華覺得自己就像一個(gè)無恥的嫖客。
劉麻子哈哈大笑,意味深長(zhǎng)地看了看林慕華,說:“男人嘛,就是要及時(shí)行樂。重慶完了,這些女人都跑到我們這邊來了,爺們兒也要好好享受一下這些女人。”劉麻子站起身攬過身邊的妓女走向舞池。
這個(gè)城市里有很多國(guó)民黨和共產(chǎn)黨,我父親是哪一個(gè)黨的?林慕華想起曾經(jīng)問過楊先生的這句話來。父親,鄧福林,楊先生,像走馬燈一樣走過他的眼前,林慕華覺得鼻腔里涌蕩著一股酸澀。
晚上,林慕華沒有回住處。小玉領(lǐng)著他去了后院的閣樓,那里面有溫暖的大床,絲綢被子。劉麻子看著他抱著女人走進(jìn)房間,才放心地坐下來繼續(xù)和妓女調(diào)笑。小玉沒有和林慕華同床,她對(duì)醉眼蒙眬的林慕華說,有一個(gè)人在屋子里等你。
等待林慕華的是陳亞蘭。林慕華的酒馬上就醒了,他心里充滿了驚異,也很警惕地看著眼前的陳亞蘭和那個(gè)叫小玉的女人。“你醉了。”陳亞蘭說,“是西鳳告訴我,你在這里的。”
西鳳曉得我來了這里?林慕華說。
西鳳看著你來的,她真是很關(guān)心你。陳亞蘭說,她一點(diǎn)也不像你的妹妹。林慕華看著她面上的淺笑,確定著是不是對(duì)自己的譏笑。陳亞蘭讓小玉退了出去,坐在林慕華身邊柔聲說,是楊先生讓我來找你的。
楊先生回來了,怎么不親自來見我?
“他不方便來,讓我給你帶一個(gè)話。”陳亞蘭說,“你做得很好。”林慕華只覺得鼻腔里的酸澀再也忍不住了,他低垂著頭,聽見陳亞蘭依然柔聲細(xì)語地說:“老鄧死了后,你對(duì)西鳳很好。楊先生很感謝你。”
“楊先生要我干什么?”林慕華說。
“楊先生要你今后和我聯(lián)系。”陳亞蘭說。
林慕華抬起頭,屏著氣說:“楊先生是共產(chǎn)黨?你是不是共產(chǎn)黨?”
“你喝醉了。”陳亞蘭看著他說,“今天晚上,你就在這里住吧。”她走過來輕輕挽起林慕華,把他拉到床邊。“我要找你的時(shí)候,會(huì)讓人通知你。”陳亞蘭給他蓋上被子說。
燈光在琉璃罩子里流動(dòng),屋子里淌滿溫暖曖昧的空氣。陳亞蘭走了,林慕華感覺渾身的勁兒被人用針管抽走了。
17軍開始對(duì)小城實(shí)行軍管,像其他富商一樣,米廠老板把廠子拋給總管劉麻子,帶著嬌妻大洋跑了。林慕華決定送西鳳去鄉(xiāng)下。西鳳苦著臉。你去和我媽媽住在一起吧,順便幫我照顧她。再說城里也不安全。林慕華說出這句話的時(shí)候,西鳳才勉強(qiáng)答應(yīng)了。
林慕華搬回了原來的住處。一切都像剛開始一樣。陳亞蘭的出現(xiàn)充滿了戲劇性,她像精靈一樣,把無比的美好呈現(xiàn)在林慕華的面前。
林慕華變得更加隨和,不再讓劉麻子請(qǐng)客了,他請(qǐng)劉麻子去李子園喝酒。有時(shí)候,他會(huì)當(dāng)著劉麻子的面把小玉帶回住處。沒有女人的屋子只是一個(gè)空殼,林慕華說。劉麻子表示贊同。
小玉是一個(gè)很漂亮的女人,如果沒有陳亞蘭和西鳳,林慕華發(fā)覺自己最終會(huì)愛上這么一個(gè)女人,和她終老。但這種想法很快就煙消云散了,每一次林慕華想要接觸她的身體時(shí),小玉就會(huì)變得僵硬,渾沒有在李子園那樣投入和溫柔。
陳亞蘭又派人來找了他兩次。一次在米鋪,一次在李子園,之后就再也沒有來人了。林慕華漸漸感到空虛,感到寂寥。他對(duì)小玉說,我想見見她。
小玉說,我都不認(rèn)識(shí)她,怎么知道她在哪里?
林慕華黯然。這個(gè)女人和陳亞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竟然說不認(rèn)識(shí)她。
事情很快有了變化。這天林慕華回到住處的時(shí)候,陳亞蘭正在門口等他。一身素裝的陳亞蘭一點(diǎn)也不起眼,頭上的藍(lán)色頭巾和臃腫的棉衣讓她看起來更像一個(gè)孕婦。“我等你很久了。”陳亞蘭說。
林慕華把她讓進(jìn)房間。陳亞蘭摘掉頭巾,嗅了嗅,說:“西鳳來過?”
“沒有。”林慕華打量著眼前這個(gè)女人,讓他思念、讓他憔悴的女人。“西鳳回鄉(xiāng)下去了。”林慕華說。
陳亞蘭被他的目光刺得很不自在,“你變化很大。”她說。林慕華訕訕地去拿桌上的水缸子。“小玉要走了,她的任務(wù)完成了。”陳亞蘭吐了一口氣,說,小玉來小城很久了,她是我們的同志。
同志這個(gè)詞語讓林慕華感到陌生。他呆呆地坐下來,以前走過李子園的時(shí)候,恍惚看見過那張面孔,要不是劉麻子,他是很難走進(jìn)李子園的,更不用說認(rèn)識(shí)小玉了。林慕華無法接受妓女小玉是他們的同志。“那么,我呢?”林慕華問。
“你是賬房先生啊。”陳亞蘭把身上臃腫的棉衣脫下來,說她今晚上就不回去了。林慕華張了張嘴,還是說:“你還是回去吧,你不怕程丹九,我還怕呢。”
陳亞蘭定定地看著他,說:“他是我爹。”
陳亞蘭要林慕華摸清米廠的情況。解放軍的先頭部隊(duì)很快就要到來,國(guó)軍把持了米廠。要想了解敵人的增減,糧食成了一個(gè)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林慕華聽完后,笑著說,這有點(diǎn)像三國(guó)演義里面諸葛亮增減灶的把戲。
林慕華在地鋪上湊合了一晚,聽著陳亞蘭細(xì)細(xì)的呼吸,感到無比溫馨。“你果真是君子。”早上,陳亞蘭對(duì)他說,“我爹沒有看走眼。”
林慕華問:“你爹說過什么?”
“他曾說你是個(gè)不錯(cuò)的小伙子。”陳亞蘭說。
又路過李子園的時(shí)候,林慕華突然覺得這句話更像小玉說的。李子園門口冷冷清清,枯卷的落葉和紙片在地面隨風(fēng)翻滾。穿著黃皮軍裝的士兵零零散散地走過林慕華的身邊,好像他不存在似的。
小城很快被解放軍拿下來。城里亂成了一鍋粥,四處是奔逃的人。一顆炮彈落在米廠后面的警備監(jiān)獄里,引起了大火,米廠、后巷燒成一片。林慕華拖著沉重的雙腿回到住所。陳亞蘭也來了,她哭著說,我爹被解放軍抓走了。
快去找楊先生啊,他也許能救你爹。林慕華說。
陳亞蘭說,楊先生早就出事了。
“上次你不是說楊先生回來了么?”
陳亞蘭抽泣著說:“上次是我爹讓我來找你的,他說這個(gè)地方你可以信任。”林慕華的心一點(diǎn)點(diǎn)地沉了下去。
程丹九的辯解和中學(xué)教員的指證相比,顯得蒼白無力。林慕華和陳亞蘭找到他的時(shí)候,他身上的血已經(jīng)流干了。“我爹不是國(guó)民黨,也不是黑社會(huì)。”陳亞蘭嘶啞著聲音對(duì)林慕華說。
林慕華帶著陳亞蘭回到住所的時(shí)候街上已經(jīng)放起了鞭炮。街道的鋪面都掛滿了五星紅旗。
五天后,林慕華和陳亞蘭走進(jìn)新建立的縣政府,要求證明程丹九是個(gè)共產(chǎn)黨員。接待他們的是個(gè)三十出頭的科長(zhǎng)。科長(zhǎng)看了看陳亞蘭,有些驚訝:“你不是廣東會(huì)館唱戲的陳亞蘭么?我說同志,你是被黑社會(huì)頭子程丹九強(qiáng)迫的吧。”
陳亞蘭說,他是我爹,他是一個(gè)地下共產(chǎn)黨員。
科長(zhǎng)皺著眉頭說:“我說同志,你不要糊涂了,怎么能認(rèn)賊做爹呢?”
陳亞蘭絕望地看著科長(zhǎng)。科長(zhǎng)揮揮手說:“有誰能夠證明呢?”陳亞蘭說龍公館的張副官。科長(zhǎng)嗤之以鼻,那個(gè)國(guó)民黨的余孽早就跑了。陳亞蘭看了看科長(zhǎng),又看了看林慕華。林慕華扶著她說,我們回家吧。
林慕華沒有去證明自己的身份,他是資本家開辦的米廠的賬房先生,有許多事情無法用嘴巴去證明的。
春天到來的時(shí)候,林慕華帶著憔悴的陳亞蘭回到鄉(xiāng)下成了親。母親對(duì)這件婚事很反對(duì),她已經(jīng)把西鳳當(dāng)做了兒媳婦。
第二年,特務(wù)劉麻子落網(wǎng),便有人指證林慕華和劉麻子關(guān)系密切。指證林慕華的是在李子園舞廳做雜活的小伙計(jì)。林慕華找不出更好的證據(jù)來證明自己就是地下共產(chǎn)黨的線人,他和妻子陳亞蘭被關(guān)進(jìn)了麻風(fēng)病院。西鳳來為他們送了行。
六年過后,麻風(fēng)病院解散,醫(yī)生證明林慕華沒有感染麻風(fēng)病,他被遣送回鄉(xiāng)下老家。西鳳攙扶著已經(jīng)年邁的母親站在村口的池塘邊迎接了他。我一直在等你回來。西鳳說。
2000年,林慕華到后巷去了一次,曾經(jīng)破舊低矮的木樓和鋪面、逼仄的街巷早已經(jīng)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樓大廈,寬闊的水泥馬路。這一年,78歲的林慕華走完了他無法被證明的一生。他對(duì)兒子說,把我的骨灰分成兩份,一份撒在陳亞蘭的墓前,一份撒在你們媽媽的墓前。
責(zé)任編輯: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