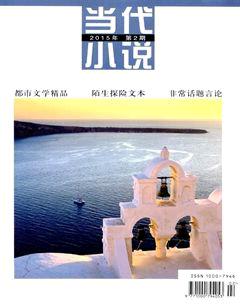你要去哪里
莫飛
她仰著頭注視詹德的側影,但詹德顯然還沒發現她在樓下。他的藍色細條紋襯衣裹著肥胖的身體在纏繞著爬山虎的歐式鐵扶欄間影影綽綽,濃密的黑發上盤旋幾縷灰色的煙。他可能在不停晃動蹺著二郎腿在抽煙,佳瑪想。
他站了起來,一手搭在欄桿上,一手夾著煙,神情像四散的煙飄忽不定。佳瑪看到一輪紅日從他的后腦勺方向順著高樓樓頂的避雷針滑落,詹德的臉頓時變得黯淡,缺乏生機。佳瑪閉了閉眼,掂了一下手里剛買的芹菜,走過狹窄陰暗的樓道。芹菜的葉子撓在她的小腿肚上,她聞到芹菜的類似某種藥物煎制過程中的溢出窗戶的氣味。佳瑪皺了皺眉頭,一些東西都可以慢慢暗示自己接受,譬如她吃不慣芹菜,但可以為詹德做。
她在廚房里做飯。攀爬著爬山虎的露天走廊連接廚房和臥室,走廊里養著一盆蘆薈,一盆茂盛的吊蘭,天晴的時候臥室里的藤椅會做客到走廊,花盆里常會積著詹德的好幾個煙頭。
佳瑪看著滯留在走廊鐵扶欄上的一抹余暉,爬山虎的綠色逐漸變得黯淡。詹德陷在另一端的臥室的藤椅里,盯著電腦屏幕,雙手敲擊著鍵盤的聲音顯示出一點生機,他的腦袋遮擋著屏幕,只露出一角的藍光在閃著。佳瑪擰亮了廚房的燈,走廊和臥室頓時都陷入了黑暗。她擺好了兩菜一湯,站在門口朝黑暗里望去。
這一天是佳瑪一個月中難得休息的一天。整整一天,詹德都坐立不安,從臥室走到廚房,在走廊上徘徊,看天上來來往往的云,時而趁佳瑪不注意的時候盯著她的后背。這一切,佳瑪都知道詹德在下一個決定,那個不可知的決定像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自己一定會在什么時候一腳踩空掉下去。佳瑪知道,自從詹德薄薄的嘴唇說話變得嚴謹和客氣,懶散地躺在寬闊臉上的眉毛在不經意間擰緊,這都向佳瑪在昭示著什么。
“剛才玩什么游戲,這么入迷?”吃晚飯的時候佳瑪問詹德。
“沒有玩游戲,在聊天。”詹德瞧了她一眼,“跟衛星在聊一些事。”
佳瑪跟衛星見過幾面,也知道詹德的這個朋友并不喜歡她。幾次見面都是衛星抱著一箱啤酒來家里,30多歲,長得皺皺巴巴,閃婚了一次,又迅速離了。他喜歡在走廊上把腿架得老高,一邊抽煙,一邊盯著佳瑪在廚房里忙碌。他的眼底總是裝著許多憂慮,從來不去臥室里上衛生間,搖搖晃晃地下樓,找一個角落方便。有次佳瑪下樓正好撞到,他慢慢悠悠地轉過身來,拉上拉鏈。佳瑪由此斷定,這個人不太尊重女性。佳瑪廠里的老板石阡子,見到女工走來,都是側著身讓捂著嘴哧哧發笑的女工先走。她相信衛星一直在幫詹德出主意,如何追求女人,以及如何擺脫同居一年多的她。
“你們天天在一間辦公室,好像總有聊不完的話題。”佳瑪一想到詹德跟衛星,一頭熊跟一只瘦猴在一塊兒咬耳朵,可是她的眼前卻浮現了抱著熊胳膊的女人。
詹德的大腮幫停止了緩慢的咀嚼,又緊緊抿了一下嘴巴,好像要收回分散的嚴謹表情,以期恢復課堂上自信的神情來展開談話。“人結交朋友,很大程度上是交流思想……思想的交流才是重要。”
他在嘲笑我沒有思想。佳瑪這樣想,雖然她知道這樣想不對,她在慪氣,慪氣會有種快感,感官上的享受,現在她想抓住詹德的只言片語大做文章。可是她知道,論夸大細節混淆思想這一點,她肯定是說不過詹德的。她像一只鼓鼓的氣球,被扎了一下,滿懷委屈又無可奈何地慢慢癟掉。
“那么,昨天一個晚上,你都在跟他交流思想?”詹德一晚上都沒有回家,也沒有打來電話。佳瑪這只軟沓沓的氣球好像乘著最后一口氣折騰一下,“是在交流女人的思想?”
詹德撂下了筷子,顯然是生氣了。可他竟然什么也沒說,在重新拿起筷子的一瞬間平息了自己的情緒。這在佳瑪看來,他在醞釀一種更大的情緒。
“昨晚衛星的新交的女朋友請客,在他家喝多了。”他看到佳瑪盯著他的嘴唇,好似期待他說,喝得不醒人事,電話忘記打了,這類帶有愧疚和安慰性質的話。詹德的話在喉嚨里翻滾了幾下,又咽了下去。
“那個女人漂亮嗎?”她不說,衛星的女人漂亮嗎?但佳瑪知道詹德并不會注意到這一點,如果她不說,他將永遠不知道她在無意中窺探到了他的秘密,在這個秘密之后的今天他所說的話對佳瑪來說都是一種謊言,所有的動作都成了虛偽的姿態。
“還不賴。”
佳瑪笑起來,詹德的用詞讓她心領神會。她不再有和詹德談下去的欲望。
晚上,佳瑪在臺燈下趕一批手工活。詹德挨了過來,他把頭蹭到她的頭上,接著又用自己的厚手掌撫摸佳瑪的頭發。
“佳瑪,沒有人比你更勤勞了。”
她停止了飛針走線,聚精會神地聽起來,甚至聽得到詹德小心翼翼的呼吸聲。
“我們廠里的女工個個都很勤勞……也和我一樣,都希望嫁一個好男人。”佳瑪側過臉,定定地注視著詹德。
詹德顯然被她的鎮定的眼睛看得有些心虛,慌忙地把嘴湊了過去,吻了一下佳瑪的眼睛。他曾經說她看人定定的眼神就像一頭牦牛,犯傻勁。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他說,“其實再早些的時候就應該跟你說說了。”
“什么事?”她口氣有些焦躁,“快說吧。”佳瑪好像做好了義無反顧的準備。
“就是關于你想進廠辦公室的事,我倒是可以想想辦法。”
她像繃緊的弦突然松弛下來,感到疲軟。佳瑪放下手中的活,無精打采地說:“都無所謂,只是一個月比待在車間多休息兩天罷了。”
她好像又想到什么警醒起來,這難道是他想踢開我,用來安撫我的辦法。
“你有什么關系可以這樣做?”
“是托衛星的關系,他說他可以幫你。”
她試探地說:“那如果成功的話可要謝謝衛星……可是如果我做不好的話,說不定會被一腳踢出廠里,到時你可得養我了。”
“說什么傻話。”詹德明顯勇氣不足。
佳瑪感到了詹德的退縮。她將整個身體使勁往詹德懷里擠,她明顯感到容納他的懷抱在往后退,她像擠進了一個泡沫之中,那些在陽光下轉動的色彩,瞬間都會消失。
詹德也感覺到了她的執拗,用粗壯的手臂緊緊摟住她,想竭力轉移她的注意力。
他們在沉默中擁抱了很久,直到詹德再也抵擋不住困意,低下了沉重的腦袋。
詹德已經睡著了,臉枕在自己的臂彎里,像一個無知的嬰兒。佳瑪靈巧的手正在給毛衣釘珠。毛衣柔軟的觸感讓她想起曾經養過的兩只羊。她把手摸到羊柔軟溫暖的肚子,接著把臉放到羊腹部。祖父說,羊是她的學費。父親給羊脖子套了圈,拉到鎮上,羊叫著。她啼哭著,看羊被拉進了賭館。那個時候她恨透了父親,站在賭館門前咬牙切齒地等到半夜,拉著輸得精光的父親要錢上學。紅了眼的父親一腳把她踹到了泥溝里。她舉著滿是淤泥的雙手像個木偶般躺在溝里,初春的月亮看著她。
詹德說得對。她有時就像一個犯了傻勁的牦牛,許多人告訴她,到了她這個年紀還去上什么學?何況她的基礎那么差,能學到什么東西?她偏偏對學校充滿了熱愛,在成年有能力的時候去實現童年的夢想,這樣有沒有意義,佳瑪沒有考慮。她只想著父親把她的羊牽走時,她絕望無助的心情,如今她用自己的能賺錢的能力去撫平這種無以平復的心情或者情緒。
她的眼睛發痛,可還是不想放下手里的針線。她有時不明白自己這樣毫不懈怠地工作最后會換得什么。她想起兩年前見到如今瘦得像竹竿上披了件舊外褂一樣的祖父母,還在常年累月伺弄著跟他們同樣貧瘠的山地。他們除了種地,已經沒有了生活。可是她還年輕啊,要一個男人還有一個吵吵鬧鬧的孩子。
佳瑪被自己的想法搞得很傷感,一不小心就扎破了手。她趕緊將手指伸進嘴巴。她倒不是怕流血。鮮血沾到毛衣上,她干零活賺的錢都得賠給東家。她懷著氣惱和絕望看了一眼詹德,他露著一張無辜的側臉,沉沉地陷在自己的深度睡眠里。佳瑪覺得從一開始被這張看似善良敦厚的臉而心甘情愿地騙了,其實這張寬闊的臉后隱藏著冷酷尖利的東西。
手指在黑暗里隱隱發痛,佳瑪沒有一點想睡的欲望。她聽到了鬧鐘的嘀嗒聲,越來越急迫地在她耳邊響起,幾乎是刺著她的耳膜進行的。她想著種種可能發生的災難,先想到他要遺棄她,找了一個說話柔和、披著一肩長發的身材嬌小的年輕女人。她想到了死,自己漂浮在河里,他站在河邊護欄上看,就像家里的走廊里,每每當他站著凝望,她想著他在看她,可是每一次,他看向的只是屋宇之上的蒼穹。這讓她泄氣、無助,一想到他把她當成對愛和恨完全無動于衷的人,讓她覺得想發瘋,想抓起枕頭捂住他的腦袋,可最終佳瑪在疲憊的思想行進中睡著了。
第二天佳瑪起得很晚,她只能去上班途中買兩個包子當早飯。詹德還在床上,他比她晚一個小時上班,即使去上班了,沒課的時候也是在辦公室里上網或者跟衛星聊天。
“我快來不及了,沒做早飯,你一會兒自己買點吃的。”佳瑪一邊穿鞋一邊對剛睜開眼的詹德說。
“你快來不及了嗎?打個的去好了,別擠公交了,現在上班高峰。”詹德好像想起了什么,眼睛一下子從蒙昧狀態蘇醒過來,“那我等你回來,我有件事跟你說。”
佳瑪看著床下的紫色的高跟皮鞋,她有些瑟縮,這雙新鞋擠腳的隱痛在提醒她,她并不適合。她幾乎想哭了,“我今天可能要加班到很晚。”
“沒關系,我會等你的。”
佳瑪覺得詹德的話像一個輕飄飄的幽靈一樣跟著她穿過廚房,走到狹窄樓道,拼命地擠壓她,又尾隨她走到路上,像風一樣從左耳竄到右耳,直到走到人群熙攘的公交車站臺,這個幽靈好像才被更多的聲音從她的耳邊趕走。
公交車帶走了佳瑪。
佳瑪暫時忘記了幽靈的事,車子里正在播報新聞。西部的哪個省的哪個市發生了兩幫人的火拼,造成了十多個人傷亡;山西的一個煤礦發生了瓦斯爆炸,去山區旅游的一輛大巴墜入了懸崖。一早上,車子里的人聽著新聞吃著包子咬著油條,喝豆漿的人得時刻注意著前方的玻璃,會精準地判斷司機的下一個剎車在什么時候。乘客臉上安然自若的神情加重了佳瑪的不安,她環顧了車內的氣氛,她不用掏出手機看時間,就知道已經遲到了。她并不害怕遲到,是打卡器上發出“咔”的一聲讓她心里哆嗦,門衛保安慵懶和嘲笑的目光讓她覺得渾身長滿了刺。遲到早退會扣除一個月的全勤獎。佳瑪工作的廠是個日資企業,要求縫紉工的針腳就像要求上班時間一樣,不能差一分一秒。
上一次遲到是什么時候?佳瑪心情灰敗十分不愉快地回想。她不愿意這些回憶重新來到眼前,可是就像撥準的鬧鐘,到點就全然不顧主人慵懶的情緒,哇啦哇啦地叫開了。那時候才認識詹德兩三周,他把她留宿在現在的那套有點奇特的居室里。可她喜歡啊,愛啊,全然都掩飾不住的興奮。完全獨立的屬于詹德和她的小天地,一端通往臥室一端是廚房,她在這兩端跑來跑去,感覺就像在云與云之間的穿梭。第二天,她被自己設定的鬧鐘驚醒,這是她住在廠區宿舍設定的時間,完全脫離了她住在詹德家的空間概念。她心里很急,可又有些害羞的樣子慢慢地穿自己的衣服。詹德伸出粗壯的胳膊摟過她。她望著寬大的臉龐,門衛上的打卡器,同宿舍姐妹的嘲笑,逐漸在她的意識里淡去。她也在消融,在詹德的身邊。她遲到了一個小時,門衛上曾向她獻過殷勤的保安,一雙遮在帽檐陰影下的眼睛像是要洞穿她還在胸口揣得熱乎乎的秘密;收發報紙郵件老頭抽著鼻子,像要從她的身上嗅出一絲放蕩女人一夜未歸的邪惡氣味來。她慌慌張張地打完卡,像一只逃出獵人眼睛的兔子,可心里還不免得意,詹德早上答應過她,以后她上夜班,他會來接她。她一想到詹德高大的身影出現在這廠區門口時,不自禁地哼起不著調的歌。連進車間時,女工人盯著她的目光好像都被這種快樂給屏蔽了。
她在廠區兩個種滿薔薇的花壇擠出的一條鵝卵石的小道上急匆匆地走著。
“佳瑪,你遲到了。”駐廠的日本經理石阡子離開十多米的地方讓開了道。他的中文很流利,但怎么聽都像嘴里含著塊生硬的石頭。
“對不起,石阡先生。”佳瑪面帶愧色地從石阡子身旁走過,但還是禮節性地向石阡子微微低了下頭。
她的車間里充滿了嚴謹和友好的氣氛,但無論哪個人遲到了,推開那扇沉重的玻璃門,所有的女工都會從布料堆里抬起粉紅的臉來,帶著激動人心的神情,瞧著別人身上的被幾分鐘時間折磨著的神經在臉上出現的惶恐與不安。前面說的車間的嚴謹和友好的氣氛一般出現在石阡子進來的時候,他常點頭哈腰巡視車間,女工們總會向他還禮、巧笑和低頭,悄悄議論這個男人的年齡,35或者37,也可能超40歲了。可是石阡子堆笑的臉和挺拔的個子,一絲不茍的頭發總讓女工們推翻自己的說法。她們在中飯的時候就會把頭布摘下,頭發散在肩上,摘下千篇一律的廠里邊角料裁成的袖套,露出自己本色的衣服,她們熱烈地期望平易近人、說話像嗑著石子一樣的石阡子與她們坐在一起,還稱他的聲音“妙極了。”有時年輕一點的女工間會為了誰在勾引石阡子而爭論得面紅耳赤,但只要石阡子一來,車間里又恢復了嚴謹和友好的氣氛,只聽得到電動縫紉機發出流利的咀嚼聲。
佳瑪趁著上廁所的時候去了一趟換衣間,查看手機,沒有任何電話和消息。詹德以前都會給她發一條信息,以便她在午飯休息時間時看到。短信的開頭,總是以各種讓佳瑪起初會臉紅心跳的昵稱開始的,寶貝、我的親親、我的小馬兒。這樣的問候短信,什么時候消失的,佳瑪想不起來了。
佳瑪縫紉機的位置前有扇不大的窗戶,被修剪成球狀的紅葉石楠遮住了大部分的空間,隔著鐵柵欄的行人和車輛便在枝葉中一閃而過,像一個微型的世界,一切來往有序,好像各人都有各人的步伐和夢想。她踩著縫紉機,像小心翼翼踩著的跳板。她想到,他睡覺的時候,她在干零活賺錢。他上班的時候,她在踩縫紉機,他從學校回家的時候,她還在踩縫紉機。他周末出去玩的時候,她還得踩縫紉機。一個月里,她只有兩天可以休息。他有大把的時間出去跟別的女人搭訕約會,她連上個廁所都得看準時間。
她幾乎氣餒地想快些結束這樣的關系。分手,不過是分手。離了他,我就不能活嗎?
佳瑪無數次地想到她和詹德的關系,以及今天晚上他將會向她提出分手的事。
詹德是成校的一名計算機老師,一周只有兩三天有課。佳瑪當初懷著美好的愿望,將幾個月的工資交到了學校。她想感受一下坐在教室板凳上的感覺,以區別于多年坐在縫紉機板凳上的感覺。那種新鮮感和滿足感還沒有持續到一個月,詹德就挨近了她的身體。
她不知道詹德喜歡她什么。詹德說喜歡她的不聰明,太聰明的女人不好玩。
佳瑪想起她曾經同居過的兩個男人。一個是在火車上認識的,做倒賣服裝生意的,樣貌都像他倒賣的服裝一樣沒有特色。他坐在她的對坐,跟她天南海北地聊,惹得她發笑,逗她勉勉強強一字一句咬著音說著濃重鄉音的普通話。在他要下車的時候,他看到她手里緊緊捏著包,問她:你要去哪里呢?她茫然地看了一眼窗外,又迅速抓起手里的包,跟著男人下了火車。他送她去上了縫紉班,半年多后她能完整地從裁剪到制作一個人完成。他帶著她去地鐵站、地下通道、天橋下賣衣服,沒有攤位,衣服搭在胳膊上,跟著多看幾眼的行人搭訕,將衣服硬塞給他們。他覺得她不夠聰明,好幾次都被客人將衣服扔到了地上,好幾次被城管追得把手里的衣服全丟了。他們同居了一年多,她克服了剛從內陸出來濃重鄉音的自卑感后便和他分了手。
第二個男人是在一家小餐館認識的,戴著油膩的廚師帽,說著一口川普,炒得一手好川菜。可她常常因為他身上的油膩味而心生嫌隙,她知道她不愛他的。她其實不知道什么才是愛,像和廠里的大多數女工聊天一樣,只說喜歡一個人,卻很少有人說愛一個人。愛也許對她們來說太重大了,或許愛就意味著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可是幾乎沒有人不想擁有愛情,她們的愛情就像用錫紙小心地緊緊地和自己可憐的自尊心包裹在一起。
她和廚師不到一個月就分開了。男的總是嫌她太聰明,有著城里的人的嬌貴和潔癖,不活絡,在到處要錢的城市里他沒有辦法和她同甘共苦。
車間的工友來喊佳瑪,通知去廠辦公室一趟。
佳瑪好大一會兒失神,看了看停止的縫紉機,又環顧了周圍忙碌的景象。她真的能離開這個環境,她搖了搖頭走出了車間。她曾經掙扎過,對生活的要求也少得可憐,可是未來真能脫不開這縫紉機?她在認識詹德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停止了思考,工作疲乏得讓她都無法懷念她所失去的東西,和正在失去的東西。
可現在她知道,她正在失去他。像一個沙漏一樣,緩慢地,由她的這一端流向另一端。她清晰得幾近痛苦,卻毫無辦法去挽回這一切。在休息日的前一天,佳瑪跟采辦員坐公交車去采買一批女員工的鞋,她就在市中心緩慢移動的車玻璃前看到詹德的,一個嬌小的女人踩著尖細的高跟鞋,身體不穩當地掛在他的胳膊上。
那天,她買了一雙平時不舍得買的皮鞋,新鞋夾得她腳痛。
如今,是不是連工作也一并失去。她突然想到今天早上自己無故遲到的事。前陣子不一直聽說,廠里效益不怎么好,訂單偏少,那就意味著員工可以少一些。
佳瑪驚得背上一身汗。辦公室里負責女工出勤和心理健康咨詢的一個矮墩墩的女人,坐在窗口的辦公桌上,用粗短的手指捧著一杯綠茶,她的嘴唇很厚,涂了很鮮艷的口紅。
佳瑪看了一眼女人的嘴唇,又看了一眼杯子,接著把目光移到了窗外。天陰沉沉地,辦公室的留著滲水痕跡的墻壁像是響應梅雨季節的潮濕,此刻正散發出一股霉味裹挾住了她。佳瑪在心底沉重地呼吸,帶著聽噩耗般的心情,等待鮮紅的嘴唇慢慢喝完茶。
“佳瑪,你們出來打工都不容易,特別像你還去過日本勞務派遣,知道一些工廠的紀律……你可不是第一次遲到了。”紅嘴唇把杯子鄭重地放到玻璃臺面上,加重了口吻,“你去寫一份檢討出來,到時掛在食堂前面的黑板報上。”
佳瑪大舒一口氣,她幾乎歡天喜地感恩戴德地向紅嘴唇鞠了一躬,“我會寫好檢討,下次再也不遲到了。”
佳瑪出辦公室門的時候撞到了石阡子。
她在這個工廠工作的幾年,石阡子總是對她投來關注的目光,就像詹德在黑鴉鴉的課堂上像發現了一顆星星一樣,激動得讓自己的眼睛閃閃發亮。
佳瑪從來不掩飾自己的美麗,可是幾個同車間的大姐告訴她,千萬不要相信男人看中的美麗,那只是年輕,像花一樣,折了就萎了。
佳瑪偶爾懷念起自己溪水潺潺放牛牧羊的童年。那是在山脈和河流切斷的內陸度過的。祖父母還在那里,他們的眼睛越來越接近塵土的顏色。父母打年輕時遷居小鎮,堵了一個橋洞當家,在里面生了五個子女,像撒魚苗一樣將他們撒了出去,之后游于大海,陷進沼澤,或者固守日漸干涸的一潭死水全看孩子們的造化。佳瑪是最小的孩子,祖父母領著長大,沒讀過幾年書,一到了16歲,她就離開了他們。從內陸漂流到沿海城市,漸漸克服了自己口音和自卑心理。
可在一口流利普通話的詹德面前,她還是有強烈的自卑的。他像太陽,而她是露珠,一眨眼,就會被蒸發得無形。可詹德大多數時候是寬厚的,總是以一種憐憫的眼神聽她講到女工們十多人住在宿舍的狀況。那種環境,她現在想起來也會覺得不舒服,所有的床鋪上系著繩子,晾滿了內衣內褲,一年四季潮濕著。有不喜歡晚上去上廁所的,就擺了幾個痰盂,宿舍里永遠都充斥著尿臊味和用電磁爐煮泡面的味道。
佳瑪站在整齊的廠區,她往外墻剝落得像一個皮膚得了白癜風患者的宿舍樓望去,覺得心在打顫。
電鈴的聲音劃破了寧靜的廠區,女工人像兩股潮水,一股涌向了宿舍樓,一股涌向了門口。天下起了雨,并不妨礙她們因為不加班而興高采烈的樣子,五顏六色的傘簇擁著像一條迅速涌動的河流,她們將奔向溫暖的家里,孩子們會為母親的提早歸來而高興,張開手臂要求抱抱。她們會擼起袖子,炒幾個小菜,和愛人喝幾杯黃酒,直到她們臉變成紅彤彤的,愛人的眼變得熾熱而深情。她們,在家里是扮演多么重要的一個角色?
佳瑪看著彩色的河流奔向了各自的家,她站在空空蕩蕩的廠區。一把黑傘移動過來,是石阡子。
“佳瑪有心事,來我辦公室坐坐?”石阡子從傘底歪著腦袋,以探詢的目光看著滿腹心事的佳瑪。
佳瑪接過石阡子泡的綠茶,盯著墻壁上的一幅畫。畫上櫻花盛開,一名穿和服的女子的背影站在成片的爛漫之下。
她感到,他在旁邊觀察她。
“佳瑪覺得這畫美嗎?”石阡子看著佳瑪沉浸到畫里的臉。
“美……其實我從來沒有看過櫻花。”佳瑪知道在這個城市里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櫻花園,春風一拂,花飛如雪。這是詹德跟她描述過的,可是他從來沒有帶她去看過。當然,佳瑪也從沒要求過什么,她的眼里,堆滿了小山一樣高的手工活。
“有機會,我可以帶你去看,櫻花盛開。”石阡子說。
佳瑪吃驚地從畫上轉到石阡子的臉上,懷疑這是自己看畫的錯覺。
她尷尬地笑笑,把手中的杯子放到茶幾上,手竟然有些顫抖。
石阡子也跟著佳瑪笑了。她不知道他為什么笑。
“你跟車間里的女工都相處得好嗎?”
“很好,”佳瑪說,“她們平常可愛議論你。”
“議論我什么?”
“有沒有結婚的問題。”
“你說呢?”石阡子又微微笑地問佳瑪。
“這個,我怎么可能知道。”佳瑪朝窗外看了一下,雨下得很大。
“其實,我很眷戀我的家鄉,背井離鄉出來總是不容易……你看,在你們中國漢字里,家的筆畫,那是個屋頂,下面是一家人,無論走多遠,總是牽著一根中軸線。”
石阡子用手指蘸著茶水在玻璃茶幾上緩慢地寫了一個“家”字,他炯炯有神的眼睛里帶著思鄉的一縷哀愁。
佳瑪咬著嘴唇看了一眼字,又把目光移到別處。窗外的雨正拍打著幾棵顫抖著的瘦竹,劈劈啪啪的聲音。
她感到有點怕他,是除開身體危險的懼怕,而是他本身所具有的親和力喚起了她身上的某部分的響應。這些東西在長年累月的機器前,過手的無數布料里,一次次無疾而終的戀愛中,她似乎一直把這種東西隱藏在內心深處。如今,她感到一種溫暖,思鄉的溫暖,家鄉那條溪流發出的聲音在召喚,或者祖父坐在門檻前用煙管吐出的濃烈的煙味,此刻都縈繞她眼前,讓她鼻子發酸。
她控制自己不讓眼淚在石阡子面前流出來。佳瑪不太明白,心底的像云團般愁緒是被一個異國人所牽引出來的。現在,他使她感到安全,雖然他曾經因多出幾分對她的友好而讓她深感不安。其實,很多時候,她都習慣于不友好的人。但她并沒有覺得她要跟石阡子做朋友,就像跟衛星一樣,表示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可她知道和他永遠做不了朋友,更不可能跟他去日本看櫻花。
“日本離我太遠了。”佳瑪知道自己的眼睛里一定含著淚,像窗外被打濕的竹子,晶亮晶亮的。
“我明白,明白……”石阡子注意到她情緒上的變化,輕輕地拍了一下她的后背。“現在雨太大了,等雨停了,你再走。”
佳瑪一無反顧地沖到雨幕中。
她一路奔跑著出了廠區。四周雨聲打在綠化帶里發出很大的響聲,皮鞋在路面薄薄的一層積水里發出啪啪的聲音,鞋里蓄滿了水,濕透的衣服緊緊包裹著身體,眼睛里也積了水,她被水包圍著。她拿起了公用電話亭的電話,想告訴詹德:她是愛他的,從他走上課堂的一刻。可是她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都沒有硬幣。
電話里發著嘟嘟的忙音。佳瑪重又走回雨里。她想起十六歲那年,瘦弱的她背著簡單的行囊走出老家低矮的門框時,祖父在她的身后問她:“佳瑪,你要去哪里呢?”
她扭著脖子回答祖父:“我不知道。”
責任編輯: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