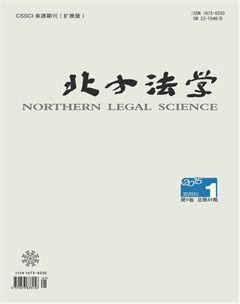中國農村治理變遷與獲致司法正義
程騫+徐亞文
摘要:在治理結構的變遷中農村獲致司法正義遭遇了困境。這包括司法服務能力虛浮、政權“內卷化”和存在治理真空、農村法律精英缺失,以及現代法律制度擠壓傳統治理規則等。從法律賦能的角度理解,農村獲致司法正義實現的重要障礙在于農民法律權能的流失。因此實現農村的獲致司法正義,不能僅靠法律制度和法律設施的建設,更需要對農民進行法律賦能。尊重非正式制度、發展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培養農村社區法工等都是可行舉措。
關鍵詞:農村治理司法正義法律賦能法治
中圖分類號:DF0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330(2015)01-0132-09
獲致司法正義(access to justice),又被譯為“獲得司法正義”、“接近司法正義”、“接近正義”,在國際學術界和實務界中尚無一個通行的、明確的界定。狹義上,這一概念一般被用來指代人們獲得法律服務和訴諸司法救濟制度的狀態。①廣義上,它涵蓋公正、明晰、全納的法律制度,獨立、中立、有效的司法系統,可及、可靠、可負擔的法律服務,普遍、公開、易理解法律信息等內容。獲致司法正義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獲致”的過程與可能;二是“司法正義”的結果與現實。“獲致”強調尋求權利救濟和糾紛解決的渠道與資源,比如可以方便地向法院提起訴訟、可以獲得便宜的法律服務等;“司法正義”強調權利救濟和糾紛解決機制的程序和實體正義,比如法庭審理過程不偏倚、調解結果符合法律規定、公序良俗等。獲致司法正義的提出是為了“解決貧困和邊緣化的人們以及弱勢群體在面對法律和權力時所經常遇到的困難和障礙”、“將社會的邊緣人變為社會中的平等伙伴”,②因此,其對于實現社會成員的平等人權、使社會成員普遍享受法治的蔭庇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中國從晚清開始開啟了法治化、現代化的進程,傳統的中國農村在這一巨變的大環境中也受到巨大的沖擊。在中國農村發生的種種變化中,最為重要的便是治理模式的改變。獲致司法正義不僅是法律問題,也是政治問題。③獲致司法正義的實現不僅需要考量法律制度、法律設施的情況,也要考慮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社會環境的情況。因此,要了解近代中國農村獲致司法正義的問題,不能不結合近代中國農村治理的變遷進行思考。
一、 近代中國農村治理的變遷及其產生的問題
自清末新政④始,中國的農村治理邁入了現代化轉型的軌道。1902年,山西巡撫趙爾巽奏議重整保甲制度。1905年,清政府下令厘定縣級以下行政官制。1909年,清政府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城鎮鄉地方自治選舉章程》,規定府廳州縣治城廂地方為城,其他人口滿五萬以上者為鎮、人口不滿五萬者為鄉,各城鎮設“議事會”和“董事會”,各鄉設“議事會”和“鄉董”,由當地居民投票選舉紳民充任,以為自治機關,辦理地方公益事宜,輔佐官治;其自治事項包括當地學務、衛生、道路工程、工農商務、善舉(慈善)、公營事業及自治所需籌款事宜等。⑤
民國時期的農村治理模式繼續發生變革。1914年、1917年、1921年北洋政府分別頒布《地方自治試行條例》、《地方自治令》、《縣自治法施行細則》和《鄉自治制》,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各省設立縣政建設實驗區辦法》,自上而下地推動鄉村治理改革。1914年河北定縣知縣孫發緒、鄉民米迪剛開啟定縣翟城村的自治改革,設立自治公所,選舉村長、村佐。⑥1926年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定縣進一步開展一系列調研和鄉村建設活動,后來其更與國民政府的鄉村復興運動融合而成為縣政建設實驗區。1931年梁漱溟以山東鄉村研究院為大本營在山東鄒平、菏澤進行實驗,兩年后兩縣由山東省政府定為縣政建設實驗區。1933年在南京國民政府的派遣之下,梅思平和胡次威分別在江蘇江寧縣和浙江蘭溪縣建立縣政建設實驗區。上述五縣成為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所主導的鄉村治理改革實踐中最杰出的代表。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政府在農村治理中的參與達到了空前深入的程度。1954年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憲法》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確認了縣鄉政權架構,規定了鄉、民族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委員會的職能,“新政權更加穩固地延伸到鄉村內部”。⑧195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提倡農民“組織起來”,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開展“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集體勞動”。⑨互助組在中國農村廣泛發展。1952年開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逐漸發展,1955年達到高潮。同年,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也迅速開始流行。1958年中共中央通過《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并大社、轉公社”的風潮席卷全國,人民公社成為農村主要生產組織和基層政權。至此,國家對農村治理的掌控達到了中國歷史的頂峰。
1978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2年《憲法》規定農村建立鄉、民族鄉政府和群眾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至1985年人民公社基本從中國農村消失,農村基層政權和經濟合作組織不再重合。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工作的通知》,推進黨政分工、簡政放權、加強村民委員會建設。⑩其后全國開始“撤區并鄉”、“并鄉建鎮”,農村基層政權組織上形成由縣、鄉鎮組成的兩級格局和“鄉政村治”的村民自治。
中國農村治理歷經一百余年變遷,構成了中國農村法治建設的政治、社會環境。其為中國農村的獲致司法正義提供了契機,然而亦產生了諸多限制獲致司法正義實現的障礙與困境。認清這些困境及其根源是思考進一步促進農村獲致司法正義之路徑的起點。
(一) 國家司法組織下沉,但司法服務能力虛浮
在古代中國,由于統治技術和統治資源的限制,國家無法對每一個村莊進行直接統治。“官不下縣”成為傳統中國國家權力在基層的重要特征。在農村,宗族、行會、長者及鄉紳通過對村民進行道德灌輸、糾紛調解以及某些強制性懲罰化解大量社會矛盾。族長、鄉紳與地方名流掌握了處理農村糾紛、扮演地方權威的權力。 這一鄉村自治的實踐以及地方的民間權威也得到官方的認同,比如明代《惠安政書》記載:“于里中,選高年有德、眾所推服者充者老,或三人,或五人,或十人,居申明辛,與里甲聽一里之訟,不但果決足非,而以勸民為善。”《教民榜文》也規定:“民間婚姻、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本里老人里甲決斷。”
然而,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行,自晚清以降國家政權向鄉村一步步深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更是使國家力量伸向農村家庭,形成“原子化的個人直接面對國家的格局”。隨著國家權力的向下延伸,國家司法組織也向農村基層滲入,派出所、司法所、基層人民法院(尤其是派出法庭)等機關涉入大量農村糾紛的處理。然而,在國家司法組織下沉的同時,其司法服務能力卻仍然有限。主要原因包括:
1.農村仍難以提供現代司法制度運行所需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首先,現代法律制度和程序精密、復雜,需要國家投入大量的資源培養具備相應知識和能力的司法工作人員充實基層司法機關,并且為他們的持續任職提供充足的薪俸、福利和職業發展的機會;其次,基層司法機關的辦公場所、辦公設備及其日常運營亦需要大量財政經費的支持;再次,農村居民便捷前往基層司法機關和法律服務機構,與之溝通、交涉的交通、通訊等物質條件亦需要相應的基礎建設。然而,中國農村大多仍處于欠發達狀態,農村經濟仍未能全面實現現代化,難以支撐現代化的基層司法制度。
2.基層法律工作人員的數量和質量仍有欠缺。一方面,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糾紛頻發,而基層法官、律師,包括法律工作者的數量卻有限,提供法律服務的人員短缺;另一方面,隨著農村經濟、社會條件的改變,農村糾紛類型亦呈現新的特點,而囿于工作環境、職業發展、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基層法律服務崗位卻難以吸引高素質的法律人,基層法律工作人員又難以獲得充分的職業培訓,因此,基層法律工作人員的素質普遍存在缺陷。
3.基層法律運行受到“地方性知識”問題的挑戰。朱蘇力發現在“送法下鄉”的過程中,“地方性知識”支撐了法律在農村的運轉,而這一知識卻為村干部所壟斷,因此,村干部幾乎扮演了傳統中國士紳在農村—國家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限制了現代司法制度在農村的運行。
(二) 國家權力擴張導致“內卷化”,國家權力回縮又產生治理真空
隨著國家權力末梢向農村的擴張,還出現了“內卷化”的問題,即國家政權機構雖在規模上擴張,但效益卻未相應提高,國家政權控制力增強的成本高昂。比如多種處理農村問題的現代化司法、行政部門紛紛建立,使有限的財政資源更加緊張,機構效率低下,卻又可能增加農民負擔。根據葉本乾的研究,2002年河南弦鄉進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和教育活動”中,有單位批評派出所辦理身份證收費過高、罰款不出示依據、隨意向農民收取費用、工作人員服務態度生硬、處理問題不及時、存在吃拿卡要的情況,弦鄉農民亦通過各種途徑反映和抵制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等行為。又如,在湖北、四川等省的實踐中,也出現貧困鄉鎮的司法所所長從事法律服務所的有償法律服務工作的情況。因此,雖然在形式上現代化的司法機構得以覆蓋農村,為農村提供現代化的法律或公民服務,但農民為了維系這些正式機構的運轉卻又承受了相當的負擔,這些服務對農民私人和公共生活的改善和農民所付出的成本是否成正比也需要認真考量。
人民公社時期國家對農村的管控達到歷史的頂峰,然而,這種高度的統治卻難以持久。因為不僅國家需要動用大量的資源來維持這種治理模式,而且它還犧牲了農業生產的整體效率。農民在私人生活中也仍堅持服從傳統的風俗習慣和原來的行為邏輯,而對驟然侵入他們生活的正式的新式規則有所抵觸。1978年之后,人民公社開始解體,原來國家伸入農村的權力末梢迅速回縮。隨著國家權力的回縮,農村社會出現治理真空。比如村民委員會這種“群眾性自治組織”就是最早由廣西宜山、羅山兩縣農民為了解決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而自發組建的。既有的國家權威撤出,新的權威尚未樹立,導致農村缺乏解決糾紛的公正、高效、廣為村民信服的權威。
(三) 鄉村精英結構流變,農民缺少公正、有力的利益保護人
在傳統中國,鄉紳、名流構成農村精英的主體。這些鄉紳、名流在農村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首先,他們為大量的農村糾紛提供調解,部分人還在糾紛進入國家司法程序時到堂作證。其次,當吏役敲詐鄉村、村民與外地尤其是城鎮居民發生沖突時,他們從中斡旋,保護鄉民。此外,他們還構成一條“自下而上的無形軌道”,“從一切社會關系:親戚、同鄉、同年等,把壓力透到上層,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從而向國家政權傳遞鄉民的需要。然而從晚清開始直至民國,隨著城市的迅速發展與農村的破敗,包括戰亂、國家與軍閥對鄉村的勒索等原因,鄉村精英或移居城市,或由富變窮。“打倒土豪劣紳”的政治活動更是對鄉紳的政治影響力有著直接的消解作用。隨著“保護型”鄉村精英的離開,追求私利的人掌握了鄉村政權與公職。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喪失了其熟悉、信賴的利益保護人。
人民公社時期,國家深入農村政治生活,原來作為村民與國家之前橋梁的鄉村精英的活動空間消失殆盡。而在人民公社解體以后,在農村治理真空填補和鄉村權威重建的過程中,力量型權威卻又占據了重要地位。村干部依靠其行政職位所享有的行政權力對鄉民進行管理,富裕村民依靠其財力及其背后所體現的個人能力獲得鄉民的崇拜與信服,鄉痞惡霸使用暴力對鄉民進行壓制與恐嚇,共同構成一種“力治”的格局。這種個體本位的“力治”強化了農村社會的離散性,但獲致司法正義的實現卻需要現代化的社會土壤,需要法律制度良好運行、法律規范普遍遵行、法律權威普遍信仰的“法治”,因此,它阻礙了農村獲致司法正義實現的土壤的形成。
另一方面,隨著現代法制對農村事務的管轄,農民需要熟悉現代法律知識、具備相應專業資質的鄉村精英來保護他們的利益,比如基層法律工作者。而這些基層法律工作者也往往集中在縣城鄉鎮,不像傳統鄉村精英那樣可以被村民輕易接近。即使農民能夠向基層法律工作者求助,囿于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法律知識、法律技能的缺陷,也難以在司法程序中最大限度地爭取利益。
(四) 陌生的現代法律制度擠壓傳統治理規則,但難為農民所接受
現代法律作為舶來品在移植至中國的過程中,面臨著與中國本土社會環境和既有社會規則對接、融合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相當的時間與努力,而在廣大農村尤其是艱巨的任務。雖然現代法制已經全面深入到農民生活之中,并且擠壓了傳統的非正式的治理規則的生存空間。農民在解決糾紛、主張權利、爭取利益、尋求正義之時很難繞過法律,但是現代法律制度對于多數農民來說仍然是一個陌生的事物。它在諸多方面與農民長期所信仰、所習慣的治理規則大相徑庭,比如:(1)在治理理念上,傳統中國農村盛行德治,強調息訟寧人,到了近代,在仍是熟人社會的農村中很多人仍然保持這一傳統理念,仍有人認為打官司是一件不好或不光彩的事情。(2)在價值上,農村社會有一些傳統價值,比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樸素的正義觀念,比如“親親相為隱”的親族價值等或不為現代法律制度所承認、接受,或為現代法律制度所轉化、重整;而另一方面現代法律制度中的一些價值,如“程序正義”、“性別平等”等又為農民所難以理解,甚至難以接受。這種價值上的沖突可能導致人們對法律的困惑與失望,因為如果農民尊重的價值得不到法律的尊重就可能使其需要無法通過法律得到滿足,如果農民無法理解法律的價值就可能對法律的權威產生懷疑甚至抵觸。(3)在程序上,傳統農村習慣通過熟人或有名望者以非正式的調解、說和解決糾紛,而在現代法律制度中,不同的司法部門、不同的糾紛類型所涉及的司法程序各有不同,各種審級、期限的規定對于農民來說錯綜復雜,既感陌生,又難理解。(4)在規則上,農民習慣以倫理道德、宗族家訓、鄉規民約等作為“論理”的依據和判斷是非的標準,而在現代法律制度中人們所遵行的規則是法律規范。農民對法律規范具體內容和精神、原則了解和把握的程度難以與其對傳統規范了解的程度相提并論。(5)在話語上,法律獨特的話語系統法律名詞對于農民來說晦澀難懂,離開專業法律人員的幫助,農民不僅可能對法律的理解出現偏差,在正式司法程序中也難以用法律話語表達自己的主張和意見。當糾紛進入正式司法程序,農民往往失去控制力而感到無助與迷茫。實證研究也表明了農民對現代法律制度的不信任或不滿意。在一項關于農民對糾紛解決機制態度的調查研究中,農民調查對象表示感到最滿意的是社會網絡,其次是政府部門,最不滿意的則是司法部門。
二、 法律賦能:促進農村獲致司法正義的新思路
(一) 從“法律與發展”到“法律賦能”
“法律與發展”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風靡拉美、亞洲等地的一次法律改革運動。這一運動的理論假設是獨立的司法制度、健全的公民權利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法律可以用來增進平等、擴大參與,限制政府專斷行為、保護公民個人自由。由于其被認為對促進發展具有實效,諸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這一理論的啟發下進行了法律改革的實驗。由于此次運動由美國主導,因此,各國的實驗紛紛以美國式的法律制度為參考藍本,以新自由主義的法律理論作為指導理論。十幾年間,在這些國家,新型的司法機構得以設立,舊的法律制度得以改革,然而,“法律與發展”運動所期許的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目標卻沒有實現,并且越來越遭受批評與質疑。在對“法律與發展”運動進行深入觀察后學者們指出:(1)“法律與發展”運動的理論假設存在缺陷,即現代法律對經濟的發展來說是必要的,但僅有現代法律仍是不夠的;法治的建設對于政治的發展具有貢獻,但政治的發展不能僅靠法治建設。(2)“法律與發展”運動對第三世界國家法律、政治、社會的實際情況不了解,忽視了各國、各地之間,尤其是其與美國情況的不同。(3)“法律與發展運動”的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受到抨擊和懷疑,其對關于法律的功能、國家—公民關系等各種問題的論斷受到挑戰,甚至有人批評新自由主義法學理論對美國本國法律制度和運行狀況的描述都存在錯誤。(4)“法律與發展”運動基本上是一個移植美國經驗的過程,然而,美國經驗恐怕并不具有普適性。
在“法律與發展”運動宣告失敗之后,各種“法治”項目興起。不同于“法律與發展”運動,這些“法治”項目不再表現出強烈的“美國中心主義”,它們主要通過推動法律、機構(如司法行政部門、法庭、警察部門等)和人員的建設,實現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可預測而有效率的司法、秩序、人權和遵守法律的政府等目標。東歐、拉美、亞洲的多國都有“法治”項目的開展,包括刑法、商法、行政法的改革,法律機構建設,法官能力培訓等。然而,“法治”項目同樣逐漸受到詬病。法律實踐家和理論家們批評“法治”項目以國家為中心,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徑,將資源集中在政府機構尤其是司法部門,對公民社會投入不足;以法律改革和機構建設的方式促進善治的假設前提值得推敲,效果缺乏實證;諸多改革對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關注不夠。
為了克服“法律與發展”運動和“法治”項目的缺陷,“法律賦能”(legal empowerment,又譯為“法律賦權”)的概念始被提出。“法律賦能”是受教育學、社會工作領域“賦能”(empower,又譯為“賦權”、“賦權增能”等)概念的啟發,以政治學上“權能”(“power”,又譯為“權力”)概念為基礎,在法學理論框架下建構的一個新的概念。所謂法律賦能,是指使弱勢群體增長信心、知識、能力、資源等權能,從而得以利用法律來保護、促進自身權利、利益,獲得機會的過程。其以弱勢群體(無權者)為對象,以法律為工具,以權能為切入點,以權利為基礎,以獲得自由和機會為目的。作為一種在對“法律與發展”運動和“法治”項目揚棄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路徑,其還包括強調擴充弱勢群體權能,關注地方正式和非正式法律制度,以社區為導向,根植于基層的需求,注重支持公民社會、促進公民社會和政府的合作。
(二) “法律賦能”對思考中國農村獲致司法正義問題的啟示
回顧晚清以降中國農村逐步被現代法律制度所覆蓋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其主要路徑是國家通過主要移植自西方的法律概念框架制定現代化的法律制度,在農村建立現代化的法律制度設施和機構,向農村提供現代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和法律服務,從而使現代化的法律理念、法律規范、法律程序、法律機構延伸到農村,在農村樹立法律權威。這一路徑還是主要體現了“法律與發展”運動和“法治”項目那種“自上而下”、“國家中心主義”、注重正式法律制度、強調官方機構建設的特點。這些努力在促進農村法治建設和獲致司法正義實現上產生了相當好的效果,但由于路徑本身缺陷的限制,尚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甚至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如前面所述司法服務能力虛浮、農民難以從現代法律制度中獲益等。
若我們在法律賦能的理論框架中重新審視上文提到的近代農村獲致司法正義在治理變遷中所遭遇的問題和困境,可以將之總結為:農民在近代農村治理變遷的過程中被逐漸去權(disempower)。這一去權的過程可以分解為:(1)在主張權利、解決糾紛過程中,傳統鄉村農民熟知的倫理道德、宗族家訓、天理人情被新的法律概念、法律規范、法律程序所取代,而這些對農民來說卻是一個全新的系統。因此,農民原有的關于權利主張和糾紛解決的知識變得沒有用武之地,而新的知識卻又不具備,造成農民在知識上的去權。(2)在傳統農村糾紛解決中常用的熟人、長者調解中,農民只需具備基本的口頭表達、談判議價、找人居中調停等基本能力即可,而在現代法律制度中,農民卻需要以普通話或書面形式進行表達,需要有能力聯系相應司法機關尋求專業人員幫助,甚至可能需要識別、搜集、固定證據。這些都是很多農民并不具有的能力,造成農民在技能上的去權。(3)在傳統農村,農民處理糾紛往往只需通過同鄉、親友或本地鄉紳即可解決或得到幫助,而在現代法律制度中,農民卻要尋求陌生的專業法律人的幫助,要和不同的司法部門、行政部門打交道。其所享有的社會網絡資源在現代法律制度中沒有那么有效,造成農民在社會網絡資源上的去權。(4)在傳統農村,農民處理糾紛往往在鄉村內部依靠熟人即可完成,而現代法律制度中的司法機關包括法律服務機構大多位于城市或至少鄉鎮之上,往返交通費用高昂,專業法律服務更是花費不菲。這讓農民承受沉重的經濟負擔,造成農民在經濟上的去權。(5)由于農民不能不面對陌生司法機關,使用陌生的法律規范與話語,在陌生的法律程序中,耗費大量的經濟與社會資源,卻不一定能收獲想要的結果,使其在現代法律制度面前倍感無助、無力,對現代法律制度感到畏懼、迷茫甚至懷疑,造成農民在心理上的去權。
由于農民在現代法律制度面前權能缺失,其法定權利無法充分實現,本來有利于他們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服務卻無法充分利用,政府和他人的法定義務他們無法監督履行。因此,即使相關的立法日趨完善,法律設施機構得到設立和發展,農民也難以實現獲致司法正義。在農民法律權能狀況未能改善的情況下,繼續以“法律與發展”運動、“法治”項目那種關注法律和制度領域的路徑進行改革,仍難以改變農民在法律制度中的邊緣、弱勢地位,農民仍難真正受惠于現代化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發展的成果。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在獲致司法正義上的問題,必須通過法律賦能,增強農民對法律的信心、增加農民的法律知識、提高農民的權利意識、培養農民的法律技能、擴充農民的法律資源(包括法律服務、社會網絡等),改變農民在現代法律制度和農村治理結構中的權能地位,使之了解獲致司法正義的具體權利內容,如何行使這一權利,以及如何促使國家落實、保障和促進這一權利。
(三) 促進中國農村獲致司法正義的若干建議
按照“法律賦能”的思路來思考促進農村獲致司法正義的路徑,歸根結底就是:“送法下鄉”不僅是法律制度和法律設施的下鄉,也是法律權能和法律資源的下鄉。結合本文前述農村獲致司法正義的困境,筆者認為,下述舉措可以為農村獲致司法正義的實現提供出路。
1. 深化法律宣傳、教育與其相關的反饋、研究
我國在農村開展普法教育已有多年,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然而在很多地方普法宣傳仍流于形式、方法陳舊,限制了普法宣傳的效果。為了讓普法在農村取得實效,要從方法和內容上改革、深化普法宣傳和教育活動。其一,在方法上,應該多使用“參與式”方法,以平等、參與、互動的方式樹立農民法律意識、傳授農民法律知識、培養農民法律技能。宣傳和教育材料不應用枯燥、晦澀的法言法語,而應以生動、活潑、本地化的語言,配以圖畫、圖表等直觀的工具展示內容;宣傳和教育不應只是通過錄音播放、傳單發放進行,而可組織村民通過角色扮演、小組討論、頭腦風暴、問題樹等活動分析本地主要法律問題,了解相關法律規定,探討問題解決途徑;普法教育不應由司法官員或村干部在講壇上高高在上地主持,而應以平等的精神,鼓勵村民發表意見;宣傳、教育的場所應當適當布置,包括多種教學用具的使用,桌椅的擺放(如魚骨型、馬蹄型等)都應根據宣傳、教育的目的進行設計和調整。其二,在內容上,普法宣傳教育不應只是向農民宣講法條和政策,還應詳細講解法律與政策規定的具體內容和對農民生活、權利的影響,講解適用法律、政策的實用方法,所涉政府部門的具體信息等,使農民不僅能夠了解法律與政策的內容,還能夠掌握運用法律與政策的方法。
法律宣傳與教育不應是一個單向的一次性的過程。相關部門應該利用參與式方法在法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中收集農民對法律制度和政策規定的反饋意見,并且對這些意見進行研究、整理,以便了解農民真實的法律需求,為改進法律制度、發展法律機構、改善法律服務提供實證的建議。
2. 尊重非正式制度
當前中國農村存在國家正式法律和非正式的民間法。民間法包括在農村社會生活中基于村民長期生活、交往和利益沖突而自發產生的鄉規民約、民間權威、習慣禮俗等。法律賦能中的“法律”不僅包括國家正式的法律制度,還包括非正式的法律制度,并且尤其應當重視非正式法律制度在農村中的作用。這是因為:(1)正式法與民間法的關系猶如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其間難以嚴格區分。尤其在中國農村,這二者共同存在,不應該存在非此即彼的對立,而應相互妥協、合作,兩相促進、融合。(2)民間法是農村社會在長期的文化進化中自發形成的規則,它能發揮指導村民行為、防止村民發生沖突、劃定并保障村民個人領域及利益范圍的作用。(3)民間法根植于農村本地歷史與環境,是“本土化知識”的一部分,為農民所熟知和習慣。農民在民間法中更具信心,也有更多的知識、能力和資源利用民間法來處理問題。雖然在法制現代化的沖擊之下,傳統民間法的權威有所消解,但其影響依然存在,依然是一種可以借用的資源。法律賦能應該整理農村非正式制度、尊重非正式制度的權威,發揮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并借之促進正式法律制度在農村的運轉。
3. 發展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
由于訴訟對農民來說是一種耗時、耗力、代價高昂的爭端解決機制,在農村發展以調解為主的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是為農民提供便捷、經濟、有效爭端解決方案的重要路徑。這是因為:(1)替代性爭端解決途徑在中國農村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大量的農村糾紛可以并且在現實中也是通過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的。(2)無論是通過司法部門、行政部門進行調解還是通過社會網絡進行調解(如宗族調解、親友調解、鄉里調解、行會調解),農民在這種“軟性”的爭端解決機制中能更好地運用其既有的知識、技能和社會資源。(3)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更加靈活、便捷,也能體現農民的需要,符合農民對爭端解決結果的期許。(4)發展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在很大程度上與尊重非正式的民間法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但是在傳統農村中盛行的調解,尤其是通過社會網絡進行調解的目的“‘不是分清當事人的是是非非,而是要促使當事人和息相安,所以有時不能真正地保護當事人的權利”,甚至有時有違國家法律的規定。因此,法律賦能所推進的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一方面要讓農民掌握法律、知道權利和救濟權利的方式,讓農民成為法治的“參與者”,促進農民在正義面前的平等,另一方面還要使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的程序和結果符合正義的基本標準,符合國家法律、人權準則和公序良俗的基本要求。
4. 支持農村公民社會和農村社區的發展
支持農村公民社會與社區發展好處頗多,主要包括:(1)大量農村公民社會組織是應允農村公共和私人生活的需要而興起的,因此,它們有利于填補國家權力回縮后的治理真空與公共產品短缺。(2)由于農村自治行政化、自治規章不完善,自治實施缺乏管理基礎,村民自治意識、熱情與能力有限等問題,農村自治未能落到實處,并且效能低下。而參與本村公民社會組織的活動則有利于增強村民參與村務管理的熱情和能力,本村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有利于擴大村民的參與途徑、建立民間的自治組織系統,因此,農村公民社會和社區的發展有利于實現有效的基層自治。(3)農村社區的發展有利于凝聚村民的公共意見,動員村民的共同行動,整合村民的公共資源,增強村民在農村社區內部獲得的心理、知識和資源支持,提高農村社區整體行動的能力和權利主張的影響力。(4)由于農村公民社會組織和社區的運行在很多方面依靠鄉規民約等非正式的民間法,由于公民社會組織和社區因解決農民生活的諸多問題而具有一定的權威,因此,其有利于充分發揮村內非正式民間法權威和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的作用。
支持農村公民社會和農村社區發展的具體行動可以包括:(1)完善農村自治規章,保障農村公民社會組織發展空間。(2)協調村內傳統群眾組織如共青團、民兵連,村民自治組織如村民小組、調解委員會、治保委員會,及新興民間組織如老人協會、互助組織等在農村自治和社區發展中的作用。(3)加強村際以及城市—農村公民社會組織的互動與合作,利用外地資源幫助本地公民社會組織和社區的發展。
5. 培養農村社區法工(community-based paralegal)
所謂社區法工是指受過一定正式訓練、使用多種法律和非法律工具以提供法律服務的非專業法律人員。他們或居住于其所工作的社區之中,或對其所工作的社區有著深入的了解。在中國語境下,社區法工應當包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律援助類公民社會組織中提供法律服務的工作人員、部分法律診所項目學生以及赤腳律師。法律賦能特別重視社區法工的培養,這是因為社區法工具備很多律師不具備的優勢。比如,社區法工關照整個社區的法律需求,而非僅僅雇傭他們的當事人的需求;準入門檻較低,培訓和在社區配置社區法工更加容易也更經濟;社區法工收取的費用比律師低廉很多;社區法工往往比律師更加了解社區的狀況;社區法工可由非政府組織聘請從而滿足社區的廣泛需求。
中國農村現在獲得的來自官方與準官方的法律服務主要是司法所提供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所的有償服務,提供服務者主要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然而由于經費和辦案人員的短缺、辦案人員素質的限制、部門利益的糾纏與沖突、辦案人員與當事人之前的隔閡等原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所支撐的農村法律服務體系還不能完全滿足農村的需要。因此,我們還需要“方便、免費、親切、顧慮少”的赤腳律師;發展基于農村社區、關注農村公共利益問題的公益法律組織;鼓勵具有豐富資源的法學院開設駐于農村社區、解決農村法律問題的法律診所,同時倡導政府給予農村社區法工更多的政策支持,吸收更多的政府財政、慈善資金給予農村社區法工經費支持,調動法學院、律師事務所和公民社會組織給予農村社區法工更多的專業支持和技術培訓,探索設立、發展農村社區法工項目的新模式。
The Governance Evolution in Chinese Rural Areas and the Access to Justice
——the Enlightenment of Legal Empowerment
CHENG QianXU Ya-wen
Abstract:The access to justice in rural China has encountered predicaments in evolu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For instance, local legal agencies are incapable of providing legal services; the interference of political power and governance vacuum coexist; the legal elite in rural areas are rare and modern legal systems have often repressed traditional governance n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empowerment, farmers loss of legal power accounts for the major obstacle to get access to justice. Such access to justice can be achieved not only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system and legal facilities but also depending on the legal empowerment for farmers. Several measures are feasible such as respecting local informal systems, developing alternative disputes resolutions and cultivating community-based paralegals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rural governance judicial justice legal empowerment rule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