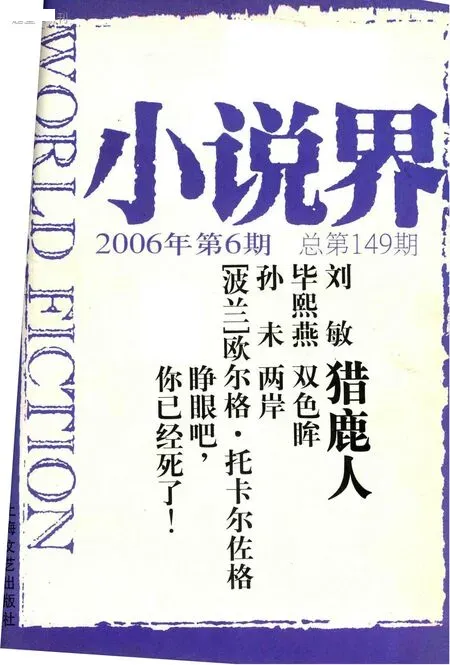崇寧記
舒飛廉
倉庚,倉庚,來年莫再鳴!
倉庚一鳴草又生。
草木青青不過一百數(shù)十日,
到頭來,又是樵夫擔(dān)上薪。
倉庚,倉庚,來年莫再鳴!
倉庚一鳴蟲又生。
百蟲生來不過數(shù)十日,
到頭來,又要紛紛撲紅燈。
倉庚,倉庚,來年莫再鳴!
……
山道轉(zhuǎn)啊轉(zhuǎn),白云深處,回蕩著樵夫的歌。平宜城,陡黎城,到了黎城山如門。一過宜城,果然是由平地進入山林,由河流、湖泊、草木、鳥獸、城池、人丁聚合起來的浩瀚平原,也因此盤曲、板蕩、聳立而成為丘陵、高山與峽谷。大朵大朵的白云將它們的暗影投在初夏翠綠的山巒中間,好像成群的鯨魚在浮游。
兩三只黑鷹高高地貼在青天上,在它們的隼眼里,忽而朝霞滿天、忽而暮云四合,春夏秋冬的變化,帶來山花如錦、夏樹如海、秋色如火、冬雪如被,或乍陰乍晴,或狂風(fēng)勁吹,或雷聲震震,或閃電霍霍,或陽光如瀑,或夜雨傾盆,將更新的萬象綜攝到這陰陽的洪爐之中,向不可知的未來演變。
“這幾只呆頭呆腦的鷹,飛著飛著,就會睡著吧,一頭摔進山谷里,才會由夢中嚇醒?”山路上,一個紅衣女客,騎在一頭倔頭倔腦的黑驢背上,騁目四顧之余,又將她的目光投向天邊。
黑驢在心里想道,李蕓這個半老徐娘,臉上白粉搽得又多,好像隨時都預(yù)備出門去說媒似的,但她還是又好看又精神,像一道晚霞明艷照人。如果她這一回進山燒香,能受到菩薩的開示,變得稍稍聰明一些就好了。老鷹在天上睡著了也就罷了,我可大意不得,這一失足,往下就是萬丈深淵,這個云夢隱俠趙文韶,就得去宜城縣買一對籮筐,一頭挑他心愛的娘子,一頭挑我這一百來斤驢肉,哭著回他的云夢縣去了。
“它們不是鷹,而是雷鳥。一般的鷹,會俯沖下來,叼走樹林中的松鼠、兔子與山雞。雷鳥對這些都沒有興趣,它們喜歡吃的是在溪澗里長出來的龍。崇寧山中的龍在春天里交配,之后母龍往溪流里產(chǎn)下的卵泡,絕不比一只精力旺盛的母蟾蜍少。如果不將這些龍蝌蚪吃掉,不要幾年工夫,流出崇寧山的漢江,恐怕就是由龍的口水匯流成的。”趙文韶牽著驢,慢吞吞地走在崇寧山回環(huán)的山道上,杜鵑花簇在他的身邊明明滅滅,好像是燃燒在陽光之下的火把,好晃眼睛。春種秋收,耕作之余,文韶兄,你熟讀《太平廣記》的好處,就是偶爾外出游歷的時候,能夠為驢背上的妻子授業(yè)傳道解惑吧!
“我不信!如果有這么多龍蝌蚪,養(yǎng)出來的雷鳥還不像烏鴉一樣成群結(jié)隊,像木劍客的武當(dāng)山后山似的,去爬武當(dāng)山的人,一不小心,就跌倒在涂滿烏鴉糞的神道上,煩死人!”在云夢縣無聊的隱士生活中,作為云夢隱俠消遣對象的一代名妓,所上的當(dāng),所受的騙,幾個谷倉都裝不完!以至于李蕓大嫂修出了“我不信”這樣的不二法門,你天花亂墜,我自巋然不信,你來咬我啊!
“你不是剛才說過,雷鳥有一個很可怕的毛病,就是飛著飛著就會睡著,一頭掉進山谷里摔死嗎?如果沒有這樣可怕的家族病,它們一定會如垂天之云一樣,遮去崇寧山的半邊天的。”趙文韶去看貼在天上的兩只雷鳥,只恨天高地遠(yuǎn),施展不開移魂大法,或者是什么鬼脈神劍,弄下一只去山澗之中應(yīng)景。黑驢心里卻在想,千萬年以來的崇寧山啊,該有多少睡著的雷鳥落到了你的山谷里!這些以龍為食的鳥兒,它們的鳥肉會是何等的鮮美!如果有一個家伙,能夠?qū)⑺鼈兊牟弊佣缦聛恚占梢欢眩綕h陽府去,一定能做出遠(yuǎn)勝過周黑鴨的鴨脖子……
“崇寧寺!”李蕓在黑驢之上驚叫起來。這一座天下名剎伴隨著她的嬌喝,出現(xiàn)在如鎖鏈一般回環(huán)的崇寧山中,終令形而上的趙文韶與形而下的黑驢由“雷鳥之辯”的深淵里解脫出來,得以遠(yuǎn)眺崇寧寺的莊嚴(yán)凈土。
原來,轉(zhuǎn)過了這一段險竣的山路,山勢下沉,豁然開朗,漢水由山腹之中鑿出來一片方圓七八里的谷地。谷地三面環(huán)水,一面接山,山如屏風(fēng),破巖間長滿松柏,雜樹相映,到山頂之上,已是白石壘壘,草木難生,山線如游龍回環(huán)在半天之中,恐怕也只有那雷鳥,可以飛越過去。而在絕壁之下,谷地之上,立起來饅頭般的兩座小山,一左一右,與它們身后的高山比較起來,自然是小巫見大巫,但其緩坡與平疇,碧草與芳樹,水脈之奇,地脈之正,在上面興建佛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鱗鱗的樓臺佛閣,已經(jīng)將兩座小山大半覆蓋。其時,天色又近黃昏,東山上涼月圓圓,夕暉由江漢平原返照上來,越過玉帶一般的漢水,由蒼翠的崇寧山壁上折返,將托舉著十方叢林的山巒染成一片黃金海洋。
山路的盡頭,是一條石橋,飛虹青霓般接向佛國,漢水幽潛碧藍(lán),嘩嘩流淌在石橋之下。此橋何年何月何人修?橋畔楓楊樹又是何年何月何人栽?楓楊樹亭亭華蓋,老得不像個樣子,恐怕由趙文韶拉著驢頭,李蕓牽著驢尾,二人一驢團成一圈,都未必能圍住大樹的腰身。夕陽興致勃發(fā)地將它染成一棵金樹,每一對扇形的小葉都像金箔一樣,輕搖晚風(fēng)中。他們站在楓楊樹下,遠(yuǎn)眺著絕壁下的崇寧古寺。趙文韶覺得,當(dāng)年,僧璨大師游蕩在崇寧山的群山之間,放下他的行囊,歇腳在此樹之下,俯瞰夕暉映照的四月溪谷,他禪定如蓮的心扉,也如同當(dāng)下他與李蕓一般,被眼前山腹中的奇景扯動。大師發(fā)愿,要將他心中的佛國,建造于此,縱使歷盡千難萬險,也不在話下。而這座單孔的石橋,也是由僧璨主持最早修起來的建筑吧,橋頭刻上的名字是:止觀橋。
“飛廉大人在他的《龍的歷史》中,記載有止觀橋與崇寧寺:‘由武林鎮(zhèn)向東, 陸行十余日,平原始盡,有城曰宜城、黎城。宜者夷也,山中人外出,過此城則一馬平川。而黎城之謂,則因此城軍民,實為我國最早見到了羲和駕車,載陽烏離扶桑之海,光照我神州者。崇寧山千山萬壑,深幽奇秀,人跡罕至,山精水怪層出不窮,自山海經(jīng)以來,不可記述窮盡。昔年有僧璨大師,流連山中,發(fā)愿修止觀橋、崇寧寺,經(jīng)十?dāng)?shù)代弟子,凡五百年,得東海龍族之助,始告成功。其寺如《阿彌陀經(jīng)》所示西方極樂世界,不可思議”趙文韶出門時做了功課,當(dāng)然,飛廉的《龍的歷史》,他讀過太多遍,每次讀到“得東海龍族之助”,他就心旌搖蕩。在過去的歲月里,在神州的江河湖海里,以飛廉的見聞,只有一條名叫望舒的龍在游弋。難道,崇寧寺的告竣,跟她也有關(guān)系?endprint
是的,那些貼在天際的鳥兒,其實算不上雷鳥,它們只是普通的鷹。這個世界上,連龍都沒有,哪里會有以龍為食的雷鳥呢?飛廉啊飛廉,你的龍的歷史寫到最后,不就是望舒的歷史么,她既神龍不見首尾,你也將這云遮霧繞的謎團藏在你的書里!
“不就是蓋幾座房子,雕幾個木頭菩薩,然后請來一堆和尚燒燒香,念念經(jīng),打打坐,用得了五百年?還什么龍族!我覺得都是這些和尚們在搞鬼,因為一時頭腦發(fā)熱,將廟蓋到了山里,說是要清修。結(jié)果時間一長,沒得香客來了,和尚們又閑得扯蛋,所以就編出這些個故事來,連飛廉那個老實頭都相信了!任他奸似鬼,也喝老娘洗腳水喲,老趙你就看著我騎著黑驢子,飛奪止觀橋,大破崇寧寺,來一個李蕓娘巧勘和尚廟,說不定,老娘也會尋到一個鐘,鐘下一個洞,洞里一群騙來的小姑娘,一個個穿著肚兜搽著香粉打扇子。我正好就湯下面,將那些和尚綁起來去送給宜城知縣砍大光頭小光頭,小姑娘們就動員她們留下,在這洞天福地,弄一個名叫崇寧院的窯子,到時候你再讓飛廉大人寫一個《崇寧院的歷史》,那些京城里的公子哥兒,江湖上的白衣少俠,還不千里萬里地尋趁過來,將金子銀子扔得滿坑滿谷……”李蕓發(fā)下的宏愿,聽得趙文韶直搖頭:沒有開過妓院的名妓,就像沒有中過狀元的進士,難免心有不甘,千千成結(jié)。那黑驢子卻連連點頭稱是,驢肝驢肺里,就一個聲音在回蕩:“我也要來!我也要來!”趙文韶見它得意,氣不打一處來,聽得懂人話了不起啊?他抬手就想將驢繩系在楓楊樹上,將這個家伙留在橋頭風(fēng)餐露宿數(shù)星星打秋風(fēng),他與李蕓獨自過橋入寺探險搜奇去也。
不讓我去掀鐘看美女,好歹也讓我偷吃兩口那饅頭山上的金光閃耀的瑤草吧,大哥,你這趙文韶也真是的,武功好,知識多,找了一個名妓老婆就了不起啊,欺負(fù)我一個畜生……黑驢眼中淚光漣漣。李蕓的心腸多軟啊,一時就奪過驢繩將它牽在身邊,勸解著她的男人: “讓它與我們一起走吧。文韶,我的左眼皮與右眼皮同時都在扯著跳,我預(yù)感到,我們不會第二次踏過這座橋。會有另外一條路,將我們帶出崇寧山。”趙文韶得聽綸音,輕輕點頭,帶著李蕓,二人一驢,踏上了夕光中的止觀橋。
一年才輪到一次的龍華法會。和尚們正在大雄寶殿上做法事,由方丈法喜帶領(lǐng)著,在殿上繞著巨大的佛像念佛。法喜身后是近百名掛單在本寺的和尚,個個臉放紅光,法衣清潔,龍行虎步,好不威儀,好像是由后面的羅漢堂上的回廊里怡然蘇醒,伸拳弄腿,一番哈欠之后,緩步走下來的羅漢一般。和尚之外,是數(shù)以千計的由山外進來燒香的香客,嗡嗡營營,繞行在大雄寶殿的高大的廊柱間,好像群蜂出沒在巨大的蜂巢,猶顯綽綽而有余地,可證大殿森嚴(yán)萬象,高峻超拔,果然是仙佛洞府。釋迦牟尼端坐在上,神目如電,斂神俯視著環(huán)繞著他不停息地旋繞著的人浪,投放在香爐中的檀香猛烈地燃燒,散發(fā)出來的香氣,將溪澗之中草木的香氣與人群污濁的氣味盡皆化合在一起,正是欲界、色界與無色界混雜起來的令我佛如來沉迷不已的世界之香。
李蕓看到了熟人!這不是武昌府胭脂路養(yǎng)心巷的劉四媽嗎?當(dāng)年李蕓的一張嘴,說遍胭脂路少人敵,堪堪就不是這劉四的對手,多少黃花閨女由渡船運到武昌,怯怯村姑,小鎮(zhèn)美人,土頭土腦,徘徊在胭脂路上,都是勞她老人家的教引,一塊硬鐵熔作熱汁,一杯熱汁變成了蒸汽,一個村姑變成了蕩女,一個蕩女變成了神女。那劉四媽看到李蕓,也是眼睛一亮,臉龐一紅:“李大姐,你也燒香來啦,燒得好燒得好,我們這樣的人,再不跟佛講一聲對不住,死了就會被打發(fā)到拔舌地獄去,什么叫拔舌地獄……就是你的舌頭像韭菜似的,長一茬,割一茬,白天有,晚上無,十殿閻王爺下酒用的黃豆辣醬醬舌頭,都指望著拔舌地獄的牢頭一桶一桶提過去!”劉四媽一邊講,一邊隨著她的圓轉(zhuǎn)走了。另外一個迎面而來的王九媽李蕓也認(rèn)得,卻是她云夢縣的麻將搭子,她跑來燒香,是因為欺負(fù)她的兒媳婦美娘跳了井心中有愧?打麻將老是輸錢好不甘心?還是因為年輕的時候瞞著她家里的老張偷戲班里的武生小李,生下的兒子小張實則是小小李?王九媽合著掌,瞇著眼,并不知道她麻將場上的對手,此刻也在佛爺?shù)拿媲袄@圈圈求麻將神技從天降。
趙文韶也看到了好幾個面熟的香客。一個是他的同窗周豐年,君山一別,二十年了吧?他長胖了,頭發(fā)也變白了。做過了禮部尚書,下一步,就是做當(dāng)朝的宰相?他青衣小帽微服私訪來到這里,是求佛托夢給那個愛畫畫的皇帝,由對蔡京大人的滿腔迷戀里脫出彀來吧,老蔡長得柔白可喜,寫的一手字龍鳳飛舞,但治理國家,不能指望長相與文藝啊!趙文韶運起觀滄海內(nèi)力,只一剎那,身材與面容都發(fā)生了改變,好像一只倭瓜變成了一只南瓜,周豐年自是認(rèn)他不出。另一個是云夢街上的屠夫老鄭,他每殺一頭豬,都會去找隔壁的吳裁縫借粉餅,將數(shù)字涂改掉,有人以為他是在記人家欠他多少串錢,他記的是生死簿啊!趙文韶常去光顧他的肉鋪,為李蕓買豬肝煮菠菜,買豬肚燉蕓豆,眼見著鄭屠殺豬的數(shù)目字,百而千,千而萬,如果每一頭活過來,會擠滿云夢縣的每一條街。吳裁縫隔壁的算命先生老周說,老鄭你下輩子,一定會變成你鄭家莊上的一頭母豬!怕不怕?怕啊,真痛苦,所以他來到崇寧寺。“崇寧山下崇寧寺,閻王不請自己去。”在見閻王之前,很多事情,也不是沒有辦法去改變的,趙文韶其實很同意這一點,他繼續(xù)扮南瓜,眼看鄭屠念著阿彌陀佛從他身邊走過,他進山之前,洗過澡,身上是艾蒿、肥皂與豬糞混雜在一起的氣味,這樣的氣味,屠夫娘子喜歡得緊吧?
黑驢呢?牽在李蕓手里的黑驢,它的一雙驢眼,也在轱轆似的轉(zhuǎn)。久違了,洞庭湖里的龍蝦精,她由羞怯的小青梅,變成了風(fēng)姿綽約的小婦人,卻還是喜歡裹著猩猩氈做的紅袍子。你和鄔歸在洞庭湖里搭了個小龍宮,搭出了窩,現(xiàn)在想下崽子吧,龍蝦配烏龜,大擺烏龍陣,洞庭春水里,啪啪啪交尾之后,是扳籽還是下蛋?龍蝦精一定是來求子的,觀音娘娘就踮著小腳站在如來佛的右邊,拿著凈瓶拈著柳枝灑灑水,這事歸她管。依我看啊,觀音菩薩你還是要大發(fā)慈悲,讓洞庭湖多一種轉(zhuǎn)基因新妖怪不是壞事,這種新妖怪如果是龍,那還不是中了彩頭?龍蝦精后面的小姑娘,穿著青色的小棉襖,看起來是十五六歲的模樣,那是一條兩三百歲的老狐貍啊,她就住在縣衙后面馬廄邊的一堆草垛里,第三排第七垛,長長的小迷宮稻草洞,她最近迷住街上馮寡婦家的小馮秀才,在三七洞里,跟人家胡天胡地纏了幾回,就覺得遇到了真愛。是將這個清俊的少年當(dāng)作煉丹的補藥,還是做好田螺姑娘,委身給人家成為良家婦女?黑驢明白小青狐的糾結(jié),做狐貍誰沒遇到這樣的問題,說到底,最后多半還是將人家當(dāng)?shù)捔耍@個并不需要如來的點撥。黑驢放眼去看,發(fā)現(xiàn)龍華法會上,龍蝦精小青狐之類的妖怪還不少,托身成人形,混雜在人群中念佛,比人更像人。所以滿堂兮人類,能坦蕩蕩以畜生的原形見如來的,就是我大黑驢獨獨一條啊,想到得意處,黑驢不禁又吭唷吭唷叫了幾聲,聽到李蕓耳朵里,還以為它也在驢頭不對馬嘴地叫“我佛我佛”呢!endprint
捐款箱在佛像下,香案前,三尺高,二尺長,一尺寬,漆得朱紅锃亮。香客到此磕頭,會看到箱面上貼著的紙條兒:“宜城漢口商行交子,最結(jié)佛緣。”一箱“崇寧通寶”的鑄銅錢,與一箱“交子”的區(qū)別,當(dāng)然是不可以道里計。趙文韶沒有兌換交子,但他有金子啊。李蕓由褡褳里摸出七八片金葉子塞到捐款箱里,這樣大方的出手,讓她牽著的黑驢都覺得很有面子,它抬頭去看,覺得座上的如來佛好像都在“呵呵”。而坐在香案側(cè)邊敲木魚的胖大法喜,也停下木魚,站起身,來到正在蒲團上磕頭的趙文韶夫婦跟前,將他的木槌,在趙文韶頭上敲了三下,在李蕓頭上敲了三下,又走到黑驢身邊,在它的驢頭上敲了三下。敲完了,他夾著木槌,又回到他的法座上,瞇縫著眼,一邊敲木魚,一邊看香客捐錢。
法會之后,是吃飯與睡覺。趙文韶發(fā)現(xiàn),法喜和尚的精明,不僅是從宜城交子上體現(xiàn)出來,齋堂與遞鋪,也都整飭得井井有條。齋堂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天干”排,遞鋪則是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十二地支”排。知客僧在大雄寶殿的臺階上發(fā)放木牌,趙文韶得到的是辛齋寅鋪,李蕓得到的是辛齋未鋪,黑驢得到的是辛齋亥鋪,所以他們按照龍華法會的安排,現(xiàn)在是坐在辛字齋堂的一條長凳上吃齋飯,吃了齋飯,就各回各鋪去睡覺,一覺醒來,自然是帶著佛賜的好運,幾千人又回到俗世,做人的做人,做妖的做妖,當(dāng)官的當(dāng)官,殺豬的殺豬,蓄妓的蓄妓,萬丈軟紅中,親,還記不記得崇寧山中的一夜?
“每一年,都會有五位香客留在崇寧山,不知所蹤,其中就有武當(dāng)山的好幾個道士,跑到崇寧寺里來,最后并沒有回紫霄宮去。外面的人傳言,這五個人是在崇寧寺的龍華法會上,當(dāng)夜受到開示,成了佛。”趙文韶對李蕓講。這時候他們已經(jīng)在齋堂里吃過了精美的素齋,去檢視過了干凈整潔的遞鋪,牽著驢,來到漢江邊上,讓它去吃青草。
“也不一定是五個人,中間說不定也有妖怪。剛才我去看我的亥字鋪,住下的,竟然全部是牛頭馬面的男妖精,雖然人模人樣,怎么瞞得過我的法眼?”黑驢邊吃草邊想,“這五個人,怕是帶的金子、銀子與交子太多,半夜被和尚們拖出去劫了財吧,我看那法喜和尚長得白胖,眼睛賊亮,一看就不是好貨。”
“可是木劍客道長講,那幾個道士也沒帶幾文錢出來,而且他們在后輩中聰明伶俐,不貪財,也不好色,可謂是后起之秀,所以木劍客才特別地上心。”趙文韶說。
“長得好,才是真的好!你這個賊漢子!我還以為你是帶我出來春游崇寧山,原來是為木劍客那個閉關(guān)的臭道士找小道士來了!”李蕓揮起粉拳,一臉?gòu)舌恋厍弥w文韶的背,趙文韶當(dāng)然是趁勢將她摟在了懷里。
黑驢由沉思與青草中抬起頭,看著這對調(diào)笑中的中年夫婦,心里又想:“這安排住宿的和尚們,將男妖與女妖分開也罷了,人家好好的夫婦,為什么要一個住寅鋪,一個住未鋪,你多弄幾間鴛鴦鋪,人家求子的求子,調(diào)情的調(diào)情,你也多收幾兩銀子的住宿費,豈非兩全齊美?讓這兩人春心萌動,三更半夜跑出來親嘴,好玩嗎?”
漢水彎彎,淙淙流水如鳴玉,河畔芳草嘉樹,落英繽紛。晝而農(nóng),夜而禪,和尚們種下不少作物,紫云英深紫一片,小麥青碧,蠶豆正在開出蝶形鳶尾般的花,豆麥的氣味蘊藻在一起,為地氣所發(fā)酵,果然是令人春心蕩漾的春天的氣息啊。黑驢不好意思地將目光由趙文韶與李蕓二人移向群星奔涌的夜空,一輪溫涼月,就掛在東方崇寧山高高的山脊線之上,像浮現(xiàn)在微茫宇宙中的一個微笑。山脊線起伏跳躍,黑驢忽然發(fā)現(xiàn),有一只老虎,白色的老虎,在沿著山脊線散步,它緩慢而有力地挪動著四肢,好像在宣告,它走過的微黑的山嶺,都是它的領(lǐng)地。
黑驢目力奇佳,趙文韶與李蕓的眼神,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李蕓握著趙文韶的手,與他一起盯著月下白虎發(fā)呆。它如何能在山脊線上散步呢?就像在刀刃上散步?如果這個時候,群星中再跳下來一個扎著英雄巾的武松,就可以貼著夜空,來一段武松打虎的皮影戲?
等到月到中天,黑驢吃飽喝足,山頂上白虎不見,趙李二人方才由春夢里醒來。他們發(fā)現(xiàn)群峰之下,崇寧丘上的佛寺,已經(jīng)燈火盡熄,沉入黑暗。由下往上看去,只有第三重藏書閣兼地藏王菩薩的座殿里,還有一柄牛油大燭在春夜的和風(fēng)中跳閃搖紅。
三人三更三重門,來聽我佛傳綸音。
黃昏里,法喜和尚用木魚槌敲他們?nèi)齻€的腦袋,雖然當(dāng)日他們看不到西游記,不懂得菩提祖師與悟空的鬼把戲,但惠能和尚傳下的《壇經(jīng)》他們都看過啊。連黑驢都注意到,除了他們仨,法喜和尚還從他的椅子上下來過兩次。一次是小青狐,一次是周豐年,每一次都是一三三的節(jié)奏……不多,也不少,不急,也不緩——難道,這就是他在本次龍華法會選定的五位大神嗎?
三更時分,月明星稀,石滑露重,草木香濃,春夜何其。黑暗中,趙李二人牽著驢,沿著臺階拾級而上。崇寧甲丘是廟宇,崇寧乙丘是齋堂與遞鋪。藏經(jīng)閣就在甲丘的頂上。藏經(jīng)閣的門已經(jīng)敞開,法喜站在門口,將手中的沙木烏桕油火把分發(fā)給前來報到的五位香客:周豐年、小青狐、趙文韶、李蕓、黑驢。其他四位也罷,黑驢如何打火把?法喜好像也有預(yù)備,用一根麻繩將火把綁在驢頭上,妥妥的——只是黑驢心里,卻在打晃,什么時候火把燒完,我這個驢頭,就得變成炭燒的了——到時候,我一定要記得將它摁熄在你這個不懷好意的胖和尚的肥屁股上——他一定是早早地將粗海鹽與孜然粒帶好了。
牛油大燭與火把照耀之下,藏經(jīng)閣廳前正中,果然扣著一口黃燦燦的大鐘。法喜一手擎著火把,一手變掌平推鐘面,大鐘輕輕挪向一側(cè),如同滑行在冰面之上。他也會大金剛神力!黑驢心想,我其實也做得到,抬起前蹄將鐘踢開,只是鐘面上,可能會留下我的驢蹄印子,這和尚卻能四兩撥萬斤,收放頗自如,高手嘛。黃鐘移,地洞出,李蕓一臉自信地看著露出來的大洞,臺階歷歷,由洞口通向不可知的黑暗,走啊走啊,那些如花似玉、周身青紫,穿著喜鵲登枝的花肚兜的鄉(xiāng)村美少女就在前面等著我們!小青狐卻有一點狐疑不定,在入住三七稻草洞之前,她可是墳堆中的常客,她今晚上,可是來學(xué)佛,而不是寫盜墓筆記的啊。周豐年朝趙文韶微微點頭,君山島上的故人,已經(jīng)彼此相認(rèn)。endprint
法喜和尚打頭,身后是周豐年,趙文韶,小青狐,李蕓牽著黑驢殿后,一行人依次入洞,初極狹,僅可通人,然而一下到洞底,就發(fā)現(xiàn)燈火輝煌之中,別有洞天,數(shù)十丈高闊的洞廳,四壁都是常年不熄的油燈——那些捐款箱里的交子,多半都是用來買烏桕油的吧。主洞四周,又有五個分洞,五個分洞之中,也各各有自己的分洞,外人沒有向?qū)нM來,會迷失在這個明亮的迷宮之中吧。法喜和尚對跟在他身后的五位客人說道:“歡迎來到崇寧地洞……一般的客人,會認(rèn)為崇寧寺就是山中的佛寺,有大殿、齋堂與遞鋪,由和尚們領(lǐng)著客人在佛像前念唱經(jīng)文,我們在龍華法會上挑選出來的客人,才會被帶入崇寧地洞來。他們會在地洞里找到自己喜歡的小洞,在洞里的油燈之下,找出四壁的經(jīng)文與秘籍看,然后寫出自己的經(jīng)文與秘籍……是的,崇寧地洞就是這樣一個圖書館,它盡可能地將世界的智慧集中在這里,然后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能量與智慧。”——看來那些捐款箱里的交子,除了買烏桕油,還要用來供養(yǎng)地洞內(nèi)的訪問學(xué)者的開銷啊,每年五人,五百年,就是二千五百人啊——是的,崇寧洞里的學(xué)者與俠客們,都會活得長久,由僧璨大師選定,由龍族參與建造的崇寧地宮,會令時間在循環(huán)之中保持微弱的平衡,但是在法喜看來,是佛法讓人們永不老去,令此地成為一個真理的桃花源。
“是的,你們由這五個分洞,金銀島、木人巷、水立方、火鳳凰、土行孫,任選一條進去,都可到達(dá)崇寧山的山腰。當(dāng)然,如果你們愿意,也可將每一條分洞與岔洞看完,再去山腰不遲,有幾位客人,甚至在地宮里待了好幾百年也不愿意出來,哪怕是浪費幾刻鐘,在山腰的草木間吹吹風(fēng)。”在法喜和尚的指點下,大伙兒在洞壁上,分別看到了“金、木、水、火、土”五個分洞——小青狐心里想,又是按五行!喂喂,按星座與血型來設(shè)計這些洞,會死啊?
原來是一個奇怪的圖書館……并不是一個淫窟。李蕓大失所望,但她知道,這個調(diào)調(diào),是趙文韶喜歡的。趙文韶看著周豐年,他的老朋友臉上也露出了喜色,在這個力量與智慧之海里,也藏有治國家的方略與安天下的本領(lǐng)吧,這些都是他愿意努力尋求的。而對他這位游俠而言,每一本秘籍與經(jīng)文,都是珍貴的,想一想前朝的玄奘花費十余年時間去天竺尋求佛經(jīng)的生死路,就會明白僧人們所積下的功德是多么的了不起。小青狐心里想,除了書生之外,也許還會有修煉出內(nèi)丹、尋求變化的辦法?她抬頭去看黑驢,發(fā)現(xiàn)那龍精虎壯的黑驢,也在驢眼灼灼地看著她,一時心慌意亂,臉都紅啦。而黑驢卻是驢軀一震:這分明就是金庸舉人在一個名叫俠客行的故事里,講的俠客島故事啊,一群傻乎乎的俠客來到俠客島武功圖書館學(xué)習(xí),其中最傻的一個家伙,領(lǐng)悟到了絕世的武功,說不定,這一回,那個石破天就是黑驢我呢!
火把之下,法喜和尚的臉色乍悲乍喜,不可捉摸。他說:“雖然進入崇寧地洞的客人,修持萬法,經(jīng)過‘僧璨法門的試煉,開悟證佛者不計其數(shù),但佛門講求緣法,五行之門,不信者莫入。各位盡可舉著燈,重新由長梯回到洞口,推開覆在洞頂?shù)你~鐘,回到遞鋪,等待天明,下山返回塵世。”好在三人一驢一狐都無返回之意,由頭上頂著火把的黑驢打頭,鉆進了木人巷,法喜和尚頷首示意,隨著眾人魚貫而入。
崇寧寺下別有洞天,原來都是出自天然。漢水流過崇寧山,其實是一分為二,其上碧玉蜿蜒,泄銀破玉,其下卻潛入山嶺之下,神龍不見首尾,發(fā)揮著鬼斧神工。五百年前的僧璨大師,看到山谷中的美景是一喜,下到山谷,發(fā)現(xiàn)甲乙雙丘之下的天生洞天,又是一喜吧。熊熊火把光之下,只見洞壁上鐘乳如麻,奇形怪狀不可方思,洞外水聲潺潺,暗河里的水在幽暗的地下流淌。木人巷曲折而深廣,狹窄處亦可并行車馬,寬敞的地方,卻是豁然開朗,群俠的火把之外,洞壁上也是三五步即有長明燈,星星點點,將山洞照得如同白晝。洞壁之下,鑿出的間間石屋,因勢賦形,層層累累,如同市集,背靠著石壁,只向洞中道路,開出一門一窗,有的石屋,其中一片漆黑,有的石屋,透過窗紙放出光芒,顯然尚有主人在其中忙碌。
黑驢頂著火把,將石屋一間一間地照明出來,只見石屋的杉木門板上,都伸拳踢腳,鐵畫銀鉤一般題寫的匾額,大概都是“九陰真經(jīng)”、“九陽真經(jīng)”、“降龍十八掌”、“太極拳”、“六脈神劍”、“易筋經(jīng)”、“乾坤大挪移”、“血刀刀法”、“混元功”、“玉女心經(jīng)”、“吸星大法”、“空明拳”云云。黑驢經(jīng)空山老僧傳功之后,已無師自通,堪堪能識到兩籮筐大字,明白這些都是江湖上練功法門,不由得四蹄騰騰,要不是李蕓拉住,早就破門而入,去學(xué)那石破天悟道去也。周豐年回頭對趙文韶莞爾道:“文韶兄,金庸舉人大作流布華夏,沒想到在這深山秘洞里,也自成一派。”原來趙文韶愁眉苦臉,裝模作樣,以“觀滄海”催動易容術(shù),還是沒有逃過人家龍圖閣大學(xué)士的法眼,早已認(rèn)出了跟隨在身后的故人。趙文韶道:“坊間盛傳,金舉人著書已畢,封筆不作,遁入深山,一心求學(xué),難道是來到了崇寧山中?只是此洞匯萃金學(xué),應(yīng)該叫金舉人巷,而不該叫木人巷啊?”周豐年也點頭稱是。
前面李蕓攜著小青狐,拉著大黑驢,已經(jīng)按捺不住好奇之心,砰砰敲上了“九陰真經(jīng)”之門,李蕓一邊敲門,一邊對小青狐講:“我這把年紀(jì),學(xué)九陰白骨爪已是晚了,但青狐姑娘你卻剛剛合適,防狼術(shù)中,沒有比這個更好使的了。”木門乍開,屋里一床、一椅、一桌,桌上有燈,燈花結(jié)得核桃大,照亮著四壁的書卷。一個老書生垂腿坐在桌子上,讀書讀到神采飛揚,一見法喜,一臉狂喜:“法喜法喜,這《楞伽經(jīng)》里,別有法門,楞伽城也可以是崇寧山,是實在,也是虛無,你們將它看作實在,我偏要將它看作虛無,一旦將它看作虛無,就到處都是縫隙,我悟了!明天我就要上山去!”法喜聽了,臉上也露出欣喜之色,合掌道:“黃施主果然是天縱之才,不到一年,就悟出了虛無法門,明天早上,我讓沙彌早早送飯,以便讓施主上山證道。”
原來是東京翰林院的翰林黃裳。在東京的時候,他天天讀經(jīng),沉默寡言,沒想到,他身上還藏有這么一個老少年。周豐年上前寒暄,多半是京中故人如何如何。小青狐上前插話,打聽九陰白骨爪的法門,黃裳有一點不屑:“金舉人講的那個九陰白骨爪,固然是可以抓開石頭,但長此以往,姑娘你的這一雙羊脂玉一樣的小手,也就毀得不像樣子了,當(dāng)年梅超風(fēng)與情郎相會,都得戴上小羊皮手套。姑娘家家的,咱不學(xué)這個,等我琢磨出‘楞伽爪,抓破虛空,你來學(xué)!”趙文韶疑惑地問:“金舉人也住在這木人巷中嗎?”黃裳答道:“木曰東,東曰生,盡人力,聽天命,是為木人巷。金舉人卻是在‘金銀島上,鉆研的是‘蜘蛛俠、‘蝙蝠俠、‘鋼鐵俠、‘絕地武土的法門。”趙文韶懂了,原來這大名鼎鼎的大宋舉人,又迷上了科幻與機甲,化身成了一個蒸汽朋克。endprint
一行人告別手舞足蹈的黃裳翰林,繼續(xù)前行。寂寂山腹,皇皇燈火,小屋之中,多半黑燈瞎火,旅客已經(jīng)入睡,三五盞油燈未滅,他們登門拜訪的人,還有小椴大師與溫巨俠,小椴大師正在“混元功”之屋里鉆研“天生真氣”,而溫巨俠的小屋,卻涂掉了石屋的牌匾,在無名之屋里,試驗著唐門的藥水,他覺得世界的奧秘,是在各種物質(zhì)的化合之中。周豐年說這是外丹的路子,而在小青狐的印象里,卻是感慨,如果小椴大師與溫巨俠沒有中年發(fā)胖的話,都還算得上是俊朗的青年,看來小沙彌們每天送來的齋飯,還是蠻能養(yǎng)人的。小椴大師的小屋里,還有一條長得像白狐的狗在半夢半醒之間,說明前往山洞修行,是能帶寵物的,也許,我該將那個可心的云夢小書生,也一并帶過來?小青狐想到那溫柔而多情的男人,又覷見黑驢垂垂累累的胯下行貨,溶溶春心發(fā)動,一張俏臉不禁悄悄變得通紅。
木人巷之洞的下半程,道路向上,所以由洞中出來的時候,已經(jīng)是崇寧山的山腰。春風(fēng)習(xí)習(xí),將山間松柏、楓楊、梧桐、烏桕、楓楊等樹木的香氣與草葉的氣味混雜在一起。一行人離開明亮的洞府,舉著火把,站在微黑的山道上,沉睡的崇寧雙丘,丘上的崇寧古剎就在腳下,眼前是西垂的殘月與點點的繁星。法喜和尚對眾人講:“春夜漫漫,良辰未至,幾位施主還有興致的話,小僧愿領(lǐng)諸位到其他的分洞瞧瞧。”李蕓與大黑驢天生好奇,尚有興趣,小青狐接連失望于三個帥哥,已經(jīng)意興闌珊,呵欠大作。周豐年問道:“其他四洞,也是大同小異吧?”法喜答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就是一萬個洞,道理也只有一個。趙文韶點頭稱是:“洞中的一間石屋,我等凡俗之人,一生都受用不盡,不用再去叨擾隱修的奇人與俠士了。只是敢問方丈,何為‘僧璨法門?如何在崇寧寺中開悟?又如何在崇寧寺中成佛?”
法喜和尚的臉上,又浮現(xiàn)出高深莫測的微笑,他領(lǐng)著眾人繼續(xù)向前。崇寧山腰的棧道,像衣帶一樣,纏繞著崇寧山峻峭的山體,他們好像是走在草木與星辰的海洋里。不久,法喜停下來,將燈舉起,照亮路邊的一個山洞,洞口三五尺見方,堪堪可令黑驢小跑進去,與崇寧山下的洞府不同,這個小洞顯然是人力掘成。法喜說:“你們聽!”周豐年、趙文韶、李蕓、小青狐、黑驢側(cè)耳去聽,小洞深杳,洞里隱隱傳來呼喝之聲。趙文韶諦聽良久,對大伙道:“有人在洞中練習(xí)太祖長拳,拳勢剛烈,力大無匹,當(dāng)世無敵。”法喜點頭:“他是征遼回來的李亮將軍。過去一年,他一拳又一拳,日夜不息,已將他的山洞,打出了一百余丈。”小青狐問:“春香是誰?”她舉著火把,照亮洞口石壁,上面歪歪倒倒地寫著“春香洞”三個大字,顏色黑紫,顯然是山洞的主人嚙咬手指,血書而成。周豐年說:“李亮將軍出身寒微,出征時,同村女子對他說,幽云十六州不光復(fù),你就不要回來。后來這個女子死于一場傷寒,她的名字就叫春香。”小青狐一聽,眼淚嘩的一下,就流了出來。
向前三五十步,又有一洞,洞中卻無聲無息。法喜說:“你們聞!”黑驢將驢頭探進黑暗的洞口,嘩的一下,流出了一嘴口水。李蕓說:“好咸!”法喜說:“這是大海的味道。峨眉山的滅絕師太,花了一年又六個月的時間,砍壞了一百三十余把倚天劍,終于鑿成了倚天洞,鑿穿了崇寧山。”果然是大海的味道,像鐵銹、咸魚、樹林中的蘑菇的氣味混合在一起,沿著幽長的一線山洞涌出來,好像一股氣味的泉水。小青狐的問題是:“滅絕師太難道不是出現(xiàn)在本朝下半場的人物嗎?而且她也只有一把倚天劍,是用天外玄鐵鍛造而成,獨此一把,如假包換的。”法喜說:“按照‘金銀島洞中的找礦與鍛煉的秘籍,普天之下,一把菜刀都可以用玄鐵來打!”這是一個沒有漏洞的故事……小青狐吐吐舌頭,與大黑驢交換著贊嘆的眼神,閉嘴了。周豐年盯著刀光劍影的“倚天洞”三個字,感嘆道:“果然崇寧山外,就是東海。平宜城,陡黎城,到了黎城山如門。山如門,進崇寧,闖開崇寧海如盆。下里巴人的謠曲,說得是一點不錯啊。”
“所謂‘僧璨法門,就是鑿穿崇寧山吧!”趙文韶看著法喜和尚,火把兀自在熊熊燃燒,六支火把投射出來的光,像是星月微明的子夜,在漫長曲折的山道上,掘出了另外一個地洞,法喜和尚,就是這個移動的光之地洞的主人。山道旁邊,有一個亭子,名叫法雨亭,法喜和尚領(lǐng)著大家,將光的地洞,移到亭中,轉(zhuǎn)身面對著崇寧山的山體,對趙文韶道:“趙施主慧根大好,宿緣深種,此山此夜,當(dāng)是前世注定。昔年僧璨大師創(chuàng)造崇寧寺,他的想法,就是寺中說法,洞中讀書,登山悟道,悟道的法門,就是鑿穿崇寧山,見海如見佛。”李蕓插嘴道:“海即是海,佛即是佛,如何見海如見佛呢?和尚莫誑我們!”法喜不理她,繼續(xù)說:“所以寺中的龍華法會,一年一度,已有數(shù)百年,萬人入寺聽法,千人入洞讀書,百人登山悟道,最后得見大海的,也不過是十?dāng)?shù)人而已。就是這十?dāng)?shù)人中,的確也有見到了海,沒有見到佛的,他們的辦法,是將崇寧山再鑿?fù)ㄒ槐椋愿魑皇┲鞣叛矍铱催@山,山間的地洞,鑿?fù)ǖ慕伲磋復(fù)ǖ慕Вㄅc不通,深淺不一,道行不一,所證果位,當(dāng)然也頗有不同。現(xiàn)在拂曉將近,晨風(fēng)西來,你們聽!”
果然起風(fēng)了。西風(fēng)由黑暗的平原里會集起來,越過宜城與黎城,吹入崇寧山脈,一直吹到崇寧山的腳下,吹過澄明的漢水,山丘上的芳草嘉木,吹到山嶺上,回旋在千百洞穴之中,洞穴大小不一,彎曲不一,深淺不一,其中小半,已經(jīng)貫通到了大海,所以晨風(fēng)嗚咽坎坷,令屏風(fēng)一般的山嶺,變成了笙竽琴瑟,都與之共鳴,生發(fā)出奇妙的天籟。甲乙雙丘上的和尚與居士們,此刻還在夢中吧,還有崇寧山外,平原上那些農(nóng)夫、官吏、土卒與商人們,他們沒有因緣,得以傾聽這天地中的法曲。
法雨亭中的四人一驢一狐,默然無語,心神俱醉。此曲只應(yīng)天上有,人間能有幾回聞。法喜和尚聽過好多遍,所以先不去說他。趙文韶修行“進化論”,周身的經(jīng)絡(luò)與血脈為之鼓動,已運行一個小周天,覺得真力源源而生;周豐年想起朝中諸般人事興亡生滅,悲從中來;李蕓則想到她在云夢縣里的稻麥豆黍,雞犬牛羊,種的種,收的收,老的老,小的小,其實也蠻有意思;法曲將小青狐又帶回了散發(fā)著青草氣息的稻草洞,想到洞中與小書生的千種風(fēng)情、萬般柔情,不禁周身發(fā)熱,春意漸濃;黑驢聽得手舞足蹈,只知道好,哪里知道好在何處,它引吭驢鳴,氳氤著大金剛神力的嗓子,金聲玉振,與風(fēng)聲相和,在山洞中回環(huán)激蕩,生發(fā)出一番全新的音樂——這倒是從前法喜和尚沒有聽到過的——在武術(shù)、史詩、田園、淫聲之外,原來驢鳴中,也有我佛西來意?法喜大和尚不禁雙手合十,喃喃念道:“善哉!善哉!”endprint
風(fēng)吹驢鳴,持續(xù)了小半個時辰,然后晨風(fēng)停息,法曲微微,崇寧山頂上,已出現(xiàn)了一絲魚肚白,山內(nèi)山外,雞鳴乍起,宣告著世界由宇宙模式轉(zhuǎn)入凡俗的模式。小青狐嚷道:“法喜法喜,我聽這神曲,都快悟了,看什么書,挖什么洞,見什么海,我要回云夢縣去,越快越好!”法喜道:“女施主,我聽說紅塵里,有一夜情、百日緣,也有白頭偕老,情欲所持,緩急不一,這悟道,也有漸頓不同法門。李亮將軍打拳是一生,滅絕師太用劍是一年,江南雷家的雷震子用火藥,得好幾天,到這金庸舉人,等他由‘金銀島上悟出‘變形金剛之術(shù),鑿?fù)ǔ鐚幧剑赡芫驮谝灰怪g,而黃裳大人,他尋找崇寧山在虛空中的縫隙,鉆研‘蟲洞之學(xué),也許,轉(zhuǎn)眼之間,就好像用穿山術(shù)一樣,出現(xiàn)在崇寧山另一側(cè)的海灘上。”
“海灘!我忘了帶比基尼了!”小青狐雖然有些懊惱,但想到還有這樣飛快的挖洞法門,也就強自按捺住了對小馮秀才的思念之情,來都來了嘛,被選進龍華法會,也不容易啊,先在崇寧山里修一個穿山佛,再回云夢去修一個歡喜佛嘛!之前李亮將軍的例子,也讓周豐年心生退意,經(jīng)法喜和尚這么一說,他也由衷地同意小青狐的想法,決心花掉一兩個月的時間,在崇寧山的地洞與山腰,努力修行,靜心思索,去尋找更高的智慧。朝廷之事,急迫如同流火,但一兩個月的緩急,也是有的,這兩個月間,難不成蔡京與徽宗,好得生下私孩子?
法喜和尚握著在緋色的晨光里漸弱的火把,領(lǐng)著小青狐與周豐年下山,返回地下尋覓石屋,回頭卻發(fā)現(xiàn),趙文韶、李蕓與黑驢走出了法雨亭,沒有跟上他們。周豐年笑著說:“文韶兄的性子還是如此和緩,看樣子,是準(zhǔn)備走漸悟的路子了。”李蕓答道:“我們再看看風(fēng)景,沒有比早上太陽出來之前更好的光線了,我家老爺子,就愛這個調(diào)調(diào)!”大黑驢想跟著小青狐去,卻被李蕓手中加力,狠狠地勒住了嚼頭。法喜和尚也不阻攔,囑咐二人一驢盡早回地洞用早膳——本寺的白面饅頭綠豆稀飯黎城蘿卜條相當(dāng)不錯,一邊就領(lǐng)著小青狐與周豐年在緋紅色的山道上走遠(yuǎn)了。
“其實不用去讀經(jīng),你已經(jīng)找到辦法了,對不對?”李蕓對趙文韶講,多么聰明的女人,“我們來,是找那幾個小道士的,并不是要成佛。”
趙文韶點點頭:“但是我也想出了一個鑿穿崇寧山的辦法,比李亮將軍、滅絕師太快,比黃裳要慢,大概與雷震子和金舉人差不多。我們且試試,能不能成佛!”
李蕓眼睛亮亮的:“怎么辦?”
趙文韶說:“驢蹄之下是什么?”
李蕓說:“山路。”
趙文韶說:“山路通向哪里?”
李蕓說:“山頂。”
趙文韶說:“山頂那邊是什么?”
李蕓說:“海。”
所以趙文韶、李蕓二人,就這么牽著驢,沿著蜿蜒的山道,按照他們發(fā)明的毫無創(chuàng)見的“僧璨法門”,施展起輕功向山頂奔去。在他們的身后,崇寧諸峰慢慢由迷離的春天晨霧中醒來,在他們的眼前,云蒸霞蔚,黎明正在到來。
世上美美的,難道不是滿頭大汗,勾腰曲身,爬到山頂,稍稍駐足,迎面吹來一陣清風(fēng)嗎?由霞光與大海中吹來的晨風(fēng)令站在山頂上的驢子一陣舒爽,覺得在山洞里摸爬滾打半夜,又跟著這一對該死的中年文青夫婦爬了小半個時辰的山,這些辛勞都得到了回報,變得好有意義。他們站在一塊棋盤一般的巨石上,巨石中央,一棵松樹蒼勁挺立。往西是纏繞在一起的山嶺,雷鳥翅下的偉大的崇寧山迷宮,浪費了多少修道人的年華;往東是一望無際的大海,激蕩在一丸紅彤彤的朝陽之下,信天翁在海上飛,鯨魚在水中游。“所謂滄海變桑田,對迷宮而言,大海就是答案。”趙文韶接過李蕓香風(fēng)細(xì)細(xì)的手帕子擦汗,初陽由海上照上來,將松樹之下的這兩個人,還有這頭驢子,通通都涂上了金粉,乍看上去,還不是像崇寧寺里木胎刷金的羅漢?
“老虎!老虎!”李蕓指著灑滿朝暉的山坡,驚叫著撲進趙文韶懷里。趙文韶與黑驢順著李蕓的手指往下看,只見一頭老虎在十?dāng)?shù)丈外的草木巖石之間,一邊輕嗅,一邊低吼,披著金色的陽光,慢慢地向山頂走來——正是昨夜他們在漢水邊上,遠(yuǎn)眺山嶺時,看到的那頭在山脊上散步的白虎。它已經(jīng)察覺到了李蕓的驚叫——這三個不去吃白面饅頭綠豆稀飯黎城蘿卜條的家伙,活該成為“云夢人驢火燒”,來給人家白虎做早餐吧?
“原來,還有一出‘文韶打虎的戲碼,小哥,我去松樹上折一根棒子給你做哨棒,只是沒有十八碗黃酒給你壯膽,文韶哥你就將就一下,去將那只老虎打死吧,順便將虎皮剝下來,我回去硝了,請小吳裁縫做成大衣,冬天穿著出門打麻將,能掃一撮箕云夢縣女人掉下來的眼珠子吧!”有會功夫的男人就是好,李蕓可不怕。
趙文韶卻沒有挺身而出,將他心愛的女人與忠厚的驢子攬到身后。他毫不思索地扯著李蕓,躍到松樹頂上,堪堪將渾身是汗的黑驢留在了巨石之上。
李蕓微微有點失落,想到這空山神僧的驢徒弟,擁有一身世間罕匹的神力,也就放下心來,站在松樹頂上,又苦口婆心地告誡黑驢:“你可省著勁踢它,用巧勁,而不是蠻力,七傷拳會不會?要震斷人家的心脈,莫弄傷人家的皮,好好的一張白虎皮,被你踢一個大洞,就不值錢啦!”
趙文韶坐在松枝上,卻是一臉的促狹:“這白虎也不是好惹,它逐日巡山,那些用‘僧璨法門,鑿穿崇寧山,見海如見佛的家伙們,拳劍火藥變形金剛,各顯神通,鑿?fù)ǘ矗缧Q蛾子由獨頭繭里鉆出頭,見著了一線天光,聞到了一絲海風(fēng),第一個見到的活物就是它。白虎聽著山腹中的動靜,哪一個洞通了,哪一個沒有,明明白白,心里吃了螢火蟲似的。等到他們伸出頭去看大海,可不是鳥吃蟲似的,鉆出一個吃一個!可惜了木劍客那幾個水靈靈的小徒弟,佛不在海上,倒是在白虎的肚子里,真是阿彌陀佛。它能夠?qū)⒛敲炊嗟母呷寺竦剿亩亲永铮幢鼐痛虿悔A你家的驢子。”這個故事太傷感了……與雷鳥吃龍蝌蚪的故事一樣,又是這老家伙編出來騙我的……李蕓祭起她的“我不信”大法,“眼下,姐姐我不關(guān)心全世界,只關(guān)心我的驢子,我還指望騎著它回云夢縣去打麻將呢。”
大海將陽光反射到黑驢的眼睛里,好像將鹽也撒了進來,聽到松樹之巔,女主人與男主人的一問一答,黑驢心中,是悲喜莫名,勇怯交替。一個是空山神僧的驢徒弟,一個是疑似吃掉無數(shù)神僧的白虎,誰能贏?昔有唐人柳宗元,曾作文《黔之驢》:“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yuǎn)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xí)其聲,又近出前后,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沖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蕩倚沖冒”是好拳法,“怒蹄之”是好腿法,“跳踉大?”咬耳朵則是王八拳了。我就是這一頭黔之驢嗎?黑驢低頭避開變得炙烈的陽光——松樹上,李蕓大姐已經(jīng)撐開了她的小花傘,奸夫淫婦啊,手拉手、腿并腿地垂在松枝上圍觀臥虎斗藏龍——黑驢向下看去,白虎正一步一頓走到峰頂,剪尾一躍,跳到巨石之上,一聲虎嘯,百谷回應(yīng),然后睜著它的兩只吊睛大眼,死死地看定了已經(jīng)四蹄匝地,驢尾上揚,紅鬃怒發(fā)的黑驢!
責(zé)任編輯 林濰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