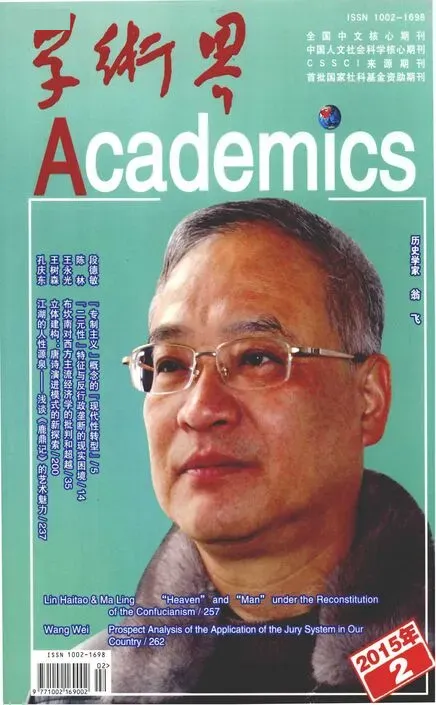泰國華文詩歌創作中的中國詩性智慧〔*〕
○沈 玲
(華僑大學 華文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一
泰國華文文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由低潮到活躍的變化。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醞釀,經過三四十年代的黑暗時期和五六十年代的繁榮發展時期,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泰國華人華僑政策的改變,泰華文學又一次陷入低潮。但自1975年中泰建交以及隨后東盟的崛起,中泰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交往日漸活躍,泰華文學也漸漸走出低谷,并努力朝著多樣化方向發展。與之相應,泰華詩歌的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大體而言,上世紀二十年代為詩歌的萌芽期,“三十年代初期就已經有數本新詩集在泰國出版,計有林蝶衣的《破夢集》《橋上集》(一九三三年),符開先的《萍》(一九三四年),以及黃崇治的《青萍集》。”〔1〕二戰后泰國文壇詩風興盛,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一度消頹,七八十年代后新體詩創作日漸熾盛。九十年以來,泰華文壇散文創作成為較為強勁的文類,但泰華文壇的作家多是各種文體兼擅,泰華詩歌創作仍處于平穩發展之中。
詩性智慧這一概念首見于維柯的《新科學》一書。在此書中,維柯從原始人認識世界的方式探討了人類藝術的發生。在他看來,通過隱喻和想象創造或構建的智慧就是詩性智慧。
“詩性的智慧,這種異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開始就要用的玄學就不是現在學者們所用的那種理性的抽象的玄學,而是一種感覺到的想象出的玄學,像這些原始人所用的。這些原始人沒有推理的能力,卻渾身是強旺的感覺能力和生動的想象力。這種玄學就是他們的詩,詩就是他們生而就有的一種功能。”〔2〕詩性智慧文化是人類的第一個文化形態,人類文明早期都經歷過詩性智慧文化,中國文明同樣是一個經歷了原始民族詩性思維的文明,但“中國的詩性智慧在本質上是一種不死的智慧”。〔3〕中華文明的持續性、漢字的表意性、中國人重直觀體驗與頓悟的認知方式又使得中國的詩性智慧中內蘊著理性智慧,換言之,中國的詩性智慧不單單具有維柯意義上的原始思維,還有邏輯思維,只不過它外在的表現形式常常是詩意的、詩性的。本文借用維柯的概念,以中國詩性智慧概括泰華詩歌創作中體現出的受中國詩學思想(主要是儒家詩教觀念)支配、有著中國古典詩學審美追求的特質。
泰華文學與中國文化關系密切,中華文化在多方面影響著泰華文學,其中原因除了中華文化本身具有的強大魅力和吸引力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創作主體的根性意識和由此而來的對本民族傳統的堅持。回顧泰國華文文學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泰華文壇創作主體最初以華僑為主,再到華僑與華人共同參與,到今天泰國華人成為活躍的創作力量。有研究者指出,“1926年后是華僑文學萌芽的年代,是在‘五四運動’催生之下出席的年代。”〔4〕“泰華文學能夠在泰國的土地上開花結果,除了一些在泰國出生作者的努力之外,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少從中國移民來的青年投進寫作隊伍。四十年代中期,由中國南來的青年知識分子特別多,其中有不少投進寫作隊伍。”〔5〕他們為泰國華僑文藝注入了新生力量。1939年到1945年間,因戰爭等原因,泰國文壇的作家們或避世,或回中國,或放棄寫作,創作人才一度凋零。不過“五十年代,六十代的新移民,或者是回歸的‘新唐’,他們加入寫作圈的為數也相當可觀。目前泰華文壇的創作隊伍,這兩個年代的作者占了一個很大的比例。七十年代的新移民作者減少了一些。八十年代呢?更少了。土生土長的作者似乎是沒有。”〔6〕可見,泰華文壇既有中國內地來泰避戰的“新唐”作家,又有泰國本土成長的“老唐”作家,而兩派作家在創作上雖然因理念不一,存在著分野,但彼此交流、互相融合已成必然趨勢。因此,隨著作家身份的轉變,泰國華文文學經歷了一個從華僑文學向華人文學轉變的過程,但無論是華僑文學還是華人文學,包括泰華詩歌在內的泰國華文文學的創作主體仍是有著同根同源文化的同一族群。
而文學作為一種表現的藝術,“表現首先是屬于想自我表現的自然,并在作品中找到了自我表現的途徑。這些作品本身也是具有表現性的,是自然所啟發的。作品給我們打開的獨特世界是自然的一種可能;在實現這種可能時,作品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實質的信息;藝術家作為一個曾經感到這一信息的人,也從中表現了自我。”〔7〕因此也可以說,以泰國華僑華人身份進行的詩歌寫作也是表現作家自我的一種手段,這種表現中自然帶有源于同一族群的文化與美學內蘊。
另外,從語源來看,泰國華文文學是泰國華僑華人以漢字書寫的文學,而語言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語言既是文化的一個構成部分,又作為文化的載體,承擔著記錄、傳播文化的功能。“新的藝術,沒有一種是無根無蒂,突然發生的,總是承受著先前的遺產。”〔8〕泰華詩歌是用漢字寫成的文學作品,對泰華詩人來說,“盡管故鄉的路條已改/故鄉的方向沒有改/青山蔥秀連連綿/溪流清急蜿蜒/林野肥沃豐裕/胎育著幸福的人民//盡管故鄉的人事已變/故鄉的土質沒有變/高齡的老樹已消逝/披上壯秀如童子軍的新橡林/油燈茅舍已無存/奠下水泥木屋和電燈//盡管嚴父慈娘已逝/故鄉的史跡沒有逝/那一所播種華文的陋室/那一段中華禮教的熏陶/把故鄉醞釀成/今日的方塊詩”〔9〕故鄉已然遠去,但承載傳統的方塊字依在,泰華詩人用祖先留下的方塊字抒寫對故鄉、對傳統的熱愛與懷念。泰華詩歌在發展過程中受到五四新詩、臺灣現代詩和大陸朦朧詩等的影響,但就其精神內核來看,在泰國華文詩歌的漢字書寫中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美學精神,蘊藏著屬于中華民族傳統的詩性智慧。
二
具體而言,泰華詩歌中的中國詩性智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中國儒家詩教觀念是泰華詩歌意緒表達的內在支撐。
中國儒家詩教觀念本身就是一個包容性強的生長性概念,先秦兩漢時期的詩以言志說、興觀群怨說、溫柔敦厚說,魏晉時期的詩以緣情說,唐宋的文以志道、文以明道、文以載道說以及以詩代史等都可納入儒家詩教傳統。泰國是一個普遍信仰佛教的國家,佛教對泰華詩壇有影響,比如1945年,泰國中華佛教研究會諸人成立了“標指詩社”,該詩社“以禪為詩,以詩協禪”進行創作,泰華詩人偶爾也在詩中寫佛教活動,不過綜觀泰國華文作家的詩觀和詩作,盡管泰華詩人是在異域的土地上進行創作,但泰華詩歌的意緒表達主要仍是受中國儒家詩教觀念的影響與支配。
首先,在對創作主體的要求上,以道德為主。
中國儒家文藝思想認為在詩品與人品二者之間,人品決定詩品,要求作家要有崇高的道德修養,只有作家作品有良好的道德修養才能寫出好的作品來,而好的作品一定要有浩然之氣。泰華詩人同樣認為:“作家的思想品德和他的作品有密切的關系:詩品是人品的反映。”“有一些人品不正的人寫出一些‘正品’的詩或文章來,總有些破綻,終有一天被人看出其虛偽的面目來。什么樣的人,就有什么樣的詩。”〔10〕因此,“作為一位當代的文藝作家,我們是應當有一顆明辨是非的心,不迷惑,不出賣靈魂,有所選擇,有所堅持。”〔11〕
其次,在創作主旨上,要求詩歌反映現實,關注現實。
儒家特別注意文學的社會功能。孔子《論語·陽貨》篇中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孔子認為,詩歌可以激發人的情志,可以觀察社會,可以結交朋友、團結人群,可以批評政治得失、表達對社會不合理現象的不滿。這雖然說的是《詩經》的社會作用,但實際上也是對詩歌這一文學體裁所具有的認識、審美、教育等社會功能的主張。孔子開啟了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理論的源頭,中國的文學創作大都要求文學發揮應有的社會功用,關注現實,反映現實,批判現實。泰華文學創作一開始即受五四精神熏陶,強調用現實主義精神進行創作,詩歌也不例外,現代主義是泰華詩歌的起點,現實主義則是泰華詩歌創作的主流。即便泰華詩歌漸漸轉向書寫個人的情感,但作家始終未曾忘懷現實,泰華作家李少儒說:“詩可以分:治世的歌頌。亂世的呼吁。憤世的諷刺。”“在文學價值上說,歌頌的文學價值,比不上亂世與憤世文學的內涵與張力。”在那些書寫屬于個體的情感中仍不時流露出作者對社會、人生和人性的關懷與反思。像李少儒、司馬攻、林牧、夏煌、老羊、曾心等人的詩歌皆是如此。
“在風雨如晦的日子里/我沉重地拿起如椽的筆/把心靈的重壓/化作濃情熱血/去傾吐弱者的辛酸不幸/去揭露世間的丑陋不平//我沒有無病呻吟的閑情逸致/更沒有吟風弄月的悠閑雅興/我僅知道我擁有一顆愛心/我僅知道我應忠于華夏詩歌精神/當世間還有多少悲凄的眼淚/當弱者還在渴求善心與同情//”“在傳統文化被糟蹋踐視的危機中/有人正把祖宗的詞語碎骨分屍/忘記自己的屬性而拼命學‘洋八哥’/狂熱地把臟似垃圾的文化崇拜模仿/我堅信文化的傳統應忠于本國的傳統/詩歌應屬于人民大眾與時代聲音//”〔12〕這是泰華詩人林牧1999年寫下的詩《我的歌》,可以看作他自己詩歌創作理想與主張的剖白,也是他文學觀念的詩意體現。詩人認為詩歌屬于大眾,屬于人民,屬于時代,作為一個有愛心與良知的詩人,在面對社會黑暗與不公的時候,要用筆去傾吐弱者的不幸,揭露世間的丑陋與不平,這才是華夏詩歌的精神與傳統。在他看來,不僅僅是詩歌如此,一切文藝創作都應該遵守這種精神,“追求高品質的‘泰華文學’”。他說:“如以文學的廣義及所含的深意而言,文藝的創作,不論時代如何變化、歷史的發展如何,還是離不開人生的啟蒙角色及社會的教育功能。”“文學是社會的投影,是歷史發展的實象記錄,是社會的良心,是時代的呼聲,是追求真理、表達理想、灌溉靈魂、觀察世態、探索生命的精神世界上層建筑。因此,一位有宏觀思想、熱愛真理、熱愛人類的作家,不能存有一種閉門造車的心態;他必須深入生活,面向人生、面向時代,熱情頌揚美好事物,站在時代的前端,并擁有一個坦蕩胸懷及宏觀思想,……寫些反映生活、具有欣賞價值又具有趣味性、有時代感及社會功能、富有地方色彩的高品質‘泰華文學’來吧。”〔13〕林牧對文學的社會功能有著深刻的認識,與其主張一致,他的詩作多是為人生、為社會而作的,有對光明的歌頌和對黑暗的批判。
再如泰華詩人夏煌也是位非常關注現實的作家,他的筆觸較多地深入到了生活在社會底層處于弱勢的人民。像《賣笑生涯》《污蓮淚》詩寫出賣靈與肉的妓女,“為了生存活下去,/我賣,/要尋刺激和歡樂,/你買!/這個人間呵,/就是估我賣你買的世界!//天災加人禍,再加強權/生活、饑餓逗得我們走投無路/什么叫人羞恥?/什么叫人的尊嚴?/它能值幾個錢?/能不能換個面包,/讓我裹腹過一天?!/啊!/說我們自甘情愿!/自甘墮落自作賤!/請你告訴我:/是誰逼使我們,/過著萬人糟蹋萬人虐!/”〔14〕這些可憐的女子“逢人嘻口笑,媚眼瞄”、“左右穿梭送吻又送抱”、“仿春俏,賣靈肉”,“人前強歡笑,/背人偷拭淚潸潸”,千萬般無奈,只是因為那一年“天災洪患過了又干旱,/赤地千里哀鴻號!/弟妹年幼堂上雙親老,/三餐難覓一餐飽。/全家生活全靠自己一肩挑。”遇上天災生活本已不易,再加人禍,“人肉販子噬人魔;/盡把純真稚女來拐騙。/甜言蜜語又誘又驕,/一紙賣身契約簽定了。/從此奴隸生活不由己,/要挖要割任人宰;/皮鞭、火炙、慘打無人告,/忍辱含羞逗賣笑!”〔15〕再如詩《膠工之歌》寫到為了生活為了一家溫飽,割膠工們不得不從半夜三更割到太陽高高升起,從山坳割到山隴上,再從山隴頂割下到山坳。《洪水浸京華》寫城市洪水后普通百姓的悲苦喜樂。《漁家樂·漁家苦》寫海上漁家戶潮來潮去辛苦捕魚,卻過著“雨打船棚水漏屋”,“蚊蚋成夜歡歌笑/盡情肆虐吮血飽”的生活。
再次,在詩歌的審美境界上,視善為最高層次的追求。
在儒家思想長期占統治地位的中國古代,雖然也有莊子一派求真的美學追求,但儒家善的追求,或者說道德追求仍是包括文藝在內的最高審美追求也是最終追求。泰華詩人早已通過創作認識到詩歌的最高審美追求是求真、求善、求美,如老羊寫道:“詩神說:詩歌的靈魂,是真,善,美。”“沒有真善美,就沒有藝術。沒有真善美,就沒有詩歌。真善美,聯結一致,相互相因,協調和諧。以真求美,真美而達善。”〔16〕從哲學層面來看,真代表知識理性,善代表道德,表現在藝術創作中,即作品中既要有知識,又要有美感,還要符合道德規定。而在真善美三者之間,詩歌創作追求知情意的統一,但最高目的是求善。就這一點來看,泰華詩人的審美追求不同于西方,而是沾染上了傳統中華文化的色彩。
詩歌是表現性的形式之一,是表達情感的藝術。《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意即詩歌因情感激發而作、呈現的是人的心靈世界,包括情感、懷抱與理想。中國古人所謂的詩緣情或詩言志正是在抒發情志這一點上獲得了統一。泰華詩人對詩歌的抒情性特征認識得非常清楚,也非常重視詩歌情感的表達。就泰華詩歌的創作實際而言,泰華詩歌是抒情為主的作品。正如詩人林牧在《我的歌》詩中吟唱的:“在浩瀚的文學海洋中/我艱辛地把苦澀的詩句抒寫/我沒有冀求獲得人們的贊語/也不曾希望奪取桂冠的野心/我僅希望能表達善意與純真/訴說心中的憂患和郁悶感情……”〔17〕詩人們用文字訴說愛情、友情、鄉情、親情、人情、離情等屬于全人類共同也是共通的情感,但無論泰華詩歌的主題多么豐富,藝術上的抒情性始終是泰華詩歌的一大特征。
泰華詩歌中,再現客觀現實的詩歌明顯少于表現作家心靈的詩歌,敘事性作品的數量明顯不如抒情性作品。舊體詩中律詩、絕句的數量大大超過長于敘事的古詩等,新體詩更是表現明顯,即便是一些反映現實、有著鮮明現實主義傳統的詩歌,泰華詩人更愛直抒胸臆而非客觀冷靜地進行敘述,間或相雜議論,但無論是抒情性詩作還是敘事性詩作,泰華詩歌中的情感表達多是和緩的、有節制的,較少不能自已,強烈直接如火山般噴薄而出的表達。
在泰華詩人看來,詩歌的真善美必須筑基于詩所要表達的情感。“感情,是詩歌的生命。沒有感情,詩歌的真善美又何所自?沒有感情,詩歌還能成為詩歌嗎?詩歌的感情,必須真摯。虛假的,做作的感情,只能引起讀者的反感。”“詩歌的感情,是詩人個人的感情。感情注入于詩中問世,這感情便不僅是詩人一個人的了。”“詩歌的色彩,是詩人用自己的心血調配的。”〔18〕這就是說情感是決定詩歌真善美的重要條件,而且詩中的情感應該是真實的,屬于作者個人的情感,詩人的創作也是真情流露之下的創作。
第二,中國古典詩學傳統是泰華詩歌言說方式的審美追求。
泰華詩歌在地域上屬于泰國文學,但從淵源來論,就如泰國作家司馬攻所說:“雖然泰華文學屬于泰國文學的一部分,但事實上,如果泰國的華文作者仍繼續用華文來從事創作的話,就不能脫離中國的文學傳統。避免不了受中國文學的影響,尤其是在詞匯以及風格和體裁方面。泰華文學必須充分利用母體文化的文學財富,以及新的創作手法,這條文學的源泉是不能分割的。”〔19〕泰華詩歌同樣不能脫離中國詩學傳統。
從形式看,泰國華文詩歌可以分為舊體詩和新體詩兩種,總體而言,新體詩創作盛于舊體詩,但是這不表示泰華詩壇放棄了對詩歌言說方式的審美追求,放棄了舊體詩的創作。比如曼谷的華文詩歌創作,其中“詩賦之盛,可以分為戰前與戰后兩個時期,戰前詩風之盛,始于華僑日報辟有《華園詩壇》,而戰后則為《世界日報》創刊的《湄江詩壇》。……戰后泰華人才濟濟,風起云涌,比之《華園》時期尤有過之而無不及。”據研究者初步統計,此時約有267人以上的舊體詩詩人,出版了17本舊體詩著作。〔20〕而泰華詩學社13周年慶祝中秋籌備會上,作家李少儒則提出了容納新體詩的主張,并得到通過,由此有了泰華詩壇歷史上第一次新舊詩聯袂大詩展,當時有舊詩一百多首,新詩30多首。有人曾感嘆,“為什么新詩的前途,經過將近六十年了,還是如此的暗淡,不能取代舊體詩的位置呢?其癥結之所在,便是新詩到現在還找不出一個路子來,舊體詩有歷史為憑據;而詞句的優美,境界的高遠,聲調的鏗鏘,可以令人神往。”〔21〕泰華詩歌紹承中華詩學傳統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習用古典詩詞語句、音律和意境。因為泰華詩人意識到“中國的古典文學中有很多超越時空的名作,都有它富于氣魄的涵蓋性——發揮詞句基型簡單的組合,概括地,涵蓋大幅度的人具象,和繁復的意象,穿越現實的感受與想象,在無限的時空間展現一個又一個壯大的景容和概念。”〔22〕所以他們在創作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借用中國傳統詩詞或襲用中國傳統詩詞意境。泰華舊體詩創作自然遵循著中國古典詩學傳統,新體詩創作則沒有如舊體詩那樣有嚴格的格律、韻律等形式方面的規定,如若拋開那些本身就以古典詩形式寫成的詩歌不談,泰華新體詩中仍有不少古典詩詞的韻味。
以泰華詩人陳博文的新體詩為例,如他的《桴屋》一詩:“何必為天地悠悠而愴然!/不要說這是蒼涼絕境,/似夢似幻,/正是一處隱逸的歸宿。/看那疏枝衰草,/竹屋茅檐,/應是適意的棲止。/算了吧!/人生就是夢幻,/不要把夢幻嵌上悲哀,/拾取那朦朧隱約,/煙籠寒水!/霧鎖秋江!/如此冷寂意境,/化成柔柔詩意。//”〔23〕短短一首小詩,化用了唐人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杜牧《夜泊秦淮》“煙籠秦淮月籠紗”、宋人秦觀《滿庭芳·山抹微云》“山抹微云,天連衰草”、辛棄疾《清平樂·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吳文英《齊天樂·贈姜石帚》“霧鎖林深,藍浮野闊”等句,而且整首詩營造出的畫面又讓人不禁聯想到陶潛的竹籬草舍和杜甫的成都草堂。他的另一首《重臨芭堤雅》:“堤邊的鳳凰花燦爛似火/又匆匆過了仲春季節/剪剪東風,吹醉游人甜夢!/云山映海!/濁浪堆雪!/風光依然旖旎。/雖是舊地重游,/但樓空人去。/往日的依偎,暗香宛在,/記得握別時,兩情依依。/曾幾何時?/顧影已成陌路,/憶舊情懷,好似春江流水,/然云山千疊,再晤必難。/就算有朝重見,/鏡中花,水里月,/徒增黯然神傷。”〔24〕這是詩人重回舊地后追憶往昔歡樂相聚場面而作的詩,詩人在詩中糅合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陰風怒號,濁浪排空”和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成“濁浪堆雪”句,還靈活化用了唐人崔顥《黃鶴樓》中的“此地空余黃鶴樓”、林逋《山園小梅》“暗香浮動月黃昏”、柳永《雨霖鈴》“執手相看淚眼”、李煜《虞美人》“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古典詩句,這些古典氣息濃厚的詞語的靈活運用讓全詩變得優雅精致。而他的《離夢》一詩以“昨宵夢里,/枕上分明相視。”和“昨宵朦朧,/枕上分明夢見。”〔25〕結構全篇,抒寫對離人的懷念,從詩句來看,模仿的是花間詞人韋莊的《女冠子》:“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但細究全詩的意境與立意,又頗有幾分蘇軾《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一詞的味道。另一首《漓江山水》“大自然留下的瑰寶,/在視影光圈中,/讓飄逸意象飛翔來去,/流進澄凈心境,/化作無限幽思。漁父依然江上催棹,/震破了一鏡春水。/陣雨悄悄灑過,/把沉睡的桃花拉出帳門。/千峰疊翠,/形態夸張,/隱約澤畔云煙里,/翻出了鳥聲帆影。”〔26〕詩寫的是漓江美景,但其中又有柳宗元《江雪》、張志和《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和屈原《楚辭·漁父》等的意境。
再比如泰國新移民詩人曉云的《愛情落難》,以“陸游的‘釵頭鳳’是我悲切憂傷的寫照/長生殿日日夜夜縈繞著我的‘長恨歌’”〔27〕擬寫失去愛情的痛苦,既貼切又雅致。她并沒有化用古典作品的詩句,而是直接在作品中嵌入古典詩詞的題目,讓讀者自己聯想起原作的意旨,再進而與作品的意境產生系連,這樣詩句既凝煉概括,又給讀者以較大的想象空間,堪稱巧妙。而司馬攻的《青冢》:“一只孤雁橫空而過/漢家天子枕濕的凄夢/被叮叮的鐵馬/呀呀雁鳴/穿破/細長的指尖/如風/連連彈在/漢元帝的心弦上/昭君的倩影/在毛延壽的彩筆下/涂成一堆/青冢//”〔28〕詩人從《漢書·元帝紀》和《匈奴傳》所記昭君之事切入,寫漢元帝與昭君的愛情悲劇,淡筆勾勒渲染的意境、心境,頗有元人馬致遠《天凈沙·秋思》和《漢宮秋》的神采。
泰華詩人對中國詩學傳統的紹承并不是僵化的。如在詩歌的音律等形式方面,雖然如朱光潛先生所言,“詩是具有音律的純文學”。〔29〕但論到新體詩創作,泰華詩人認為音律不應當成為束縛詩歌創作的問題。如老羊即提出:“新詩要不要押韻?我想這問題沒有什么爭論的必要。我一向以為,押韻與否,作者自便。問題在于,整首詩有沒有詩意。詩的句子,不同于散文的句子。但有時與散文句子并沒有什么分別。有些詩句,在整首詩中是詩句,拆開來也是詩句。有些則不然,在整首詩中是詩句,拆開來是散文句子。……整首詩有詩意,可以是構成這首詩的各個句子都充滿詩意;也可以是并非每一個句子都是有詩意的句子。押韻的詩是這樣,不押韻的詩也是這樣。我個人是偏愛有押韻的詩的,但不因此而主張寫新詩非押韻不可。”〔30〕他認為不泥于詩押韻與否,而要求詩有詩意。“不能說,沒韻的詩不是詩。不能說,不押韻的詩比押韻的詩好。韻腳整齊的句子排列,不一定就是詩。”〔31〕這種看法相當圓融。“詩,要寫得好,并非只寫給自己讀,而是要寫給多人讀的。越好的詩,應該是越好讀。因其好讀,也才有越多人讀。因其讀之好懂,領會其內涵,愛其意境與句子的美,深深與詩人共鳴。這就是好詩,多人愛讀的好詩。這樣的詩,如果句子押韻押得好,使讀者讀得更加有味,樂意去背誦,甚至比押韻還更易上口,更好記,更能引起讀者背誦的興趣,更能久記不忘,那么,又何必強求詩人押韻呢?”〔32〕
由此可以看到,泰華詩人并不刻意強求全部的泰華詩歌都與中國舊體詩傳統保持一致的形式規定,而是以是否為人理解,是否具有意境作為詩美的評價標準,在詩的形式與內容之間,泰華詩人無疑是將內容視為更重要的一面。正因為此,我們在泰華詩歌,尤其是新體詩中既能讀到如夏錦的《重逢》、曾心《賞月思》這類押韻的作品,又能讀到如陳博文《生之流轉》、范模士《抹不去的離愁》之類質樸流暢,不講究韻押的詩。
另外,對泰華詩人而言,“詩歌的語言,飽和思想,加上美的色彩,加上鏗鏘的音調,才能扣人心弦。蒼白的思想,單調而枯燥的詞語,只能使讀者感到疲勞或昏昏然”。〔33〕扣人心弦的好詩是充實的思想、優美的語言和鏗鏘的音調的完美結合。在他們看來,“好的詩,會給予讀者廣闊的想象的空間,但是,不管怎么寬怎么廣,也不論讀者各人的經歷有如何的不同,那種種想象,到底不能脫離詩人所要表達的中心意念的。”〔34〕詩歌需要想象,但想象的基石還是思想,是詩歌想要表達的主要內容。這完全是唐代白居易“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的注解。
三
以上從兩個方面剖析了泰華詩歌創作中蘊藏著的中華詩性智慧。需要指出的是,盡管說泰華詩歌創作中明顯地體現出中國傳統詩性智慧,但并不等于說泰華詩歌、泰國華文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盡管在泰華詩歌發展的初期,作者和作品內容都與中國有著密切聯系,包含泰華詩歌在內的泰華文學也曾一度被認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泰國華人政治身份的變化,泰華文學已然是泰國文學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與泰國境內其他語言創作的文學一起共同豐富了泰國文壇的創作實績。可以說,中華文化在本民族族群內部的潛在傳承方式決定了泰國華文文學創作中無論語言形式還是藝術表現都無法脫離中華文化的胚胎,但文化在異域傳播與族群代際間傳承過程中必然伴隨的變異性,泰國華文文學創作主體來源的多樣、身份的多重轉變又導致了泰國華文文學中的中國詩性智慧中融合了屬于泰國的本土經驗。
因為泰國華文文壇很少有專門從事創作的人,絕大多數泰華作家是在工作之余從事文學創作,而且從泰華文壇萌芽期起直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泰國的華文作家們多在報紙、雜志上發表作品,少有人將作品結集出版,因此雖然當時的作家們創作了不少的精品,但可惜的是沒有能完好地保留下來。研究資料的空白給我們今天的研究帶來了一定的困難,我們期待著未來有更多的舊作被發現、出版,以便于進一步充實學界對包括泰華詩歌在內的泰華文學的研究。
注釋:
〔1〕〔5〕〔6〕〔10〕〔19〕〔28〕司馬攻:《司馬攻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528-529、582、582、368、526-527、196頁。
〔2〕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182-183頁。
〔3〕劉士林:《中國詩性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頁。
〔4〕〔20〕〔21〕洪林:《泰國華文文學史探》,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126、126頁。
〔7〕杜夫海納:《美學與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16頁。
〔8〕魯迅:《致魏猛克》,《魯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381頁。
〔9〕林文輝:《一手沒公開資料》,曼谷:泰華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84-85頁。
〔11〕〔12〕〔13〕〔17〕林牧:《大山的足跡》,曼谷:泰華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27、83、28、82頁。
〔14〕〔15〕夏煌:《紅木棉》,曼谷:泰華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55-56、64-66頁。
〔16〕〔18〕〔30〕〔31〕〔32〕〔33〕〔34〕老羊:《老羊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280、281、239、280、240、282、308頁。
〔22〕李少儒:《畫龍壁》,曼谷:泰華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9頁。
〔23〕〔24〕〔25〕〔26〕陳博文:《陳博文文集》,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228、236、233、229頁。
〔27〕曉云:《問情為何物》,曼谷:泰華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88頁。
〔29〕朱光潛:《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