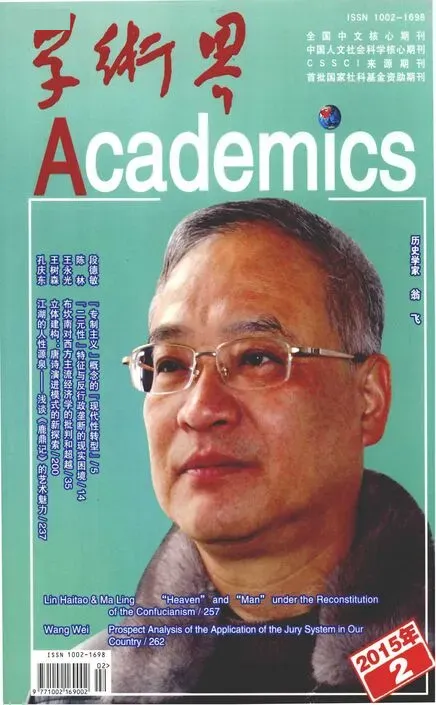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漢英合作翻譯研究
○喬令先
(甘肅民族師范學院 外語系,甘肅 合作 747000)
在當前全球化文化背景下,鼓勵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國門是在中華民族物質文化日益發達的基礎上推介精神文化,豐富和繁榮世界文化的重要舉措,體現了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和諧辯證統一。我國學者王寧在與哈佛大學教授戴維·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的對話中共同強調了翻譯對于世界文學的重要作用:“世界文學的一個決定性特征就在于它必須得到很好的翻譯”(戴姆拉什),“判斷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屬于世界文學必須依循一些客觀的標準……首先,它必須通過翻譯的中介超越自己的民族、國家以及語言的疆界”。〔1〕中國外文局副局長兼總編輯黃友義從譯作可接受性的角度出發,發現“近年來,國際上知名度比較高的譯本都是中外合作的結果”,認為“中譯外絕對不能一個人譯,一定要有中外合作”。〔2〕
由于歷史的原因,英語成為了全世界應用泛圍最廣的國際通用語,漢英合作翻譯就成了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國門的一條捷徑。但是,英、漢語之間“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對立必然會影響到翻譯過程中兩種文化間的交流和互動以及世界文化的健康發展。當前的漢英合作翻譯總體上著重強調在正確理解和表達原文內容的基礎上,突出目的語讀者的地位和目的語文本的可接受性,卻忽視了漢語言文化的傳播和漢英文化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忽視了文化傳播對于漢英翻譯的重要意義。
一、合作翻譯綜述
合作翻譯貫穿于我國翻譯發展歷史的始終。支謙《法句經序》中維祗難等對佛經翻譯的討論可以被認為是我國最早涉及合作翻譯的文獻;我國古代佛經譯場則是合作翻譯的典型案例。梁啟超從譯者的角度把“將佛經翻譯史分為三個階段:外國人主譯期(以安世高、支婁迦讖為代表)、中外人共譯期(以鳩摩羅什、覺賢、真諦為代表)和本國人主譯期(以玄奘、義凈為代表)”。〔3〕馬祖毅、任榮珍從譯者的角度和譯者的合作方式把漢籍外譯中的合作翻譯概括為三種情況,“一是本國人員小規模的合作;二是本國人員大規模的合作,即集體討論翻譯,或集體分工翻譯;三是跨國合作”。〔4〕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受到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政府在對外翻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對外翻譯具有明顯的組織性、計劃性特征。耿強以“熊貓叢書”為個案,從贊助人(patron)的角度和譯作的接受效果闡述了(合作)翻譯中的“政府譯介模式”。〔5〕
從譯作的接受效果來看,我國古代佛經翻譯時期,“中外人共譯期的合作翻譯由于‘口宣者已能習漢言,筆述者且深通佛理,姑邃典妙文,次第布現’,克服了主要由外國人主譯的‘訛謬淺薄’”。〔6〕然而,在漢籍英譯史上,以本國人員為主體的漢英合作翻譯模式缺乏比較成功的案例;而且,根據最新相關研究結果,〔7〕政府譯介模式,即“由中國政府發起,有本土譯者主譯的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總體來說不是很成功”。〔8〕因為,“翻譯工作者處理的是個別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9〕,如何化解兩種語言文化之間矛盾沖突成為了以本國人員為主體的漢英合作翻譯模式面臨的最大障礙。但是,跨國合作,尤其是家庭合作,卻不乏非常成功的案例,比如中國的楊憲益和戴乃迭、美國的葛浩文等,他們夫妻雙方分別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在合作翻譯過程中不僅對各自的母語文化非常熟悉,而且對各自的工作語言也非常熟悉。這樣既有助于對原語文化的理解,翻譯出來的作品又比較符合目的語的語言文化習慣,比較容易被目的語讀者所接受,所以這種跨國合作的模式自然就比較成功,譯作的影響也較大。
二、當前漢英合作翻譯模式存在的問題分析
鮑小英根據拉斯韋爾傳播過程模式,〔10〕從傳播學和譯介學的角度論述了中國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包含“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途徑”、“譯介受眾”、“譯介效果”五大要素的譯介模式;鮑小英在與黃友義關于譯介主體的討論中,黃友義特別強調了跨國合作這種譯介主體之間的合作方式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意義。當前“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漢英合作翻譯著重體現了譯介主體和贊助人在合作翻譯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突出了譯介內容選擇中的民族文化特征,卻忽視了譯介途徑的選擇、譯介受眾的可接受性和譯介主體之間的合作方式,忽視了各要素之間的協調統一,從而未能達到預期的譯介效果。
1.以本國人員為主體的漢英合作翻譯模式
在以本國人員為主體的漢英合作翻譯模式中,以漢語為母語的譯介主體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情況下,相對于目的語語言文化,譯介主體由于深受主體語言文化—漢語言文化的影響,通常具有良好的漢語言文化修養和深厚的漢語言文字功底。但是,譯介主體的漢語言文化本位意識決定了譯介內容的選擇;譯介主體“對本土文化和文學都懷著保護和外推的意愿”〔11〕,他們所選擇的文本通常具有濃厚的漢語言文化特征。尤其是以政府機構為贊助人的“政府譯介模式”,譯介內容的選擇更是受文學和意識形態的影響,“有損中國形象的作品很難走向國際市場,更不用說那些含有不同于當局、政治制度和基本方針內容的作品”(同上)。“譯者(譯介主體)對他們自己以及自身文化的理解是影響他們翻譯方法的因素之一”〔12〕;“文化結構決定了原語文化和目的語文本中的現實構建,譯者對文化結構的處理技能決定了翻譯產品是否成功”〔13〕。這種單向性的合作模式使譯介主體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僅僅局限于漢語言文化,缺乏漢英兩種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互動,譯介主體對原語文化在目的語文本中的現實構建勢必會形成和目的語文化、目的語文本和目的語讀者的閱讀期待之間的矛盾沖突。而且,“任何兩種語言都不會完全相似,都不能代表相同的社會現實。不同的社會團體所處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不只是貼有不同標簽的相同世界”〔14〕,譯介主體由于缺少與譯介受眾之間的交流和溝通,缺乏對譯介受眾及其語言的了解,“一味刻意保留中國特色語言,完全拿對內的話語,不加任何背景解釋,直接翻譯成外文,而不注意外國讀者能否理解,就達不到交流的目的”〔15〕。再者,這種單向性的漢英合作翻譯模式中,由于譯介主體缺乏與英語世界媒體和出版社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譯介途徑相當狹窄。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譯介內容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影響譯介效果。
2.跨國合作翻譯模式
跨國合作翻譯模式可以分為兩種基本形式:一種“與林紓、龐德的翻譯活動相似,即從事漢英文學翻譯的譯者一般不懂中文,通常和講漢語的人(學者或學生)進行合作翻譯”;〔16〕另一種就是合作雙方都是雙語人(bilingual)的跨國合作,也就是說,合作雙方分別以漢語或英語為母語,同時對自己所從事翻譯工作的工作語言也比較熟悉。
第一種形式的跨國合作翻譯中,譯介主體分別是以英語為母語卻不懂漢語的英語譯者和以漢語為母語的中介譯者。這種形式的合作翻譯與“跨文化闡釋式翻譯”〔17〕比較類似,以漢語譯者的文本闡釋和英語譯者的釋譯為主要特征。由于受漢語譯者英語語言能力和漢、英兩種語言文化之間差異的影響,合作過程中容易產生漢語譯者對漢語言文化信息的傳達和英語譯者對漢語言文化信息理解的錯位,產生“有限的闡釋”和“過度的闡釋”(同上)現象,甚至會由于英語譯者的“文化預設”(cultural presupposition)而造成對譯介內容的誤讀、誤譯。而且,英語譯者憑借其母語的先天優勢,有時甚至是出于一種文化優越感,在合作過程中省略或改寫不符合英語語言文化習慣和英語讀者閱讀期待的內容。由于以英語為母語的譯者不懂漢語,合作雙方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溝通,所譯出來的作品很難進行嚴格的校譯。這種合作模式雖然譯介效果較好,但是卻造成了原語文本中文化內容的走失或走樣,失去了文化交流的意義,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傳播和中西方文化之間的交流和互動。
第二種形式的跨國合作翻譯中,合作雙方,即譯介主體分別以漢語或英語為母語,同時對自己所從事翻譯工作的工作語言也比較熟悉,能夠忠實地表達原語文本的內容。目前,漢英跨國合作翻譯中,由于考慮目的語文本的可接受性,通常以英語譯者為主,漢語譯者為輔。在翻譯過程中,在不違背原作基本思想內容的情況下,不符合英語語言文化習慣的表達通常會發生改寫,造成原語文本中文化意義的走失、略譯和改寫,或者是以目的語文化范式替代原語文化范式,抹殺了原語文本的文化特色,不利于英語讀者對漢語言文化的理解,甚至會造成對漢語言文化誤解,進而影響英、漢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和溝通。
三、“文化本位意識”在漢英合作翻譯中的意義
1.“西學東漸”—“西化”與“東學西漸”—“東化”—“東學西傳”
“‘西學東漸’—‘西化’”與中西方社會在政治、歷史、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緊密相關,體現了人們對中西方文化之間的關系、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動的實質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動的必然趨勢的逐步深化認識。
“西學東漸”一詞最早出現于191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學東漸記:容純甫先生自敘》(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容宏著,徐鳳石、惲鐵樵譯)中。“近代中國所謂‘西學’,即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總稱,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西方文化,主要指文藝復興以來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歐美文化”。〔18〕胡適于1929年在《中國今日的文化沖突》一文中正式提出“全盤西化”一詞,并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認為我們不僅在物質上、機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會、道德等各個方面都不如人。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大力介紹、引進西方社會文化,為改革開放增添了活力,大大推進了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西學東漸”和“西化”反映了歷史上中西方文化發展之間的對比關系,西方文化在我國的傳播方式以及我國知識分子對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動的認識,一方面體現了我國知識分子利用西方先進知識和文化改造中國社會的理想和愿望,并且為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另一方面卻忽視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和傳播,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失衡。
隨著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以及人們對文化和文化交流活動實質的進一步深刻認識,與“西學東漸”、“西化”相對應的“東學西漸”、“東化”也就應運而生。古代中國高度發達的物質文化奠定了精神文化發展和“東學西漸”的基礎。“根據歷史事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東學西漸’從來沒有中斷過”。〔19〕“絲綢之路”就是物質文化“東學西漸”的典型案例;在精神文化方面,“漢籍之翻譯外傳……根據文獻記載,可以大致定為公元508年與534年之間”。〔20〕近代以來,即使是在“西學東漸”思想占主流的中國文化領域,“東學西漸”仍然沒有中斷過。1921年,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文明輸出”的理念,認為“我們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將我國固有文明輸出”。〔21〕隨著歷史的變革,中華文化在經歷了“西學東漸”、“西化”之后,日益繁榮昌盛,國際地位明顯提高;中華民族對厚重的本民族文化、中西方文化之間共融共生的互補關系和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動的實質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和認識。本世紀初,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積極倡導“文化互補論”,提出“21世紀應該是‘東化’的世紀”,認為“我們中國不但能夠拿來,也能夠送去”。〔22〕
“西方人在傳播推廣自己的思想成果時毫不隱晦,有時甚至后邊是架著槍炮的……我們的文化,是沒有把刀架到別人脖子上逼人就范的基因的。”〔23〕所以,“東學西傳”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了當前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華文化在自我認識、自身文化發展和傳播以及與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流過程中的開放性、自覺性和主觀能動性,并且是在尊重中西方文化之間差異和求同存異的基礎上謀求共同繁榮的發展道路,體現了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平等協作以及世界文化發展過程中中西方文化和諧共生的文化生態平衡。
2.漢英合作翻譯中樹立“文化本位意識”的必要性
“傳統文化曾是中國老百姓的‘信仰’,但這種‘信仰’因為各種原因而不斷被削弱”。〔24〕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和“西化”的思想一直在我國思想文化界占據著統治地位,我國的翻譯活動總體上以文化輸入為主,而文化輸出則明顯處于一種劣勢狀態。長久以來,在這種“西化”的過程中,中華文化中滲入了越來越多的西方文化因素,呈現出一種雜合性特征。在與西方文化的對話中,漢語言文化主體不得不順應西方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而其本身的文化主體意識逐漸淡薄,中華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被逐漸邊緣化。這與“西學東漸”和“西化”過程中中華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接納和吸收恰好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同時也是“西學東漸”和“西化”給中西方文化之間關系發展帶來的一種負面效應,即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的對立與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排斥。由于缺乏中華文化輸出,西方社會缺乏對中華文化必要的了解和認識,再加上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中華文化在西方社會的誤讀就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正常現象,“對于以英語國家和地區為代表的西方世界來說,中國常常是以‘他者’的身份存在;人們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社會中神秘、丑陋、古怪、黑暗的東西顯示出特別的興趣,因此偏愛揭露陰暗面的文學作品”。〔25〕所以,漢英合作翻譯中樹立正確的“文化主體意識”和“文化本位意識”,加大對中華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推介力度,完善推介方法和手段,對于改善中華文化的主體形象,提高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影響和地位,豐富和繁榮世界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四、“文化本位意識”框架下的漢英合作翻譯策略分析
1.樹立正確的文化交流意識:平等、互補、共榮
人類文化之間的傳統共性是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交流和溝通的基礎;不同文化所特有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性特征。漢英合作翻譯要樹立文化間平等、互補、共同繁榮發展的文化交流意識,推進與其他國家和民族文化之間的互動合作,增強弘揚漢語言文化的自覺能動性。要實現漢語言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接軌,必須首先找到人類文化之間的傳統共性,作為漢英文化間平等交流與和諧發展的文化基礎,創造與世界文化接軌的前提條件;并且在尊重漢英文化之間差異的基礎上,增強英語文化對漢語言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轉變英語世界對漢語言文化的認知態度,提高英語文化接受漢語言文化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把漢英合作翻譯當作豐富英語文化和繁榮世界文化的重要途徑。
2.合理選擇文本
Nord Christiane〔26〕將文本功能分為信息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感染功能(appellative function)和寒暄功能(phatic function),并且把“忠誠”(loyalty)原則引入功能主義模式,提出了“功能加忠誠”(function plus loyalty)的翻譯原則,認為“文本功能是使目的語文本按照既定目的在目的語情境中的各功能要素的總和。忠誠指譯者、原語文本作者、目的語文本讀者和翻譯活動發起者之間的相互關系”。〔27〕在當前“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漢英合作翻譯中的文本選擇要按照弘揚漢語言文化、促進漢英文化交流與合作、繁榮世界文化的基本目標,凸顯文本的信息功能和感染功能,選擇能夠有效傳遞漢語言優秀文化信息的文本,并且要合理利用合作翻譯中英語譯者以英語為母語的語言文化優勢,在忠實于原語文本、原語文本作者和漢語言文化的基礎上,協調與目的語文本、目的語讀者和目的語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增強目的語文本的感染功能,忠實、有效地傳遞漢語言文化信息,促進漢英兩種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
3.完善合作方式
依上所述,譯介主體在漢英合作翻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以往的漢英合作翻譯中,要么是以漢語譯者為主體的單向合作,要么漢語譯者在與英語譯者的雙向合作中處于一種從屬地位,只是起到一種輔助性的作用。因此,要提高漢英合作翻譯的傳播效果,增強漢英翻譯在傳播漢語言文化中的功能,必須綜合單向合作與雙向合作的優勢,首先提高漢語譯者的英語語言文化修養,培養對漢語言特有文化的識辨能力和漢英語言文化之間進行比較鑒別的能力;其次,漢英翻譯過程中漢語譯者要樹立正確的漢語言文化主體意識,正確處理翻譯過程中信息功能和感染功能之間的關系,在忠實、有效傳播漢語言文化信息的基礎上尊重英語語言表達習慣;第三,在校譯階段要充分發揮漢語譯者的主觀能動性,突出漢語譯者和漢語言文化的主體地位,發揮漢語譯者的主導作用,凸顯漢英翻譯活動傳播漢語言文化的功能,及時糾正合作翻譯過程中對漢語言文化的誤讀、誤譯。
五、結 語
當前的漢英合作翻譯理應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承擔起傳播中華文化,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與合作,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地位的重任。譯介主體,尤其是漢英合作翻譯中的漢語譯者要樹立正確的文化交流理念,立足于中西方文化平等、互補、和諧發展和共同繁榮的基本觀點,在堅持“文化本位意識”的基礎上,努力改進漢英合作翻譯模式,提高漢英合作翻譯的傳播效果,促進世界了解中國,維護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間和諧共生的文化生態平衡。
注釋:
〔1〕〔17〕王寧、戴維·戴姆拉什:《什么是世界文學?——王寧對話戴維·戴姆拉什》,《中華讀書報》2010年9月8日第22版。
〔2〕〔15〕鮑小英:《中國文化“走出去”之譯介模式探索——中國外文局副局長兼總編輯黃友義訪談錄》,《中國翻譯》2013年第5期。
〔3〕〔8〕〔16〕馬會娟:《英語世界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現狀與問題》,《中國翻譯》2013年第1期。
〔4〕〔20〕馬祖毅、任榮珍:《漢籍外譯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22、29頁。
〔5〕〔7〕耿強:《中國文學走出去政府譯介模式效果探討——以“熊貓叢書”為個案》,《中國比較文學》2014年第1期。
〔6〕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3頁。
〔9〕王佐良:《翻譯:思考與試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年。
〔10〕拉斯韋爾傳播過程模式:美國學者Harold Lasswell于1948年首次提出了“五W模式”或“拉斯韋爾程式”的過程模式,包括構成傳播過程的五種基本要素,即誰(who),說什么(what),對誰說(to whom),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拉斯韋爾:《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年。
〔11〕〔25〕王穎沖、王克非:《現當代中文小說譯入、譯出的考察與比較》,《中國翻譯》2014年第2期.
〔12〕Levef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p.14.
〔13〕Bassnet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3rd ed.).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p.8.
〔14〕Sapir,Edward.Culture,Language and Personality.Berk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6,p.69.
〔18〕郭延禮:《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
〔19〕〔22〕季羨林:《東學西漸與“東化”》,《光明日報》2004年12月23日。
〔21〕蔡元培著、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北大1921年開學式演說詞》,《蔡元培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3頁。
〔23〕陳彥:《理直氣壯講好優秀傳統》,《人民日報》2014年7月8日第15版(文藝評論)。
〔24〕王立群:《傳統文化熱,別只停留在熒屏》,《人民日報》2014年7月17日第5版(文化)。
〔26〕〔27〕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