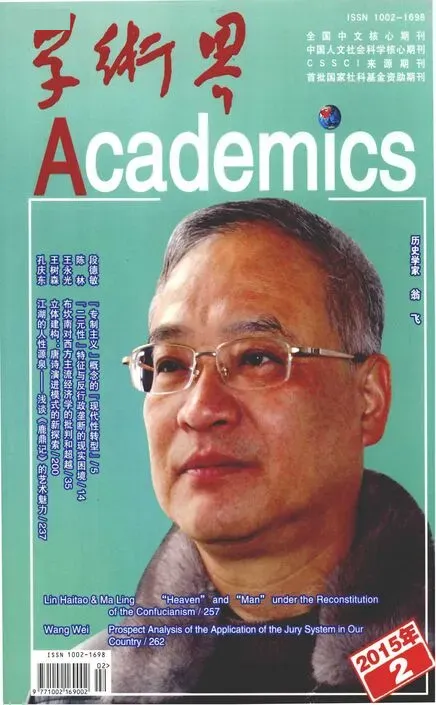“私人執法”是否存在——與徐昕教授商榷
○史永平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2)
一、“執法”與“法律執行”是同一概念嗎
徐昕教授通過《法律的私人執行》提出了“私人執法”的概念,他認為“執法”是“法律執行”的同義詞,而執法又可以分為“私人執法”和“公共執法”。〔1〕不少學者都認同這種提法,有人甚至把“私人執法”當作下一步法制改革的思路。〔2〕然而究竟執法與私人能否統合成為一個概念,首先要考察執法和法律執行的涵義。“法律執行”(也稱為“法的執行”)是一個法學、行政學、公共管理等學科都要大量觸及的概念。然而不論是大眾媒體還是日常生活的其他領域,“法律執行”經常與“執法”的概念混同使用。〔3〕然而,法律執行作為法學研究中一個基本的概念,和日常語義中的“執法”有著本質的區別。
法理學界一般認為,法律執行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廣義上的“法律執行”是國家機關的一切適用法律行使職權的活動。這種廣義的理解普遍存在于媒體報道、民眾討論和一部分法學論述中。正如有學者指出,廣義的法律執行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法律授權、委托的組織及其公職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貫徹實施法律的活動,它包括一切執行法律、適用法律的活動”〔4〕。這種觀點的問題在于把適用法律進行裁判的司法活動和法律執行活動混為一談。西方的現代分權制使得法院屬于司法機關,而不屬于法律執行部門。為何我國普遍存在這種理解?我國法制史、思想史譜系中沒有分權的傳統,而且素來存在“諸法合體”、“諸權不分”的現象,最高統治者即是法律的制定者,同時也是法律的執行者和裁判者。這個傳統的結果是社會中的司法、執法不分,把所有形式的公共權力的部門統稱為“政府”的一部分。即便做出區分,對于司法機關的理解也往往是錯誤的。〔5〕
自啟蒙思想以來,三權分立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設計被大部分西方國家認為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因而分權制度存在于大部分西方政府與社會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念中。隨著現代政治法律哲學的發展與分權思想和制度的傳播,法律執行的另一種狹義觀點逐漸普及開來。〔6〕這種狹義理解則認為,法律執行是政府的重要活動。這種狹義的理解是基于現代政治學中的分權理論而演化的,這個狹義的理解的基本結論之一是,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狹義的政府是專指行政機構的范疇。而法律執行乃是行政機關(狹義的政府)對法律進行推行的總稱。狹義的法律執行也就是行政執法,即不包括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的相關活動,僅指的范疇是法律執行(執法)是國家行政機關、法律委托授權的具有行使權力資格的單位、法人等主體,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執行法律賦予的行政、管理、服務等職權而進行的活動。如前所言,廣義地理解法律執行會造成較大的理論和實踐中的混亂,因而狹義的法律執行是我國主流法學界比較認同的概念。我們認為,法律執行應該僅指行政執法,而不包括法的適用(司法)和法的制定(立法)等活動。現代法治發達國家的政治體制普遍要求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不應混同,而應有一定程度地制約和分離,進而把國會、法院和政府機關看作是獨立的行使各自職權的機構。即便在中國,也有可能和必要區分權力的不同職能、不同屬性。因而我國的法律執行,也必須采取狹義的理解,也就是法律執行是指政府為主的、代行政府行政職能的其他授權機關為輔的行政、管理、服務等活動。〔7〕從這種狹義的理解出發,似乎法律執行本身就等于執法。〔8〕
然而,在何種條件下法律執行和執法是同一概念?在何種情況下是不同的?為何存在這種差異?主要是因為法律執行本身可以對應英文中完全不同的兩種概念。
第一種,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狹義的法律執行,在英文中可以翻譯為law enforcement,此時的法律執行可以簡稱為執法。英語中的law enforcement可以代指以一種(通常來自政府)強制力來確保法律被人們所遵守和法律不被違反的過程。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決定了能擁有強制力去貫徹法律實施的主體主要就是政府機關,而政府中最直接的具有以上屬性(如強制力、懲罰犯罪等)執法活動的最典型、最普遍的情況就是警察機構的活動。因此,在某些語境下執法機關(law enforcement agencies)就是警察機關的代稱。但是在另外一些特殊的語境下,法律執行和狹義的“執法”不是一回事,不能互相轉換。英文中另外一個表達execution of laws是法律執行的另外一種翻譯方式,此時法律執行不能被簡稱為“執法”。西文中的執行(execution)不僅僅涉及成文法的實施,更是一個政治、行政和管理的概念。因此從廣義上說,execution的對象可能是一般的自然人、法人等簽訂的不具有公法效力的法律文件。在法律領域,execution of laws作為法律執行的對象,不是一般的已經生效的法律條文,而是除了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成文法之外,各種規章、司法裁判和仲裁的文書、乃至私人訂立的合同、遺囑等。其二,主體范圍不同,execution的主體不僅限于政府機關。正是由于其對象不僅限于制定法(因為制定法的執法者通常由政府行政機關擔任),而是幾乎所有的生效法律文件。那么私主體之間簽訂的合同、單方訂立的遺囑的執行人資格必定是涵蓋了所有的私主體。簡言之,與law enforcement相比,execution of laws的執行者不單單是指公法上的行政機關,更包括了私法上的一般主體。
二、“執法”與“法律執行”是等同的概念嗎
以上分析得出,西文中從狹義上理解的law enforcement可以翻譯為執法,但是并不兼容私主體。只有當執行者作為executor時,可以屬于私人或者私法上的主體,這里我們還能否翻譯為“執法者”呢?我們認為不應當混同兩種翻譯,應當嚴格區分作為“enforcer”的執法者和作為“executor”的執法者。因為“執法”一詞的本意中也包含著國家職能和國家強制力的因素。如果非要把執法理解為“對法律的執行”,那么顯然“執行”是“執法”的上位概念。根據“屬”加“種差”的邏輯學概念定義,那么執行是執法概念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換言之,屬于執法行為必然也是一種執行,然而“執行”的行為卻未必屬于“執法”。諸如私人之間訂立、履行合同的行為、遵守法院判決的行為,可以視為對法律文書的“執行(execution)”,但是這種私人間的行為卻未必能稱之為“執法”。如前所言,“執法”的本質在于其強制性而不是執行性,因而本意是enforcement而非execution。與公法上的法律執行(law enforcement)相比,execution of laws更應該翻譯為“法律文件執行”或者“法律相關執行”,并且execution of laws不能簡單成為執法。當執行者(executor)屬于私人或者私法上的主體時,就不宜翻譯為執法者。因為執法者這個概念之中包含著國家職能和國家強制力的因素。這種私主體對私人訂立的法律文書的執行行為當然可以稱為“合同執行”或“遺囑執行”,抑或是私人對法院判決的執行也可以叫做“判決執行”。但是無論是“合同執行”或“遺囑執行”或者私人的“判決執行”,都不能也不應簡單的翻譯為“執法”。
漢語中固有的執法含義也不能兼容私主體的范圍。“執法”本是漢語固有之詞匯,中國語境下的執法有“執國家之公器”的含義。《說文解字》記載:“執(執的繁體)者,捕罪人也。從丮從幸,幸亦聲”。可見執法最早的含義中就有代表國家機關逮捕審判犯罪之人的意思。“丮”是掌握的意思,是一個象形字,其形狀類似于用手去把握某種東西(“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可見漢語中“執法”者,并非簡單的遵守法律,而是秉持一國之公器,執掌法令,代表國家伸張正義的公共行為。可見,中國文化中的執法有兩個特征,其一是執法的對象是國家法律,而不是一般的私人意志,所以執法的主體也必須是代表國家的執掌國家公權力之人。其二,執法具有一定懲罰性、強制性。由于我國古代之法律體系呈現“民刑不分、以刑為主”的特點,執法實際上主要是指刑法上的執行,尤以“捕罪人”為代表。所以,執法和執法者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是“公法”的概念,并不是私人行為和私法上概念。諸如私人之間訂立、履行合同的行為、遵守法院判決等行為,雖然在現代管理科學中可以視為對法律相關的“執行”,但是這種私人間的行為卻不能在中國語境下簡單等同于“執法”。
由以上分析可知,“私人”與“執法”是一對矛盾的概念。因為執法概念之中包含著國家職能和國家強制力的因素。而私主體對私人訂立的法律文書的執行行為當然可以稱為“合同執行”、“遺囑執行”甚或“判決執行”。但是無論是“合同執行”“遺囑執行”或者私人的“判決執行”,都不是公法意義上的“執法”。
三、“私人執法”概念之內在矛盾
必須承認,“私人執法”是一個較少有提及的領域,確實,徐昕教授提出的“私人法律執行”在學科內部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徐昕教授認為“私人執法”的概念對應的英文翻譯是private enforcement of law,并在西方的文件中得到了全面、確實的研究。〔9〕
《執行》一文在一開始就斷定,私人執法(private enforcement of law)和公共執法(public enforcement of law)是執法的兩種形式、兩種類別。〔10〕但是否西文中幾篇論文就足以構成概念的科學依據?這種提法本身是否符合科學概念的規律?如前文所述enforcement of law這個詞語在西文中早已經有明確的概念,是指以一種(通常來自政府)強制力來確保法律被人們所遵守和法律不被違反的過程。這里的enforce是指借助強力和強制手段來推行法律。實際上,西方的法學家也不否認enforcement of law確實需要政府作為強制力的保障,只有國家和公共領域的權力才能有效地推進法律執行。因而執法在總體上是一個公法的概念,執法的推進離不開其本質屬性中的公共性(publicity)。〔11〕另外enforcement這個詞本身就具有-force-這一詞根,表明了其中蘊含了“力”這一基本元素。法律執行中所蘊含的力的要素,與法律本身所具有的國家強制的性質是一脈相承的。〔12〕實際上,波斯納(Posner)之所以強調private enforcement of law這樣一個標題,并非是他沒有認識到法律執行與國家強制力的內在的、本質的關聯,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觀察到了這種關聯,所以在討論一些特殊現象時才不得不加上private這樣一個特殊的冠詞來加以修飾。
《執行》一文中對私人執法的舉例還說:“在當代法律制度中,公共執法和私人執法實際上混合交錯。私人為預防違法犯罪的自我保護行為,如雇傭私人保鏢,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公共執法之替代。”〔13〕但是《執行》一文卻沒有解釋清楚:為何雇傭私人保鏢是公共執法之替代呢?為何“私人保鏢”屬于執法行為呢?私人保鏢的主要目的是保護自我的財產安全,和“公共執法”本來就是涇渭分明、公私有別。所謂的“預防犯罪”只是雇用私人保鏢的一個間接的、附帶的社會效果,其本質還在于“自我保護”,即所謂的自衛權(這里的保護既包括財產安全也包括人身安全)。實際上人人都不希望犯罪發生在自己身上,并盡力避免之。〔14〕那么這里的“自衛權”(或者自我財產保護權)是純粹的公權嗎?這里存在兩個可能性:其一,作者認為自衛權或者保護自我的人身安全之權利不是私權,私人沒有保護自我財產的權利,因為自衛權只屬于公權力“公共執法”范圍,那么當雇傭私人保鏢時,這種公共執法的“權力”就被替代了。假使自衛權只是公權才有的權能,私人無權行使自衛權的話,雇傭私人保鏢就屬于不可能被允許的行為、就成了徹頭徹尾的違法行為。顯然,這個假設是荒謬的,一個違法行為本身就是法律所禁止的行為,不可能被國家法律所承認,更不能稱為“執法行為”。又何來“公共執法之替代”一說呢?其二,作者或許又認為自衛權是一個開放的概念,不完全屬于公權也不完全屬于私權,可以視不同的行為主體產生不同的性質變化。換言之,作者一定認為保護自我的人身安全之權利乃是一個“部分的”私權。〔15〕但此時“自衛權”本身就是可以由私主體來行使的,其法律性質和公共執法屬于并行不悖、互不干涉之關系。國家執法是國家職能,私人保護財產也是權利所在。那么此時也更不可能存在所謂“公共執法之替代”,因為這時雇用私人保鏢本身和“公共執法”分屬于兩種性質的行為,并且在法理上可以分別地、獨立地存在。總而言之,不論其作者接受了哪種邏輯,都不可能得出“雇傭私人保鏢,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公共執法之替代”這樣的結論。
《執行》一文的本質問題,在于認為私力救濟就是“私人執法”。“私力救濟”的歷史意味著早在啟蒙思想之前國家普遍承認私人執法的存在,這個歷史出發點本身沒有問題。〔16〕但是在現代法律發展和現代性的政治理論已經把執法權收歸“國家”的前提下〔17〕,現代的法制譜系中私力救濟還是否等于“私人執法”?“私力救濟”和“私人執法”到底有無區別?我們發現《執行》一文認為并沒有區別:“私力救濟者亦可視為私人執法者,只是私人執法從法律執行角度保護權利,而私力救濟則從權利保護角度關涉法律執行。”徐昕教授認為二者并無本質之區別,只是關注的角度不同而已,是對同一種現象的不同描述。
然而在現代法治語境下,私力救濟和私人執法有著本質的區別。盡管二者都涉及“私人”這一概念,都不借助于國家強制力的實施,二者仍然存在重大區別:私力救濟乃是國家承認的合法的行為,而私人執法(就徐昕教授所舉的例子看)則往往屬于非法行為;私立救濟乃是維護私人合法權利的行為,而私人執法往往超出合法權利的界限導致損害他人權益;私力救濟往往運用非強制手段達成其保護權利的目的,如協商、調解、私人仲裁或者委托“私人或民間組織機構”等〔18〕,而私人執法則使用強制、暴力和脅迫性手段達成其目的,如黑社會性質組織、強制扣留拘禁乃至私刑等等。
從徐昕教授所舉的外延和我們對執法內涵分析可以看出:私人執法(enforcement)的癥結不在于其私人性,而在于其代替國家機關的使用暴力(forcibly)性。實際上,《執行》一文中的“私人執法”如果也是“執法”,那么“執法”作為上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國家強制力因素,離開了國家強制性本身那又何談“私人執法”呢?我們看到,《執行》一文中所舉的例子諸如“私人討債者”、“商場搜身”和“私人刑罰”都被視為所謂的“私人執法”。〔19〕由此種種,似乎私人采取暴力解決問題就是“私人執法”。但是,“執法”雖然具有暴力的特征,但是單純的暴力卻不足以構成執法。《執行》一文也認同主流的執法概念是,國家司法、行政機關及執法人員依法定職權范圍和程序將法律規范適用于現實的社會關系之活動,但這些活動除了暴力性之外,一定還有一個“合法性”或者“有效性”的本質內核。而《執行》一文中的例證是否合法、有效,本身就值得討論。
四、“私人執法”的社會解讀:一場誤讀
《執行》一文的最后還重點介紹了“私刑”作為私人執法的一個歷史例證和歷史解釋。在這一章的開頭作者就說到:“私刑,即無懲罰權的人對他人非法施加懲罰。”〔20〕然而奇怪的是作者在其后的章節中又說道:“私刑也不見得一概非法”,因為“此種處罰使用的強力在合理范圍內,屬合理的私人執法……。”〔21〕這里徐昕教授似乎又把部分的私刑歸為兩類,一種是非法的,另一種屬于合理合法的范疇。至此我們要問到底“私刑”是合法行為還是非法行為?“無罰權者”的懲罰又怎么會是部分地合法呢?仔細看其中所舉出的例子不難發現,實際上作者混淆了“一般的教育手段”和“刑罰”的區別。首先要確定的是,作者所言的私刑首先必然是“刑”,也就是具有一定程度“刑罰”。但是,后文中所舉出的例子中,而無論是“父母對子女的輕微責罰”、“領導批評”還是“老師責令學生留校反思”等等這些行為固然是合法的懲戒措施,但是卻絕對夠不上“刑罰”的標準。
此外并非所有的懲戒措施都屬于“刑罰”,只有“刑罰規定的由特定機關限制或者剝奪一定權益為內容的強制性制裁方法”。〔22〕《執行》一文中所提到的“父母對子女、學校對學生執法手段若超出相當性,也為法律禁止”,那么一般的“管教”、“管理”和“刑罰”是否只是量的區別,沒有本質差異?這里恰恰是有著重大的區別:首先,刑罰的對象一般只能是成年人,或者已滿十四周歲以上的犯有特殊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而管教的對象往往是年齡較小的,不具備完全的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其次,二者的程度、效果不同,被管教、管理的對象仍具有選擇權和自主性,其所受的輕微懲罰不是剝奪性的,當事人仍然可以不服管教或者管理乃至選擇離開,而刑罰卻是剝奪性的強制性的,受到刑罰的人沒有任何選擇余地。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刑罰只能以國家強制力和《刑法》規定的程序和形式來實施,不得任意濫用。例如我國《刑法》規定的,刑罰的形式只能是剝奪生命的死刑和剝奪人身自由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附加刑還可能有剝奪財產權和政治權利的“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可以獨立適用),驅逐出境”。以上就是我國《刑法》所規定的刑罰的全部形式。《刑法》之外的其他的任何形式的限制、剝奪他人合法人身、民主權利的行為都屬于非法行為乃至犯罪行為,例如教師和父母均不可毆打未成年人,領導談話也不能以強制拘禁的方式進行。盡管我國社會習俗和傳統因素等導致一些政府沒有及時介入未成年人的權益受損案件,但這種現象的存在絕不意味著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侵害是合法的。〔23〕實際上,不僅私人不能使用刑罰,連國家公務機關的人員也不能非經法定審判而適用刑罰,刑訊逼供、非法拘禁等也是絕對不被允許的。顯而易見,《執行》一文中所舉的那些“合理私刑”的例證本身連刑罰都不是。
退一步說,如果作者認為傳統意義上的私刑是可以非經國家、非經特定機構、非經法定程序的前現代概念,那么至少也應該具有“強制性”和“制裁性”這兩個任何時代都必須具有的“刑”之特征。我們也承認,我國古代社會一度存在“私刑”,并且認可某些私人之間施加刑罰的合法性。例如:古代的父母對不合行為規范的子女有權進行懲罰,《唐律疏議》中還規定:“教令違法……不合有罪。”也就是父母在對子女施以管教的時候如果發生了不符合法律的行為,也不會按照犯罪來處理。〔24〕但是即便是古代的私刑也必須有“強制性”,即被刑罰的主體沒有選擇不受刑罰的權利,二是“制裁性”,即子女也必須受到足以損害其基本權利的嚴厲懲罰。盡管古代社會的某些場合下,諸如家長、族長等“私人”(更多的應理解為非國家主體)可以任意地剝奪他人權利乃至施以刑罰,但是作者認為那些所謂“現代私刑”實際上并不具備這些特征。
現代社會的大多數國家不僅廢除了肉刑,而且都把執法權收歸了國家,而且以一種近乎壟斷的方式排除了私人作為刑罰的實施者的可能性。實際上,該文作者也承認,“在一般觀念中,執法指國家司法、行政機關及執法人員依法定職權范圍和程序將法律規范適用于現實的社會關系之活動,私人除作為執法對象和守法外,與執法毫無關聯。”〔25〕實際上在一個法治社會中,任何刑罰都只能由國家法定的機關經過法定的程序并于公平的審判之后方可執行。而法律執行作為一個現代的法學概念,無法也不應該容納“肉刑”、“私刑”這樣的前現代行為。〔26〕《執行》一文的一大本質矛盾,是“私人執法”作為科學的法律概念如果能夠存在,則必然要排除非法行為。任何執法行為如果要產生(正面的)法律效果,就必須遵守國家法的強制性規定。
換言之,任何的執法行為首先需要的是合法行為,不能是非法行為。否則,各種犯罪行為、侵害他人人身和財產權利的行為就被包括進“執法行為”來。這種將“非法行為”同“執法行為”混為一談的觀點,不僅將與“執法”概念本身的合法性要求產生嚴重沖突,而且如果把一些非法的暴力行為(有時披上維護權利為目的外衣)都稱之為“執法行為”的話,那甚至有美化犯罪行為的嫌疑。《執行》所舉的其他例證如:民間收債人、私人偵探、“私人通緝令”和“私人罰款”等類別,也很難說不是非法行為。此文中的大部分例證都涉及所謂“利用非法手段來達至合法目的”,有的甚至連合法的目的都談不上,而我們知道即使是為了維護權益而使用非法行為也是被禁止的。比如,實現債權是合法的,而使用暴力脅迫則是非法的,故此雇傭黑社會使用暴力來討“本屬于自己的債”仍屬于非法行為。更不用說,雇傭私人偵探等行為的目的往往就是刺探他人隱私、乃至竊取他人的商業機密的非法效果。
在《執行》一文中,作者的“私人執法”的例子還有“私人搜身”。所謂“私人搜身”往往是指商場等主體由于懷疑當事人盜竊而采取的搜身、限制人身自由的行為。但是其本質是非法行為,“商場無權對消費者實施搜查行為或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動用私刑。”〔27〕我國《憲法》第37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商場既非公安機關,也沒有經正當程序的授權,自然不可能有“搜身權”,但就是這樣一個明顯違法的例子,卻被《執行》一文當作私人執法成立的證明。
五、余論:“執法”的后現代解讀
正如“私人執法”的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問題一樣,《執行》一文其作者的態度是矛盾的,也是負責的,但是總體的論證過程仍然不盡人意。我們必須承認,徐昕教授的出發點是好的,不難看出徐昕教授的本意是:私人執法是避免公權力的過度擴張,保障私人權利的必要手段。真如其所言“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公權力不可能也不必要壟斷一切事務。”〔28〕誠然,公權力的過度擴張甚至取代私權利是社會的災難,同時也會造成嚴重的集權后果。我們相信限制公權仍然是現代社會中需要大力研究的一個課題。
然而,一個預設的好的出發點,并不一定能經受科學概念的檢驗。《執行》一文的“私人執法”理論試圖通過歷史的、前現代的種種例證,說明“私人執法”有利于限制權力,但是這種對前現代的社會現象(如私刑)的“同情”的理解反而使得作者沒有看到其“前現代”的本質。急于否定“執法”的現代性特征,反而使其陷入了“無法無天”的后現代泥沼。正如有些后現代理論認為現代的國家建構是暴力、集權的象征,只有原始的自然狀態是理性場景。〔29〕或許諸如“私刑”的這種沒有國家強力干涉的“自然狀態”確實有助于我們理解自身,但是“非國家性”的代價也是必然聯系著野蠻性、暴力性、非理性等因素。顯然,這種樸素的甚至原始的制度不能成為現代法治和權利保障制度中的一種可行性答案。現代的“國家性”固然值得警惕,但也不可不見其“理性主義”和“現代性”的本質內核。實際上,現代法治國家還沒有哪個能放下國家性的框架,而把“執法”的權力再度回放到私人手中。
《執行》“私人執法”的概念持有者始終把政府壟斷的“執法權”視為法治的頭號天敵,并認為:“我國長期偏好于行政管理式的執法,以國家處罰和制裁作為重要治理術,試圖通過公共制裁實現法律的目標,較少考慮是否必要、可行、能否真正執行,或者未考慮調動私人與國家共同執法的可能性。”但是,《執行》一文卻沒能提供一種可行的、具體的替代方案。即便例舉了“私人執法”的例證,也恰恰是反應了法治倒退而不是進步。
實際上,執法權的壟斷是現代法治的特征,只有前現代的社會、后現代的理論中才存在執法權的分散。現代的框架下,不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各地,執法權統一歸于政府正是法治的體現,執法權的散亂分布才是法治混亂的標志。如果說現代社會的標志是公權與私權的各司其職、界限分明,那么我們反對的就不只是用公法取代私法,也必須反對用私法取代公法。正如《論自由》最早被嚴復先生翻譯為《群己權界論》一樣,現代社會中自由之保障在于公私權界的分明。“私人執法”這一概念所危害的,恰恰是公私權之間的明確分野,造成了私人行為闖入本來由國家機關行使的公共權力空間。
徐昕教授所擔心的公權力侵蝕私人領域乃至取而代之的現象固然不利于自由的保障。但是反之,私權濫用暴力乃至借用“執法”之名冒充公權而侵害他人權利的現象如不加制止,則普通人尤其是弱者的自由將消失殆盡。須知,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侵權案件、犯罪案件不是發生在政府與私人之間,而恰恰是發生在私主體之間,而導致這種侵害之所以不斷擴大和持續的原因,往往不是政府的行為不當而是政府的不作為。〔30〕“權利不可侵犯”這一概念,不僅是對政府越權行為的限制,更看重的是限定權利時必須經過“正當程序(due procedure)”,《執法》一文沒有回答、但是又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結果是“私人執法”從其本質而言,不可能具備這種正當程序,因而無法保證其不被濫用。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現代社會必然是公私領域分明的社會,公權力不能取代私人的領域。同時,對他人私權的尊重也必然要求即便是私人在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時不得未經法定程序而使用暴力乃至越俎代庖。
注釋:
〔1〕〔9〕〔13〕〔19〕〔20〕〔21〕〔25〕〔27〕〔28〕徐昕:《法律的私人執行》,《法學研究》2004年第1 期。
〔2〕近年來認同“私人執法”這一概念并對其進行探討的論文還有:丁國峰:《反壟斷法私人實施的法理基礎和具體路徑》,《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王虎,李鋅淦:《整體主義視野下我國食品安全私人執法模式研究》,《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夏藝菡:《論美國反托拉斯法私人執行制度對我國執法的啟示》,《當代經濟》2011年13期;萬宗瓚:《法經濟學視角下的“私人執法”》2012年第13期。
〔3〕例如,在體育賽事中,居中裁決裁判的行為也被大量的稱為“執法”或者“比賽執法”。
〔4〕張文顯主編:《法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4頁。
〔5〕直到現今,我國社會仍然普遍地把“公、檢、法”統稱為司法機關,而不是分別看待。
〔6〕張文顯、李龍、舒國瀅、公丕祥等人分別主編的四個不同版本的法學教材都堅持以“狹義”的執法為準。
〔7〕這里就產生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國法院中所謂“執行庭”是司法機關還是執法機關?我們認為,法院中執行機構應當屬于執法機關。因為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的分野,不是取決于機構名稱(執行庭聽上去像是法院的一個特別法庭),也不是取決于其所處的地點或者直屬上級機關的性質。而取決于其功能,例如聽上去是立法機關一部分的“全國人大安全保衛處”,實際其功能明顯不是立法,而是某些行政功能——如保衛安全、設立巡邏、懲治犯罪等,所以它即使設立在全國人大的辦公系統內部,地點也在全國人大的公共地點,它仍然不是立法機關。同樣的,法院的執行庭并非運用法律進行裁判的機構,而是執行已經生效的法律判決的機構(正如監獄是執行眾多刑事法律判決的機構),即使它的設立是在法院內部,它仍然不屬于司法機關。
〔8〕我國雖然不奉行三權分立的制度,但是在制度的設計上,我國也把法院、檢察院為代表的司法機關、國務院及各級政府代表的行政機關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立法機關看作是分別行使各自職權的機關,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屬性。例如,雖然我們不提倡司法獨立的口號,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四條都明文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由此可見,盡管我國并不奉行三權分立或者司法獨立原則,但是政府作為執法機關的職能確實與人民代表大會和法院有著明顯的區分。
〔10〕William M.Landes and Richard A.Posner,The Private Enforcement of Law,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4,No.1(Jan.,1975),pp.1-46.
〔11〕Francis E.Rourke,Law Enforcement through Public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24,No.2(Winter,1957),pp.225-255;Bruce Smith,A Preface to Law Enforcemen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291,New Goals in Police Management(Jan.,1954),pp.1-4;Ray Erwin Baber,Factors in Law Enforcement,Social Forces,Vol.8,No.2(Dec.,1929),pp.198-208.
〔12〕孫國華:《法是“理”與“力”的結合》,《法學家》2001年第3期。
〔14〕作者似乎想通過一組三段論來自我證成。大前提:通過公法意義上的“預防犯罪”是政府公共職能,然后小前提:雇傭保鏢屬于“預防犯罪”,來證明結論:雇傭保鏢屬公共職能。但是我可以明確地說,雇傭保鏢不是公法意義上的“預防犯罪”行為。雇傭私人保鏢雖然不利于犯罪的發生,但是并不是對社會整體的犯罪預防,因為其既不具備社會意義上的“預防犯罪”這種目的,也與公安機關的作為國家治安機關對社會整體安全負責同時預防犯罪的職能范圍不同。私法上的民事行為往往會帶有保護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目的,但是并非所有類似這樣的不利于犯罪發生的行為可以界定為公法意義上的“預防犯罪”,正如購買防盜門可以預防盜竊,但我們很難說:“購買防盜門”的行為已經不單單是民事行為,而是代替政府在“預防犯罪”。
〔15〕為避免邏輯的荒謬性,并根據此文的上下文來判斷,我們認為第二種可能性更大一些。
〔16〕〔17〕賀海仁:《從私力救濟到公力救濟——權利救濟的現代性話語》,《法商研究》2004年第1期。
〔18〕范愉:《私力救濟考》,《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22〕馬克昌:《刑法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8頁。
〔23〕史永平:《當代中國親權制度的倫理基礎及其現代走向》,吉林大學2011年碩士論文。
〔24〕史永平:《家長權的現代遺存——一個法制發展史的視角》,《理論界》2014年第11期。
〔26〕“肉刑”就是傷害人的肉體的刑罰,是一種嚴酷而原始的刑罰手段。我們之所以把“肉刑”和私刑并列,乃是因為二者在傳統社會中處于一種“共生”的狀態,即私刑往往都以“肉刑”的方式進行。
〔29〕Victor Tadros,Between Governance and Discipline:The Law and Michel Foucault,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18,No.1,(Spring,1998),pp.75-103.
〔30〕例如,屢禁不止虐待和遺棄未成年人現象,往往起因于此。李超、畢榮博:《從未成年人保護看國家監護制度的構建》,《青少年犯罪問題》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