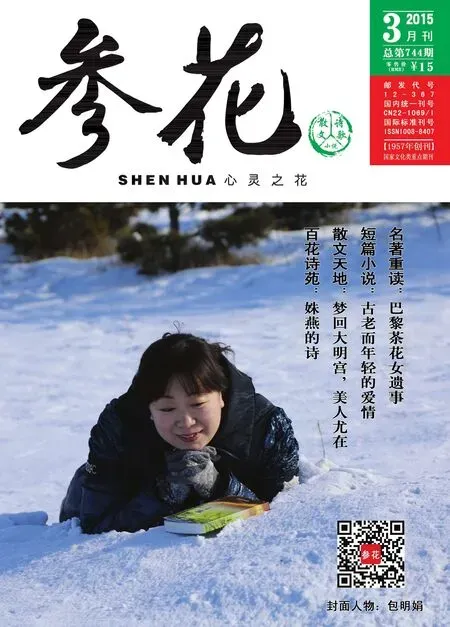魯巳己
◎王彥耘
魯巳己
◎王彥耘
魯巳己是“四和園”酒館的常客。
最早,這是個(gè)茶館,是由四個(gè)回族人合伙開(kāi)的,起名“四和園”。“四和園”的干貨,做得很地道,有吊爐干貨、小爐干貨、油炸干貨、蒸鍋干貨。吊爐干貨有各式月餅、大小提江、半月兒、雞焙子;小爐干貨有白饦、干墊兒、鍋盔、油旋兒、五香焙子、糖三角兒、擦酥焙子;油炸干貨有油餅、麻花、麻葉兒、油折子;蒸鍋干貨有:現(xiàn)蒸饃、干酥饃。可惜,這些傳統(tǒng)小吃后來(lái)沒(méi)了。原因是,“四和園”改為了大眾飯館。改大眾飯館后,二掌柜、三掌柜、四掌柜覺(jué)得沒(méi)意思,就抽股而退剩大掌柜馬海濤一人支撐。馬海濤讓廚子做燴菜,白菜,豆角,土豆,豆腐,粉條。有時(shí)候也做燴酸菜。在后面做好,用大盆端出來(lái),在堂口上賣(mài),一塊錢(qián)一碗。沒(méi)肉,放少量素油。主食是饅頭,米飯。到改革開(kāi)放,八十年代中期,馬海濤把“四和園”大眾飯館,改為“四和園”酒館。門(mén)臉兒做了裝修。還做了一個(gè)食品柜,擺涼菜。涼菜很豐富,炸花生豆、帶皮五香花生;雞爪、雞胗、雞翅膀、熏雞、腌雞蛋;醬牛肉、羊頭肉、羊蹄子、羊肝兒、羊腦子,粉皮、米涼粉。菜類(lèi)有,芋頭絲、黃豆芽、豆腐皮、豆腐干、小蔥拌豆腐,主食是燒麥。
燒麥的主料羊肉,選的是達(dá)爾罕茂明安聯(lián)合旗草地上的綿羊肉。是剔了筋頭巴腦的。面粉,選的是巴盟小麥特制精粉。輔料,蔥,選的是沙爾沁大蔥;姜,選的是上好的姜。用本地產(chǎn)的純胡麻油拌餡。醋,選的是山西榆次西特老陳醋釀造廠生產(chǎn)的老陳醋。
這燒賣(mài),真材實(shí)料,但價(jià)高。別的館子,三塊錢(qián)一兩的時(shí)候,“四和園”的燒麥,一兩,五塊。提過(guò)幾次價(jià),從五塊,八塊,十塊,提到十二塊。每次提價(jià),都沒(méi)有影響“四和園”燒麥的聲譽(yù)和它的火爆。每天6點(diǎn)30分開(kāi)門(mén),6點(diǎn)45分就有客了。大都是一些老顧客。7點(diǎn)半以后,人就越來(lái)越多,來(lái)晚沒(méi)座,只能等。有些老顧客很自覺(jué),吃好,喝足,騰地方,走人。有些就不那么自覺(jué),吃完,喝足,蹺二郎腿,叼根煙坐那里海聊。尤其是那些吃“硬早點(diǎn)”的,特能耗。一兩燒麥,三兩燒酒,坐那里慢慢地啜、嘬。耗兩三個(gè)小時(shí)是常有事。
“四和園”酒館早晨火,中午淡,晚上,不火也不淡。晚上來(lái)客,大都是些酒徒,酒友。比如,大眾浴池修腳的老王頭,新時(shí)代理發(fā)館的李師傅,毛毛匠張小撓,豆腐王李海龍,每晚必來(lái)。這些老主顧,來(lái)的時(shí)間不一樣。大眾浴池修腳的老王頭,每晚七點(diǎn)過(guò)十分準(zhǔn)到。要兩羊蹄子,一碟花生米,三兩酒,坐那兒慢慢喝。他抽煙,一根接一根地抽。毛毛匠張小撓,豆腐王李海龍,八點(diǎn)同時(shí)來(lái)。坐一張桌,喝同一種酒,都喝本地產(chǎn)的散白酒。這倆喝酒也慢,喝酒快點(diǎn)的數(shù)新時(shí)代理發(fā)館的李師傅,他一兩的杯子一口一個(gè),能喝七八兩。下酒菜是羊頭肉,每次都約半斤。八兩酒,半斤肉,一會(huì)兒就完了。喝完酒,吃光肉,拿根牙簽,走人,邊走邊剔,從來(lái)不在酒館耗時(shí)間。
有一個(gè)人特能耗,他叫魯巳己。中午晚上來(lái)。一日兩餐都在這里。中午,二兩燒麥,半斤白酒。喝的也是散酒。晚上,改為一兩燒麥,半斤白酒。偶爾,要半個(gè)羊腦子,下酒。他是個(gè)老師,是本鎮(zhèn)二中的語(yǔ)文老師。小鎮(zhèn)上的人,有一半人認(rèn)識(shí)他。他五十多歲,胡子拉碴的,不修邊幅。教了半輩子書(shū),一點(diǎn)也不像個(gè)老師,倒像個(gè)老農(nóng)。他總是悶悶不樂(lè),從不與人交談。
一天,我突然產(chǎn)生了想過(guò)去跟他攀談的念頭,就端著酒和下酒菜過(guò)去了,他警惕地瞅了我一眼。我做了自我介紹,他也不與我搭訕。我說(shuō),張清河是我的朋友(張清河也是二中老師)。他臉上立刻現(xiàn)出了一點(diǎn)暖色,我伸出手來(lái),說(shuō),認(rèn)識(shí)一下吧,多個(gè)朋友多條路。他勉強(qiáng)地伸出手來(lái),我握了他的手。他手很粗糙,粗糙得像一位剛從田地里干完活的老農(nóng)的手。疙疙瘩瘩的,滿(mǎn)手老繭。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一個(gè)教書(shū)先生竟有如此粗糙的手。
我說(shuō),聽(tīng)清河說(shuō),在學(xué)校你是教語(yǔ)文的?
他答,嗯。
我問(wèn),教幾年級(jí)?
他答,一年級(jí)。
我問(wèn),一天上幾節(jié)課?
他答,三節(jié)。
我又問(wèn),還有其它課嗎?
他回答,沒(méi)有。
回答的簡(jiǎn)單,讓我尷尬的快要窒息了。我掏出煙,遞他一支,他接了。一看是“中華”,沒(méi)抽,把它夾在了他的耳朵上,抽他的“黃山”。我跟他喝酒,他沒(méi)拒絕。幾杯下肚,他臉上出現(xiàn)了潮紅。我沒(méi)話(huà)找話(huà),跟他聊天,他還是問(wèn)一句答一句。我有點(diǎn)失望。就在我想找個(gè)托詞離他而去的時(shí)候,他突然把座椅往我跟前挪了挪,臉上顯出興奮的樣子,說(shuō),您是名人,又是名記,認(rèn)識(shí)的人肯定不少。您能不能把我兒子弄到漠南?我兒子是漠南師范學(xué)院畢業(yè)的,他很優(yōu)秀。給他找個(gè)中學(xué),小學(xué)也行。
我說(shuō),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再說(shuō),教育系統(tǒng)我也沒(méi)認(rèn)識(shí)的人。
他說(shuō),這沒(méi)關(guān)系。你是記者,認(rèn)識(shí)的人肯定不少。人托人,攻死人。關(guān)鍵是看您想不想給辦。想給辦,把這事擱記在心上,肯定能辦成。兄弟,您要是真的給我把這事辦成了,我不會(huì)虧待您的。
他把“您”字說(shuō)得很重。
我不想騙他,誠(chéng)懇地對(duì)他說(shuō),不是我不想辦,確實(shí)我沒(méi)那個(gè)能力!
他說(shuō),能力您有。只是我們的關(guān)系還沒(méi)處到那個(gè)份上,您說(shuō)是不?咱們慢慢來(lái),一回生,兩回熟嘛!我是個(gè)實(shí)在人,慢慢您就了解了。不瞞您說(shuō),昨個(gè)兒晚上,半夜,我夢(mèng)見(jiàn)我老爹了。他現(xiàn)身在我床前,跟我說(shuō),孩子的事兒你不要急,有貴人相幫呀!早晨起來(lái),我還琢磨來(lái)著,這貴人是誰(shuí)?
說(shuō)到這里,他停頓了一下,掩飾了一下他的窘態(tài),然后說(shuō),真的,我爹去世好多年,有八年了,從來(lái)沒(méi)夢(mèng)見(jiàn)過(guò)他,昨個(gè)兒晚上,我不僅夢(mèng)見(jiàn)了他,他還托夢(mèng)與我……
我聽(tīng)后,哭笑不得。
這段對(duì)話(huà),是我今年春季有事,回我的小鎮(zhèn),在“四和園”第一次與他見(jiàn)面,發(fā)生的。
事后,我了解了他的情況。他原來(lái)是個(gè)回鄉(xiāng)知青。1977年,國(guó)家恢復(fù)高考,他考上了漠南師范專(zhuān)科學(xué)院。畢業(yè)后分配到二中,不久就結(jié)婚了。他老婆薛梅花,本鎮(zhèn)人,潑悍、刁鉆。有點(diǎn)像魯迅先生筆下的“康大叔”。婚后兩人感情不和,常打架。他打不過(guò)他老婆。不久,他就染上了不良嗜好,開(kāi)始嗜酒。他幾乎每天都是醉醺醺的。越這樣,薛梅花就越瞧不上他,變本加厲地找借口跟他吵,跟他鬧。甚至不讓他上床睡覺(jué)。讓他到外屋去睡。漸漸地,他變得習(xí)慣于逆來(lái)順受,不出怨言了。結(jié)婚七八年,他們一直沒(méi)孩子。后來(lái),抱了一個(gè),是個(gè)男孩兒。孩子長(zhǎng)大后,很愛(ài)學(xué)習(xí)。后來(lái),孩子以?xún)?yōu)異的成績(jī)考上了大學(xué)。也是漠南師范專(zhuān)科學(xué)院。這讓他的生活充滿(mǎn)了希望。原以為孩子畢業(yè)后,他能提前退休,讓孩子接他的班。沒(méi)想到,孩子畢業(yè)了,政策卻變了,不讓提前退休。沒(méi)辦法,他托人花了三萬(wàn),把孩子安排進(jìn)二中附小。代課,是零時(shí)工。
我的朋友張清河說(shuō),這魯老師太窩囊!好幾次去他家,碰巧遇上吃午飯,你說(shuō)他有意思不,在自己家吃飯,不說(shuō)理直氣壯地坐在飯桌前吃,端著個(gè)飯碗圪蹴在門(mén)口吃。他咋能這樣呢?老婆再厲害,那也是你的家呀?我就不信,你理直氣壯地坐在飯桌上吃,她能不讓你吃?唉,這人呀,太老實(shí)就是不行!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你說(shuō),他工資又不少,每月五六千元掙,咋就那么低三下四?
我說(shuō),這是性格。有一種人,天生就懦弱。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部小說(shuō)《窮人》,里邊就描寫(xiě)過(guò)一位老人——老波克羅夫斯基,就是由于妻子潑悍而痛苦,染上了不良嗜好,每天醉醺醺的,那作派跟他差不多。
我問(wèn),這魯巳己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我朋友說(shuō),有,肯定有!要不,他老婆怎么那么不待見(jiàn)他?
我理解了。唉!這男人啊,在那方面不行,確實(shí)是一件令人尷尬的事!
我對(duì)魯巳己產(chǎn)生了同情。從那次我們倆對(duì)話(huà)之后,我回到漠南。不久,正好我大學(xué)的一位同學(xué),榮升漠南市教育局副局長(zhǎng)。有一次,我們聚會(huì),在抽煙喝茶的功夫,我就趁機(jī)對(duì)他說(shuō),我有個(gè)親戚的孩子是漠南師范學(xué)院畢業(yè)的學(xué)生,想找個(gè)學(xué)校,哪怕是小學(xué)也行……
他當(dāng)時(shí)就答應(yīng)了。并說(shuō),過(guò)些日子,等他工作穩(wěn)定后,把孩子有關(guān)材料拿過(guò)來(lái)。
我這次回來(lái),其中要辦的一件事,就是想告訴魯巳己這個(gè)消息。
我掏出手機(jī),撥了他的號(hào)(上次分手他給我留過(guò)他的手機(jī)號(hào)碼)。
他聽(tīng)見(jiàn)手機(jī)鈴響,接了。我說(shuō),魯老師,你回頭看,我是誰(shuí)?
他回頭一看是我,立刻端著酒和下酒菜過(guò)來(lái)了。他坐下后說(shuō),幾時(shí)來(lái)的,我咋就沒(méi)看見(jiàn)你?
我說(shuō),你進(jìn)來(lái),誰(shuí)都不看。戳在那里動(dòng)都不動(dòng)——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說(shuō),孩子的事有眉目了。明天你把他的有關(guān)手續(xù),畢業(yè)證、身份證、自薦表,并把孩子的所有有關(guān)手續(xù)復(fù)印一份給我。
他聽(tīng)了,非常高興。不由我分說(shuō),跟老板要了一瓶衡水老白干,一盤(pán)醬牛肉,一個(gè)涼拌芋頭絲,二兩燒麥。
那一晚,我和他,幾乎把一瓶酒喝光了(他喝得多,有六七兩)。
……
他兒子的事,最后我還真的給他辦成了。后來(lái),我每每一想起這事,自己都覺(jué)得失笑:一個(gè)與我素不相識(shí)的人,僅僅跟我喝了一次酒,跟我冒昧地提出要我?guī)兔Γ瑤退麅鹤诱夜ぷ鳎疫€竟然當(dāng)回事兒,給他辦成了。這是一種什么心理?究其原因,除了同情,我覺(jué)得,還有另外一種東西感動(dòng)著我。
那就是,我從他身上看到了人類(lèi)的高尚情感——對(duì)兒子的無(wú)限的愛(ài)!
(責(zé)任編輯 梁辰)

顏士富與兒童文學(xué)作家龔房芳合影
顏士富,江蘇泗陽(yáng)人。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曾任《短小說(shuō)》編輯,現(xiàn)任《林中鳳凰》文學(xué)雜志編輯。自1990年先后在《雨花》《小說(shuō)月刊》《故事大觀》《百花園》《青春》《短小說(shuō)》《天池》《楚苑》《鄭州日?qǐng)?bào)》《鄭州晚報(bào)》《淮海晚報(bào)》《宿遷晚報(bào)》等報(bào)刊發(fā)表短小說(shuō)200余篇,作品入選《2009年微型小說(shuō)精選》《中國(guó)微型小說(shuō)名家名作百年經(jīng)典》(第十卷)《財(cái)富泡泡塘》《選擇游戲》《宿遷十年文學(xué)精選》等權(quán)威選本。多篇作品被《微型小說(shuō)選刊》《海外文摘》《熱讀》《大河報(bào)》等選載。有小說(shuō)被《小說(shuō)選刊》列入全國(guó)期刊小說(shuō)概覽。連續(xù)獲得兩屆吳承恩文學(xué)獎(jiǎng)、江蘇省大眾文學(xué)獎(jiǎng)、“太倉(cāng)杯”勤廉微型小說(shuō)全國(guó)征文三等獎(jiǎng)。傳略入編《小小說(shuō)作家辭典》、江蘇省志文學(xué)卷。已出版《足跡》《蒼生》《師魂》《顏士富小小說(shuō)自選集》,編著《泗水飛歌》《獨(dú)特視角看宿遷》作品集。
王彥耘,男,內(nèi)蒙古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內(nèi)蒙古包頭市《包頭廣播電視報(bào)》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