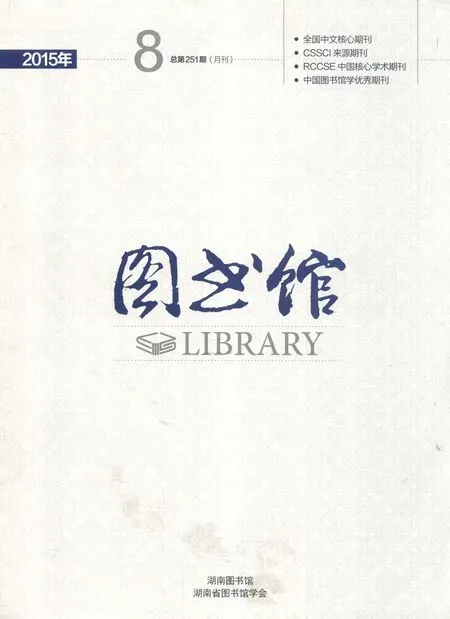權利理論視閾下圖書館權利概念的辨析與解讀
——圖書館權利若干命題的困惑與思考之一
魏建琳(西安文理學院圖書館 陜西西安 710065)
權利理論視閾下圖書館權利概念的辨析與解讀
——圖書館權利若干命題的困惑與思考之一
魏建琳
(西安文理學院圖書館 陜西西安 710065)
〔摘 要〕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對權利概念的產生、發展演變以及多元分歧的現狀進行了梳理。“圖書館權利”是普遍的權利文化在圖書館活動中的具體體現,其概念不應是新創出的一種權利,而是在已有人權體系中尋找自身的定位與歸屬。圖書館權利是圖書館活動中為道德、法律或習俗所認定為正當的利益、主張、資格、力量或自由。參與圖書館活動的所有人都是權利主體,不同權利主體有不同的權利內容,憲法是最終衡量正當與否的標準。
〔關鍵詞〕權利 權利理論 圖書館權利 概念
1 問題的提出
2005年1月8日,在黑龍江大學召開了“中國圖書館學會首屆峰會”。峰會共探討了5個議題,“‘圖書館權利’是本次峰會討論最為熱烈的議題”[1]。“峰會”之后,《圖書館建設》、《圖書館》、《圖書情報知識》等專業期刊相繼推出專欄“專門探討‘圖書館權利’的一些相關問題”[2]。同年7月, 在廣西桂林召開中國圖書館學會學術年會以“圖書館權利”為主題專設“分會場”,繼續為“研究”推波助瀾。“自2005年起,中國圖書館學界掀起了一股‘圖書館權利’研究熱”……[3]時至今日,討論越熱烈,分歧與差異似乎越大。由于缺乏對基本概念和命題的共識,似乎都在探究“圖書館權利”,但各自所指卻南轅北轍。這不能不說是“圖書館權利研究”熱鬧喧囂背后的一種隱憂。“學人們對‘圖書館權利’概念的認識存在著明顯的差異。”[4]
“權利”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不是圖書館學專有的研究范疇。“現代社會人們一般把它作為一個法律概念。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權利首先是一個哲學概念,至少是一個政治哲學概念,也是一個倫理學和社會學的概念。”[5]因而,筆者擬探賾圖書館權利的法學、歷史學、政治學的理論淵源,打破成見,在法學、政治學的權利理論視閾下對圖書館權利概念做一番全新的辨析與解讀。
2 權利概念理論探賾
2.1 權利概念的產生
從歷史上看,權利的概念產生于中世紀的西歐。古代社會,“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個人必須高度依賴群體……人的權利觀念淡薄。”[6]中世紀的歐洲,實行土地封建制度,土地歸領主或貴族所有,平民只能租種貴族的土地。因而,平民必須絕對服從貴族的權威,向貴族盡各種義務,如繳納大量的賦稅、服徭役與兵役等。而貴族對平民則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此時此地,只有貴族的“權利”,而“權利”等同于“權力”。
到了公元十二世紀,“西歐的農業生產力開始迅速提高……農產品出現剩余,貿易開始重新出現,而這種狀況所導致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城市的出現。伴隨著城市出現的就是市民階級的壯大”[7],此時的歐洲出現了一個與“政治社會”對立的“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主體是市民階級,市民階級從事的主要活動是商業貿易,“這種商品經濟關系所要求的行為意志自由和契約行為的對等性,使得原來自然經濟關系中不具有自我意識的廣大社會成員開始感到自己的存在,感到自身的人格尊嚴和生存價值,從而追求自主生存的生活。”[8]對上述社會背景,“唯物史觀的經典作家對此做過精湛分析……馬克思把權利產生的社會形態概括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9]
“人的獨立性”一旦成為社會普遍的訴求,就必然會與中世紀的黑暗現實產生尖銳的矛盾。矛盾沖突中,市民階級萌生了強烈的權利意識,“提出權利來與封建專制制度相對抗。”[10]西歐一批思想巨擘,如洛克、康德、孟德斯鳩等“立足于商品經濟社會關系發展導致的人的主體狀態變革的現實趨勢,借助傳統思想資源,將市民群體要求享有的平等自由的基本權利,論證為人的本性要求,論證為人擁有的出自自然本性的絕對權利……以先驗論的方法,賦予它們神圣的社會地位”[11],在歐洲掀起了一場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思想啟蒙運動。思想啟蒙運動“導致人的思想和精神的覺醒,催生了個性解放和個人利益的追求意識,催生了思想和信仰的自主意識,培育了人們追求權利人格的主體自覺性”[12]。從此,西歐社會誕生了一個全新的與“權力”相分離的“權利”概念。從此,“權利”概念逐步成為西方價值觀的核心并發展為一種全球文化。特別是從此,世界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人類走進了“權利時代”。
2.2 權利概念的發展與演變
權利的概念產生于近代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需要,是人類社會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權利概念在歐洲誕生之初,其核心內容是“自由權”。這是因為“市民階級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個人自由,沒有自由也就沒有行動、營業與銷售貨物的權利”[13]。這類樸素的權利要求被洛克等啟蒙先驅論證為“天賦人權”,“歸結為自由、平等和所有權”[14]。“天賦人權”是一種“要求國家不得侵犯與干擾的權利”[15],其所指的自由“是一種反對國家干預的自由,屬于消極自由的范疇……其范圍包括宗教自由、人身自由和財產自由”[16],“作為思想自由胚胎的宗教自由……逐漸發展為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與結社自由等‘表達自由’。”[17]“表達自由”一般是指“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是其延伸權利也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此項權利應該就是圖書館學術界熱議的“知識自由”、“智識自由”以及“信息自由”的本源。
以“自由權”為核心的“天賦人權”,被后世的權利理論研究者們命名為“古典人權”、“自然權利”、“第一代人權”。“第一代人權”通過“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思想啟蒙,經歷了歐美資產階級大革命的血與火的洗禮,經過了《權利法案》(英國)、《人權宣言》(法國)、《獨立宣言》(美國)的不斷確認與宣示,逐步發展為歐美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繼而發展為“普世價值”。
“第一代人權理論”為資產階級反抗封建專制提供了理論武器,“但這一理論的唯心論破綻又是顯而易見的”[18],它的邏輯前提假設與人類的經驗事實相距甚遠。對此,“不要說用馬克思主義去擊破,就是休謨、邊沁、密爾、奧斯汀等分析法學家以及薩維尼等歷史法學家在這些問題上的發難,就足以摧毀它的哲學基礎。”[19]“第一代人權理論”“實質上是其所處時代正在興起的市場經濟形態中的社會主體狀態的一種非歷史性的曲折反映”[20],“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其人權保障的重點是資產階級要求的財產權和契約自由”[21],而對于廣大勞動者的人權則在表面自由平等的商品經濟關系中“被否定、限制或虛置化……僅具有形式意義”[22]。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做過深刻的剖析。由于過分強調競爭和自由使自由資本主義在獲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實現了物質財富的高度積累之后,對公平的漠視又使其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后果,助長了人性的進一步墮落,致使社會矛盾加劇。在經歷了不斷的“經濟危機”與“階級沖突”后,國際社會出現了二元分化,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社會主義的價值內涵之一是平等,該價值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思和否定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結果。因而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公有制”、“按勞分配”,一般都將“平等權”置于諸項權利之首[23]。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亦“不再公開確認‘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將福利國家上升為國家理念”[24],開始關注“實質平等”,開始保障“勞工權益”。從權利理論的視角,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殊途同歸”,以“平等”價值為核心的“社會權”成為兩大陣營共同的關注點。
“社會權”又稱“福利權”、“受益權”、“平等權”、“積極權利”或“第二代人權”。廣義的社會權利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這一權利還可以再分為經濟權利、狹義的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社會權”中所說的“經濟權利”并非是指“從事經濟活動的權利”,而是指“工人享有的、與勞動場所有關的權利”,包括勞動的權利;同工同酬的權利;休息的權利;接受就業培訓的權利;喪失工作能力時獲得救濟的權利;失業時享受生活保障的權利等。“狹義的社會權利”是指“與社會保障和社會安全有關的權利”,包括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免于饑餓的權利;健康的權利等。“文化權利”雖然與經濟和社會權利一起提了出來,但是人們對文化權利的關注遠不如后者。由于對“文化”一詞理解上的不統一,所以“對于這一基本概念,任何關于人權的文件都未做出確切的界定”,“人們對文化權利任意組合,文化權利散見于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各種文件”,對文化權利的認知抵牾矛盾之處甚多。一般認為“文化權利”[25]包括:文化認同的權利;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權利;信息權;文化遺產權等。
從“第一代人權”到“第二代人權”,從“自由權體系”到“社會權體系”,從“追求自由”到“主張平等”,“人類追求的權利的范圍也日益擴大,人權的內涵也日益豐富。人們對人權的理解也從普遍的自然權利、政治權利,日益擴大到社會經濟生活權利等各個方面”[26]。“二戰”以后,聯合國先后制定了《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進一步確認與明確了“權利”的相關概念。從此,“權利”由“利益主張”固化為“國際規則”,成為現代人類的共同價值,成為現代文明的核心概念。
2.3 權利概念的多元與迷茫
權利的概念產生于歷史發展的需要,歷史與現實的需要引起對“權利”問題的學術探究。自近代以來,“權利”一直作為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特別是法學研究的核心范疇被學術界所關注。“概念”是一個學科的基石,是學術探究的基礎,也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前提。古今中外,“到底有多少人給權利下過多少次定義,似乎還沒有人作做具體的確切統計,但就目前學界所掌握的現有資料分析,僅從國外引進的并為大家所耳熟能詳的權利概念或定義就不下十余種”[27]。但是,“無論中外哪一位法學家、學者對權利所作出的詮釋均未獲得普遍的共識;而且每一種權利定義皆遭到過批評或質疑”[28]。
雖然不同的學者“站在各自的、不無一定局限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上界定權利,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們對權利問題的理解”[29],但是權利概念的多元化導致了“權利這個詞在不同的背景中具有不同的含義”[30],“權利”成了一個最具有“歧義性”的“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權利語言經常被濫用,關于權利及其涵義的討論也時常發生一些誤解。”[31]權利概念的多元與分歧導致了“權利概念的濫用與迷茫”。
3 圖書館權利概念的辨析與解讀
3.1 圖書館權利界定的個人之見
2000年以來,圖書館業界圍繞“圖書館權利”諸命題展開了大量探討,其中不乏對“圖書館權利”概念的各種界定。筆者以為,對“圖書館權利”的界定不能忽視和淡化了對“權利究竟是什么”的探究,應該對“‘圖書館權利’的‘權利’到底是什么,它具體的抽象的范疇是什么”的探究作為“圖書館權利”研究的前提與基礎。要回答“‘圖書館權利’的‘權利’到底是什么”的命題,首先必須厘清“圖書館權利”的“權利”是對圖書館活動原生命題的抽象概括,也是普遍的權利文化在圖書館活動中的具體體現,因此對圖書館權利界定就不應該是在圖書館活動的范圍內的“創新”,而應是在已有人權體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與歸屬。這是因為“如果仍然把人權看作是最高的道德權利,就要使其數量盡可能地減少……我們需要承認新的權利,但是,人權無謂的擴展,只會引起使人權的真正思想貶值的危險,因而逐步地削弱所有人權。我們應該對于承認既不清楚又不迫切需要的新人權的潛在危險保持高度謹慎”[32]。另外,從學術角度而言,“學者在使用概念并確立命題的過程中須慎之又慎。如果有新的認識因而需要確立一個命題,則必須經過證明。”[33]如果說對“國際上‘圖書館權利’研究是否已有成熟的理論”的命題尚有分歧、尚有爭議的話,那么中國的“圖書館權利”研究毫無疑義尚處于萌芽狀態,尚不具備把握本質并定義新概念的充分條件。
3.2 權利概念的再探究
在“權利理論”的視閾下對“圖書館權利”的概念進行辨析與解讀,意即從已基本形成共識的“權利理論”出發,對“圖書館權利”的概念內涵做出定義或詮釋。但是,由于現代“權利”的概念在發展豐富的同時也導致了權利概念的多元與分歧,使“權利”成了一個“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34]。故之前的理論探賾尚不足以對“圖書館權利”的概念內涵做出定義或詮釋,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探究與辨析。
“迄今為止,中外思想家、學者對權利所作的界說可分成兩大類:一為從權利本質屬性的界說,可稱為權利本質論;一為從權利具體情形的界說,可稱為權利實證分析論。”[35]
關于權利的本質,格勞秀斯和19世紀的形而上學法學家們強調的是倫理因素,認為“權利”的本質是“道德”,把權利看作“道德資格”。而耶林等學者則使人們注意到權利背后的利益,認為“權利的實質是普遍的功利”,“權利就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36]。馬克思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視角對“權利”所蘊涵的“經濟關系”屬性做了更進一步的剖析,其理論對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權利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權利本質論的代表人物是夏勇和張文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夏勇教授曾對“權利的本質”做過精到的分析,“他歸結出權利成立必不可少、也是基本的五大要素:利益、主張、資格、力量、自由”[37],認為“上述五個要素中的任何一個要素都能表示權利的某種本質,那么,以這五個要素中的任何一個要素為原點給權利下一個定義都不為錯。究竟以哪一個要素或哪幾個要素為原點來界定權利,則取決于界定者的價值取向和理論主張”[38]。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張文顯教授系統歸納了近代以來思想巨擘、法學名人從本質屬性界定權利的最具代表性的八種學說,即資格說、主張說、自由說、利益說、法力說、可能說、規范說、選擇說,“對中國當代相關學界之權利理論影響深遠,以至于中國相關學界對權利本質的認識,要么是對某一學說的肯定或認同,要么是對相關學說的概括或折衷。”[39]
“由于從權利的要素或屬性界說權利的結果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分析法理學的法學家開始了對權利分類和具體情景的實證分析……他們注意分析權利概念包含的豐富內容,并把義務和法律關系等概念聯系起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法學家霍菲爾德。”[40]霍菲爾德認為:“分析法律概念的最好方法,是訴諸‘相反者’(opposites)和‘相應者’(correlatives)的關系圖表,然后舉例說明它們各自在具體案件中的范圍和應用。”[41]霍菲爾德歸納了四對相反的概念和四對相應的概念進行邏輯分析 ,“把權利置于現實的利益關系來理解,并側重于從實在法的角度來解釋權利”[42]。雖然“霍菲爾德的權利分析圖解遠非在邏輯上嚴謹科學,在內容是完整無遺”[43],但是他在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里通過實證分析來理解和敘述權利概念,“細致地揭示權利概念的豐富內涵”[44],為全面和深入地認識權利,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作為法學等學科基本范疇的權利,盡管界定起來如此之難,卻仍是國內外學界孜孜以求其精確性的范疇。因為,每當概念的一些含義被弄得明晰易懂以致為許多人所知時,就標志著自我認識和理解的增長,并使富于智識的思想和行為成為可能。”[45]很顯然,正是由于這些學者們孜孜以求的探索,才使得“圖書館權利”的研究有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3.3 圖書館權利的內涵詮釋
如夏勇教授所言,“從以上可見,僅僅從某個特定的角度給權利下一個定義并不難,以這五個要素(利益、主張資格、力量、自由)中的任何一個要素為原點給權利下一個定義都不為錯,但這樣做容易導致權利問題的簡單化、庸俗化”[46]。同理,為“權利”的“下位類”——“圖書館權利”下定義也是如此。如果隨意擷取一個“權利界說”,在其前加上“圖書館”的限定,似乎一個“圖書館權利”的定義就直接“躍然紙上”。但是,如此簡單、機械地“照搬”,很明顯有悖于學術研究的宗旨。
筆者查閱了許多中外專家學者對于“權利”所下的定義及其闡釋,但仍感覺“一頭霧水”。困惑中“避重就輕”四字讓筆者豁然開朗。既然“現代圖書館核心價值或最基本的理念,包括對全社會普遍開放、平等服務、對弱勢群體優先服務,以及支持智識自由等,就理論的源頭而言,都可上溯到權利這一概念”[47],那么,對于“圖書館權利”概念的探究就是每個圖書館從業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對“圖書館權利”這一概念的內涵,即其本質屬性的總和,尚有認識盲點,尚不能用簡潔而明確的語言加以界定的話,那么就不妨暫且“避重就輕”,回避“下定義”,僅是“作詮釋”,僅對“圖書館權利概念內涵”的某些性質或特點進行適當辨析與解讀。
在“作詮釋”前,必須先借用夏勇教授的定義作為邏輯起點。夏勇教授曾經給權利下一個這樣的定義“權利是為道德、法律或習俗所認定為正當的利益、主張、資格、力量或自由”[48]。既然認同夏勇教授的觀點,那么理所當然也可以為“權利”的“下位類”——“圖書館權利”下一個這樣的定義:“圖書館權利是圖書館活動中為道德、法律或習俗所認定為正當的利益、主張、資格、力量或自由”。但是,夏勇教授卻如此評價他所做出的這個定義:“這個定義并不是完美的,甚至可以說是沒有多大意義的”[49]。既然如此,那么筆者簡單、機械地“照搬”,所給出的定義自然更不是完美的,更沒有多大意義。如果要使這個定義盡可能地接近于完美,盡可能地有點意義,就必須要做進一步的探究,做進一步的辨析解讀,然后對這個定義中的一些模糊之處做出適當的解說。
這個定義的第一個模糊之處是“圖書館活動”。“圖書館活動”,顧名思義,就是在圖書館這個場所(也可以界定為“空間”,包含“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所發生的一切行為。這個“一切行為”可以概括歸結為“人與人的關系”與“人與物的關系”兩大范疇。“權利”就是“人權”,自然需要在“人與人的關系”范疇中進行探究,探究圖書館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權利關系。如果要將“圖書館活動”具體化,就包括傳統的文獻搜集、整理、保存、提供等活動與創新的文獻檢索、信息咨詢、知識服務、展覽、講座、閱讀推廣等活動。在這些活動中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管理關系與服務關系,而這些不同的關系中都存在共同的權利關系。
厘清了“圖書館活動”的概念后似乎又發現了一個新的“模糊”,即“人與人的關系”中的“人”是指哪些人?答案似乎很明確——讀者、館員與圖書館組織(法人)。但是這個明確的問答在權利理論的視閾下還需要做更進一步的辨析與說明。在權利理論的視閾下,上述問題應表述為:在圖書館活動中所存在的權利關系中的“權利主體”是哪些人?“權利主體”具有哪些性質或特點?
2000年以來,圖書館業界圍繞“圖書館權利主體”的界定命題展開了大量探討,或支持“讀者權利”,或認同“館員權利”,或認定“圖書館職業權利”,觀點分歧,各執己見。筆者以為,在權利理論的視閾下認知,“權利時代”,人權具有普遍性,是人人都應享有的權利。所以,在權利時代,參與圖書館活動的所有人都是權利主體,包括讀者、館員、法人以及其他,只是不同權利主體的權利內容會有所不同。
所謂“權利時代”,是人們對近現代社會特征的一種主觀概括,只有在“權利時代”才能生成健全的“權利人格主體”。對于“權利人格主體”的特征,馬克思概括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具體講就是,一方面,社會主體普遍擺脫傳統社會的人身依附,擁有自主平等的經濟人格,享有人身自由、財產自由和人格尊嚴,每個人都能自由平等地追求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社會主體普遍認同“人道主義”,產生了“人的道德權利或應有權利的觀念”[50],這種權利觀念提倡“既珍視自己的權利又尊重別人的權利”,使權利在“本質上帶有‘正當’的意味”[51]。這是普遍意義的“權利人格主體”的特征,自然也是參與圖書館活動的“權利人格主體”的特征。
明確了“圖書館活動”與“圖書館權利主體”后,接著需要辨析的認識盲點是“為道德、法律或習俗認定為正當”的標準是什么?
夏勇教授之所以對他所下的定義評價不高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為道德、法律或習俗認定為正當’,也有著許多不同的解釋”[52],因為如此就無法對“利益、主張、資格、力量或自由”做出清晰明確的界定。對此,筆者以為“有著許多不同的解釋”是“權利時代”“啟蒙階段”的必然現象。啟蒙時期,人權一詞停留在應然層面上,是政治哲學和法哲學討論的話語形態,權利理論建立在不同的價值觀之上,自然“見仁見智”,這是不同價值基礎與不同研究方法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而2004年“人權入憲”使人權獲得了實然的法律地位,成為法律規范,實現了人權由道德形態向法律形態的轉變。這就意味著憲法作為最高的規范層次,會凌駕道德、法律或習俗之上,成為最終衡量正當與否的的標準。
4 結論與討論
2004年“人權入憲”標志著一個“權利時代”的到來,社會各界激起了對“權利”話題的濃厚興趣,圖書館行業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在圖書館學研究領域,“中國圖書館人對于權利的研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圖書館學發生重大轉變的標志性研究之一”[53]。
但是,同法學等研究領域已形成了成熟的“權利本位范式”,“提供了共同的理論背景和理論框架……足以空前地把一批擁護者吸引過來,使他們瞄準一個方向、圍繞一個論域開展大兵團研究”[54]的狀況相比,圖書館權利的研究卻顯得差距明顯。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業界對“圖書館權利”概念的認識存在著明顯的分歧,貌似都在探究“圖書館權利”,但各自所指卻南轅北轍。概念的混亂使研究難以為繼,討論亦不可能。故蔣永福先生在“‘圖書館權利’研究反思”[55]中將“‘圖書館權利’概念的具體內涵如何把握?”列為我們仍需研究并澄清的首要問題。
筆者以為,當前業界對“圖書館權利”概念的認識存在分歧,其具體內涵無法把握的根本原因在于:絕大多數的“圖書館權利”概念界定都是圍繞著“是誰的權利”而展開,而對于“權利究竟是什么”的命題或語焉不詳,或刻意回避。這也許有其各種原因,但是,在有意無意間忽視和淡化了對“權利究竟是什么”的探究,卻會產生概念上的混淆與誤讀,導致概念的具體內涵無法清晰把握。
“權利究竟是什么”是法學等學科“權利理論”探究的核心論域,因而筆者以為,“圖書館權利”的概念應在“權利理論”的視閾下進行辨析與解讀。
筆者從歷史發展的視角對“權利”概念的產生、發展演變以及多元分歧的現狀進行了簡單梳理,在此基礎上認為,“圖書館權利”諸現象是普遍的權利文化在圖書館活動中的具體體現,因而“圖書館權利”概念不是新創出的一種權利,而是在已有人權體系中尋找自身的定位與歸屬。是故筆者“移植”夏勇教授的界定為“圖書館權利”下了一個定義:“圖書館權利是圖書館活動中為道德、法律或習俗所認定為正當的利益、主張、資格、力量或自由”,并對定義中“圖書館活動”、“圖書館權利主體”、“為道德、法律或習俗認定為正當”的標準做了詮釋解讀。
倍感慚愧的是,由于對“圖書館權利”命題認識盲點頗多,故文中避重就輕,對有些命題有所回避,希望今后能與業界專家同行圍繞以下命題繼續探究。
首先,關于“圖書館權利主體”的話題,圍繞此話題,業界觀點分歧,爭議不斷。筆者以為,如果將“圖書館權利”界定為“圖書館”的“權利”,那么毫無疑義,這個“權利”是“職業權利”,“權利主體”是“圖書館(法人)”。但是,如果將其界定為“圖書館場所”“圖書館活動”中所存在的“權利現象”,那么,在權利時代,參與圖書館活動的所有人都是權利主體,只是不同權利主體的權利內容會有所不同。
其次,關于“圖書館權利內容”的命題,如文中所述,當今“權利”存在“自由權體系”與“社會權體系”的劃分,那么“不同圖書館權利主體”的“不同權利內容”其實都可以最終歸結為“自由權”和“社會權”。否則,或是“偽權利”,或是“不同的權利概念”。
最后,關于“衡量正當與否的的標準”命題,如文中定義,如果“不正當”則構不成“權利”。但是并非只要自己認為是合理、正當的需求,就可以稱之為“權利”,“正當”應有客觀的標準。筆者在文中認為,憲法會凌駕道德、法律或習俗之上,成為最終衡量正當與否的的標準。但是,“憲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規定只是一種框架性規定,具體內容當然有賴于部門法來規定,憲法不能替代部門法律的功能”[56]。而“圖書館立法”的窘境卻無疑讓這個“衡量正當與否的的標準”顯得異常“模糊”。
如果說“衡量正當與否的的標準”只是讓人覺得“模糊”的話,那么“利益、主張、資格、力量或自由”在圖書館活動中的具體所指則更加讓人“迷惑”。許多“迷惑”也成為文章的一個未竟的話題,留待下次的進一步探究……
(來稿時間:2015年2月)
參考文獻:
1. 畢紅秋.權利正覺醒 激情在燃放——中國圖書館學會2005年峰會綜述.圖書館建設,2015(1):12-14, 29
2-4.程煥文.圖書館權利的來由.圖書館論壇, 2009(6):30-36
5,10,30,51.辛世俊.公民權利意識研究.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6
6,8,9,11,12,18,20-22,29,35,37,39,40,43,45,50.菅從進.權利制約權力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7,13.方新軍.權利概念的歷史.法學研究,2007(4):69-95
14-17,23-25,32,33.鄭賢君.基本權利研究.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19,54.張文顯,姚建宗.權利時代的理論景象.法制與社會發展,2005(5):3-15
26.尹奎杰.權利思維方式論.法制與社會發展,2004(1):18-30
27,28.范進學.權利概念論.中國法學,2003(2):15-22
31,34,36,38,41,42,44,46,48,49,52.夏勇.權利哲學的基本問題.法學研究,2004(3):3-26
47,53.范并思.權利、讀者權利和圖書館權利.圖書館,2013(2):1-4
55.蔣永福.“圖書館權利”研究反思.圖書館建設,2008 (4):59-61, 65
56.吳家清,杜承銘.論憲法權利價值理念的轉型與基本權利的憲法變遷.法學評論,2004(6):3-9
〔分類號〕G250
〔作者簡介〕魏建琳(1967- ),男,西安文理學院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Concept of Library Rights in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Rights Theory——Perplexity and Thinking on Some Propositions of Library Rights
Wei Jianlin
( Library of Xi’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mbs that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multiple divisions of concept of rights and thinks that “library right” is common culture of right’s concrete embodiment in the library activities, its concept should not be creates a new kind of rights, but to find their own positioning in the existing system of human rights. Library rights are interests, claims, qualification, strength, or free that are recognized as legitimate by the morals, laws or customs in the library activities. Everyone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library is right subject, different subject has different rights content, spec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ultimate measure of legitimate or not.
〔Keyw ords 〕Rights Right theory Library rights Con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