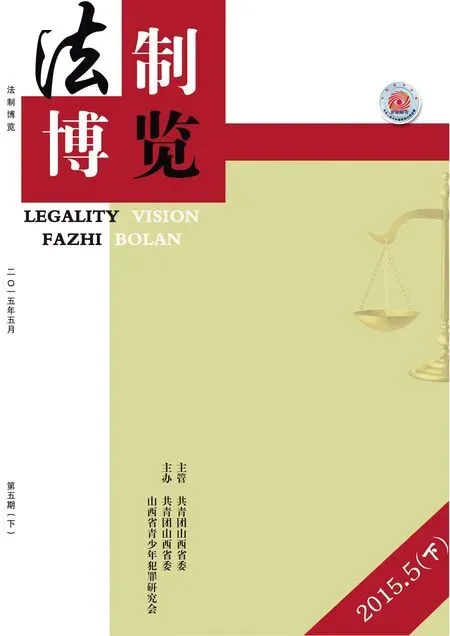域外瀆職罪主體比較研究
雷 劼 范凌坡
鄂州市鄂城區人民檢察院,湖北 鄂州 436000
?
域外瀆職罪主體比較研究
雷劼范凌坡
鄂州市鄂城區人民檢察院,湖北鄂州436000

摘要:我國刑事法律法規對于瀆職罪主體的規定經歷了由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的“國家工作人員”,到修訂后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且有相關的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對“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進行界定,視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處理,這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規定有很大區別。本文通過簡述我國立法例,并省察他國及我國臺灣地區法立法例,比較個中區別,以資法律實務參考。
關鍵詞:瀆職罪;主體;域外;評析

瀆職犯罪,又叫職務上的犯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依法履行職責或者超越權限、濫用職權,實施的妨害正常國家管理公務活動的犯罪。1952年4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開始施行,該條例對貪污罪的主體進行了規定,這也是我國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對職務犯罪的主體進行規定。其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兩高分別以立法、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的形式對職務犯罪的主體進行規范和明確,尤其是對瀆職犯罪的主體進行了許多立法嘗試。
一、我國瀆職罪主體之規定
我國刑法及其立法、司法解釋對于瀆職罪主體在97刑法修訂前后兩個時期存在明顯差異:97刑法之前的法律法規將瀆職罪的主體設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并通過一系列立法、司法解釋不斷擴充,將國有企事業單位、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均納入在列,這是關于瀆職罪主體第一階段的規定;1997年刑法修訂之后,瀆職罪主體范圍有明顯的限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成為這一時期瀆職罪的主體,其后的相關解釋對其范圍同樣進行了補充規定,但刑法對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一直未有明確界定。因此,在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中對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識分歧比較大,大陸刑法學界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界定標準,有三種理論——即職能主義理論、身份主義理論和折衷主義理論。
第一,職能主義理論。職能主義理論主張根據行為人是否從事公務、是否在事實上實施了國家機關公務職能來確定主體身份。至于行為人是否具備國家機關公務人員的編制身份,則不是判斷其是否能夠成為瀆職犯罪適格主體的根本因素,行為人所為的“公務”才是判斷關鍵。
第二,身份主義理論。身份主義理論主張認定瀆職犯罪的主體應當遵循職務類犯罪的共性,由于職務犯罪是具備特定身份者所犯之罪,所以,作為職務犯罪分支的瀆職犯罪主體理所當然地應具備嚴格的身份才是適格主體,沒有這種身份,則其不可能構成瀆職罪。
第三,折衷主義理論。折衷主義理論系將職能主義理論與沈份主體理論有機結合,認為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理應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的人,若不具備該身份則其必不應也不能從事公務。根據刑法條文、人大司法解釋以及高檢院、最高法對瀆職罪主體的4個司法解釋的具體規定來看,我國立法體例系采取折衷主義。
二、域外瀆職罪主體之規定
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就瀆職犯罪的主體的刑事法律規定模式主要可以歸結為三類:首先是德國、日本及我國臺灣等地刑法將公務員界定為瀆職罪主體,進而具體規定公務員的范圍;其次是俄羅斯、匈牙利等將瀆職罪的主體設定為公職人員、公務人員,并進一步確定公職人員、公務人員的范圍;最后是意大利、瑞士等國將公務員和受委托從事公務服務、公需服務人員作為瀆職罪的主體。分析有關國家瀆職罪主體刑事法律,不難發現均是以身份(組織)和職務(功能)來劃定公務員的范圍,德、日便是如此,下面主要介紹德國、日本以及臺灣地區刑事法律中如何確定瀆職罪主體范圍。
(一)德國之規定
現行德國《刑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公務員系指依德國法之下列人員:a.任公務人員或法官者,b.擔任其他公法上之勤務關系者,c.其他經指定在官署或其他機關或其委托從事公共行政工作者,而其履行任務所選用的組織型態,在所不問。”①
從德國刑法的上述規定不難看出,其對于瀆職罪主體的刑法設定與我國有些許類似,同樣從是否具備公務員的嚴格身份和是否切實履行了國家管理職責兩個標準進行界定。十一條第二款第一項和第二項明確了公務員特指任公務的人員、法官和其他以公法確定的公務職能承擔者。這體現了德國刑法對于瀆職罪的主體同樣著眼于職務犯罪的身份特征,要求具備特定的公務身份才能成為瀆職罪的主體。同時,十一條第二款第三項同樣將不具備特定身份,但是履行的特定公務職能的人納入了公務員范圍,即可成為瀆職罪的適格主體。經指定和受委托從事公共行政是從工作職能出發將其視同公務員,這體現了德國刑法對瀆職罪的主體不僅從身份上進行考察,同時兼顧功能性的考察。②
(二)日本之規定
日本現行《刑法》第七條第一、二項規定:“本法所稱公務員,指官吏、公吏、依法令從事之議員、委員及其他職員。稱公務所者,謂公務員執行職務之處所。”③日本1907年刑法典公布后,幾經修訂,1995年5月12日修正通過第一項:“本法所稱公務員,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職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公務之議員、委員或職員”,是為日本現行法針對公務員定義之規定。④
日本關于瀆職罪主體的規定,同樣兼具考察犯罪人身份和犯罪人公務職能兩個方面。一方面,刑法明確規定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職員是公務員,只要具備相應的身份,即可成立瀆職罪的主體;另一方面,刑法還規定他依法令從事公務之特定人也應當視作公務員,在其實際有法令依據履行公務職能的時候,也可以是瀆職罪的適格主體。對于刑法條文中規定的“法令”、“公務”等要素的范疇,日本學者普遍認為應從寬把握,如抽象的部門規定可以作為公務依據的“法令”,“公務”的界限不應以公法界定的權責為限。
(三)臺灣地區之規定
臺灣舊《刑法》有關公務員概念之立法定義的第十條第二項,僅系簡要地規定為:“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于公務之人員”,其具體意涵究竟為何,實務的運用上產生許多爭議。時至2005年2月新法通過,將同條項之內容大幅修訂,公務員的范圍限定為依法以及受委托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中從事國家管理有關公共事務者。
修訂后的刑法條文中“依法令服務于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者”,系指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所依法令任用之成員,其依法代表、代理國家機關處理公共事務,即應負有特別服從義務。至無法令執掌權限者,縱服務于國家機關,例如僱用之安保或清潔人員,并未負有特別服從義務,即不應認其為刑法上公務員。如非服務于國家機關,而具有依“其他依法令從事于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權限者”,因其從事法定之公共事項,亦應視為刑法上的公務員。此類型之公務員,例如: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其他依政府采購法規定之各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采購等人員,均屬之。受國家機關依法委托從事與該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因受托人得于受托范圍內行使該機關公務上之權力,故參考貪污治罪條例第二條后段及國家賠償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應認其屬刑法上公務員。
三、我國及域外瀆職罪主體之比較
(一)97年刑法修訂前主體范圍規定之評析
截止到1997年修訂《刑法》實施以前,79年《刑法》和立法、司法解釋已經將瀆職罪的犯罪體規定為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等。此種規定確保司法實踐中,公職人員中有失職瀆職行為的,基本都可為瀆職罪的主體被追究刑責,這種基本符合我國國情的法律規制,對于該時期打擊瀆職犯罪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1979年之前的瀆職罪主體相關規定也有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相關規定將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全部納入了瀆職罪主體范圍,這與瀆職罪系侵犯國家行政管理職權這一客體的特質存在一定的出入,將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當然地納入國家工作人員范疇值得商榷;二是瀆職罪名不多,尤其是玩忽職守罪和徇私舞弊罪這兩個罪名屬于口袋罪名,在司法實踐中易被濫用從而人為擴大打擊范圍,有悖于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原則。
(二)97年刑法修訂至今主體范圍規定之評析
根據現行刑法及相關規定,瀆職罪的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刑法條文對于國家機關的定義并未進行明確,也沒有列舉解釋,這就導致在實踐中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兩個概念容易產生錯誤解讀,導致檢察機關辦理瀆職侵權案件過程中出現司法尺度不一的情況,影響司法公正和依法查辦職務犯罪。此外,刑法、新修訂的刑訴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等實體法、程序法、訴訟規定對于瀆職罪的主體規定也存在沖突,進一步造成司法實踐中的混亂。從建國至今我國法律對瀆職罪主體規定的演變歷程來看,經歷了一個由相對寬泛到一定程度限縮的過程,當前的瀆職罪主體規定與刑事司法實踐之間還存有一定差距,需要我們結合司法辦案工作實踐不斷總結,以求盡快完善的瀆職犯罪主體法律規定體系。
(三)域內外主體范圍規定之對比評析
通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對于瀆職罪主體的稱謂不同國家和地區稍有不同,德、日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都在法律條文中將瀆職罪的主體定義為“公務員”,我國香港地區將瀆職罪的主體定義為“公職人員”,大陸地區稱“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對主體規定的形式也略有不同,如德國及香港立法,均在條文詳細列舉公務員類型之范圍,是列舉式的立法模式,而大陸立法是先舉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概括規定,接著列舉國有公司、企業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相比較而言,域外刑事立法就瀆職罪的規定具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確定性。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域外就瀆職罪主體立法與我國差異較大,許多國家的立法是盡立法之能事以求細化、明確瀆職罪的適格主體,從而減少和避免刑事司法實踐中的爭議,確保司法統一和憲法法律權威。二是廣泛性。許多國家和地區對于瀆職罪的主體規定非常寬泛,由于域外對于國家管理職能的設定與我國區別較大,對于公務以及相關的從事公務人員的認識和責任負擔要求也不同,導致了有些國家和地區瀆職罪主體范圍較寬,一些企業管理人員、普通雇員都可能成為瀆職罪的主體。⑤
我國系采取概括加列舉的規定方式,一方面概括說明了瀆職罪的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另一方面,通過立法、司法解釋,對“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范圍通過列舉的方式框定。我國特殊的政治、社會環境決定了國家治理體系的特殊性,許多國有企事業單位雖然未經法律明確授權,卻實際履行一些管理國家的職權,而概括加列舉的立法方式對于這類人是否屬于“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能否納入瀆職罪主體范圍留下了爭議空間。瀆職罪主體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我們已經走過了六十多個春秋,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在充分考慮我國特殊國情的情況下,積極學習國外先進立法經驗,才能使我國有關瀆職罪主體的立法進程走得更加順利。
[注釋]
①王曉明.我國刑法中的國家工作人員研究[J].西南政法大學,2011.
②蔡墩銘譯.德日刑法典[M].臺灣:五南出版,1993,12:7-8.
③[日]牧野英一.日本刑法通義[M].陳承澤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20.
④王曉明.我國刑法中的國家工作人員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2011.
⑤陳智元.國內外瀆職罪犯罪主體比較[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7(1).
[參考文獻]
[1]蔡墩銘譯.德日刑法典[M].臺灣:五南出版,1993,12:7-8.
[2]陳智元.國內外瀆職罪犯罪主體比較[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7(1).
[3][日]牧野英一.日本刑法通義[M].陳承澤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20.
[4]張晶,付蕾.論瀆職罪主體的界定[J].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6(1).
[5]易明剛.論我國刑法中的國家工作人員[D].河南大學,2003.
[6]馬長生,尤金亮.中外瀆職罪主體的比較研究[J].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4).
[7]江禮華.論國家工作人員范圍的界定[J].中央檢察官管理學院學報,1998(4).
作者簡介:雷劫,鄂城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范凌坡,鄂城區人民檢察院助理檢察員。
中圖分類號:D924.3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5)15-01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