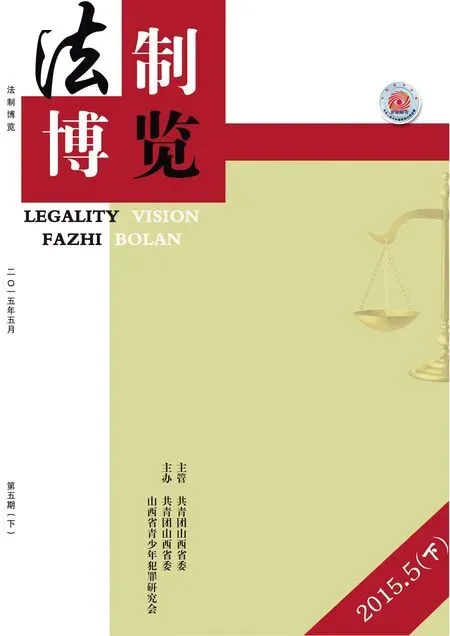財產型犯罪性質研究:以盜竊罪為例
李舒楊 楊永新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北京 100083
《尚書》記載:“逾垣墻,竊馬牛,誘臣妾,儒則有常刑”。恩格斯也曾指出:“從動產的私有制度發展起來的時候起,在一切存在著這種私有制的社會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竊”。由此可見,無論古今、無論海內外,在各個時期都把盜竊這種財產型犯罪作為打擊的重點。
一、“字源”
(一)中國
在原始社會公有制制度中,人們共生產、共生活、共勞動,互相間沒有階級區別,更沒有剝削與被剝削。人們生活在這樣的原始共產主義條件下,自然沒有盜竊行為的發生。但是,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產品產生了剩余,私有制便產生了。在私有制條件下,社會財富分配不均,于是盜竊行為產生了。
“盜”一字自古有之。甲骨文寫作“ ”。其中,“”(“次”)表示人的貪欲。“”(“舟”)表過河越界(筆者認為也可解為“皿”,放置食物的器皿)。因此,甲骨文中“盜”即表“為滿足貪欲而過河越界”,亦可解為“由于看到他人食皿中的食物產生貪欲”。隨著時間的發展,“盜”在篆體中寫作“”說文解字中有云:“盜,私利物也。從,,欲皿者。”也就是說“”字形采用“”作為偏旁,偏旁中有“”意為“水”,下半部分為“”意為器皿。所以“”表示對他人的器皿垂涎欲滴。
在古漢語中,“盜”字本義為動詞,為“過河越界,劫走或掠奪財物”,在演進中,本義消失。后作動詞時,意為“行竊、偷竊”。在《荀子》中有云:“竊貨曰盜。”作名詞時,意為“行竊者、偷竊者”。
“竊”一字,篆文寫作“”,由“”,即穴,意為穴、鼠洞;“”即“廿”,意為吃;“”即“米”,意為雜糧;“”卨,意為蟲子。所以這個字解釋為“蟲子將食物和雜物拖入洞中。”
在古漢語中,“竊”字本為動詞:蟲子將食物拖入洞中。后逐漸演進,動詞作“入宅行盜”講,也作“陰謀占有”意;也作副詞講,意為“偷偷地、私下里”。
飲食問題不是小事,正所謂“民以食為天”。從源頭來看,“盜”與“竊”都與糧食有關,在中國古代,“盜”、“竊”都源于封建社會人民對于基本生活資料——“糧食”的保護。
(二)西方國家
拉丁文中,盜竊罪寫為:Furtum。但是有關Furtum(即盜竊罪)的分類十分明細。例如:Furtum rei意為竊取;Furtum manifestum意為現行盜;Furtum nec manifestum意為既遂盜竊;Furtum usus意為竊用等。不得不說,拉丁文如此詳細的、具體的分類可以看出,西方社會羅馬法對于盜竊的規定是帶有分析性的,能夠分解出各種構成要素,便于把握。
二、盜竊罪的歷史沿革
盜竊罪是古今中外刑法中最常見的犯罪,也是一種古老的犯罪形態。人類社會從有了私有制、有了物質生活條件的剩余后,就出現了盜竊犯罪。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鞏固統治,都將盜竊罪作為打擊的重點之一。
盜竊罪在中國第一次出現于《周禮》。在《周禮司厲》中記載“盜賊之任器、貨略、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尚書》有云:“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意為,盜竊行為需要根據行為的輕重、盜竊貨物的數額多少而接受制裁。奴隸制下刑法盜竊的對象有“牛馬”、“臣妾”。保護“牛馬”目的在于保護封建社會的生產資料和交通工具;保護“臣妾”目的在于維系人倫關系和家庭關系的穩定。其究極目的仍為維護封建統治與鞏固地主階層的地位。
西漢開國帝劉邦,將秦朝的覆滅歸結為專任刑法、嚴刑苛罰。所以,他提出“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劉邦廢除秦朝立法,但盜竊罪仍舊屬于懲處的三大罪名之一。
《唐律》中規定的“盜”的概念與當今并不相同。“盜”不僅包括盜竊、搶劫等行為,還包括謀反、謀大逆、造謠惑眾等犯罪行為。但在處罰上仍同犯罪數額相聯系。《宋刑統》中,對盜竊罪的規定進一步細化——對盜竊罪的概念進行了界定:“盜竊人財,謂潛行隱面而取”,也就是說秘密竊取他人財物即為盜竊。在刑法方面,同樣與盜竊犯罪數額相對應。元朝時,《大元通制》中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肉刑,懲戒盜竊犯罪時,“初犯左刺右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后,為了保護生產資料,對“盜牛馬者”、“盜驢騾者”有了進一步更加細化的規定。明、清時期再次廢除肉刑,但是擴大了盜竊罪的范疇——將“帝室之罪”、“內亂之罪”、“國交三罪”都歸入盜竊罪的范疇。
近代時,我國首次將“盜竊罪”限定為“以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犯罪對象只限為財產。并具體劃歸了罪名:普通盜竊罪、竊占最、加重竊盜罪等。
新中國成立之后,黨和政府也從未仿宋過對盜竊罪的打擊和預防。建國厚道幾十年,我國被認為是盜竊犯罪按法律最低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預防盜竊犯罪最有成效的國家之一。
在西方,根據羅馬法所規定的,盜竊罪也需要收到懲罰,雖然與我國古代的懲罰程度略有區別。在《十二銅表法》中,盜竊的懲罰是將私人制裁與私解相結合,且根據盜竊犯年齡和其行為結合的嚴重程度來確定其懲罰的級別。處罰時,對現行犯和非現行犯有所區別,打擊的重點放在現行犯盜竊犯罪上。
進入封建社會后,在《薩利克法典》中,對盜竊罪進行了細化的分類,比如“竊奴”、《竊豬》、《盜竊干草》等,均有詳盡的規定。在法國資產階級歌名勝利后,其《法蘭西共和國刑法典》對后代盜竊罪產生了深遠影響,規定“欺詐地竊取不屬于自己之物者,成立盜竊罪”,雖然講盜竊與詐騙在同一個罪名中規定,但是犯罪行為卻又具體描述。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對于盜竊罪的制定日趨合理。
近代以后,英國1968年盜竊發規定:“一個人如果不誠實地挪占屬于另一個人的財產,并意圖永久地剝奪財產,屬盜竊罪”。在進行認定時,對于盜竊罪中的“不誠實”的定義進行了更加準確的限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刑法典》規定,意圖不法占有竊取他人動產的即為盜竊罪。此法典將盜竊罪的犯罪對象限定為動產。且將盜竊罪劃分為單純盜竊罪名和加重盜竊罪名。
德國歷史法學派奠基人薩維尼針對自然法學派的哲學演繹方式,提出了“歷史的”思維方式,為當時的法學指出了新的思路和方向。然而,歷史并非精致的,而是運動的。同樣法律并不是一條條規范的、只能遵守的規范章程,而是需要不斷修改和演進的、符合民族、符合當下社會情況的時刻跟進的動態思維。法是存在社會中的,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因此法與人類、與社會密不可分。
中國傳統法律和羅馬法相比,在盜竊的處理上的不同,實際上是將盜竊罪劃為公法還是私法的問題。對盜竊的不同處理方式反映了兩者完全不同的法律觀念。中國將盜竊劃為公法,目的在于維持政治秩序的立場,鞏固國家政權的通知,將盜竊納入國家管理的范疇,這里貫穿秩序性思維;然而羅馬法則是以保護私有財產的立場,將盜竊視為對私人財產的侵犯,劃入了司法處理,這里貫穿的是規范性思維。作者認為,在固有思維習慣里,接見、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時,應以自己民族的實際需要為基礎。
古人云:“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當今法律的修訂,也應參考歷史的演進。當研究西方法律的時候,也應順應自己民族的社會發展和民族特征,滿足本民族的實際需要。
[1]李克非.盜竊罪的立法沿革與比較研究[J].政法論壇,1997,03:41-43+56.
[2]許儉,熊建華.盜竊罪歷史考察[J].科技信息(科學教研),2007,35: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