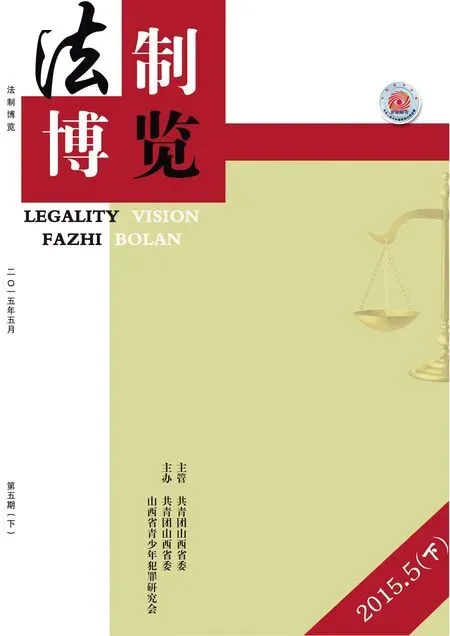利益集團在能源立法中的影響及其規制對策:以能源資源產權公平配置為背景
孫 哲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2
政府權力對市場運行的過度侵蝕造成能源資源產權配置過程中的政府主導,政府意志主要通過行政立法、部門立法的形式表現出來,政府利益膨脹帶來立法的偏向性,導致能源資源產權配置不公和行政壟斷壁壘。在這一過程中,能源國企作為壟斷利益集團,對于政府行為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
一、國企利益集團更易達成集體行動
(一)國企與民企利益集團具有不同的利益訴求
利益集團是為了實現和維護特定目標和共同利益,在政治過程中采取集體行動的組織化群體,他們利用自身資源最大限度地參與政治過程,影響政府公共政策,以實現團體成員的最大利益。同屬能源產業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本應具有相同的利益追求,但由于制度的人為界分,資源產權上的配置不公,使得能源產業形成國企寡頭壟斷格局,個別能源國企特別是能源央企,憑借掌握的各種資源,力圖鑄造制度壁壘,維護其壟斷利益,而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則希望通過法律轉型擺脫基于出生所帶來的不公平待遇,在公平的市場環境中進行競爭。利益追求上的根本分歧導致同屬能源產業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劃分為不同的利益集團,但都期望通過影響政府政策和立法,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不過,立法結果卻一如既往的繼續維護國有企業的利益而忽略民營企業的利益,其中除了政府利益影響外,國企和民企利益集團是否能夠達成集體行動以影響立法,成為應當考慮的關鍵因素。
(二)國企與民企利益集團的行動邏輯
中國利益集團遵循“社會內生演進”的成長邏輯,[1]由于缺乏支持性制度為成員提供有效激勵以達成集體行動,中國利益集團的集體行動具有自發性的特點,導致國企利益集團和民企利益集團在實施集體行動上的大相徑庭。對于民企利益集團來說,能夠帶來利益增進的立法是向集團成員提供的一種公共物品,集團中的部分企業通過努力影響立法之后,所有企業均可享受由此所帶來的利益增長。由于民營企業數量眾多,任一成員只能獲得影響立法所帶來的平均收益,卻要承擔全部成本,而競爭對手則可以免費獲得同等收益,那么搭便車問題就會抑制民營企業會自發從事影響立法的活動。[2]另一方面,組織全部或部分民營企業從事集體行動必須額外增加成本以達成一項協議來決定分工協作和成本分擔,對于成員數量眾多的民企利益集團來說,這種組織成本同樣耗資甚巨。
與此相反,作為壟斷寡頭地位央企利益集團呈現出小集團的特征,使得央企從事影響立法活動的收益遠高于其成本。一方面,央企本身規模巨大,任何偏向性立法所帶來的邊際收益增加都是十分顯著的,而成員數量有限使得能夠免費分享公共物品的集團成員十分稀少,加之寡頭央企成立時的定位區分,通過搭便車行為獲得收益的其他企業難以對行動企業構成競爭威脅,因此,即使無法達成集體行動,單個央企也具有足夠的激勵去實施影響立法的活動。另一方面,由于央企大都由國資委投資設立,協調相對容易,而成員數量稀少又進一步降低了組織成本,因此更容易實施集體行動。
二、國企利益集團對能源立法的影響
作為寡頭壟斷集團,能源央企在從事影響立法的活動時,更加注重從產業總收益中分取更大份額,而非通過提高能源效率來創造更大的產業總收益。雖然公平配置產權有助于市場機制的運行和能源效率的提升,但央企只能獲得由此所帶來的部分收益,卻要承擔全部成本,不僅包括影響立法的行動成本,而且包括喪失壟斷地位所帶來的機會成本,因此央企集團更加傾向于通過影響立法繼續維持能源資源產權不公平配置的狀況。另一方面,央企利益集團會減緩社會采用新技術的能力,減緩為回應不斷變化的條件而對資源的再分配,并因此降低經濟增長率。由于技術創新會帶來新產品或新的生產方法,可能改變集團或其成員之間的相對實力,威脅集團生存,在無法立即模仿這種技術創新的情況下,能源央企對技術創新通常采取謹慎態度。而能源領域的創新必然是是重新組合生產要素的破壞性創新,減緩采用新技術的速度也就同時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導致低效率的生產活動得以長期維持。此外,央企通過制造特殊的市場供給和異常情況,提高了政府管制的復雜性和政府的范圍,[3]使得政府權力對能源市場的滲透更具正當性,方便央企通過“俘獲”政府部門以引導政策制定和立法。這也意味企業將更多資源用于尋租領域而非從事生產活動,使得生產性激勵消退,而獲得產品更大份額的激勵得以提高。
應當指出的是,能源產業處于由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轉型的特殊歷史階段,但化石能源企業多為國有企業,新能源企業多為民營企業,新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同時意味著民營企業對國有企業的替代,以及國有企業被迫的戰略轉型和壟斷地位喪失,這是國企利益集團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國企利益集團通過影響立法,限制民營企業的發展,維持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使得能源結構的轉型步履維艱。
三、利益集團影響立法的規制策略
(一)通過行業協會促成民營企業的集體行動
前已述及,民企利益集團雖然也有影響立法以實現自身利益的動機,卻難以克服搭便車問題,導致無法達成集體行動為集團提供集體物品。因此,實現能源資源產權公平配置的目標需要為民營企業利益集團的成員提供“選擇性激勵”,通過鼓勵或懲罰集團成員來克服搭便車問題,動員集團成員實施影響立法的集體行動。[4]由于這種“選擇性激勵”是針對集團成員個體而非整體的激勵性措施,目的在于增進能源民營企業這一特定社會群體的福利,因此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范難以發揮激勵集團成員的任務,而通過行業協會的“非法律性懲罰”則往往更能實現“選擇性激勵”的效果。
首先,作為行業自律組織,行業協會能夠通過收取會費等方式,將集體行動的成本內化進所有成員的成本核算體系,克服外部性所導致的搭便車問題,對于拒絕繳納會費的成員,則可以采取征收罰金、降低名譽、集體抵制、開除、市場禁入等方式進行懲罰。其次,行業協會本質上是協會成員建構的一種網絡性和組織性的關系實體,有助于實現集團成員由陌生人到熟人的角色轉換,建立穩定和持續性的交往關系,降低集團成員之間的協調成本,同時這種“重復博弈”的環境也為缺乏國家強制力的“非法律性懲罰”提供了適用空間。再次,作為具有共同潛在利益的企業聯盟,行業協會對于能源民營企業的發展現狀和行業標準有著更為深入的了解,易于建立有效的信息搜集和爭議解決機制,能夠更合理的分配集體行動所帶來的收益和成本,使得“選擇性激勵”措施更具針對性和專業性。[5]
(二)通過行業協會聚合民營資本以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
行業協會的作用不僅體現在提供“選擇性激勵”以促使民營企業從事影響立法的集體行動,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整合民營資本以形成對抗政治國家的市民力量。
曼瑟·奧爾森認為,具有足夠權力創造和保護個人財產權利、強制執行各種契約、受到約束而無法剝奪或侵犯個人權利的“強化市場型政府”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條件。“強化市場型政府”意味著政府與社會總體福利具有“共容利益”,能夠從社會總產出增長中獲取較大份額,并因社會總產出的減少遭受極大損失,因而更傾向于通過立法提高產權效率以增加社會總產出,而非熱衷于從現有總產出中分取更大份額,這種具有“共容利益”的“強化市場型政府”必須以民主政體為基礎,[6]其核心是保證政府政策和立法產生于自由的政治競爭過程和多元利益集團的政治博弈。
由于行政機關集行政執行權和行政立法權于一身,缺乏應有的法律約束,造成行政機關的行政專制局面,而長期以來以國有經濟壟斷為主導的政治經濟體制,使得能源國企憑借資源產權優勢建立產業壟斷地位,成為能源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支柱,同時也成為國家政治統治的重要支撐。行政權力的運行失范與能源國企政治經濟權重的過度膨脹,促使行政機關與國有企業之間建立進退一致的共同利益關系,國有企業主導立法,行政機關及其公務人員通過政策立法維護國企壟斷地位,同時也在捍衛自身政治利益,形成具有潛在共同利益的“政府——國企利益集團”,將經濟領域的壟斷延伸至政治領域,排斥自由的政治競爭過程,徹底割裂政府、國企與社會整體福利之間的共容利益。因此,想要建立具有共容利益的“強化市場型政府”就必須通過民營企業的發展來降低國有企業的政治經濟權重,但由于國有企業是國家政治統治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代表,發展民營經濟就意味著對政府行政權力的制衡與約束。換言之,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競爭事實上已經演化為以民營企業為代表市民力量與政治國家的對抗。
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任一民營企業都難以完成對抗政治國家的任務,但行業協會能夠通過“非法律性懲罰”等手段,將分散化的民營企業組織起來,形成行動一致的強大利益集團,改變單個企業與政府談判時的弱勢局面,節約和分攤政企談判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同時,相對于單個民營企業而言,以協會團體形式出現的民企利益集團能夠更為有效的參與到國家政策制定和立法過程中,對政府施加實質性的壓力或潛在壓力威脅,迫使政府在行權時必須顧及行業協會及其所代表的民營企業對政策法規的回應,形成對政府權力的社會制約,促使政府權力運作的規范化。因此,通過行業協會整合民營資本,能夠增強民營企業的議價能力,使得這種市民力量切實參與到政治博弈過程中,形成自由的政治競爭格局,倒逼政治體制轉型,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
[1]陳水生.中國利益集團的成長邏輯與動力機制研究[J].南京社會科學,2011(7).
[2]曼瑟·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7-12.
[3]曼瑟·奧爾森.國家的興衰[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61.
[4]曼瑟·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34.
[5]魯籬.論非法律懲罰——以行業協會為中心展開的研究[J].河北大學學報,2004(5).
[6]曼瑟·奧爾森.權力與繁榮[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