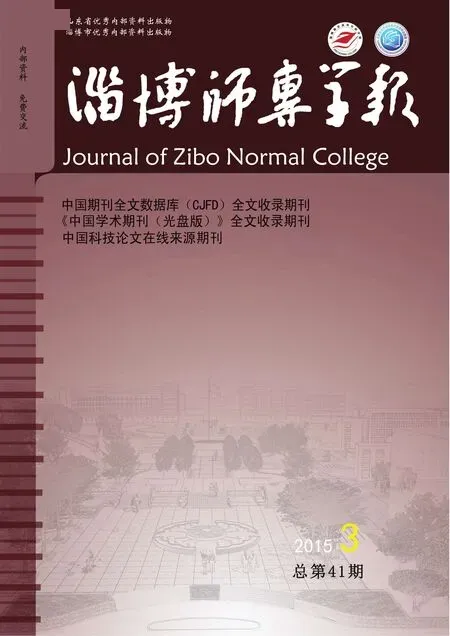李長之《魯迅批判》與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的比較
王 麗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
李長之《魯迅批判》與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的比較
王 麗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魯迅學”不僅見證了魯迅的不斷被發掘,也見證了魯迅研究者們的學術心路。李長之與李歐梵來自兩個時空的人因魯迅結緣并產生思想的碰撞,為我們深入理解魯迅提供了不同路徑。李長之的《魯迅批判》與李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各自特色,二人研究的基點、側重點、評論風格迥異,獨特新穎,在魯迅研究史上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與意義。
視角;側重點;批評色彩
魯迅自其成名作《狂人日記》于1918年5月15日發表于《新青年》月刊上后,一直備受文學界關注。近百年來對魯迅、魯迅作品的關注有增無減,蔚為可觀。今天,“魯迅學”已得到共識,研究魯迅及其作品的數量遠遠超過魯迅自身創作的數量。在浩如煙海的研究著作中,我們認為李長之的《魯迅批判》與李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時間跨越近半個世紀,研究成果斐然,具有時代代表性且具有可比性。通過對兩者的對照研究,可幫助發現魯迅研究所走過的路程。
一、李長之、李歐梵各自研究魯迅的視角
李長之,1910年10月30日生于書香門第,幼年接受新式教育,學用白話文寫詩歌和散文,上初中時在老師的影響下,接受新文化運動的新思想,并有幸閱讀魯迅作品《吶喊》,參加“救國十人團”,到藥店檢查日貨。學生年代有很多學生深受魯迅思想影響,用李長之的話說便是“在生活上,我們有時麻木,拯救了我們的,就是魯迅的那支筆”。對于魯迅,李長之在情感上并不陌生,甚至是其文學道路的領路人之一,“我受影響頂大的,古人是孟軻……現代人便是魯迅了,我敬的,是他的對人對事之不妥協。不知不覺,就把他們的意見,變作了自己的意見了”。
1935年,李長之完成了魯迅學史上第一部成體系的學術專著《魯迅批判》,隨即由北新書局出版。這也是魯迅生前親自批閱過的批判他的唯一一部專著,此時李長之年僅25歲,是個還未畢業的清華學子。在李長之之前,關于魯迅的評論已經有七十多篇,但這些評論絕大多數都是印象式、即興式,沒有系統的論述[1]。李長之撰寫《魯迅批判》時,評論界正流行偏重政治分析和階級剖析的批評,激進的批評家感染時代話語模式大都離開文學本有的特性去評判作家與作品。許多文學評論都在追求政治、經濟學那種嚴肅權威的架勢,而李長之采用精神分析方法探索魯迅精神、性格,不依附任何權威,堅持文學批評的獨立品格著實難能可貴。“批評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權威,屈服于時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虛榮和金錢),屈服于輿論,屈服于傳說,屈服于多數,屈服于偏見成見(不論死得自他人,或自己創造),這都是奴性,這都是反批評的。千篇一律的文章,應景的文章,其中決不能有批評精神”[2]。
李歐梵1942年生于河南太康,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1962年赴美深造,之后在美國各大高校任教。各種不同文化的碰撞為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視野,促使他愛好廣泛,不受任何“中心”的牽絆。李歐梵于1987年出版了《鐵屋中的吶喊》英文版,中文翻譯版出版于1999年。正因為李歐梵是海外漢學者,“對我而言,邊緣才是真正自由的,因為我不受‘中心’情結的牽制,可以隨意轉變視角,擴展視野,由中而西……”,李歐梵的這種身份為魯迅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種視角,一種中立、較客觀的視角。不同于李長之與魯迅同時代的“養育于五四以來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新鮮、銳敏、富于朝氣,李歐梵對魯迅的研究是建立在關于魯迅的原始資料不斷完善、魯迅研究已有幾十年成果、世界文化交流廣泛的基礎上,以“現代性”這一時代主題為切入口,重新確定魯迅作品的文學價值。
二、各所側重、獨創突出
李長之的《魯迅批判》與李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兩部著作都是以魯迅生平為線索,論及作家及其作品,結構布局相似,所論問題既有共同點又有明顯的區別,側重點不同,異彩紛呈,觀點獨特,視角新穎。
(一)根據各自理論體系系統論述魯迅小說創作特色
1.李長之“不虛美、不隱惡”的評價準繩
李長之自中學時代便開始接受魯迅,魯迅作品曾是像李長之這類有志青年的精神食糧,其對魯迅的敬仰之情不言而喻。但一拿起“批判”之筆,李長之又是個有著獨立人格、自我判斷能力的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因為求真,我在任何時候都沒有顧忌,說好是真說好,說壞是真說壞”[3]。李長之認為魯迅的所有小說并非都是藝術精品,在兩個結集里,有八篇東西是完整的藝術,分別是:《孔乙己》《風波》《故鄉》《阿Q正傳》《社戲》《祝福》《傷逝》《離婚》。這些作品有很多共同點:對農村社會之深切的了解,對于愚昧、執拗、冷酷、奴性的農民之極大的憎惡和同情并且那詩意的、情緒的筆,以及那救生的信念和思想……[3](P37)。也有幾篇東西寫得特別壞,壞到不可原諒的地步,如《頭發的故事》《一件小事》《在酒樓上》,這些作品要么故事太簡單,要么不美不親切,要么沉悶又平庸……[3](P93)。 從李長之的評價總結我們可以發現,他的評價標準是傳統小說的套數:情節生動有趣、塑造典型人物、主題明確。如其對《在酒樓上》的評論:“說什么什么,怎么樣呢,還是單調……故事簡單,是材料的問題,獨白而落于單調,是手法的問題”。另外,李長之大都就小說內容作為判斷依據,較少小說形式的考究。當時魯迅盛名滿天下,對其小說都是贊譽之聲,拋開李長之這些批評是否恰當,能說出這些話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就需要勇氣。
2.李歐梵對魯迅小說的現代性探索考察
李歐梵從“現代性”出發對魯迅短篇小說進行品鑒,這是全書最中心的部分,也是李歐梵用筆最著力的一部分。李歐梵對魯迅短篇小說“現代性”的探索分為內容、形式兩部分,通過對具體文本的分析,向我們展示了魯迅是如何轉化并超越傳統文學,向小說形式與內容注入新的生命。一是現代化技巧的嘗試。如《狂人日記》中文本套文本、日記形式,《藥》象征主義,《風波》集體諷刺……人物刻畫上表現出觸目的、怪異的意象,深入國民性劣根。還有敘述藝術,象征敘述的運用,李歐梵庖丁解牛般對魯迅的作品進行一一分析。一是內容上的“獨異個人”與“庸眾”。這是魯迅小說里常出現的兩大對立意象,“獨異個人”是精神界戰士,試圖拯救“庸眾”靈魂。“庸眾”以觀看“獨異個人”為樂趣,“獨異個人”被視為“人民公敵”。魯迅的價值還在于不抱著盲目的希望化解兩者矛盾,介于希望與絕望之間的不確定性,脫離了中國傳統文學中那種大團圓結局的喜劇色彩,避免了盲目樂觀,展示了知識分子的理性思考。
從李長之到李歐梵,我們可以發現對于魯迅小說研究的一個大進步,從依據傳統小說評價標準到以“現代性”為依據發現魯迅不走老路、敢于創新的精神。
(二)將雜文納入研究范圍,超乎同時代人的視野
1.李長之藝術地看待魯迅雜文
李長之是第一個從藝術上去分析魯迅雜文的評論者。李長之將《野草》《朝花夕拾》都歸入雜文中,不認為《野草》是散文詩。詩注重主觀、情緒,從自我出發,純粹的審美,而《野草》攻擊愚妄者,禮贊戰斗,諷刺的氣息勝于抒情的氣息。李長之把魯迅雜文創作看成一個技術、思想不斷成熟的發展過程,評價的標準是“好的文章總得從容,無論哀與樂,愛與憎,都不能例外”。李長之喜歡魯迅雜文,卻不妨礙其對它的判斷:“長處是常有所激動,思想常快而有趣,比喻每隨手即來……”“有時他的雜感文卻也失敗,其原故之一,就是因為他執筆于感情太盛之際,遂一無含蓄”“太生氣了,便破壞了文字的美。”[3](P131)
魯迅雜文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飽受爭議,瞿秋白、茅盾、馮雪峰等左翼評論家高度稱贊,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是這樣給魯迅雜文定性的:“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斗的‘阜利通’……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于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于民眾斗爭的同情”[4]。而以陳西瀅、林語堂、梁實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又竭力貶低魯迅雜文的價值。李長之不附和時論,堅持從文學角度剖析作品,實屬不易。
2.李歐梵探索魯迅雜文的獨創性
李歐梵以中國的文學傳統為背景來衡量魯迅作為現代作家具有的獨創性程度,認為雜文最具代表性。李歐梵具體分析了魯迅雜文的由來與繼承性:偏愛魏晉文章、受章太炎影響、關注明末小品文、《新青年》“隨感錄”中的“雜感”“雜談”提供了自由表達的可能;總結了魯迅雜文的特色,即區別于其他人雜文的因素。對魯迅從小說創造轉向雜文寫作,評論家看法不一,普遍看法是魯迅創作力枯竭,瑣事煩身,李歐梵發現魯迅雜文中也有狂烈的創造性,體裁的區別是絕對不能限制他的感受力。
李歐梵發現魯迅雜文中也充滿寓意、象征色彩,其雜文創作反映了魯迅現實處境、精神狀態、思想轉向,概括了雜文不同階段的特征:1927年前的隱喻傾向;1927至1929轉變階段魯迅關于文學和革命之間復雜關系的一系列思考以及他的思想發展;1930年后參與政治斗爭后的雜文,被瞿秋白稱贊為戰斗的“阜利通”,從文學角度看,未免籠罩著過多的對社會事務的關心,充滿辛辣的諷刺,帶有摧毀性,視界和深度由此而削弱,卻被過分強調了;生命垂危時的雜文寫作,讓人倍感親切,在新的思想廣度中把人引向了他早期雜文抒情的、隱喻的意味。[5]
新時期以來研究者們開始重新看待《野草》這個集子。李歐梵設專章討論《野草》,將它看作散文詩集,是魯迅對形式試驗和心理剖析的兩種沖動的結合,是交織著召喚、意象、隱喻三層次的象征主義藝術的巨大收獲。這與李長之對《野草》的定位相去甚遠,但也更有說服力。
(三)李歐梵強調魯迅與傳統文學的復雜淵源
李長之在對魯迅人生階段分類時,將魯迅1881至1917作為一個整體,視為其精神進展的第一階段,是個體成長與準備的時期。如此,魯迅歸國后的那段經歷就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似乎可有可無。李歐梵對這一時間段以1909年8月魯迅留日回國為界,分別論述。李歐梵特別強調了魯迅1909年至1917年間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設立專章“傳統與‘抗傳統’(counter-traditions)”討論魯迅這“沉默的十年”[6],認為魯迅這一時期看似沉寂,實則在蓄積力量,獨自進行的思索提供了后來文學創作的溫床[5]。早期研究通常忽略魯迅這十年的心路路程,認為它就是魯迅自己所說的“回到古代”消磨時間,后來也有學者研究魯迅對傳統文化的看法。涉及到這一時期,如王瑤的《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系統論述了古典文學對魯迅作品思想與藝術的影響,而李歐梵是第一個專門論述沉寂的十年里魯迅如何對古典文學再接受與批評的學者,并強調了這看似可有可無的十年確為魯迅提供了獨立思考、潛心學習、蓄積勃發的機會。魯迅對古典文學的研究見諸于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首先他給予神話與傳說極高地位,其次迥異于傳統考證研究的關于文學如何寫史的觀念,再者從更廣闊的背景中去研究小說。
魯迅對傳統文學的興趣不僅體現在研究小說,還表現在將傳統文學因素引入《故事新編》的創作,甚至寫作舊體詩。《故事新編》包括八個故事,全選取傳統題材,神話、傳說,抑或傳說中的歷史人物,但魯迅又不是簡單的套用傳統,而是借用傳統題材賦予新的故事、新的人物形象、新的寓意,是對傳統創造性的繼承。同所有受過傳統教育的知識分子一樣,魯迅在青年時期也寫舊體詩,不同的是,魯迅一直寫,特別是三十年代,舊體詩創作更多也更好,不是簡單的應酬之作,而是繼續了早期小說、散文詩的思想探索。
(四)魯迅為何只寫短篇小說
李長之認為“長于寫小說的人,往往在社會上是十分活動的,十分適應,十分圓通的人,……魯迅不然,他對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貼近了……這都不便利于一個人寫小說。魯迅內傾,不合群,不適合創作長篇小說,“是詩人而不是小說家”,他缺少一種組織的能力,這是他不能寫長篇小說的第二個原故。李長之還認為魯迅一生只有短篇小說,后期轉為雜文寫作是其創作力缺乏的表現。李長之從魯迅性格等方面評定其對長篇小說之力不從心,評定的過于草率,缺乏科學根據,這是他的不足。但李長之將魯迅定義為“詩人”確是獨創性的,并且具體論述了魯迅為何是位詩人、是怎樣的詩人。后人一概統稱魯迅為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而不具體考究“思想”“文學”“革命”之涵義的做法確實不及李長之的較真、嚴謹。
李歐梵對此問題也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述。首先思考了魯迅選擇短篇小說的原因,據他的考查,大概有三方面的理由。一是受外國文學的影響,其翻譯的《域外小說集》內容主要就是短篇小說;二是直接的傳統體裁的淵源,魯迅在學術上興趣是偏重于唐代及其以前的傳奇、志怪(都是短篇);三是在“五四”反傳統背景中,小說寫作本身就可以說是一種思想上的叛逆行為,它反對那種重詩輕小說的文人傳統的主流[5](P51)。可見,魯迅并不是寫不出長篇而是偏好短篇。其次,李歐梵認為魯迅喜好神話與傳說,著迷于小說史在于它的“虛構性”,《故事新編》中選取傳統題材(神話、傳說、傳說中的歷史人物)卻對其再創作似乎暗示魯迅創造力的旺盛。再者,李歐梵認為魯迅雜文中也有狂熱的創造性,體裁的區別不能限制他的感受力,并不是因為才思枯竭,而是其看中雜文的實效性。
(五)魯迅是文學家、思想家還是政治家
李長之在考察魯迅作品時就說魯迅在思想上還不夠一個思想家,只是一個猛烈對抗舊社會、舊制度的戰士,止于一個戰士。但在文藝上,魯迅卻是個詩人,他擁有詩人具備的情緒、情感、印象。在給魯迅總體評價時給出了魯迅為什么不能算是思想家的理由:“因為他是沒有深邃的哲學腦筋,他所盤桓于心目總的,并沒有幽遠的問題。他似乎沒有那樣的趣味,以及那樣的能力。”[3](P160)李長之進一步指出魯迅本質上是虛無主義,對于未來有些迷茫,沒有形成可供后人參考的思想體系。李長之就讀于清華大學時從物理系傳入哲學系,學習西方哲學,其對魯迅沒有形成體系的思想不能算是思想家的思維,而是來自西方哲學邏輯。
對魯迅的定位一直是學界熱點,盡管魯迅本人曾非常謙虛地表示自己不是什么“教授”“人生導師”,可后人不予以理會,依舊給魯迅帶帽子,或出于愛戴、敬仰之情,或出于政治意圖考慮,甚至是出于借魯迅之名給自己帶高帽。最后,毛澤東在1940年1月9日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給出了權威了定位:“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此后近四十年時間里,作為“思想家”“革命家”的魯迅不斷被強調,而作為“文學家”的魯迅一直無人問津。曾經李長之的一句“魯迅在思想上夠不上一個思想家”成了他此后生活與學術的屏障。
李歐梵重新確立魯迅作為知識分子的立場,而不是政治活動家,對毛澤東的著名論斷提出質疑。李歐梵發現魯迅關心的是文學與革命的理論問題,在政治承擔的框架以內確定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問題,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問題,而且其對政治的看法是變化的,這實際是否定了魯迅是革命家的論斷。李歐梵認為,在魯迅的生活與思想中文學占據主要地位。
三、迥異的批評色彩
(一)李長之情感化評論
閱讀《魯迅批判》,能感受到作為批評者的李長之鮮明的個性、獨立的人格。李長之堅持“不虛美、不隱惡”的評價準繩評點作品,其內在的準繩便是自己對小說、詩歌的情感性體認,而不是完整的理論體系。李長之缺乏關于魯迅的原始資料,只能根據作品、時人印象分析魯迅性格特點及其對魯迅創作的影響,批判的同時也毫不掩飾其對魯迅的崇敬之情。值得關注的是李長之并沒有從其崇敬之情出發闡釋魯迅及其創作,而是褒貶兼論之。
(二)李歐梵理性化評論
在《鐵屋中的吶喊》中,李歐梵具體分析了魯迅幼時家庭環境的狀況,家庭變故對魯迅生活與心靈的影響,運用心理分析試析父親的病危、缺席對魯迅內心深處可能潛在的影響,母親的性格、能力在魯迅成長過程中的意義。李歐梵細致地觀察魯迅童年的興趣愛好:對幻境、鬼怪和神話書感興趣,愛好繪畫,長期對于“雜學”以及“小傳統”通俗潮流的興趣,發現魯迅創作、學術的歷史根源。李歐梵對魯迅求學之路更是細致考究,甚至考察了魯迅在學校所學的課表,魯迅求學時期所看之書,所感興趣的譯作以及報刊。李歐梵對魯迅選擇醫學與棄醫從文原因進行了現實的思考,而不單純是幻燈片事件對他的刺激。當時中國學生認為醫學是日本可提供最好訓練的學科之一,魯迅棄醫從文可能是魯迅醫學科目考試成績平平,卻偏好文學類知識。李歐梵具體分析了魯迅認同并提倡尼采超人觀念,對魯迅選擇翻譯西方小說的原因進行多方面考察,比如稿費較高、魯迅是民族主義愛好者導致對俄國與東歐文學的愛好,魯迅個人的文學趣味……這些繁瑣而又細致的工作對深入了解魯迅思想與創作必不可少,也為我們從事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種不人云亦云的態度與踏實、不走捷徑的方法。
在《鐵屋中的吶喊》中,我們看不見李歐梵的個人喜好及對作品好與壞的粗暴界定。李歐梵大量搜集原始資料、親朋好友對魯迅回憶文章以及相關研究資料,運用心理分析法,試圖盡可能還原真實、鮮活的魯迅,避免魯迅的不斷神話與僵化,成果累累。
李歐梵最后還關注了一個普遍忽略的問題:魯迅后期對馬克思主義美學和蘇聯文學的學習。王富仁曾有論文《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試圖探索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之間的關系,而李歐梵主要探索魯迅三十年代對蘇聯文學及從蘇聯引入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的接受情況,填補了魯迅生平后期學習、思想變化等研究不足的漏洞。
總之,李長之與李歐梵來自兩個時空的學者因魯迅結緣并產生思想的碰撞,為我們深入理解魯迅提供了不同路徑。李長之的《魯迅批判》與李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各自特色,二人研究的基點、側重點、評論風格迥異,獨特新穎,在魯迅研究史上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與意義。
[1]溫儒敏.李長之的《魯迅批判》及其傳記批評[J].魯迅研究月刊,1993,(4).
[2]李長之.批評精神[M].重慶:南方印書館,1942.
[3]李長之.魯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4]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A].李宗英, 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5]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6]錢理群.十年沉默的魯迅[J].浙江社會科學,2003,(1).
(責任編輯:黃加成)
The studies on Lu Xun witness not only the constant exploration of Lu Xun’s works, but also the researchers'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Coming from two different worlds, Li Changzhi and Li Oufan become attached because of Lu Xun, and produce the collision in thoughts, which provides a different path for ou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Lu Xun. The paper will expound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i ChangZhi’sLuXunCriticismand Li Oufan’sIronHouseScreamfrom the aspects of basis, focus, criticism style, hoping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ies of Lu Xun.
perspective; focus; criticism
2015-05-11
王麗(1990-),女,江西都昌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2013級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
I206.6
A
(2015)03-003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