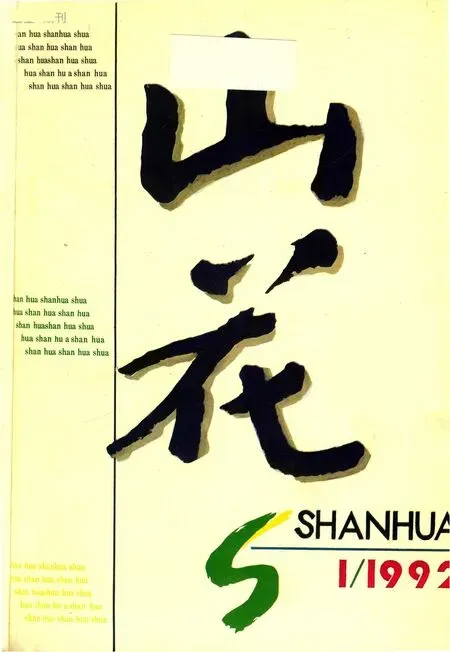蕭紅哀歌:那被無限放大的私生活(外三篇)
馬小鹽


當許鞍華導演執(zhí)導的影片《黃金時代》在影院票房慘敗之時,蕭紅的私生活卻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熱衷消費的民國甜點。各大網(wǎng)站的寫手們,紛紛開始兜售一種名叫“蕭紅和她的男人們”的隱私瑪卡龍,一時形成集體消費蕭紅隱私的盛大奇觀:有女性主義者歷數(shù)蕭紅情事借此控訴男權社會,也有男性寫作者借蕭紅情史意淫自身與文學女青年上床的浪漫主義情懷,更有寫手因蕭紅男女行為之輕率直斥其為賤貨,行文起筆間呈現(xiàn)出一副生殖器管理員的圣潔容顏,宛如蕭紅穿越時空的搶占了他們的性資源。這一切的一切,對于早已逝去的蕭紅而言,幾近侮辱。一位作家,本該以書做資,以文立世,無奈在死后多年,亦要在筆名的盾牌上,集齊后來者緋聞八卦的七彩箭鏃。
蕭紅在《呼蘭河傳》中寫道:“呼蘭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熱鬧的人就特別多,我不知道中國別的地方是否這樣,但在我的家鄉(xiāng)確是這樣的。”其實,蕭紅是知道的。不僅呼蘭河城如此,整個中國亦如此,七十年后的中國仍舊如此。呼蘭河城是中國社會的一面縮微之鏡。只不過那些熱衷窺探他人隱私的呼蘭河看客,如今轉世為一些網(wǎng)絡寫手。娛樂時代,一切都有被娛樂化的可能。但對一部作家的傳記式影片,舉目望去,四處散溢著八卦的氣息,卻難以看到一篇可圈可點的影評,豈非咄咄怪事?雖然我并不贊同因對現(xiàn)實的不滿,從而過度美化民國,并將民國命名為黃金時代。但——至少,民國時期的文人們,不會群體熱衷于他人隱私,而是在追尋整個種族的出路與未來。
僅《黃金時代》本身而言,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彼此交織的電影敘事語言,使得這部影片呈現(xiàn)出詩的肌質,而非傳統(tǒng)的傳記編年史敘事。在一個詩被嚴重邊緣化的時代,這樣的影片注定在大眾那里無法獲得青睞。整部電影的敘事方式與蕭紅的《呼蘭河傳》彼此互為鏡像:蕭紅的《呼蘭河傳》的體裁介于散文與小說之間,《黃金時代》的敘事處于紀錄片與故事片的模糊地帶。正是這搖擺行進于兩種涇渭分明的體裁邊界的模糊感,導致小說文本與電影文本,呈現(xiàn)出一種詩意的“越界”美來。在我看來,蕭紅的一生的關鍵詞是:越界。即若放在當今,蕭紅亦是一位屢次“越界”的女性。現(xiàn)實生活中道德越界,作品中體裁越界。當然,影片有它自身的敘事缺陷。導演的女性主義視角,令她在蕭紅身上傾注了過多的悲憫與憐愛。這便使得影片中的蕭紅,更像獻給“黃金時代”的一份美麗祭品,而非一個被自身性格與時代裹挾前行的女作家。蕭紅一生屢戰(zhàn)屢敗的愛情,不僅僅是男權社會下“被損害被侮辱”的女性這么簡單,亦與她自身性格密切相關。蕭紅對男性有著嚴重的依賴感。每一個她經(jīng)過身邊的男人,皆是救援她脫離苦海的一葉方舟。只是這方舟接龍,最后皆演變?yōu)橄乱粋€噩運的開端。蕭紅的性格,極其多面。她不僅軟弱多情,還嫵媚強悍。她逃離家庭,跟隨一個個男人,皆是性格中的強悍所致,而非僅僅是出于無奈。無論是文字,還是愛情,蕭紅皆是個在刀尖上跳舞的女人。也就是說,是蕭紅一直在選擇噩運,而非噩運選擇了蕭紅。這是東北女人蕭紅與上海小資張愛玲截然不同的地方。誰若看不出蕭紅性格中強大狂野的一面,誰就沒有讀懂蕭紅以及蕭紅的小說文本。可影片卻將蕭紅塑造為三重受難者:時代的受難者,男權社會的受難者,愛的受難者。這樣一個美化過的“受難者”形象,必然是一個因時間的距離扁平化在照片中的“蕭紅”。她不豐滿,亦不真實。
所有的實驗電影,面對市場都有它的尷尬之處:比起傳統(tǒng)的故事片,實驗電影的敘事語言不但是“反電影”的,時間語言也往往不是線性的,而是斷裂與縫合的。而這時間的斷裂與縫合,必要邀請觀眾調動思維并積極參與進來。在一個早已習慣了視覺快餐的時代,讓觀眾進入“視覺反芻”并享受視覺慢餐,肯定會面臨票房慘敗。許鞍華在上映前就屢次強調“收回投資方成本”就好,顯然明白影片在市場上所面臨的困境。但壞票房未必是壞電影,也未必一定是好電影。就電影藝術而言,許鞍華的《黃金時代》是一部中上之作。它的美學失誤,不僅僅在于人物形象的扁平化,還在于影片中過多插入的同代作家對蕭紅的評價。這些片段繁多矯情,過度文藝腔,有說教之嫌。好似導演出于對演員表演藝術的不信任,從而強迫觀眾認同蕭紅是一位偉大的女作家。這是整部影片的美學青春痘,幼稚天真,突兀難看,顯然毫無存在的必要。
在我看來,蕭紅的文學才華,一點也不低于張愛玲。這一南一北的兩位女作家,是剛剛擺脫“女子無才便是德”時代的文學雙生花。蕭紅書寫了她所經(jīng)歷的鄉(xiāng)村生活,張愛玲記錄了她在上海的城市經(jīng)驗。兩個人皆從女性視角出發(fā),一鄉(xiāng)一城,各自填補著民國時期的文學空間。從成名作《生死場》的前半部便可看出,蕭紅具有書寫鄉(xiāng)村生活的天賦。通過蕭紅的書寫,我們看到饑餓年代的農人們,愚昧、堅忍、殘酷,動物一般地在大地上盲目地生生死死。這當然得力于蕭紅的童年經(jīng)驗。但蕭紅的《生死場》并無魯迅所捧的高度,它只能算一部青澀之作:為了迎合彼時的左翼意識形態(tài),作者在小說的后半部虛構了她所不熟悉的農民革命。空洞的口號,莫名的暴動,導致小說前半部與后半部宛若腰斬,邏輯難以自洽,文本斷裂明顯可見。一旦拋掉外界強加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蕭紅原本具有的寫作天賦便渾然天成的顯露出來,《呼蘭河傳》便是作家恢復心靈自由的成熟之作:祖父、后花園、小街、大坑,鄰人、火燒云等繁雜多樣的人與事物,皆在蕭紅具有靈性的筆下真實地呼吸起來。
蕭紅是幸運的,在適當?shù)哪甏龅搅嗽撓嘤龅娜耍瑢懥讼雽懙淖髌贰J捈t是不幸的,生前四處流浪,情感千瘡百孔。恰恰是蕭紅的幸與不幸,成就了蕭紅的作品與人生。正如蕭紅在給蕭軍的信中所寫:“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是的,此時此刻,是所有藝術家的“黃金時代”,無論蕭紅還是所有的在者。
眼淚敘事下的羊民審美
科學研究表明,作為一種人類感情的表達方式,眼淚具有精神上的排毒功能。心理學家甚至建議抑郁癥、焦慮癥患者感覺不良時多多哭泣,以便疏導難以承受的精神壓力。這是一種哭泣療法。這療法在我國古代曾經(jīng)壯麗地上演過,孟姜女便是那個以自身的眼淚理療集權社會全民焦慮的最佳女醫(yī)師:民眾通過孟姜女神話中的眼淚敘事,形成滾滾的集體淚濤,不但在故事的表層上哭倒長城,還以話語轉喻的方式詛咒湮滅著秦始皇的暴政。
在我國的美學傳統(tǒng)中,眼淚敘事一直有著一席之地。只要閱讀一下從古到今的中國典籍,我們便會知曉,眼淚敘事基本上是一種關于女性的敘事方式,湘妃竹上的斑點、絳珠仙草(林黛玉)的還淚,皆是女性眼淚敘事的經(jīng)典范本。眼淚是寫在女性面頰上的詩行,也是女性獨有的秘密武器。對大部分男性而言,女性的眼淚是一種令人手足無措的核武器,它兼具撒嬌、哀怨、悲苦、痛悼、歇斯底里等難以索解的功能。
讓我們設想這樣一幅場景:在喉管樂器式咽哽的伴奏下,晶瑩如露的淚珠緩緩的滑過一位美女的面龐……這等場景,必然會召喚起任何一位具有紳士風度的男士的憐香惜玉之情。當然,女性的眼淚敘事要看她所面對的客體。林黛玉可以對多情男兒賈寶玉如此哭泣,卻萬不可對肌肉男武松如此哀麗。沒準不懂眼淚詩學的武二郎面對林妹妹的眼淚,心煩意躁,一拳砸下,如此一來,林妹妹的眼淚敘事不但喪失全部美學語義,還會使得美人兒花容失色,口鼻血溢。
由此可見,無論神話還是小說、電影,所有的眼淚敘事都具女性的陰柔特征,這也是現(xiàn)代大眾文化領域內的煽情旗手多為女性作家的根本原因。古典時代,眼淚敘事尚有顛覆反叛的語義(孟姜女哭長城),當代大眾文化中的眼淚敘事,似乎只剩下喚起觀者的同情心的這一項虛弱功能。誘導觀看者感動并且珠淚滾滾,是當代大眾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瓊瑤阿姨的《梅花烙》、韓劇《藍色生死戀》皆是此中楷模。大眾看完這些影視劇,最多的反饋是:“我看哭了”、“感動死了”等等等等。由此可見,眼淚敘事的終極目的,便是利用文本主人公的悲慘境遇,來召喚藏匿在觀者淚腺下的淚水,從而涓滴成海,形成一種規(guī)模壯大的集體淚場。廣場舞的阿姨們以噪音與身體圈畫她們所占領的高地,眼淚敘事專家們則以觀者淚水的盎司來度量他們作品是否直抵大眾之心。
我沒有去影院觀看張藝謀的新片《歸來》,因我對張藝謀目前的才華不抱任何希望。只從這兩天眾多影評中的兩個關鍵詞“哭了”、“感動”中便可推斷出,《歸來》是一部沒有多少藝術含量的大眾影片。它的價值,很可能在于僅是一枚蓄意制造的催淚彈。昆德拉說:“由媚俗而激起的情感必須能讓最大多數(shù)人分享”。而影院,便是“能讓最大多數(shù)人分享”媚俗情感的最佳場所。在一個黑箱子一般的公共場所里,為一個悲慘的故事集體痛泣,既模糊了觀者的面目,又宣泄了觀者的情緒,簡直是一場情緒大鍋飯,只不過這大鍋飯是由電影文本與觀者互相交融的眼淚、鼻涕作為主要食材而被消費。
對中國人而言,流淚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將流淚升華至思維,則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因我們從小便被各種各樣的感人故事所飼養(yǎng),諸如馬克思在圖書館閱讀時留下的腳印,董存瑞炸碉堡等等。這種教育唯一的后果是:我們被規(guī)訓成一群感情極度發(fā)達、理性思考能力幾乎為零的羊民。羊民一大特征便是喜歡被頭羊所引導。前兩天看到一則新聞:新疆有一群羊,因為頭羊的判斷性失誤,群羊紛紛跟著跳崖壯烈犧牲。民眾如同羊群里的羔羊一般生存,對羊民而言,流淚是直接的情感反映,思考則要累及腦細胞,所以羊民們最喜歡消費的便是煽情文本。被羊民們深愛數(shù)十年的余秋雨、于丹的煽情散文,便是一大佐證。
多情很容易,感動亦很容易,尤其是一大群人在一起感動。我記憶里最深的一次群體感動,便是小時候由學校組織看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影院里一片嗚咽聲,我的那位男同桌更是哭得淚落滿面不能自抑,還是我遞給他一塊手絹才止住了他的咽哽。 昆德拉說“媚俗的根源就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而我認為,媚俗最最根本的緣由在于對崇高情感的絕對認同。因為愛上帝,所以上帝一定不拉屎。因為愛祖國,所以祖國一定很美好。因為愛A,所以A一定完美無缺……這個推理公式可以應用在任何崇高情感的狂熱之上。羊民在這個情感公式里實現(xiàn)了雙重謀殺:因為拒絕理性,所以謀殺了理性。因為愛客體,所以謀殺了客體的真實存在性。
真正的電影大師,不會利用簡單的煽情手法到達藝術核心。我們只要看看哈內克的影片《鋼琴教師》與《愛》,便會明白,大師級導演如何冷峻隱忍地呈現(xiàn)人性的復雜性。觀影若干年后,我都能記起《鋼琴教師》里的最后一個鏡頭:女主角一個人走在街頭,帶著她胸前不可遮掩的自我刺殺的創(chuàng)口,與整個人流逆向而行。這才是藝術精品的最佳歸宿:大腦,而非淚滴。女主角的創(chuàng)口深深地烙進觀者的腦細胞,給予觀者震撼性思考,而非被觀者的淚光所映照——淚水流完的那一刻,便如廢棄的紙巾一般被拋進垃圾桶。
文革是全體中國人的創(chuàng)傷性事件。如何將這個創(chuàng)傷性事件真實、藝術、反思地呈現(xiàn)出來,考驗的是導演的綜合實力與藝術水準。將一場創(chuàng)傷性民族災難,演變?yōu)楹唵蔚纳壳閯。瞧胀ㄋ囆g家亦該避過的誤區(qū)。感動是大眾文化的最為重要的指標,而非藝術精品的主要表征。我想,這也是法國戛納電影節(jié)將張藝謀的《歸來》放入非競賽展映的根本原因。法國人文底蘊豐厚,藝術生態(tài)正常,當然不會將低端的大眾消費品歸于精品一欄。中國的藝術生態(tài)一向紊亂,這里匯集了騙子(制片人不履行與編劇簽訂的合同)、乞丐(給點小錢就大唱贊歌的影評人)、抄襲犯等等江湖大忽悠,再加上資訊資本的推波助瀾,于是作為羊民的觀眾們,只能認為感動便是衡量一部影片好壞的最高標準,眼淚便是贈送給一部影片的最佳贊頌。
一百年前,蔡元培便開始在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上倡導美育:“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是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由于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為強,轉薄為厚,有待陶養(yǎng)。陶養(yǎng)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yǎng)的作用,叫做美育。”一百年后,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審美,仍舊活在“感情推動力的薄弱”之中。中國的歷史,便是原地打轉的罩著眼布的驢子的歷史。什么時候,民眾的審美,能從簡單眼淚敘事上升至理性思維,便是民族曙光的真正到來之時。
身體經(jīng)濟學的荒誕探戈
每個人皆有一具無法擺脫的身體,人們依靠它來日常生活。古希臘哲人認為,身體是靈魂的寓所,沒有身體,靈魂便喪失存在的家園。現(xiàn)代社會中的身體,則是商品化的身體,被性的符號標記、覆蓋、纏繞的身體。性是身體商品化的最佳源泉,性的彩旗早已將靈魂驅逐出界,占據(jù)身體的每一個細胞,并寫滿獨有的性符碼與性語言。
身體的投資:整容
希臘神話講,塞浦路斯國王皮格馬利翁酷愛藝術,他不愛現(xiàn)實中的女人,只愛自己雕塑出來的女體。這則神話,既是藝術家癡迷于藝術品的頌歌,亦道出了一個古老的男權話題:理想女性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存在,理想女性只是男性的藝術創(chuàng)造物。現(xiàn)代整容術是皮格馬利翁故事的反轉:整容界的勇士們,不懼冰冷的手術刀,爭先恐后的篡改自己的容顏,為的是取媚于想象中的那個男人——那個一直凝視著她們,愛撫著她們,為她們的完美而癡迷的皮格馬利翁。
前段時間有媒體報道,國內機場、邊境等出入境關口每天都出現(xiàn)好幾個“范冰冰”,其外貌與本人證件照片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屢次被檢查人員攔截盤查。范冰冰式的錐子臉,不但在民間被模仿,還被影視明星大量拷貝。以致一時間,影視屏幕上皆是錐子臉,觀眾眼光稍不敏銳,便會分辨不清誰是誰。更有網(wǎng)民熱傳韓國2013選美照片,參賽的所有女士幾乎是同一張臉。東亞大陸的女性,熱衷于集體篡改自身身體的運動,可與麇集在一起扭動的廣場舞來媲美。
世界美在多元,同一張面孔會使曾經(jīng)的美貶值為平庸。東方女性一直在求同:同樣的美德,同樣的衣著,甚至同樣的身體與容貌。小時候讀《大眾電影》,曾看到索菲亞羅蘭寧愿放棄電影女主角而不肯在自己的鼻子上大做文章的報道。索菲亞說:那是我獨有的鼻子,我獨特的符號。這告知我們,西方女人一直在求異:不同的德行,不同的穿衣風格,不同的面容。西方女人也整容,但像影視明星皆饑渴于同一張面孔的行為卻頗為少見。由此可見,求同的根本,在于人格是否獨立。沒有獨立人格的女性,多忙于求同,這樣她會有更多的安全感。韓國小姐千人一面,中國女星百人一頜,再次證明了這一點。現(xiàn)代意義的整容術,從身體的角度彰顯了東方女性的盲從人格,泛濫的美貌已非美貌,而是空無的洞穴,容貌的深淵。
普通女性篡改容貌,為的是嫁一個富有的男人。這類女性想象中的皮格馬利翁,“屌絲”,他應該身份高貴,物質富裕,頗有品味,最好還是某一領域的“國王”。明星整容,則是期待用改頭換面的方式來取悅大眾的流行審美,進而獲得巨大收益。顯然,明星們心目中的皮格馬利翁,不是具體的某一個人,而是龐大的觀眾群體,是十三億中國人。但兩者的背后,皆是身體經(jīng)濟學的邏輯在運轉:整容是一種投資。身體經(jīng)過整容進入市場,成為一種可篡改可買賣可交換可明碼標價的商品。身體,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身體,而是被深度異化的“性感”的物體。一具明晰可見的身體,性符碼累積得越多,性感指數(shù)越高,它的市場價值就越離奇。
身體的使用價值:裸露
2013年,車展上的車模以無底線的裸露來吸引消費者。導致消費者質疑:我們究竟是去買車,還是買肉?性吸引力,成了車展的一大風景。廣告商非常清楚,對男人而言,站在車旁的車模與汽車是同構的:車模就是汽車,汽車就是車模。汽車是現(xiàn)代男人的座駕,也是現(xiàn)代男人的馬。粵語片中,常常聽到這樣的臺詞:這是誰?我馬子。所謂“馬子”,無非是可騎乘的座駕,而非女朋友的代名詞。“馬子”是坐騎,是情婦,是性宣泄物。當裸露過度的車模站在珠光寶氣的車旁,無非再次從性消費的角度煽動男人們:看看,這就是你美麗的“馬子”,你可以任意騎乘它。
法國哲學家弗朗索瓦·于連在《本質或裸體》一書中談及“赤裸”與“裸體”的本質區(qū)別:赤裸是欠缺、貧乏以及剝奪,裸體藝術卻將赤裸轉為豐盈。當然,于連談的是古典時代的“赤裸”與“裸體”,而非現(xiàn)代性下的這兩個詞匯。古典時代,沒有整容術,赤裸的人體必然是不完美的。繪畫藝術家如何將這“赤裸”的身體轉變?yōu)榫哂兴囆g感的“裸體”,是頗費功力的。現(xiàn)代車模,大多是被整容術篡改過身體文本的模特,她們不懼怕赤裸,她們知道她們的身體早被整容師篡改成值得觀看的裸體藝術。她們是完美之物,增一分則長,減一分則短。如果說整容是她們對身體的投資,裸露則是她們的生存武器,也是她們身體唯一的使用價值。
4月,行為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傳記在中國出版,傳閱者眾。書中有大量行為藝術中拍攝的處于苦難中的裸露照片。顯然,在瑪麗娜這里,裸露也是一種身體經(jīng)濟。我不想對瑪麗娜的行為藝術進行任何評論,只想問一個問題:為什么女性更喜歡以自己裸露的身體作為藝術或商品的載體,而男性則多以他人的身體作為藝術或商品的載體?是什么決定女性如此沉迷于自身的肉體?不回答這些根本的問題,女性藝術或商品毫無意義。男權社會,女性是被“看”的物。當代女藝術家的責任,是擺脫歷史的被“看”的位置,而非一成不變地將男性的眼光,再次撒播在自身的身體之上。如若需要男權目光的環(huán)視,那也應是麥當娜式的顛覆+挑戰(zhàn)式的環(huán)視,而非將自身展覽為受困的、麻木的、苦難的裸體。藝術的覺醒首先是靈魂的覺醒,女性的救贖在于如何走出身體的苦難與榮耀,走出的那一刻,便是得救的那一刻。
身體的剩余價值:隱私
從2008年陳冠希的“艷照門”事件開始,每一年的年初,全民窺隱幾乎成為一種大眾狂歡節(jié)。2010年的“獸獸門”,2011年的“合肥小三門”,2012年的“官員艷照門”,2013年的常艷女士“性日記”,皆翻開中國年度身體隱私史的第一頁,并寫下極為壯觀的窺隱篇章。短短幾天,常艷女士的“性日記”,就被網(wǎng)民大量下載。人們互相傳閱,彼此驚嘆。原來,象牙塔內的圣徒們私下里奉行的卻是土豪西門慶的生活方式。
翻開2013年度身體隱私史第二頁的是女權主義者木子美。因柴靜《看見》一書的出版,木子美在2012年年末就在微博上發(fā)起反“女神”運動,“揭露”了“女神”柴靜的諸多私生活,將柴靜“譽”為二十一世紀的林徽因。2013年年初,木子美轟轟烈烈的反“女神”運動,最終演變?yōu)橐桓彪[私的多米諾骨牌。這副骨牌不但牽涉出“女神”柴靜身后諸多的男人,還牽涉出柴靜節(jié)目幕后的策劃者,更牽涉出幕后策劃者的私生活以及幕后策劃者的丈夫安替與木子美頗為糾結的北京一夜情。從別人的隱私起,于自身的隱私終,木子美女士的反“女神”運動,充滿了荒誕與悖論:作為性自由先驅,她鄙視“女神”性生活混亂,卻不鄙視她自身;作為女權主義者,她憎恨男公知的虛假,卻渴望男公知對她的認同;作為公眾人物,她不但自曝隱私,還認為曝光他人隱私亦屬理所當然。
2013年度身體隱私史第三頁的是歌手兼文藝女青年吳虹飛。她以戲謔的口吻,在微博上宣稱,要公布所有與她上床的男公知的名單,打款給她的可免曝光之災(大意如此)。網(wǎng)民一時嘩然,轉帖圍觀者眾,更有五毛、窺隱癖好者連連叫好,曰:讓人們看看公知們的嘴臉。不多久,吳女士再次發(fā)貼,說她僅僅是想開個玩笑。但這個所謂的“玩笑”,將早已污名化的“公知”一詞,再次涂抹為猥褻、色情、淫亂、毫無責任心的代名詞。
任何一個成年男女都該明白,身體是自己的身體,若雙方自愿,與某人發(fā)生性關系,是彼此共有的秘密。因為上床,而要求對方對自己擔負責任,是頗具中國特色的私生活。它建立在這樣的邏輯之上:我的身體不是單純的身體,我的身體是有待出售的物體。我的身體一旦與你發(fā)生性關系,從此便售賣給你。因此,身體對一些曝隱狂而言,成了一個極具威力的提款機與訛詐核彈:你不給我錢,我便會曝光你在何時何地與我發(fā)生過性關系。你必須為我曾經(jīng)售賣給你的身體買單!
在一個半極權半后現(xiàn)代社會,人們娛樂匱乏,無所事事,窺隱成癖。《知音》雜志的銷量說明,中國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窺隱群體。隱私,是身體文化的剩余價值。出賣隱私,是對身體文化的二度壓榨。對一些人而言,出賣隱私會獲得如下收益:1,提高知名度。2,獲取同情值。3,炫耀性交史:我和某某名人有過性關系或我和一大群名人有過性關系。裸露者無非給民眾展示分布在身體上的各種各樣的性符碼:紅唇、尖頜、豐臀、肥乳、長腿、私處等等。隱私兜售者卻將所有的性符碼吸進性磁場,進行赤裸裸的性媾和。從身體裸露到出賣隱私,中國人的身體經(jīng)濟學,發(fā)生了從點到面、從靜態(tài)到動態(tài)、從照片到黃色錄像帶、從公共領域到私人地帶的質的飛躍。
我們看到,無論整容還是裸露,無論出賣自身還是他人隱私,大多以女性的身體作為主體,男性的身體幾乎缺席。這告訴我們,身體經(jīng)濟學,究其根本是色情女體的經(jīng)濟學。物化的女體,無窮無盡的舞動在現(xiàn)代性的樂符下,身上懸掛著密密麻麻的男權觀念所賦予的性勛章,卻高喊著女權主義……在觀者看來,種種身體鬧劇,與任何主義無關,它僅僅是一場身體經(jīng)濟學的荒誕探戈在上演。
賤文化的精神分析
自2014年始,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出現(xiàn)一種古怪的異相,大量網(wǎng)絡哄客玩弄一種自認為幽默的話語游戲:他們自來熟的稱權傾朝野者為干爹、名動江湖者為岳父、金富天下者為老公。這種在公共領域與權力、名聲、金錢無底線的網(wǎng)絡調情,以自甘為人子、人婿、人妻的身份定位,話語口蹄疫一般席卷著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于是出現(xiàn)了“國民岳父”、“國民老公”之類的新名詞。魯迅小說文本中塑造的阿Q,即若打架,亦要以潛臺詞為“我是你爸爸”的方式獲得精神勝利。一百年后的一些中國網(wǎng)民,看上去宛若阿Q的轉基因兄弟:阿Q信奉的是精神勝利法,他們癡迷的則是精神自賤法。在權力、名聲、金錢這三個龐然大物面前,“我是你爸爸”式的中國傳統(tǒng)精神勝利法,驀然發(fā)生了基因突變,變成了精神自賤法。它以螞蟻上樹的抱大腿模式,改變?yōu)椤拔沂悄銉鹤印薄ⅰ拔沂悄闩觥薄ⅰ拔沂悄闫拮印钡鹊热鰦商捉醯男∽州叿Q呼,從而響徹互聯(lián)網(wǎng)。
顯然,這是繼2005年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定義哄客之后,哄客中出現(xiàn)的又一類別。在哄客中的罵客、贊客、笑客,逐漸淪陷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之后,賤客一躍成為網(wǎng)絡主流力量。在半威權半娛樂的后現(xiàn)代社會,罵客因其罵語道出真相的殺傷力,有可能獲得《紅樓夢》中焦大一樣被捆綁起來、嘴塞馬糞的悲催下場。于是一些聰明的罵客選擇了沉默,而另外一些不肯沉默的罵客則成為現(xiàn)代版焦大。著名罵客方舟子的遭遇,便是頗為生動的一課。在沒有英雄的歲月里,贊客或被資本所收買,轉化為專職給新上市的電影、電視、書籍等奉獻贊美謀取利益的按摩星人,或成為微信中手指輕輕一按的點贊黨。笑客在嘲笑了數(shù)十年的芙蓉姐姐、鳳姐之后,因匱乏新的娛樂偶像,逐漸審美疲勞,笑聲亦漸漸渺茫喑啞。隨著罵客、贊客、笑客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活躍度的銳減,賤客群體日漸崛起。他們以打不死的小強般的自輕自賤的生存姿態(tài)日益壯大,形成了一道鮮艷靚麗的賤文化彩虹,懸掛在2013—2014年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的各大門戶網(wǎng)站上。
互聯(lián)網(wǎng)的賤文化早已存在,它在中國生存發(fā)育了將近二十年,只是在2013—2014年,迎來了專屬于它的春天。互聯(lián)網(wǎng)賤文化不是大陸的本土特產(chǎn),而是舶來品,香港演員周星馳的影片便是賤文化的最初母體。1994年《大話西游》在大陸上映,1997年再度走紅,導致周星馳在大陸有著難以估量的擁躉。每次周星馳影片上映,無論好壞,皆可在票房凱旋。而周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大多為草根階層,他們生活空間逼仄,生存環(huán)境惡劣,放棄尊嚴、自輕自賤是其一種基本的求生策略。在我看來,周式影片之所以在大陸走紅,只因它是半威權半娛樂社會的最佳鏡像:在一個公權力無限膨脹、個人權利無絲毫保障的年代,人只能以自輕自賤的方式茍活,并用虛假的娛樂笑聲給自身解壓。一些生存境遇與周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頗為契合的大陸民眾,無非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鄙賤與渺小。但在1997—2012年之間,因公知群體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理性引導,雅文化與俗文化互相制衡,賤文化根本無法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的主流力量。其時,這種賤文化只局限在周星馳的粉絲之間。他們將周氏影片中的臺詞拷貝進互聯(lián)網(wǎng)對話,宛如識別同類的暗號或密碼,從而形成早期小規(guī)模的賤文化群體。
2006年左右,有文章將芙蓉姐姐稱為賤客的代表,這顯然是一種認知錯覺。賤客的本質在于自輕自賤,而非傳統(tǒng)話語中他者的叱罵,諸如“犯賤”、“賤人”、“賤貨”等等。這些詞往往是被動語態(tài),賤客卻屬主動語態(tài),它大多源于主體對自身的身份確認。自出道以來,芙蓉姐姐一直自認艷如貴妃,冷若黛玉。由此可見,芙蓉姐姐是傳統(tǒng)賤文化中的一員,她是阿Q的傳人,傳承的是阿Q是精神勝利法。賤客則是后現(xiàn)代賤文化的主體,他們是阿Q的反轉鏡像。賤客們的偶像是周星馳,賤客信仰的是精神自賤法。一旦遇到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賤客們?yōu)榱松姘踩坏珪暗偷綁m埃里”,有時甚至會“低到褲襠里”,尋求強大之物來依傍,其中的代表性詞匯,首推2013年囂張塵上的互聯(lián)網(wǎng)詞匯:屌絲。
由此可見,賤文化盛行的時代,往往是威權管制日漸嚴酷的時代。人有求生的本能,為了生存下去,將直立的軀體放低(尊嚴的象征),對強大之物首先雙膝下跪或者匍匐于地,無非是示弱之意:大爺,我比你矮一截,你放過我吧,讓我活下去吧。2013年,是互聯(lián)網(wǎng)賤文化大規(guī)模爆發(fā)的一年,大量中國網(wǎng)民自稱“屌絲”。彼時,著名導演馮小剛對這種網(wǎng)民將自身譬喻為陽具旁的一根毛的鄙賤稱呼,頗為惱火,發(fā)微博直接指斥,卻受到屌絲群體的激烈反擊。屌絲們認為一向頗有幽默感的馮導喪失了幽默感,應該被時代所拋棄。但“屌絲”一詞,在表達自嘲與不滿的話語之路上,已經(jīng)走的太遠。它已經(jīng)不是話語的反諷,而是反諷過度之后的自殘。自殘的回旋鏢擊穿了反諷者的假面,顯露出無知無賴者的投名狀:我就是強權(屌)旁的一根毛(絲),我就是要依傍強權,我還要堅定的簇擁在強權的周圍……
我們仔細回顧一下2013年的互聯(lián)網(wǎng),便會發(fā)覺,自稱屌絲與國民干爹,幾乎是同一時間出現(xiàn)的事物。然而,媒體對這個艷幟高揚的賤文化首席詞匯毫無警覺,甚至大張旗鼓地四處傳揚。由此可見,2013年,是文化潰敗最為嚴重的一年。恰恰是這一年,賤客們積累了若干年的賤文化意識形態(tài),從隱學走向顯學,一舉擊破雅文化、俗文化,從而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主流文化的生力軍。在我看來。2013年是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的分水嶺。如果說2013年之前,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還在媚俗與媚雅之間搖擺,2013年之后,則與此二者皆無大關聯(lián)。公知群體的日漸衰落,使得大量網(wǎng)民的認知進入混亂狀況。周星馳影片中只解構不建構的自嘲式娛樂,令他們在“媚賤”之路上一路狂奔,永不駐足。
2014年互聯(lián)網(wǎng)網(wǎng)民忙著與名流們攀親認爹的文化現(xiàn)狀,是2013年賤文化的延綿與繼續(xù)。大量在韓寒的微博下高聲昵呼“岳父”的男性網(wǎng)民、在王思聰?shù)奈⒉┫侣暵晪蓡尽袄瞎钡呐跃W(wǎng)民,無非是2013年那些自稱屌絲的同一人群。明目張膽的表達自身對權力、名聲、金錢的崇拜感、饑渴感、依附感,對一個自喻為“屌絲”的賤客來說,顯然不存在絲毫困難。孟子言所言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國古典文化中所要求的人之尊嚴,在此灰飛煙滅、蕩然無存。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巨大的人情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往往不是憑借本身的才華、能力、信用、品格等等公平地生活在這個國度,而是依靠各種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因此,找關系、搞關系、靠關系就成了中國人生存法則的三部曲。賤客們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找爹認父的舉措,除了娛樂之外,無非是將現(xiàn)實生活的里的種種丑惡,復制拷貝進互聯(lián)網(wǎng),獲得一種虛擬快感。在一個公知被嚴重污名化的時代,自尊、自強、自愛的公民遙不可見,只有自輕、自賤、自殘的賤客,才能夠蟑螂般生存下來。站立在賤文化大旗下的賤客們,既解構不了現(xiàn)有的任何政治意識形態(tài),又傷及自身的存在與尊嚴。這是空心人的反抗,在猥褻低下的笑聲后面,是寸草不生的沙漠。2015年,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一百周年。我們悲觀地看到,一百年過去了,公民社會離我們仍舊遙遠,賤民社會卻從阿Q到賤客,子子孫孫,無窮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