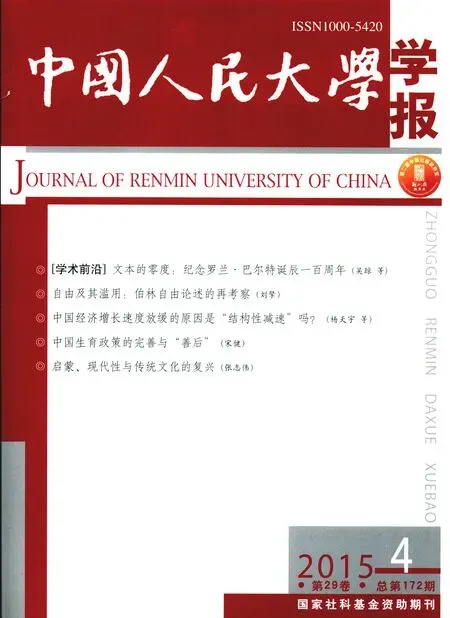我國集體爭議處理制度:特點、問題與機制創新
程延園 謝鵬鑫 王甫希
?
我國集體爭議處理制度:特點、問題與機制創新
程延園 謝鵬鑫 王甫希
近年來,我國集體爭議在數量和規模上都呈現上升態勢,成為影響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與多數國家針對不同類型爭議采取不同的機制和處理程序不同,我國勞動爭議處理制度設計主要針對權利爭議、個別爭議,而對以停工、怠工為主要形式的集體爭議,尤其是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集體協商爭議尚未納入現行法律調整的范圍,導致實踐中集體爭議處理路徑模糊、處理機構多變、處理方式不一。因此,健全暢通有序、公正及時的集體爭議處理制度,建立從應急治標到長效治本的集體爭議解決機制,是創新我國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的重要任務。
集體爭議;勞動關系;爭議處理機制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勞動關系的利益主體、利益訴求和外部環境已經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對進一步完善集體協商和集體爭議處理制度提出了迫切要求。面對新的形勢,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健全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加強爭議調解仲裁”、“創新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暢通職工訴求表達渠道”的改革任務;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共中央、國務院2015年3月印發的《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明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工作的指導思想、工作原則、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完善集體協商及其爭議處理機制,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勞動關系矛盾,是創新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的重要任務。目前,我國勞動爭議處理制度主要是針對個別勞動爭議,以停工、怠工為主要形式的集體爭議,而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集體爭議尚未被納入現行法律調整的范圍。集體爭議和群體性事件的沖突性較強,涉及面較廣,影響較大,是勞動爭議處理的難點和重點。健全暢通有序、公正及時的集體爭議處理制度,建立從應急治標到長效治本的集體爭議解決機制,是加強勞動關系矛盾源頭治理的重要舉措。
一、我國集體爭議處理制度的類型和特點
在雇傭關系中,工人與其雇主之間自然會存在對未來預期的差異。盡管他們有共同的利益,但也存在著分歧。他們之間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一是因現有的法規、協議、應享權利如何執行或解釋引發的“權利爭議”;二是因設定新的合同、權利和條件引發的“利益爭議”。權利爭議主要是個別爭議,但也會涉及多個勞動者的情形。利益爭議則主要是集體爭議,是工會在集體談判過程中為了勞動者集體利益與雇主或雇主組織之間產生的爭議。利益爭議源于集體談判的失敗,是勞資雙方為簽訂、更新、修改或擴充一項集體協議的談判最終陷入僵局而產生的爭議。將勞動爭議進行分類的法律意義在于,在多數國家,因為爭議的種類不同,因而設置了不同的解決爭議的機構,采用了不同的法律程序。權利爭議的處理多采用仲裁、訴訟方法解決,因為既定權利的確認相對容易,而利益爭議則由于其復雜性和專業性,通常由政府或專業人士進行仲裁、調解,而很少采用訴訟途徑。[1]
我國在集體爭議種類的劃分上與國外存在較大差異。2007年頒布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7條規定:“發生勞動爭議的勞動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共同請求的,可以推舉代表參加調解、仲裁或者訴訟活動。”根據這一規定,通常認為,個別爭議是勞動者一方不足法定集體爭議人數,爭議標的不同的勞動爭議;而集體爭議則是勞動者一方達到法定集體爭議人數,爭議標的相同,并通過選出的代表提起申訴的勞動爭議。這一理解與國際通行的勞動爭議的劃分并不相同。我國勞動法律沒有明確區分權利爭議和利益爭議,有關集體爭議的界定、類型和處理機制,散見于不同法律,尚無統一、明確的規定。在我國勞動爭議處理法律制度中,還沒有清晰地界定和區分個別爭議和集體爭議、權利爭議和利益爭議的類型和范圍,實踐中這四種類型的爭議往往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從集體爭議的現狀和現有的成文法規定來看,集體爭議主要分為三類,即所謂十人以上有共同請求的集體勞動爭議*所謂十人以上有共同請求的集體勞動爭議,是一種集體性的勞動合同爭議,爭議標的主要是圍繞著勞動合同的相關勞動條件和合同變更等展開,與集體合同并無聯系,爭議性質也不是利益爭議。國際慣例所稱的集體爭議,是工會或勞動者團體在集體談判過程中為了集體利益與雇主或雇主組織之間產生的爭議,并不是個體勞動者人數簡單的相加。本文所指集體爭議的含義與后者一致。、集體合同爭議以及自發性的集體行動爭議。現行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具有以下特點:
(一)集體爭議處理制度設計主要針對權利爭議、個別爭議
《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勞動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共同請求的,可以推舉代表參加調解、仲裁或者訴訟活動。這類“多個勞動者有共同請求的爭議”,實際上是多個勞動者共同主張權利的爭議,本質上是一種個別勞動爭議,因而仍然按照個別爭議的處理程序解決。目前《勞動統計年鑒》有關集體爭議的數據,也僅限于通過仲裁訴訟渠道解決的多個勞動者有共同訴求的集體勞動權利爭議。我國《勞動統計年鑒》所采用的集體爭議概念,與國際慣例所稱的集體爭議是集體談判中所產生的爭議并不相同。在國際慣例中,集體爭議并不是個體勞動者人數簡單的相加,而是以工會或勞動者團體作為主體的爭議。
集體合同爭議包括簽訂和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的爭議。《勞動法》第84條規定:“因簽訂集體合同發生爭議,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成的,當地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可以組織有關各方協調處理。”“因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爭議,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成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因簽訂集體合同發生的爭議,是圍繞勞動者未來利益的爭議,通過協商和協調處理,而不是通過司法或準司法途徑裁決,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處理簽訂集體合同爭議的原則相似。因履行集體合同發生的爭議,是對既定權利發生的爭議,沿用個別勞動爭議的仲裁訴訟程序處理。但在現實中,集體合同爭議案件卻為數很少,也沒有公開的集體合同爭議的統計數據。至于自發性的集體利益爭議,比如停工、怠工,實際上與簽訂集體合同的爭議處理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停工、怠工等集體行動往往是作為集體談判中工人方的威懾力量向資方施加壓力。現行爭議制度主要是針對權利爭議(尤其是個別爭議)所設計的,利益爭議(尤其是集體爭議)實際上并未納入現行法律調整范圍,缺乏相應的法律規范,由此產生的產業集體行動事實上處于自發和無序狀態。
(二)工人集體行動爭議從啟動到實施都發生在體制外
以停工、怠工為主要形式的集體行動爭議,已經逐漸成為現階段我國集體爭議的主要形式。目前所發生的停工、怠工事件,從啟動到實施都發生在體制外。在集體行動前,通常沒有工會的組織和授權,行動過程中沒有企業工會的支持,集體行動后也少有企業工會參與協調處理。大量的集體行動游離在正式的制度之外,都是工人繞過工會采取自發行動方式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由工會組織的集體行動案件屈指可數。在我國實行單一工會的制度背景下,這其實涉及一個非常復雜的話題,這就是工人的停工、怠工行為到底合法不合法。由于法律沒有明確規定集體爭議權,因此,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工人的集體行動爭議被當成“突發性事件”、“群體性事件”或者“維穩事件”來處理,有些地方甚至動用警力、法院等國家機器來處置。
(三)“先罷工后談判”,而不是“先談判后罷工”
不同于我國的“先停工后談判”的集體利益爭議模式,市場經濟國家的集體行動往往處于集體談判過程的末端,表現為集體談判過程出現僵局或破裂,在無法達成協議時,通過停工、閉廠等形式向對方施加壓力,以重新達成協議。從談判陷入僵局到當事各方決定或者開始采取集體行動之前,爭議預防和解決程序可以介入。[2]這些程序通常由法律法規予以規定,或包含在勞資雙方業已存在的協議中。現階段,我國勞動者在停工等自發性集體利益爭議之前,很少存在集體協商,反而希望借助停工等集體行動倒逼政府介入,引起公眾和社會輿論的關注,促使雙方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這種“先停工、后協商”的行動邏輯與市場經濟國家“先協商、協商不成再以停工威脅”的行動邏輯截然相反。
二、我國集體爭議處理制度面臨的問題
由于對“集體爭議”、“利益爭議”尚未形成一致結論,我國在處理路徑上也將其或者完全納入到個別勞動爭議的處理程序,或者過分依賴政府的協調作用,缺失以利益爭議為調整對象的集體爭議處理機制。我國集體爭議處理制度面臨的問題是:
(一)缺乏強制性的行政協調方式和終結機制
我國的集體爭議處理制度中,有類似于國外集體談判的處理機制,如《集體合同規定》第49條規定:“集體協商過程中發生爭議,雙方當事人不能協商解決的,當事人一方或雙方可以書面向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協調處理申請;未提出申請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認為必要時,也可以進行協調處理。”這些規定明確了集體協商爭議的處理方式是行政協調,其啟動方式可以由勞資雙方申請,也可以是勞動行政部門認為必要時組織協調處理。由于缺乏強制協調機制,導致實踐中出現了公安部門甚至司法的介入,通過司法方式強制調停。在這種情況下,集體協商爭議往往難以真正妥善解決,如沃爾瑪常德店勞動爭議案件。2014年2月28日,沃爾瑪常德店向常德市總工會報告,稱因經營不善提前解散。3月5號,公司單方貼出了《停業公告》和《員工安置協議通知》,宣布3月19日起停止營業,同時為員工提供了轉崗安置和領取N+1經濟補償終止勞動合同安置方案。該店員工在工會主席黃興國帶領下采取了維權行動,認為企業裁人程序違法,要求支付雙倍的賠償金。3月18日上午,派出所出動警力并出手傷了店內員工。3月21日下午,警方清場,并抓走幾名員工,其中一名維權員工被拘留五天。3月28日,沃爾瑪董事會決定撤銷常德公司,公司公布《關于終止勞動合同的公告》,發出《單方面終止勞動合同書》,以《勞動合同法》第44條為由,與65名員工終止勞動合同。4月25日,員工和分店工會分別提起勞動爭議仲裁申請。6月26日,仲裁委員會駁回了員工的全部仲裁請求。[3]該案引發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這一爭議到底是集體協商爭議還是履行集體合同爭議?如果是集體協商爭議,應由行政部門協調處理;如果是履行集體合同爭議,則應通過仲裁訴訟解決。在停工期間,常德市有關部門多次組織協調會,但各方未能達成一致,最終這一具有集體利益爭議特點的案件進入了仲裁程序。在我國目前的制度設計下,仲裁只支持勞動者的合法性訴求,而對于超越法定標準的合理性訴求的裁決必然是勞動者敗訴。
另外,對于簽訂集體合同爭議,法律只規定了協調處理,至于具體如何協調,如果協調不成,是否有集體行動權,最終以什么方式化解集體行動,法律并沒有作出明確規定,缺乏最后的終結機制。如果以傳統的仲裁方式解決沖突,存在的問題是如何確定員工訴求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勞動者的集體行動往往既涉及合法性問題,也涉及合理性的判斷,比如員工要求增加工資、獲得更高的經濟補償金時,會使行政部門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如果在調停糾紛時,因為它是群體性活動,就迫使資方接受比較高的經濟補償金或者超過法定標準的賠償,可能會產生一個負面的比照效應,甚至造成連鎖反應。一些法院的調研報告指出:勞動爭議中員工惡意訴訟高發,勞動者的訴訟請求不再是單純地索要勞動報酬,而是由此附帶擴展至年休假工資、社會保險、兩倍工資、賠償金、高溫津貼、精神賠償等訴求,索賠金額呈現高位態勢。[4]可見,目前勞動爭議中勞動者的訴求既有合法性訴求,也有大量合理性訴求,該報告顯然認為其實勞動者提出了大量不合理的請求,但恰恰在利益性糾紛中很多是對合理性的判斷。
(二)缺乏專門的集體利益爭議處理機構
目前,各地對集體利益爭議的處理方式基本以調解為手段,差異主要在于處理機構,實踐中出現了黨政領導的應急處理機構、勞動行政部門、勞動仲裁、三方機制、社會第三方等多種處理模式。[5](1)黨政牽頭的應急處理模式。我國各地都曾出現過由黨政牽頭處理集體爭議的模式,這種模式是在地方黨委的領導下,由地方政府牽頭,成立統一的“勞動社會保障突發事件應急處置領導指揮機構”,以當地政府副職作為總指揮,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信訪部門、政法委等參與,其他部門如公安、司法、信訪、建委、工會、村委會等配合。這種處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我國集體爭議處理的特色。其優點是能夠在多部門參與下迅速而全面地解決有關事件,但存在的問題是:它是以維穩的方式來解決勞動糾紛,啟動的條件較高,成本較高,不具有長效機制。(2)勞動監察為主的處理模式。主要出現在勞動爭議發生的早期,先由勞動監察部門到場,第一時間介入,收集、確認有關事實和證據。如果企業存在違法行為,則進行處罰,同時引導企業與勞動者開展集體協商,引導員工合法爭取自己的權益。在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時,由勞動監察部門從中調解,如調解失敗,則啟動勞動爭議處理的聯動機制,如由當地維穩辦、公安局、調解組織等共同參與。其優點是快捷、高效,能夠較早、較快地解決爭議。但存在的問題是:勞動監察部門的職責主要在于查處勞動違法行為,不應對當事人之間的勞動糾紛直接進行處理。(3)勞動仲裁機構為主的模式。在集體勞動爭議發生后,由勞動仲裁機構為主組織有關人員前往發生爭議的用人單位進行爭議處理。首先對勞動爭議進行調解,調解失敗后引導當事人進入勞動爭議仲裁程序。其優點是仲裁機構比較中立,專業水平較高。但存在的法律障礙是:仲裁應以當事人提起申請為前提,當事人沒有申請,則仲裁無法依法主動介入。(4)三方機制處理模式。在勞動爭議發生后,由工會、企業聯合會以及勞動行政主管部門組成專門機構來協調處理勞動爭議。三方機制中政府不以行政手段介入,而是以中立的第三方身份進行居中調解,通過勞資雙方的代表構成三方的格局,協調勞資沖突。其優點是符合勞動爭議解決的三方原則,但存在的問題是在實踐中比較難以發揮作用。(5)社會第三方介入的處理模式。在發生集體爭議時,由各方都比較信任的社會第三方介入來調解和協調各方利益的模式,社會第三方主要包括勞動法專家、律師、社會化調解機構等。其優點是符合國際發展的趨勢,但目前還比較少見。盡管不同的處理模式在實踐中都有成功的案例,但由于缺乏專門的處理機構,因而難以形成集體爭議處理的長效機制。這些模式的共同之處是政府在爭議解決中作用明顯,是爭議解決的主導者,爭議往往牽動多個政府部門,勞動者傾向于以停工等非制度化方式促進爭議的解決。
(三)集體協商的空間不明確
雖然工人通過集體行動啟動了集體談判程序,但在我國當前的法律制度下,集體協商談判的空間仍不明確。集體談判的空間涉及勞動的法定標準和約定標準。我國勞動標準由三個層次構成:第一個層次是勞動法律法規,我國法律法規中對勞動標準做了大量規定,如工時工資、社會保險、勞動條件、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企業經濟性裁員的處理程序等;第二個層次是企業內部的規章制度和集體合同;第三個層次是當事人的勞動合同和其他約定。企業的規章制度和集體合同是同時運行的兩個通道,通常企業愿意選擇有更大自主權的規章制度而不是集體合同來調整內部員工的權利義務,這就導致使用規章制度來代替集體合同,使得工資、福利待遇等利益訴求能夠談判的空間非常有限。
(四)缺乏集體行動法律責任的豁免機制
現行法律并沒有明確賦予勞動者集體行動權,更談不上對勞動者參加集體行動的法律責任實行豁免。勞動者組織或參加集體行動,可能因其行為的破壞性而承擔勞動法律責任、侵權法律責任、行政法律責任和刑事法律責任。例如,勞動者采取怠工、停工等行動必然會離開工作崗位,而一旦離開工作崗位,就可能因違反勞動紀律而被企業解除合同。同時,勞動者的集體爭議行動必然造成企業生產的中斷,可能構成破壞生產罪。如果勞動者采用堵路、堵橋等方式,妨礙公共場所秩序和交通秩序,可能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因此,在缺乏民事免責和刑事免責的情況下,勞動者很難通過集體行動爭取利益,反而可能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同時,法律也沒有規定勞動者集體行動期間企業方的權利義務,如是否可以解雇罷工員工,是否可以雇傭罷工的永久性替代者,是否需要支付員工罷工期間的工資、社會保險等。
三、創新我國集體爭議處理機制
集體爭議是較為特殊的一類爭議,不同國家大都設計了專門的制度促成勞資之間爭議的解決,避免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處理集體爭議的核心理念就是在法律上認可勞資自治在解決集體爭議中的作用,這意味著工會和雇主及其組織自愿達成的爭議處理協議應該優先于國家的強制性裁決。明確區分和界定爭議的類型,逐步完善我國集體爭議立法是實現和諧勞動關系的當務之急。
(一)區分權利爭議和利益爭議
對勞動爭議進行類型化區分并分別設計不同的解決程序,不僅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勞動爭議解決的一般經驗,更是由爭議當事人之間訴求多樣化的事實所決定的。簡單地以人數眾多(十人以上)來界定集體爭議,并沒有將當事人的訴求考慮進來。但從爭議處理的實踐來看,在人數眾多的勞動爭議中,勞動者的訴求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合法性訴求和合理性訴求。對于合法性訴求,因為已經有明確的規則,所以最終可以通過司法途徑依法解決。而對于法定標準之上的合理性訴求,它涉及調整當事人之間利益的規則的制定,也涉及利益在當事人之間的分配。針對該類爭議不存在裁決的規則,所以無法依法裁決。合理性訴求解決的根本在于當事人達成合意,解決程序的根本也在于通過協商、調解、施壓等措施,使得當事人達成合意。要絕對避免按照人數多少區分爭議類型的做法。目前出現的“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現象,與我們對勞動爭議類型的劃分不無關系。如果僅以人數多少區分爭議類型,而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必然導致群體性爭議越來越多。當前,在勞動仲裁中出現的一個現象是,越來越多的群體性糾紛不通過仲裁來解決,因為當事人知道通過仲裁得不到想要的利益,而更多地是通過停工、怠工等方式,迫使行政介入調停,通過行政方式迫使企業支付法定標準以上的工資,這就會形成惡性循環。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來看,勞動爭議中權利爭議的解決,主要涉及如何運用現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的問題;而利益爭議的解決,則主要涉及如何建立一個促使當事人達成新合意,訂立新的集體合同或者企業規章的問題。權利爭議可以采取仲裁、訴訟方式解決,而利益爭議在處理時不存在法律或者合同依據,因此,該爭議不宜由司法機關以裁判的方式處理,各國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處理過程的具體步驟、處理程序的啟動原則和處理機構的性質等。從國外的經驗看,各國均將利益爭議排除在司法機關的受案范圍之外,而由其他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予以解決。
(二)將無序的集體行動轉化為有序的集體協商
大多數國家都要求集體行動應該在集體談判出現破裂或者陷入僵局之后進行,沒有通過協商談判,沒有通過不記名投票同意的不允許罷工,罷工必須由工會發動組織,并且在罷工前要履行通知義務。[6]如日本規定沒有經過集體談判就采取爭議行為是不正當的。[7]韓國、英國都規定了集體行動前必須要大部分工會成員通過不記名投票同意之后才能進行。而集體協商的前提是談判主體的獨立性和代表性,在勞動者一方則涉及員工的結社權或職工代表的權利。我國工會法確認了工會享有集體協商權,但目前絕大多數的集體行動都脫離于工會之外。為了扭轉這一趨勢,必須回歸到先集體協商、再集體行動的正常路徑:一是要加強工會的代表性,使勞動者能夠通過工會表達利益訴求,將無序的訴求表達納入工會的通道;二是可以考慮賦予勞動者在特殊情形下的代表權。如在沒有建立工會的企業,如果勞動者要求與企業集體協商,則可以由企業所在地的地方總工會組織職工投票選舉集體協商代表,在發動集體行動時,也可以由集體協商代表組織。確立并落實工會或特殊情形下的代表權,是將無序的集體行動轉化為有序的集體協商的關鍵。
(三)明確權利義務豁免及壓力機制
由于缺乏集體爭議處理的終結機制,造成不得不動用公安、司法的力量平息案件,使得案件處理時面臨對企業和員工的責任豁免問題。許多國家對罷工期間勞資雙方的權利義務豁免進行了法律規制。如日本法律規定:“因同盟罷工或其他對抗性行為而造成損失時,凡正當者,雇主不得以此為理由而要求工會或者工會會員賠償。”在勞動者享受罷工民事和刑事免責的同時,雇主有權利不支付參加罷工勞動者的工資。我國可以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建立集體行動的壓力機制和勞資雙方權利義務豁免機制。如規定集體行動的目的必須是為了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勞動者的經濟地位等而產生的利益糾紛,不能因為權利爭議而發動集體行動;集體行動的發起者必須是企業工會或者通過選舉的職工代表;勞動者要發動集體行動,必須先經過集體協商,只有在集體協商被拒絕或陷入“僵局”的情況下,勞動者才能通過工會或者集體協商代表發動集體行動。在符合這些條件的情況下,工人的集體行動可以免除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但雇主也無需為停工的工人支付工資。
(四)建立專門的集體利益爭議處理機構
現行法律規定利益爭議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主管自無異議,問題的關鍵是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中哪一個機構主管,該機構采取何種組織形式運行。從目前各地的實踐來看,除黨政齊抓共管的應急模式外,平常狀態下與勞動部門有關的協調處理的機構設置有三種:以勞動監察部門為主的設置;以仲裁部門為主的設置;以三方機制為主的設置。這三種設置分別都有相應的地方實驗。從總體上看,目前利益爭議的解決主要依靠政府單方進行,這種政府直接面對勞資雙方的爭議解決,一旦處理不當,極易將勞資之間的經濟矛盾轉化為勞動者與政府之間的政治矛盾。從國外的實踐看,政府在利益爭議的解決中大多扮演的是組織者角色或者協調者角色,無論是調解還是仲裁,都依托于針對個案組建的第三方委員會。[8]因此,從發展趨勢上應該通過第三方機構來解決爭議。當然,這種第三方機構在初始階段可以政府為主體,隨著調解員與仲裁員隊伍的成熟,政府角色將回歸,逐步實現爭議解決機構的獨立化與中立化。
(五)建立專門的終結處理機制
我國對于集體利益爭議只規定了勞動行政部門可以依申請或依職權“協調處理”,筆者認為,有必要細化“協調處理”的手段和程序。協調處理的具體形式包括調解、裁決、推動集體協商等。協調處理有兩種啟動方式:一種是依申請啟動,另一種是依職權啟動,需要明確各自的適用條件。由于利益爭議在本質上歸屬于勞資自治的范疇,涉及憲法層面的企業經營自主權與勞動者的勞動權,在法治化的原則之下,應將依申請啟動作為原則,將依職權啟動作為補充。當集體利益爭議涉及郵電、通訊、公用事業等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或者對整個地區社會、經濟具有重大影響,以及已經演化為較大規模停工影響社會穩定時,勞動行政部門應當依職權協調,主動介入案件,強制對勞動爭議進行處理。
應當細化協調處理的過程、期限與協調書的效力。綜合國際經驗,集體利益處理有很多不同的程序和機制,但總體上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在一些國家,法律強制規定在當事人一方采取集體行動前,爭議必須先提交調停/調解,并在預先設定的時間內完成。在有的國家,法律規定宣布談判陷入僵局到采取集體行動期間為“冷靜期”,規定勞動行政機關有責任在“冷靜期”內幫助各方解決爭議。在冷靜期內,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不僅不得采取激化矛盾的行為,而且應履行如下義務:第一,勞動者復工;第二,企業如實披露企業財務、經營等狀況,為協商、調解提供信息保證;第三,雙方確定協商談判代表;第四,用人單位繼續支付勞動者工資;第五,誠意協商。如果調解無法解決爭議,則進入依職權裁決程序。總之,必須建立專門的終結機制,將行政協調解決停工、怠工事件的機制正規化,明確到什么時候、什么機構以什么方式做出最終的決定可以使爭議行動至少可以暫停。
[1] J.Benson.“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Japan:the Rise of Individualism”.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HumanResourceManagement,2012,23(3):511-527.
[2] Stokke,T.A.,and A.A.Seip.“Coll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The Nordic Countries Compared”.JournalofIndustrialRelations,2008,50(4):560-577.
[3] 譚暢:《沃爾瑪常德店勞資糾紛員工仲裁請求被駁回》,載《新華網》,2014-06-27。
[4] 章寧旦:《成本低賠償高致勞動爭議惡意訴訟多頻發》,載《法制日報》,2014-11-21。
[5] 楊欣、姜穎:《我國重大集體勞動爭議現狀及處理機制分析——以G省的調研數據為據》,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3(4)。
[6] S.Jefferys.“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Conflicts in Five European Countries”.EmployeeRelations,2011,33(6):670-687.
[7] 楊欣:《日本集體勞動爭議處理的法律與政策探析》,載《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4,28(1)。
[8] A.J.S.Colvin.“American Workplace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Individual Rights Era”.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HumanResourceManagement,2012,23(3):459-475.
(責任編輯 李 理)
The Coll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in China:Characteristics,Problems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CHENG Yan-yuan1,XIE Peng-xin1,Wang Fu-xi2
(1.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2.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Labor Relations,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New Jersey 08854,USA)
In recent years,collective dispute has displayed a rising trend in both number and scale,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 However,unlike most countries that use different processing mechanism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isputes,the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in China is primarily designed for the right dispute and individual dispute. The collective dispute,which is mainly in the form of lockout and sabotage,especially for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dispute such as demanding higher wages and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has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current legal adjustment. Thus,the resolution path of collective dispute is vague,the resolution institution is volatile and the resolution approach is variable in practice. Improving smooth and orderly,fair and timely coll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coll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rom lash-up superficial solution to long-term fundamental solution are important tasks for innovating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labor relation.
collective dispute;labor relations;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北京市重大集體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研究”(13FXB018)
程延園: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謝鵬鑫: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王甫希:美國羅格斯大學管理與勞動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新澤西 08854)